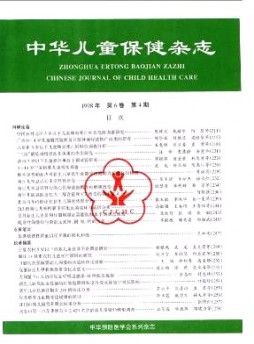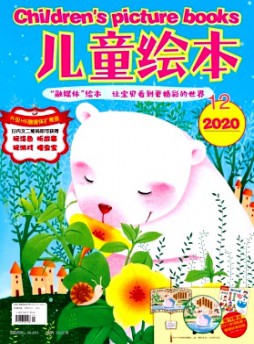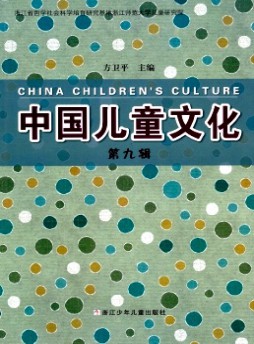兒童閱讀眼動研究統計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兒童閱讀眼動研究統計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閱讀眼動研究文獻分布時間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閱讀眼動研究的發展脈絡。統計結果(表1)發現,我國“三大教育”領域閱讀眼動研究文獻在時間分布方面有以下特點:第一,數量少。在CNKI的“三大教育”學科領域,以“眼動”+“閱讀”為主題詞檢索,僅獲得有效文獻28篇,與相同領域主題詞是“閱讀”的28219條文獻記錄相比較,其總量非常少。其中,檢索結果,1986年前有效文獻為0篇。1986年以來,年平均有效文獻僅有1.1篇。文獻篇目最多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6篇。2011年次之,有5篇。第二,出現晚。“三大教育”領域閱讀眼動研究第一篇文獻資料出現年份為1986年。而中文閱讀眼動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國外對閱讀的眼動研究則始于1879年[2]。第三,增長趨勢明顯。從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國內“三大教育”領域對閱讀眼動研究比較稀少,而2000至2009年十年間出現了19篇有效文獻,2010至2011年,兩年時間就出現了7篇有效文獻。相對而言,近十年的文獻數量呈上升的態勢。“文獻來源”既可以作為主要陣地,用來展示閱讀眼動研究的成果,便于同行對研究成果進行搜集,也可折射閱讀眼動研究是否進入“三大教育”前沿,成為一線教師熟悉的科研方法。統計結果表明:在28篇閱讀眼動研究有效文獻中,公開發表的論文有12篇,分別發表在11種公開期刊上,除《天津師范大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2篇外,其他期刊均只收錄有1篇,這10個刊物按刊出閱讀眼動研究文獻時間先后為《心理科學》、《教育教學論壇》、《教育科學研究》、《吉林教育科學(普教研究)》、《天津市教科院學報》、《浙江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心理發展與教育》、《淮南師范學院學報》、《心理學探新》及《心理科學通訊》。其中,進入學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類2000–2011年版中文核心期刊的論文僅有1篇,刊于2001年07月的《教育科學研究》①。除去以上文獻,另外16篇源于博士、碩士論文庫及會議的文獻,分別為博士論文3篇、碩士論文12篇以及會議文獻1篇②。其中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3篇,碩士論文2篇。其他為遼寧師范大學碩士論文4篇,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篇,河南大學碩士論文、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西南大學碩士論文和首都師范大學碩士論文各有1篇。從統計的數據看,華東師范大學和遼寧師范大學近年來對兒童閱讀眼動研究比較關注。
對兒童閱讀眼動研究論文的作者所在單位進行統計分析,其目的一方面是為同行間的交流與學習提供一個參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展現兒童閱讀眼動研究課題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情況,反映研究人員構成方面的特點或局限。統計結果發現:第一,文獻第一作者所在單位是小學或中學約占7.14%(見表3),文獻第一作者所在單位是高校的(見表4)約占92.86%。第二,國內兒童閱讀眼動研究的主要力量來自天津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及東北師范大學,他們共公開發表研究文獻19篇,占檢索到的28篇文獻總量的67.85%。對“文獻主旨”進行分析目的在于考察研究我國“三大教育”領域閱讀眼動研究的重點和范圍。在對文獻題目和關鍵詞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文獻摘要和全文,對文獻的主要內容和文獻主題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1)28篇文獻共有關鍵詞120個,其中有107個關鍵詞僅出現1次。出現2次以上的關鍵詞13個,“眼動”出現23次。(2)閱讀眼動研究的內容有三類:一為閱讀眼動基礎研究,其中包括兒童閱讀眼動的特征或發展研究、閱讀眼動障礙研究;二為閱讀應用的研究,包括閱讀眼動教學(策略或實效)研究、閱讀情境研究(獨立和陪讀)、閱讀媒介(圖文)研究;三為閱讀眼動研究文獻述評(評介)。其中應用研究的文獻占57.20%。(3)缺乏對兒童閱讀認知心理理論層面探索的研究,缺乏對閱讀教學界熱點話題諸如“語感”和“文感”的相關研究。
研究方法影響著研究的路線和結果。據統計,28篇有效文獻多數使用兩種以上的研究方法,其中,“文獻法”使用率最高,達92.90%。“眼動測量法”使用率次之,達60.70%。另外,有39.30%主題詞含有“眼動”的文獻,研究中并沒有進行眼動實驗,只是引用他人的眼動研究結果。根據表6,“眼動測量法”研究使用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使用者集中在華東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天津師范大學、河南大學等高校院所。第二,閱讀眼動實驗材料選擇上,繪本和漢語的語篇閱讀眼動研究相對豐富。漢語(文字)材料的語言單位涉及詞、句和篇,英語(文字)有字母、句和篇。檢索中沒有找到有關漢字和英語單詞認讀眼動研究報告。第三,有不同體裁作品的閱讀眼動研究報告。例如“科技文”閱讀眼動研究。第四,眼動實驗被試以小學生為主,其年齡、受教育情況與閱讀眼動關系的研究相對受重視。第五,部分實驗屬于基礎研究,即對閱讀眼動事實的發現和驗證;部分屬于應用研究,即服務于閱讀教學和訓練。沒有發現解釋漢語閱讀認知心理的理論研究。第六,不同高校在實驗材料和被試的選擇上存在一些差異,其中,華東師范大學較關注學前兒童繪本的閱讀研究;遼寧師范大學相對關注小學教材排版效果的研究。綜上統計和分析,在學前、初等、中等教育學科領域,我國閱讀眼動研究表現了以下特點:第一,兒童閱讀眼動研究起步比較遲,研究成果比較有限。第二,文獻主要源于學術性強、面向高校的期刊,及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至今,僅1篇相關文獻出現在“三大教育”學科領域的核心期刊。與“三大教育”一線教師存在隔閡。第三,研究力量主體是高校教師和博士、碩士研究生,極少研究者來自中小學教師隊伍。第四,本次檢索到的閱讀眼動研究觸及閱讀眼動基礎研究、閱讀應用的眼動研究和閱讀研究文獻述評(評介)。閱讀認知過程的探索缺乏,閱讀教學熱點話題未關注,理論上缺乏創新。第五,“眼動記錄法”在“三大教育”閱讀研究中的使用不普遍,能掌握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者集中在高校。另外,從被試和實驗材料選擇的角度看,“三大教育”閱讀眼動研究已經具有一定的廣度,但總體而言,不夠豐富,系統性欠缺。
綜上可見,我國閱讀眼動研究存在著以下值得反思和重視的三個問題。一是研究成果不被閱讀教學界所了解。本次研究檢索到的文獻僅有一篇源于進入學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類2000–2011年版中文核心期刊。反映出閱讀眼動研究未能對一線閱讀教學起到引領或參考的作用。二是系統性研究比較缺乏。盡管“天津師范大學是國內眼動研究的發源地,位于國內眼動研究最前沿,引領著國內眼動研究的發展方向”[3],但天津師范大學僅對閱讀者和閱讀材料題材類型閱讀眼動特征進行了系列的研究。類似地,華東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只對繪本閱讀、小學教材插圖進行一系列的探討。這種現象反映出該類研究的系統性不足。正如閆國利、白學軍曾指出:“盡管目前我國學者對漢語閱讀的眼動研究雖然已涵蓋了字詞、句子、語篇和不同文體等方面,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泛和深入,但由于我們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且研究者感興趣的領域不同,導致研究比較零碎,不夠系統。”[4]三是缺乏對語文教育熱點話題的關注。例如,到目前為止閱讀眼動研究還未將《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中反復提到的“語感”及近年來備受重視的“文感”具有什么特點,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如何影響閱讀認知過程等與心理學關系非常密切的問題納入研究對象。
眼動測量法能有效地反映閱讀認知加工過程“怎么樣”,從而為某些閱讀現象“為什么”和閱讀訓練可以或應該“如何”設計提供佐證,是研究閱讀認知過程最直接的方法之一。我們期待著有更多的眼動研究者關注學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學科領域的閱讀,從而為我國的語文教學帶來更多的啟迪和真正的革新。(本文作者:呂小君單位:溫州大學教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