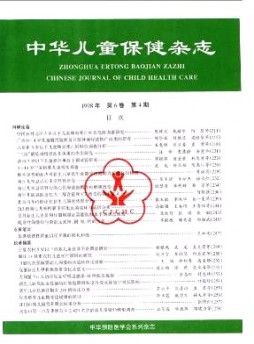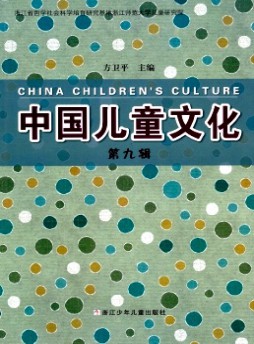兒童文學理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兒童文學理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種序列符號,表明那些事物是處在現代之后并接現代之踵而來。”①既然“后現代”是“接現代之踵而來”,如果持著歷史的目光,就應該深刻地理解或走進現代性,否則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各種后現代思想和理論。所以,我認為,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而言,還不能急切地“走出現代性”。我這樣說,是因為在我看來,一方面中國兒童文學在創作實踐上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現代性”任務,另一方面目前的兒童文學理論在“現代性”認識上還存在著諸多的語焉不詳乃至錯誤闡釋。反對“現代性”必須“在場”,必須首先身處“現代性”歷史的現場。人們曾經對激進的后現論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過這樣的批判:“博德里拉的這種‘超’把戲,只是一名唯心主義者匆匆路過一個他從未蒞臨、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沒有認真去對待的環境時,浮光掠影地瞥見的一點皮毛而已。”②中國兒童文學界屈指可數的幾位操持后現論話語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不在“現代性”歷史的現場這一問題。吳其南的《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和杜傳坤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是兩個用后現論批判現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結語”以“走出現代性”為題,后者的第一章“反思與重構: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中的一節的題目就是“發生論辯證:中國兒童文學起源的現代性批判”。對于兒童文學史研究的這兩部著作來說,通過對史料的梳理、辨析,通過對當時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國“環境”的歷史性把握,來闡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歷史,乃是應該具有的“在場”行為,但是,在我看來,這兩部算得上運用后現論的著作,在解構“現代性”時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觀點,都出現了不“在場”的狀況。下面,我們稍稍作一下具體的說明和分析。吳其南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經歷了三次啟蒙。……前兩次,從戊戌維新到五四,中國兒童文學尚處在草創階段,啟蒙作為一種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兒童文學中有多大的表現,……只有新時期、八十年代的新啟蒙,才在兒童文學內部產生影響,出現真正的啟蒙主義的兒童文學。”
③我的觀點恰恰與吳其南相反,縱觀中國兒童文學的百年歷史,“真正的啟蒙主義的兒童文學”恰恰發生于“草創階段”,它以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為代表。我在《“兒童的發現”: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現代文學研究在闡釋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時,往往細讀不夠,從而將‘人的文學’所指之‘人’作籠統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決的‘人的問題’里的‘人’理解為整體的人類。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學》的思想論述邏輯之后,卻發現了一個頗有意味、耐人尋思的現象———‘人的問題’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體的人類,而是指的‘兒童’和‘婦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內。在《人的文學》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對整體的‘人’的論述,還具體地把‘人’區分為‘兒童’與‘父母’、‘婦女’與‘男人’兩類對應的人。周作人就是在這對應的兩類人的關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學’的道德問題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兒童和婦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學》的這一核心的論述邏輯,也是思想邏輯,體現出周作人的現代思想的獨特性以及‘國民性’批判的獨特性。”“其實,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張的‘人’的文學,首先和主要是為兒童和婦女爭得做人的權利的文學,男人(‘神圣的’‘父與夫’)的權利,已經是‘神圣的’了,一時還用不著幫他們去爭。由此可見,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學’這個問題上,作為思想家,周作人表現出了其反封建的現代思想的十分獨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學》發表兩年后撰寫的《兒童的文學》一文,其實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表述的一個方面的啟蒙思想,在兒童文學領域里的再一次具體呈現。此后,周作人在《兒童的書》、《關于兒童的書》、《〈長之文學論文集〉跋》等文章對抹殺兒童、教訓兒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啟蒙,是吳其南所說的“專指意義上的啟蒙,即人文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沖突”。周作人的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對規劃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方向至為重要。“吳其南認為‘只有新時期、八十年代’才‘出現真正的啟蒙主義的兒童文學’,其閱讀歷史的目光顯然是被蒙蔽著的。造成這種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整體的歷史事實,比如對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理念,對周作人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思想的全部面貌,沒有進行凝視、諦視和審視,因而對于周作人作為思想家的資質不能作出辨識和體認。”②再來看看杜傳坤的“中國兒童文學起源的現代性批判”。杜傳坤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這部著作中對“兒童本位”論這一“發現兒童”的現代性思想進行了批判,認為“五四兒童本位的文學話語是救贖,也是枷鎖。”③杜傳坤這樣分析現代的“兒童的發現”———“兒童被認同才獲得其社會身份,而其社會身份一旦確立,馬上就被置于知識分子所構筑的龐大的社會權力網絡之中———只有滿足了國家與社會需要的‘兒童’才有可能獲得認同,因此,成為‘兒童’就意味著獲得監視。監視實踐要求為兒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兒童文學專家、教育專家、心理專家從事一門專業的監督任務,在這一監督中,一種社會無意識逐漸得以形成———兒童具有內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為了能夠在未來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兒童必須習得成人為其規定的知識、道德與審美能力……”④我認為,這也是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性的不“在場”的闡釋。要“在場”就得從籠統的宏觀敘事,走向具體的微觀分析。在中國,“兒童的發現”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兒童的發現”具體體現為他的“兒童本位”理論。當杜傳坤指出“成為‘兒童’就意味著獲得監視”時,最應該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現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中發現“監視”兒童的證據,發現周作人認為“兒童具有內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證據。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撐杜傳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語,反而隨處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觀點。我們信手拈來兩例。
“以前的人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甚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歲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為順應自然生活各期,———生長,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們對于誤認兒童為縮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對,就是那不承認兒童的獨立生活的意見,我們也不以為然。那全然蔑視的不必說了,在詩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愛國,專為將來設想,不顧現在兒童生活的需要的辦法,也不免浪費了兒童的時間,缺損了兒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這樣的言論不恰恰是對杜傳坤所說的“只有滿足了國家與社會需要的‘兒童’才有可能獲得認同”這一觀念的批判嗎?“昨天我看滿三歲的小侄兒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個煤球的鏟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樣子用右足踏鏟,竭力地挖掘,只有條頭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滿是汗了,大人們來叫他去,他還是不歇,后來心思一轉這才停止,卻又起手學搖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臺階上了。他這樣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戲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藝術的化境。這種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悅樂,幾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義,與時時處處拘囚于小主觀的風雅大相懸殊:我們走過了童年,趕不著藝術的人,不容易得到這個心境,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學玩,正是我們唯一的道了。”②在這樣的話語里,我們看到的完全是與“兒童具有內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這一觀念相反的兒童觀。如果按照杜傳坤的觀點,即將“監視”兒童視為“現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就是反現代性的;如果認為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是現代性的,那么杜傳坤所判定的現代的“監視”兒童,就不是現代性的。我本人是將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性的最為杰出的代表。我在《論“兒童本位”論的合理性和實踐效用》一文中指出:“絕對真理已經遭到懷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說歷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兒童本位’論就是歷史的真理。‘兒童本位’論在實踐中,依然擁有馬克思所說的‘現實性和力量’。不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對于以成人為本位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都是端正的、具有實踐效用的兒童文學理論。它雖然深受西方現代思想,尤其是兒童文學思想的影響,但卻是中國本土實踐產生的本土化兒童文學理論。它不僅從前解決了,而且目前還在解決著兒童文學在中國語境中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根本問題。作為一種理論,只有當‘兒童本位’論在實踐中已經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實踐中能夠繼續發揮效用,就不該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現實語境里,‘兒童本位’論依然是一種真理性理論,依然值得我們以此為工具去進行兒童文學以及兒童教育的實踐。”③錢淑英在《2013年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熱烈中的沉潛》④一文中,指出了當前圍繞著“兒童本位論”的學術分歧。從錢淑英的“與此相反,以吳其南為代表的研究者則站在后現代建構論的立場,對‘兒童本位論’進行了批評和反撥”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讀出關于“兒童本位論”的認識、評價上的分歧,似乎是“現代”與“后現代”的分歧這一信息。可是,我卻想說,在本質上,我與吳其南、杜傳坤的分歧不是“現代”與“后現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現代性”歷史的現場,準確、客觀地把握了“兒童本位”這一現代思想的真實內涵的分歧。我對于哈貝馬斯將“現代性”視為“一項未竟的事業”,抱有深切同感。現代性思想的相當大部分,依然適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這個正在建構“現代”的具體的歷史語境里,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性”還是“一項未竟的事業”的時代里,我們只能、只有先成為現代性的實踐者。不論在現在,還是在將來,這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們也得在自己的內部,使“現代”已經成為一種個人傳統之后,才可能對其進行超越,才有可能與“后現代”對話、融合。這體現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種規律。
二、必須“走進”的后現論
我雖然批評了杜傳坤、吳其南的后現代話語中的某些觀點,但是對兩位學者積極汲取后現論資源的姿態卻懷著尊重,并且認為,這樣的研究能夠把對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我從他們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兒童文學、兒童文化的發展方面,現代思想和理論依然富含著建設性的價值,可以在當下繼續發揮功能,而后現論也可以照出現代性視野的“盲點”,提供新的建構方法,開辟廣闊的理論空間。現代社會以及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精神結構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出現的某些后現代思想理論就是對這一變化的一種十分重要的反應。后現論關注、闡釋的問題,是人的自身的問題,對于知識分子,對于學術研究者,更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某些方面來看,后現論是揭示以現代性方式呈現的人的思維和認識的局限和盲點的理論。與這一理論“對話”,有助于我們看清既有理論(包括自身的理論)的局限性。因此,“走進”后現論是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研究不可繞過的一段進程。后現論中具有開拓性、創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對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后現論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論資源。不過,如同“現代性是一種雙重現象”(吉登斯語)一樣,后現代主義理論也存在著很多的悖論。我的基本立場,與寫作《后現論———批判性的質疑》一書的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的立場是一致的———“我們并不接受那種認為歷史已經發生了徹底的斷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論模式和思維方式去解釋的后現代假設。不過我們承認,廣大的社會和文化領域內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它需要我們去重建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同時這些變化每每也為‘后現代’一詞在理論、藝術、社會及政治領域的運用提供了正當性。
同樣,盡管我們同意后現代對現代性和現論的某些批判,但我們并不打算全盤拋棄過去的理論和方法,不打算全盤拋棄現代性。”①“自覺地進行學術反思,在我有著現實的迫切性。我的兒童文學本質理論研究和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上,面臨著有些學者的質疑和批評,它們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我愿意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其中最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質論(不是本質主義)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這一問題,而與這一問題相聯系的是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起源即兒童文學是不是“古已有之”這一問題。”②我所說的“有些學者的質疑和批評”指的就是來自吳其南、杜傳坤等學者的后現論話語式的批判(盡管沒有指名)。在中國兒童文學界操持“后現代”話語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質論”與“本質主義”的區別。吳其南在批判現代性時說:“關鍵就在于人們持一種本質論的世界觀,現實、歷史后面有一個本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東西在那兒,人們的任務只是去探索它、發現它。”③杜傳坤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一書中認為:“聯系當代兒童文學的現狀,走出本質論的樊籠亦屬必要。對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而言,五四兒童本位的文學話語是救贖,也是枷鎖……‘兒童性’與‘文學性’抑或‘兒童本位’似乎成了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創作的一個難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啟蒙的辯證法,啟蒙以理性顛覆神話,最后卻使自身成為一種超歷史的神話,五四文學的啟蒙由反對‘文以載道’最終走向‘載新道’。兒童本位的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同樣走入了這樣一個本質論的封閉話語空間。”①我的立場很明確,“本質論”與“本質主義”并不是一回事,我贊成批判、告別“本質主義”,但是不贊成放棄“本質論”,為此,我特別撰寫了《“反本質論”的學術后果———對中國兒童文學史重大問題的辨析》一文,以事實為據,指出了以吳其南為代表的“反本質論”研究的學術失范、學術失據的問題。我在文中說道:“犯這樣的錯誤,與他們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現論中激進的‘解構’理論,進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質論的學術態度直接相關。從吳其南等學者的研究的負面學術效果來看,他們的‘反本質論’已經陷入了誤區,目前還不是一個值得‘贊同的語匯’,‘反本質論’作為一項工具,使用起來效果不彰,與本質論研究相比,遠遠沒有做到‘看起來更具吸引力’。”在論文的結尾,我作了這樣的倡議:“我想鄭重倡議,不管是‘反本質論’研究,還是‘本質論’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學術語言里,把‘世界’與‘真理’、‘事實’與‘觀念’區分清楚,進而都不要放棄凝視、諦視、審視研究對象這三重學術目光。我深信,擁有這三重目光的學術研究,才會持續不斷地給兒童文學的學科發展帶來學術的增值。”②近年來,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現論,希望借鑒后現論,解決自己的現代性話語所難以解決的重大學術問題。盡管我依然堅持兒童文學的本質論研究立場,但是,面對研究者們對本質主義和本質論的批判,我還是反思到自己的相關研究的確存在著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沒能在人文學科范疇內,將世界與對世界的“描述”嚴格、清晰地區分開來。有意味的是,我的這一反思,同樣是得益于后現論,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羅蒂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借鑒后現論的過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質論研究的局限性,明確發展出了建構主義的本質論。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義的一項運用后現論的學術工作,是運用建構主義的本質論方法,解決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文學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學術問題。
一直以來,以王泉根、方衛平、吳其南、涂明求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而我則反對這種文學史觀,認為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它沒有“古代”,只有“現代”。但是,在論證各自的觀點時,雙方采用的都是將兒童文學看成是一個“實體”存在這種思維,而這種思維具有本質主義的色彩。所謂將兒童文學看成是一個“實體”存在,就是認為兒童文學可以像一塊石頭一樣,不證自明———如果一個文本是兒童文學,那么就應該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兒童文學。在我眼里是兒童文學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錯了。這樣的思維方式使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的討論,陷入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國兒童文學的起源問題不說清楚,兒童文學這一學科就沒有堅實的立足點。是借鑒自后現論的建構主義本質論幫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認識到兒童文學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而是現代人建構的一個文學觀念。依據建構主義的本質論觀點,作為“實體”的兒童文學在中國是否“古已有之”這一問題已經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夠成立的問題只是———作為觀念的兒童文學是在哪個時代被建構出來的。于是,我撰寫了《“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得出了“兒童文學”這個觀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現代”被建構出來的這一結論。在《論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念的發生———以美國影響為中心》①一文和《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②一書中,我進一步考證了周作人的“兒童文學”概念的建構過程。
三、未來指向:融合“現代”與“后現代”
第2篇
縱觀陳伯吹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不難發現他的一些基本觀點和呈現出的優勢、特色:
注重教育作用陳伯吹從不諱言兒童文學所擔負的教育任務和兒童文學作品應有的教育意義。在堅持兒童文學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態度一以貫之,極其鮮明,斬釘截鐵,毫不含糊。他緊緊扣住兒童文學的特點、特殊性,反復論述、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年齡特征和藝術特征,以及思想性、藝術性與兒童性的統一。他強調教育意義應該“融合在兒童情趣之中,深藏在藝術形象里頭”,“附麗在具有詩情畫意的想像本身”,“是個輕松愉快的過程”;明確否定和反對那種一味強調思想性和教育意義而忽略、輕視藝術性的錯誤觀點。陳伯吹1956年提出的、曾當作“童心論”批判的那個著名觀點:“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于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是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實際上是對兒童文學特殊性首先要照顧兒童年齡特征的一個形象的、生動的詮釋。無非是強調了解兒童、熟悉兒童是兒童文學作家第一位的工作。只有了解熟悉少年兒童的思想、感情、趣味,才能寫出為他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從而也才能發揮它的教育作用。
長于宏觀研究陳伯吹在理論研究中堅持從實際出發,力求從宏觀上把握兒童文學現狀,對成績、發展趨勢、存在的問題和發展前景作全面考察、透辟分析和判斷。發表于上世紀40年代的《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兒童讀物的檢討與展望》和50年代的《關于兒童文學的現狀和進展》《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談兒童文學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等論文,都是陳伯吹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占有大量材料,條分縷析,深思熟慮,作出的概括和總結。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陳伯老作為一個兒童文學領軍人物所具備的那種高瞻遠矚、洞察全局的氣魄和才能。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年屆耄耋的陳伯老依然堅持每年對“兒童文學園丁獎”(后改名為“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品作鳥瞰式的述評,并結合年度創作狀況作概括的回顧和展望。
第3篇
[論文關鍵詞]方衛平;兒童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藝術化
批評和藝術,是兩個很難讓人聯系到一起的詞。前者指對文學理論的探討和對作家作品及相關文學現象的闡釋評價,它容易引起讀者深奧,甚至艱澀的感覺,是偏于理性的詞語;而藝術則往往為欣賞者帶來形象感,相較于批評,是一個帶有感性色彩的詞。不過,在讀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后,我不由得將這兩個詞聯系到了一起,原來,批評也可以很藝術。
其實,方衛平教授對批評方式的藝術化的傾心可以從他對“藝術”一詞的鐘愛中見出,在《文集》中,藝術一詞所用的頻率非常高,諸如藝術狀態…、藝術內容、藝術思維、藝術對象、藝術敏感、藝術召喚、藝術蹤跡、藝術秩序、藝術偏態、藝術回歸等詞語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頻繁地使用了藝術一詞,不管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我看來,《文集》所達到的兒童文學批評的藝術化效果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兒童文學理論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匯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別是作者的專著《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以下簡稱《批評史》)和《法國兒童文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卷二是作者的單篇評論性文章和專著《兒童文學接受之維》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對中外兒童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進行的闡述,也是單篇評論性文章的結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論、評三部分,我以為,作者的批評的藝術化這一風格在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批評的藝術化,通常是指批評主體批評思維的藝術化和批評呈現形式(批評文本)的藝術化。于《文集》,作者無論是對文學理論批評史和文學發展史的探究,對文學現象的思考,還是對作家作品的體味和闡發,總是能以自己的學術激情和智慧對當時的文化語境進行獨到的研讀和體悟,進而以自己個性化的學術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既具理論深度又不失批評活力的學術文本。
文學史的書寫,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對史料進行藝術化處理顯得極為重要,這就需要書寫者對歷史的獨特悟性和對歷史尺度的準確把握,這種悟性和把握主要見諸書寫者以個人的史觀對史料進行篩選,并以此為基礎,完成文學史的文本敘事形態。
閱讀《文集》第一卷《批評史》和第四卷《導論》,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觀而辨證的史觀。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者,作者往往能對具體的文學批評作出客觀的評價,不管是肯定還是指出不足,他都不會以現今的標準去苛責前人。如在談到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對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影響時,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說,“雖然前蘇聯的理論模式在今天看來帶有許多消極因素和歷史局限,但它曾經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起到過促進的作用,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從中,作者對歷史把握的態度可窺一斑。此外,“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因果決定論所能決定得了的”、“理論的自信與理論的寬容同樣重要”、“當然,現代早期兒童文學研究中存在這些不足是難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評述在書中也時而出現。不僅是文學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滲透著作者的這一史觀,如“歷史的發展充滿了辯證法”,“歷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客觀現實,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學史觀決定著文學史書寫者親近歷史的方式,方衛平先生以自己對文學史持有的激情體悟著文學史。“作者一反傳統的史論述著中多見的述著者冷靜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場,以及隱蔽的‘幕后論理者’的角色慣例,頻頻在史論闡述的前臺‘亮相”,這既是作者對文學史懷有激情的一個注腳,也是作者親近文學史的具體方法——述評,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貫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評史》和《導論》都是對歷史的描述和對史實的理論闡發的結合,歷史描述顯得客觀而冷靜,理論闡發則透出作者的激情。兩者的結合可以為文本帶來活力和跳動感,而不見了文學史敘事中易于出現的沉悶之感。
文學史觀還決定著書寫者對史料進行收集、篩選和布局的方式。翔實、準確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嚴謹的治史態度。作者在《批評史》的“后記”中提到,“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更由于這一研究領域(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蕪,人們常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存在過的那些理論批評現實”,可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記中提到,為確定中國現代第一部《兒童文學概論》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還是“周侯于”,而翻閱了大量資料。正是作者治學的嚴謹,為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放心。雖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諸般努力,但,作者并沒有為此將自己收集的史料進行全盤羅列,而是以自己敏銳的眼光對史料進行解讀、篩選,這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導論》的工作即是“宏觀描述與微觀分析、總體把握和個案研究”的相互體認。《導論》主要是依照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敘述的,這即是“宏觀描述”、“總體把握”的一側。具體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對法國兒童文學進行了整體的把握,闡述了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主要特點,不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體論述部分述評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沿革。就“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時間為緯對法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分期,且他對每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紀被概括為“法國的自覺”,18世紀被概括為“盧梭的世紀”,19世紀被概括為“黃金時代”,作者將法國兒童文學發展中的這一時期特征闡明為世紀特征,對此,他在前言中做了這樣的闡述:“法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節奏與世紀更迭的自然時序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它確實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趣的歷史發展事實——對于本書來說,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敘述線索和邏輯框架”;不僅僅限于“世紀特征”,“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還體現在作者對各個歷史時期內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準確把握上,如19世紀的塞居爾夫人、喬治·桑、儒勒·凡爾納、埃克托·馬洛等,20世紀的圣·埃克蘇佩利、保爾·阿扎爾、馬塞爾·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當時一個時代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水平的作家。史料與理論支撐的緊密融合,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層次特色。人類學、文化學、闡釋學等中外文藝理論在作者的論評說時有涌現,但作者并不是為了搬用理論而用理論,他通常在這些理論的挪移中,與文學史料貼切結合,從而為自己的理論建構而用。
如果說史觀和親近文學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觀上的努力方向的話,那么對史料進行收藏、篩選和布局的方式則是讀者所見到的文本呈現方式,也是讀者借以對作者藝術化書寫文學史的風格進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觀上的內蘊同時也決定著他親近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論評中呈現出來的又是怎樣的藝術化方式呢?
理論探求是對思想深度展開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書名《思想的邊界》極富哲理性,但相信讀者讀后的強烈感覺是思想無邊界。“邊界”和“無邊界”看似矛盾,其實正是作者藝術化批評處理的結果。邊界是文本觸角延伸的限域,無邊界則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達到的空曠遨游狀態。在有邊界的文本格局里,飛翔著的思想卻沒有邊界。從有邊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論格局為“理論探索”、“批評縱橫”和《兒童文學接受之維》三個版塊。雖然,三個版塊各有側重點,“理論探索”是對兒童文學中一個個具體理論點的探究,“批評縱橫”主要是對兒童文學現象的考察,包括對一些理論批評者和批評著作的考察,《兒童文學接受之維》是對兒童文學中的“接受”課題進行的闡發,但是,不同的豐富性正突現著作者的批評個性,他總是選取能觸動他的理論感動的批評點,這些批評點或者是在當時的兒童文學理論中尚且處于模糊狀態、有待探討的,或者是雖引起了諸多的理論關注,但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的話題,如“理論探索”中的“兒童文學理論邏輯起點”話題、“兒童本體觀”話題、“經典”話題、“兒童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話題、“兒童文學的深度”話題和“少年讀者”話題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儲備,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對這些話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將童年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等觀點都給予了當時的探討以推動作用。“批評縱橫”中“對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體系建設”的考察、對“浙江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近代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重要評論者的評論等。在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銳的理論眼光,通過對當時復雜的現實的透視,發出了自己的批評聲音;《兒童文學接受之維》選取的是兒童文學理論中受到普遍關注、并被加以諸多探討的“接受”問題展開的思考。作者在對中外文藝理論,如接受美學、解釋學、新批評等理論的信手拈來中,在對相鄰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物遺傳等學科知識的熟稔運用中,在將“接受”與現實兒童文學發展的聯系拷問中,將“接受”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在作者營造的思想空間中,讀者體驗到的是思想上沒有邊界的展開和漫游。
作為一位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方衛平教授既親身投入這一領域中出現的許多重大探索,也為其中某些固守的觀念而焦慮;既有對探索精神的積極肯定,也有對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問題進行的思考;既主動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樂意甚或期盼聽到其他批評者不同的理論聲音。
對文本的闡釋集中體現了闡釋者以自身的理論功底對文本進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與闡釋》,一則日文本,一則日闡釋,此卷正是對文本進行的闡釋,包括了“創作尋蹤”、“年度論評”、“作品解讀”、“域外偶拾”和“夢尋小記”五個模塊。文本在這里獲得了廣義上的涵義,它既是指記載了兒童文學創作者創作足跡的具體作品,如《灰顏色白影子》、《彭懿童話文集》、《六年級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兒童文學整體創作軌跡的文學記事,如1990年少年小說的發展,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兒童文學的發展等。進入作者理論批評視野的往往是當時兒童文學領域中的焦點文本,這顯示了他的學術敏感性,如“創作尋蹤”中對《中國少年文學書系》、對少年文學、對新的藝術常態及對《兒童文學選刊》等進行的思考,“作品解讀”中對常新港、梅子涵、張之路、班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關注,“域外偶拾”中對拉丁美洲的兒童小說、日本的“晴天下豬”等現象給予的注視。
作者在文本闡釋的批評角度的切人、批評尺度的拿捏、批評過程的推演、結論的得出及希望的表達等方面都具個性。盡管具體的評論文章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評擅長由描述切人論題,如《一份刊物和一個文學時代——論》、《青春的萌動——當代青少年文藝現象的描述和思考》、《論當代兒童文學形象塑造的演變過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論和材料的支撐下,他將批評層層推演、不斷深入,這種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將結論拋給讀者,而是使讀者在閱讀的帶動下完成自我意識中的推理過程,進而順應地獲得和接受結論的過程,藝術化的批評實現的是藝術化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