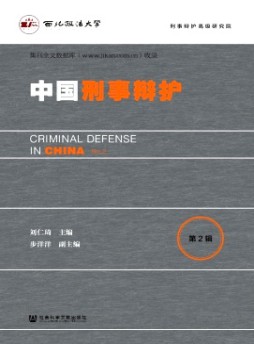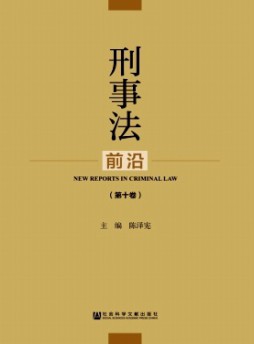刑事訴訟中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刑事訴訟中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各地區(qū)法律法律法規(guī)之間存在差異,則證明標(biāo)準(zhǔn)也有所不同。通常情況下,證明標(biāo)準(zhǔn)既有客觀層面證明,也有主觀層面證明。英美法律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為“排除合理懷疑”、大陸法則為“內(nèi)心確定無(wú)疑”,而我國(guó)則使用“事實(shí)清楚,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作為證明標(biāo)準(zhǔn)。本文分析了我國(guó)刑事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理論與實(shí)踐基礎(chǔ),同時(shí)簡(jiǎn)要敘述了我國(guó)法律當(dāng)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并從“排除合理懷疑”的使用要有條件、重構(gòu)“階梯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等方面探究我國(guó)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完善措施。
關(guān)鍵詞
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排除合理懷疑”
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刑事訴訟當(dāng)中證據(jù)制度以及刑事證明的重點(diǎn)內(nèi)容,當(dāng)事人、律師、法院以及檢察機(jī)關(guān)在行使自身權(quán)利過(guò)程中都需依賴(lài)證明標(biāo)準(zhǔn)。刑事訴訟當(dāng)中,只有某一項(xiàng)證據(jù)無(wú)法完成證明任務(wù),需收集一定量的證據(jù),且證據(jù)之間相互吻合,沒(méi)有沖突,方能達(dá)到證明的目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僅是當(dāng)事人賴(lài)以訴訟的武器,同時(shí)也是法官審理案件的依據(jù)。故而,證明標(biāo)準(zhǔn)對(duì)一起刑事訴訟案件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一、我國(guó)刑事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理論與實(shí)踐基礎(chǔ)
(一)價(jià)值論基礎(chǔ)證明標(biāo)準(zhǔn)對(duì)案件待證事實(shí)的確認(rèn)有直接影響,甚至左右著案件的確認(rèn)因訴訟結(jié)果,同時(shí)對(duì)申請(qǐng)?jiān)V訟的社會(huì)沖突所取得的價(jià)值評(píng)論造成較大的影響。因此,形式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需要體現(xiàn)刑事訴訟法自身的價(jià)值,即程序的公正性。形式訴訟的價(jià)值體現(xiàn)在法律程序的公開(kāi)公正,且要求法官在判決案件時(shí)將自身放置于中立地位,不得將個(gè)人主觀情感夾雜于審判過(guò)程中。訴訟過(guò)程中,法官應(yīng)明確表示自身與訴訟方以及被訴訟方處于同樣地位,客觀地評(píng)斷案件以及證據(jù)。法官在審理案件過(guò)程中可以為雙方提供證明的流程以及待證事實(shí),但不可為某一方進(jìn)行證明活動(dòng)。證明活動(dòng)完全由訴訟方自身完成,法官只負(fù)責(zé)從法律以及程序方面對(duì)其所提供的證明以及主張的實(shí)施加以確認(rèn)。法官在審理案件過(guò)程中,不僅負(fù)責(zé)對(duì)案件進(jìn)行裁決,還需對(duì)訴訟方以及被訴訟方進(jìn)行保護(hù),使雙方擁有平等的訴訟地位。法官需注意,對(duì)雙方的保護(hù)并非指示靜態(tài)的保護(hù),應(yīng)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對(duì)兩者進(jìn)行幫助。通常情況下,訴訟方較弱,法官便應(yīng)給予其保護(hù)與幫助,使得訴訟方有與被訴訟方同等的訴訟參與能力以及相等的訴訟機(jī)會(huì)。然而法官也不應(yīng)完全偏向于訴訟方,由于訴訟方當(dāng)中的公安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能夠運(yùn)用大量的司法手段以獲取證據(jù),因此被訴訟方在證明程序中擁有反駁訴訟方或是之一證據(jù)的權(quán)利。除此以外,若訴訟方所提供的證據(jù)以及證明活動(dòng)都不能達(dá)到形式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使被訴訟方?jīng)]有提出有力證據(jù)證明自身無(wú)罪,被訴訟人可被認(rèn)定為無(wú)罪。
(二)哲學(xué)基礎(chǔ)第一,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論原理。辯證為物主義理論認(rèn)為,主、客觀之間的沖突,實(shí)際是雙方認(rèn)識(shí)過(guò)程之間存在差異。主觀必須服從于客觀,而認(rèn)識(shí)則應(yīng)當(dāng)來(lái)源于實(shí)踐,這象征著認(rèn)識(shí)與實(shí)踐之間的差異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逐漸統(tǒng)一。人類(lèi)對(duì)事物的認(rèn)知過(guò)程便是將主、客觀進(jìn)行統(tǒng)一的過(guò)程,這在形式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當(dāng)中同樣適用。刑事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僅包括主觀因素,同時(shí)也包括客觀因素。刑事訴訟的證明過(guò)程,其實(shí)是由訴訟方對(duì)證據(jù)進(jìn)行收集、審閱以及運(yùn)用的過(guò)程。證明過(guò)程中,訴訟方會(huì)按照法定形式以及流程進(jìn)行證據(jù)的收集,之后再進(jìn)行搜集及整理,進(jìn)而得出可證明自身結(jié)論的證據(jù)。訴訟方的活動(dòng),不僅含有訴訟方的主觀認(rèn)識(shí),同時(shí)也是客觀事實(shí)的陳列,也滿(mǎn)足法律程序的需求。應(yīng)將辯證唯物主義認(rèn)識(shí)論作為基礎(chǔ)聯(lián)合案件實(shí)際情況設(shè)立證明標(biāo)準(zhǔn)。第二,真理具有相對(duì)性以及絕對(duì)性。真理絕對(duì)性共有兩方面內(nèi)容:一方面,真理應(yīng)與客觀世界當(dāng)中所發(fā)生的事件以及客觀內(nèi)容向匹配,若與客觀存在出入,則不可認(rèn)定為真理。另一方面,真理絕對(duì)性還指能夠探索并認(rèn)識(shí)客觀世界。人類(lèi)每次探索新的知識(shí)獲取新的認(rèn)知,便與客觀世界更為接近。
(三)實(shí)踐依據(jù)立法工作人員在制定法律以及建立證明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結(jié)合國(guó)家的實(shí)際情況決定,立法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便是證明標(biāo)準(zhǔn)。證明標(biāo)準(zhǔn)雖然是依照立法人員的已知建立而成,但最后還是會(huì)受到民眾生活條件的限制。不同時(shí)代的證明白標(biāo)準(zhǔn)需適用于該時(shí)代的實(shí)際情況,如物質(zhì)條件、社會(huì)治安狀況以及人民素質(zhì)等。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客觀規(guī)律,并不會(huì)因?yàn)槟骋蝗说囊庾R(shí)而發(fā)生改變。而這也證明了,證明標(biāo)準(zhǔn)需不斷發(fā)展與提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人違背這一規(guī)律希望一步到位的人,不僅不能建立合適于社會(huì)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還會(huì)使得社會(huì)矛盾激化,自身也會(huì)受到波及。如在君王通知的時(shí)代,某個(gè)領(lǐng)袖希望建立客觀真實(sh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必然會(huì)受到大部分人的反對(duì),統(tǒng)治也會(huì)受到波及。由此可見(jiàn),刑事訴訟當(dāng)中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可過(guò)低,也并非越高越好,而是應(yīng)當(dāng)盡量與當(dāng)前實(shí)際向結(jié)合,經(jīng)過(guò)不斷實(shí)踐得出合理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就我國(guó)目前而言,治安方面還有待提高,證明標(biāo)準(zhǔn)與刑法功能的應(yīng)用有密切關(guān)系,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建立往往由統(tǒng)治階級(jí)對(duì)秩序的需要而進(jìn)行調(diào)整。若社會(huì)動(dòng)蕩不安,國(guó)家降低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也不可厚非。如今,我國(guó)刑事訴訟案件數(shù)量極高不下,社會(huì)治安問(wèn)題頻出,對(duì)我國(guó)治安管理與民眾正常生活造成較大的負(fù)面影響。不僅如此,我國(guó)部分案件上有待斟酌。因?yàn)椴糠职讣?dāng)中,即使部分被訴訟方極有可能確實(shí)存在犯罪事實(shí),但由于證據(jù)沒(méi)有達(dá)到證明要求,而被無(wú)罪釋放。可見(jiàn)我國(guó)訴訟程序還有待完善,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也應(yīng)適當(dāng)降低。
二、我國(guó)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完善措施
(一)“排除合理懷疑”的使用要有條件“合理的懷疑”出現(xiàn)于我國(guó)《法官職業(yè)道德基本準(zhǔn)則》當(dāng)中,可見(jiàn)該詞組已然成為司法工作當(dāng)中可以使用的詞組。排除合理懷疑共分為兩個(gè)部分:其一,實(shí)體意義之上所建立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待證事實(shí)清楚明了。其二,程序意義之上建立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證據(jù)能夠有效證明待證事實(shí)。待證事實(shí)清楚明了的意義不是指要求訴訟方完全還原案發(fā)當(dāng)時(shí)的情景,而是指在不違背法律約束的情況下,法官通過(guò)庭上所呈證據(jù)以及訴訟方及非訴訟方的論述所獲得的案發(fā)情況,也可稱(chēng)之為“法律事實(shí)”。該類(lèi)實(shí)施有以下特點(diǎn):第一,該類(lèi)事實(shí)需要訴訟方或被訴訟方在證明過(guò)程中通過(guò)提供證據(jù),利用合法手段進(jìn)行事實(shí)證明。第二,法官對(duì)被訴訟方的量刑均有相對(duì)應(yīng)的決定性證據(jù)并加以證明。第三,案件當(dāng)中不存在邏輯沖突,且沒(méi)有合理的懷疑,證明被訴訟方犯罪事實(shí)的證據(jù)確鑿,同時(shí)所有證據(jù)都已經(jīng)過(guò)驗(yàn)證,與案件事實(shí)相悖的證據(jù)全部否定。第四,按照訴訟方以及被訴訟方所提供的證據(jù)。法官已然自?xún)?nèi)心確定被訴訟方確實(shí)存在犯罪行為,并依然沒(méi)有合理懷疑。“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強(qiáng)調(diào)了訴訟方提供證據(jù)時(shí)應(yīng)注意數(shù)據(jù)的數(shù)量以及質(zhì)量,確保質(zhì)量與數(shù)量符合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要求。訴訟方若希望自身“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需注意以下幾點(diǎn):其一,訴訟方所提供的證據(jù)應(yīng)具備一定的客觀性,能夠確實(shí)幫助訴訟方證明待證事實(shí),且該證據(jù)的取得應(yīng)借助合法程序獲取,不得利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jù)。不僅如此,證據(jù)還需按照以法定形式呈交執(zhí)法院。其二,證據(jù)必須在法庭之上展出。同時(shí),法官要求訴訟方與被訴訟方針對(duì)所展出的證物進(jìn)行陳述以及反駁,通過(guò)證明結(jié)果評(píng)定該證物的可信度,以此確定證物的真實(shí)性。其三,訴訟方所提供的證物應(yīng)與自身、其他證據(jù)要以及案件待證事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不得存在沖突甚至是對(duì)立,造成邏輯方面的矛盾與沖突。其四,若訴訟方與被訴訟方針對(duì)某一無(wú)證存在不同意見(jiàn),提出該證物的一方需提出其他相關(guān)證據(jù)以證明該證據(jù)的可信度。其五,訴訟方在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過(guò)程中物法繼續(xù)舉證,或放棄舉證責(zé)任,而證據(jù)尚未到達(dá)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情況下,法院應(yīng)判定證據(jù)不足、被指控的犯罪罪名不成立的無(wú)罪判定。上述便是對(duì)證明標(biāo)準(zhǔn)當(dāng)中如何排除合理懷疑的分析,不僅符合形式訴訟的需求,同時(shí)也具有較強(qiáng)的可操作性。
(二)重構(gòu)“階梯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刑事訴訟案件各階段證明標(biāo)準(zhǔn)各不相同,具體如下:其一,立案證明標(biāo)準(zhǔn)。立案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刑事訴訟當(dāng)中最低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該標(biāo)準(zhǔn)具有較強(qiáng)的主觀性,若公安機(jī)關(guān)認(rèn)為被訴訟方存在犯罪事實(shí),便可立案調(diào)查。對(duì)犯罪事實(shí)證明也較為簡(jiǎn)單,只需證明犯罪事實(shí)確實(shí)發(fā)生,便能夠進(jìn)行立案,被訴訟人、案發(fā)時(shí)間、作案手段等都無(wú)需證明。但立案也具有一定條件。第一,僅有犯罪事實(shí),公安機(jī)關(guān)不能進(jìn)行立案,還需確定公安機(jī)關(guān)有權(quán)對(duì)該犯罪事實(shí)進(jìn)行刑事責(zé)任追究,若有權(quán),便可立案調(diào)查。其二,提起公訴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我國(guó)對(duì)案件申請(qǐng)公訴的標(biāo)準(zhǔn)設(shè)定為“事實(shí)清楚,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然而針對(duì)法院以及檢查機(jī)關(guān),該標(biāo)準(zhǔn)的意義并不相同。第一,未進(jìn)行訴訟方與被訴訟方互相展示證據(jù),并相互辯論環(huán)節(jié)時(shí),證據(jù)的“事實(shí)清楚,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僅為檢查機(jī)關(guān)認(rèn)為,有可能與最后的判處結(jié)果有所不同。第二,檢察機(jī)關(guān)與法院之間也存在一定區(qū)別。檢察機(jī)關(guān)更加具有主觀性,而法院更多需要客觀性。法院在正式審理案件前需先對(duì)案件進(jìn)行初步審查,根據(jù)審查結(jié)果決定是否開(kāi)庭審理。其三,有罪判決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訴訟方若希望證明被訴訟方有罪,則需達(dá)到“事實(shí)清楚,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的標(biāo)準(zhǔn),由此可見(jiàn),刑事訴訟當(dāng)中證明標(biāo)準(zhǔn)遠(yuǎn)遠(yuǎn)比公訴申請(qǐng)所定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更為嚴(yán)苛,兩者之間存在遞進(jìn)關(guān)系。此時(sh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應(yīng)低于公訴申請(qǐng)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但也不可過(guò)高,使得訴訟注意的尊嚴(yán)以及訴訟效率對(duì)案件事實(shí)真相產(chǎn)生影響。
(三)證明標(biāo)準(zhǔn)與對(duì)象要相適應(yīng)如今,我國(guó)訴訟理論當(dāng)中還沒(méi)有對(duì)訴訟方以及被訴訟方之間的差別進(jìn)行研究,法律僅規(guī)定了訴訟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所需達(dá)成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但對(duì)被訴訟方提供證據(jù)所達(dá)成的標(biāo)準(zhǔn)卻并未設(shè)立相應(yīng)的規(guī)定。司法時(shí)間當(dāng)中也僅僅注重明確訴訟方所承擔(dān)的證明責(zé)任,卻并未設(shè)立被訴訟方需承擔(dān)的證明責(zé)任。我國(guó)法律應(yīng)為被訴訟方設(shè)立明確的證明責(zé)任。具體如下:其一,被告人可以當(dāng)庭對(duì)訴訟方所提出的證據(jù)進(jìn)行反駁,或是從邏輯思維以及經(jīng)驗(yàn)方面對(duì)訴訟方的證據(jù)以及推論進(jìn)行辯駁之外,若被訴訟方存在部分較為特殊的情況,被告方可當(dāng)庭說(shuō)明。如被訴訟方可提出自身患有精神類(lèi)疾病、有法律授權(quán)、自當(dāng)防衛(wèi)等理由,并提供相關(guān)的證據(jù)或說(shuō)明。上述辯護(hù)即為肯定性辯護(hù),被訴訟方只需將上述證據(jù)證明至“證據(jù)占優(yōu)勢(shì)”的地步即可。其二,被訴訟方除了完成上述肯定性辯護(hù)之外,還可向法院提供與訴訟方相悖的證據(jù),對(duì)訴訟方進(jìn)行反駁。法院對(duì)被訴訟方具有“疑罪從無(wú)”的保護(hù),在法院當(dāng)中可以提出對(duì)自身有力的證據(jù)為自身進(jìn)行辯護(hù)。故而,被申訴方若想法院提供證據(jù)以證明自身所主張的待證事實(shí),或是反駁訴訟方的證據(jù),無(wú)需與訴訟方的證明要求相同,只需令法官相信,或是所提供的證據(jù)可能性較大即可。
三、結(jié)語(yǔ)
刑事訴訟案件在我國(guó)所遇案件當(dāng)中占有一定比重,而刑事證明標(biāo)準(zhǔn)也直接贏了案件的判斷結(jié)果。故而,立法者應(yīng)更為關(guān)注如何設(shè)定刑事訴訟當(dāng)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以便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能夠發(fā)揮自身最大的效用。
參考文獻(xiàn):
[1]宋世杰、彭海青.刑事訴訟的雙重證明標(biāo)準(zhǔn).法學(xué)研究.2001(1).
[2]李瀟瀟.論民事訴訟中自由證明的構(gòu)建.河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6).
[3]謝登科.論刑事簡(jiǎn)易程序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當(dāng)代法學(xué).2015(3).
[4]李訓(xùn)虎.證明力規(guī)則檢討.法學(xué)研究.2010(2).
[5]張家驥.對(duì)證明責(zé)任和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理論反思.法制與社會(huì)發(fā)展.2012(2).
[6]王寧.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探究.法制與社會(huì).2012(7).
作者:葉怡航 單位:廣西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