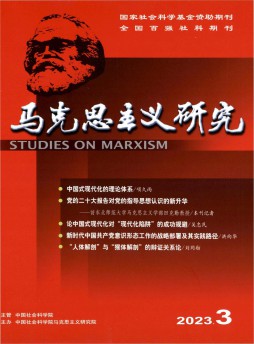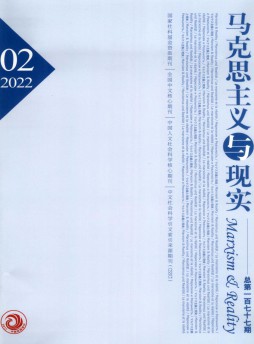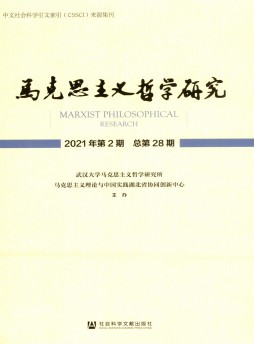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科技教育思想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馬克思主義科技教育思想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延安時期,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為推進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始終把科技教育作為救亡圖存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制定了一系列發展科技教育的方針政策,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廣泛的科技教育活動,多方培養邊區所急需的科技人才和科技干部,有力地促進了邊區科技事業的發展。黨在依托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大力推進邊區科技教育,不僅積累了豐富的領導和管理科技教育工作的經驗,而且從邊區實際出發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科技教育思想并付諸實踐,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技教育思想。是時,陜甘寧邊區不僅是黨中央所在地,而且也是黨領導下的整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指導中心。因之,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探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科技教育思想,無疑對當下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為邊區社會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服務
延安時期,在邊區這片“自然科學的光輝從未照臨過的荒地上”,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發展科技教育事業有著明確的目的導向,那就是解決邊區生產實踐和軍事斗爭的實際需要,即特別強調科技教育為邊區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的需要服務。這時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發展科技教育事業的指導思想。對此,《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明確指出,邊區的文化教育政策“只有在堅持長期抗戰與增進人民幸福的總目標之下來提倡自然科學,才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2],強調科技教育與邊區的經濟建設、抗戰事業的緊密結合。這無疑為黨領導下的邊區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早在1939年5月,黨中央為促進邊區工業生產的進步和國防經濟建設的成功,在延安創辦了自然科學研究院,研究院的任務是“開展科學研究,協助政府發展經濟建設,推進生產事業,解決邊區物質困難,改善人民生活”。但因邊區隨后遭到了進一步的封鎖,導致外來科技人員日益減少,以致邊區科技力量滿足不了科技發展的需要。因此,邊區科學事業的發展僅僅依靠國統區的人才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自己培養科技人才。同年底,黨中央同意邊區科技人員的兩個具體建議:第一,把自然科學研究院改為自然科學院,創辦自己的高等學校,以培養邊區所急需的科學技術人才;第二,成立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廣泛把科學技術人員組織和團結起來,以更好地擔負起服務邊區建設的任務。正是黨中央的高瞻遠矚,邊區的科技和科技教育事業蓬勃發展起來。
1940年2月,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確今后總的奮斗目標是:“為著爭取抗戰建國的最后勝利,為著完成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我們要加強自然科學運動,掌握與提高自然科學成為抗戰中的戰斗力量,為抗戰到底,為加強團結,為力求進步而服務,來配合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抗戰。我們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戰線,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打擊敵人的奴化政策。”這不僅適應了抗戰形勢和邊區建設的需要,而且大大推動了邊區科技及其教育事業的發展。黨創辦延安自然科學院,是適應抗戰形勢和建設邊區的迫切需要。1940年2月,自然科學院在其招生啟事中指出的辦學宗旨即是:“以培養抗戰建國的技術干部和專門技術人才為目的”,明確了是時黨領導下科技教育的任務。9月,自然科學院第一任院長李富春在開學典禮上作報告時又指出,我們黨必須培養和造就革命的技術人員,困難再大也要堅持辦好這件事,如果不抓好這樣的基礎工作,就談不上自力更生,就搞不好根據地建設和新中國的建設。11月,叔仁在訪問延安自然科學院時,問及自然科學院的教育目的,自然科學院的教務處長慎重地告訴他,在今天抗戰建國中,教育目的是為著充實國防建設的力量,準備建國中的新芽。可以說,邊區的科技教育及其學術活動從一開始就直接在黨中央的領導和關懷下,并與抗戰建國的歷史重任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當時特殊的戰爭環境下,黨中央和邊區政府舉辦科技教育并非易事。以如何發展科學技術研究和科技教育為例,邊區教育界就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為結束無原則和無休止的爭論,促進邊區科學技術研究和科技教育能循著正確的道路前進,第二任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撰文指出,在全面戰爭時期,“我們不是為科學而研究科學,不是企圖在科學上爭取地位造成特殊的科學家”,“無論在高深的學理方面或粗淺的技術方面,總的任務是為著生產,為著解決抗戰的物質問題”,并著重指出,“尤其在中國,科學和技術落后,人力物力財力亦有限,且當著戰爭的破壞和封鎖的嚴重時期,更不容許有無組織無計劃的行動,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應該如此”,認為“科學的中心任務當然是經濟建設,在目前對于軍事建設更為必要”,進一步闡明了黨關于科技教育為邊區社會經濟建設及革命戰爭服務的教育方針。
及至1944年5月24日,合并后的延安大學正式開學,又明確其辦學方針之一是,以適應抗戰與邊區建設的需要,培養與提高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實際干部為目的,并確定邊區建設方面的政策方針和經驗總結為延安大學教學的主要內容,技術課以適應邊區建設當前需要為度。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延安大學及其自然科學院努力創辦一種新型的大學,有力促進了邊區科技教育界的團結協作,配合了邊區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的需要。是時,陜甘寧邊區除創辦了高等科技教育外,還舉辦了不少中等技術學校和短期訓練班,為邊區民用工業和軍事工業大力培養中級技術員和技術工人。與之同時,為邊區社會經濟建設及革命戰爭服務的科技教育方針也貫穿于實際教學過程中。以延安自然科學院建立的機械實習工廠為例,徐特立為其規定的方針就是為教學服務,為邊區建設服務。在這個方針指導下,機械實習工廠既為教學服務,又為邊區建設服務,積極滿足邊區工業、衛生等部門機械維修配件和工具、模具等方面的需要,為紡織酒精、玻璃、造紙、肥皂和制堿等廠提供了機器設備,并大量生產銅紐扣和醫療手術用具等。這些不僅有力地推動了邊區抗戰事業的發展,而且促進了邊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二、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和學以致用的原則
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辦教育必須遵循這一原則,科技教育尤其如此。對于延安時期年輕的共產黨人來說,他們不僅不陌生這一原則,而且已將其付諸實踐,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可以說,黨和邊區政府領導科技教育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和學以致用。1940年8月,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學院開學典禮上代表黨中央提出自然科學院的任務是:培育既通曉革命理論又懂得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員,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人才。徐特立在接替李富春擔任第二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期間,高瞻遠矚、力排眾議,十分重視理論聯系實際,認為“科學教育與科學研究機關以方法和干部供給經濟建設機關,而經濟機關應該以物質供給研究和教育機關。三位一體才是科學正常發育的園地”。1942年,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學院舉行的教育方針討論會上又直接指出:“我們要與軍工局、建設廳等機關所屬的各工廠農場密切聯系起來,把理論與實際做到真正的聯系”。經過熱烈討論,師生們一致的意見是:“自然科學院學生的培養目標既要急當時的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之急,又要著眼于全國解放后的全面經濟建設培養人才,要貫徹理論聯系實際,教育要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的方針。”
是時,延安自然科學院為能使師生做到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創辦了一些實習工廠,作為院內的實習基地;另一方面,又與邊區的農場和工廠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作為院外的實習基地,實現了教育、科研與生產的緊密結合。在當時的環境下,邊區科技教育戰線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邊區工農業生產急需什么樣的建設人才,自然科學院和邊區的技術訓練班就培訓并輸送什么樣的建設人才。以陜甘寧邊區農業學校為例,其即以培訓縣、區兩級農業技術干部和管理干部為宗旨。農校教學的課程以農業科學知識為主,學習農作物的栽培管理、改良土壤、合理施肥和選育良種等知識,學員是邊上課、邊勞動實習,農事試驗場既是學生的課外勞動實驗場,又是學校的生產自給基地,在試驗場培育出的良種都交由地方推廣。在辦學過程中,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建設廳廳長劉景范以及各專員、縣長等多次親臨學校指導。1940年9月,在原延安八路軍衛生學校基礎上擴建而成的中國醫科大學,為明確醫大的性質、任務、教育方針和工作細則,隨之修訂了新的學校規章。在教學內容上規定,要求采取“少而精”的原則,做到理論密切結合實際,減掉不必要的繁瑣理論的講解,編寫出較為適用的、便于學員學習的簡明教材,教學效果有了較大的提高。此外,在具體的教學中,還根據學員文化程度的差異,采取不同的教學方式。是時,中國醫科大學除了為革命培養衛生干部外,還經常協助邊區政府和駐軍解決一些衛生工作問題。1942年12月,聶榮臻在晉察冀軍區擴大衛生會議上做總結講話時進一步指出,我們衛生部門的專家“需要了解全部隊全邊區的衛生情況,加以研究整理后,提供大家執行,發揮治療的威力,並把這些東西教給學生,使學生不會停止在書本教條上,而能與邊區的實際聯系起來”,即必須使醫學運用于邊區的具體環境。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其通過的《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中①,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在于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著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要求“凡擔任學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應認真地研究教課內容與教學方法,使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原則,在教課內容與教學方法中貫徹起來”,并要求在具體的教學中,“陜甘寧邊區及其鄰近地區的實際材料,應經過各種調查研究的方式充分地利用之”。
以晉察冀邊區白求恩衛生學校為例,該校根據黨的教育方針和政策,結合白求恩的建議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共同擬制了衛校的教育方針和教學計劃。在大掃蕩開始后,衛校結合邊區戰爭的特殊環境,因地制宜開展教學活動,創造了游擊教學、武裝上課和行軍教學等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使學員做到在干中學、學中干,通過邊學邊干培養和鍛煉學員的戰場醫療救護能力。據當事人后來回憶[14]220,該校除辦有軍醫、調劑和護士班外,還舉辦了老干部班和高級軍醫班,先后培養了1000多名衛生技術干部,極盛時期在校學員達720多名。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校長周揚對過去的延安教育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指出今后延安大學的教育在學制與課程等各方面都應切合實際,做到為邊區人民服務。對此,也指出延大在今后的辦學中,要為實際服務,不要鬧教條主義。接著,在講話中,又進一步號召大家積極參加生產實踐,把學與用聯系起來,做到在生產中學。最后,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今后延大的辦學方針是,要做什么就學什么,適合于我們需要的東西就學,對我們不適用的東西就不學。
是時,這些黨和政府領導人的講話便成為延安大學辦學的指導方針。在堅持教學與生產實際相結合原則的辦學方針下,延安大學的教師多數是邊區實際工作部門的負責人,自然科學院69%的教員是由邊區各有關單位工程技術人員兼任的。據當事人胡吉全后來回憶,他所在的物理系被正式改為機械工程系,學員們參加了煉鐵實習,一邊生產,一邊上課,完成了金屬材料課程的學習。與之同時,學校還結合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地雷戰,給他們教授國防化學中有關炸藥和爆炸方面的課程,邊學邊實習。學員們在這樣的教學安排下,既學到了系統的專業知識,又鍛煉了實際的工作能力。與之同時,黨和邊區政府除鼓勵科技人員深入實際向勞動群眾學習外,還積極組織教育界與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之間的相互交流。如自然科學院的教員兼職擔負邊區政府建設廳的工作,軍工部門的工程師為自然科學院的學員講課,醫科大學的教員兼醫院的醫生等等。這樣做,一方面為邊區科技人員提供了多方面的實踐機會,促進了他們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另一方面也彌補了邊區科學研究條件的不足,推動了邊區科學技術水平的全面提高。
三、把科學理論與思想政治理論的學習緊密結合起來
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邊區的科技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延安時期,為了在戰爭環境下辦好科技教育,培養出邊區軍事斗爭和經濟建設所需要的科技人才,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十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將馬克思主義與專業技術的教授、學習有機結合在一起,促使他們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分析問題、指導實踐。李富春早在延安自然科學院開學典禮的講話中,就明確提出其人才培養的目標是“革命通人,業務專家”,即培養的人才“不能只限于在學校里學習科學知識,還必須學習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在學會掌握自然科學這一武器的同時,學會按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正確運用”。徐特立到任后,十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和學校的校風、學風建設,主要從以下三個渠道開展了自然科學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是開設政治理論課;二是組織學員參加必要的社會活動和生產勞動;三是充分發揮黨組織的作用,結合業務教學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據胡吉全回憶,延安自然科學院政治課的質量很高。李富春任院長時,不僅親自講過黨的建設,而且還給師生們做過政治報告。徐特立任院長時,堅持每周講一次政治課。、林伯渠、等同志都曾來校做過報告。與之同時,自然科學院的黨組織生活會和學習小組的生活會也都抓得很緊,通過這種經常性的意識鍛煉,以促進師生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
1940年,中國醫科大學在其修訂的新校章中,規定學校的性質和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身體健康,能為民族解放與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革命醫務技術干部。據薛公綽回憶,延安時期的中國醫科大學非常重視政治教育,每周除由政治教員給學員講一、兩次政治課,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外,還結合當時的形勢學習《中國問題》、《論持久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共產黨人發刊詞》、《論聯合政府》等文件,政治課教學也盡量聯系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和學員思想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展開,并在課后積極引導學員聯系實際進行討論。是時,、、等也都曾先后來校做報告,講述國內外形勢。1943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在《關于衛生部門中的教學問題的通令》中又重申,“為配合著整個軍隊建設,其教學方針:應以軍隊衛生勤務學、近代之醫療技術為主要課程,輔以政治策略教育、自然辯證法,從事軍醫建設,適應戰爭需要。”
1941年,中共中央在其的《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中,對不需要補習文化的專門性質學校的要求是:專門課課時占80%,政治課課時占20%。根據這一決定,作為黨中央創辦的培養黨與非黨各種高級與中級專門科學及技術人才的學校,延安自然科學院政治學習每周一天,專業課學習每周五天。其中,政治學習包括政治課、形勢教育和黨的組織生活。為此,李富春、徐特立在任院長期間,都給學生們講過政治課、黨課,并給師生們作過政治報告。此外,、林伯渠和等中央領導同志也都曾來校作過政治報告。這不僅為邊區培養了技術干部,而且也為新中國準備了技術干部隊伍。1942年,中央政治局在其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中,又明確規定“在職干部教育,應以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四種為范圍”,強調“對一切在職干部,都須給以政治教育。其范圍,包括時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項”,指出“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專門業務局部情況與局部政策之外,還能通曉一般情況與一般政策,擴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狹隘不懂大局的弊病”,認為“好談一般政治而忽視專業業務的傾向是不對的,但局限于專門業務而忽視一般政治的傾向,也是不對的”。在當時極為惡劣的戰爭環境下,自覺強調政治學習與專業學習并重,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培養人才的遠見卓識,并為新中國高等自然科學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為使邊區的教育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首先指出,有了根據地就要做工作,要做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等項工作,以便給日寇以最后的打擊。其次,又指出延安大學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學,這三項是延安大學要學的,也是延安大學要做的。接著,又指出今后延安大學在政治上的具體任務就是,學習統一戰線、三三制和精兵簡政的方針,學習各種政策與方法。
這一講話精神在延安大學制訂的辦學方針中得到了具體的貫徹和落實,表現為其辦學方針之一便是:“進行中國革命歷史與現狀的教育,以增進學員革命理論的知識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思想,并進行人生觀與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養學員的革命立場與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這一辦學方針下,延安大學除開設專業課外,全校開設的共同課程有邊區建設、中國革命史、革命人生觀和時事教育等。這大大促進了學員崇高革命理想的形成,從而為抗戰建國培養了急需的德才兼備的人才。延安時期,黨在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科技教育思想,一方面是是時中國先進科學思想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馬克思主義科技教育思想中國化的最初理論成果。其不僅在思想層面上激發了邊區科技工作者的科學研究的熱情,而且在實踐層面上直接推動了邊區科學事業的發展,由此使黨領導下的邊區科技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從而為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科技教育思想和科技教育實踐的發展、深化和創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戰爭環境的局限使得是時黨的科技教育事業還不可能真正廣泛而深入地開展起來,所取得的成績也還有限。不過,也正因如此,這一時期黨的科技教育思想便顯得更為珍貴、更有價值。可以說,對黨在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科技教育思想進行總結的深度和高度,決定著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出發的坐標。
作者:侯強 單位:江蘇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