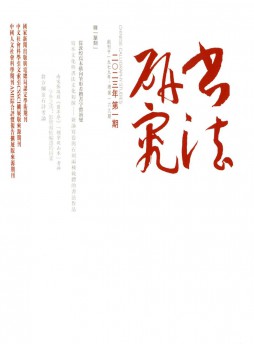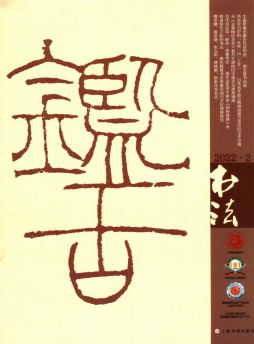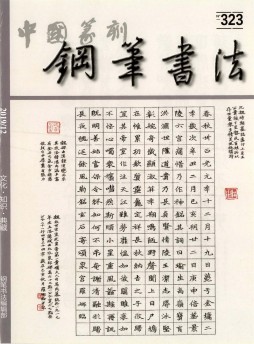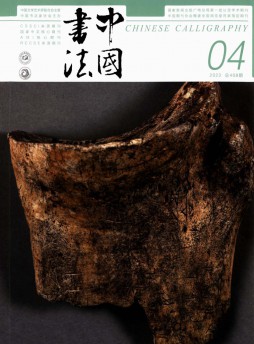書法創作理論探索的困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書法創作理論探索的困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同歷史的其他時期相比,當代的書法創作無疑是非常繁榮的,當代書法創作的多元化,風格的多樣性,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不能相比的。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作為一門中國的本土藝術,在全球文化背景和當代審美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書法在發展和創新方面也遇到了歷史上所沒有遇到過的難題,書法創作表面的繁榮不能掩飾發展的困境。正如陳振濂所言:“書法家似乎無法在一個寬泛的立場上尋找零星的動力,這使它目光日趨狹窄,觀念日見保守,再加上長時間地強調實用所帶來的觀念混亂,書法當然越來越萎靡而漸漸失去了生命力,不但繼續前行步履十分艱難,就連原有的歷史悠久與體格恢宏也開始了誘人的色澤。”[1]。同當代書法創作的表面的繁榮相比,書法創作理論的探索則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缺位乃至迷失,沒有很好地回應當代的創作需求,給當代書法創作以理論的支撐。本文就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出現的書法理論探索論文做一梳理和評價。
一、現代派書法探索的迷失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大批接受西方現代派藝術理論和日本前衛書法影響的書法家,他們對中國書法的未來出路懷有憂患意識,同時這些書法家在同西方藝術家的對話中,有一種話語缺失的感覺,產生了一種文化自卑的心理。這些藝術家在書法的現代性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嘗試,試圖打破中國書法相對封閉的審美話語系統,為中國傳統書法找到一條突破的路子和西方對話的方式。這個時期,前衛書法家們和傳統派的書法們紛紛加入到這個探索的隊伍當中,呈獻給讀者各種新鮮的書法觀念和作品樣式,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在現代派書法家看來,傳統的書法形式和觀念已經落后于當代的審美趨向,已不能滿足當代人的審美需求,人們必須借鑒或融合其他的藝術形式和藝術觀念,才能突破原有的審美系統,為書法的發展另尋出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了“書法字象”派、“書法繪畫”派、“書法構成”派,“書法觀念”派、“書法裝置”派、“書法行為”派、“書法結構”派等,這些書法流派以各自的觀念和方式給中國的書法界帶來新鮮的感受。如“觀念書法”派,發起人認為,在書法創作中,一切的手段和材料、文化、藝術、形式和語言都可以成為資源,它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給予“書法”以觀念的表達,或以“書法”為基因進行觀念的表達,它重視的是表達,而不是書法本身。再如“書法解構”派,提倡者借用西方解構主義方法,對中國的漢字和書寫方式進行破解和重構,臆造了只有他們自己才懂的書法,如徐冰的《天書》文字,雖然具有漢字的外形,但它們完全不是漢字,它們只是漢字筆畫的拆借與重新組合,人們只能像讀天書一樣來破解這些文字的含義。邱振中的《待文字考》系列,對作者來說,漢字只是創作的一種材料,就如繪畫中的顏色一樣,邱振中對漢字筆畫進行了拆借,卻沒有對之進行重新組合,這些筆畫脫離了原來的文字,自由地飄蕩,又可以隨意地與其他筆畫進行組合,如飄蕩的能指,沒有什么具體的含義。如果說徐冰的《天書》和邱振中的《待文字考》等,還帶有漢字書寫的性質,那么像“書法行為”派、“書法繪畫”等流派,則完全成了另外的表現方式,已經完全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寫了,如“書法行為”派就如同其他行為藝術一樣,人們可以不借助筆墨紙張,表演性行為本身就成為一種書寫或創作了。
伴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花樣頻出的現代書法創作嘗試,書法理論界也涌現出了大量的有關現代書法理論方面的論文,如洛齊《書法主義宣言》、王冬齡《現代書法精神論》,王南溟《理解現代書法》,以及一系列的活動和講座等等,他們鼓吹現代書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現代書法思潮。書法在這個時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重視,它寄托著那些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書法家的愿望,他們認為,書法這門藝術可以嫁接世界上其他的諸多藝術,在書法這棵樹上生出一朵朵瑰麗的奇葩,也可以把書法作為資源,為其他藝術提供養分,創造出別樣的藝術形式,如楊應時的《書法作為資源: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新方向》、邱振中的《源自書法——對一類藝術的命名及其他》等,都有這樣的思考。在現代書法思潮的影響下,那些書法家和理論家從實踐和理論上都做了嘗試和思考,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當代化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喧囂之后,一些理性的書法家對書法的本體和邊界做了冷靜的思考:這些花樣百出的試驗之作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法?當跨越了傳統書法的筆墨、結體、章法等等一系列的疆界和法則之后,我們又如何來定義書法?現代主義的藝術思潮是不是適用于中國書法這門獨特的藝術?在經過這樣的思索之后,人們逐漸有了這樣的共識:“現代書法實際上已經不是書法,它不過借助于書法創作的技巧與部分原則來進行創造,即使是借助于書法的那些技巧與原則,也已經過了現代意義上的改造與重組。同時,現代書法也并非繪畫,盡管它也依靠造型來訴諸視覺而對心靈產生沖擊的力量,但這種造型較之繪畫更為單純,更為深刻,因而其對于心靈的震撼更為沉重而悠遠。”重歸傳統依然是一條不可或缺的路子,但如何發展又是書法家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傳統與現代,繼承與發展依然是繞不開的話題。
二、新古典主義與新空間的美學的取舍
當今書壇上三種流派的局面并存,它們是:傳統派、現代派、繼承上創新派,三種流派以不同的藝術主張和思想創作著不同風格的作品,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由于傳統派缺少創新意識,已經很大程度上不能適應當代人的審美需要,而現代派又脫離了書法的本體特征和書法規律,儼然成為一種游戲,最終不被人們所認可。書法要繼承和創新,那么傳統和現代依然是書法創作繞不開的兩個方面,新時期,產生了“新古典主義”、“新空間美學”、“學院派”、“民間書法”等書法創作理念的探索。
(一)新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提出者周俊杰認為,當沉寂了多年的書法藝術,以其深入民族心理的漢文字及其抽象的線條,以其充滿深刻理性又充分顯示藝術感性的審美特征,以其適宜于表達主體精神,宣泄主體情感的功能及既有深沉歷史感又有充滿現代藝術感的諸種因素,在當代一些藝術形式急遽滑坡之時,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在全民族各個階層普及開來之時,它迎合了人們的審美需求。但如何尋找能適合時代需要,又能達到新的藝術高峰的書法創作呢?周俊杰認為:“只有首先在自己民族藝術優秀傳統中,尤其充滿雄渾、博大、豪邁、稚拙之氣的古典時期去尋找那失去的一切,同時吸取外國古今的藝術精華,進行一次深刻的、全面的書法復興運動,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什么是“古典時期”?周俊杰把兩漢以前的書法史稱為“古典時期”,他認為這個時期的書法是書法史上的“兒童期”,不論是甲骨文、金文、隸書、草書,它們最大的特征是純真,意趣十足,同時蘊含著宏偉、豪邁、質樸的藝術氣息,這是兩漢以來書法的圓熟和俗氣不能比的。周俊杰認為,我們提倡“新古典主義書法”觀,就應該從兩漢以前的書法的優秀品格中吸取營養,尋找“氣度”與“生命圖式”,進行“繼承上創新”。如何繼承創新呢?周俊杰認為應該恢復“古典時期”的藝術形式——純真與足以震撼人心的、傾向于陽剛之氣的蓬勃生命力的表現,是借助于古典書法藝術的光芒激發出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更高層次的生命形態,不論一切器物、骨料、木料、石料、步帛、紙張所顯示的文字,均可作為營養;同時,要有高度的藝術修養,能把握藝術本質、民族心態,時代需要,能洞察藝術發展的規律,并能吸收、融會傳統民族藝術之精華,在歷史發展中顯現出自己的個性。“新古典主義”在取法的原則和方法上,把兩漢以來的書法成就幾乎都取消了,不免犯了狹隘的書法史觀和美學觀。固然,兩漢之前的書法呈現出稚拙、純真、博大等特點,但它畢竟只能體現那個時代的審美觀。歷史在前進,人們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追求也會發生變化,呈現出時代的特點和個性化的審美傾向,清梁巘《評書帖》中所說的“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就是這個意思。“新古典主義”雖然強調一個“新”字,但其實也是一種復古主義的表現,并沒有多少新意。在中國書法的創新中,可以借鑒的資源很多,而兩漢之前的書法只能是一個方面,如果因為偏愛一方,而否定其他,這樣的觀點無疑是狹隘的。
(二)新空間的美學王南溟提出了所謂的“新空間的美學”書法觀,提倡從空間的角度上,對中國的書法傳統空間來一番革新,創立一種新的書法審美空間。中國的書法是一種時空交錯的藝術,從空間方面來說,漢字的結構、章法的安排等屬于空間性的,它們服從于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和心理結構;從時間的角度來說,漢字書寫的過程、書寫的節奏、一張作品的完成等方面,都屬于時間性質的。從最基本的筆順推移開去的字與字之間的行進順序,構成了書法創作過程的總體時間順序,每一根線條的頭尾、每一組線條的連接,乃至整篇作品的線條呼應,都具備一定的運動軌跡,而且時間的展開和創作是同步進行的,創作者的心理沖動、感情起伏等方面都有一個明顯的軌跡,它不但為創作者的情緒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也為欣賞者從線條中去把握作者的情緒變化提供了線索。從時空交錯的角度來說,書法的創作是時間和空間相互轉換的過程。空間到時間的感覺轉換,即意味著從復雜的框架架構向單線的流動,呈現為一種動態的情勢,而時間到空間的轉換,則是創作過程中,通過一種線性的流動方式,完成對字型和章法的安排。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中,每一個空間都是時間延續中的一個片斷或一瞬間,而每一段時間都是由眾多空間構成的。空間是時間延續的基點,時間則是空間生存的條件,二者是互相包含的,不能為了時間性而犧牲空間性,也不應該為了空間性犧牲時間性,二者之間沒有誰先誰后的問題。古典書法在處理時空問題上,注意二者的完美結合,“新空間美學”提出者王南溟則認為:古典書法對章法的時間性的強化限制,甚至剝奪了書法空間性的探索,這成了傳統書法的致命弱點,楊維楨、王鐸、康有為等人雖然對書法空間性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但是并沒有動搖傳統書法章法體系,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書法的章法的模式和時間性特點。傳統以一種強大的力量和慣性制約著人們的審美方式,要想對古典書法進行變革,就必須在書法的空間性上做文章。王南溟認為書法的章法秩序是一個封閉的模式,而且阻礙了書法的空間發展,書法不擺脫章法體系,就不會在形式上得到解放。如何解放書法的傳統空間呢?由于書法首先是以文字的可讀性和可辨認性為書法創作的基礎,人們的書法創作必須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變形或改造,如果違反了這個規則,就脫離了書法的本質。“新空間美學”則認為:“現代書法必須以犧牲文字為前提,現代書法才有建構的可能性,現代書法要以文字創作材料而不是書法內容的新美學結構的建立,才使我們有支配、處理文字的現代書法,因為現代書法需要先解放點畫從而解放空間。”
因此文字的模糊乃至不能辨認是最為重要的,它迫使讀者直接進入書法的空間領域,而不是從文字認讀入手,這樣可以打破書寫式和連貫式的惰性思維方式,塑造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書法審美新空間,它更多是強調漢字造型和空間的構造。這樣的空間新美學是以犧牲書法的時間性為基本特征的,傳統書法講究的書體結構、節奏規律、章法布局在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空間,而這種空間也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空間,它是一種帶有私人性的空間,一種個人感覺化的空間。“新空間美學”無疑是受西方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的影響。表現主義注重主觀表現,反對模仿,而抽象主義則注重打破規則,采用變形重組的方式構筑一個新的藝術世界。書法的表現性和它的造型性為崇尚西方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的書法理論家找到了一條嫁接之路,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二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決定了二者的不可通約性,用西方藝術思維方式套用或者改造中國的本土藝術,尤其是書法,似乎是行不通的。
三、學院派書法與民間書法的思路
大學書法學科的建立和培養的系統性及科學性為書法人才的成長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培養的方式和理念的健全是一個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學院派書法”的提出,無疑提供了一種思路。“民間書法”則另外提供了一種思路和方法,為書法創作指明了另外一種途徑。
(一)學院派書法新時期,高等院校書法學科的建立為培養書法專門人才提供了便利和條件,大量的書法人才通過選拔進入高校接受系統的書法教育。但我們也看到,雖然從20世紀60年代陸維釗、沙孟海等人開拓性地在中國美術學院成立書法學科到現在,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但書法學科畢竟是新成立的一門學科,學科的設置和培養的目標尚處于探索階段,有的高校乃至模仿和抄襲老牌高校的教學計劃和培養方案,更為嚴重的是,某些高校的教師理論水平和實踐水平都還不高的情況下,就成立書法學科,這樣培養出來的書法人才其創作水平可想而知。業余的書法愛好者往往又缺少系統的學習和專門的指導,他們即使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但常常在另外一方面有所欠缺,不能對書法創作有全面的把握,尤其是思想上的欠缺,導致了對書法創作規律的深刻認識和狹隘的書法觀。針對這樣的現狀,陳振濂提出了“學院派書法”這一概念,對書法學科的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什么是“學院派書法”?陳振濂是在借鑒其他藝術學科的學院建制下提出的一個新名詞,如戲劇學院、音樂學院、美術學院等等,這些學院都有自身的體系和規范,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養方案和訓練方法,而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學科,則缺少學院的建制,還附屬于其他學科門類,陳振濂認為,書法如果要成為獨立的學科,就必須有自己的學院建制,建立規范,使書法走向專業化、獨立化的道路,培養具有傳統功底和時代意識的專門書法創作人才。陳振濂的“學院派書法”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涉及到書法的各個方面。在書法創作方面,陳振濂提出了美學認同、技術品位、形式基點、主題要求等一系列的要求,形成了他的學院派書法創作理論。在美學認同方面,陳振濂認為既然提出“學院派”書法創作模式,就應該有相應的美學理論,否則就不能走向自我確立,走向成功,走向時代與歷史的前面。在陳振濂看來,書法作為一門特殊的視覺藝術,必須以書法的視覺性來定位,當我們認識到了書法的視覺性特點,就可以把不同于書法的美術流派,從觀念到手法都應該被包括在當代書法藝術的選擇視野之中。
但同時陳振濂又強調,書法既然為“書法”,就必須堅守書法藝術的本位特點,符合書法藝術的基本規范,任何的創新必須以此為基點,這是學院派書法創作必須強調的兩點。在技術品位方面,陳振濂認為,傳統的書法局限于“書寫之法”,是古典書法對“技法”理解的最大不足,既然書法是藝術創作,那么寫字行為也只是一個具體行為,并不是全部的行為內容,在書寫之“法”以外的其他技術手段,也應受到相應的平等對待,為達到一種特殊的創作效果所運用的一切手段,無論是書寫的筆法、章法、字法、或者紙張效果、形式效果,各種技術效果的制作方法,都應該是平等的。在書法創作中最主要的已不是固定的寫字之“法”,而是創作效果。在形式基點方面,陳振濂提出了“形式至上”的創作理念,并把它作為創作的基點來看待。陳振濂認為,實用文字的書寫的傳統意識已經嚴重束縛了我們藝術的想象力,因為書寫只關注書寫的線條以及由此帶來的“書風”,而對于“寫”這一行為以外的種種形式手段不屑一顧。傳統的書寫法則以一種固定的方式成為人們的書寫準則之后,人們只是重復原有的書寫方式,而每件作品形式的獨特性往往被忽視了。由此,陳振濂提出了“形式至上”、“效果至上”、“作品至上”的創作原則。“學院派書法”創作的要求就是:“從書家個性走向每件作品形式的獨特性”、“從單調的書寫形式走向靈活豐富的視覺形式”、“從古典形式走向現代書法形式”。在主題要求方面,陳振濂認為,相對其他藝術門類主題的鮮明,書法創作重視的是技術,包括用筆、結體、章法等方面,人們看重的是字的好看與否,往往缺少了一定的主題,缺少了思想的支撐,而且缺乏落實到具體作品中的構思。由是,陳振濂為新的書法創作模式提出了一個思想和主題要求,作為“學院派書法”的創作目標:書法既然是創作,那么書法家在創作時必須有思想,并且,一般的思想還不行,必須有針對這一件作品所產生的特定的思想,我們通常稱之為“主題”或“構思”。什么是創作“思想”呢?
對陳振濂來說,思想就是作品表現了作者什么樣的意圖、他所運用的技巧與意圖之間的關系、他所選擇的表現形式是否恰當地表現了意圖,以及作品介入社會和時代乃至干預社會和時代的能力等方面。陳振濂認為,當書法創作一旦以構思和主題為依托,可以徹底打破古典書法以技巧包治百病的弊端,從而還為書法創作以藝術創作的應有面目,而且還能使自己有效地與現代派拉開距離。陳振濂特別強調了書法創作介入社會和時代以及干預社會和時代的作用,他認為文字的內容是與書法的藝術表現和創作構思都沒有多大的關系,書法介入社會生活不能僅靠文字內容,它只是很小的藝術傳達,書法介入社會生活的途徑主要是“視覺形式語匯本身”。當形式被藝術家以一定的序列組合、構成、按照某一種具體的思想指向進行視覺擴展之時,形式就具備了明確的意義。陳振濂認為,只要把書法作為視覺藝術的立場與形態不變,大到宇宙空間,小到宇宙芥塵,什么都可以表現;這樣的創作模式會大大開拓思維空間與表現空間,因此也對書法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書法家必須同時是思想家,而且創作過程必須是思想展開的過程,它是構思、形式、技巧的三位一體。陳振濂的“學院派書法”創作理念對書法創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但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看到,他在強調書法的“視覺性”性時,卻遺漏了書法的抒情和寫意功能,在反復強調書法的本體性時,卻忽視了書法傳統的某些東西。書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視覺藝術,它根植于傳統的審美習慣,書法的用筆方法、結體、章法、形式特點都有自己的一套規律,任何的創新還是要尊重傳統的這些東西。為了達到書法的視覺效果,陳振濂認為一切方式都可以運用,這只能是一種探索性的行為,至于欣賞者能不能接受則是另外一回事了。視覺藝術是當代藝術的主流,藝術的創作方式和欣賞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書法創作方面,書法作品的寫意抒情功能逐漸讓位于視覺功能,但是書法創作過程的意趣表達和視覺表現還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犧牲了意趣,那么視覺形式也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審美形式。在主題和構思方面,陳振濂特別強調書法家思想的作用和介入社會生活的能力,他要求書法家同時是思想家,這似乎對書法家有所苛求了,書法家在創作時要有構思和思想的介入,但他不一定非是思想家;書法表現個人或者時代精神風貌,但不一定非要介入乃至干預社會生活,書法藝術的特殊性和單純性,是不可能做到這些的。我們還看到,陳振濂在強調“學院派書法”的同時,遺漏乃至否定了民間書法社團和個人的探索,這其實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思想。
(二)民間書法書法界雖有“官方”和“民間”之說,但如何對“官方”和“民間”進行定義,二者的分界在哪里“,民間”書法存在的時間域,“官方”書法和“民間”書法在審美方面的差別等等問題,也一直是書法界爭論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從時間段上來分,把戰國時期以后一直到唐代以前出現在民間的書法,可以稱之為“民間”書法,這個時間段里,書法逐漸走向完善和成熟,人們對書法的認識也逐漸加深,書寫中實用的因素和審美的因素分界日漸明顯;從審美方面來說,“官方”書法,往往也被稱為“經典”書法,它包括碑、帖、簡等,已經被書法史所承認,并成為后世學習的典范,一般帶有雅化、精致的特點,而“民間”書法由于處在書法發展的交界點,或者由于書寫者的非創作意識因素,常常帶有雜糅、粗礪、天真野逸等特點,呈現出與“經典”書法不同的風格面貌。“官方”書法也稱“經典”書法,它們一直占據著書法的主導地位,那些被稱之為“經典”的書法成為人們學習的對象,被人追捧,而那些數以萬計的簡牘、殘紙、碑刻、瓦當等民間書法則被冷落乃至被丟棄銷毀,只有到了明清之后,隨著碑學的興起,人們才對這些具有書法因素的民間書法產生興趣,從這些“民間”書法吸取新鮮的東西,更新書法的創作要素,這也對當代書法創作以啟發,為沖破、否定經典書法理論中的雷池戒規找到了證據和源泉。20世紀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出土了大量的漢簡、敦煌卷子、以及金石文字等民間書法,也成為當今書法創作吸取的對象。白謙慎在《二十世紀的考古發現與書法創作》中,列舉了幾個當今書法家對這些對象的學習和成就,也許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當經典的書法被反復學習和借鑒之后,已經慢慢失去了它們的新意,而書法可以借鑒的資源又非常有限,于是民間書法便成為我們取法的對象,民間書法中那種古樸、天真、稚拙氣息可以彌補經典書法中的那種我們熟悉的東西,給書法創作以陌生感和新鮮感,尤其是當代書法審美多元化的今天,這樣的探索和借鑒顯得尤為重要。但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看到,某些書法家在取法于“民間”書法的新鮮要素時,由于缺少對書法史的認識和眼光,而走向了書法創作的反面,以一種反書法的面貌出現,這樣的書法不但不給人以美感,而且會誤導大眾。“民間”書法概念的提出,無疑給書法理論以新的創作思路,但如何界定“民間”和“經典”,二者的審美趣味、風格特點等等如何區分,又是一個難題。在歷史上,“民間”和“經典”從來都不是嚴格區分的兩個概念。新時期還有一些書法創作理論的提出,如王鏞等人的“藝術書法”、于明詮的“新文人書法”等等,也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被人遺忘了。相比八九十年代的書法理論探索的相對多元和繁榮,21世紀的書法理論探討則顯得更為沉寂。
四、余論
當今,人們的生活水平日漸提高,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越來越高,書法創作呈現出的繁榮局面,滿足了不同層次人的精神需求,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相對于書法創作的繁榮,書法理論界則顯得沉寂,尤其是書法創作理論方面,書法理論家不能很好地總結當代書法創作現象,也不能在理論方面給于當代書法創作以更多的指導,書法創作和書法創作理論出現了隔膜的現象。當然,當代的書法理論家在書法創作和建設方面不是沒有作為的,不論是“現代書法”概念的提出,還是“新古典主義”、“學院派”等說法的提出,都對當今的書法創作有所啟迪。但我們也注意到,由于這些理論家審美情趣、學術視野、書法史觀等原因,他們在提出建設性策略的同時,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偏頗,有的太過激進。我們期待,在書法創作繁榮的同時,書法創作理論也能跟進,能很好地解答當代書法存在的問題。
作者:劉元良 單位:四川文理學院教育學院
- 上一篇:綠色建筑在城市規劃設計中的運用范文
- 下一篇:醫院HRP中的成本管理理論探索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