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上奏文書的書法藝術(shù)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上奏文書的書法藝術(shù)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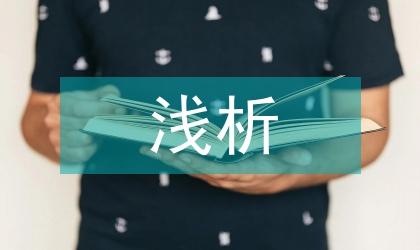
一、魏楷
魏楷書體此時在高昌流行,與歷代高昌王所采取的政策是分不開的。高昌王國的這些上奏文書大都處于麴氏王國延昌年間,即麴乾固在位期間,也有義和和延壽年間的,所以這些上奏文書的書法藝術(shù)水平反映了麴乾固、麴伯雅和麴文泰在位期間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水平。公元555年,突厥打敗柔然,統(tǒng)一了漠北地區(qū),在高昌王麴寶茂和麴乾固在位期間,幾乎斷絕了與中原的往來,所以中原的史籍中并沒有與之相關(guān)的記載。地域上的隔絕導(dǎo)致了文化的交流不暢,也導(dǎo)致了高昌的書法藝術(shù)不能與中原內(nèi)地的書法藝術(shù)演變保持一致,所以呈現(xiàn)出保守的特點。直到公元607年麴伯雅在位期間,麴伯雅攜帶世子麴文泰兩次使隋,才加強了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所以隋朝的魏楷書體傳播到高昌地區(qū),對該地區(qū)的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而高昌王此時依附于大隋王朝,為了討好隋朝,在政府的官方文書中使用隋朝流行的魏楷書體也在情理之中。
二、行楷
上奏文書中,除了兩件魏楷書體之外,其他的上奏文書大都是行楷書體。行楷書體,是介于楷書與行書之間的一種書體。但是行楷書體并不是指文書中的每一個字都是行楷字體,而是縱觀全篇,具有楷書和行書兩種筆意,姑且稱之為行楷。行楷字體,是以楷書筆法為基礎(chǔ),如字形偏長,左高右低,但比楷書書寫自由,又比行書規(guī)正。如《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年)六月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中的“將軍”是規(guī)正的楷書寫法,結(jié)體緊密,筆法規(guī)范,筆順和行筆也不可以隨便改變;《高昌民部殘奏》的“將軍”二字是行楷書體,結(jié)體靈活多樣,書寫自由瀟灑,還可以根據(jù)個人書寫習(xí)慣和筆畫順序呈現(xiàn)不同的書寫形態(tài),筆畫的連結(jié)、替代和減省也會使字形變化多樣,而且行楷書體的筆畫字數(shù)也可以改變,如規(guī)正楷書的“將”有10畫,“軍”有9畫;而行楷書體的“將”是9畫,“軍”是七畫,筆畫都有所減少。所以行楷書體是在楷書基礎(chǔ)上簡化筆畫、增強連帶以加快書寫速度的一種書體。當然,在書寫過程中,我們不能只強調(diào)某一方面,如果只強調(diào)楷法,容易使字體僵化,不靈活,影響字體的結(jié)構(gòu)和書寫的節(jié)奏;但如果只強調(diào)速度,容易使字體雜亂無章,難以辨識。因此,行筆過程中,楷書筆法和行書筆意要保持適中,楷行兼顧,不可偏頗一方,遵循行楷書體的書寫規(guī)則。
行楷書體此時在高昌地區(qū)非常流行,除了受內(nèi)地書法藝術(shù)發(fā)展的影響之外,西域獨特的民族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西域一直是以漢族為主、多民族雜居的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多以游牧為生,在西域地區(qū)各種文化兼容并蓄,共同發(fā)展,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地域特色的書風。楷書形成于漢魏,歷經(jīng)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代達到頂峰。此時高昌王國的楷書僅處于發(fā)展階段,再加上當?shù)厣贁?shù)民族追求自由的民族特性,因此受隋楷嚴謹法度的影響不大,所以不管是民間文書,還是官方文書,都以書寫便捷、瀟灑自由的行楷書風為主。西陲邊境這種胸懷博大、瀟灑自由的書風保持了楷書初興階段所具有的靈氣和活力,自在奇肆的意態(tài)表現(xiàn)了邊疆人民心靈的質(zhì)樸和襟懷的坦蕩。
三、行草
行草作為一種特殊的字體,形成于漢代。吐魯番文書中的行草字體多出現(xiàn)在契約和官方文書最后的批文部分,如《高昌延昌年間兵部殘奏》《高昌延昌廿七年(587)某月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四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某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七月十五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七月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八月十五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這些文書的批文部分所出現(xiàn)的“伯雅”“紹徽”“歡”“僧道”“奇乃”“佛圖”“養(yǎng)生”“患”“樂”“慶儒”“友”,都屬于行草書體,非常具有個性,倚側(cè)多姿,形態(tài)多樣。在吐魯番所出土的文書中,除了上述字體以外,尚未發(fā)現(xiàn)甲骨文、金文、大篆等文字,就是小篆,由于難于辨識,不方便使用,也只是在一些官方文書的印鑒上使用。在這批上奏文書中也沒有發(fā)現(xiàn)小篆字體,就連帶有隸書意味的楷書也沒有出現(xiàn),或許由于出土文書的隨機性,能證明這些的文書還未發(fā)現(xiàn)吧,這還有待考古專家們的進一步發(fā)掘。
這批上奏文書,有的保存比較完好,書法字體比較清晰,如《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四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某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587)七月十五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shù)奏行文書》等,這些兵部買馬的上奏文書,雖然內(nèi)容不完整,但整篇的字體和章法還是比較清楚的。但是也有些文書殘損比較嚴重,如《高昌延昌十四年(574)殘奏一》《高昌延昌十四年(574)殘奏二》《高昌時間不詳都官殘奏一》《高昌時間不詳都官殘奏二》等,雖然破損厲害,但從僅存的字體和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也可以判斷出它們所處的年代。據(jù)孟憲實先生研究,這批上奏文書有的通過綰曹郎中和高昌令尹上奏給高昌王,有的直接上奏給高昌王,但從書法藝術(shù)的視角看,這批文書不管是否經(jīng)過綰曹郎中和高昌令尹,最終都是要上呈給高昌王看的,所以書寫這批文書的書寫者的書法功底肯定不低,甚至代表著當時書法藝術(shù)的最高水平。所以通過研究這部分文書文本的書法藝術(shù),可以看出當時在高昌官方文書中所使用的書法藝術(shù)水平。上至所好,下必行之,也可以說這部分上奏文書的書法藝術(shù)水平不但代表著當時書法藝術(shù)的官方通用水平,也直接影響著民間書法的價值取向。
從出土文書中的字體演變來看,不僅內(nèi)地字體的演變和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能迅速及時地影響和傳播到西域地區(qū),而且西域地區(qū)的書家所進行的筆法上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嘗試也可能使內(nèi)地書法家受到啟發(fā)。如王羲之被稱為“書圣”,王體書法歷來是書法界的瑰寶,但是從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我們看到,類似王體的書法字體在吐魯番地區(qū)早已出現(xiàn),只是后來被王羲之發(fā)現(xiàn),并進一步提高升華而已。試想如果沒有邊疆書法的創(chuàng)新和探索,王羲之這種書體的出現(xiàn)可能還要往后拖延,“書圣”花落誰家,還未可知啊!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曾經(jīng)在河西任職,河西距離高昌較近。在吐魯番出土的文書和墓磚中有很多與顏真卿書法風格相近的書法作品,尤其是行書作品,所以可以推斷顏真卿也從高昌地區(qū)汲取了豐富的營養(yǎng)。高昌地區(qū)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深受內(nèi)地書法藝術(shù)的影響,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內(nèi)地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高昌地區(qū)與中原內(nèi)地互相影響,共同發(fā)展。
在目前所出土的文書中,上奏文書雖然僅有18件,但足以證實行楷書體是麴氏高昌王國時期官方通用的標準書體。除了這18件上奏文書,吐魯番地區(qū)還出土了大量的其他文書、碑刻、墓磚和墓表,都保存了大量的有關(guān)書法藝術(shù)發(fā)展的珍貴資料,所以吐魯番出土的具有書法藝術(shù)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文書是西域地區(qū)和我國各族人民寶貴的文化財富。我們應(yīng)該繼續(xù)深入探尋其中蘊藏的奧秘,深掘它們的審美價值,弘揚我國優(yōu)秀的書法傳統(tǒng)文化。(本文作者:劉藝銘單位:塔里木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