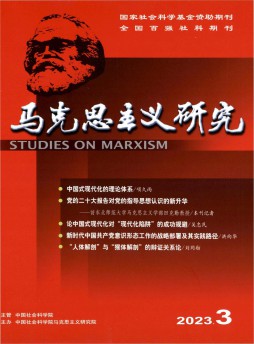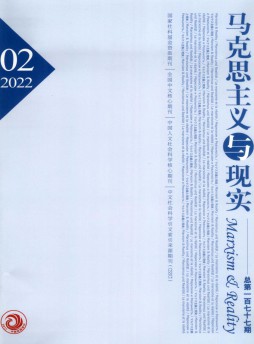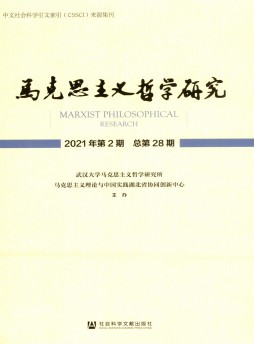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馬克思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將作為古典經濟學之哲學基礎的實證主義標識出來,是為了凸顯下述一點:馬克思正是在古典經濟學停留于事實和現象的地方繼續向前推進,實現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性超越,認識這一點,對于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的語境和路徑極為關鍵。眾所周知,馬克思走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道路與他對黑格爾式思維方式的拋棄和批判密切相關。黑格爾哲學雖然開辟了一條走向現實事物的道路,但終究是流于抽象的,在某種意義上,黑格爾哲學體系越是完善,它對事物的歪曲就越是嚴重,因為體系的完善只是來自于邏輯的考慮,而非對現實事物考察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哲學的工作不是使思維體現在政治規定中,而是使現存的政治規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學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⑨因此,當馬克思經過對物質利益問題的苦惱和疑問之后,開始拋棄那種讓現實適應思辨、讓事物適應觀念的思維方式,而轉向了對現實事物的直接把握,馬克思開始走一條與黑格爾思辨哲學完全相反的道路:不是從觀念和體系出發,而是從現實生活出發,這條道路便是政治經濟學的道路。不過,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并不當然地等同于“從現實生活出發”,因為馬克思發現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根本無法揭示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例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從古典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并采用它的語言和規律,但最后卻得出了與它截然相反的結論。古典經濟學極為重視經濟事實,像勞動、資本和土地的互相分離,工資、利潤和地租的互相分離,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因此被古典經濟學當作理論前提,但是古典經濟學只是囿于經濟事實的范圍來說明經濟規律,并把資本家的利益作為不可觸犯的最高原則,從來不曾說明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分離以及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分離是如何產生的,由此也就導致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等更為真實的經濟事實的掩蓋。試舉一例,按照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勞動的主體理應享受產品,然而同樣按照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勞動者只能將自己的勞動(力)出售,因此就只能獲得勞動(力)的價值。前者是符合事實的,后者也是符合事實的,但兩者卻存在明顯的沖突,而古典經濟學居然對如此明顯的沖突毫無關注,除了階級利益所決定的立場之外,這不能不說是局限于事實范圍的實證主義眼光造成的謬誤。令人費解的是,當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之后,緊接著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下了一段似乎是贊成實證主義的話:“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
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⑩這段話因為出現了“實證科學”的字眼而引起了學者們關于馬克思哲學或歷史唯物主義究竟是哲學還是“真正的實證科學”的爭論,而在筆者看來,單從概念的角度無法把握馬克思對“實證科學”的理解,而應該從理論研究的實際表現把握馬克思對“實證科學”的態度。馬克思使用“實證科學”、“現實生活面前”、“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等明顯具有實證色彩的概念,主要用意是與黑格爾式的思辨哲學相區別。既然黑格爾哲學是以抽象概念凌駕于現實生活的方式歪曲了現實生活,那么作為對黑格爾哲學的反撥,馬克思哲學從黑格爾哲學的反面,即以從現實生活出發解釋概念這種方式來表述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十分自然的,這是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式哲學話語中往往帶有實證色彩概念的原因。然而,這一點并不能成為馬克思贊同實證主義的理由,因為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所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
當馬克思論及黑格爾式哲學的時候,主要的任務是批判思辨哲學,還沒有合適的語境來闡發對于實證主義的理解,但是只要有合適的語境,他對實證主義的同樣批判的態度也就明顯起來。具體來說,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的批判可以從兩個層面加以理解。一個是觀點層面的批評性闡述。同樣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在這里,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義者單純依靠想象來研究歷史的抽象方式,也批判了經驗主義者單純依靠事實來研究歷史的實證方式。在《剩余價值學說史》一書中,馬克思指出: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不過是把日常生活過程中的某些現象按照它們外表上顯現出來的樣子加以描寫、加以分類、加以敘述,并列入簡單系統的概念規定中”。
這就注定不能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和根源。除此之外,馬克思還把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稱作“粗率的經驗主義”,并指出這種“粗率的經驗主義,已變為錯誤的形而上學、經院主義,挖空心思要由簡單的、形式的抽象,直接從一般規律,引出各種不可否認的經驗現象,或用狡辯,說它們本來和這個規律相一致。”由此可見,馬克思對那種從事實出發再到事實的實證主義方式是持批評態度的。另一個是方法層面的歷史性研究。馬克思深知,對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的拋棄并不能克服實證主義,更不能超越實證主義,只有揭示出古典經濟學囿于事實范圍而無法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和本質規律,才能真正把握經濟現實,也才能超越實證主義。馬克思的《資本論》研究與古典經濟學相同的地方是:都從經驗事實出發,分道揚鑣的地方在于:古典經濟學始終對經驗事實進行直觀描述和實證考察,它們所找到的經濟規律都是建立在對經驗事實的肯定性理解基礎上,而《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建立在對經驗事實的“暫時性”理解基礎上,對每一種經濟形式都是從其不斷的運動中去理解,這樣,當古典經濟學以事實之名一再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然化、超歷史化的時候,馬克思卻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成是一個暫時性的、充滿自否定精神的歷史性事物。可見,馬克思是通過歷史性的研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視野,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超越了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
三、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真實意蘊
“批判”是《資本論》一書的重要關鍵詞,如何理解這里的“批判”關系到能否正確地把握《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從字面來看,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指將批判矛頭對準古典經濟學,即運用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不過這種理解還只是理論工具主義的理解,即把批判當做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這意味著批判被作為工具運用于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批判處于一種純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脫離具體的內容。換言之,批判與政治經濟學仍然是外在的,即使脫離了批判,政治經濟學仍然成其為政治經濟學。很明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理論工具意義上的批判,而是理論本質意義上的批判,即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側重于從政治經濟學本質的意義上來理解批判,政治經濟學以批判作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規定而體現于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這表明批判已經成為《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內在結構和本體基礎,政治經濟學與批判是內在結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為《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闡述就表達了從理論本質意義來理解批判的觀點:“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這段話非常重要,因為它表達出馬克思通過辯證法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本質的理解,而不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工具的理解。只有從本質而非工具的意義上去理解批判,我們才能科學地理解《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正是《資本論》在理論本質的意義上實現了批判,《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才不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學,而是以批判為內在結構和本體基礎的政治經濟學,這是我們把握《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何以可能的關鍵之點。《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從批判的視角、從“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的層面切入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理過程、內在機制及其歷史極限。可以說,《資本論》的價值立場、研究方法和觀點結論都需要在批判的意義上才能合理理解,下面我們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全面展示《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真實意蘊。首先,《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現在批判的價值立場上。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一點看起來像是以客觀化的方式對待研究對象,但是對現實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分析必然會引申出價值問題。馬克思深知,用來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評價尺度不能是抽象的價值訴求,而應當是經濟的事實和嚴格的邏輯,只有在對現實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科學分析基礎上,價值目標的提出才是有意義、可行的。馬克思提醒讀者:“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馬克思將價值訴求奠基于客觀分析之上的做法使得其價值立場具備了科學的基礎。同時,經由《資本論》的研究,科學意義上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既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又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暫時性”產物,這樣馬克思必然采取與古典經濟學家們辯護的價值立場截然相反的立場:批判的價值立場。馬克思指出:“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
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之時,資本家及其理論代表總會反思危機之前所施行的各種經濟和社會政策,然而所有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完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良資產階級生產制度的前提上。就此而言,資本家及其理論代表對資本主義的理解還遠遠沒有達到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辯證法理解水平,而與之相對的是,馬克思徹底地從“不斷的運動”中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位和命運,由此體現在價值立場上必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次,《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現在批判的研究方法上。《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辯證法、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等,這些方法的靈魂和核心是辯證法,而《資本論》的辯證法在本質上又是批判的,因此《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質也就容易理解了。不過這些還是形式化的說明,問題仍然有待展開,我們就以抽象上升到具體方法中的“抽象”為例來說明。由于“具體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體”中的“抽象”是同一個概念,因此容易被人理解為同一個抽象。實際上,這種理解抹殺了抽象的不同類型。馬克思指出,古典經濟學從人口、民族、國家等“具體”開始,一步步分析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這些“抽象”關系當然是現實事物的最一般的規定,問題在于古典經濟學停留于這些“抽象”關系中,把“抽象”關系當成是事物現實的、完整的規定,從而導致了對現實事物的抽象化,這正是古典經濟學從實證主義走向抽象哲學的錯誤路線。而“科學上正確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體,即從事物的抽象規定再現出事物的“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正確方法的開始環節:“抽象”,不可能是古典經濟學錯誤路線的結果,即具體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就像正確不能以錯誤的東西作為自己前提的道理一樣,這就提示我們:這里的“抽象”只能是科學意義上的抽象。那么,什么才是科學意義上的抽象呢?而且,這種抽象與批判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呢?就第一個問題,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這就指明了抽象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的區別,自然科學方法的本質在于量化,而抽象方法的本質在于不可量化,既然如此,關于經濟形式的不可量化如何可能呢?馬克思認為,把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范疇按照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順序排列是不行的,因為這只是一種實證的方法,還根本談不上對各種范疇及其相互關系的本質把握。科學的方法是按照各種范疇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按照它們內在的邏輯關聯排列,從而展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機制,這就是科學的抽象。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將商品的感性一面,即使用價值交給自然科學家去研究,而高度重視商品的抽象一面,即價值,因為價值作為一般人類勞動,代表著商品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它在資本運動過程中表現為自我分裂、自我解決、自我同一的東西,由此可以發展出資本運動的整個序列,即《資本論》三卷所闡述的“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可見,商品的抽象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簡單規定,然而卻是包含著整個復雜經濟運動的簡單規定,要理解這一點,只能依靠冷靜的“抽象力”。就第二個問題,《資本論》的抽象是科學批判的前提。馬克思給《資本論》規定的理論任務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規律,這就只能訴諸抽象方法,而非實證方法。仍然以商品問題為例,古典經濟學關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即發財致富意義上的商品,而馬克思關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之間的矛盾,即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使用價值使得商品成為有用物,但商品只能在與其他商品相交換的關系中才能成為有用物,即商品只有在其作為一般人類勞動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為使用價值,這樣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就始終處于矛盾關系中,這個矛盾以萌芽的形態包含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矛盾。就此而言,理解商品價值的抽象特征,就成為理解資本主義的矛盾本質,從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關鍵。再次,《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現在批判的觀點結論上。所謂“批判的觀點結論”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結論的批判,而且是作為批判的觀點結論、以批判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觀點結論。就此而言,《資本論》把批判的側重點放在了對抽象統治個人的批判和對資本壓迫勞動的批判上面。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抽象“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而物質關系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可以歸結為資本,因此抽象統治個人,就是資本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
資本能夠具有“獨立性”從而統治個人,本質的原因在于資本就是無限增殖自身,因此必然要把一切事物納入資本增殖的環節當中,這樣資本具有了統治的主體性,本來是人的勞動產物的資本,現在反過來成為控制人和奴役人的主體,而同時人只能在資本增殖鏈條中獲得自己的現實感和力量感,因此資本增殖這一抽象維度便成為人的主體性存在的唯一尺度。所謂資本壓迫勞動,就是資本“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如果沒有工人的活勞動,那么資本就只能是僵死的物。針對這種現象,馬克思用一個比喻予以深刻說明:“勞動是酵母,它被投入資本,使資本發酵。”對于抽象統治個人和資本壓迫勞動的現象,《資本論》是堅決批判的,然而《資本論》的批判是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矛盾,從而指出人類走向解放的道路為目的的,即資本的增殖邏輯終將導致資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因此批判并不是《資本論》的目的,通過批判敞開解放的道路才是《資本論》的目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將解放的任務交給實踐,還把它交給一個特定的階級:無產階級。這是因為資本壓迫勞動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壓迫方式,歷史上的壓迫往往具有一看便知的明顯特征,而資本壓迫勞動卻“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議定的結果”。這種自由形式掩蓋著非自由的本質,它以其隱蔽性成為一種最牢固的統治:“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獨立性這種假象是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擬制來保持的。”資本壓迫勞動是通過雇傭工人受雇于整個資本家集團來保證的,在這種情況下,對資本壓迫勞動的反抗就只能采取階級反抗的方式,而不能也不應該采取個人反抗的方式。就此而言,《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一切堅持個人主義、宣揚以個人為主體來反抗權力壓迫的理論批判分道揚鑣了。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懂得馬克思從《共產黨宣言》直到《資本論》始終強調無產階級國際聯合以反對資本主義的內在原因。
作者:鮑金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上一篇:青年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范文
- 下一篇: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