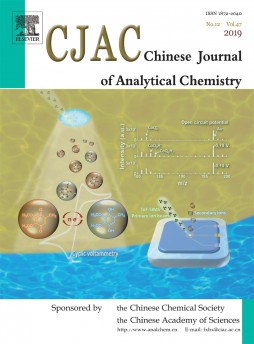分析學術編輯工作中的理解活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分析學術編輯工作中的理解活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解釋學視域下編輯的理解之應用
伽達默爾繼承了海德格爾存在論的思想,認為人的理解活動是一種存在方式,是整個人類世界經驗的組成部分。理解過程本身就是理解者和理解對象雙方尋找和創造共同語言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視界融合的過程。理解是前理解的投射。前理解是我們的歷史存在,是由我們歷史地被拋的存在狀態決定的。伽達默爾談到的“任何理解都是自我的理解”,指都是基于理解者自己的解釋學處境的理解。編輯的理解活動也是一種自我理解,是基于編輯的視域的理解。編輯的學術背景、專業局限、知識觀點等不可避免地會對其理解活動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審稿結果和與學者對話的質量。伽達默爾解釋學的核心概念“效果歷史”揭示了解釋學的應用功能,他強調了應用在解釋學中的根本作用[3]。“所有的讀都包含一個應用,以致誰讀某個文本,誰就自身處于他所理解的意義之中”[4]。對于伽達默爾,被理解的意義總是應用于我們,并且體現為對我們而言的26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意義。因而,理解之應用就在解釋者和其對象之間采取了視域融合的形式,這個融合被伽達默爾理解為一個對話過程。論文總是基于編輯或專家的視域和前見而被理解的。當學術編輯在審閱稿件、閱讀專家審稿意見等時,他既不需要也無法排除自己的視域,而是會以自己的視域為出發點,逐漸地擴展到理解對象所處的意義之視域,最終,隨著他自身視域的擴展,他和理解對象的視域融為一體。在問答結構的對話中發生的就是這樣一種視域融合。編輯與學者之間的理解需要這兩者的相互參與,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過程。編輯總是帶著自己的前見與視域參與理解活動。“越是一場真正的談話,它就越不是按談話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而進行”[5]。編輯和學者作為對話參與者,都是對話的被引導者。編輯和學者的對話總是圍繞著一個論題而展開,受論題本身規律的約束和支配,其進程和結果不是編輯或學者某一方能完全支配的。編輯與學者是在問與答的過程中實現意義溝通。要使這種對話過程順利進行,必須確保編輯和學者具有同等的發言權,并且具有理解對方的誠意。
伽達默爾在談論無談話能力的時候論及了語言和理解之間的關系。造成無談話能力的因素有無傾聽能力、不存在共同語言和缺乏積極的對話態度等。他指出,“只要人們找到共同語言并最終找到了共同語言,那么相互理解就一定能成功”[6]。優秀的學術編輯既是編輯又是學者,這種雙重身份會對審稿、編稿、約稿等產生積極的影響。學者型編輯自身的學科背景、知識結構、學術立場、學術風格是他們理解活動的必要條件,他們的一切理解活動都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這些因素能夠在理解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畢竟,學術編輯在某一領域越有造詣,越了解該學科領域的前沿、熱點問題與研究動態,就越能高屋建瓴地開展該領域的選題策劃活動,從事該領域的審稿、組稿等相關工作也會如魚得水。學者型編輯能與作者、專家擁有共同的學術語言,產生思想的碰撞,在此過程中可以消除不當的學術偏見,產生新的合理的見解,并達成相互理解。真正優秀的編輯能根據論文主題自身的規律對作者的寫作進行指導,就像真正的談話高手如蘇格拉底能夠依據話題本身的規律對對話者進行引導一樣。
2解釋學視域下編輯的理解之達成
劉少奇同志曾指出,編輯活動是一種高水平的創作活動[7]。編輯要對作者的學科背景、學術觀點等有全方位的了解與把握,在尊重和理解作者的基礎上對其作品進行再創作,最終呈現給讀者大眾的作品是作者與編輯共同創作的結果。伽達默爾認為,講話的意義不能被限制在已被說出的話語之中,已被說出的與未被說出的話語一起構成一個意義整體[8]。“若要理解說出的話語,不僅要理解已說出的成分,還要理解潛藏在其中的想說的或不得不說的東西,即‘內在話語’,因為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意義的整體。語言符號所表達的只是說話內容的某一方面,它所展示的理解總是不完全的,我們還必須理解體現在其中的話語或理性,關注內在話語本身并對它進行追問,以不斷地獲得更加完善的理解”[9]。語言的思辨結構表明,語言中已言說的部分和未言說的部分一起構成無限可能性的統一。這意味著,只有當編輯與作者或專家達到相近甚至同等的高度或水平,編輯對作者或專家所涉獵的領域具有透徹的認知的時候,編輯才能既把握作者或專家已言說的東西,又能體悟到他們已說出的話語背后未言說的東西,從而把握他們的語言構成的意義整體。這表明學術編輯本身具有較為精湛的學術造詣,是構成與作者或專家平等對話或真正意義上的對話的基礎,也是完成高水平創作的前提。否則,學術編輯對作者論文的優劣沒有發言權,也無法把握專家言說的東西。“責編如果沒有自己的研究領域,與學者交往時總有那么一種隔膜。交流難以深入,交情自然難以深化”[10]。“誠如編輯學家鄭俊琰所說:不平等地位下的編輯不能當,只有與學者平行,才能當好編輯”[11]。因此,編輯應當不斷提升自己與作者或專家進行學術對話的能力。
編輯活動往往注重和強調編輯本身的主體地位與作用,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容易被淡化或忽視。編輯是主體,論文作者、審稿專家也是主體。“真正的主體只有在主體間的交往關系中,即在主體與主體相互承認和尊重對方的主體身份時才可能存在”[12]。因而,編輯一方面要充分地積極地發揮自身的主體作用,進行策劃選題、組織稿件、解構與重構稿件的意義、編輯加工等創造性勞動,另一方面要認識到論文作者或審稿專家的主體性,意識到他與論文作者、審稿專家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并主動與這些主體進行交流、對話。伽達默爾分析了“我—你”關系在解釋學中的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指的是這樣一種對“你”的經驗:把人當作物,從而人成為對象,并且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對之進行考察與把握。他認為人不可用對待物的方式和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同類,因為人不是物,人是具有尊嚴的存在。很顯然,這種“我—你”關系是不可取的,這樣的關系存在于編輯工作中是不適宜的。康德也強調過,我們不應把人當作工具,而應當承認人就是目的。
第二種“我—你”關系類型是:“你”被承認為一個人,而非物。與第一種類型相比,該類型強調“你”是一種反思關系,而不是一種直接的關系。當這種類型的“我—你”關系應用到編輯的理解活動中時,具體表現為編輯對作者或專家的理解和把握是基于編輯自身的視域,僅通過編輯單方頭腦中純粹的抽象的思辨活動達到對作者或專家的理解,而不是在現實生活中通過與作者或專家進行直接的現實的雙向的交流所獲得的理解。這種層面的理解仍是不夠的。一個編輯往往要負責多個欄目,由于編輯自身視域的限制,其專業背景和主觀偏好很容易影響稿件的處理結果。有時看到一篇待審論文的題目,編輯就會迅速判斷其學術水平,想當然地判斷論文質量,匆忙做出處理決定。單純基于編輯一方的視域對論文進行判斷,很多時候是片面的。承認自己有可能是錯誤的是解釋學的前提。因而,編輯需要求助于論文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求助于與該論文有共同語言的學者,同時向作者了解他想真正表達的內容,從而努力克服偏見,實現真正的理解。這種真正的理解建立在第三種“我—你”關系類型之上。
第三種“我—你”關系類型強調,在人類的理解行為中,真正地把“你”作為“你”來進行經驗是最為重要的。這意味著,我們不要忽略“你”的要求,以便讓它能對我們真正說點什么。這體現在編輯工作中,就是要與作者或專家進行直接的現實的雙向的交流。具體表現為編輯要經常和作者或專家溝通,知道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或想表達的是什么,了解并關注他們在學術上的進展,聽取他們的需求和建議,同時要讓他們知道編輯目前的需求,了解刊物當前的動態。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經啟用微信公眾平臺,不定期地推送學術論文,學術訊息與學術動態,由于微信的受眾廣,微信公眾平臺可以很好地發揮宣傳與推廣的作用。編輯要多參加學術會議,通過這種途徑不僅可以發現作者、約到名家稿件、宣傳刊物,還可以與眾多作者或專家直接地面對面地進行學術對話與交流,增進情誼與理解,提高自身的學術對話能力。編輯平時進行審稿、編稿或約稿時,也需要通過打電話、發郵件、微信或QQ聊天等方式,頻繁地與作者或專家聯系,與他們展開平等而真誠的對話,努力實現真正的相互理解。編輯要在為學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增進彼此的理解,同時在達成理解的過程中優化自己的服務。真正優秀的編輯能起到作者和審稿專家之間的橋梁作用。優秀的學術型編輯能夠比較客觀地判斷審稿專家對論文的審稿意見是否合理,可以對專家的意見進行取舍,在綜合編輯部修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最終修改意見,并評判作者按照此修改意見所做的修改是否到位,然后再本著對期刊負責的態度決定稿件是否錄用。當不同審稿專家的審稿意見截然相反時,編輯的決定就顯得更為關鍵。當作者對審稿專家的審稿意見產生誤解時,編輯還能幫助作者正確地理解專家的意思。很多稿件在刊發之前都經過多輪的反復修改,學術期刊都很注重作者對修改意見的回復,每輪修改都會要求作者既要返回修改稿,還要附上詳細的修改說明。為盡量避免誤解,在稿件處理過程中編輯要注重與作者的雙向學術交流以及與審稿專家的雙向學術交流,并且恰當地擔當起作者與審稿專家的雙向學術交流的中介;在校對環節應當注重作者校對,尤其是“編輯稿的作者校對和二校后的作者校對”[13],采用編輯校對和作者校對相結合的方式。另外,編輯自身掌握的編輯出版行業的知識、編輯的職業特點、判斷標準等也會對其理解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總之,要充分發揮編輯、作者與專家三方的力量,共同提高稿件質量。
伽達默爾強調經驗的否定性。對于解釋學經驗而言,事物要表現自身,就必須否定地對待自身[14]。要達到對文本的理解,就必須拒斥與文本的意義不相符合的那部分我們的前見。他人有可能是正確的,我們要有理解他人的善良意志。不論是編輯還是作者或專家,都要虛懷若谷,將自己的偏見先懸置起來。如果我們頭腦里充滿的只是自己的看法,無法向他人敞開并傾聽他人的意見,我們是很難實現真正的理解的。他人有可能是正確的是解釋學的前提。在編輯工作的人際交往中體現了善意的理解的重要性。解釋學強調人要有謙遜的態度,要能夠破除我26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執。在真正的解釋學經驗中,有對個人視域的部分否定,這種否定性是一種生產性的因素。正是通過這種否定性,理解才會不斷變得更為豐富。“我—你”關系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包含提問與回答。在伽達默爾看來,對話首先意味著傾聽,傾聽是一種向新經驗敞開的態度。審閱論文或閱讀審稿意見時,文字對編輯顯現出的意義就是編輯對它的理解,這是它向編輯述說的東西。理解是通過主體間的對話實現的。編輯和學者通過文字或發聲語言進行問與答的過程是視域融合的過程,也就是實現相互理解的過程。只有當編輯和學者之間的關系具有平等性、開放性和相互性時,才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在編輯工作中,應當注重編輯和學者之間的相互傾聽、相互理解,注重對話與和諧。
- 上一篇:探究學術期刊編輯話語范文
- 下一篇:少兒報刊編輯轉型路徑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