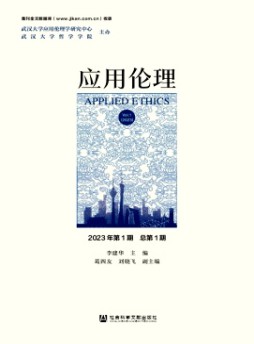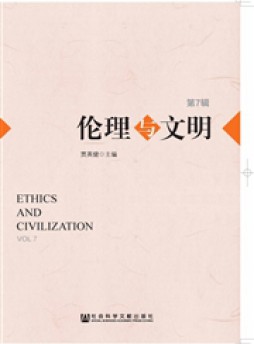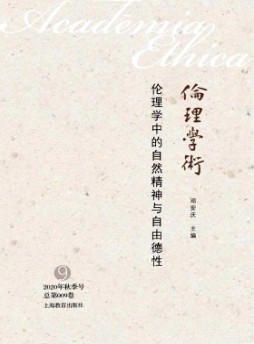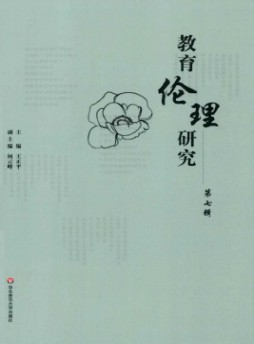倫理本位的中國文化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倫理本位的中國文化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中國社會(huì)構(gòu)造的基本特征
第一,“職業(yè)分途”是中國社會(huì)另一個(gè)顯著特征。在西方社會(huì),生產(chǎn)資料與勞動(dòng)者是長(zhǎng)期分離的,生產(chǎn)資料占有者不勞動(dòng),勞動(dòng)者不占有生產(chǎn)資料。例如,在中古社會(huì),地主擁有土地但不耕作,農(nóng)奴耕作而不能自有其土地;在近代社會(huì),資本家擁有工廠及設(shè)備而不操作,工人勞動(dòng)而工廠甚至勞動(dòng)產(chǎn)品都不為其所有,這樣的結(jié)果就是形成剝削與被剝削的情勢(shì)。在政治上,無論是中古社會(huì)還是近代社會(huì),要么是封建貴族,要么是資產(chǎn)階級(jí)壟斷寡頭長(zhǎng)期把持政權(quán),農(nóng)民與工人幾乎無機(jī)會(huì)擔(dān)任國家公職人員。所以,整個(gè)西方社會(huì)是屬于兩部分人的“階級(jí)對(duì)立”的社會(huì)。在梁漱溟看來,中國社會(huì)卻沒有形成這種兩面的形式。在經(jīng)濟(jì)上中國社會(huì)之所以沒有形成像西洋社會(huì)那樣生產(chǎn)資料為一部分人壟斷,梁漱溟認(rèn)為有三個(gè)原因:第一,土地很早便解脫于封建束縛而自由買賣,人人得而有之;第二,遺產(chǎn)很早便是諸子均分制,而非長(zhǎng)子繼承制;第三,蒸汽機(jī)等大機(jī)械未發(fā)明,集中大規(guī)模生產(chǎn)遂無可能。由于第一第二點(diǎn),使土地不能集中而壟斷之,由于第二第三點(diǎn)是資本不能集中而壟斷之。這就造成中國社會(huì)是一個(gè)“個(gè)人作個(gè)人的工,個(gè)人吃個(gè)人的飯,只有一行一行職業(yè),而缺乏兩面對(duì)立階級(jí)”的社會(huì)。但歷史的現(xiàn)象并非與理論分析完全契合,比如雖然古代中國社會(huì)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但結(jié)果不必然導(dǎo)致“人人得而有之”。相反,古代中國土地集中的問題一直是影響政權(quán)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在政治上,梁漱溟認(rèn)為中國政治同樣沒有形成階級(jí)對(duì)立,或者說是缺乏階級(jí)的。一方面由于中國的君主是“孤家寡人”,除了少數(shù)皇親國戚外,沒有與之有共同利害關(guān)系之人。另一方面由于中國選官制度是科舉制度,使得下層人士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jìn)入國家官員系統(tǒng)。皇帝“一人在上萬人在下”使之不能與眾人為敵,只得“愛民如子”,平民百姓特別是讀書之人信奉“學(xué)而優(yōu)則士”,士又需忠于其君。所以在古代中國,階級(jí)對(duì)立之勢(shì)終未構(gòu)成。梁漱溟對(duì)中國社會(huì)階層的分析,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斷言“(中國)經(jīng)濟(jì)上未構(gòu)成剝削被剝削兩面,政治同樣未構(gòu)成統(tǒng)治被統(tǒng)治之兩面”,這顯然與主流認(rèn)識(shí)不符,但中國社會(huì)階級(jí)對(duì)立之勢(shì)確實(shí)不如西方社會(huì)那般嚴(yán)重,用“職業(yè)分途”來代替“階級(jí)對(duì)立”也無不妥。
第讓他,倫理本位與職業(yè)分途彼此順益交相為用。梁漱溟認(rèn)為,一方面由于社會(huì)組織之倫理化,使經(jīng)濟(jì)上趨于分散不趨于集中,趨于消費(fèi)本位不趨于生產(chǎn)本位,階級(jí)對(duì)立不成,助成職業(yè)分途。此外,倫理化的社會(huì)還造成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橫向平面發(fā)展,而不是縱向?qū)αl(fā)展,“彼此不是宗族便是姻親,不是姻親便是鄉(xiāng)里世好。”這就很難形成階級(jí)社會(huì),而是順成職業(yè)社會(huì)。另一方面,由于社會(huì)職業(yè)分途,土地及資本不易集中,社會(huì)上多是些小農(nóng)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營其業(yè)。小農(nóng)基本全靠一家人共同努力,自然形成“相依為命”的樣子;小工學(xué)徒與東家?guī)煾狄嗍浅ο嗵帲哺士喙不茧y,彼此深相結(jié)納;小商各地奔走,倒賣貨物,也是與人交善。所以導(dǎo)致社會(huì)各職業(yè)內(nèi)倫理關(guān)系更加密切,凡事講情義,而不是西方社會(huì)勞資雙方相維以利,相脅以勢(shì),遇事依法解決,彼此不發(fā)生私人感情。梁漱溟還認(rèn)為,政治經(jīng)濟(jì)兩面也是互為影響,協(xié)調(diào)一致,以共成此局。他說:“由政治上無階級(jí),自不容許經(jīng)濟(jì)上有階級(jí);經(jīng)濟(jì)上之壟斷不成,政治上之壟斷亦不能有;互為因果。”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梁漱溟并不是一個(gè)至少不是一個(gè)完全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但這并不影響他從社會(huì)構(gòu)造層面和社會(huì)階層層面得出中國是一“倫理本位,職業(yè)分途”的社會(huì)。在梁漱溟看來,社會(huì)構(gòu)造是文化的骨干,其他只不過是皮肉,“若在社會(huì)構(gòu)造上,彼此兩方差不多,則其文化必定相近;反之,若社會(huì)構(gòu)造彼此不同,則其他一切便也不能不兩樣了。”他按照社會(huì)構(gòu)造的不同將世界文化分為三大類型:個(gè)人本位文化———英美等國;社會(huì)本位文化———蘇聯(lián)等國;倫理本位文化———中國。如上文所述中國社會(huì)以倫理組織,是一“倫理本位”的社會(huì)構(gòu)造,所以其文化自然是“倫理本位”文化。何謂本位?本位即重點(diǎn),個(gè)人本位重點(diǎn)在個(gè)人,社會(huì)本位重點(diǎn)在社會(huì),倫理本位重點(diǎn)在倫理關(guān)系中之對(duì)方。
二、中國“倫理本位”文化的二重性
“倫理本位,職業(yè)分途”是中國社會(huì)構(gòu)造的基本特征,這一特點(diǎn)導(dǎo)致了中國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國文化以“倫理情誼,人生向上”見長(zhǎng),另一方面又因“倫理本位”而缺乏“科學(xué)技術(shù),團(tuán)體組織”。
第一,崇尚“倫理情誼,人生向上”是中國“倫理本位”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梁漱溟看來,“倫理本位”的社會(huì)構(gòu)造使得中國特別崇尚“倫理情誼”,彼此能夠出于“仁愛之情”和“是非之義”自動(dòng)承認(rèn)旁人,而不是像西方民主社會(huì)那樣為外力所迫。例如在倫理社會(huì)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財(cái)產(chǎn)是不分的,分則被視為背理,是曰“共財(cái)之義”。即使父母不在,兄弟分財(cái),也是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財(cái)于貧者,是曰“分財(cái)之義”。“通財(cái)”適用于親戚朋友之間,原則上是要償還的。但遇到某一機(jī)會(huì),如救濟(jì)孤寡貧乏,施財(cái)便是一種義務(wù)。正如梁漱溟所指出,中國人情感抬頭,欲望置后。其實(shí)中國人原本并不排斥欲望,只因“因情而有義”“其情益親其義益重”,導(dǎo)致義務(wù)觀念抬頭,“慈母每為兒女而忘身,孝子亦每為其親而忘身。夫婦間、兄弟間、朋友間、凡情感厚底處處替對(duì)方設(shè)想,念念以對(duì)方為重而放輕自己。”梁漱溟把這種以對(duì)方為重的人生態(tài)度稱為“人對(duì)人”的態(tài)度,并認(rèn)為它要優(yōu)于西方以“人對(duì)物”的態(tài)度來對(duì)待人。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是發(fā)端于西方社會(huì),這與他們以自我為中心,不尊重旁人的文化不能說不無關(guān)系。此外,“職業(yè)分途”的社會(huì)促使每一中國人都有創(chuàng)造其自己前途的機(jī)會(huì),“人生向上”便成了中國文化的又一大優(yōu)良傳統(tǒng)。不像在西洋階級(jí)社會(huì)里,經(jīng)濟(jì)上政治上機(jī)會(huì)都為一部分所壟斷,只有革命才能開拓自己的命運(yùn)。用梁漱溟的話說就是西洋是“向外用力”,而中國則是“向內(nèi)用力”。他以一個(gè)讀書人為例,“一個(gè)讀書人,通常是在考試制度之下決定他的前途。得失成敗,全看自己如何……你只有回環(huán)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責(zé)怨,自鼓舞,自得,自嘆……”其他行業(yè)雖無考試制度,亦有“行行出狀元”“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之說。所努力者,也不是一己之事,而是為了全家老少,為了光大門庭,為了積德積財(cái),以遺子孫等。所以梁漱溟認(rèn)為中國人雖是無宗教之人生,但中國人為了完成目標(biāo),用其畢生精力,精神上是有所寄托的。立志、要強(qiáng)、勤儉、有志者事竟成……等優(yōu)秀傳統(tǒng)無不體現(xiàn)“人生向上”的生活態(tài)度,這也是中華民族一直延續(xù)至今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第二,缺乏“科學(xué)技術(shù),團(tuán)體組織”是中國“倫理本位”文化的最大偏失。首先,梁漱溟在《命運(yùn)》中以中西醫(yī)為例來說明中國學(xué)問不能自己解釋自己,不是科學(xué)之路。在他看來,凡是學(xué)問都有其方法與眼光,而不在乎得數(shù)。與西醫(yī)以身體為研究對(duì)象不同,中醫(yī)以生命為研究對(duì)象,中醫(yī)切脈著意整個(gè)生命,而不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從這一點(diǎn)說,中醫(yī)是有其獨(dú)特方法與眼光的,能算是一門學(xué)問。但無奈普通中國醫(yī)生只會(huì)運(yùn)用古人得數(shù),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醫(yī)不能算是一門科學(xué),科學(xué)都是數(shù)字化精確化的,中醫(yī)卻常常是囫圇不分的。以咳嗽吐血發(fā)燒為例,西醫(yī)將病與癥分開,著眼于癥的精確觀察,而中醫(yī)將這些通通看作病,其實(shí)這只是病的癥候而已。西醫(yī)能發(fā)現(xiàn)病菌,中醫(yī)則未能,原因恐怕在于此。梁漱溟指出中西醫(yī)學(xué)上的不同,實(shí)可以代表一切中西學(xué)術(shù)不同:西醫(yī)走科學(xué)之路,中醫(yī)走玄學(xué)之路,“一面的根本方法與眼光是靜的、科學(xué)的、數(shù)字化的、可分的。一面的根本方法與眼光是動(dòng)的、玄學(xué)的、正在運(yùn)行中不可分的。”
至于這兩條路誰更高明,梁漱溟認(rèn)為最終中國的方法會(huì)占優(yōu)勝,但無奈現(xiàn)在還不能說明自己,只能待西醫(yī)慢慢進(jìn)步、轉(zhuǎn)變來解釋中醫(yī),并最終將中醫(yī)收容進(jìn)來。其次,梁漱溟以歐洲中世紀(jì)社會(huì)對(duì)照出中國社會(huì)之缺乏集團(tuán)生活,或團(tuán)體組織。歐洲中古封建社會(huì)團(tuán)體生活表現(xiàn)在宗教、政治、經(jīng)濟(jì)等方方面面,“教會(huì)之于教徒,好比今日國家之于國民,宗教彼此間對(duì)抗相爭(zhēng),較之今日國際間還要激烈。政治上則有大大小小無數(shù)封建單位,并且政治與宗教牽混糾纏,更增加了團(tuán)體間之對(duì)抗相爭(zhēng)。經(jīng)濟(jì)上則一農(nóng)村就是一團(tuán)體……還有工商業(yè)集中在都市,每一都市,也是一團(tuán)體……凡此種種,皆為中國所無。”梁漱溟將后來西方社會(huì)個(gè)人主義抬頭歸因于中古社會(huì)嚴(yán)重的團(tuán)體生活,認(rèn)為前者是后者的反動(dòng),因?yàn)椤岸窢?zhēng)與團(tuán)體相聯(lián),和平與散漫相聯(lián)”。而中國是缺乏集團(tuán)生活的,有宗教卻沒有組織嚴(yán)密彼此抗?fàn)幍慕虝?huì),有鄉(xiāng)自治卻無市自治。由于無個(gè)人對(duì)抗團(tuán)體之必要,就導(dǎo)致了后來個(gè)人的隱沒;又由于缺乏團(tuán)體生活的鍛煉,導(dǎo)致了中國人缺少紀(jì)律習(xí)慣、組織能力、法治精神等。
三、中國新文化的未來走向
梁漱溟以社會(huì)構(gòu)造為基點(diǎn)、以中西文化比較為視角分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質(zhì),并明確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優(yōu)勢(shì)和不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未來走向的問題上,梁漱溟提出要“發(fā)揮中國的長(zhǎng)處以吸收外國的長(zhǎng)處”。第一,以中國精神引進(jìn)團(tuán)體組織。一是以固有“倫理情誼”之精神適用于團(tuán)體與個(gè)人之間。梁漱溟認(rèn)為中國不是缺乏自由民主,而是缺乏進(jìn)步的團(tuán)體組織。對(duì)于近代以來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shí)分子一直希圖將西方的自由主義、個(gè)人主義、權(quán)利觀念等現(xiàn)代性觀念引入中國的做法,梁漱溟并不贊同。相反,他認(rèn)為引入自由主義等觀念對(duì)中國來說是藥不對(duì)癥,因?yàn)橹袊幌裎鞣皆粓F(tuán)體干涉過甚。對(duì)于缺乏團(tuán)體生活的中國來說,真正需要的恰恰不是個(gè)人主義之離心力,而是團(tuán)體生活之向心力,這樣才能治中國“散漫”之病。但如果過于抬高團(tuán)體以壓個(gè)人的結(jié)果便是專制和統(tǒng)制,專制和統(tǒng)制又將會(huì)加重中國老百姓的“被動(dòng)”之病。在梁漱溟看來,只有將“倫理情誼”之精神來適用于團(tuán)體與個(gè)人之間才能同時(shí)治“散漫”“被動(dòng)”之病。因?yàn)閭惱砭裨谟谧鹬貙?duì)方,適用于團(tuán)體與個(gè)人之間,即是團(tuán)體要尊重個(gè)人,個(gè)人要尊重團(tuán)體。這樣既使中國人從散漫入組織,又使中國人從被動(dòng)變主動(dòng),一個(gè)民主的團(tuán)體生活便實(shí)現(xiàn)了。二是以“人生向上”精神引入團(tuán)體組織。不管是社會(huì)團(tuán)體還是作為國家機(jī)構(gòu)的地方自治團(tuán)體,其目的都是為了團(tuán)體內(nèi)民眾謀福利,只不過福利不同罷了。西方社會(huì)團(tuán)體組織比中國多,公共福利觀念就比中國強(qiáng)。福利不能不要,但身在大大小小的團(tuán)體中的個(gè)體眼里不能只有福利,那樣會(huì)造成懶惰。所以梁漱溟認(rèn)為,應(yīng)該將“人生向上”的中國精神引入團(tuán)體,福利應(yīng)該隸屬“人生向上”之內(nèi),“向上精神提振起來,則地方公益自然興辦,福利自然實(shí)現(xiàn)”。
第二,以團(tuán)體組織運(yùn)用科學(xué)技術(shù)。團(tuán)體組織和科學(xué)技術(shù)在西方各自發(fā)展得都很好,但梁漱溟認(rèn)為二者在西方的配合卻很糟。在西方,一切新技術(shù)的發(fā)明都是資本家私人占有,而不是掌握在社會(huì)公共手里。這就導(dǎo)致新技術(shù)帶來的經(jīng)濟(jì)利益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權(quán)力都?xì)w資本家所有。團(tuán)體組織(此處指國家)雖有進(jìn)步,但也為其所左右。所有內(nèi)部演化為階級(jí)斗爭(zhēng),外面則演化為民族斗爭(zhēng),本民族和其他民族都深受其害。為避免這一錯(cuò)誤,中國文化建設(shè)該如何呢?梁漱溟提出,以團(tuán)體組織引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這樣技術(shù)所帶來的利益自然歸于公共所有。在此,他以農(nóng)村養(yǎng)蠶為例,提倡蠶農(nóng)組織合作社,實(shí)行生產(chǎn)合作。這樣“要采用任何一新技術(shù)一新設(shè)備總非合作社辦不了。甚至需要合作社的聯(lián)合才行。技術(shù)越進(jìn)步,越需要大聯(lián)合,而后乃能采用……如是技術(shù)隨組織而來,即是技術(shù)操于組織之手,一切好處自然歸公。”國家也一樣,利不集中,權(quán)亦不集中,這樣從小范圍到大范圍,從國內(nèi)到國外,都是和平安定的。在《中國文化的命運(yùn)》中,梁漱溟深刻分析了中國文化的特點(diǎn),并指出了中國未來文化的走向。他不僅建構(gòu)理論,而且在實(shí)踐中親身投入到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yùn)動(dòng)中。不管其實(shí)踐結(jié)果如何,其憂國憂民的情懷和九死一生的探索精神,值得中國每一位知識(shí)分子學(xué)習(xí)。用他自己對(duì)自己的評(píng)價(jià)就是:一個(gè)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dòng)的人。
作者:陳文劍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