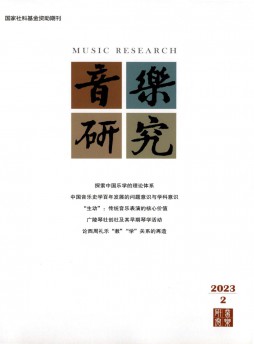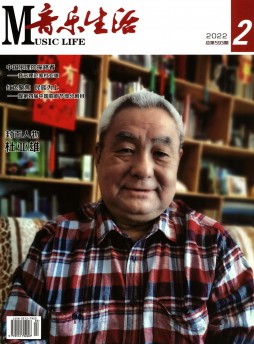音樂學科分類情況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音樂學科分類情況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提要:通過對音樂美學學科的動態考察,本文認為音樂美學不再是音樂學和普通美學的分支,也不是它們的交叉,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
關鍵詞:音樂美學學科歸屬
1964年,意大利音樂美學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要寫一部《西方音樂美學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esthetics),他碰到的首要問題是音樂美學到底是什么,音樂美學到底能否歸屬于一般美學。他說:
音樂美學對我們來說含義是什么?試圖在一種有關音樂的美學與思考藝術和美的更加普遍的背景當中所理解的美學之間加以區分是合理的嗎?在這個領域當中音樂需要一個與其他音樂藝術形式不同的對待嗎?[1](p1)
而此時,起源于德國的音樂美學在西方已經走過整整180年的歷程。1784年,德國詩人、音樂理論家舒巴特(C.F.D.Schubart,1739-1791)在《關于音樂美學的思想》(IdeenzueinerAsthetikderTonkulst)一文中提出了AsthetikderTonkulst這個詞。一般人都把這篇文章的發表看成是“音樂美學”作為一門現代意義上學科出現的標志。
無獨有偶,1982年,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威廉·奧斯丁(WilliamW.Austin,1920-2000)在翻譯德國音樂學家卡爾·達爾豪斯(CarlDahlhaus,1928-1989)的Musik鋝thetik這部書時,徑直將書名譯作AesthetiesinMusic,他在前言中寫道:
在德語世界中,可以將兩個原本已經非常模糊和抽象的詞匯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Musik鋝thetik——達爾豪斯教授此書的書名。德語讀者似乎用不著去追問達爾豪斯,他論述的究竟是“音樂的一種美學”,還是“音樂的權威美學學說”,或是“某些音樂的某些有意思的美學”,還是“所有音樂的美學理論”。此書的譯者可以將此書書名擴展成諸如“對歐洲音樂的主要美學理念的系統性綜述和歷史性批判”之類的東西,但這簡直不象個書名!我干脆將其直譯成《音樂美學》(EstheticsofMusic),與原著Musik鋝thetik靠近。[2](p3-4)
威廉·奧斯丁試圖用AestheticsofMusic這一個英文詞來消除非德語世界的讀者由Musik鋝thetik一詞可能產生的歧解,似乎并沒有取得什么實質性效果。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音樂美學研究對象的界定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直到今天,人們對于音樂美學的認識,依然十分模糊。正如達爾豪斯(1980年)所說:“音樂美學,至少在現在,并不是一個普遍被認可的常規學科。”[2](p2)伊沃·蘇皮契奇(IvoSupicic,1928-)說:“許多音樂史家否定音樂美學部分地是由于他們有時可能把某些寄生的美學文獻與真正的音樂美學混淆了。”[3](p17)
1991年,《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編輯部發表短評,提出對音樂美學的基礎理論進行研究,主要包括:“方法問題、對象問題、哲學基礎問題以及本體論問題。”[4]本文試圖將學術界有關音樂美學學科屬性的各種觀點分類列出,分析它們各自的立論根據,最后將這些爭論融入音樂美學學科發展的進程中,結合時代的特點,從動態的角度考察音樂美學的學科歸屬問題。
一、關于音樂美學的學科歸屬,學界大概有以下四種不同的觀點。
情感作用中脫離出來的形式,他就是一個形式主義者……”。[6](p55)卡爾·轉載自論文先生網,請保留此標記達爾豪斯說:“席勒的音樂經驗毫不貧乏,也是在意識到要試圖構思自己的美學系統就必須考慮到音樂美學時才開始對音樂理論感興趣的。”[6](p43)“散見于席勒論著中不多的音樂美學思考不是獨立的,而是與論證相結合在一起的,其目標遠離音樂。”[6](p43)恩里科·福比尼也注意到席勒的音樂美學與哲學系統之間有緊密的聯系。[1](p213)
文藝美學。文藝美學與生活美學并列,從屬于美學。”[9](p4)于潤洋說:“音樂美學作為一般的美學的一個分支,是從音樂藝術總體的高度研究該藝術不同于其他藝術門類的特殊本質的基礎理論學科。”[10](P124)我們姑且不論這種類分與類從是否準確,但我們必須強調,完全歸屬于哲學和普通美學,音樂美學就會喪失自己的特點和立場。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前蘇聯音樂美學家的偏失中得到些許警示。克林列夫說:“音樂美學(跟其他的藝術美學一樣)的基本問題,當然是藝術作品中思維對存在的關系問題。什么是第一性的——現實還是音樂?音樂是現在人意識的反映呢,還是與現實無關的人類心靈的流露?唯物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現實是第一性的,音樂表現人對這一客觀的、存在于人類意識之外的現實世界的關系。而唯心論的回答是:音樂是第一性的,它的本質不是客觀,而是主觀,是人類的體驗和思想本身的表現。”[11](pp.7-8)我們看不出克林列夫所論的音樂美學與唯物論哲學之間有什么不同。
這種極端的傾向,自然要受到音樂美學家們的反對。伊沃·蘇皮契奇認為,把音樂美學與純哲學知識贊同起來是錯誤的。[3](p19-23)恩里科·福比尼說得稍微委婉一些:“如果我們接受羅伯特·舒曼所聲稱的‘美學原則在每一種藝術中都是一樣的,只有材料是不同的’,我們也許就不會試圖寫這樣一本書(《西方音樂美學史》)了。”[1](第1版前言,p1)隨后,他還批評了將音樂美學泛化為一般哲學的傾向:“如果我們把音樂美學狹義地界定為對音樂的系統的哲學考察,可以公平地說,它現在正處于彌留之際。”[1](p423)赫爾曼·克雷茲施馬爾(HermannKretzschmar)曾試圖將“音樂美學”和“哲學美學(PhilosophonAesthetik)”作區分,以抵制那些脫離實際的哲學思辨。
一種觀點認為,音樂美學是音樂學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3](p16)阿曼德·馬查貝(ArmandMachabey)把音樂學定義為:研究、系統闡述和解決與音樂史、它的美學和音樂自身以各種各樣形式表現的問題。[3](p15)蕭友梅說:“樂學是研究音樂的科學,我已經說過了。我們大概可以分開五方面去研究他。若是依著研究科學的方法排列起來,當然第一是聲學,第二是聲音生理學,第三是音樂美學,第四是樂理(狹義的樂學),第五是音樂史。”[5](p104)于潤洋說:“音樂美學同時也是音樂學的一個子學科。”[10](P124)
評論的一般是音樂圈外人,即律師、神學家或作家,這就標志著技術判斷與審美判斷之間形成的差別程度:技術是專家們的事,而公眾覺得要對審美上的事情負有責任,其代言人是起著批評家作用的音樂圈外人。”[6](P7)
一種觀點認為,音樂美學是音樂學與美學的交叉學科:
顧名思義,音樂美學就其性質來說,既可說是用美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音樂的美和審美的部門美學,又可說是音樂學中側重于研究音樂藝術基本規律與特征的一門基礎性的音樂理論學科。音樂美學的這種雙重屬性,說明它是美學與音樂學之間的一門交叉學科,它的特點在于美學與音樂學的結合。一方面,音樂美學作為美學的一個分支,需要從美學的角度來研究音樂藝術中的美學問題,使自己成為藝術哲學——美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音樂美學又是音樂學的一個部門。[12](PP.267-268)
為了不偏向音樂,也不偏向美學,汪森提出了一種折中的看法:“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應牢牢鎖定音樂,但研究方法及其最終所表現出來的學術形態應為美學或哲學理論。”[13](p78)有人擔心這種說法會導致將音樂美學看作是音樂與美學簡單的相加。茅原說:“這個新的質不能離開音樂和美學這雙重屬性,音樂屬性與美學屬性都是音樂美學的不可被代替的本質屬性。離開了音樂,那就是一般美學,離開了美學,就談不到是音樂美學。”[14](P2)
一種觀點認為,音樂美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伊沃·蘇皮契奇認為,在“承認音樂美學在關于音樂知識的整體中的地位——一種地位,以超出音樂學學科自身的這個定義,考慮在音樂的美學理解中哲學思辨的重要性”的條件下,“音樂美學也是一個學術學科。”[3](p15)修海林、羅小平:“我們認為,就中國音樂美學這一門獨立學科研究而言,是以音樂的存在和音樂美的存在為對象的。”[15](p66)茅原說:“音樂美學這個學科,以專門研究音樂而區別于一般美學,以對音樂進行哲學美學思考而區別于一般音樂學。”[14](P1)
二、在討論音樂美學學科歸屬這一嚴肅的課題時,我們并不想輕率地表示支持哪一類觀點。但我們必須明確,已經用過的兩種方法絲毫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種是語言學的方法,即從語言結構的層面來說明音樂美學的學科歸屬。“音樂美學”在德文中是一個合成詞Musik鋝thetik,在英文中也是個合成詞AesthetiesinMusic。用中文表述的“音樂美學”既可看作是“音樂的美學”,也可以看作是“音樂和美學”。如果是前者,音樂美學就是美學的分支;如果是后者,音樂美學就是音樂和美學的交叉。這樣的分辨,實在沒有什么學術意義。一種是靜止的學科分析方法。如果我們截取康德、謝林、席勒、黑格爾等人的音樂美學來定性,音樂美學自然是普通美學體系中的一個分支;但如果我們截取李斯特(FranzLiszt,1811-1886)的音樂美學來定性,音樂美學又成為音樂學的一個部分。
從這一場持久的爭論中,我們得到一個啟示,只有將學科放到動態的進程中進行全面考察,才有可能揭示學科真正的歸屬,并進一步明確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這種嘗試,見于卡爾·達爾豪斯的理論中。與一些片面的觀點不同,卡爾·達爾豪斯的觀點包含了更多的歷史辯證法。首先,他追述了哲學音樂美學的淵源。他說:
18和19世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和音樂的關系——尼采除外——所表現出的特點是音樂經驗、哲學認識和音樂史作用之間極為不恰當的比例。音樂經驗貧乏比如康德和謝林,或囿于成見比如黑格爾和叔本華,都沒有阻礙哲學——迫于一定程度的系統壓力——獲得對音樂美學的認識,這些認識首先是被音樂家反抗,最后被接受和‘過渡’到觀念中,有時甚至是‘進入’到音樂的觀念中。[6](P180)
古典典美學的完善》(《藝術的文化功能》,卷I,柏林,1931,第19頁)說道:
音樂與哲學的關系在有突出成效的階段期間本應該引起史學家們的注意,因為這種關系的表現,即美學,可以理解為以哲學為基礎的音樂史現象。從哲學的癥結所在而引申出來的音樂美學,作為音樂觀對音樂在文化系統中進行了重新定位,它作為音樂思想不僅從哲學中借用概念,而且本身就是哲學。成熟的哲學狀態與特有的藝術家的創造力不謀而合,這一歷史事實是美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的前提,甚至是美學作為一個哲學癥結的前提,因為美學必定要與哲學的中心問題從根本上聯系在一起,才能成為哲學學科。[6](P28)
學科是一個教育學的概念,它是依據一定的教學理論組織起來的科學基礎知識的體系。[16](p434)學科萌芽于人類教育實踐中。在中國,西周中期就形成了以禮樂為中心的學科體系,當時的教育由六門學科組成:禮、樂、射、御、書、數。周代的大司樂還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到漢代,大司樂分為太樂和樂府兩個部門。太樂署主要掌管雅樂,樂府負責收集民間音樂。在中國,音樂理論與音樂表演相對獨立。音樂理論與天人合一的哲學體系長期共存,以哲學和政治倫理學的形式對音樂表演的形式和內容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這點與卡爾·達爾豪斯的理論十分契合。《幸福園》中的哲學女神的左邊寫著:“七股智慧的清泉來自哲學,它被稱為自由藝術”;右邊寫著:“圣靈是七門自由藝術的創造者——語法、修辭、辯證法、音樂、算術、幾何、天文。”[17](p55)六藝和七藝是最早的學科的模型。在古希臘學者的眼中,哲學是一切認知的完成者,是所有學科的鋪路人。在中世紀神學家眼中,自由藝術的創造者是圣靈。
真正的學科體系,卻是市民大學與市民教育興起的產物。卡爾·達爾豪斯說:
從整體上看,音樂美學體現了有文化教養的中產階級音樂愛好者的精神(音樂美學遭到詆毀,此轉載自論文先生網,請保留此標記即部分原因所在),它起源于是18世紀,但在20世紀面臨解體。19世紀音樂美學的基本觀念(音樂美學主要是一個19世紀的現象)認為,思考音樂、談論音樂和實踐音樂一樣重要,合格的聆聽必須具備哲學和文學的前提。[2](p1)
在理性主義的學術氛圍中,音樂美學逐漸獲得獨立的地位。恩里科·福比尼說:
浪漫主義后期達到了完全的成熟。[1](第一版前言,p3)
毫無疑問,18世紀以后的音樂,已經走出了純粹的哲學知識的范圍之外,成為音樂科學的一部分。19世紀以來,人們沿著音樂美學的重要問題進行追溯,發現起源于18世紀現代音樂中的許多美學思想,一直都潛伏在源遠流長的音樂文化中。于是,音樂美學順著時間的隧道前后摸索,勾畫出音樂美學在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的軌跡,并試圖超越音樂本身,與音樂學之外的其他學科進行對話。這一階段的音樂美學,已經是“既包括科學又包括哲學的音樂美學”了。[3](p16)
我們討論音樂美學的歸屬,還有一個隱性的目的,那就是試圖回答這樣一些問題:音樂美學究竟要走向哪里?將以什么樣的面目在未來呈現?正如恩里科·福比尼在《西方音樂美學史》的十一章所提出的“未來會怎樣”:
音樂美學將走向哪里?音樂美學仍然以任何有意義的觀念形式出現嗎?是否音樂美學具有像規律一樣的真實性呢?[1](p422)
我們不可能單純地在哲學范圍內回答這些問題。人類已經走出了含混的哲學時代,經過了實證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洗禮,哲學的方法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但哲學的結論不能再作為我們演繹的基礎。我們也不可能單純在音樂學的范圍內回答這些問題。學科劃分越來越細,整體的知識一再被切分到不可知的地步。于潤洋指出音樂史學和音樂美學領域存在學術視野過于狹窄的問題,他說:
音樂學與其它相關人文學科之間,音樂學各子學科之間、甚至子學科的內部相互疏離甚至隔絕的現象相當普遍。僅以我比較熟悉的音樂史學和音樂美學領域為例,音樂史學缺乏對當代中外史學理論的關注;在對中國的和西方的音樂歷史研究之間缺乏相互溝通,甚至在中國的或西方的音樂歷史研究中,將古代和近現代相互分割,忽視整體性研究。而相似的情況,在音樂美學領域中,在不同程度上同樣存在。
音樂學必須闖開大門,回到它作為人文學科的本質,[19](p6-13)而音樂美學正是音樂學回歸于人文的一個絕好的窗口。我們更不可能在哲學與音樂學的雙重范圍內來解決音樂美學要面臨的問題。在音樂美學發展歷程中,要么是哲學思辨,要么是音樂經驗,純粹的音樂學與純粹的美學之間幾乎沒有出現過重疊。我們甚至不可能在18世紀以來的音樂美學傳統中回答這些問題。恩里科·福比尼和卡爾·達爾豪斯等人的探索必須得到尊重,根據他們的看法,18世紀以來的音樂美學觀點已經深深地藏在以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公元前580-前500)、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傳統中并且持續影響至現當代。我們也不必拘泥于中國音樂美學自20世紀初就打上的德國學派的印記,在西方不斷向古希臘智慧乞靈時,中國音樂美學也應該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追溯源頭,東西方共同的智慧,可以更大地擴大我們的視野。
宋瑾曾經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音樂美及其相關’是一座房子,持各種態度的人們分別從‘哲學之門’、‘美學之門’或‘科學之門’進入,中國學者的做法亦如此,定義表述雖各有不同,在對象的約定上卻仍是‘音樂美及其相關’這座房子,定義表述的不同只是對同一個對象的不同取景。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即如是。”[20](p35)我們套用這個比喻,音樂美學是一條寬廣淵深的河流,它曾經一度從美學、科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大河里取水,但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河床,就將澆灌自己的園地,不可能再回到其源頭。因此,我們以學科發展的動態視野來看,音樂美學從夾縫中走出來,獨立直面了大量的課題,既不可能重歸于哲學,也不可能拘囿于一般意義上的音樂學,更不會是哲學與音樂學的交叉。音樂美學已經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盡管還有待成熟,但它一直處在永無終結的進程中。
擴展閱讀
- 1音樂情緒在音樂賞析中的表現
- 2傳統音樂和民族音樂
- 3音樂欣賞
- 4現代音樂爭
- 5音樂欣賞
- 6西方音樂作品音樂學探究以及音樂技術分析
- 7音樂主題旋律
- 8音樂舞蹈
- 9音樂美學思想
- 10教會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