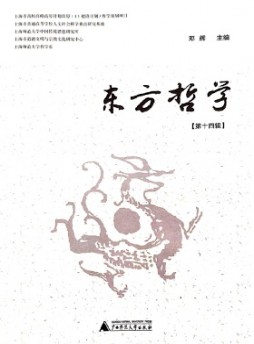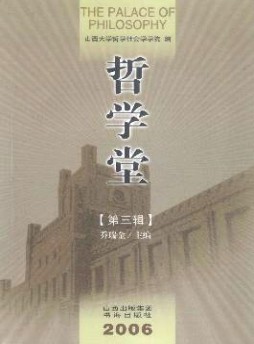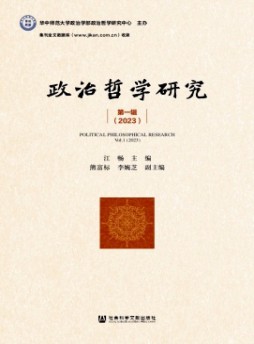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中國(guó)語(yǔ)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中國(guó)語(yǔ)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90年代以來(lái),“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兩個(gè)概念經(jīng)常混用,學(xué)術(shù)界、學(xué)術(shù)管理部門(mén)與各級(jí)政府部門(mén)仍在不加區(qū)分地使用這兩個(gè)概念。實(shí)際上“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是學(xué)術(shù)管理部門(mén)使用的概念,在當(dāng)時(shí)體現(xiàn)了建國(guó)后的50年代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的特征,而“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是現(xiàn)代科學(xué)共同體使用的學(xué)術(shù)概念,是科學(xué)共同體的內(nèi)部學(xué)科分類(lèi)意識(shí)的體現(xiàn)。這兩個(gè)概念指稱(chēng)的對(duì)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場(chǎng)域的概念雙軌現(xiàn)象就產(chǎn)生了。這種概念雙軌現(xiàn)象是不同場(chǎng)域內(nèi)部不同邏輯運(yùn)作的結(jié)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場(chǎng)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場(chǎng)域?qū)崿F(xiàn)他場(chǎng)域的異地統(tǒng)治會(huì)產(chǎn)生概念的場(chǎng)域危機(jī),從而引發(fā)學(xué)術(shù)管理部門(mén)與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緊張關(guān)系,但學(xué)術(shù)管理部門(mén)以及許多學(xué)者不加區(qū)別地混用這兩個(gè)性質(zhì)不同的概念,這種概念生態(tài)混亂的情形是到了歷史反思的時(shí)候了。概念生態(tài)的混亂的一個(gè)主要表現(xiàn)就是沒(méi)有注意到當(dāng)代中國(guó)語(yǔ)境中的概念雙軌現(xiàn)象,也沒(méi)有概念意識(shí)。
當(dāng)前中國(guó)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面臨的一個(gè)主要問(wèn)題就是對(duì)所使用的概念沒(méi)有明確的概念意識(shí)。所謂概念意識(shí),就是對(duì)概念產(chǎn)生的社會(huì)背景與概念基本內(nèi)涵進(jìn)行分析,并注意其適用的范圍與概念自身的變化及其與社會(huì)的互動(dòng)。長(zhǎng)期以來(lái),中國(guó)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界的概念意識(shí)是不強(qiáng)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適和魯迅都談到了這個(gè)問(wèn)題。胡適在1920年的《提高與普及》的演講中說(shuō):“現(xiàn)在所謂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實(shí)在說(shuō)得痛快一點(diǎn),就是新名詞運(yùn)動(dòng)。拿著幾個(gè)半生不熟的名詞,什么解放、改造、犧牲、奮斗、自由戀愛(ài)、共產(chǎn)主義、無(wú)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1]胡適對(duì)這種低層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對(duì),主張對(duì)新名詞進(jìn)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適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個(gè)大弊病》一文中也說(shuō):“名詞是思想的一個(gè)重要工具。要使這個(gè)工具確當(dāng),用的有效,我們必須嚴(yán)格的戒約自己:第
一、切不可亂用一個(gè)意義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2]
而魯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開(kāi)頭就說(shuō):“中國(guó)文藝界上可怕的現(xiàn)象,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并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于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jiàn)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chēng)之為表現(xiàn)主義;多講別人,是寫(xiě)實(shí)主義;見(jiàn)女郎小腿肚作詩(shī),是浪漫主義;見(jiàn)女郎小腿肚不準(zhǔn)作詩(shī),是古典主義。”[3]魯迅說(shuō)的雖然是文藝界的情況,但對(duì)于學(xué)術(shù)界來(lái)說(shuō),概念意識(shí)同樣重要。鄧正來(lái)也曾指出,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知識(shí)界對(duì)“建構(gòu)者與被建構(gòu)者”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了某種集體不意識(shí),也就是中國(guó)學(xué)界對(duì)西方社會(huì)科學(xué)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學(xué)術(shù)概念的集體不意識(shí)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現(xiàn)象,實(shí)際上是學(xué)術(shù)缺少自主性的表現(xiàn)。而“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抽象名詞也存在著鄧正來(lái)所說(shuō)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進(jìn)行胡適所說(shuō)的“分析清楚”的歷史梳理工作。
“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主導(dǎo)的學(xué)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國(guó)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的體制化方式存在。這個(gè)學(xué)科概念的產(chǎn)生受到了蘇聯(lián)學(xué)者30年代學(xué)科分類(lèi)模式的直接影響,在中國(guó)語(yǔ)境中具有學(xué)科性與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的雙重屬性。1966年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取消后,這個(gè)概念仍繼續(xù)使用。1973年,這個(gè)學(xué)科概念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得到空前強(qiáng)化,其學(xué)科性則被遺忘。與此相對(duì)應(yīng)的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共同體自發(fā)形成的“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學(xué)科概念逐漸被遺忘,從而呈現(xiàn)出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概念生態(tài)現(xiàn)象。對(duì)“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演變的歷史分析為重建科學(xué)共同體的學(xué)術(shù)自主性提供了一個(gè)當(dāng)代概念的分析個(gè)案,也有助于建構(gòu)科學(xué)共同體的概念認(rèn)同意識(shí)與概念自主意識(shí)。
一、1955年學(xué)部制與“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體制化
“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國(guó)文獻(xiàn)里是找不到的。據(jù)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來(lái)我國(guó)大學(xué)教育之進(jìn)步》一文中的介紹,國(guó)立北京大學(xué)在民國(guó)十年(1921年)決議成立四門(mén)研究所,即“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國(guó)學(xué)、外國(guó)文學(xué)四門(mén)”。[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請(qǐng)變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個(gè)附件中,也是將“自然科學(xué)院”、“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院”、“教育學(xué)院”、“哲學(xué)院”等作為并列的機(jī)構(gòu)。[6]在50年代以前,中國(guó)的“哲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并沒(méi)有合并在一起。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現(xiàn)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新名詞?通過(guò)部分材料的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gè)新名詞的產(chǎn)生與建國(guó)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蘇聯(lián)化傾向有著直接的內(nèi)在因果關(guān)系。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處處長(zhǎng)的黎澍在《認(rèn)真清理我們的理論思想》一文中說(shuō)到建國(guó)后許多詞語(yǔ)都是由于俄語(yǔ)翻譯而產(chǎn)生的,如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1982年被譯成《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而“資產(chǎn)階級(jí)法權(quán)”、“愛(ài)國(guó)主義”等這些名詞,也都是翻譯未定,已經(jīng)用濫了的詞語(yǔ)。[7]黎澍的意思是說(shuō)對(duì)這些名詞應(yīng)重新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從而重建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理論體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況相類(lèi)似的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詞語(yǔ)也是因俄語(yǔ)翻譯而產(chǎn)生并接受下來(lái)的。
從學(xué)術(shù)意義上說(shuō),學(xué)術(shù)共同體自身是不可能出現(xiàn)“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樣不符合學(xué)術(shù)習(xí)慣的概念的。哲學(xué)運(yùn)用其哲學(xué)方法展開(kāi)具體的學(xué)科研究時(shí),有“政治哲學(xué)”、“文化哲學(xué)”、“經(jīng)濟(jì)哲學(xué)”、“歷史哲學(xué)”、“藝術(shù)哲學(xué)”、“科學(xué)哲學(xué)”等學(xué)科,這些哲學(xué)分支學(xué)科主要是從哲學(xué)角度分別研究政治、文化、經(jīng)濟(jì)、歷史、藝術(shù)、科學(xué)。但是作為一門(mén)學(xué)科,在世界學(xué)術(shù)中從來(lái)沒(méi)有倒過(guò)來(lái)稱(chēng)呼的,如“哲學(xué)政治”、“哲學(xué)文化”、“哲學(xué)經(jīng)濟(jì)”、“哲學(xué)歷史”、“哲學(xué)藝術(shù)”、“哲學(xué)科學(xué)”等,這些名詞作為一個(gè)學(xué)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時(shí),從學(xué)術(shù)自身的邏輯來(lái)說(shuō),也只可能出現(xiàn)“自然科學(xué)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哲學(xué)”這些更大的哲學(xué)學(xué)科的分類(lèi),也就是說(shuō)分別從哲學(xué)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人文科學(xué)。在中國(guó)“自然科學(xué)哲學(xué)”作為一個(gè)學(xué)科主要是指“自然辯證法”。而“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哲學(xué)”這樣的概念在世界學(xué)術(shù)界得到普遍認(rèn)可,但在中國(guó)卻很少提起,因?yàn)?955年有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因俄語(yǔ)翻譯而產(chǎn)生的概念后,“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這個(gè)真正學(xué)科性質(zhì)的概念反而很難產(chǎn)生了。[8]于是一個(gè)獨(dú)特的概念生態(tài)現(xiàn)象就出現(xiàn)了。
從現(xiàn)有出版材料來(lái)看,“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來(lái)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的產(chǎn)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產(chǎn)生情況十分類(lèi)似,都是受到了蘇聯(lián)的影響。據(jù)郭沫若介紹:“‘民族形式’的提起,斷然是由蘇聯(lián)方面得到的示唆。蘇聯(lián)有過(guò)‘社會(huì)主義的內(nèi)容,民族的形式’的號(hào)召。”[9]“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一固定概念同樣也是受到了蘇聯(lián)的啟發(fā)而產(chǎn)生的。1949年11月,中國(guó)科學(xué)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礎(chǔ)上又成立了學(xué)部,正式成立學(xué)部也是受到蘇聯(lián)的影響。竺可楨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記中說(shuō):“從1953年2月去蘇聯(lián)學(xué)習(xí)科學(xué)院的組織后,才決定成立學(xué)部,分為數(shù)理化、生物地學(xué)、技術(shù)科學(xué)及社會(huì)科學(xué)4部門(mén)。籌委會(huì)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體領(lǐng)導(dǎo)機(jī)構(gòu)。”[10]1955年6月1日,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成立大會(huì)在北京召開(kāi),大會(huì)宣告成立四個(gè)學(xué)部:物理學(xué)、數(shù)學(xué)、化學(xué)部;生物學(xué)、地學(xué)部;技術(shù)科學(xué)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并選出了四個(gè)學(xué)部的常務(wù)委員會(huì)。[11]6月2日,中國(guó)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郭沫若作了《在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成立大會(huì)上的報(bào)告》,報(bào)告中說(shuō):“解放以來(lái),我們一直在遵照的指示,進(jìn)行著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別在1952年與1953年之交,中國(guó)科學(xué)家和整個(gè)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進(jìn)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xué)習(xí)。”[12]細(xì)讀郭沫若工作報(bào)告,可以感受到當(dāng)時(shí)學(xué)術(shù)的政治色彩,而“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概念以“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這一體制化的形式出現(xiàn)了。
“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和“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這兩個(gè)概念略有差異,前者是學(xué)科概念,相當(dāng)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個(gè)文科規(guī)劃與管理的機(jī)構(gòu),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執(zhí)行部門(mén)。“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一出現(xiàn)就體制化了,從而具有與生俱來(lái)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特征。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是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詢(xún)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國(guó)家的科技規(guī)劃,而之所以成立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據(jù)曾任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副主任、宣傳部副部長(zhǎng)的龔育之的介紹,是因?yàn)?953年中國(guó)科學(xué)院訪(fǎng)蘇代表團(tuán)回國(guó)后,想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院士制,但是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有些學(xué)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個(gè)先不搞院士,先搞一個(gè)學(xué)部委員的想法。另外,傳統(tǒng)的院士制有一個(gè)特點(diǎn),叫“院士自治”,這樣就可能發(fā)生科學(xué)自治與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之間的矛盾。蘇聯(lián)建國(guó)初期就發(fā)生過(guò)這個(gè)問(wèn)題,后來(lái)花了好大力氣才逐漸解決。同時(shí)也不打算承襲國(guó)民黨時(shí)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爐灶,成立學(xué)部。搞了這么一個(gè)學(xué)部委員的制度,并不是說(shuō)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條件還不成熟。[13]
因此從表面上看,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鑒蘇聯(lián)從事科學(xué)規(guī)劃與管理的經(jīng)驗(yàn),同時(shí)又根據(jù)自己的實(shí)際科學(xué)水平作了一個(gè)折衷的處理,先成立學(xué)部,等科學(xué)水平上去后再實(shí)行院士制。但實(shí)際上根據(jù)李真真的研究,暫不設(shè)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蘇聯(lián)的院士權(quán)力太大;中國(guó)與蘇聯(lián)的情況不同,中國(guó)的科學(xué)家中黨員少,科學(xué)家的思想體系還是舊的,還沒(méi)有完成觀念上的根本轉(zhuǎn)變,這樣很難保證黨的領(lǐng)導(dǎo),保證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甚至有人認(rèn)為提出設(shè)院士是向黨奪權(quán),而設(shè)學(xué)部,其委員的條件及權(quán)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學(xué)界內(nèi)部的需求與黨的政治目標(biāo)的互動(dòng)首先體現(xiàn)在學(xué)部制還是院士制的選擇上,而這種選擇本身既是這種互動(dòng)的結(jié)果又蘊(yùn)含了對(duì)學(xué)部的權(quán)利的限制。[14]在學(xué)部制與院士制的制度選擇上,謝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選舉是學(xué)術(shù)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學(xué)部則是政治干預(yù)學(xué)術(shù),體現(xiàn)了對(duì)科學(xué)家的不信任,其學(xué)部委員是高度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當(dāng)時(shí)負(fù)責(zé)意識(shí)形態(tài)部門(mén)的主要官員都是學(xué)部委員,而延安知識(shí)分子在新意識(shí)形態(tài)建立過(guò)程中往往比高層更左傾。所以從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學(xué)部制標(biāo)志著中國(guó)科學(xué)體制由落后代替先進(jìn)。[15]
由于1955年的蘇聯(lián)科學(xué)院實(shí)行國(guó)際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國(guó)的學(xué)部制,所以“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這個(gè)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學(xué)者的學(xué)科分類(lèi)模式的影響。只是這個(gè)學(xué)科模式在30年代的蘇聯(lián)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國(guó)一直沒(méi)有將這個(gè)學(xué)科模式體制化,到1955年成立學(xué)部時(shí)才具有可能性。不過(guò)這個(gè)概念與中國(guó)科學(xué)院訪(fǎng)蘇代表團(tuán)的制度模仿并沒(méi)有直接的體制繼承關(guān)系。
在1966年“”爆發(fā)時(shí),“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被陳伯達(dá)等人取消,而其他學(xué)部得以保留。后來(lái)物理學(xué)、數(shù)學(xué)、化學(xué)部以及生物學(xué)、地學(xué)部?jī)蓚€(gè)學(xué)部分成了四個(gè)學(xué)部即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部、化學(xué)部、生物學(xué)部、地學(xué)部。由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在十年“”中被取消,但中國(guó)的文科總得有一個(gè)規(guī)劃與管理的機(jī)構(gòu),所以在“”結(jié)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的前身就是原屬于中國(guó)科學(xué)院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由于中國(guó)科學(xué)院是以自然科學(xué)為主的,當(dāng)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機(jī)構(gòu)不再叫“中國(guó)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而是直接叫“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這體現(xiàn)了對(duì)“”中以教條化的哲學(xué)統(tǒng)治科學(xué)的一個(gè)反思與批評(píng),這當(dāng)然是歷史的進(jìn)步,也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執(zhí)政部門(mén)決心改正錯(cuò)誤,逐步實(shí)現(xiàn)學(xué)術(shù)管理的科學(xué)化。1993年10月,經(jīng)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委員改稱(chēng)中國(guó)科學(xué)院院士。不過(guò)這個(gè)時(shí)候,因?yàn)椤罢軐W(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學(xué)與技術(shù)科學(xué)方面的院士,沒(méi)有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方面的院士,而“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也沒(méi)有設(shè)立院士。“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作為一個(gè)體制機(jī)構(gòu)雖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一概念不但沒(méi)有取消,反而得到更為廣泛的使用。從這一特殊的社會(huì)現(xiàn)象也可以看出體制與體制概念的不同社會(huì)意義。
從時(shí)間上說(shuō),為什么偏偏不遲也不早,要在1955年提出這個(gè)概念?這可以從兩個(gè)層面進(jìn)行分析。第一,1955年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形勢(shì)。第二,建國(guó)后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歷史背景。
1955年正好是國(guó)內(nèi)無(wú)產(chǎn)階級(jí)大力批判資產(chǎn)階級(jí)唯心主義思想的一年,特別加強(qiáng)對(duì)哲學(xué)思想的控制,也是知識(shí)分子思想改造運(yùn)動(dòng)繼續(xù)大力開(kāi)展的時(shí)期。
其次,“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產(chǎn)生在當(dāng)時(shí)還有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國(guó)際歷史背景。這個(gè)歷史背景就是建國(guó)后中國(guó)在一段時(shí)期中的蘇聯(lián)化傾向。1949年10月,中蘇友好協(xié)會(huì)總會(huì)召開(kāi)成立大會(huì),總會(huì)長(zhǎng)劉少奇在會(huì)上講話(huà)指出:“我們要建國(guó),同樣也必須‘以俄為師’,學(xué)習(xí)蘇聯(lián)人民的建國(guó)經(jīng)驗(yàn)。”“蘇聯(lián)有許多世界上所沒(méi)有的完全新的科學(xué)知識(shí),我們只有從蘇聯(lián)才能學(xué)到這些科學(xué)知識(shí)。例如經(jīng)濟(jì)學(xué)、銀行學(xué)、財(cái)政學(xué)、商業(yè)學(xué)、教育學(xué)等等。”[16]所以在50年代初期,中國(guó)全方位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這在當(dāng)時(shí)缺少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經(jīng)驗(yàn)的歷史情境中,作為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中國(guó)自然是十分必要同時(shí)也是必須的。
在當(dāng)時(shí)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對(duì)文化教育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
第
一、對(duì)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教育體制的影響。特別是科學(xué)院的設(shè)立與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調(diào)整。張應(yīng)強(qiáng)先生指出,中國(guó)科學(xué)院的模式是學(xué)習(xí)20世紀(jì)50年代蘇聯(lián)科學(xué)院模式的產(chǎn)物。科學(xué)院設(shè)立了一大批實(shí)體研究所,擁有一個(gè)完整龐大的管理層,科層化特征非常明顯,實(shí)際上成為政府的一個(gè)職能部委。[17]在50年代初期,在中國(guó)工作的蘇聯(lián)顧問(wèn)近10000名。在蘇聯(lián)顧問(wèn)的影響下,蘇聯(lián)式的機(jī)構(gòu)和管理方法也被引進(jìn)來(lái)。這種機(jī)構(gòu)變化尤其影響了教育和科研的進(jìn)行。1952年,中國(guó)高等教育進(jìn)行大規(guī)模改組,就是按照蘇聯(lián)的模式,而學(xué)者只好放棄以前熟悉的英語(yǔ),中途改學(xué)俄語(yǔ)。[18]在1952年高校院系調(diào)整中,許多學(xué)科被取消,如撤銷(xiāo)了大學(xué)里所有的社會(huì)學(xué)系。其理由有兩條:一是認(rèn)為社會(huì)學(xué)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學(xué)科,無(wú)產(chǎn)階級(jí)有了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社會(huì)學(xué);二是認(rèn)為社會(huì)問(wèn)題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所特有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根本不存在社會(huì)問(wèn)題……辯證唯物主義者只承認(rèn)有社會(huì)科學(xu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承認(rèn)有什么“社會(huì)學(xué)”。[19]吳國(guó)盛也指出,50年代院系大調(diào)整,將文科理科工科嚴(yán)格分開(kāi),大力發(fā)展理工科,輕視文科。正是從50年代開(kāi)始,社會(huì)上出現(xiàn)明顯的重理輕文思潮。[20]這樣就擯棄了歐美的綜合性大學(xué)模式,采用前蘇聯(lián)單科性的高校模式。就連許多自然科學(xué)學(xué)術(shù)刊物也要受到哲學(xué)思想的控制。如1952年龔育之在《人民日?qǐng)?bào)》上發(fā)表一篇題為《糾正科學(xué)刊物中脫離政治脫離實(shí)際的傾向》,批評(píng)《科學(xué)通報(bào)》忽視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竺可楨于是與郭沫若商議從三卷開(kāi)始,改變辦刊方針,將已付印之稿收回,為此損失了數(shù)千元。[21]
第
二、建國(guó)后在學(xué)術(shù)界用馬列理論改造資產(chǎn)階級(jí)思想,這也是直接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yàn)。蘇聯(lián)十月革命后改革資產(chǎn)階級(jí)思想,中國(guó)作為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在方式上操之過(guò)急,讓知識(shí)分子難以適應(yīng)。對(duì)此,潘光旦在一篇文章中說(shuō)到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上是只能讀馬列的書(shū),其他哲學(xué)的書(shū)不鼓勵(lì)閱讀。潘光旦說(shuō):“在我們中間,有些朋友可能對(duì)原有的大學(xué)還是不夠放心,特別是在思想與理論的傳授上擔(dān)心教授們學(xué)習(xí)不夠,怕他們?cè)诶碚撋铣雎┳樱O誤了下一代的青年。所以在這次課程改革的時(shí)候,一遇到和理論有關(guān)涉的課程,這些朋友所反映的意見(jiàn)便特別審慎。如果有所主張,也好像是在暗示,馬列的理論而外,其他的理論最好能盡量避免。教授們于學(xué)習(xí)馬列的理論以后,當(dāng)然會(huì)對(duì)它們有所批判。”[22]
第
三、蘇聯(lián)的學(xué)科建設(shè)對(duì)中國(guó)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直接影響。在蘇聯(lián),社會(huì)學(xué)和心理學(xué)被認(rèn)為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科學(xué)。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也仿效蘇聯(lián),阻止對(duì)這兩個(gè)領(lǐng)域的研究。自1953年蘇聯(lián)的幾個(gè)心理學(xué)家到北大之后,所有西方的心理學(xué)說(shuō)都被認(rèn)為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只有蘇聯(lián)的學(xué)說(shuō)才可以講授。[23]
因此,在50年代的中國(guó),存在著對(duì)蘇聯(lián)的科學(xué)管理體制與意識(shí)形態(tài)宣傳全盤(pán)接受的現(xiàn)象,對(duì)蘇聯(lián)的理論在當(dāng)時(shí)并沒(méi)有進(jìn)行細(xì)致的分析就被接受下來(lái),而且沒(méi)有很好地與中國(guó)的本土經(jīng)驗(yàn)相結(jié)合,因而理論的教條主義現(xiàn)象十分明顯。
二、1955年“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雙重屬性
從內(nèi)容與性質(zhì)上說(shuō),“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在1955年產(chǎn)生的時(shí)候,這個(gè)概念就具有雙重屬性,即學(xué)科性與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是一個(gè)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主導(dǎo)的學(xué)科概念。首先,我們來(lái)分析這個(gè)概念的直接來(lái)歷和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
曾任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繩對(duì)為什么叫做“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作了一點(diǎn)說(shuō)明。胡繩說(shuō):
“科學(xué),一般說(shuō)來(lái)包括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我們把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放在一起講,但哲學(xué)并不屬于社會(huì)科學(xué),它既和社會(huì)科學(xué)有聯(lián)系,又和自然科學(xué)有聯(lián)系。”[24]
把“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放在一起講,就成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表面上看,“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放在一起講,似乎是兩個(gè)并列的概念,但又不完全是并列的,而是基于并列但又具有從屬性質(zhì)。胡繩的這段話(huà)是典型的蘇聯(lián)的科學(xué)管理觀念。胡繩說(shuō)哲學(xué)并不屬于社會(huì)科學(xué),在學(xué)術(shù)上確實(shí)如此,不過(guò)胡繩也沒(méi)有說(shuō)出后半句話(huà)。也就是說(shuō),從學(xué)科上說(shuō),哲學(xué)當(dāng)然不屬于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是屬于人文科學(xué)的,但是倒過(guò)來(lái),在當(dāng)時(shí)50年代中國(guó)的特定歷史情景中,社會(huì)科學(xué)卻是屬于哲學(xué)并由哲學(xué)來(lái)領(lǐng)導(dǎo)的,社會(huì)科學(xué)的發(fā)展受到哲學(xué)的引導(dǎo)和控制。當(dāng)然,50年代的哲學(xué)是特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xué),實(shí)際上是教條化僵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xué)。
曾任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第二任院長(zhǎng)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馬洪對(duì)為什么叫做“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也作了一點(diǎn)說(shuō)明。馬洪說(shuō):
“因?yàn)檎軐W(xué)是社會(huì)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的綜合科學(xué),所以我們叫‘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25]
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蘇聯(lián)的科學(xué)管理觀念。照馬洪的說(shuō)法,其實(shí)還應(yīng)該有“哲學(xué)自然科學(xué)”的概念。馬洪實(shí)際上點(diǎn)明了在50年代,在中國(guó)不管是社會(huì)科學(xué)還是自然科學(xué)都要受哲學(xué)的引導(dǎo)和改造,這種做法明顯是受到了蘇聯(lián)的直接影響。1955年6月中國(guó)科學(xué)院成立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時(shí)并沒(méi)有給“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下一個(gè)定義,當(dāng)時(shí)就是把“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當(dāng)作文科來(lái)看待的,但卻不使用傳統(tǒng)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這主要是受到了蘇聯(lián)的影響。1955年成立“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時(shí),在現(xiàn)在看來(lái),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上有五個(gè)可供選擇的概念,即“文科學(xué)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人文科學(xué)學(xué)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但在這五個(gè)概念中我們選擇了一個(gè)受蘇聯(lián)影響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如同院士制與學(xué)部制的制度選擇一樣,概念選擇不只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語(yǔ)言問(wèn)題,從概念選擇中也可以看出建國(guó)后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在走向體制化過(guò)程中沒(méi)有很好地繼承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反而受到了蘇聯(lián)的影響,把自己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遺忘了。
胡繩和馬洪的解釋只是一個(gè)字面上的解釋?zhuān)瑢?shí)際上“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是從30年代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的一個(gè)文件中移植過(guò)來(lái)的。黎澍說(shuō)蘇聯(lián)理論界在30至50年代曾經(jīng)為中國(guó)理論界所推崇,這是歷史事實(shí)。“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的一個(gè)文件,但作了一點(diǎn)變動(dòng)。據(jù)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zhǎng)的龔育之介紹說(shuō),在1930年,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在一個(gè)《關(guān)于自然科學(xué)戰(zhàn)線(xiàn)的決議》的文件中說(shuō):
“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方面,對(duì)所有一切反馬克思主義以及從而反對(duì)列寧主義的觀點(diǎn)予以無(wú)情的批評(píng),無(wú)論它們是怎樣偽裝起來(lái)的。”[27]
在1930年12月,紅色教授學(xué)院的哲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支部通過(guò)了一個(gè)決議,決議中說(shuō):“自然科學(xué)戰(zhàn)線(xiàn)的狀況同哲學(xué)戰(zhàn)線(xiàn)的狀況密切聯(lián)系著。”[28]這實(shí)際上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改造自然科學(xué)。而“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把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huì)科學(xué)方面的任務(wù)同在自然科學(xué)方面的任務(wù),看成是完全一樣,沒(méi)有任何區(qū)別的”。[29]其實(shí)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這些論斷在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國(guó)內(nèi)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yàn)楣伯a(chǎn)主義科學(xué)院的主要缺點(diǎn)之一是脫離了蘇聯(lián)廣大的科學(xué)界,過(guò)于封閉狹隘,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哲學(xué)輕視科學(xué),后來(lái)在1936年2月,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被并入蘇聯(lián)科學(xué)院。[30]丹尼爾•貝爾也注意到了蘇聯(lián)在30年代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中的冷戰(zhàn)意識(shí)形態(tài)。貝爾說(shuō):“馬克思沒(méi)有說(shuō)過(guò)自然科學(xué)是意識(shí)形態(tài)。不過(guò),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在20世紀(jì)30年代的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者,聲稱(chēng)存在著‘資產(chǎn)階級(jí)的科學(xué)’和‘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科學(xué)’。因此愛(ài)因斯坦的相對(duì)論作為‘唯心主義的東西’而受到了攻擊。”[31]蘇聯(lián)在30年代以來(lái)的一個(gè)學(xué)科政策就是實(shí)行教條化簡(jiǎn)單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xué)對(duì)社會(huì)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的絕對(duì)控制。當(dāng)時(shí)世界分為社會(huì)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yíng),在這種冷戰(zhàn)歷史情景中,蘇聯(lián)的這個(gè)政策不可避免地為建國(guó)后的中國(guó)所效仿。但在這個(gè)效仿過(guò)程中,哲學(xué)被政治化了。
對(duì)此,在1980年擔(dān)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書(shū)記處書(shū)記的胡喬木在一次會(huì)議上對(duì)我們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學(xué)術(shù)政策作了反思與自我批評(píng)。
胡喬木批評(píng)長(zhǎng)期以來(lái)哲學(xué)書(shū)都是“照一個(gè)格式”[32]寫(xiě)出來(lái)的,這就是哲學(xué)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表現(xiàn)。由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也使得這個(gè)概念具有強(qiáng)烈的政治性,同時(shí)作為管理機(jī)構(gòu)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應(yīng)地展開(kāi)了許多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改造與批判的工作。如1955年夏季,中國(guó)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連續(xù)召開(kāi)“座談會(huì)”,對(duì)梁漱溟的反動(dòng)哲學(xué)思想進(jìn)行批判,當(dāng)時(shí)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主任是潘梓年。[33]正是因?yàn)檫@個(gè)概念的意識(shí)形態(tài)性強(qiáng),所以龔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說(shuō)自己有一個(gè)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為什么自然科學(xué)十四條,文藝十條,高教六十條,都制定了,就是沒(méi)有制定關(guān)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工作的條例,甚至都不記得有要制定這樣條例的動(dòng)議。大概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同黨的理論建設(shè)、理論斗爭(zhēng)關(guān)系密切,情況復(fù)雜,很難把它當(dāng)作一個(gè)業(yè)務(wù)部門(mén)的工作來(lái)制定條例吧”。[34]
另外有一個(gè)現(xiàn)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955年“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產(chǎn)生后,雖然它具有學(xué)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學(xué)學(xué)者與人文社會(huì)學(xué)者對(duì)這個(gè)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以竺可楨為代表的自然科學(xué)學(xué)者對(duì)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仍然理解為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界自身的“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在內(nèi)心深處并沒(méi)有采用這個(gè)新概念。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楨日記中見(jiàn)不到“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來(lái)代替“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因?yàn)樵隗每蓸E看來(lái),“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其實(shí)就是原來(lái)學(xué)術(shù)界認(rèn)可的“社會(huì)科學(xué)”。如1955年6月1日,科學(xué)院正式成立學(xué)部大會(huì),竺可楨在當(dāng)天的日記中說(shuō):“學(xué)部委員代表講話(huà),生物地學(xué)部秉農(nóng)山,社會(huì)科學(xué)部陳援庵,數(shù)理化學(xué)部陳建功及技術(shù)科學(xué)部代表侯德榜講了話(huà)。”[35]其實(shí)不是“社會(huì)科學(xué)部”,而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而人文學(xué)者就接受了這個(gè)概念,并成為自覺(jué)的理論思維,如蔡尚思在一篇題為《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工作者首先應(yīng)當(dāng)是革命者》一文中說(shuō):“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作為社會(huì)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為無(wú)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服務(wù)的,是為革命的政治斗爭(zhēng)服務(wù)的……要成為一個(gè)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工作者,首先必須做一個(gè)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革命者。”[36]而且在1955年前后,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科學(xué)院內(nèi)部對(duì)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這兩個(gè)概念使用的主體是不一樣的。
據(jù)謝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張稼夫在科學(xué)院第23次常務(wù)會(huì)議上的報(bào)告中,提出了建立學(xué)部的完整設(shè)想,當(dāng)時(shí)的想法是:“成立學(xué)部,以改善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工作,擴(kuò)大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機(jī)構(gòu)。擬分為基礎(chǔ)科學(xué)、技術(shù)科學(xué)、生物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四部。”[37]1953年7月張稼夫在報(bào)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會(huì)科學(xué)部”而不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而在1953年的3月,中國(guó)科學(xué)院訪(fǎng)蘇代表團(tuán)已經(jīng)考察過(guò)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的科學(xué)院體制,“社會(huì)科學(xué)部”在科學(xué)院的內(nèi)部會(huì)議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來(lái)在提交中央時(shí)就發(fā)生了變化,即由“社會(huì)科學(xué)部”變成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這相當(dāng)于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自我審查機(jī)制。據(jù)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國(guó)科學(xué)院黨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bào)告,報(bào)告中就主張?jiān)O(shè)立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而1954年4月8日,科學(xué)院召開(kāi)第一次學(xué)部主任會(huì)議,并宣告學(xué)術(shù)秘書(shū)秘成立,并設(shè)立了社會(huì)科學(xué)部。[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學(xué)院黨組與學(xué)術(shù)共同體兩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中國(guó)科學(xué)院黨組使用的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是站在黨的立場(chǎng)上,而科學(xué)院的學(xué)部主任會(huì)議與學(xué)術(shù)秘書(shū)處作為科學(xué)共同體并沒(méi)有采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這個(gè)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社會(huì)科學(xué)部”。中國(guó)科學(xué)院在使用“社會(huì)社會(huì)部”還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上,存在著一些細(xì)微的差異,在不同場(chǎng)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況存在。當(dāng)然,1955年6月,科學(xué)院學(xué)部正式成立后,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就逐漸代替了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
其次,“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也具有學(xué)科性特征,學(xué)科性是其第二重屬性。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在1930年的《關(guān)于自然科學(xué)戰(zhàn)線(xiàn)的決議》的文件中說(shuō):“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方面”,這是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的學(xué)者在30年代的三類(lèi)學(xué)科分類(lèi)模式。后來(lái),1944年,潘梓年在《學(xué)術(shù)自由的思想問(wèn)題》一文中就明顯沿用這一說(shuō)法,文章說(shuō):“蘇聯(lián)的人民向來(lái)保有思想自由,學(xué)術(shù)自由等等的民主權(quán)利……學(xué)術(shù)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學(xué)來(lái)講,是要包括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以至哲學(xué)等一切學(xué)術(shù)思想來(lái)說(shuō)的……同樣的自然科學(xué),在有些先進(jìn)國(guó)家就發(fā)展得遲慢以至于停滯,在蘇聯(lián)等民主國(guó)家就發(fā)展得非常之快。”[39]潘梓年盛贊蘇聯(lián)是民主國(guó)家,而且可以看出潘梓年對(duì)蘇聯(lián)的政策十分了解,所以行文中有明顯的蘇聯(lián)詞匯。30年代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的這一學(xué)科分類(lèi)模式在40年代被采納。1940年2月,陜甘寧邊區(qū)自然科學(xué)研究會(huì)在延安成立,在成立會(huì)上講話(huà)說(shuō):“自然科學(xué)是要在社會(huì)科學(xué)的指導(dǎo)下去改造自然界,這里的‘社會(huì)科學(xué)’當(dāng)然首先是指馬克思主義。”[40]實(shí)際上在建國(guó)前已將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三者聯(lián)系在一起了,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對(duì)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指導(dǎo)關(guān)系。建國(guó)后中國(guó)政府機(jī)關(guān)也一直沿用前蘇聯(lián)30年代的表述方式,如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chǎn)階級(jí)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文件中說(shuō):“在自然科學(xué)方面,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化學(xué)、生物學(xué)、地學(xué)等領(lǐng)域中都有新的創(chuàng)見(jiàn)……同時(shí),我們不應(yīng)該忘記在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方面所表現(xiàn)的飛躍的進(jìn)展。”[41]再如當(dāng)時(shí)任部長(zhǎng)的陸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的報(bào)告,報(bào)告中說(shuō):“在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領(lǐng)域里,階級(jí)斗爭(zhēng)也是比較明顯的。胡適的哲學(xué)觀點(diǎn),歷史學(xué)觀點(diǎn),教育學(xué)觀點(diǎn)和政治觀點(diǎn),大家都批判過(guò)了。批判胡適,這是階級(jí)斗爭(zhēng)在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里,雖然自然科學(xué)本身沒(méi)有階級(jí)性,但自然科學(xué)工作者卻是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chǎng)的。從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學(xué)家中間,有過(guò)盲目崇拜美國(guó)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學(xué)家中也有所謂“非政治化”的傾向。批判這些錯(cuò)誤的東西也是完全應(yīng)該的。”[42]這些學(xué)科表述方式與30年代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科學(xué)院的學(xué)科表述方式相同。俞偉超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回憶學(xué)科分類(lèi)說(shuō):
“關(guān)于‘人文科學(xué)’,這個(gè)說(shuō)法是最近變得突出起來(lái)的。過(guò)去在中國(guó)的學(xué)科分類(lèi)中沒(méi)有‘人文科學(xué)’的分法,過(guò)去我們稱(chēng)‘社會(huì)科學(xué)’,也就是科學(xué)體系中區(qū)別于自然科學(xué)的部分,都?xì)w作是‘社會(huì)科學(xué)’。這是根據(jù)蘇聯(lián)的科學(xué)分類(lèi)而來(lái)的。這個(gè)詞在蘇聯(lián)20世紀(jì)20年代才出現(xiàn)。”[43]
俞偉超先生的晚年回憶基本正確,但不太確切。“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在1871年的俄國(guó),在由恩•弗列羅夫斯基撰寫(xiě)的《社會(huì)科學(xué)入門(mén)》一書(shū)中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44]并不是在20世紀(jì)20年代才出現(xiàn)的。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在蘇聯(lián)出現(xiàn)的是將“哲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并列的情況。
因此可以看出在前蘇聯(lián)的表述中“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三者之間既是并列的學(xué)科概念,但同時(shí)把“哲學(xué)”放在最前面,是實(shí)現(xiàn)哲學(xué)對(duì)社會(huì)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控制。到了中國(guó)以后,只是把“哲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合在一起講了,也就是胡繩說(shuō)的我們是“放在一起講”的,而蘇聯(lián)是并列分開(kāi)的,但實(shí)際上概念的分開(kāi)還是并列并無(wú)實(shí)質(zhì)的區(qū)別。這里的“哲學(xué)”用學(xué)術(shù)的視角來(lái)分析,實(shí)際上是“人文科學(xué)”的代名詞。不用“人文科學(xué)”這一概念而使用“哲學(xué)”實(shí)際上完全背離了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自身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完全受到了蘇聯(lián)的影響。一個(gè)完全依照學(xué)術(shù)邏輯的學(xué)科分類(lèi)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而不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這種“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三大學(xué)科分類(lèi)模式在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界早就得到普遍的認(rèn)同。如清華大學(xué)校長(zhǎng)梅貽琦在1941年的《大學(xué)一解》一文中說(shuō):“今日而言學(xué)問(wèn),不能出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文科學(xué)三大部分。”[45]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書(shū)中也提到大學(xué)教育應(yīng)增加共同必修的科目,此種科目應(yīng)為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人文科學(xué)的基本課程,尤其重要的是人文科學(xué)。[46]在三大學(xué)科中,潘光旦最重視的是人文科學(xué)。胡適也是如此,胡適在三大學(xué)科中,最注意的也是人文科學(xué)。唐德剛說(shuō)胡適,“胡先生談話(huà)時(shí)總是用‘人文科學(xué)’這一名詞。我就很少聽(tīng)到他提起‘社會(huì)科學(xué)’,更未聽(tīng)到他提起過(guò)‘行為科學(xué)’這一名詞。‘社會(huì)科學(xué)’是個(gè)什么東西,他不太了了。”[47]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情景中這三個(gè)學(xué)科變成了前蘇聯(lián)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或者中國(guó)的“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在這些學(xué)科概念表述中,“人文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都被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化教條化的“哲學(xué)”代替了。
其實(shí)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早在20年代就使用“人文科學(xué)”的概念,如1922年,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學(xué)的《大同大學(xué)章程》中規(guī)定,大學(xué)理科第一年所讀,須有國(guó)學(xué)1學(xué)程,英文1學(xué)程,德文或法文1學(xué)程,及人文科學(xué)1學(xué)程。[48]梁?jiǎn)⒊?923年的一部書(shū)中也談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分類(lèi)的觀念。梁?jiǎn)⒊f(shuō):“清儒頗能用科學(xué)精神以治學(xué),此無(wú)論何人所不能否認(rèn)也。雖然,其精力什九費(fèi)于考證古典,勉譽(yù)之亦只能謂所研究者為人文科學(xué)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體之人文科學(xué)已甚遠(yuǎn)。若自然科學(xué)之部,則欲勉舉一人一書(shū),且覺(jué)困難。”[49]梁?jiǎn)⒊?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學(xué)”的學(xué)科觀念,說(shuō)明其學(xué)術(shù)視野的宏闊。所以朱紅文說(shuō):“完全用社會(huì)科學(xué)取代人文科學(xué),否定“人文科學(xué)”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這種反人文科學(xué)的觀點(diǎn)是我國(guó)和前蘇聯(lián)學(xué)術(shù)界的一種占統(tǒng)治地位的觀點(diǎn)。這種觀點(diǎn)的產(chǎn)生和盛行是唯科學(xué)主義思維方式的一種表現(xiàn),它堅(jiān)持一種狹隘的科學(xué)觀,一種直線(xiàn)的、機(jī)械決定論的社會(huì)觀,幻想或總想建構(gòu)一個(gè)簡(jiǎn)單明了、便于計(jì)劃和操縱的社會(huì)世界。[50]不過(guò)更確切地說(shuō),在50年代的中國(guó)和前蘇聯(lián)是用“哲學(xué)”來(lái)代替“人文科學(xué)”,而不是用“社會(huì)科學(xué)”來(lái)代替“人文科學(xué)”,于是“人文科學(xué)”概念被逐漸遺忘。概念的選擇也是一種學(xué)術(shù)支配權(quán)的爭(zhēng)奪。鄧正來(lái)認(rèn)為,學(xué)科的制度化進(jìn)程也關(guān)涉到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文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的邊界劃定以及隱含于其間的支配爭(zhēng)奪問(wèn)題。[51]因此在中國(guó)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建構(gòu)過(guò)程中,除了對(duì)建構(gòu)者的被建構(gòu)狀況需要進(jìn)行反思以外,對(duì)于學(xué)科之間的權(quán)力爭(zhēng)奪與概念的使用也需要關(guān)注。雖然“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是一個(gè)學(xué)科與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為主導(dǎo)的,但是當(dāng)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成立后,作為一個(gè)文科的學(xué)術(shù)規(guī)劃與管理的機(jī)構(gòu),還是為中國(guó)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發(fā)展做了不少貢獻(xiàn)。
由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是當(dāng)時(shí)文科最高管理與規(guī)劃的機(jī)構(gòu),為國(guó)家的總體發(fā)展做出了許多貢獻(xiàn),但當(dāng)時(shí)的一些政治野心家為了實(shí)現(xiàn)政治陰謀,想要取消“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如黎澍說(shuō):“陳伯達(dá)在1965年先后兩次向科學(xué)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各研究所,遣散全體研究人員……1966年,‘’為了篡黨奪權(quán),大搞現(xiàn)代迷信,最怕社會(huì)科學(xué)。他們?nèi)P(pán)否定解放以來(lái)社會(huì)科學(xué)的成績(jī),采取各種野蠻手段,砸爛研究機(jī)關(guān),取締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毀棄大量科研資料,禁止寫(xiě)作和發(fā)表學(xué)術(shù)著作。”[52]這樣“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作為一個(gè)機(jī)構(gòu)在1966年“”爆發(fā)時(shí)被取消了,不過(guò)“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概念仍然繼續(xù)使用并且在1973年淪為一個(gè)單一化的意識(shí)形態(tài)概念。
1955年提出“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以后,其學(xué)科性與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的雙重屬性是共存的。學(xué)科性的發(fā)展時(shí)好時(shí)壞。在有些年份,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工作得到較好的貫徹實(shí)行,如1956年4月“雙百”方針提出后,在1956年8月由中國(guó)科學(xué)院與高等教育部聯(lián)合組織在青島開(kāi)學(xué)術(shù)座談會(huì),于光遠(yuǎn)在會(huì)上強(qiáng)調(diào)“哲學(xué)應(yīng)該更多地向自然科學(xué)學(xué)習(xí),不應(yīng)該站在自然科學(xué)之上向自然科學(xué)發(fā)號(hào)施令。哲學(xué)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學(xué)家學(xué)習(xí)。哲學(xué)只有向科學(xué)學(xué)習(xí)才能指導(dǎo)科學(xué)。”[53]于光遠(yuǎn)實(shí)際上是糾正以往哲學(xué)對(duì)科學(xué)盲目發(fā)號(hào)施令的不合理現(xiàn)象。
但隨著政治左傾現(xiàn)象的加劇,“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越來(lái)越得到強(qiáng)化,而概念內(nèi)在的學(xué)科性就被遺忘了。關(guān)于“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在1973年終于完全淪為單一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概念的內(nèi)容。
三、“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場(chǎng)域性啟示
“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產(chǎn)生與存在有其歷史原因,這個(gè)概念主要是受到蘇聯(lián)學(xué)科分類(lèi)模式的影響,在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分析就接受下來(lái)了。在1955年的中國(guó)語(yǔ)境中,這個(gè)蘇聯(lián)式的概念一進(jìn)入中國(guó)就被體制化了,而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在其體制化進(jìn)程中特別需要繼承自身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包括自身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概念,從而逐漸形成良好的概念生態(tài)與學(xué)術(shù)自主性。在中國(guó)語(yǔ)境中這個(gè)概念的學(xué)科性與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性的雙重屬性將會(huì)長(zhǎng)期共存,這個(gè)概念與“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在不同場(chǎng)域也將長(zhǎng)期共存。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中國(guó)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發(fā)展迅速,但對(duì)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的管理還停留在1955年的水平。當(dāng)前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的混亂現(xiàn)象與學(xué)術(shù)管理體制的落后有其內(nèi)在聯(lián)系。其中一個(gè)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許多管理人員并沒(méi)有相應(yīng)的概念意識(shí)。當(dāng)然,不是說(shuō)“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這個(gè)概念不能使用,實(shí)際上,我們應(yīng)該繼續(xù)使用這個(gè)概念,但在使用這個(gè)概念時(shí),應(yīng)有明確的概念意識(shí),要明白這個(gè)概念不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概念,它只是政府部門(mén)使用的用于學(xué)科管理的專(zhuān)有概念,而學(xué)術(shù)界內(nèi)部,則應(yīng)使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這一學(xué)術(shù)共同體認(rèn)同的概念,而一個(gè)求真的學(xué)者整天念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無(wú)疑也是缺乏概念意識(shí)。不同的人說(shuō)不同的話(huà),不同的場(chǎng)合也得說(shuō)不同的話(huà),這也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這兩個(gè)不同場(chǎng)域的概念對(duì)學(xué)術(shù)管理部門(mén)與學(xué)術(shù)界的當(dāng)代啟示。
[1]胡適《胡適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頁(yè)。
[2]胡適《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頁(yè)。
[3]魯迅《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yè)。
[4]鄧正來(lái)《關(guān)于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的思考》,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年版,第46—47頁(yè)。
[5]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論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頁(yè)。
[6]同上,第420頁(yè)。
[7]黎澍《黎澍自選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頁(yè)。另見(jiàn)1988年5月6日《人民日?qǐng)?bào)》。
[8]“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這樣的學(xué)科概念在中國(guó)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產(chǎn)生,后來(lái)才逐漸被學(xué)術(shù)界意識(shí)到還有這么一個(gè)學(xué)科的存在。如[美]R•S•魯?shù)录{,《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曲躍厚、林金城譯,三聯(lián)書(shū)店,1988年版。另外參見(jiàn)歐陽(yáng)康主編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哲學(xué)》,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十九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頁(yè)。原文題為《“民族形式”商兌》。蘇聯(lián)的這個(gè)號(hào)召是出自《聯(lián)共布中央委員會(huì)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huì)的政治報(bào)告》。
[10]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三冊(cè),科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頁(yè)。
[11]王亞夫、章恒忠主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大事記》,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頁(yè)。
[12]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建國(guó)以來(lái)重要文獻(xiàn)選編》,第六冊(cè),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9頁(yè)。
[13]龔育之、王志強(qiáng)《科學(xué)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8頁(yè)。
[14]李真真《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第4期。
[15]謝泳《1949年后知識(shí)精英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從院士到學(xué)部委員》,《開(kāi)放時(shí)代》,2005年第6期。
[16]同上,第4頁(yè)。
[17]楊東平主編《大學(xué)之道》,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頁(yè)。
[18][澳大利亞]約翰•默遜編著,莊錫昌、冒景珮譯《中國(guó)的文化和科學(xu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9頁(yè)。
[19]鄧偉志主編《社會(huì)科學(xué)爭(zhēng)鳴大系:社會(huì)學(xué)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yè)。
[20]吳國(guó)盛《讓科學(xué)回歸人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頁(yè)。
[21]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三冊(cè),科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頁(yè)。
[22]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頁(yè)。原載《光明日?qǐng)?bào)》1950年6月1日。
[23][澳大利亞]約翰•默遜編著,莊錫昌、冒景珮譯《中國(guó)的文化和科學(xu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頁(yè)。
[24]胡繩《胡繩全書(shū)》,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頁(yè)。這是胡繩于1986年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lián)合舉行的報(bào)告會(huì)上的講話(huà)。
[25]馬洪《開(kāi)創(chuàng)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的新局面》,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頁(yè)。這是馬洪在1982年11月,在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院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huà)。
[26]如在《江蘇教育總會(huì)上學(xué)部請(qǐng)改南菁學(xué)堂為文科高等學(xué)校書(shū)》(1907年)中說(shuō):“今學(xué)政已改設(shè)提學(xué)使,分駐寧蘇兩省垣,江陰僻在一隅,交通亦不甚便,似不如去高等廓落之名,而存文科優(yōu)美之實(shí),彬彬文學(xué)之風(fēng)。”見(jiàn)朱有瓛主編,《中國(guó)近代學(xué)制史料》,第二輯,上冊(cè),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頁(yè)。不過(guò),1907年的文科主要是指?jìng)鹘y(tǒng)的文史經(jīng)學(xué)。
[27]龔育之《科學(xué)•哲學(xué)•社會(hu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頁(yè)。另見(jiàn)《龔育之文存》,下冊(c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4—1527頁(yè)。
[28]龔育之,《科學(xué)•哲學(xué)•社會(hu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頁(yè)。
[29]同上,第105頁(yè)。
[30]龔育之《龔育之文存》,下冊(c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9—1533頁(yè)。
[31](美)丹尼爾•貝爾《意識(shí)形態(tài)的終結(jié)——五十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張國(guó)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頁(yè)。
[32]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頁(yè)。這是胡喬木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第一次黨代會(huì)上的報(bào)告。這次黨代會(huì),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成立以來(lái)的第一次大會(huì)。原文題為《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的根本任務(wù)》。
[3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頁(yè)。梁漱溟在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的批判會(huì)上提交的發(fā)言草稿題為《準(zhǔn)備向潘梓年先生談的話(huà)》,文中一開(kāi)頭就說(shuō):“所有現(xiàn)在對(duì)我的批判是說(shuō)給廣大群眾的,還是說(shuō)給我的?是要肅清我和我的思想在群眾中的影響,還是要使我得到改造?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是在前者。后者雖亦在要求之中,卻不能不居于次要,因?yàn)槟秋@然不是馬上可得的事。”
[34]龔育之《龔育之文存》,下冊(c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頁(yè)。原文題為《幾番風(fēng)雨憶周揚(yáng)》。
[35]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科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頁(yè)。在另外的日記中,如1955年6月22日記載,4個(gè)學(xué)部在北京向蘇聯(lián)代表團(tuán)提意見(jiàn),竺可楨代表生物地學(xué)部,潘梓年代表社會(huì)科學(xué)部。見(jiàn)頁(yè)572。其實(shí)潘梓年代表的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在以后的日記中竺可楨都將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理解成社會(huì)科學(xué)。見(jiàn)第574頁(yè),第594頁(yè),第641頁(yè),第679頁(yè),第686頁(yè)等。
[36]蔡尚思《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思想史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yè)。
[37]轉(zhuǎn)引自謝泳《1949年后知識(shí)精英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從院士到學(xué)部委員》,《開(kāi)放時(shí)代》,2005年第6期,原文出處見(jiàn)《中國(guó)科學(xué)院史料匯編(1953年)》,第95頁(yè)。
[38]李真真《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第4期。
[39]丁守和主編《中國(guó)近代啟蒙思潮》下卷,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頁(yè)。原文發(fā)表于1944年3月26日的《新華日?qǐng)?bào)》。
[40]龔育之《龔育之文存》,下冊(c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3頁(yè)。
[41]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建國(guó)以來(lái)重要文獻(xiàn)選編》,第六冊(cè),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1頁(yè)。
[42]陸定一《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頁(yè)。原載《人民日?qǐng)?bào)》1956年6月13日。1956年草擬了自然科學(xué)發(fā)展十二年規(guī)劃,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十二年發(fā)展規(guī)劃也在擬定。(第508頁(yè))但官方?jīng)]有人文科學(xué)的提法。如這個(gè)報(bào)告的主要報(bào)告對(duì)象是中國(guó)的自然科學(xué)家和社會(huì)科學(xué)家、醫(yī)學(xué)家、文學(xué)家、藝術(shù)家的,沒(méi)有提到人文科學(xué)家。
[43]劉文鎖《漸中語(yǔ)類(lèi)——俞偉超先生晚年思想隨錄》,《東南文化》,2005年第4期。
[44]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俄國(guó)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頁(yè)。
[45]劉瑯、桂苓主編《大學(xué)的精神》,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8頁(yè)。
[46]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頁(yè)。另外在第355頁(yè),潘光旦也說(shuō):“文法的學(xué)生應(yīng)多習(xí)些自然科學(xué),理工的學(xué)生應(yīng)多習(xí)些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文科學(xué)。”
[47]唐德剛《胡適雜憶》,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頁(yè)。在該書(shū)第47頁(yè),胡適自嘲說(shuō):“你看我們學(xué)人文科學(xué)的,我學(xué)了一輩子,現(xiàn)在還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48]朱有瓛主編《中國(guó)近代學(xué)制史料》,第三輯,下冊(cè),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頁(yè)。大同大學(xué)的人文科學(xué)課程主要是公民要義、哲理學(xué)、歐州學(xué),可見(jiàn)以西方的學(xué)科為主。
[49]梁?jiǎn)⒊吨袊?guó)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頁(yè)。1928年何炳松出版的《通史新義》的自序中就說(shuō)明自己寫(xiě)這本書(shū)采用了最新的人文科學(xué)研究成果,持的也是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人文科學(xué)三大學(xué)科的學(xué)科分類(lèi)方法。
[50]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xué)——人文科學(xué)方法論導(dǎo)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頁(yè)。
[51]鄧正來(lái)《關(guān)于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的思考》,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年版,第47頁(yè)。
[52]黎澍《黎澍自選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頁(yè)。
[53]龔育之、王志強(qiáng)《科學(xué)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