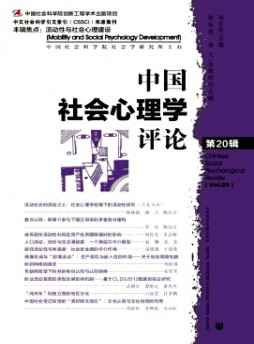社會心理的演變與對審美文學的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心理的演變與對審美文學的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學藝術的發展軌跡印證了這一理論,可以說,一個時期的社會心理決定著該時期的文學基本面貌。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作為一種驅動力,會形成新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這必然會召喚新的文藝思潮的誕生,從而又推動新的審美規范的確立,催生出新的文藝作品。例如,文藝復興以后,當時社會心理中對人的發現和認識,以及對人性的張揚,讓當時的文藝作品充滿了人性、真實性,與宗教藝術相比,充滿了世俗化色彩,使新的審美趣味得以產生,也讓新的文藝思潮得以流行。而到了二戰后,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空前劫難,熱核戰爭的恐怖,東西方冷戰、貿易大戰、生態環境惡化,政治熱情的消退,這一切都讓理性中心主義受到懷疑和批判,一切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科技取得了突飛猛進,各種新技術被廣泛地應用到生產生活領域,經濟也持續增長,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使娛樂消遣廣受歡迎,從而引起了心理機制和行為模式的巨大變化,精神上的幻滅感、不穩定感加強,求新求異,及時行樂成了他們的共同心理。后現代藝術就這樣成為了裝飾,走向了市場,開始了藝術的大轉折開始。科技的發展給藝術開辟了新的領域,消費時代的到來使藝術成為了商品,政治的熱情已經消退,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享樂心理漫延開來,于是娛樂化、商品化、平面化、世俗化的當代審美文化應時而生。
可見,社會轉型期各社會群體的心理需求促進了當代審美文化的內容與形式的變化,社會心理是推動當代審美文化產生的內在動因。當代審美文化對社會心理的反映是以隱喻的方式來體現的。社會心理對當代審美文化的影響并不一定都能得以一一對應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影響也可能是間接的,委婉的,以一種轉喻或隱喻的修辭手法或表現方式來體現。審美文化有著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表象,而所指的影響甚至制約卻是始終存在的,多義性的背后如風箏線一般總能追溯它的社會心理根源。隱喻總有著相似性的解讀,在語言的、圖像的、造型的等各種文本中,我們總能找到社會心理與審美文化二者結合的以符號為具體表現形式的隱喻傳達。如大眾對時尚的追逐與從眾心理,審美文化文本中自我表白的盛行與自戀心理,快餐文化的風靡與浮躁心理,各種審美文化文本的心理安慰功能與孤獨心理,戲說文本與顛覆性文本的泛濫與游戲心理等等,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在當代審美文化的各種編碼方式中,都有著特定社會心理的所指。我們可以在各種審美文化文本中解碼其中的社會心理動因,可見當代審美文化中的種種現象不僅是其表面化的信息,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心理中的多種復雜因素。
當代審美文化是現時代社會心理的折射。當今社會正經歷著一場充滿生機和希望,同時也充滿紛亂和蕪雜的變革,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思想交匯,市場經濟確立,全球時代到來,科技迅猛發展,打破了長期不變的穩定的社會狀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多元文化態勢造成了多元價值的沖突,社會心理必然會隨之發生變化,從而引發審美趣味和審美風尚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以世俗化、大眾化、感性化和消費化為特征,一方面促使大眾的享樂思想、個體取向、多元選擇、符號化意識逐漸增強,另一方面,在社會出現了失衡的情況下,容易誘發物欲橫流和收入不均現象,導致精神的失落和迷茫。激烈的競爭和紛繁的變化,角色的迷惘與心理的沖突,使許多人的心理趨于失衡邊緣,產生相應的心理偏移。社會心理的變化在當代審美文化中留下許多繁復、輪回的印跡,這種印跡彰顯了失衡的社會心理導致當代審美文化產生感性膨脹和兩極發展的隨動變化。具體而言,當代社會心理的轉型表現在下述四個方面:從重理性到重感性;從重集體到以個人為中心;從單一唯美到求新求變;強調身份符號的代言作用。而這些變化反映到當代審美文化中,就具有了種種與之相應的表現。
從重理性到重感性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是尊崇理性至上。孔孟儒學開創了中國傳統思想史上仁義第一的道德傳統,宋明理學更是把道德本體論是最基本的哲學體系,歷史上各家對仁、禮、理、心、道的形而上的孜孜以求,對“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存天理,滅人欲”等觀念、精神地位的過高抬舉,導致現實人生和個體生命被忽視的客觀存在。與此相應的是溫柔敦厚,深沉內向的人格和清淡平和的審美趣味,人的自然欲望處于長期被貶抑的狀態。全球化經濟的登場打破了這種平衡,社會進入一個從一個平衡到另一個平衡之間的過渡期,這是一個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舊的東西已經被破除,而新的東西尚未建立的后工業社會的空無狀態。傳統情理之間的關系被完全顛覆,理想失落了,崇高退場了,世俗的現實的生活方式占了上風,感官主義、享樂主義、游戲心態是最盛行的時尚,實用主義原則橫行天下。與以往社會相比,物質豐富程度達到頂峰,精神供給卻出現了嚴重匱乏,現代人成了失去精神家園的靈魂漂泊者,一種焦慮情緒彌漫開來,本能地尋找可以疏緩的渠道。
“消費”成為開啟這個渠道的快捷方式。究其原因,是根源于商品消費過程中裹挾而來的生活泛審美傾向。現代生活處于圖像和商品的包圍之中,讀圖時代注重的是形象和表面,對于審美對象的娛樂性和感官刺激性的要求愈見顯然。費瑟斯通曾言,它們被“賦予美的預約,提供美的佐餐。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作為代用品的使用價值之間既統一又有差異的這種雙重性質,使得商品具備了一種審美的影像,不管它可能是什么,它肯定會為人們所夢想和追求。”
這種審美活動已經失去了精神烏托邦的傳統意義,而變成了經濟和利潤的代言人,它把一切都轉變成為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價值。世俗的享樂被極大地強化了,廣告中不斷是宣揚著各種快樂幸福的生活方式,清貧和節約不再是生活的主調,大眾審美文化不斷生產出種種欲望,刺激大眾的消費,馬克思曾指出如果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這就演示了審美心理的流變過程。廣告文化,明星文化,時尚文化、網絡游戲,都建立在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基座上。從精神升華到感官娛樂的轉變,表現出肯定現世享受、身體快感、世俗生活的傾向,它是審美大眾化、世俗化、商業化從而不得不媚俗化的結果,它只作用于人的肉體快感,失去了精神自由的含義。人的感性的解放是時代進步的標志,然而當過度沉溺于感官快樂之時,就會造成對人文精神的巨大沖擊,導致對精神追求和終極價值的削弱。如此一來,人生就充滿游戲、恍惚、戲謔感,把人引向精神墮落和意識危機。
從重集體到以個人為中心
中國長期以來的以家國天下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讓國人形成一種群體思維模式,重群體性,輕個性,個人從來就屬于集體和國家,唯獨不屬于自己。個體意識處于消隱狀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地位的明確,“利人利己”的經濟倫理蘊含于等價交換原則中,互惠互利的思維讓人們的自我意識日益增強。同時,舊有體制的打破和西方思想的涌入,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給人們帶來的沖擊,由此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給個體的自我實現提供了現實機緣,生活和文化的多元化也給人們提供了多樣的選擇性,讓人們有機會重新塑造自我,個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每個人在參與競爭的時候都面臨著自我表現和自我選擇,于是怎樣讓自己與眾不同和更富有競爭性是讓人們絞盡腦汁的問題。參考現成案例,為自己規劃成功之路成為最輕松的解決方案。作為行為參照的偶像已經從保爾變為比爾,由戰斗英雄變成致富能手,這反映了大眾人生價值觀的變化,后者這種成功型的現實榜樣更能實現個人價值。人們的這種個性至上的訴求代表了社會心理中的個性自由要求,只有當實現自我成就、體現自身價值,才能符合社會的要求,得到大眾的認可。倘若得不到滿足,就容易產生逃避心態,用消極的態度來應對現實對自我的壓制,在各種消遣娛樂中釋放無助感與受挫感。至于那些傳統意義上的真理、理想、理性和永恒等“權威”概念都已經沒落,人們把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都轉向了自我。在自我意識極度膨脹的時代背景下,自戀與對個性的追逐正是對外界逃避和厭惡的表現形式之一。
人們對自我的關注越來越多。瞬息萬變的外部世界和浩如煙海的信息資訊迷惑了已然沒有多少信仰的人們,人們把對國家民族集體的關懷轉為對自身感覺的滿足,自我從來沒有獲得過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過度的自我表現所形成的審美時尚再次將個性訴求轉變成共性關懷,隱含著求異和從眾心理的二律背反。時尚的流行正是由一小部分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人,自我表現自我張揚的結果,當它一旦被大眾群起而仿效之的時候,又會有新的時尚被那些想將自我從蕓蕓眾生中標舉出來的人來創立。不僅是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個人化,這股風也吹到了文學界,時代的變遷讓“詩人變成個體性寫作的基本單位,甚至是不再熱衷于打出宣言或張揚旗號,也不再注意什么‘主義’,而是關注自己當下生存狀態或本能寫作狀態。于是,……開始強化個人寫作和自己對重組中的自我形象的感受。同時還有一部分詩人開始進入非主流的、反審美的、對大寫的‘人’的精神逃逸性寫作。”這就是話語體系的標新立異,于是大力渲染性、欲望、變態的作品大行其道,私人敘事和關照人性的作品增多了,當個性化始終無法明確實現的前提下,人們只得繼續生活在焦躁的、欲望永難滿足的狀態之中。
從單一純粹到求新求變
追求新奇、趨新求異、標新立異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心態,但是在以往許多社會歷史時期這種想法受到社會環境的約束或禁止。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封閉的農業社會,它要求的是穩定和秩序,儒家的仁和禮都是為了維護整個社會的一致性。長期以來,這種經濟結構和生存狀態強化了我們的民族心態,形成了中華民族以和諧穩固“少私寡欲”、清靜克制為核心的人生態度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統治者一方面宣揚他們統治人民的合理性,說他們是“順天承命”、“聽天由命”來治理國家,這種歷史積淀下的文化心理反映在審美上就是以恬淡中和溫柔敦厚為美。然而從心理學上看,長期的刺激會導致對其分辨率下降,美感和快感都具有不確定性。大腦皮層長期受某種單一刺激,必然會阻隔神經的興奮度,這時只有用新的更強烈的信號才能重新激起神經興奮。反之就會形成審美疲勞,所謂熟視無睹便是此意。當前社會的轉型成為這種興奮劑的藥引。社會蛻變過程的快速性無情地將人們拋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運轉的全球化時代,快節奏、多信息、高速度、強競爭是這個時代的唯一標志。文學也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再到私人寫作,身體寫作,新新人類寫作、網絡寫作。
文化的多樣化使得各種時尚潮流異彩紛呈,出現多元共存的局面。講個性,講從眾,講狂野,講內斂,講前衛,講傳統,種種審美觀念并行不悖。千百年緩慢沉寂的局面被喚醒了,自得其樂的田園牧歌被狂熱震撼的搖滾打斷了。人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不再堅持心靜如水,面對變化莫測的世界,人們在匆忙這中急急追趕。這是一個《浮躁》的時代,充滿了《喧囂與躁動》,人們的心也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得不安份起來。當宏大敘事被消解的時候,永恒、真理、價值、意義、上帝這些人類本來的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被宣告成為虛無的時候,當無深度、無意義的后現代文本充斥我們的文化空間之時,漂泊無依,失去家園的感覺侵擾人們的內心,人們變得浮躁了,在太多的信息面前只需要蜻蜓點水、浮光掠影地掃描一回,新奇、變換的東西才合他們的胃口,一種東西剛流行起來,馬上就會有升級版跟上,在不停的更新換代中,在不斷的時尚追逐中,當代人才能找到自己沒有被時代拋棄的心理根據。
強調身份符號的價值
過去的人們通常沒有足夠的金錢來滿足自己的時尚追求,即使有也主要集中于商品的現實功用,商品的符號化消費主要集中在特權階層。生產力的發展和消費經濟的興盛為大眾提供了投射自己各種幻想和欲望的符號消費及欲望消費的可能性。審美文化正是打著具有優雅品味,提高生活格調的招牌來隱藏其強大的消費邏輯。廣告傳媒等話語權力無孔不入,不遺余力地宣傳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安逸悠閑的幸福生活,而這些身份符號是通過購買產品來達到的,精神上的超越、心靈上自由已經成為必須通過擁有物質產品才能到達的目的地。人們在生活節奏飛快的時代只有憑借符號來表明自身,人可以通過消費來界定其在生產關系中的位置,這種斗爭能讓消費者找到認同感,給自己找到屬于一個特定社會階層的滿足感。時尚就是生產各種符號,滿足人們各種夢想的場地。人們對時尚的從眾心理表明“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使用價值)———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用來當作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或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
這就是“符號操縱”和“記號價值”,這種符號的需要是消費意識形態精心創造出來的,經過審美文化的浸淫成為種種生活模式的典范,形成當代審美文化中對符號的依賴。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社會心理變化的背后,有一個主要的核心,那就是個體欲望被張揚過后的對快感的青睞,正是在熱衷快感的享樂主義心理的指引下,當代審美文化中敘事方法與策略的轉變,以及由此延伸的種種實現方式,無一不應和著社會心理中對快感的強調。簡而言之,社會心理的變遷促使大眾審美心理的快感轉向,這種轉向決定了以快感尋求為基本原則的當代審美文化的美學特征,在此種心態的推動下,審美文化在各個方面迎合社會心理的快感動機取向,而社會心理在審美文化領域也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調控力,當快感訴求無盡漫延時,戲說、惡搞等就成為大眾不間斷獲取快感的通用手法。
作者:丁筑蘭單位:貴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