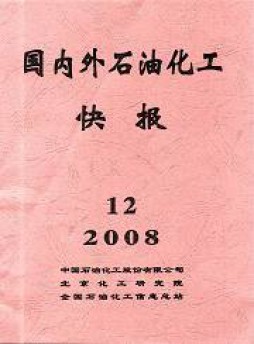國內家具設計理念梳理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內家具設計理念梳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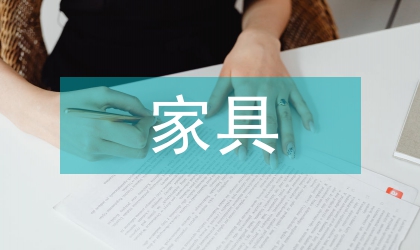
全球化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西方文化在迅速傳播的同時,也誘發了非西方國家對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它是一種本土文化身份意識的覺醒。有了這個前提,全球化的下一步進程便會逐漸顯現出“非西方的諸多民族國家對自己民族文化的重新發現和建構”這一趨勢,也可稱其為“一個嶄新的歷史任務”[1]252。可見,針對傳統文化的借鑒和創新行為,并不是全球化的外在需求,而是這一背景下的必然結果。設計是文化促進下帶有主動性、針對性和聯想性的人類行為[2](P22),與此同時,設計也在人(設計者與使用者)—物—環境間相互影響和彼此“教化”的行為鏈發展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自身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設計也理所當然地負有以上“歷史任務”中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因此,關于傳統設計的當代轉化問題就不只是風格上的創新、思想上的懷舊或者純粹的設計方法論研究等等那么單一,而是“再建構”和“再發展”于中國設計領域的時代體現。具體到中國當代家具設計,就是指傳統家具設計中核心理念的當代轉化。需要正視的是,目前一些針對設計轉化的思想偏離了對傳統核心理念的把握,甚至一些思想本身就有表意上“張冠李戴”的錯誤,導致無法歸納出明確和直觀的設計實踐方法,其成果也必然是乏善可陳。幸運的是,類似“中國主義”和“新中式”等前期研究已然不同程度地詮釋和促進了傳統與現當代設計文化的交流,而“新中國主義”的創新思想進一步完善和深入了以上兩者的理論成果。因此,當務之急是在“百家爭鳴”的當代家具設計思想中撇清“孰是孰非”,在梳理中把握思想源頭的合理性,同時為傳統家具和當代設計建立起更為合理的交流平臺。
一、優良轉化原則的建立
站在當代家具設計的角度重新審視傳統,“借古喻今”或“古為今用”的意義就不只是回顧與傳承那么簡單了,借鑒與創新才是轉化與擴展設計思想的良好途徑,而設計思想是設計文化得以建立和發展的源動力,它促成了設計者、物和使用者之間的文化約定。據統計,目前針對轉化思想的研究普遍涉及到如下概念或名詞:仿古設計、復古設計、中國風、新中式、中式新古典主義等。作為設計思想的外化,對現行多種概念的梳理有助于轉化源頭上的“撥亂反正”,以便建立起合理而成熟的指導思想,具體標準如下:首先要明確體現傳統設計中的核心理念,不提倡順手拈來,否則就失去了“指導”的意義;其次要把握傳統和當代設計的共通點以便建立起高速的轉化平臺,包括對審美特征、社會需求、生產工藝等多方面的綜合考量;最后要關注時代的命題,即倡導生態改善并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目標。以上標準能夠較為完整地對當代設計轉化思想加以評判,可稱其為優良轉化原則,而其具體實施也必定包含從“變化到教化,再到新變化的全過程”[2]42,符合設計文化發展的基礎模式。
二、當代家具設計思想及其梳理
1.梳理依據的建立
對差異性的深入了解往往是建立明確性的捷徑。事實上,針對當代設計轉化的諸多探索中仍然存在著模糊的分界,主要表現在概念與思想間的“詞不達意”。因此,為了突出其中的差異性,這里將引入表意的語義學概念進行分析。表意多指語言符號與它所表現的概念或事物之間的關系,或者能指系統和所指系統構成的表達含義的功能。所指和能指是索緒爾提出的語言符號內部的兩個要素,所指代替符號的概念,能指代替符號的音響形象,即發音[3]95-101。若從表意來看,仿古設計、復古設計、中國風、新中式和中式新古典主義各自的所指之間具有明顯的差別,不能一概而論地將以上能指都拉進傳統設計的當代轉化這一所指范圍中,避免在濫用能指任意性的同時,忽略了能指和所指間的同一性。同時,這些概念中的相應設計思想也會隨著以下表意分析逐一顯現,為衡量其是否符合優良轉化原則提供了本質依據。
2.仿古與復古設計
《辭海》中,“仿古”的解釋有二:一為摹擬古器物或古藝術品,二為模仿古人;由此可見,仿古設計的所指范圍應主要為古玩的鑒賞和收藏領域。《髹飾錄》尚古篇有“仿效”一說,其解為“模擬歷代古器及宋、元名匠所造,或諸夷、倭制等者”,意同“仿古”,其目的在于“為好古之士備玩賞”。仿古設計在中國傳統設計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別是中晚明時期興起的復古思潮金石學,它從審美需求上極力促進了仿古設計的繁榮[4]114-122。然而,仿古絕非照搬照抄,《髹飾錄》“總論成飾而不載造法”,為的是鼓勵工匠“溫古知新”,意思是在溫習古法和古器物的過程中,能夠有所頓悟并創出新意,即“不必要形似,唯得古人之巧趣與土風之所以然為主”[5]。“復古”在《辭海》中有恢復舊制的含義,泛指恢復舊的制度、風尚等。復古設計在《長物志》的造物思想中屢有提及。其中幾榻卷有“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的天然幾設計方法,而“黑漆斷紋者為甲品”、“床以宋、元斷紋小漆床為第一”[6]的理念均體現出設計者對“斷紋”這一古制元素的偏愛,并借此使器物“俱自然古雅”。綜上可知,仿古設計和復古設計中的確不乏從“借鑒”到“創新”的過程,但此過程的形成是以傳統設計為主場的,鮮有與當代設計的對接,是游歷于當代設計之外的獨立范疇,可將其視為傳統設計的純粹延續。因此,若將二者的所指與優良轉化原則掛鉤,是一種表意上的錯誤。
3“.中國風”
“中國風”是中國傳統設計史中值得深究的重要命題,然而,若將其所指用來描述傳統設計的當代轉化這一設計行為,也不是十分準確,原因何在?首先,在韋伯英語大百科全書中,“中國風”的含義有兩個方面,一是指18世紀歐洲出現的一種裝飾風格潮流,以復雜的圖案為特征;二是指用這種風格裝飾的物品,或采用這種風格的實例。“中國風”的所指實際上是一種基于中西文化交流下的裝飾風格,而中國漆家具(楚式家具)和瓷器在西方的流傳和影響是這一風格誕生的主要誘因。“中國風”也是早期西方人對神秘中國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詮釋。它起源于法國,并隨著法國裝飾設計學派的運動對洛可可風格的興起產生了巨大影響[7]66-73。然而,裝飾只能稱為中國傳統家具設計中的重要部分,而非優良轉化原則中所強調的核心理念。自傳統哲學興起之時就有莊子“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①的說法;明文震亨借《長物志》提倡“寧古無時,寧樸無巧,寧儉無俗”的造物思想,并在各篇的具體論述中多次提及“石用方厚渾樸,庶不涉俗”、“黑漆古、光背質厚無文者為上”等裝飾節制的設計理念;就連記載古代漆器工藝的《髹飾錄》都反對刻意的裝飾,強調取法自然,忌“淫巧蕩心”,“行濫奪目”,避免“過奇擅艷,失真亡實”②。著名學者王世襄曾將明式家具的裝飾概括為“大體樸素”,“簡單到使人不覺得是裝飾”,卻能“以少許勝人多許”[8](P260)。其次,“中國風”的另一所指通常為“中國風格”,主要指當代設計中的傳統元素表現,而這些元素一般直接采用未經加工轉化的具有象征性質的傳統符號,包括書法繪畫、日常器物、建筑園林或者其中的紋樣和色彩。從這個層面看,“中國風”又意同“復古設計”,同樣沒有走出依附傳統設計的囹圄。
4“.新中式”與“中式新古典主義”
總的看來,“新中式”和“中式新古典主義”似乎是針對設計轉化且表意較為全面的當代設計風格。“新中式”及由此衍伸出的“新中式家具”,是劉文金先生在2002年由南京林業大學主辦的“首屆中國家具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上提及的,其具體解釋為:一,基于當代審美的對于中國傳統家具的現代化改造;二,基于中國當代審美現狀的對于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家具的思考[9]。而“中式新古典主義”可以歸納為在中國傳統美學的規范之下,運用現代的材質及工藝,去演繹傳統文化中的經典精髓,使作品不僅擁有典雅、端莊的氣質,并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設計方法[10]153-154,184。可以說,“新中式”和“中式新古典主義”在表意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確存在同一性,但究其所指,兩種思想偏重于宏觀的設計評價風格,缺乏微觀的設計指導,存在進一步被細化的可能。例如前者的“中國傳統家具的現代化改造”,后者的“傳統美學”和“經典精髓”等,這一系列概念的理解需要較高的傳統文化修養和較強的傳統設計理念的過濾能力,即一種傳統文化上的自覺性。對于大多數當代設計師來講,傳統設計思想始終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具體表現為:家具創作未能在“中”與“新”之間找到合理的轉化點,且大多徒勞于脫離了文化功能的符號堆疊,劉文金先生稱其為對“原文化結構中分離出來的孤零零的視覺樣式”進行的拼貼與剪裁[9]89。而此種設計思想的惡化已經促成了大范圍的仿像氤氳,使得中國傳統設計中的精英文化——意象被影像所替代[1](P128),即拈來了“中”的影像,卻未賦予“新”的意象。
三、優良轉化原則下的“新中國主義”
1“.新中國主義”的建構依據
什么樣的指導思想才是符合優良轉化原則的?針對此疑問的答案不妨從“中國主義”尋起。“中國主義”是方海在其《現代家具設計中的“中國主義”》一書中首度提及的。全書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傳統家具設計在世界家具史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而這種地位和影響力恰恰源自傳統家具設計的核心思想或者先進理念。早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交替時期,以美國格林兄弟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家具設計師就發現了中國傳統硬木家具中蘊含著可貴的先進理念,他們從中借鑒了形式、功能或者設計原理并創作出諸如布蘭卡的起居室椅和蓋姆博的餐廳椅等廣受贊譽的作品,方海將此類家具或家具設計思想稱為“中國主義”[11]3。“中國主義”的誕生不但明確了中國傳統家具設計中的核心思想,即形式、功能或者設計原理,也見證了傳統與西方現代設計之間的成功轉化,是迄今該領域中較有說服力的研究,得到中外學者的一致認可。然而,“中國主義”的提出立足于西方現代家具設計,是對“中體西用”的總結,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的當代家具設計領域,但其對傳統家具的研究成果依然能夠給予我們莫大的啟示。有鑒于此,筆者在遵循優良轉化原則的基礎上,對“中國主義”進行了本土化的創新,確立了“新中國主義”的設計思想。此二者是在內容上的補充與銜接,思想上的交流與傳承。
2“.新中國主義”轉化的優良體現
“新中國主義”的所指為中國當代設計師從傳統家具設計中借鑒的功能、結構與形式;或者靈感直接來源于傳統家具設計中的功能、結構與形式的當代家具。它是具有正確表意,同時也符合優良轉化原則的當代家具設計思想。
(1)傳統設計的核心理念
“新中國主義”首先明確了傳統家具設計中的核心理念:適宜的功能、嚴謹的結構和簡約的形式[12](P46-48),三者的核心地位具體論述如下:以中國椅子的靠背板設計為例,它從早期軛架中的橫棖逐漸演變為較為舒適的豎向藤編框格,并最終形成了符合人體背部曲線的S形實心靠背板,而這種突出的功能性也對西方家具設計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13]23。事實上,“制器尚用”說幾乎涵蓋了中國傳統設計的方方面面:始于春秋末年的《考工記》有“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其內)與步相中也”①;明《長物志》也有“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撿取”②。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明式家具簡潔的功能性帶動了西方的中國家具研究,克雷格•克魯納于1940年首次在美國雜志上將中國家具與西方的“功能主義”聯系起來。R.H.埃爾斯沃思曾在其《對中國家具的一些深入思考》中對中國傳統家具的結構大加贊賞:“沒有其他文化能夠創造出它這種把設計與結構融為一體的美”、“中國硬木家具的結構是各個零部件連接起來的”、“它的連接方式是一種簡單的榫卯接合”。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也認為中國家具結構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完整體系,體現了一種簡單明確的有機組合,合乎力學原理的同時也兼顧了實用和美觀[8]230,而榫卯則是這一結構得以實現的關鍵。同時,中國榫卯結構的悠久歷史亦可追溯到新石器時期的木作技術[2]41。傳統家具設計中的形式是由功能和結構同時決定的,古斯塔夫•艾克在《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提到,明式家具有“準確無誤的比例感;對形式的觀念(嚴格或微妙)永遠符合于功能,同結構含義不可分離”[13]32,而類似的理念在傳統文獻中也多有記載:“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后。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后”③;“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余,上可臥筆四矢”④分別說明了箭和筆床的實用功能對尺寸形式的約束。
(2)傳統與當代的理念對接
“新中國主義”體現著傳統設計中與西方同步的先進理念,這些理念至今仍然是當代家具設計中的主導思想,諸如功能主義和簡約主義。其中,中國傳統家具所表現出的形式是當代簡約主義的前身。中國工匠們在家具的制作手法上盡顯節約用料之能,保留承重必需的部件而去掉一些無用的橫檔和支撐部件[11](P64-73),以至于艾克將一件中國三角幾描述為“簡化到僅剩下構造所必需的最少成分”[13](P16)。事實上,傳統家具特別是由壺門臺座發展的一支,其演化本身就是利用結構對部件進行簡化的過程。這種立足本土的思想前瞻性有利于傳統和當代設計的對話,也在借鑒之“古客體”和創新之“今客體”之間建立了直觀的共通點。
(3)可持續思想的當代命題
中國傳統設計思想在對人、物和環境的關系協調方面自始至終都遵循著樸素的可持續設計生態觀,而這種觀點也直接反映在功能、結構和形式的核心思想中,具體表現為人與環境的“天人合一”,人與物的“物盡其用”,以及物與環境的“物競天擇”,而這些先進的生態觀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從《周易》緣起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周易》、陰陽五行說、儒、釋、道以及三教合一的理學等都為傳統的設計行為設置了一系列客觀規律之下的限定因子,而這種限定是由人、物和環境間天然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所形成的,它們貫穿于器物設計中的功能、結構和形式,也由此建構了設計中的可持續行為鏈,并保證其中環環相扣的緊密性。
小結
設計思想不僅是設計者、使用者和物之間的文化約定,也是設計行為的前提和來源,其方向的合理與否直接導致實踐創作中的優劣表現。目前,針對傳統設計文化在現當代的應用研究已有頗多積累,其中亦不乏獨到的見解與精辟的論述,然始終未能在傳統的適宜轉化方面實現有效的促進,以致設計之物“浮形于事”、多做“表面文章”,且未達傳統之精髓,為何如此?實乃思想未能理清亦未見梳理之故。因此,筆者對當代家具設計的主要思想逐個分析、歸其原位、撥亂反正,并進一步肯定了“新中式家具”等思想的積極作用和啟發價值。最后,本著優良轉化原則的評判標準,筆者在諸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建構起更為完整與成熟的“新中國主義”設計思想,以期進一步推進傳統設計中核心理念的當代轉化,并試圖為中國當代家具設計的發展豎立一盞指路明燈。
擴展閱讀
- 1國內媒介文化
- 2國內公債史
- 3國內購物旅游探究
- 4國內檢察權分析
- 5國內村民分化研究
- 6國內小額信貸監管分析
- 7國內武術文化研究綜述
- 8國內物流金融
- 9國內毒情形勢表述
- 10國內翻譯研究綜述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國內產業調研
- 2國內安全保衛論文
- 3國內外形勢論文
- 4國內對財務風險的研究
- 5國內博士論文
- 6國內市場營銷方案
- 7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研究
- 8國內工程造價管理現狀
- 9國內的公共藝術
- 10國內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