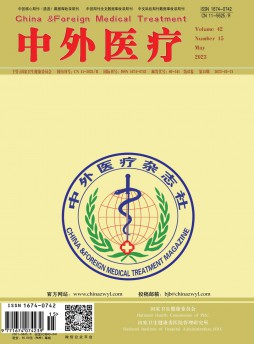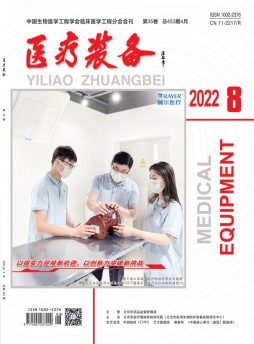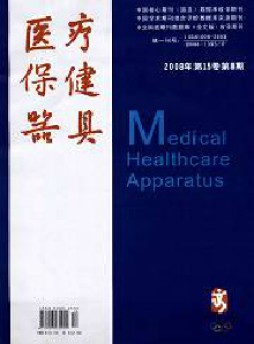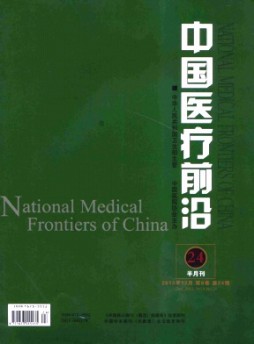醫(yī)療和健康服務(wù)定性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醫(yī)療和健康服務(wù)定性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guó)心理衛(wèi)生雜志》2015年第七期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伴隨健康服務(wù)研究(healthserviceresearch)的興起,英美醫(yī)學(xué)界逐漸關(guān)注源自社會(huì)科學(xué)(以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為代表)的定性研究,倡導(dǎo)將定性研究引入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研究,而心理衛(wèi)生領(lǐng)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美醫(yī)學(xué)界對(duì)定性研究的興趣主要來(lái)自兩個(gè)方面:首先,定性研究能夠彌補(bǔ)定量研究的不足,探討定量研究不能回答的問(wèn)題;其次,定性研究能夠橋接研究與實(shí)踐之間的鴻溝,更好地將知識(shí)轉(zhuǎn)化為有效的服務(wù)[2]。在此基礎(chǔ)上,英美醫(yī)學(xué)界對(duì)定性研究的倡導(dǎo)經(jīng)歷了一個(gè)變遷過(guò)程:從使用定性研究作為定量研究的補(bǔ)充,整合定量與定性研究,到建立以多學(xué)科合作為基礎(chǔ)的綜合研究體系。然而,時(shí)至今日,整合定量與定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倡導(dǎo)和探索層面,建立多學(xué)科合作的綜合研究體系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
1當(dāng)前醫(yī)療和健康服務(wù)領(lǐng)域中運(yùn)用定性研究存在的問(wèn)題
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研究在引入定性研究的過(guò)程中面臨的困難,以及整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障礙,在當(dāng)下醫(yī)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的探索性接觸中表現(xiàn)為:一方面,醫(yī)學(xué)界在引進(jìn)定性研究的過(guò)程中既有對(duì)“異域風(fēng)情”的熱望和期待,也有一種基于喪失自我而產(chǎn)生的忐忑和焦慮,禁不住追問(wèn)定性研究方法的科學(xué)性;另一方面,社會(huì)科學(xué)界在輸出定性研究的過(guò)程中既有被認(rèn)同的自豪與滿足,也有一種基于“嫁女”而產(chǎn)生的疑慮和不安,為定性研究可能在轉(zhuǎn)介過(guò)程中變得面目全非而焦慮。這種相互懷疑和張力構(gòu)成雙方合作的潛在障礙。出現(xiàn)這種局面,醫(yī)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雙方都難辭其咎。一方面,醫(yī)學(xué)界在一定程度上將定性研究的方法與理論視角進(jìn)行切割,將定性研究簡(jiǎn)化為一種資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技術(shù),并移植到自身領(lǐng)域。這種移植的實(shí)質(zhì)是在維系本學(xué)科傳統(tǒng)(自然科學(xué)的認(rèn)識(shí)論和方法論)合法性基礎(chǔ)上的削足適履。其后果是采用定性方法收集資料,卻又希冀對(duì)定性資料進(jìn)行定量處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社會(huì)科學(xué)界在潛意識(shí)里將定性研究的具體方法上升到理論層面,淡忘了定性研究本身存在一個(gè)歷史變遷的過(guò)程,不僅懷疑其他領(lǐng)域的研究者理解、接受和操作定性研究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拒絕“他者”發(fā)展定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2關(guān)于定性研究的認(rèn)識(shí)誤區(qū)
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在方法層面(包括資料的收集和分析)的差異是顯而易見(jiàn)的。從資料收集的層面來(lái)看,定量研究使用統(tǒng)計(jì)抽樣法則確定研究對(duì)象,采用問(wèn)卷、量表等結(jié)構(gòu)化調(diào)查方法收集數(shù)據(jù)資料;定性研究則采用理論抽樣規(guī)則確定研究對(duì)象,采取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獻(xiàn)檔案等半結(jié)構(gòu)或開(kāi)放式方法收集文本類資料。從資料分析的層面來(lái)看,定量研究基于數(shù)理統(tǒng)計(jì)使用推論的方式對(duì)研究問(wèn)題及假設(shè)進(jìn)行檢驗(yàn);而定性研究則基于對(duì)現(xiàn)象的描述和解釋(文本分析和話語(yǔ)分析等)使用歸納的方式得出結(jié)論。深入考察,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區(qū)別絕不僅僅存在于方法層面。換句話說(shuō),自然科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之間的張力雖然更多表現(xiàn)為方法上的大相徑庭,但雙方基于不同知識(shí)傳統(tǒng)建構(gòu)了認(rèn)識(shí)論和方法論層面的具有意識(shí)形態(tài)意味的對(duì)立才是形成這種張力的根源。借用人類學(xué)的視角,這種對(duì)立構(gòu)成了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互為“他者”的局面,也是阻礙雙方相互理解、認(rèn)同和接納的根本原因。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部分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領(lǐng)域的研究者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間在方法差異之外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區(qū)別[1]。在他們看來(lái),這種深層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研究問(wèn)題、研究目標(biāo)以及秉持的社會(huì)理論這三個(gè)方面。
在研究問(wèn)題方面,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數(shù)量的問(wèn)題(例如某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頻次和頻率),定性研究回答的是定性的問(wèn)題(例如某種現(xiàn)象的性質(zhì)和實(shí)質(zhì),發(fā)生的原因和機(jī)制);在研究目標(biāo)方面,定量研究側(cè)重可靠性,定性研究側(cè)重有效性;在社會(huì)理論方面,定量研究的出發(fā)點(diǎn)是結(jié)構(gòu)理論,定性研究的基礎(chǔ)是行動(dòng)理論。這一比較分析不能說(shuō)完全精準(zhǔn),但不乏洞見(jiàn),已經(jīng)觸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的方法論和認(rèn)識(shí)論問(wèn)題。研究問(wèn)題關(guān)涉的是問(wèn)題的類型和意義:什么樣的研究問(wèn)題是有意義的?研究目標(biāo)是關(guān)于知識(shí)生產(chǎn)和評(píng)價(jià)的標(biāo)準(zhǔn):什么樣的回答是有價(jià)值的?社會(huì)理論則指出了研究者的世界觀對(duì)研究本身必然產(chǎn)生的影響:研究問(wèn)題和方法背后的合法性基礎(chǔ)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這一洞見(jiàn)揭示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屬兩個(gè)不同的知識(shí)傳統(tǒng),各自有著自己生產(chǎn)問(wèn)題、知識(shí)的路徑以及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暗示并不存在一個(gè)共同的、普遍的衡量和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研究領(lǐng)域?qū)Χㄐ匝芯康闹匦抡J(rèn)知意味著崇尚科學(xué)主義的自然科學(xué)霸權(quán)的一種內(nèi)省,這為開(kāi)啟自然科學(xué)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平等對(duì)話提供了可能。這種平等對(duì)話應(yīng)該建立在這樣一個(gè)前提基礎(chǔ)之上:定性研究不僅僅是一種技術(shù)層面的研究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指引和設(shè)計(jì)具體研究方法的理論視角。因此,如果醫(yī)學(xué)研究者希望引入定性研究,那么他們不僅需要了解和掌握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技術(shù)的定性研究,更需要理解、認(rèn)同和采納定性研究背后的理論視角。
3定性研究的理論視角
從歷史起源來(lái)看,定性研究源自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接觸和碰撞,具體表現(xiàn)為西方文明在認(rèn)同文化多樣性的基礎(chǔ)上試圖理解非西方文明的努力。19世紀(jì)末,伴隨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地位的確立,定性研究也被確認(rèn)為必要且合法的研究方法。相對(duì)于西方文明來(lái)說(shuō),非西方文明是作為一個(gè)異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人類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以“他者”的視角來(lái)理解“他者”,而西方文明在理解異文化的過(guò)程中逐漸習(xí)得并借助“他者”的視角來(lái)反觀己身,實(shí)現(xiàn)對(duì)本文化的理解。20世紀(jì)20年代,經(jīng)由芝加哥社會(huì)學(xué)派的努力,定性研究被引入社會(huì)學(xué)作為研究西方社會(huì)、城市文明的一種必要研究方法;60年代之后,定性研究逐漸擴(kuò)展到經(jīng)濟(jì)學(xué)、文化研究、心理學(xué)、教育學(xué)和醫(yī)學(xué)等領(lǐng)域。梳理作為人類學(xué)分支之一的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脈絡(luò)可以清晰地透視定性研究的理論視角。早期的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致力于描述和理解異文化(包括現(xiàn)存的原始部落、非西方文明傳統(tǒng))的醫(yī)學(xué)知識(shí)體系,比如疾病名稱、分類、病理解說(shuō)和治療手段。在與西方的生物醫(yī)學(xué)比較之下,這些非西方社會(huì)的疾病知識(shí)往往被認(rèn)為是非理性的迷信,而相應(yīng)的治療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毫無(wú)科學(xué)依據(jù)的巫術(shù)。
文化相對(duì)論的出現(xiàn)使得西方文明能夠?qū)⒎俏鞣轿拿髦糜谔囟ǖ臍v史和社會(huì)背景中重新考察,從“他者”的視角,而不是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chǎng)出發(fā),想當(dāng)然地以簡(jiǎn)單-復(fù)雜、落后-進(jìn)步、原始-文明的框架來(lái)解釋非西方與西方的差異。當(dāng)然這一過(guò)程對(duì)于西方文明來(lái)說(shuō)也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chǎn)物:經(jīng)歷過(guò)兩次大戰(zhàn)的沖擊,西方文明內(nèi)部的問(wèn)題逐漸凸顯,在擴(kuò)張和殖民過(guò)程中得到強(qiáng)化的文明自信受到挑戰(zhàn),西方社會(huì)秉持的信仰、價(jià)值甚至科學(xué)體系越來(lái)越受到來(lái)自內(nèi)部的質(zhì)疑和批判。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huì)思潮興起則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針對(duì)西方文明以自我為中心建構(gòu)的真實(shí)、客觀與科學(xué)的反省和解構(gòu)。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通過(guò)跨文化研究,將西方的生物醫(yī)學(xué)體系與非西方文明傳統(tǒng)(比如中國(guó)、日本、印度和伊斯蘭)中的醫(yī)療體系進(jìn)行比較,得出了一個(gè)基本結(jié)論:醫(yī)學(xué)知識(shí)和實(shí)踐是一個(gè)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是特定社會(huì)與文化的歷史產(chǎn)物。在此基礎(chǔ)上,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通過(guò)反思、批判西方生物醫(yī)學(xué)體系(包括教育、臨床、科研、技術(shù)和衛(wèi)生政策諸方面),揭示了生物醫(yī)學(xué)體系背后的西方中心主義,暗示了生物醫(yī)學(xué)體系的相對(duì)性。簡(jiǎn)單地說(shuō),從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看來(lái),生物醫(yī)學(xué)只是西方文明在工業(yè)化基礎(chǔ)上建立的一套關(guān)于健康、疾病的解釋和應(yīng)對(duì)方法,并不具有所謂的普遍真理性。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認(rèn)為,以工業(yè)化邏輯為基礎(chǔ),生物醫(yī)學(xué)的一個(gè)核心特征是將人看做一部機(jī)器,疾病則是導(dǎo)致人這部機(jī)器拋錨的問(wèn)題,其結(jié)果是將“病人”與“正常人”區(qū)分開(kāi),將“病”與“人”分離開(kāi)來(lái),將生物醫(yī)學(xué)的疾病知識(shí)與患者的疾病體驗(yàn)切割開(kāi)來(lái),使用生物醫(yī)學(xué)意義上的疾病范疇替代患者的疾病體驗(yàn),并且賦予生物醫(yī)學(xué)定義、解釋和應(yīng)對(duì)疾病的霸權(quán),相對(duì)剝奪患者感知、敘述、解釋和應(yīng)對(duì)自身疾病的合理性。最終將“治病”和“救人”切割開(kāi)來(lái),或者將醫(yī)療的終極目標(biāo)從“救人”轉(zhuǎn)化為單純的“治病”。
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家凱博文指出病(disease)與疾(illness)分別是醫(yī)生和患者對(duì)于同一現(xiàn)象(疾病)的兩種解釋模式:前者是基于生物醫(yī)學(xué)的概念和理論的解釋模型,后者則來(lái)自患者基于疾病體驗(yàn)(具有社會(huì)及文化內(nèi)涵)的解釋模型。不同之處在于,科學(xué)主義賦予前者以描述、定義、解釋和應(yīng)對(duì)疾病的唯一合法性。病與疾的分離以及對(duì)后者的忽略甚至否認(rèn)是生物醫(yī)學(xué)面臨的核心問(wèn)題。要糾正這一問(wèn)題,凱博文認(rèn)為,必須在承認(rèn)生物醫(yī)學(xué)建構(gòu)疾病體驗(yàn)的相對(duì)性的基礎(chǔ)上,關(guān)注患者關(guān)于疾病的敘述和體驗(yàn),即從患者的視角出發(fā),通過(guò)患者關(guān)于自身疾病的解釋模型來(lái)理解患者的疾病知識(shí)與體驗(yàn)。這一理念顯然是以人類學(xué)的基本理論視角(從“他者”的視角出發(fā)來(lái)理解“他者”的生活世界)反映在醫(yī)療及健康領(lǐng)域中運(yùn)用的產(chǎn)物。其實(shí)質(zhì)是承認(rèn)和恢復(fù)患者在醫(yī)療過(guò)程中的主體性和能動(dòng)性。近年來(lái),生物醫(yī)學(xué)包括精神醫(yī)學(xué)愈來(lái)愈強(qiáng)調(diào)患者參與醫(yī)療的過(guò)程,強(qiáng)調(diào)從“治療”到“康復(fù)”的理念轉(zhuǎn)換,包括提倡社區(qū)康復(fù)及同伴教育,不能不說(shuō)是西方社會(huì)沿著這一脈絡(luò)反思整個(gè)生物醫(yī)學(xué)體系的產(chǎn)物。
4定性研究的實(shí)質(zhì)
當(dāng)下,經(jīng)由多種學(xué)科(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醫(yī)學(xué)、教育學(xué)等諸多學(xué)科)的參與和發(fā)展,定性研究的運(yùn)用領(lǐng)域大大擴(kuò)展,具體方法也不一而足,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焦點(diǎn)小組、文獻(xiàn)法、話語(yǔ)分析等等在內(nèi)的研究方法都被貼上了定性研究的標(biāo)簽。不論這些方法的形式如何變化,定性研究的實(shí)質(zhì)在于如何通過(guò)研究對(duì)象的視角來(lái)理解研究對(duì)象。現(xiàn)代人類學(xué)的奠基人之一馬林諾夫斯基根據(jù)自身在異文化地區(qū)的研究經(jīng)歷提供了如下方案:學(xué)習(xí)當(dāng)?shù)厝说恼Z(yǔ)言,長(zhǎng)時(shí)間(至少一年)與當(dāng)?shù)厝松钤谝黄穑瑓⑴c他們的日常生活,了解并掌握當(dāng)?shù)厝说娘L(fēng)俗和習(xí)慣,才能學(xué)會(huì)從他們的視角出發(fā)來(lái)理解他們的生活。這種研究方法被稱為實(shí)地工作(fieldwork,人類學(xué)領(lǐng)域常見(jiàn)的另一個(gè)譯法是“田野工作”),其核心是參與觀察。簡(jiǎn)言之,參與觀察的實(shí)質(zhì)是把研究者當(dāng)做研究工具投入到研究對(duì)象的生活世界中,以參與的方式進(jìn)行觀察,通過(guò)研究者與研究對(duì)象的日常生活互動(dòng),經(jīng)由研究者的親身體驗(yàn)來(lái)收集研究資料,最終實(shí)現(xiàn)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理解。人類學(xué)認(rèn)為,只有通過(guò)研究雙方的高強(qiáng)度互動(dòng),才能幫助研究者擺脫基于自身文化價(jià)值觀念的先入之見(jiàn),實(shí)現(xiàn)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真正理解,而不是從研究者的視角出發(fā),使用研究者既定或預(yù)設(shè)的概念框架去剪切、翻譯研究資料。不難看出,人類學(xué)實(shí)地工作的方法論與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論存在重大不同。在自然科學(xué)中,研究工具是可校準(zhǔn)的、外在于研究者的;而在實(shí)地工作中,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是一個(gè)活生生的人。在自然科學(xué)中,研究者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影響是必須避免的,以期獲得客觀的資料;而在實(shí)地工作中,研究者和研究對(duì)象的互動(dòng)被視為獲取有效資料的唯一途徑。在自然科學(xué)中,研究場(chǎng)景是受到研究者高度控制的(比如實(shí)驗(yàn)室,或者通過(guò)結(jié)構(gòu)化問(wèn)卷的方式進(jìn)行控制);而在實(shí)地工作中,研究者應(yīng)該盡量避免施加控制,使研究在接近自然的日常生活場(chǎng)景中進(jìn)行。這樣做的目的在于,研究者得以聆聽(tīng)研究對(duì)象在日常生活狀態(tài)下的敘述,觀察研究對(duì)象在日常生活狀態(tài)下的行為,了解研究對(duì)象在日常生活狀態(tài)下的思維模式,而不是通過(guò)結(jié)構(gòu)化的問(wèn)卷獲得研究對(duì)象在特定時(shí)點(diǎn)和場(chǎng)景下對(duì)自身的觀念、態(tài)度和行為的公開(kāi)表達(dá)(publicstatement)。在人類學(xué)看來(lái),日常生活是復(fù)雜的,作為行動(dòng)者的人是具有能動(dòng)性的,人的語(yǔ)言、行為和思維既受到社會(huì)規(guī)范和文化價(jià)值的形塑,同時(shí)也必然操弄、改變和塑造社會(huì)規(guī)范和文化價(jià)值。研究對(duì)象在特定情境下的公開(kāi)表達(dá)往往并不反映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和思維,很多時(shí)候只不過(guò)反映了他對(duì)社會(huì)規(guī)范的認(rèn)知,或者對(duì)研究者需求的感知。
因此,人的語(yǔ)言、行為和思維之間既不具有一致性,也不具有可替代性。參與觀察強(qiáng)調(diào)通過(guò)研究雙方的深度互動(dòng)來(lái)收集資料就是希望在最貼近日常生活的狀態(tài)下,綜合比照考察研究對(duì)象的敘述、行為和思維,以期獲得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完整理解。這一點(diǎn)對(duì)于醫(yī)療和健康服務(wù)研究來(lái)說(shuō)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治療依從性的問(wèn)題為例,在人類學(xué)看來(lái),人的知識(shí)、態(tài)度和行為的改變并不具有同步性。掌握正確的知識(shí)不一定帶來(lái)態(tài)度的改變,而態(tài)度的改變也不一定就會(huì)表現(xiàn)為事實(shí)上的行動(dòng)。因此,患者治療依從性的狀況既不完全取決于患者對(duì)疾病、藥物知識(shí)的掌握和對(duì)服藥重要性的認(rèn)知,也不完全取決于對(duì)治療效果的感受,而是很可能受制于其他諸多因素,比如醫(yī)患溝通、患者的工作性質(zhì)、生活模式、家庭關(guān)系和人際交往等等。相應(yīng)的,如果要改善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單純強(qiáng)調(diào)疾病和藥物知識(shí)教育的干預(yù)模式顯然是不夠的。當(dāng)然,定性研究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實(shí)地工作,并且由于學(xué)科制度和規(guī)范的原因,在醫(yī)學(xué)及健康服務(wù)研究中引入原汁原味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必然存在諸多客觀限制。比如人類學(xué)要求的長(zhǎng)時(shí)間的參與觀察,在特定的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研究中可能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事實(shí)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經(jīng)歷了發(fā)展和變遷,被引入到不同研究領(lǐng)域(包括健康服務(wù))中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huì)研究方法[5]。重要的是,在具體方法差異和變遷的背后,定性研究的內(nèi)涵和實(shí)質(zhì)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僅不回避研究雙方的互動(dòng),相反就是借助這種互動(dòng),通過(guò)研究者的親身經(jīng)歷來(lái)收集研究資料。比如在深度訪談中,定性研究強(qiáng)調(diào)訪談雙方是處于平等地位的對(duì)話者,訪談是對(duì)話性質(zhì)的雙向交流,而不是由研究者按照預(yù)先擬定的問(wèn)題向研究對(duì)象收集自認(rèn)為需要的信息的單向調(diào)查過(guò)程(即研究者主動(dòng)提問(wèn),研究對(duì)象被動(dòng)回答)。同時(shí)在訪談過(guò)程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也不僅僅是訪談對(duì)象講述的口述信息,還應(yīng)該結(jié)合觀察的方式,通過(guò)觀察訪談對(duì)象的表述方式、表情和肢體語(yǔ)言來(lái)實(shí)現(xiàn)對(duì)敘述的綜合理解。
5醫(yī)療和健康服務(wù)領(lǐng)域運(yùn)用定性研究的價(jià)值和方向
回顧歷史,醫(yī)學(xué)與定性研究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并不是由20世紀(jì)90年代興起的健康服務(wù)研究催生。公共衛(wèi)生與社會(huì)醫(yī)學(xué)理念的誕生早就將醫(yī)學(xué)置于更大的社會(huì)背景,甚至世界體系中進(jìn)行考量,健康、疾病和醫(yī)療等概念也早已擴(kuò)展到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文化等范疇中得以重新定義。醫(yī)學(xué)與人類學(xué)的合作與20世紀(jì)中葉的國(guó)際公共衛(wèi)生項(xiàng)目不無(wú)關(guān)系,50至60年代,西方工業(yè)化國(guó)家致力于向發(fā)展中國(guó)家及貧困地區(qū)推介先進(jìn)的醫(yī)學(xué)知識(shí)和技術(shù),以期改變這些地區(qū)糟糕的健康和醫(yī)療狀況。在此過(guò)程中,具備生物醫(yī)學(xué)、公共衛(wèi)生專業(yè)訓(xùn)練的西方醫(yī)療專家遭遇了意料外的困難:這些“落后”地區(qū)不是歡迎、接納先進(jìn)的醫(yī)學(xué)知識(shí)、技術(shù)和設(shè)備,而是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拒絕和抵制行為。在西方專家看來(lái),這是荒謬和不可理喻的:難道這些人不想改善自身糟糕的健康和醫(yī)療狀況嗎?他們認(rèn)為,這些落后地區(qū)的人們由于無(wú)知和迷信表現(xiàn)出拒絕和抵制的不理性行為。如何改變這一狀況?既然人類學(xué)是研究“落后”的“異文化”的專業(yè)領(lǐng)域,那么讓人類學(xué)家參與到這些項(xiàng)目中來(lái)就順理成章了。人類學(xué)家認(rèn)為,首先需要反思的是這些項(xiàng)目的目的,其次需要理解的是當(dāng)?shù)厝说男枨蟆T谌祟悓W(xué)家看來(lái),國(guó)際公共衛(wèi)生項(xiàng)目的理念實(shí)質(zhì)上是西方文明秉持的技術(shù)至上的意識(shí)形態(tài):技術(shù)可以解決一切問(wèn)題,而當(dāng)?shù)厝宋幢卣J(rèn)同這一理念。因而,國(guó)際公共衛(wèi)生項(xiàng)目失敗的根源是文化沖突,具體表現(xiàn)為地方醫(yī)療文化與西方生物醫(yī)學(xué)文化之間的沖突。因而,在傳遞和接納生物醫(yī)學(xué)知識(shí)和技術(shù)的這一文化互動(dòng)中存在著一種文化障礙(cul-turebarrier),解決的辦法則需要從當(dāng)?shù)厝说囊暯浅霭l(fā),理解當(dāng)?shù)厝嗣媾R的問(wèn)題和需求,發(fā)展具有文化適應(yīng)性(culturaladaptability),具備文化能力(culturalcompetence)的國(guó)際公共衛(wèi)生項(xiàng)目。人類學(xué)介入國(guó)際公共衛(wèi)生運(yùn)動(dòng)的這段歷史對(duì)醫(yī)療領(lǐng)域運(yùn)用定性研究具有相當(dāng)?shù)膯⑹竞徒梃b意義。在今天看來(lái),如果把這一歷史事件的國(guó)際背景置換為一個(gè)特定國(guó)家甚至地區(qū),并且承認(rèn)不同人群(比如以性別、年齡、民族、社會(huì)階層和生活地區(qū)等特征進(jìn)行劃分)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化差異,不難發(fā)現(xiàn)各種疾病知識(shí)的宣傳教育、健康意識(shí)和服務(wù)模式的推廣項(xiàng)目在實(shí)踐中存在的問(wèn)題與當(dāng)年國(guó)際公共衛(wèi)生項(xiàng)目的遭遇是如此的相似。醫(yī)學(xué)、公共衛(wèi)生與社會(huì)科學(xué)在歷史上的交匯不僅證明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基礎(chǔ),而且展示了定性研究的引入帶來(lái)的實(shí)質(zhì)性變化是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的擴(kuò)展,讓研究者可以看到原有的視角和框架忽視甚至否認(rèn)的那些因素和變量實(shí)際上與研究主題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關(guān)聯(lián)。在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研究中引入定性研究,首先需要明確一點(diǎn),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不存在絕對(duì)意義上的孰優(yōu)孰劣的問(wèn)題。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著各自擅長(zhǎng)回答的問(wèn)題。定性研究的特長(zhǎng)在于通過(guò)類似解剖麻雀的個(gè)案方法來(lái)回答“是什么”和“為什么”這一類的問(wèn)題。這就意味著并非所有問(wèn)題都可以,或者適合采用定性研究。
是否采用定性研究取決于研究問(wèn)題的性質(zhì)。對(duì)于特定的研究問(wèn)題來(lái)說(shuō),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最適合回答該問(wèn)題的方法。那么,一個(gè)更具操作意義的問(wèn)題是,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研究中的哪些環(huán)節(jié)適合引入定性研究?簡(jiǎn)要梳理英美醫(yī)療及健康服務(wù)領(lǐng)域自20世紀(jì)90年代開(kāi)始出現(xiàn)的明確使用定性研究的相關(guān)研究文獻(xiàn),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發(fā)。第一,定性研究可以幫助定量研究提煉并優(yōu)化研究問(wèn)題與假設(shè)。定量研究往往過(guò)于專注方法本身,具體表現(xiàn)為日益強(qiáng)調(diào)發(fā)展完善、精細(xì)的數(shù)理分析模型,相對(duì)忽略研究問(wèn)題和假設(shè)的生產(chǎn)過(guò)程。事實(shí)上,定量研究的意義和價(jià)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問(wèn)題和假設(shè)的意義和價(jià)值。定性研究的特長(zhǎng)可以在這方面發(fā)揮作用。在定量研究之前,如果以定性研究為先導(dǎo),提煉出研究問(wèn)題和假設(shè),并在此基礎(chǔ)上設(shè)計(jì)定量研究方案,不僅可以避免研究者的先入之見(jiàn),打破從主觀假設(shè)出發(fā)收集資料驗(yàn)證假設(shè)的循環(huán)論證,而且可以提升定量研究問(wèn)題的意義和價(jià)值。相關(guān)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主題:患者關(guān)于特定疾病的敘述、態(tài)度、體驗(yàn)和應(yīng)對(duì)方式,從患者的視角重新理解作為致病原因的某些日常行為和生活習(xí)慣,患者就醫(yī)選擇,參與治療的體驗(yàn),特定疾病的社會(huì)和文化內(nèi)涵,健康與社會(huì)變遷的關(guān)系。第二,定性研究可以幫助橋接定量研究中較為薄弱的從研究到實(shí)踐的環(huán)節(jié)。健康服務(wù)研究的焦點(diǎn)在于設(shè)計(jì)健康服務(wù)的體系和模式,而設(shè)計(jì)出來(lái)的體系和模式最終是否能轉(zhuǎn)化為有效的實(shí)踐,則有賴于服務(wù)提供者與消費(fèi)者的互動(dòng)。這一環(huán)節(jié)也是定性研究可以發(fā)揮作用的地方。定性研究不僅可以參與到服務(wù)體系和模式的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而且可以參與對(duì)服務(wù)實(shí)踐效果的評(píng)估,進(jìn)一步幫助健康服務(wù)專家修正和完善相關(guān)體系和模式。相關(guān)研究側(cè)重關(guān)注消費(fèi)者需求,服務(wù)資源[22],服務(wù)體系和模式,醫(yī)患互動(dòng)。第三,部分研究既追求對(duì)特定現(xiàn)象的量化描述、分析,同時(shí)也希望解釋現(xiàn)象的性質(zhì)、原因和機(jī)制,也可以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比較典型的研究主題包括特定患者人群的生活狀態(tài),健康與社會(huì)因素的關(guān)聯(lián),一般人群關(guān)于特定疾病防治措施的認(rèn)知與接受狀況,特定人群的健康觀念和態(tài)度。
作者:郭金華 單位:北京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系,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