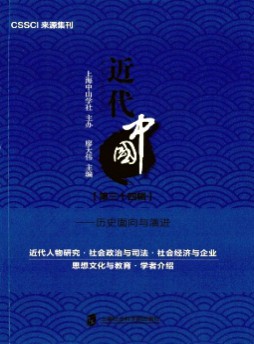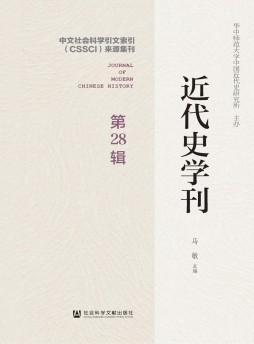近代廣播的興盛與嬗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近代廣播的興盛與嬗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藝研究雜志》2015年第七期
廣播是民國時期新興的媒體形態。自1923年廣播電臺引入中國以來,廣播事業迅速崛起,成為與傳統報刊并駕齊驅的大眾傳播媒介,而娛樂也成為早期播音的重要內容。20世紀30年代,隨著民營電臺的迅猛發展,娛樂節目更成為風靡各大電臺的主力節目形態。相較傳統的演藝形態,播音娛樂節目在演出形式、觀賞模式上都有顯著差異。民國播音娛樂節目的發達意味著一種新的娛樂方式與娛樂取向的出現。作為民國時期新興的大眾傳播方式,廣播的崛起及其所營造的大眾狂歡究竟對傳統娛樂行業造成了何種影響?播音娛樂又如何面對全新的社會浪潮?呈現出何種差異?對于上述問題,學界探討明顯不足。本文試圖以廣播對傳統演藝形態的影響為例,探討具體社會處境中媒介傳播方式變更與相關行業變革間的內在關系。本文不準備對現代演藝形態的變遷作各行業內的具體考察,而只是希望從“傳播模式”的角度,探討傳播方式的變革與近代演藝形態轉型間的關聯。另需特別指出的是,本文僅是對民國時期廣播所引發的演藝形態嬗變的有限觀察,只是呈現出兩者間的內在關聯,并不認為傳播方式的變革對現代演藝形態的命運有決定性的作用。
一、現代娛樂播音的盛行
娛樂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屬性之一。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娛樂形式經歷了自我娛樂、人際娛樂、群體娛樂到大眾娛樂的過程,也反映出人性總體上從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到精神屬性的拓展。民國廣播電臺的興起與發展,為娛樂邁出傳統娛樂形態、走向大眾娛樂提供了全新的技術手段和傳播平臺。自廣播播音伊始,娛樂就與廣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娛樂節目也成為近代廣播播音的重要內容。1923年1月,外商奧邦本所設廣播電臺仍在試驗階段時,音樂歌唱即是電臺試播的主要節目。據《申報》報道,該臺1月27日的試播節目為“八時大陸報今日之新聞、八點一刻本埠著名滑稽家海乃(Mr.MarkHanna)君布其特別之歌調、八點半為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之奏樂聲、八點四十五分美國大學俱樂部之四人合奏聲、九時為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中之喝采聲”①。除報告《大陸報》的新聞外,該臺所播幾乎全是娛樂性的節目。作為民國新興的大眾傳播媒介,廣播具有傳播快、影響大、受眾廣等特點,娛樂播音作為新的娛樂形態受到市民的熱烈追捧,收音機也成為民國家庭娛樂“流行”與“時髦”的象征性符號。娛樂播音的流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娛樂節目成為各電臺播音最重要的節目類型。其二,收聽娛樂播音成為市民較普遍的娛樂方式。只要對民國時期各廣播電臺的節目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公營電臺還是私營電臺,娛樂節目都是其最普遍、最不可或缺的節目類型。娛樂節目的泛濫甚至給人一種錯覺,離開了娛樂節目,電臺便不成其為電臺。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隨著民族資本的崛起與近代商業的繁榮,民營商業電臺迅速興起,在消費主義的刺激下,娛樂播音呈現出一派喧囂。熱衷廣播事業的俞子夷曾對1934年4月5日上海28家廣播電臺播送的節目做過統計,驚訝地發現:“拿28家平均起來,非娛樂的(節目),每家平均不過1.3檔罷了。娛樂的每家平均有7.75檔。每日每家平均播送七八時的娛樂,娛樂的機會真多。”②俞子夷所說的“一檔”約指三刻或一小時。如此看來,這些電臺非娛樂類的節目,每天平均播出不到一個半小時,而娛樂類的節目則多達七、八個小時。這一現象并非“偶然”,即便是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娛樂播音在其節目中也占據了很大比重。該臺1934年9月24日至30日間的播音節目統計顯示,節目類型主要有音樂、新聞、演講、常識及其他幾類,其中音樂類節目比重最高,占39.3%③。專以“灌輸主義”為宗旨的中央廣播電臺,娛樂播音盛行如斯,其他商業電臺娛樂播音之盛當不難想見。可見,娛樂節目的流行乃是民國廣播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④。一般來說,播音節目的設置總是受到市場需求、聽眾審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節目的流行往往起因于社會極為旺盛的消費需求。伴隨著收音設備在市民階層中的逐步普及,在20世紀30年代,收聽娛樂播音已成為市民熱衷的娛樂方式。廣播電臺設置之初,因收音機價格不菲,家用收音機多是社會上層的“奢侈品”。然而,隨著民國廣播及收音裝置的迅速普及,播音娛樂也日益大眾化,不再只是社會精英和有產階級獨享的“奢侈生活”。署名“金全”的作者談道:現代各種娛樂機關已化為有閑階級的獨占物,無線電是民眾化的娛樂機關,可使全國民眾,人人得在晚餐后團聚,欣賞第一流音樂家演奏,農村漁舍寂寞之人,或年老殘疾頹廢之身,均可收聽,身心得為之舒適。⑤金全所論雖不無理想化的色彩,其時廣播也并非人人皆可收聽,但廣播播音使得信息流通的時空范圍有效擴大、收聽人數與日俱增卻是不爭的事實。魯迅在《知了世界》中就曾生動描述無線電的盛景:天熱的時候,各家都把門窗大開,裝著無線電收音器的人家,“便把音波放到街頭”,“與民同樂”。然而,因為全是“咿咿唉唉,唱呀唱呀”的娛樂節目,沒完沒了,以至讓人生厭“,耳根沒有一刻清靜”⑥。上海弄堂的這一幕并不鮮見,另一作者也有類似的觀察:“一共全弄堂沒有十家人家,天電竹桿卻豎了十幾根,大的六燈七燈也有,小的礦石收音機也有。一到晚上,耳朵內無論在東西各面總覺得丁冬的有弦子聲。”⑦弄堂里“電桿林立”,收音機不時“與眾同樂”,甚至到“沒完沒了”的狀態,都反映出娛樂播音已經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成為市民日常休閑、家庭娛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新的娛樂方式:市民娛樂形態的轉換
娛樂播音的流行一方面表明社會有著旺盛的娛樂需求,另一方面也指示了都市娛樂中新的娛樂形式與消費取向。雖然,廣播播音的視聽效果和現場感尚無法與親臨劇院相比,但廣播娛樂節目的豐富性、便利性以及低成本卻令傳統娛樂消費望之莫及。昆曲票友吳淞亞得知申報館有昆曲廣播后,輾轉購得一部收音機,收聽節目后,按捺不住激動之情撰文寫道:“使吾國最優美之音,假能媒之力傳至數百英里之外,不勞舟車勞頓,友朋紹介而克親罄,欬如在一室之內者。申報館之功為不朽矣。”⑧吳淞亞的筆下已然將廣播娛樂的優勢展現無遺。娛樂播音能“傳至數百英里之外”,聽眾再也不必“舟車勞頓”親臨現場,卻又能獲得“如在一室”的真切感受。娛樂播音提供了一種跨越時空的互動,顯然也重構了市民娛樂中公、私空間的界限。因為廣播節目的優勢明顯,以致很多收音機的擁有者往往不愿再大費周章地去擁擠的公共場所觀賞傳統娛樂表演。收音機猶如一個奇妙、充滿魔幻色彩的“匣子”,將滑稽、歌唱、戲曲、相聲、彈詞、蘇灘等各種娛樂節目匯集在一起。借助新的技術手段,市民只要旋開按鈕,靜候在家中便可以在舒適、愜意的狀態下聽到字正腔圓的表演。“告別劇場”看似是不經意的選擇,卻意味著傳統消費空間的轉移與新的消費空間的生成,娛樂的公、私空間界限被重新改寫。在新的消費空間中“,家”所獨具的溫馨舒適為娛樂休閑提供了最佳場所。“家”中的休閑不但省卻了奔波勞累之苦,也更容易達到徹底的放松,進而獲得內心的愉悅與滿足。民國時期的一位聽眾,就以悠然的筆調描繪了他在家中收聽娛樂節目的愜意心態:優美之音樂,每于不知不覺之中,能陶怡性情,一曲甫終,胸襟□□,故每當晚飯之后,華燈初上之際,集家人于一室,徐開話匣,則南腔北調,歐歌古樂,惟吾所欲。一日勞碌至是盡釋,其快樂為何如哉。且話片之中,除音樂與戲劇外,尚有演說、國語,及英文等均足為敎育之助,自修之需也。是以娛樂之中,除電影外,當推話匣為第一矣。⑨不難想見,“華燈初上”時,全家人齊聚一室收聽廣播的其樂融融,娛樂節目不僅讓人“勞碌盡釋”,全家歡聚更是充滿溫情。這種感覺之難忘,體驗之深刻,以至有聽眾將播音娛樂視為圍爐團坐時“無上之娛樂品”⑩。民國市民家庭中收音機往往都被擺放在顯赫的位置,其他空間和娛樂活動都圍繞著它組織起來,由此亦可見娛樂播音在家庭空間中占據的重要地位。娛樂播音不僅引發娛樂空間的重新分配,一定程度上也重新編排了市民的生活時間。一位初次接觸無線電收音的聽眾如是說:我拿了幾樣小東西便連上了,竟然能聽到美麗而悅耳的歌曲!我是被它迷住了,真也不想把聽筒從耳上拿下來。可是一等到那討厭的吃飯鐘響了,我才不得已的把聽筒放下,對著那礦石收音機呆呆的看了一下,走回家去,但我的耳膜,似乎還跟著那可愛的音樂共鳴呢!與這位無線電迷類似的癡醉者為數不少,電影女星陳玉梅購買收音機后,“大部分的時間,伴著收音機生活”,而另一位明星葉秋心“在家里用膳時,必定也要開收音機,否則就飯難下口”。這些娛樂節目的忠實聽眾,對收音節目的酷愛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娛樂播音也幾乎改寫了他們的生活作息,決定了他們組織日常活動的時間流程。娛樂播音的影響顯然并不只局限于這些有收音機購買能力的市民,娛樂播音面向大眾的特點也不失機會地為那些無力購買收音機的勞工大眾制造出更多的娛樂機會。例如民國的商家就時常開著廣播,以新鮮玩意兒吸引聽眾、招徠生意。一位“濂裔”的作者觀察說:“無線電本為高尚娛樂品,滬上自開洛公司放送無線電后,裝者頗多。一般商店乃利用此無線電之傳遞音樂,有即用之以作廣告者。如大馬路之某商號,大新街之某電料店等均將此無線電放音機裝在門首。蓋機中有時忽放音樂,有時忽唱戲曲,有時忽報市情。無日不吸引多數人之駐足而聽,此亦善于利用廣告者。”這些商家的精明之舉自然吸引到不少的聽眾,在上海便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在稍為熱鬧的馬路,“每一家裝有無線電收音機的商店門口,總是圍著許多人在那里聆聽無線電的播音”。《申報》觀察說“:滑稽在播音圈里很有相當魔力,尤其是沿馬路的商店,他們最喜歡收聽滑稽,同時可以吸引主顧上門。低級社會沒有力量購置收音機的,總是成群結隊地跑到商店門口去過癮,這種情形我們在馬路上時常可以看到。”商家利用娛樂播音來吸引主顧,不僅將馬路轉變成了新的娛樂空間,也為一般的民眾提供了娛樂的可能。且不管商家是否真的借此謀得利潤,一般的勞苦大眾倒可能在其中“感受到樂趣,把他們的疲倦和煩惱都能忘去”。顯然,娛樂播音為傳統“馬路娛樂”注入了新的內容,為普通階層營造了新的娛樂環境,增添了他們的娛樂體驗。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公園等公共場所大量裝置收音機,以豐富市民生活,增加城市的娛樂氛圍。在廣州,政府決定在中央公園設置放音臺,免費提供給市民收聽廣播,以致市民紛紛在播音時涌入中央公園。有媒體這樣描繪其時的盛況“:等到八點鐘,已經沒有地方了,來的人還源源不斷。”這種因廣播而生成的“公共空間”無疑塑造出一種全新的娛樂形態和生活方式。技術的變革總是會引發社會生活的悄然變化。從消費模式上看,傳統娛樂形式的消費者需要離開家庭涌向固定的娛樂場所,而娛樂播音的聽眾則只需要打開收音機,不再與表演者面對面就可以完成消費。消費者從“觀眾”變成了“聽眾”,從“現場”轉變為“不在場”。無論是居家的家庭娛樂,還是馬路、公園等公共空間中的娛樂廣播,都在傳統的娛樂方式之外開辟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娛樂形態。收聽者無論在家中還是在公共空間中進行收聽,事實上都是一種新的生活選擇。
三、傳播技術的變革與演藝形態的分化
傳播技術的變革對近代演藝行業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娛樂播音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現代娛樂業的結構,影響了現代娛樂形態的嬗替。首先,娛樂播音節目的發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市民的娛樂方式,娛樂空間的轉換也分流了傳統演藝界的觀眾,新的娛樂形式不可避免地對傳統娛樂業造成了沖擊。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30年代前,傳統休閑娛樂行業主要集中在茶館、戲院等場所,觀眾則主要以這些地方附近的市民為主。不過,一方面茶館、戲院人多混雜,部分社會精英不太喜歡前往喧囂嘈雜的場所娛樂;另一方面在傳統男女有別的觀念影響下,部分婦女和兒童被排除在外,即使在開放女客之后,很多婦女和兒童也對在公眾場合進行娛樂心存顧慮。廣播出現之后,娛樂播音提供的“居家娛樂”的休閑方式使得人們不必再涌向人頭攢動的公共場所,播音廣播使得娛樂更為私密化、自由化。空間感的消逝使得“聽戲”在某種程度上代替了“看戲”,信息渠道的變化部分地改變了聽眾聚合的方式,進而分化了出入戲院、茶館的人流。一位叫錢云的聽眾就坦白說“:影戲院加價到了八角半之后,尚未曾踏進過院門,好在家里有一具收音機,就這樣坐坐聽聽,無意間還含著節約,豈不甚好。”錢氏的選擇頗具代表性,揭示出在消費成本的顧慮下,不少傳統影戲院的潛在觀眾轉而成為娛樂播音的追捧者。
娛樂播音對傳統娛樂表演的巨大沖擊也可以在娛樂行業的對抗性舉措中看出端倪。一些娛樂表演活動為保證演藝“票房”的收入,轉而也對娛樂播音加以抵制。1931年上海工部局的一次會議就有委員提出抗議說:“近來所舉行之音樂會已見滿座,一經播音,結果將使音樂會收入減少,除非所收特準播音之費,足抵音樂會收入之損失。”正因為“播音”的關系,很多觀眾不再光臨音樂會,而改以“廣播”收聽,這使得音樂會收入損失巨大,最終引發了收取“特準播音費”的提議。暫且不談廣播播音有無自由播音權,是否需要交納“特準播音費”,這種抗議表明那些家里購置收音機的市民以聽廣播來代替其他娛樂在當時已成為較普遍的選擇,娛樂播音對影、戲院的“生意”構成了直接的影響。在新的傳播語境下,依靠固定空間演出的戲院、影院,如果不能提供更深刻的感觀體驗,顯然不足與大眾傳播的洪流相抗衡,衰落之勢幾乎不可避免。娛樂播音對“言語”的依賴也使得傳統演藝行業內部出現明顯的分化。民國時期,廣播播音的出現確使不少傳統演藝活動都借助無線電贏得了更多的聽眾與愛好者。類如歌曲、相聲、滑稽等娛樂節目多在電臺走紅,這從其時播音演藝團隊的活躍程度上即可見一斑。上海是無線電最為發達的城市,隨著娛樂播音的興起,圍繞各電臺廣泛組織有各式演藝團體(如歌唱團體、滑稽團體、相聲團體等等)。在這些社團中,以歌唱團體尤為矚目。一些專為播音而設的“歌唱社”,如“明月社”、“大同社”、“甜姐兒社”等,與商業電臺交相輝映,成為滬上播音界的“新寵”。據統計,1936年到中央廣播電臺參與播音、制作文藝節目的社團就有幾十個之多,如音樂歌唱團體有稚鳴社、怒吼社等25個社團;國樂彈詞有律社等5個社團;話劇有海燕話劇社等7個社團。演藝團體的活躍程度猶如晴雨表,直接反映出相關節目類型的景氣指數。然而,觀察這些借助廣播迅速發展的節目,不難發現它們大抵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偏重于“言語”的表達。娛樂播音的特點主要是依靠“聲音”而傳播,故而偏重于“言語”的節目自然大放光彩,偏重于空間、舞臺、肢體的娛樂節目則多無緣“觸電”。
廣播播音對“言語”的倚重,甚而在民國時期還催生出新的藝術形態,其中尤以廣播劇最具典型。廣播電臺初設之時,主要是新聞(語言)和音樂(曲藝)類節目為主,隨著節目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開拓,出現“廣播劇”這種廣播業獨創的戲劇形態。廣播劇對言語的強調非常明顯,民國的理論家甚而將廣播劇視為“純粹訴諸聽覺的一種戲劇”。廣播劇通過營造逼真的聲響效果、擬態化的環境,在民國時期獲得了極大成功。廣播劇對“言語”特點的重視和拓展在第一部廣播劇《恐怖的回憶》中就有生動的反映。該劇采用戲劇的形式,分為第一、二兩場,不過表現各種聲響極為逼真。“第二幕時,槍炮聲,轟炸者,人聲喧嘩,慘呼悲號”。“若去年曾受此痛苦而今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者聞之,則其感觸又何如也”。該劇“每半小時播送機關槍聲、炮聲等以醒聽眾,擬聲極肖,可謂開播音界之首創,聽眾皆誤為舶來品之留聲機片,實質人為之也”。概言之,娛樂播音與傳統的舞臺表演確有很大的差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聽眾只能靠“聽”覺來感受聲浪,娛樂播音大大弱化了“舞臺”的布景與運用,基本上全然依賴表演者的“言語”進行表達。播音的這種特性為一些擅長言語的說、唱類節目提供了充分發展的空間,類似相聲、滑稽、彈詞等“曲藝”類節目由于適合廣播播音的要求發展迅速,在電臺呈現出一派“繁榮”。但顯然地,那些強調肢體藝術及舞臺效果的藝術形式,如雜技、舞蹈等則一時較難通過純粹的“聲音”來表現,無法直接參與大眾傳播,這些“不合時宜”的演藝形態顯得較為被動,有些甚至陷入危機。只需將民國時期各類場所化的演藝形態與各廣播電臺節目表中的娛樂形態略加對比,便不難發現有些演藝形態根本就沒有機會走上電臺。作為一種新的大眾化傳播工具,廣播在豐富市民娛樂形態的同時,無疑在客觀上也導致了民國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發展的不平衡。
四、娛樂播音:大眾文化的表征
麥克盧漢曾把廣播比喻為“共鳴箱”,他說廣播以人與人直接打交道的私下親切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然而它其實是一種具有魔力的、能扣動早已忘卻的琴弦的、潛意識的共鳴箱。作為“共鳴箱”,廣播在受眾與社會之間架起了聯系的橋梁,有力量將心靈和社會合而為一。廣播與大眾文化呈現出一種極為復雜的關系,廣播既生產、傳播大眾文化,同時也深受大眾文化影響,展現、反映大眾文化的趨勢與特征。就此而言,娛樂播音不僅是文化權力在播音平臺相互角力競爭的結果,同時也直接體現大眾文化的情緒與風向。近代以降,西方藝術蜂擁而入,民國時期各類西洋樂器、演唱以及流行音樂開始充斥大眾娛樂空間。東西方文化的頻繁接觸與交流,也使得東西方藝術形態內在的競爭性關系日益緊張。以現代音樂最典型的歌曲為例,早在清末,漸興的學堂樂歌已為新音樂文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類歌曲絕大多數都采用了日本或西式的曲調,反映出鮮明的現代音樂特征。“五四”以后,主流文化心態對傳統的“揚棄”與對西方精神價值的“追捧”,更是導致舊式曲藝戲劇越來越受到知識青年的排斥,而西方藝術中“平等”、“獨立”、“自由”乃至“革命”的主題和內容則成為新的謳歌對象,這些特征在娛樂播音中有著淋漓盡致的反映。從表現上看,作為迎合西方價值觀念的重要表現形式,都市中親西方的“上流”階層普遍表達出對鋼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和藝術歌曲、歌劇、交響樂等演藝形態的偏好,甚至對西方音樂藝術的欣賞成為身份與地位的標簽和象征。與此同時,傳統娛樂形態熏陶下的老一輩受眾退出歷史舞臺后,受輿論界對傳統“舊樂”抵制心理的影響,新一代的娛樂興趣不再留戀于那些舊式的傳統,舊式戲曲的光芒很快被新音樂和流行歌曲所取代,新型音樂創作迅速崛起,現代藝術歌曲與抒情歌曲越來越受到都市民眾的喜愛。這一時期不少的音樂創作者都將自己的集子以“新”命名,從而將現代音樂推向了前臺。與此同步,都市中流行的廣播播音也為新音樂運動的狂飆突進完成了技術上的準備。廣播新技術生產與接收的分離,使得時間與空間的有效性大為擴展。借助娛樂播音,面向“大眾”傳播的現代音樂正日益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果說晚清西方藝術形態的涌入導致了東西方藝術形態的緊張與疏離,那么20世紀20年代以來廣播播音的盛行,則迅猛地推進了現代音樂的步伐,并促使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加速分化。
流行音樂的興起堪稱這一時期娛樂播音參與大眾文化制作的典型。作為民國大眾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廣播在信息傳播的同時,自然地參與了大眾文化的生產與制作。歌曲最能體現時代風貌與社會變遷,尤其是現代歌曲,其歌詞內容、歌曲旋律、演唱技巧、伴奏配器等更是與時代背景、流行情趣等息息相關。現代流行歌曲的風靡與廣播娛樂播音的發達幾近同步,這充分展示了兩者之間內在的緊密關系。黎錦暉創作的中國第一首現代流行歌曲《毛毛雨》誕生于1927年,此后經黎明暉演唱,通過收音機和留聲機傳遍大街小巷。民國時期,廣播、電影與唱片等載體造就了大批歌星、影星,這些娛樂界的時尚明星幾乎成了現代流行文化的引領者。有“金嗓子”美譽的周璇就成名于一家民營電臺和《大晚報》舉辦的“播音歌星競選”。周璇一生共演唱了兩百余首歌曲,這些歌曲之所以得以廣泛傳播,很大程度都要歸功于娛樂播音。周璇在這次比賽中一炮走紅,最后以落后白虹不多的票數名列第二,獲得“金嗓子”稱號。隨后,周璇開始在上海“友聯”“、新新”“、青鳥”等電臺播唱,受到聽眾熱情追捧。周璇代表性的作品如《四季歌》、《天涯歌女》、《夜上海》、《何日君再來》等,通過廣播和留聲機,風靡了大半個世紀,影響了幾代人。白先勇在《上海童年》中就曾回憶他童年時代上海的“周璇熱”“:那時上海灘到處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圓’,戶戶‘鳳凰于飛’。”最令白先勇不能忘懷的是周璇那首《龍華的桃花》“:上海沒有花,大家到龍華,龍華的桃花都回不了家!”流行歌曲在20世紀30年代的盛行,既與大眾傳播的平臺、工具的推動有關,同時也是受眾娛樂觀念、大眾文化自我選擇的結果。在這種新式娛樂節目興起的同時,傳統曲藝戲劇地位的相對弱化則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中國音樂也由此進入了新音樂與傳統音樂并行的“多元化社會音樂結構”的新時期。娛樂廣播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社會大眾文化的直接表現,具體節目形態的流行與式微事實上直接反映了大眾審美與社會心理的變遷過程。廣播節目的設置受到大眾文化的制約,反映文化市場的需求與方向。特別是商業電臺,聽眾成為電臺的生命線,在節目設置上更需要考慮迎合聽眾的口味。而廣播電臺的增多,娛樂節目的豐富,為聽眾發揮其選擇自由提供了可能。聽眾一旦擁有了收音機,便可以接觸到音樂、歌曲、戲曲、曲藝、話劇、廣播劇等涵蓋中外的豐富多彩的娛樂內容。這種的局面盡管看似欣欣向榮,但在“趨新趨西”文化心態影響下,各節目間的內在競爭卻使“百花齊放”得“新勝舊汰”成為必然。廣播節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國流行文化的發展軌跡。如果以時間的順序羅列出上海灘上廣播電臺節目設置的比例分布,或者各個時段最受聽眾歡迎的節目形態,當不難看到流行文化“變動”、“流行”的特征在電臺中具體是如何體現的。1939年6月,上海婦女補習學校的一份針對學生娛樂興趣的調查顯示,面對“你最喜歡哪幾種無線電播音?”這一問題,前五位的答案分別是音樂、歌唱、故事、話劇、滑稽。這幾種娛樂形態中,音樂與歌唱無疑都是新式的娛樂節目。音樂、歌唱的獨領風騷表明部分受眾的娛樂興趣已經發生了轉移。不過也應看到,盡管新式學生對音樂、歌唱情有獨鐘,但仍有不少的觀眾迷戀那些“觸電”的傳統節目。俞子夷曾描述30年代中期娛樂播音的特征“,娛樂中彈詞占第一,私定終身后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可以說是大眾最歡迎的了。歌唱、話劇等可算是后起之秀,平均每家也有一檔”。《鳳凰月刊》曾在上海舉行最受歡迎的廣播節目評選。結果,當時的彈詞《小伙計》當選“最佳開篇”故事。這次評選總共收到3184人投票,其中1745人選《小伙計》。這些評選清楚地折射出民國滬上普通市民的娛樂與審美傾向。同時也指明,盡管歌唱、話劇等新的藝術形式漸趨流行,但地方性的、傳統的娛樂和節目形式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它們仍然受到許多人的歡迎。民國時期的受眾群體、娛樂市場與消費形態都呈現出新舊并立、復雜多元的結構。
當然,娛樂播音對大眾文化的生產根本源于商業利潤的驅動,娛樂形態的流行與否受到社會文化、受眾審美等多重因素的制約,這之中當然還飽含著阿爾都塞所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生產、社會秩序對大眾文化的操控。從這一角度觀察,娛樂播音的變化也是官方認同的“現代性”、社會輿論慣有的道德底線、時代語境賦予的民族話語以及聽眾自我選擇等多重因素不斷協商的結果。1933年5月29日,旅滬寧波同鄉會就部分電臺仍在播送“四明文戲”唱片一事致函各相關電臺,申明立場:查無線電播音機播送各種新聞、商情、音樂等等,原為發展文化,便利商業,并輔助社會娛樂,立意至善。詎近有一二無線電播音臺,為牟利起見,竟采用四明半客唱片,詞語淫穢,不獨有關風化,而且影響國譽,實與播音原則未盡吻合。值此風俗頹廢之際,豈再容推波助瀾,流害社會。為此專函警告。至希查照,迅予停止此種穢褻唱詞之播送,庶于國譽風化兩有裨益,當為貴電臺所樂從焉。民國娛樂播音的迅速崛起致使廣播播音規范并不成熟,特別是民營商業電臺為爭取聽眾,有意無意地增加了播音內容的“淫詞穢語”,故而類似于禁止“四明文戲”的社會輿論,甚至禁播的行政舉措時常可見。嚴獨鶴就批評上海各電臺所播送的娛樂節目多數是“靡靡之音”“,對于民眾德性和社會風化很有妨礙”,因此強烈要求“加以糾正”。特別是在國難當頭、國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電臺卻依然不關國事,終日“陶醉于俚詞艷曲”之中,讓知識精英痛感民眾的麻木。嚴氏的憂患不無道理,即使在“八•一三”事件后的上海,上海的廣播電臺仍然生活在“醉生夢死”之中。“我們細看節目,真是失望。再聽播音把指針轉到利利電臺,就聽到程李的毛家書,開篇叫作宮怨,是楊貴妃吃醋,倒不如嫁個風流郎,朝歡暮樂度時光”。“這國家生死存亡之秋,還唱這種歌兒,優游自得,真叫不知亡國恨了”。在救亡的時代語境下,流行與救亡被知識界制作成為一種話語悖論。一方面,抗日救亡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在電臺中反復播放,喚起、激發民眾的愛國熱忱;另一方面,大量的娛樂播音節目則被納入禁播的范圍,這其中雖然確有“有傷風化”的作品,不過因為道德標準模糊不清,顯然也有不少的作品遭到誤傷。顯然地,社會精英和地方政府都試圖通過操控播音娛樂的內容進而對大眾娛樂加以掌控,將其政治主張灌輸在播出的節目之中,試圖把“新的”“、積極的”“、進步的”要素灌輸其中以“教化”聽眾。民國播音娛樂的主題傾向,無論是浪漫史、“淫蕩”、“暴力”,還是愛國、現代、西化,顯然都反映了外部社會轉型和政治的演化。在民國的娛樂聲浪中,受眾的選擇、意識形態的生產與操控,商業與消費文化的表達互相交織,彼此裹挾,從而塑造出復雜多樣的社會文化形態。在看似雜亂無序的娛樂播音浪潮中,既有新的催生,也有舊的掙扎。盡管糾纏與沖突不斷發生,不過就總的趨勢來看,聽眾審美越來越表現出對“現代性”的迷戀、“流行”的追捧,現代大眾文化明顯呈現出“流行性”、“現代性”、“民族性”的趨向,傳統的娛樂節目盡管還有較大的市場,但日趨邊緣化的趨向卻愈發明顯,現代的演藝形態與娛樂形態正在不斷被重塑與改寫。
五、小結
本雅明論述說:新技術、新生產和消費方式,19世紀工業化帶來的所有變化,已經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人的感性,并由此在世界上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隨著整個存在方式對人類集體的改變,同樣也改變了他們的感知方式。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出現的廣播播音對于傳統農耕文明的中國社會而言就是這樣一種新技術、新生產和新的消費方式。民國時期,娛樂播音成為各廣播電臺播音的重要內容。娛樂播音的盛行意味著一種新的娛樂生產、娛樂消費方式的生成。作為一種新的娛樂方式,娛樂播音的發達一定程度改變了舊有娛樂生產、傳播的方式,引發了近代娛樂形態的嬗替。相較傳統的演藝形態,民國娛樂播音節目的演出形式有著顯著差異。娛樂播音基本上全然依賴表演者的“言語”進行表達。播音的這種特性為一些擅長言語的說、唱節目提供了發展空間,類似相聲、滑稽、彈詞等“曲藝”類節目由于適合廣播播音的要求得以迅速發展,而那些不適合播音的藝術表演形態則因失去了“流行”的機會處境維艱。盡管舊式的節目仍有相當的生命力,但音樂、歌曲、廣播劇等新式節目的比重日益增加,舊有娛樂節目的式微已屬必然。廣播在民國時期的崛起及其對娛樂形態、大眾文化的改寫與重塑,無疑是近代大眾傳播語境下技術、娛樂與社會多元互動的一個縮影。
作者:龍偉 單位: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
- 上一篇:茶園文化與國人早期的觀影方式范文
- 下一篇:醫療和健康服務定性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