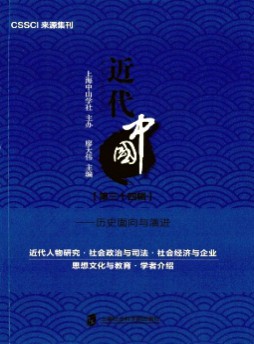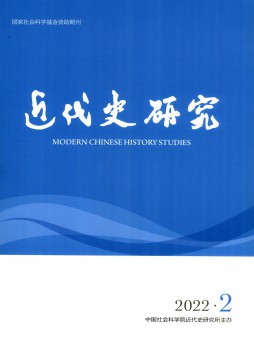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 加拿大 多元文化主義 族群權利 民族融合
加拿大自上世紀70年代領風氣之先、建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以來,在政治思想研究領域也產生了諸如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查爾斯?泰勒(Charles Tylor)、馬格利特?穆爾(Magaret Moore)等一大批影響世界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家。隨著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在世界上的傳播,國內學術界也展開了對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討論。本文擬在對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國內有的學者認為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具有“超越時空”價值的觀點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多元文化主義(multieulturalism)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猶太人學者霍拉斯?卡倫(HoraceKallen)1915年發表的《民主對熔爐》(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Pot)一文中。1924年,他在《美國的文化與民主》(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在此前的1922年,帶有多元文化主義精神的“馬賽克”概念和“多元文化”概念也在加拿大出現。但由于當時整個西方世界處在帝國主義階段,這種剛剛出現的新思想并未得到人們的積極響應。二戰以后,隨著亞、非、拉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和美國民權運動的展開,以及加拿大社會內部法裔民族和英裔民族之間矛盾的加深,多元文化主義重新成為熱門話題。在這一背景下,加拿大于1971年率先制定了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之后,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等國家紛紛仿效。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其理論成果,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也在加拿大獲得了巨大發展,并在西方世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什么是多元文化主義?加拿大學者克林?坎貝爾(C.Campell)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認為加拿大是由許多種族和少數民族群體組成的,作為群體,他們在介入財富和富裕上都是平等的。”查爾斯?泰勒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就是一種“承認的政治”。吉托?博拉菲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涉及到一個群體或具有不同文化經歷的社會群體的共存。”上述學者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含義各有不同的解釋,但就其共性而言,多元文化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在自由主義框架內以尋求族群平等與共存為目標、以承認族群權利為核心的政治思潮與政策。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家把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論,以國家承認和維護族群權利作為其核心內容。在他們看來,近代自由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把個人作為終極的道德主題,個人權利具有優先的地位。以此為基礎,自由主義主張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應該受到平等的對待、平等的關懷和尊重。針對自由主義的這種以個人權利為本的“平等的關懷”理論,詹姆斯?塔利認為這只不過是想在充滿文化差異的現代國家建立一種“一致性帝國”;在這一帝國中,所有的公民都得到了平等的尊嚴,然而它又以“一致性”為借口,消滅了原住民和其他外來族群的自治權利和文化傳統。在威爾?金里卡看來,這種忽視族群文化差異與集體權利的認識,“是一個極大的不平等,這個問題不解決將成為最大的不正義”。因此,在現實的政治建構中,應改革自由主義這一傳統,在國家框架內增加對少數族群權利的保護。具體而言,一是國家“對不同的少數民族文化采取特別的措施”,給予少數民族“特殊地位”,也就是通過“不同的公民權來保護文化共同體免受不必要的解體”;另一方面就是賦予這些群體以權力,如金里卡所言:“只有當一種措施明確規定了某一社群自身可以行使確定的某些權力時,才可以把它視為一項群體的權利”。
顯然,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在承認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的同時,賦予少數族群以一定的“集體自治權”,以協調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與多元文化主義所主張的“集體權利”之間的沖突。這種制度設計,既保護和承認了不同族裔的群體權利,又使這些群體中的每個成員依然具有公民歸屬感。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者對族群集體權利的強調是以族裔文化為基礎的。他們在闡述文化對族群的意義時,反思了近代自由主義在此問題上的局限性。在他們看來,近代自由主義不論是從“契約論”角度證明的個人的自然權利,還是從功利主義角度證明的個人幸福、自由,就其共同特征而言都是把個人及其所屬的文化共同體分離開;認為人是一個獨立、自由、平等的“原子”,是目的本身,具有終極價值。
第2篇
關鍵詞:現代性;古今之爭;波考克;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對現代性的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近二三十年中國的現代性研究也逐漸起步,在政治思想領域,自由主義有柏林和羅爾斯等為代表,特別是其兩種自由的區分影響很大;施特勞斯學派則因隱微寫作與重啟古今之爭而聲名大噪;此外就是劍橋學派,以以斯金納和波考克為代表,其中波考克雖然在中國不甚知名和流行,但卻是深入理解現代性,特別是古今之爭必不可少的一個路徑。波考克說他“秉持這樣一種歐洲視野:伴隨著古代地中海帝國奔潰歷史的是商業社會的不斷興起和擴展,但與此同時依然受到古代價值的挑戰。”[1]這開啟了他對馬基雅維里時刻的理解。
一、馬基雅維里時刻的意涵
雖然用“時刻”(moment)這一表達是斯金納的提議,但2003年波考克指出“該術語(‘時刻’)既可以指馬基雅維里的出現及其對政治思考的沖擊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也可以指他的著作所指出的兩個理想時刻之一:或是指‘共和政體’的形成或奠基成為可能的時刻,或是指這種政體的形成被認為帶有不確定性并在它所屬的歷史中引發危機的時刻。”[2]
第一個“時刻”,即馬基雅維里活著并寫作《君主論》和《論李維》的時代,具體指“佛羅倫薩思想……1512至1537年,出現了馬基雅維里、圭恰迪尼和詹偌蒂的轉折性著作。”[3]這是個佛羅倫薩時刻,馬基雅維里是其中的最強音。另外一個含義則是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熔煉,即《君主論》和《論李維》中包含的“理想”:拯救危機中的共和國或創建共和國。就具體的歷史而言,指1494年法國軍隊到達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統治土崩瓦解之時。馬基雅維里最初是參與到了政治之中的,其寫作《君主論》也懷抱著再次參與政治的期待,但并未成功,這種雄心從政治轉移到了寫作。書寫如何“拯救危機中的共和國”甚至“奠基新的共和國”。波考克認為“這樣的時刻彼此無法分割,因而就出現了‘馬基雅維里式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共和國深陷歷史的緊張或矛盾之中,這樣的緊張或矛盾要么出自自身,要么來自外界。”從“時刻”出發“考察了早期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許多(但不是全部)有關這種‘關鍵時刻’的經驗和關節點。”[4]對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的考察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因為“我們遭遇了‘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古代’與‘現代’自由概念的差異,在我看來《時刻》所關注的正是他們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的歷史仍在進行中,并沒有終結”,[5]或說英國在近代也經歷了這樣的關鍵時刻,因而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段政治思想史。
波考克所揭示的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可被理解的。簡要說,有一個理解模式,它有三個要點:積極公民、武裝共和國與區別于“right”(正義或權利)的“virtue(德行)”。
積極公民是想過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人的總稱,“具有政治知識的即被統治有參與統治的”人,不是純粹被統治的奴仆。這種思想在根底上可以說是“極端的古典思想”,并且“從政治上和道德上說,‘公民生活’是抵抗‘命運’肆虐的唯一力量,也是個人具有美德的必要前提。”[6]武裝共和國則是馬基雅維里對古代思想的改造,原型是“武裝的先知”摩西及其所建立的“國”。思想基礎就是“武裝公民”,這是“virtue(德行)”的核心內涵,“羅馬意義上的virtue,即馬基雅維里使用并力圖復興的托斯卡納意義上的virtue的羅馬意涵,意指個人采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能力。”“它既是高度公共性的,也是高度個性化的。”[7]
這個模式也可以被稱為“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思想模式,以此模式衡量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能夠承認早期近代英國(英格蘭)政治思想中有許多這種“關鍵時刻”的經驗和關節點。
二、近代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
從上述思想模式的三個要點看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是一個簡要而非全面的方式,不過從這個三個要點確實能夠看到一種不同于歐洲大陸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方式。
首先,從積極公民生活這個角度來看,就面臨一個問題,這源自英格蘭自身的歷史,“在這個文化中并沒有出現對‘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相對簡單的選擇以及共和主義對歷史自我形象的改造。” “僅僅理性和經驗絕無可能提供把個人稱為公民的理由,只有復活古代的政治‘德性’(virtus)和政治動物(他有著統治、行動和做出決斷的天性)的觀念,才能做到這一點。”[8]這意味英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出現與歷史‘時刻’或說事件――1640年代的內戰有關,在其中古典共和主義理論發揮了它的作用,這種作用是英國“公民”觀念產生的重要部分。
第二個要點即共和國。這與一份文件有關,即1642年6月21日的《陛下對兩院十九條建議的答復》,它不僅是英國政治思想上一份至關重要的文獻,也是打開馬基雅維里分析之門的鑰匙之一。這份文件有兩個關節點意義,一是在英格蘭第一次重現了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政府理論,而這種重現(復興)也正是1494年后意大利政局步入緊張狀態的重要思想結果之一。產生于內戰期間的兩個政治思想巨著《利維坦》和《大洋國》,其思考和思想理論的建構“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穩定與和平。”“自然之路需要和平,和平之路需要服從法律。在英國,法律必須成為大眾的法律,而這些大眾的法律的總和必須等同于共和國。”[9]“英格蘭人從天性上說是贊成君主制和習俗的動物,采取平衡和共和政體的語言,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憲法受到了失序的威
脅”。[10]這意味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對佛羅倫薩版將會有不小的修改。
第三點,“德行對抗命運”這一模式在英國的變換。哈林頓是波考克考察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核心人物。在哈林頓的《大洋國》之前的時刻,“德行”不是道德而是武裝,這是馬基雅維里思想的一個特色內容。在16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的思想家中,強調“威尼斯模式”,使“它能夠成為羅馬的反題,因此有助于把人們的注意力從馬基雅維里的軍事平民主義上移開。”不過在英國則不一樣,英格蘭此時的統治就是刀劍的統治。并且“刀劍的時刻可以由君主、立法者或先知占據,也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占據。”[11]
英國實際政治中,“有兩點尤其是產生和代表了英國共和主義的思想,首先是對武裝的強調,將政治自由等同于軍事力量;第二個特征是普遍意識到的偶然性,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輝煌,共和政體的生命依然是動蕩的和短暫的。”[12]雖然其目的不過是論證“事實上的權力”是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權,但是“當軍隊反對這個政權時,尼德漢姆就會發現自己處境尷尬,英格蘭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歷史就會有一個新的起點。”[13]這個新的起點就是哈林頓。
哈靈頓在“德行對抗命運”的模式中引入了“財產”,從而促成了這一模式的變換。《大洋國》是哈靈頓的核心作品,“該書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標志著突破范式的時刻。”按照馬基雅維里的觀念對英格蘭政治理論和歷史進行重要修正。因為“他要為英格蘭的軍事共和國辯護,把它說成是‘武裝平民’的統治。”他為此不僅“編造了刀劍的公共歷史”,還“提出了一種公民理論”,“說明英格蘭人是公民,英格蘭的共和國要比自封的圣徒寡頭政體更接近上帝”。“把這些認識納入歐洲和英格蘭的政治權力的一般歷史之中,其基礎是馬基雅維里擁有武裝對于政治人格必不可少的理論。”[14]乃是其關鍵性創新之處。
武裝平民與積極公民結合的公民理論,還有一個關鍵點,這就是設定政治人格的基礎是財產。哈靈頓對馬基雅維里所強調的“嚴重的道德腐敗,公民人格的實際解體,是政府衰敗的主因”做了重要修正:“政府的‘腐敗’與其說是因為公民不再展現適合于他的美德,不如說是因為政治權威的分配不再與對它其決定作用的財產分配適當地聯系在一起。”哈靈頓把財產稱為“命運的恩惠”,并且“他特別聲明,他關于財產和權力關系的一般法則,對動產和不動產同樣適用。”因而“自由財產的功能變成了為自由的公共行動和公民美德而拿起武器,從而也是人格的表達。”[15]
簡言之即“自由和獨立取決于財產”,因而財產稱為了一種公民資格,更進一步是美德來自于自由財產,因而對抗“命運”必須有自由財產,如此而來,對自由財產的侵蝕就可被理解為“腐敗”這一命運的體現物。
在哈靈頓之后,“德行對抗命運”的模式先是轉換成了“德行對抗腐敗”,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出現了一種新觀點:“變化現在不在被視為純粹的混亂,而是被視為可以理解的社會和物質過程。美德的對立面不再是‘命運’,而是變成了‘腐敗’。”腐敗不僅僅指官員的腐敗或生活的腐化,政客收受賄賂濫用權力等政治腐敗行為,而是“在圭恰蒂尼那兒最先看到的那種含義:用私人權威取代公共權威,用依附取代獨立。”[16]從1688年到1776年,盎格魯語系的政治學的中心問題,不是能否反抗惡政,而是建立在庇護權、公債和軍隊職業化上的政權是否會腐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腐敗不是一個權利問題,而是一個“德行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申明反抗的權利得到解決。
政治思想決定性地轉向了德行與腐敗的范式。[17]光榮革命后的英國“不論哪個黨派的作者都不想為股票買賣和對公債市場價值的投機性操作辯護,它(信用)被普遍視為罪惡。”“簡言之,托利黨抨擊牛市,輝格黨抨擊熊市。”[18]爭論的核心點雖然是財產,但實際上的中心依然是“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因為不動產依然被看作是美德的基礎,而商業財富的重要性雖然被提及,但貿易被認為是新型腐敗的原因,信用更是被公認為“邪惡”。
三、反思古今之爭的新路徑
商業使“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發生變換乃至改變“德行”本身的含義。商業帶來的改變看起來不可逆轉,盡管一些著名思想家都反對這一趨勢,但是商業社會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德行也借助于“風尚”的概念進行重新定義,個人脫離了享有公民權的農民-武士世界,進入了“商業和技藝”的交易性世界。這些新的關系從性質上來說是社會關系而非政治關系,因此他們使個人能夠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德行”,而只能被稱作“風尚”。埃德蒙?伯克說“禮儀風尚比法律重要。……它既可襄助道德,補充道德,也能徹底毀掉道德。”[19]
改變“德行對抗命運(腐敗)”模式的是商業社會與自由主義的崛起。人取代了自然,權利取代了德行,擴張性的帝國取代了共和國,最終的災難性后果到今天已經差不多又快被忘卻了。
第3篇
徐復觀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有著現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返本開新”。在此文中,筆者將對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目的――其獨特的“開新”之路――作簡要論述。
關鍵詞:徐復觀;中國思想史;仁性;知性;民主
徐復觀是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與牟宗三、唐君毅并稱為“現代新儒學三大師”。與其他二人相比,徐復觀不是以建構個人哲學體系著稱,而是以中國思想史研究名世。他之所以注重中國思想史研究,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的新生比個人哲學的建立更重要。徐復觀一生游走于學術與政治之間。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主要通過現實的政治參與來為中國動蕩的社會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經過熊師“起死回生的一罵”,五十年代開始,轉而走上了學術之路,期通過對中國文化“現代的疏釋”,使自己的學術研究有補于中國、世界。徐復觀作為港臺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其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即“返本開新”。徐復觀是通過其中國思想史研究來完成其理論上的“返本開新”之路的。無疑,“開新”(開出科學與民主)即是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目的。
一、“仁性文化”與“知性文化”的“攝”與“轉”
徐復觀認為“仁性”和“知性”是人性的一體兩面。中國人發展了是人性中的“仁性”一面,進而形成了“仁性文化”;西方人發展了人性中的“知性”一面,進而形成了“知性文化”。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可能、也有必要融通與轉進,“可能”在于二者同為人性所發出,“必要”在于二者的結合可以解決中西方文化面臨的困境。徐復觀致力于通過“攝智歸仁”與“轉仁成智”來實現中西文化的融通與轉進。
首先,我們來論述徐復觀的“攝智歸仁”思路。此種思路是徐復觀面對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所形成道德精神是不同的。中國“仁性文化”下所形成的道德精神,認為人在自身與現實生活中即可找到自足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其特點是現實的、自足的。他提出,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價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話、迷信的力量,使每一個人能在自己一念之間,即可于現實世界中生穩根、站穩腳,并憑人類自覺之力,解決人類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產生的危機,中國文化在這方面的成就,不僅有歷史地意義,同時也有現代地、將來地意義。[4] (P.3)而西方的道德精神與中國的道德精神不同,西方的道德精神是知識型與宗教型的。一方面,“知性文化”形成了西方人以知識為道德提供基礎的特點。早在古希臘的哲人蘇格拉底那里,便形成了知識即道德的思想。到了近代,歐洲的倫理學家常常對道德的根源進行形而上學的求索;另一方面,宗教上的罪惡感是形成西方道德的另一個基礎。如基督教的原罪觀念,要求人們通過信仰上帝獲得救贖。西方的道德精神,在歷史上曾起到了積極的意義。人們追求知識,造就了西方近現代的科技文明;追求天國,造成了西方人虔誠的。但西方“知性文化”的過分膨脹,造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困境。一方面,知識的極端運用,導致了科技理性主宰一切,不承認價值上的東西;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人們更加注重對物的追求,而拋棄了原有的宗教虔誠,罪惡感喪失殆盡。此二者共同導致了西方物欲的泛濫與人們精神的空虛。面對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徐復觀提出了一條救治思路,即“攝智歸仁”。“攝智歸仁”是以“仁”來衡量、判斷“智”的成就。以“仁”來統攝“智”,使“智”在作用的過程中,能得到“仁”的規約、引導,以朝向有利于人生價值之實現的方向進發。此即徐復觀的“攝智歸仁”思路。
其次,我們來論述徐復觀的“轉仁成智”思路。此種思路是徐復觀面對中國物的匱乏進而導致“仁性”的困厄而提出來的。在徐復觀看來,中國文化未能在物的方面得到很好的發展,物的貧瘠致使中國“仁的文化”得不到充實。對于此種困境,徐復觀提出的解決之道是“轉仁成智”,即從“仁”中“轉”或“生發”出“智”來,以彌補因單方面“仁”的強化,而導致科學技術的弱化,又反過來對“仁”的限制。徐復觀認為:“今后的儒學之需要科學,不僅系補其人性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所缺的一面,而且也可輔助我們文化已經發展了的一面。仁性和知性,道德和科學,不僅看不出不能相攜并進的理由,而且是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的人性的整體。”[3] (P.38)“仁性”與“知性”共同組建了人性之全,中西兩種文化的融合,勢必既也有利于西方走出困境,又有利于中國的復興。此即徐復觀的“轉仁成智”思路。
下面我們對徐復觀的“攝智歸仁”和“轉仁成智”進行簡要的評析。徐復觀認為“仁性”與“知性”是人性的一體兩面,將來的中國和西方必將向人性之全的方向發展,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徐復觀認為,在此二者中,“仁性”因其具有價值色彩,所以是更根本的、更重要的,而“智”的作用只是對“仁”起滋養作用,提供“仁”所需的物質基礎。因此,無論是“攝智歸仁”還是“轉仁成智”,都因對“仁”的過渡執著而帶有價值一元論的色彩。導致徐復觀價值一元論的根本點,在于其認為“仁性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價值,有著虛靈不滯的品格并且是沒有古今之分的。徐復觀認為:“文化的價值方面,不能分古今。價值的基本精神,沒有古今的分別。”[5] (P.7)黃克劍對徐復觀這種認識的批評可謂切中要害。黃克劍認為,道德價值的具體實現是要受一定的歷史境遇局限的,它不可能在歷史之外孤芳自賞。道德價值的超越性是在對道德價值歷史地實現過程中的批判與超拔,因此,其超越性與虛靈不滯的品格,不能被理解為與歷史現實絕對隔絕的存在。超越性存在于現實的超越過程之中,而不是與現實無干的絕對存在。現代新儒家諸學者都重視道德虛靈不滯的“常”性,但如果將這種“常”性絕對化,就有可能忽略道德價值歷史地實現的具體性和局限性,將道德價值的人間性遺忘。此外,儒家的“仁”不是脫離歷史上一個個具體的個人的道德修養的抽象價值,而是在其每一次呈現的過程中都有其確定內涵,這內涵不可能與特定背景下的知性無關。沒有仁愛的知識和沒有知識的仁愛同樣是危險的,徐復觀缺少對傳統儒家脫離知性的“仁”的反思和批判。[6] (P.41)其實,“仁性”與“知性”是一種平等的關系,任何一方面對另一方面的宰制,反倒使宰制的一方失去其本來價值。“知性”不反對“仁性”,反過來講,“仁性”也不能“轉”出“知性”。就“仁性”不能發出“知性”而言,“轉仁成智”不能成立,就“知性”不屬于“仁性”而言,“攝智歸仁”也不能成立。其實,西方現代道德的危機,并不在“智”本身,而在使用“智”的人的道德危機。因此,對西方“智”的濫用的救治,需要通過“仁”的提升來救治“不仁”所導致的結果;而對中國“智”的不足所導致的物的匱乏,需要通過“智”的提高來滿足。如此,則全矣。
二、儒家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
徐復觀后半生遠離現實的政治爭斗,走上了學術的道路,但是其對政治的關注卻一如既往,可以說其是以學術的方式回歸政治。在徐復觀看來,現代化內在地包攝著民主政治,中國民主政治之建構,僅依靠儒家的政治思想顯然行不通。儒家政治思想有民本而無民主,有禮治而無法制,無法直接承擔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而直接引進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是行不通的,因為西方民主政治也有其短處,即缺少道德自覺的精神。
那么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當采取何種方案呢?徐復觀通過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希望將儒家的道德觀念與西方的權利觀念結合起來,建立一種以儒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徐復觀曾說:“要以中國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為民主政治的內涵,改變中西文化沖突的關系,成為相助相即的關系。”[2](P.320)那么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西方的權利觀念該如何結合呢?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徐復觀首先駁斥了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是導致專制制度的根源之觀點。徐復觀認為,儒家的政治思想不是導致古代專制制度的根源,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根源在以韓非子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想,而法家之外,都有著民本的要素。法家思想的基本理論預設是人性惡理論,認為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這種理論所導致的政治制度是這樣的,君主高高在上,臣民俯首在下,君主對臣民有著絕對權威,而臣民對君主必須絕對服從。法家思想也必然反對儒家的性善論,反對儒家君主修身以安百姓的思想。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不應為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負責。那么儒家與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徐復觀認為,在中國古代長期的專制社會中,儒家在專制制度的重壓下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歪曲”,但也起到了補偏救弊的作用。在其看來:“儒家思想,乃從人類現實生活的正面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虛無空寂,也不能逃避向觀念的游戲,更無租界外國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以擔當人類現實生存發展的命運。在這種長期專制政治之下,其勢須發生某種程度的適應性,或因受現實政治趨向的壓力而漸漸歪曲;歪曲既久,遂有時忘記其本來面目”[1] (P.8),但即使這樣,“儒家思想,在長期的適應,歪曲中,仍保持其修正緩和專制的毒害,不斷給與社會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華民族,度過了許多黑暗時代,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來的道德精神的偉大力量”[1] (P.8)。可見,徐復觀認為兩千年來的歷史,有良心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雖然在專制制度的重壓下,受到現實政治一定程度的歪曲,但還是盡到了一些補偏救弊的責任。以上,我們知道儒家不但不應為中國古代專制制度負責,而且還對減輕專制制度的毒害盡了補偏救弊的責任。徐復觀認為,對于民主政治而言,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各有其優缺點。這就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結合成為可能。徐復觀近三十年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掘井及泉,挖掘出了儒家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接合點。
首先,雖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包涵著民主政治的重大精神因素,但是卻缺少民主政治的主體,這使得古代中國終究沒能發展出民主政治,因此我們需要學習西方民主政治,使中國形成民主政治的主體。徐復觀認為,儒家政治思想中蘊涵著對人性的尊重,并且民本的思想與民主也很接近,此外,禮治中的禮的思想也與制定法的規范只有一墻之隔,此三者都已與民主政治有著某種程度的契合。但是,中國缺少民主政治的關鍵因素――政治的主體。他指出:“儒家總是居于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政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明的對照”[2] (P.83),總之,中國缺少“真正政治的主體”[2] (P.83)。徐復觀認為,政治主體的建立,需要將儒家的政治思想,從以統治者為起點,來為人民負責的思想,變為以被統治者為起點。補上我國歷史中未經歷的階段――個體權利自覺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到客觀的構造。[2] (P.83)
其次,儒家政治思想重視個人的義務勝于權利,其是以個體道德的自覺來成就群體的和諧,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個人權利的爭逼出群體的不爭。兩相比較,前者要優于后者。因此,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當吸取儒家政治思想之長。徐復觀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第一階段的根據,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第二個階段的根據,是相互同意的契約論。自然法與契約論,都是爭取個人權利的一種前提,一種手段。所以爭取個人權利,劃定個人權利,限制統治者權利的行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義。在劃定權利之后,對個人以外者盡相對的義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二義。因為民主政治的根源是爭個人權利,而權利與權利的相互之間,必須有明確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圍,乃能維持生存的秩序,于是法治便成為與民主政治不可分的東西。”[2] (P.82)可見西方民主政治產生的理論依據是以爭成其不爭,以私人的利益的爭來成就集體的利益。這種通過爭成就的不爭,是通過人與人的互相限制逼出來的,而非出于個人道德的自覺與自愿,因此不一定安穩,時時有可能崩塌的危險。與此相比,中國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可貴之處,是以個體道德的自覺,來成就群體的利益。因此,徐復觀看來,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中,應當吸取儒家思想重視個體道德自覺的方面,這樣的民主政治建構才能更牢靠。
以上是徐復觀對儒家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的分析。徐復觀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無疑是希望在中國的大地上重新復興儒家,其不只希望儒家在思想上的復興,更希望儒家思想能夠參與到現實政治的建構。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徐復觀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思路大體是這樣的:首先補上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個體權利的自覺,再通過儒家的責任、義務觀念超越由孤立的個人組成的共立狀態。在我們看來,個體權利的自覺匪易,而對孤立的個人組成的共立狀態的超越尤難。徐復觀所提出的這樣一種中西結合的思路,其思想初衷無疑是好的,但這種思路在現實的實現上如何呢?就連徐復觀自己也認為“未免有點近于神話”。既然現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我們必須經歷民主政治,也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上去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成果,那么徐復觀的這種思路無疑是值得借鑒的。但現實的情況,往往要比人們想象的還要復雜。目前看來,中國的儒家思想想重新成為意識形態的主導只能是一個夢幻,其只能作為一種傳統的精神資源被批判地吸收,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一種精神依憑。
參考文獻
[1]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上)[M].上海:海書店出版社,2004.
[2]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第1卷[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3]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第2卷[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4]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第4卷[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