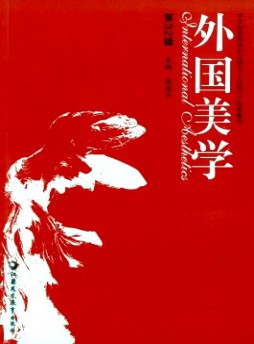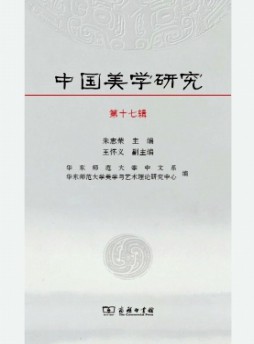美學思想的當代意義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美學思想的當代意義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南京社會科學雜志》2015年第九期
漢末至魏晉是中國美術發展的重大變革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產生了前代所未有的新畫風,產生了以繪畫為職業的文人畫家,而且形成了獨立的審美意識和藝術精神,留下了我國美術史上第一批畫論,無論是美術實踐還是美學思想,都對后世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顧愷之又處于最顯赫位置,往往被視為人物畫和山水畫之祖,而其“遷想妙得”、“傳神寫照”等美學命題則被視為魏晉玄學的美學思想完成,揭開了中國藝術思想的新一頁。由于這一獨特位置,自唐以來,顧愷之一直受到歷代研究的重視。本文試圖在中國文化自信呼聲高漲這個語境中進一步探索其實踐和理論的當代意義。與一般美術史對技法的偏愛有別,本文更加突出德沃夏克“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的概念,從魏晉時代國人思想變革角度強調顧愷之“遷想妙得”、“傳神寫照”乃是藝術之自由、個性和神圣精神的體現,而歸根結底源自對時代課題的回應、生命意義的追求和精神進步的開拓。
一、圖像史與精神史:藝術作品的韻味
從鑒賞角度說,“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屬完全,為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唐代以來,顧愷之在中華美術史上獲得了不可動搖的至上地位。湯垕從藝理角度的評價則幾成標準見識,“顧愷之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①。唐以來,圍繞顧愷之的“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之妙產生了大量的評論和研究。千百年來,從其作品的品第高下,到其“傳神論”和繪畫技法的內涵和意義,再至其時代特點及普遍價值,以及涉及一般藝術史事實的生平、作品真偽、畫論校勘等,各方面均形成了重要成果。在今天,圍繞這些問題產生新論不僅困難,而且甚至已無必要。不過,有一個宏觀問題始終是有巨大價值的,即顧愷之“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之妙在中華藝術史上的一般意義和在今天的特殊意義。這個問題,涉及對中華藝術史發展內在脈絡和當代動向的基本理解,當下的藝術史研究理應重視。就顧愷之來說,他的作品以及美學思想的巨大影響是個基本事實。顧愷之絕非是那種單線條的形象。在思想底蘊上,儒釋道兼容并包;人物、山水、什物神話等題材在其繪畫作品中均有涉及;除《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等傳世作品外,其畫論亦開中國美術先河;當然,其在詩、賦、記、序等文學形式上的造詣亦得到廣泛承認。簡言之,他可稱得上布克哈特所稱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那種“全才”(L’uomouniversal),即代表著個人完美化的那些知識分子②。由這樣的人開始中華藝術史的新篇章,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仍然需要追問的是,他的貢獻僅僅在于代表著晉風作為一個繪畫新時代的出現(如同時代謝安稱贊其畫“自生人以來未有也”),還是把審美提升到文化自覺的高度?在后一意義上,顧愷之不只是我國藝術史上的一個環節,而是中華文化審美精神的原型代表之一。
經過千百年研究積累,這一點已經得到公認:顧愷之的創作和畫論使得漢代繪畫多重動態、外形生動的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注重外形轉向內心世界,由注重形似轉向注重神韻,這便把繪畫境界提到一個新的水平。不過,真正在理論上清晰而有說服力地闡明這一事實意義的,當屬徐復觀和李澤厚。前者認為以顧愷之為代表,在中國人的心靈里所潛伏的與生俱來的藝術精神在魏晉時代成為文化的普遍自覺③。后者則論證,魏晉的“人的覺醒”帶來了“文的自覺”,“韻”和“神”成為中華美學的重要范疇,顧愷之當推首功,即“魏晉玄學的美學在繪畫理論上的完成”④。這種評論十分重要,它不只是解決了顧愷之的歷史地位問題,而且更重要是其對背后中華藝術乃至文化的獨立理解問題。可以說,徐復觀和李澤厚的深刻之處正在于他們對中華文化變遷的獨立理解,以其為背景亦闡述了一種獨立的藝術史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其與德沃夏克關于“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概念一致,即將美術視為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之精神的凝結和體現,因此要理解一種特定的藝術,必須理解其產生時代的精神史⑤。徐復觀強調,中華文化的審美精神在先秦老莊道學中便已蘊育,然而在魏晉之玄學支持下才得以成為普遍自覺,關鍵在于藝術性生活與藝術上的成就之合一;在李澤厚看來,從漢代的宇宙論轉向了魏晉玄學的本體論,其中心課題是要探求一種理想人格的本體,人的內在的精神性成了最高的標準和原則。他們二人都強調了藝術精神主體之獨立的意義。這一時代精神恰恰是在秦統一中國之后最為漫長(369年)而復雜(大小30多個王朝)的分裂和割據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文化上,這同樣是中國歷史上與先秦諸子百家之形成相比肩的時期,中華藝術精神的自覺表達在其中則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其確切的意義便在于,如徐李二人所指出的,代表著人的覺醒。甚至,對照西方歷史,它是早熟的“文藝復興”。由此不難理解,顧愷之雖具魏晉特色,但其意義卻不受時代限制。我們無意卷入更復雜的爭論,而是以此作為切入口來闡明顧愷之對于今天文化創造的意義和價值。那種意義和價值維系是對精神史的貢獻而不是某種獨特的藝術風格,風格可能像今天的時尚一樣,“唐肥漢瘦”,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藝術精神卻始終是由文化自覺所維系的。正是這一點解釋了顧愷之對儒釋道的兼容并蓄的接納、創作與評論的并舉、其集“才絕,畫絕,癡絕”于一體的“全才”特征。因為,這正是其全方位地介入時代的征兆,亦是其觸摸到時代精神的前提。在這里,我們通過其《維摩詰像》的解讀簡要地說明。
在顧愷之研究中,唐代張彥遠的一個評論影響很廣,他稱“遍觀眾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知。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幾忘言之狀,陸與張皆效之,終不及矣。”⑥關于這一評論,后世產生多種反應,其中流行之一便是以他的“以形寫神論”來詮釋技巧的精湛或者粗劣,簡言之,將問題鎖定在技巧上。然而,這種在研究和教學都很普遍的技巧中心論或技巧崇拜論恰恰是藝術之細枝末節,套用歐陽修《賣油翁》之說,即“手熟”問題。實際上,真正具有震撼力的形式不是手熟而是心巧問題。顧愷之創造的形象,并不比其他人(如后來的吳道子)所作更代表維摩詰本人,而是代表著東晉名士的理解人格。要知道,正是在魏晉之亂世,維摩詰成為知識分子追求精神解放和個性自由的象征。正是圖像史與精神史之間的那種深刻關系決定了圖像的命運。在藝術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在西方近代藝術史上,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所創造的自由女神形象,不就是通過把18世紀逐步形成的現代性基本價值的自由精神置于真實的歷史進程中使之具象化嗎?在其被描述為“現實主義”的風格中不是同樣包含著顧愷之的“遷想妙得”之意嗎?所以問題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技巧,而在于圖像與精神之間的契合關系。更近的一個例子便是羅中立1980年創作的《父親》,其成為當代中國藝術的典范之作,并不在于其“照相寫實主義”風格,而是在后“”時代當人們從個人崇拜和政治狂熱走向普通百姓和生活時,他在最好的時候把中國農民形象如此生動而典型地呈現在國人面前,點出了時代主題。正如本雅明所言,藝術作品的意義在于其歷史性,即由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可復制的獨一無二的個性。可以說,顧愷之在中國繪畫初成階段,不僅以其實踐體現了這一點,而且在其畫論中以獨特的時代語言暗示了這一點。也正是這個問題的普遍性,使之超越魏晉時代的局限而對中華藝術史具有一般的參照意義。如果說顧愷之的藝術實踐和理論是自覺的,那么,這種自覺便在于對文化之根和時代精神的自覺。沒有這一點,就談不上文化的創造。
二、形式與內容:技法的意義
“遷想妙得”、“傳神寫照”是顧愷之畫論的要旨,這兩個要旨也是其最受關注的方面。也因此,對于這兩個命題的解釋汗牛充棟。與傳統偏愛從技法角度來闡明其意的做法不同,本文將立足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觀念將重點放在“什么叫遷想”和“何謂神”兩個問題上。在這兩個問題上,徐復觀和李澤厚同樣是我們思考的先驅。不同的是,我們不再重復他們基于語言學和文化史的復雜考證,而將重點置于其作品《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解讀上。一般認為,《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上極為生動的人物形象是魏晉風度的恰當體現。這些形象之形態動態的“骨”、“氣”關系清晰地表明了從“本于立意”到“歸乎用筆”的藝術法則。因此,傳統研究的焦點落在“用筆”上。今天看來,這是有局限的。故且不論全部藝術史已經清晰地表明藝術乃自由的技藝,如果美術實踐將自己固于格式最終將違背藝術精神從而喪失其文化創造意義,僅就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系來講,是否能夠脫離顧愷之的“神”(立意)而講清其“形”(用筆),這也是大可爭論的。關于“神”的解讀,在全部顧愷之研究中,徐復觀是最具深刻見地的學者。在他看來,魏晉時代,人倫鑒識作了藝術性轉換后,便稱為“神”,而這一觀念出于莊子。也就是說,“神”是中國文化用來評論人的用語,成于先秦而流行于魏晉。通過深入的文化史考察,他認為神即為精神,無論“神貌”、還是“風韻”等,都是同義的。他說,魏晉時代,“當時的藝術性的人倫鑒識,是在玄學、實際是在莊學精神啟發之下,要由一個人的形把握到人的神;也即是要人的第一自然的形相,以發現人的第二自然的形相,因而成就人的藝術形相之美”⑦。所以,有關“氣韻生動”思想要與傳神問題聯系在一起。在徐復觀之后,李澤厚進行了更為精細的文化史考證,不僅直接支持徐復觀的意見,而且做了進一步深化,在康德藝理基礎上,對魏晉文化精神和顧愷之的“遷想妙得”做出極為深刻的分析。在李澤厚看來,魏晉時代,不再僅僅從倫理道德的觀點來觀察和評價人,而且把個體的智慧、才能和性格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從而使先秦就提出的形神問題上升到審美高度。他認為,“一般常把顧愷之所說‘傳神’或‘寫神’之‘神’,解釋為人物的精神或內在生命。這看來也不錯,但失之空泛籠統,未顧及東晉時期對‘神’的特定的理解。……這‘神’不僅僅是一般所說的精神、生命,而是一種具有審美意義的人的精神,不同于純理智的或單純政治倫理意義上的精神,而是魏晉所追求的超脫自由的人生境界的某種微妙難言的感情表現。它所強調的是人作為感性存在的獨特的‘風姿神貌’,美即存在于這種‘風姿神貌’之中”⑧。
在此,“神”與藝術家個體所感悟和體驗的人生境界聯系在一起。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顧愷之等人代表的魏晉美術明確地表達了中國藝術的自覺。如果“神”是如此,那么,無論是“骨法”概念在顧愷之那里第一次明確地進入繪畫理論,還是其將“遷想妙得”作為重要的美學命題,都不難理解。因為,“骨”同人的精神有密切聯系,它便成為重視“傳神”的顧愷之之落點;而“遷想”作為不受形象束縛的自由想象,恰恰是主體精神自由的最佳表達。在李澤厚看來,“遷想”是一種自由想象,是一種“神會”,是一種精神性的感悟,“其最終目的是在直感地領悟把握那由想象所得的形象呈現出來的某種微妙的‘神’,亦即某種提到了形而上的哲理高度的精神、心靈的表現”⑨。至此,李澤厚基于中華文化變遷的整體結構和魏晉時代特色完整地解釋了顧愷之藝術實踐和畫論的內在邏輯,“傳神寫照”、“遷想妙得”等等美學命題,指向的都是一個中心問題:如何開拓一種人生境界。藝術之手法,如文學之修辭,乃變形技巧。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皮相(形式)上的像與不像,而是骨子(意義)上的個性。“眾皆謹于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顧愷之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不只因為其技藝超群(手熟),而是源自對生命和人生的獨特理解,不僅代表了魏晉時代表達的自由境界,而且直指人之存在之個性意義。如張彥遠早就指出的那樣,“顧愷之之跡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有全神氣也”。⑩正是在這一點,他的作品能夠超越時空,不斷地給后人以啟迪。神是人的本質,也是一個人的特性。傳神,作為人物畫的傳統,正是從顧愷之開始的。在上述語境中,我們再來看《洛神賦圖》。《洛神賦圖》依據曹植的《洛神賦》而作。一般認為,顧愷之文學想象轉化成了藝術形象,從而實現了某種藝術飛躍。在這種飛躍中,愛情元素和道教元素結合在一起,成為其“遷想妙得”藝術思想的一個佐證。盡管由于史料缺乏,我們難題再現其創作動機,但同樣可以肯定,這種解讀仍然丟失了一個維度。實際上,必須注意的是,在曹植以前,陳琳、王聚、楊修都寫過《神女賦》,且都是模仿舊傳宋玉所作《神女賦》、《高堂賦》。就此而言,曹植的《洛神賦》只是時代流行題材的運用。
這種流行說明什么問題?固然,《洛神賦》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意縫蜷卻又因人神殊途而無法交接的惆悵哀怨,但如果由愛情題材推演出反封建禮教問題,顯然是過度發揮了。社會界限與神人之間界限的隱喻使用,它表達的恰恰是被其限制的自然、自由。這正是顧愷之與曹植的相通之處。反過來,顧愷之的特殊之外在于,它借由這樣一個題材,以具體的形象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想象力。這不正是我們后人在其(臨摩)作品上感受最深的東西嗎?更進一步,我們就可以說,這一作品,其意義也不在于其人物形象或者吸引人的道教元素,而在于其整體的布局所展現的境界。在這一點上,陳綬祥對顧愷之作品之平面布局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視。他認為,從造型的角度看,中國繪畫自發端便傾向于觀念表達,這源自中華文化對觀念與符號的重視。在中國文化,“名”所造就的文化作用高于“實”所引起的具體感受,后者乃西方繪畫的重點。正是因為這一點,在技法,中國繪畫重“布局”而輕“再現”,即重視主體的經驗而輕視客觀的法則,顧愷之是先驅。其《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人物形象與空間關系貫穿著空靈飄渺的“神”、“氣”等感覺。在整體上,陳綬祥認為,“正是由于這種布局上的安排,終得以將繪畫從狀物、錄形、記事、表言等功能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引導人們去品味那外部無限的世界與內心無限的情愫,并在重視人的感情經驗與的總體特征上統一成空靈玄遠的境界,‘象’在其中,‘道’亦在其中,‘文’在其中,‘人’也在其中了。就此而論,這種布局觀念成為中國繪畫構圖的基本原則則是必然的”瑏瑡。換句話說,顧愷之的繪畫以其整體體現了象、道、文、人等追求的統一性,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是中國文人畫傳統的開創者。如果與西方繪畫作一對照,我們可以說,中國畫,整個畫面構成的是一種意境,而非一種西方與象征機制聯系在一起,總是受到客觀規則(無論透視法,還是明暗法)限制的能指。意境作為可依“意”而變的布局,其底蘊在于自由、個性和生命體驗,它超越了象征。這正是中國文人畫的獨特之處。就此而言,中國藝術之精髓在于:扎根生活,傳達生命意義。
三、表意與教化:藝術活動的境界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于天然,非繇述作。”瑏瑢張彥遠在其《歷代名畫記》中開篇便如此敘述,這亦是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文人畫之意義的準確定義。孔子早就定義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雖然在“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中沒有繪畫的位置,“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沒有藝術的位置,但如徐復觀和李澤厚所證,在魏晉時代,經由從教化到審美的轉換,(繪畫)藝術也便是變相的立言。也正是因為此,從繪畫史角度講,魏晉明顯地改變了漢代繪畫故事(傳統教化手段)顯著地占據著地位,代之以形象,但并沒有放棄說教。在顧愷之那里,《女史箴圖》便是典型。對于這個作品的摩本,我們不展開分析,而只是強調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顧愷之依據張華的《女史箴》創作為《女史箴圖》,無論動機是以具象推進后者諷諫妃嬪修德養性,為社會樹立品德典范之目標,還是將之推廣到更大范圍,對廣大婦女進行說教,他都是中國知識分子那種獨特的道德自覺。我們可以將之看作是魏晉的獨特時代要求,在政治動亂、思想危機的背景下,維護綱常名教成為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義務。
不過,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中華五千年綿而不絕,無論與政治層面的士大夫,還是社會層面的鄉紳,抑或文化層面上的文人,知識分子在其中所起作用十分突出。無論先秦時代的爭強好勝的諸子百家,還是魏晉時代喜歡獨立特行的文人墨客,抑或至近代在憂患和焦慮中或徬偟或吶喊的知識分子,歷朝歷代,無不體現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感。藝術領域并不是例外。因此,我們必須在今天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當我們回首顧愷之這樣的中國繪畫先驅時,是否能夠脫離這個事實去評論他的作品和思想?這是顧愷之研究必須要回應的問題。實際上,百年前,當有人將近代中國之沉淪歸結為文化之衰敗,直接提出拋棄文人畫傳統時,1921年,陳師曾便直接回應了這個問題。他在《文人畫之價值》的結論部分寫道:“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蓋藝術之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應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謂感情移入,近世美學家所推論,視為重要者,蓋此之謂也歟?”在中國文人畫起點上,顧愷之顯然集中了陳師曾所言這四素,更重要的是,在魏晉代表的中國美術史新的起點上,顧愷之代表著以獨立的審美精神向時問的那種只有藝術才能具有的特殊價值。他的例子告訴我們,只要提升境界、敢于引領精神進步就是創造新的文化。徐復觀曾經強調,“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出藝術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關鍵,并由此而在繪畫方面,產生了許多偉大的畫家和作品,中國文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不僅有歷史的意義,并且也有現代的、將來的意義”。本文試圖強調,盡管顧愷之具有魏晉時代的特殊烙印,但他卻能夠超出時代限制成為中國美術的一般代表。當代藝術的文化自信,并非意味著在悠久的歷史中找出像顧愷之這樣曾經很了不起的老祖宗,而是堅信只要像這些先賢一樣———立足社會,勤于回應時代課題;扎根生活,精于傳達生命意義;提升境界,敢于引領精神進步———便能夠創造輝煌的文化,這正是由一代又一代先賢們創造的文化上的自信。
作者:封鈺 單位: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
- 上一篇: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問題范文
- 下一篇:醫學檢驗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