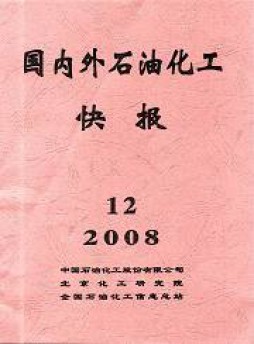國內婦女參政的生態環境解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內婦女參政的生態環境解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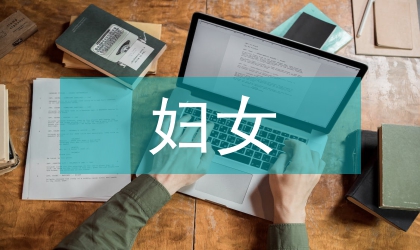
與西方不同的根本特點是,中國的婦女參政運動是在政府徹頭徹尾的政治動員下所完成的。我國的第一次婦女解放運動發生在1895年戊戌維新運動中,是那些初步覺醒并受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萌發了“權力”意識的婦女發動的。她們發表《男女平等說》等文章,公開爭取女權,要求“設貴婦院于頤和園”,薦拔女性“受職理事”。她們主要是伴隨當時清末政府提倡女學,發展女性教育而出現的。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婦女參政與國家有緊密的聯系。在此后的各個歷史時期,婦女參政更是同中國不同政黨和各種婦女團體聯系在一起。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及中國國民黨二大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案》中,都確認了男女平等原則和助進女權實施。
建國后,中國女性在政治參與上更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黨和政府的法律文件上明確規定了婦女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為婦女參政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其次表現在為培養女干部的成長的特殊政策,這些無不體現了我國在政策上的性別公正,有效地促進了女性參政。然后改革開放后,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差額選舉制和競爭聘任制的引入和完善,性別保障措施的明顯弱化,我國的婦女參政一度落入低潮。這種從產生還是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婦女參政都與國家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密聯系的現象,在西方國家是不存在的。中國婦女政治參與權的獲得主要是由于黨和政府的一定程度上的強制方式,大規模、有效的組織和動員。但同時理論上得不徹底性,導致黨和政府還未對傳統性別文化進行深入的認識和判斷,尚未對傳統的“男強女弱”和“男外女內”等性別本質主義作徹底清算。參政的女性未擺脫性別本質主義的文化思維定勢的阻礙,使運動至始至終還停留在從法律層面爭取參政權階段,而未進入具有參政意識,自覺參政的更深層次。
二、政府主導型婦女參政模式的可能性分析
李小江在《新時期婦女運動和婦女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婦女與國家的關系,在西方女權運動中是一個弱點,因此長期以來是西方女權主義理論中的一個盲點[1]。”基于此,1995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指出:關注和推進婦女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決不僅僅是婦女的事情,而是政府的責任。閔冬潮在《婦女研究在美國、西歐的歷史、現狀與發展》闡述到:“總地來講,國家作為婦女權利爭取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婦女狀況及地位的長遠的、重大的變化有賴于政府的行政干預,要通過制定和執行反性別歧視的法令法規才能實現。聯合國通過的《到2000年提高婦女地位內羅畢前瞻性戰略》中的不少建議都是必須由各國政府來執行的。”其次,聯合國自2O世紀7O年代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倡導“社會性別意識主流”觀念。在1995年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上,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政策的主流。社會性別意識主流化意味著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社會發展和政府的公共決策主流,其核心內涵是從人的基本權利出發,重新審視和反思現存的兩性關系和性別規范,清理和消除兩性發展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壁壘和障礙,促進男女兩性的全面健康發展。
(一)政治土壤——我國傳統社會結構生產方式所形成的國家權威觀農村自然經濟和土地國有化是我國傳統社會生產方式的主要特點,這兩大特點為政府主導婦女參政模式的構建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
首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它是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小農式的自然經濟方式,使得古代中國的人們安于局限于隔離的小村莊,無心與外界進行更多的溝通,也就產生了他們對經驗的尊重以及對權威的敬畏。而要聯合這些零碎的整體,就要求產生了一個超越各個小村莊之上的集中的權力進行統一的規劃、組織和管理。
這個權力就是國家。白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里的一篇《由治水的社會經濟環境來決定的集權制的政統統治模式的選擇》中就深刻指出“共同的利益訴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河意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愿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
最后就是土地國有化。我國一直以農業經濟為主,農村公社長期保存用于分配土地和組織耕作的權力,而后這種權利是歸奴隸制、封建制國家所有。當時包括奴隸主、封建地主以內的私人雖擁有土地,但實際上只是一種對土地占有、使用與具體支配的權力,它只能進行權力的讓渡,卻不能否定國家對土地絕對的所有權。在此意義上,恩格斯曾指出:“在整個東方,公社或國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語言中甚至都沒有‘地主’這個名詞。”這種國家土地所有制的獨特性也是形成我國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1853年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指出:“東方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國家通過占有土地,同時也占有了土地的一切生產形式。它反映在社會政治結構上,就是個人對集體的高度依附,個人對國家的絕對服從。正是由于我國傳統社會結構生產方式的兩大特點使國家權威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也產生了我國上強下弱,整強個弱的特點。
上就是整體,下,則是一個個分散的軟弱的個體,而且他們之間沒有形成功能耦合或彼此間沒有什么聯系,根本提不出同一的目標,或者目標小而分散,因此難以產生足夠強大的力量。而在另一層面的意義上說,中央權力的強大,對整個社會產生主導影響;而民眾的力量相對弱小,它們既表現為一個個分散的軟弱的個體;又表現為具有高度的政治服從感,而這些為政府主導型婦女參政模式的構建提供了可能性。
(二)文化土壤——儒家文化傳統所形成的臣服型文化特定的文化觀產生于特定的環境和社會結構。儒家強調“天地萬物一體”觀念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觀念,從各個方面構建起一個龐大的體系,將人的主體性淹沒在對統治階級的無條件服從中。首先,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養性成為第一要素,這樣導致的后果是參政意識泯滅于修身養性之中。其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觀念也就是權威主義的“三綱”所體現出的權威服從意識,政治自主意識的缺乏必然導致政治參與意識的薄弱。最后要強調的是,用于文化意識形態的塑造的根本途徑:“忠、孝”。綜合起來,這些也就具備了產生我國臣服型政治文化的總綱領,它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深深浸透于國民的靈魂,浸透于國民靈魂深層的思維、意識、認知和情感。因此我國自主意識和參政意識特別薄弱,而國家意識,服從意識卻特別強烈,而這些是建構政府主導型婦女參政模式有利的政治文化因素。
作者:韓藝珍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擴展閱讀
- 1國內公債史
- 2國內購物旅游探究
- 3國內媒介文化
- 4國內檢察權分析
- 5國內村民分化研究
- 6國內小額信貸監管分析
- 7國內武術文化研究綜述
- 8國內物流金融
- 9國內毒情形勢表述
- 10國內翻譯研究綜述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國內產業調研
- 2國內安全保衛論文
- 3國內外形勢論文
- 4國內對財務風險的研究
- 5國內博士論文
- 6國內市場營銷方案
- 7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研究
- 8國內工程造價管理現狀
- 9國內的公共藝術
- 10國內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