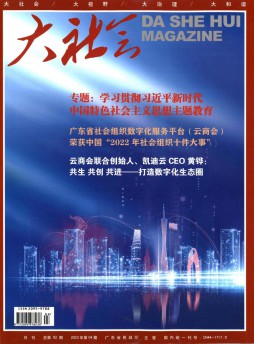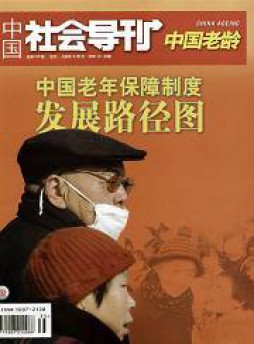社會經濟史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經濟史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
一般說來,時間序列和空間位置是認識、把握事物的兩個基本觀照點。如果仍然認可歷史學是一門依據時間維度研究歷史現象的學科,地理學是一門依據空間維度考察地表現象的學科,那么,至少對于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言,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的考察則是缺一不可的。人類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在相應的空間展開的,將歷史現象放在產生它的空間(區域)中進行時空結合的考察,通過由此所形成的各種聯系,探討歷史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變化以及變化的形成、意義及其機制,由此展現出來的歷史內容顯然會更加豐富多彩,也更接近歷史真實。如若不然,不僅無法確切揭示人地關系,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認識和把握亦會受到局限。再者,諸多事例表明,歷史進程不僅在時間序列上有發展的快慢進退之別,在空間結構上也會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和不平衡性。世界范圍內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特別是在中國這樣地域廣大,自然、社會條件復雜多樣,開發、發展先后參差,民族眾多、歷史悠久的國家。誠如傅衣凌先生所說:“由于自然環境的差異和生態平衡的改變、歷史上開發時間的先后、人口的流動和增減,以及經濟重心的轉移等等因素的影響,各個地區的生產技術水平、生產方式、社會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萬別,而且還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出現周期性和不規則的變化。”Ⅲ(第4頁)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如果不考慮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空間結構的不平衡性,極易產生以偏概全甚或徒發空論的偏頗,這在以前號稱“宏觀”敘事的“綜合”研究中曾有過深刻教訓,且已成為社會經濟史區域研究持續不衰的基本動因。
毫無疑問,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同時歷史進程也是復雜多樣的。從認識論層面言之,人類認識乃不斷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的發展過程。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規律性,總是通過偶然性、隨機性乃至千差萬別的多樣性表現出來的。著名學者黃宗智論及中國經濟史中的規范認識問題時指出:“從方法的角度來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于擺脫既有的規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觀或量的分析,很難免套用既有理論和信念。”微觀研究應該有多種途徑,如時間尺度上的、空間尺度上的、分門別類的等等。而所謂偶然性、隨機性、多樣性的產生,總是離不開空間依托的,分區域的(或日地方的)系統研究也正是空間尺度上的微觀研究途徑之一,注重考察、認識空間結構的差異與特點及其產生原因、變化軌跡及規律,“避免把某一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一些聯系套用到另一歷史過程中去”。當然,這里所說的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都是相對的,因為,即使考察同樣的問題,站在不同的層面上,或使用不同的考量尺度,也會有高低、大小不同的視野,從而產生不一樣的“觀”感。
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不可忽視甚或放棄整體觀照。如前所述,社會經濟史區域研究的主要前提之一是社會經濟發展在區域上的不平衡性或日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所謂不平衡乃整體觀照下的不平衡,差異則更是存在于不同區域之間,離開對整體和其他區域的觀照、比較而孤立地談某一個區域,平衡或不平衡也就無從談起了。人們經常提到的區域特色或日區域特征,更應該是在整體觀照下,相對于其他區域而凸顯出來的,而不是站在本研究區域立場上給自己粘貼標簽。吳承明先生早已指出:“區域經濟史研究,有縱的方面和橫的方面兩個要領。一是由于劃定區域,可將研究時段放長,探討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和階段性或周期性變化。西方稱為空間與時間研究方法,近年頗為流行。另一個是區域與區域之間的關系和比較,即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個區域,而是以其他區域作為環境來進行考察,包括勞動、資本和產品的移進移出,技術的傳播,以及擴散、互補、競爭等效應。”這種縱橫交叉、結合的方法,當為深化區域研究的有效途徑。事實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視為一條盡量接近歷史真相的途徑,而不是以區域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
為尋求區域特征,整體觀照、與相關區域進行比較固然非常重要,然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基礎仍然是扎實、系統的本區域研究。換言之,社會經濟史區域研究不能停止于就一個區域論這個區域,但必須從全面、深入研究這個區域出發,如果沒有這個出發點,缺乏堅實的基礎,進一步的解讀、觀照、提升、比較等等,無疑將成為空中樓閣。其實,大一統中國的史學研究富有重視區域研究的傳統,司馬遷《史記》中精彩的經濟史、社會史分區論述,習史者大多耳熟能詳,至于中國多層次地方志的普遍、長期持續修纂,就更是有力的說明,盡管地方志修纂與歷史研究不無差異,地方史亦不等同于區域史。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區域性研究高潮又一次興起,雖然不能說已經沒有“研究一個區域有什么意義”之類的疑問,卻已經無法阻擋區域研究朝著更高層次深入發展。
二
就近些年言之,區域研究活躍、成果突出者如明清以來華北社會經濟史和華南社會經濟史研究,長江下游以及徽州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等,這些研究都以不同層次的空間為研究對象,表現出強烈的區域色彩,而且都在摸索適應本地區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有的研究群體已積累了較長時間的研究成果和經驗,正在摸索一條比較適合本區域研究的路徑,并提出了一些理論性的思考,甚或力圖提出一些基于本地區研究、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總體認識。同時,區域史的研究,也有力地促進了學科交流、交叉,譬如田野調查這一方法或途徑,就為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者所認可、采用,而且開辟了搜集、利用新材料的途徑,史料的種類和來源隨之拓廣,所謂“多重證據”的論證方法也較過去更為常見。
長江中游地區位于中國南北方交匯、東西部過渡地帶,無論從氣候到地形,都具有“中間過渡”特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分野上看,北鄰中原文化、南接嶺南文化,分別受到南北兩大文化圈及巴蜀、西秦、吳越等文化的影響,同時亦以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影響著周邊相鄰各區域文化。在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許多重大的社會經濟變動都與長江中游地區息息相關,留下了非常豐富的、不乏濃墨重彩的歷史內容。遠者不說,即以宋元以來言之:如在“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以及“無湖不成廣”的人口流動浪潮中,長江中游地區居于重要的中樞地位。如眾所知,此次人口流動所及區域,遠不止于諺語點明的江西、湖廣、四川等數省區,江、浙、閩、廣、豫、皖、陜諸省無不波及,并由此拉動了大半個中國的人口。而且,人口流動浪潮帶來的不只是中國人口數量、人口分布的變動,與此相伴隨的資源開發、經濟增長、社會流動影響深遠。再如從諺語“蘇湖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的轉換,說明的不僅是長江中游糧食生產、運銷的重要地位,更隱含著長江流域乃至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區域資源開發、區域農業結構、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空間結構的某種深刻變化。如果需要,這類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因此,對于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言,長江中游地區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值得學術界給予高度關注的地區。
然而,相對而言,長江中游的區域研究原本卻是比較薄弱的,即就長江流域來說,研究成果的數量和水平原本不僅不能和下游地區比,在有些方面也不及上游地區。有鑒于此,約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我們開始較多地關注、探討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社會經濟問題。在彭雨新先生的指導下,首先從水利問題人手,當初的基本思路是:農業經濟在中國傳統社會占絕對主導地位,中國農業的發展與水問題的解決息息相關,農業水利是考察、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的最佳切入點之一。后來,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展,學術研究的內在脈絡也在自然延伸、貫通。如由研究水利而關注水、旱等自然災害,因為水利與水旱等自然災害實為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用水之利”與“去水之害”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被割裂開過,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興利與除害并舉、水土兼治為特征的系統治水的思想。再如由研究平原湖區而關注周邊山區,江河中下游平原之水問題與上游山區之來水來沙息息相關,以此為基礎,無論自然因素還是社會條件,上下游之間、山區與平原之間就建立了無法割斷的相互聯系,尤其中下游平原之于上游山區更是如此。山區(高地)與平原(低地)之間不僅有水沙流動,而且有人口流動、能源流動、資金融通、產品交換等,于是有涵蓋區域人口流動與資源開發、經濟增長、社會變遷乃至于環境演變等內容的綜合研究。
作為這方面繼續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和《光明日報》理論部共同舉辦了“14世紀以來長江中游地區環境、經濟與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學者聚集珞珈山麓,圍繞歷史上長江中游地區的開發與發展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交流,會議論文及討論所及,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區域環境演變與歷史自然災害,宗族、聚落與社會組織,移民、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法律、社會風俗與社會控制,公益事業(社會救濟、災荒救助等)與水利灌溉等公共領域,城市環境與城市空間、功能,近代城市與市場網絡,民族地區經濟等。對社會經濟史區域研究的理論方法亦有探討,如對區域劃分的標準與模式的論述,“地方性知識”概念在區域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對“民間文書”性質的認定及其解讀等。其中有的是全新的研究課題,有的是在原有研究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化、提升,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大多以豐富、扎實的史料為基礎,通過實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或填補了長江中游地區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某些空白。
三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論文對新史料的發掘、利用也頗為重視、用力,一批民間文獻包括各類碑刻、案卷、家譜等被發現并運用到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實證中,如《華陂堰簿》、《槎灘碉陂山田記》、《槎灘碉石陂事實記》、《五彩文約》、《鐘九鬧漕》、《民間案卷》、《華國堂志》等,這些民間文獻與相應的田野調查相結合,對相關研究主題的深化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展現了很好的長江中游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新史料利用前景。如眾所知,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給古老的歷史學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如攝影、掃描、計算機等技術的普遍運用,使許多過去不容易看到、甚或無法看到的文獻比較容易看到了,過去很難甚至無法辨認的文字,現在能夠辨認了。這種變化也給學術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歷史研究要出新、拓展、進一步提高水平,除了理論方法的創新外,作為實證研究基礎的史料的發掘,特別是非傳統文獻類史料(包括口傳史料)的發掘利用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明清以來的歷史研究尤其如此)。民間文獻如譜牒、碑刻、契據文書、書信、日記、村落文書、民編啟蒙教材、民間宗教的經文案卷、祭文本等,有別于以官方或社會精英話語為中心的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如正史、實錄、朝廷檔案、政書、地方志等),由于它們主要來源于民間,直接反映或貼近基層社會生活,而且包含有幾乎涵蓋民間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內容,因此可以彌補以往“大歷史”、“宏觀敘事”類研究中普通民眾聲音缺失、對基層社會如何運行不甚了然等不足,可以說為社會經濟史研究追求像過去關注朝廷、官府那樣關注民間,像過去關注上層那樣關注基層,像過去關注精英那樣關注大眾,像過去關注重大事件那樣關注日常生活提供了資料條件,有利于拓展、深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當然,這里講重視非傳統文獻、民間文獻的搜集、利用,并不是要忽視甚或放棄傳統文獻、官方文獻。恰恰相反,我們堅持認為,只有將上述兩種文獻結合起來,相互補充、參證,相互觀照,才可能獲得對社會經濟史相對真實、完整的理解。
此次研討會和該論文集的出版,肯定會對長江中游區域社會經濟史、環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同時,我們也期待著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