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股引進戰略利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企股引進戰略利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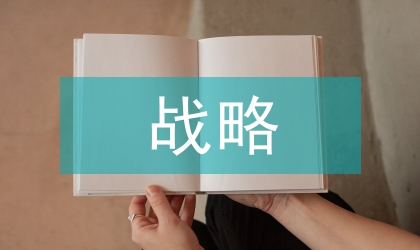
戰略投資者的含義及特征
戰略投資,是站在投資者角度對投資地位的界定,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中長期戰略性并購投資,是為達到戰略目的的投資,例如,通過投資,可獲得穩定的市場(被投資企業是下游企業時),或者能獲得穩定的供貨(被投資企業是下游企業時)。戰略投資與戰術投資相對應,前者是一種著重全局的投資、是一種長期投資、重大投資,后者側重于局部、是一種著眼短期利益的較小規模投資。
從事戰略投資的國內外投資者即為戰略投資者。戰略投資者是指以謀求長期戰略利益為目的,持股量較大且長期持有,擁有促進被投資企業業務發展和價值提升的實力,并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法人投資者。與戰略投資者相對應的是財務投資者或套利性投資者,其投資目的是套利,通過擇機投資擇機變賣,追求短期投機利益,它們一般不深入參與公司治理,對持股量也沒有太高的要求。按照1999年7月《中國證監會關于進一步完善股票發行方式通知》,證監會把法人投資者分成戰略投資者和一般投資者。把與發行公司業務聯系緊密且欲長期持有發行公司股票的法人,稱為戰略投資者;把與發行公司無緊密聯系的法人,稱為一般法人。對籌資者而言,戰略投資者是超大型股東,非戰略投資者則屬中小股東。
戰略投資者應當具有如下特征:與標的企業有緊密聯系業務往來或者從事的行業具有一定的互補性,擁有促進發行人業務發展的實力或能夠規避不同時期的行業風險。追求長期戰略利益,而非短期市場行為,能夠長期穩定持股,不會因為暫時的獲利而變現。這是其區別于一般法人投資者的首要特征。持股量較大。如作為戰略投資者的美國福特公司持有江鈴汽車29.96%的股權,為其第二大股東。上海寶鋼集團持有首鋼股份1200萬股,為第二大股東。有愿望也有能力參與標的公司的經營管理。
2005年11月,為解決股權分置改革引起的股份全流通可能引起的市場壓力,商務部、中國證監會發出《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涉及外資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提出允許境外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進行戰略性投資。之后,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多家大型國企,高調引入瑞士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RBS)、新加坡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等戰略投資者。這是后股權分置改革時代我國引進戰略投資者的積極實踐。
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對國企股改的好處
首先,能為股改公司籌集到一筆巨額資本。但當一家公司或銀行并不需要更多資本,或者所需資本能很方便通過金融市場籌集到時,這一好處便顯得微不足道。
其次,境外大股東的介入,會使國企股改公司資本結構得以調整。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國有股比例,有利于形成相對制衡的股權結構,有利于遏制國有股“一股獨大”問題,有利于改善股改公司治理機制。戰略投資者一旦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可選派管理人員進入公司管理層,參與決策并實施監督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監督公司決策與管理,優化了公司治理結構,有利于防范內部人員控制問題。
第三,股改公司從此有了真正為自己操心的“東家”。這些戰略投資者雖然可能只是“二東家”、“三東家”,但他們在為自己的資本操心的同時,產權處于虛置狀態的國有“大東家”和廣大中小投資者都可“搭便車”獲得收益。
第四,可能同時引來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術以及市場信息和網絡,有利提升公司價值和某一方面甚至某幾方面的優勢。
第五,在外來資本運作的帶動、示范和擠壓效應下,國有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收益也會逐步提高。
第一,非對等交易。國有資本出讓了部分股權和控制權,未必能換來管理理念、制度和技術。對每一個“理性人”而言,真正最具競爭力的核心理念、關鍵技術是不輕易外傳的。
第二,“隧道效應”。存在境外資本牟取國有資本和國內其他股東利益的可能性。這是因為被選中的這些戰略投資者,往往有豐富的資本運作經驗,有設計、營銷復雜衍生金融產品的技能。在戰略投資者授意下,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國內公司可能前往海外經營金融產品或其他產品。出現虧損,轉回國內,由全部股東分擔,有了盈利則留在海外繼續周轉,甚至據為己有。這也是一種“隧道效應”,戰略投資者通過各種隱秘的隧道攫取國有股東及其他股東的財富。
第三,控制權旁落。引進戰略投資者后,國有股仍虛置,其他中小股東雖產權清晰但因“小”而“散”,很難掌握控制權。于是,極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是戰略投資者“一股獨大”或“數股獨大”。一旦實際控制權旁落他人,再采取法律的、行政的一系列補救措施,還不如及早防范,醫“未病之病”、“初病之病”。
第四,“合謀”。還可能出現的一種風險,是戰略投資者和國有股權人、和管理層串通,共牟國有股股東和其他中小股東財富。
第五,資本抽離。2008年底和2009年初,瑞士銀行(UBS)、李嘉誠旗下慈善基金、蘇格蘭皇家銀行(RBS)等多家引入剛滿三年的戰略投資者,紛紛全部或部分拋售所持中資銀行和公司股票,中方要求的“持股最短時間”最終成為這些戰略投資者實際持股的最長時間,戰略投資者演變成“戰略投機者”。我國現行制度規定的股權退出成本太低。如規定的解禁期太短,減持股權的申報程序過于簡單,未要求減持者必須尋找到資質更好的投資者接盤、以防減持的股份落入投機套利者之手等。
另外,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還可能存在國有股權價值被低估、無形資產歸屬糾紛、出現文化沖突、可能觸動法律或國家利益等一系列不確定性問題。
國企改革中吸引境外戰略投資者應注意的問題
從近一時期瑞士銀行、李嘉誠投資基金、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RBS)大筆拋售甚至出清中國銀行H股、新加坡國有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拋售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H股的經驗看,我國國企改制過程吸收的海外所謂“戰略投資者”并不可靠,他們往往首先是“戰略投機者”。對股東而言,股權流動性越強,越易于變現,越愿意投資;對股份公司而言,促使其改善管理,提升業績,防止股東流失。近期境外資金的大規模抽離,也給政府部門制定深化國企股改的方案提供了啟示:不管吸收的是戰略投資者,還是非戰略投資者,都是趨利避害者。
第一,繼續引進更可靠、更穩定、更善意、更積極的戰略投資者,促進國企股權結構多元化,公司治理科學化,管理理念國際化,以及國有資本收益最大化。
第二,可嘗試換股或交叉持股等多種形式,增強中外資企業之間戰略合作的穩定性、持久性。
第三,提高進入門檻,加大退出成本,對引進的戰略投資者規定限制性條款,減輕資金抽離可能對國內經濟造成的沖擊。對戰略行業、重要行業,應不允許外資進入,以維護國內產業安全、宏觀金融安全和微觀財務安全。境外資本對國內金融企業、能源企業、大的行業龍頭企業的參股、控股,應經過人代會至少是人代會專門委員會的辯論、表決,而不應只是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如國資委、財政部)拍板,從股份公司的組織制度看,股東會是公司最高權力機構,最重大的決策應由其作出。如果把我國國企視為一個企業,則全民皆股東,全國人代會就是我國國企的的股東代表大會。國務院及其部門只能在人代會的授權范圍內,吸引較小數額的境外投資,對數額較大的引資,均應有人代會專門委員會辯論、表決,通過后交由國務院及其職能部門執行。中石油并購美國尤科斯公司失敗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國公司并購國外企業,即便公司股東樂意,政府也不反對,但只要國會議員反對,并購照樣會擱淺。何況,在美國,國會議員并非尤科斯的股東,在中國,人大代表還兼具全民股東代表角色,把國有股權(全民股東股權)轉讓給境外戰略投資者,理應征得其同意才對。
第四,改變重境外、輕國內的現狀,逐步吸收有實力、重信譽、懂管理的國內法人或大型民營企業,成為國企的戰略投資者。重外輕內,其實是一種投資歧視,是對國內潛在戰略投資者的歧視。
第五,特別要注意股權轉讓收入的處置這一要害關鍵問題。國有股權轉讓給國內外戰略投資者后,也是一種國有股減持。要保證轉讓國有股權所得收入的管理安全、運用合理。國有股轉讓,只不過是把國有資產從股權形式變換成現金形式,國有資產不再以資本金形式存在于企業而已。從所有權關系看,轉讓國有股獲得的現金資產,仍為國有資產,屬全民股東所有。只要通過市場機制確定公道價格,應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最需關注的是轉讓收入如何掌控和分配。由于轉讓收入會比較龐大,很可能達數萬億元之巨,因此,強化對其管理和運用十分必要。
可由全國人大授權成立專門機構管理這筆資產的收繳和運營。由國資委將轉讓國有股權收入交給人大國有資本管理委員會,能體現這種主從之間的財產法律關系;財政部負責全國財政收入和支出,是政府主管經常性收入和支出的專門機構。為避免國有股權轉讓收入被財政列入預算然后以經常性支出花費掉,最好由人大設立的專門委員會來管理這筆本屬全民所有的公共資產。
先立法,后支出。立法完成后,再依法管理支出。筆者認為,這筆基金運營的宗旨不應是讓富人更富(如不用于營利),而首先是不讓窮人更窮,如用于補償原國企貧困職工,用于社會保障與救濟、彌補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振興老工業基地、建設新農村等專門開支,通過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使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尤其應用于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民醫療及養老服務、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等方面,解決多年來有心解決而無力解決的老問題。
產權制度變革過程,國有股權轉讓將產生巨額現金收入。反對將這些收入視為經常性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經常性支出。拉美一些國家(如阿根廷)在公用事業私有化過程中,把一些公共設施轉讓給外國公司(主要轉讓給歐洲和北美企業),但可怕的是,外國公司所支付的資金并沒有被用于國家需要的工業基礎與公共設施建設,也沒有被用于社會保障和公民福利,而是最終落入政客的腰包。為防止類似情況在我國發生,本文建議將這些收入不要急于支出,而是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一部專門法,將這些收入建成一筆專項基金,把基金管理的目的、管理主體、收入和支出的程序、基金的用途等問題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先立規矩后辦事,并且這個規矩定得越細微越具可操作性越好。
擴展閱讀
- 1國企問題
- 2國企改革
- 3國企預防腐敗
- 4國企監管中的審計功能
- 5中國國企產權改革
- 6國企海外并購戰略
- 7國企檔案管制特色與策略
- 8國企股引進戰略利弊
- 9國企貪利職務犯罪
- 10國企融資面臨難題
精品推薦
- 1國企中層干部述職報告
- 2國企員工思想匯報
- 3國企行政工作計劃
- 4國企思想匯報
- 5國企宣傳工作計劃
- 6國企深化改革工作計劃
- 7國企內部審計工作計劃
- 8國企檔案管理
- 9國企行政管理論文
- 10國企審計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