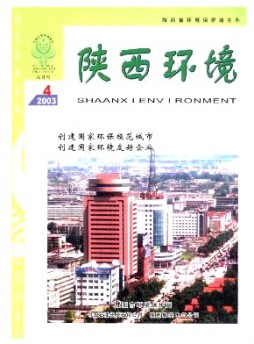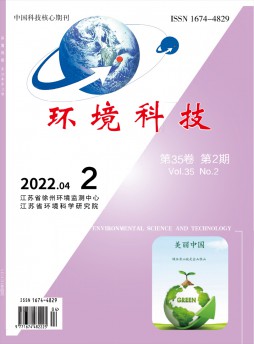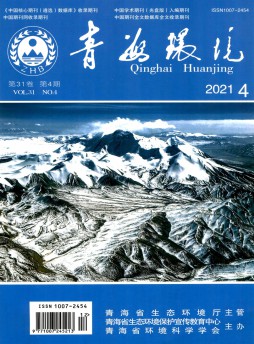環境法規對出口的影響解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環境法規對出口的影響解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可以圍繞兩條核心途徑展開:一是國際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生產規模擴大是否對環境造成了消極影響;二是研究途徑是環境規制對一國貿易模式的影響。一國的貿易模式取決于其比較優勢,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會傾向于出口該類商品,而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則更偏向于進口。隨著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比較優勢的涵蓋范圍逐漸從資本和勞動力這兩大基本要素慢慢向外擴展到技術要素和其他投入,環境規制的引入則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比較優勢的內涵。
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僅僅知道環境規制是影響一國比較優勢,影響世界范圍內污染性產業布局的眾多因素之一。環境規制會提高污染性產業的邊際成本,迫使該產業從環境監管嚴格的國家轉移到監管相對寬松的國家,由此改變了本國的貿易結構和貿易模式。但如果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上升無法抵消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上述現象就不會出現。因此,這個問題需要結合現實產業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才能有說服力。
一、文獻綜述
國外在貿易與環境的實證研究領域有大量的文獻,這些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大約1997年之前使用橫截面數據的早期研究,他們把貿易橫截面變化與產業層面、國家層面或者區域層面的環境規制成本聯系起來。這類研究最后得出的結論都是環境規制的差異對貿易流沒有顯著影響;第二階段把環境規制當作內生變量,發現內生性的環境政策對貿易流的影響是顯著的。
橫截面研究都是以國際貿易的HO(Heckscher-Ohlin)模型為基礎而進行的,采用回歸分析法,但是在解釋變量選取和內生變量的控制上有所差異。Tobey(1990)是這類文獻中最廣為引用的,文中把23個國家5個污染密集型產業的貿易出口額與要素稟賦和環境規制指標進行回歸,發現環境規制指標是不顯著的解釋變量①。但在接下來的省略變量檢驗中,環境規制對出口沒有影響的原假設是不能被拒絕的。另一種計量方法是把貿易橫截面數據與產業特征指標聯系起來,以Kalt(1988)、GrossmanandKrueger(1993)為代表。典型的研究是以各個產業橫截面的貿易出口額作為被解釋變量,把投入要素和污染處理成本作為解釋變量。這些產業通常選擇制造業部門,但更多時候是選擇制造業中的污染密集型產業。上述研究大都無法證實環境規制對貿易有直接的影響,他們對此的解釋是環境處理成本(PAC)只占總成本的極小一部分,但近期的研究發現環境政策的內生性和不同行業的特征帶來的異方差會對實證結果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CopelandandTaylor,2004)。
國內的研究遠沒有國外豐富,大都采用回歸分析的實證方法,其研究體系和沿承性相對松散,也沒有形成連貫的研究。趙玉煥(2009)、李沫(2009)均用回歸分析的方法來分析了環境規制對紡織品貿易的影響。尹顯萍(2008)對中國和歐盟的環境規制指數與進出口指數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回歸分析、T檢驗與F檢驗,認為歐盟環境規制的相對嚴格化是中歐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從而使我國承擔了更多的環境成本。傅京燕(2008)采用中國24個行業的環境規制指標與要素稟賦建立了面板分析系統,針對內生性問題把能源指標標準煤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同時還進行了穩健性檢驗來比較環境規制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綜上,環境規制與國際貿易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有兩個難點,其一環境規制或者環境嚴格度的衡量問題,其二環境規制的內生性問題。第二個問題本文通過改良實證方法來解決,但第一個問題很難得到改善。因為環境稟賦的界定與環境污染損害的測度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產業之間缺乏可比性,無法形成統一的衡量標準,因此會影響理論分析的有效性。本文將建立一個環境規制強度評價指標體系對其進行評估。
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界定
不同的產業其對環境的污染程度不同,受環境規制影響的程度和對環境規制的敏感程度也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對環境規制較為敏感的污染密集型產業,因此,將建立產業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不同行業對環境的污染強度。
產業環境污染指數主要用來對現有制造業的環境污染強度進行衡量和排序,必須完整地反映出此產業的所有污染情況。文獻中比較常見的方法就是用污染處理成本指標來劃分污染密集產業和清潔產業,有些文獻直接采用此指標,有些文獻則是用污染處理成本占其銷售總額的百分比②或者用污染處理成本占產業總成本的百分比③來區分。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把不同行業的污染排放物總量相比較來對各產業進行排序。由于中國官方沒有公布制造業下分產業的污染處理成本數據,本文只能通過第二種方法來建立產業環境污染指數。
工業污染包括廢氣、廢水、和固體廢物三類,不同產業排放的工業污染種類有所差異,非同類的污染物不能直接在總量上相加,應先把不同產業的三類污染物排放指數化,再對指數進行相應的處理。基于此理念,產業環境指數由工業廢水排放指數、工業廢氣排放指數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指數共同構建,產業環境污染指數越高,產業的污染密集程度越高,產業環境指數建立的具體方法如下:
首先,用三類工業污染總排放TPij除以工業生產總值TVij,分別計算出各產業單位產值所排放的三類污染物數量PPVij;然后,對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序列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無綱量的工業廢水排放指數、工業廢氣排放指數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指數;最后,對以上三個污染物排放指數進行加總,得到產業環境污染指數EPi。其中,j為污染排放物類別,分別是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和工業固體廢物(j=1,2,3);i則為各個不同的產業,共30個(i=1,2,……30)。
通過上述方法計算,可以得到我國28個行業在2001~2009年間環境污染指數④,計算出各個行業9年內環境污染指數的平均值,并按照降序排列,可以得到行業污染強度的排序,如表1所示,越靠前的行業污染越嚴重。
通過表1可以看到,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20)、造紙及紙制品業(10)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19)這三個行業的平均環境污染指數都超過了1,在28個產業中污染程度最為嚴重,屬于污染密集型產業。而紡織服裝業(6)、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11)和電子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27、26)的平均環境污染指數都在0.01左右,在28個產業中屬于相對清潔的行業。以此方法排序的產業環境污染程度與國外文獻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劃分基本一致。CopelandandTaylor(2004)認為鋼鐵、有色金屬、工業化學、紙和紙制品以及非金屬礦物制品這五個行業是污染最密集的⑤,這與表1中排位前5的行業相同。因此,本文選取表1中污染最為密集的前四個產業作為實證分析的研究對象。
三、模型構建及數據說明
(一)HOV模型以及擴展
本文的實證分析采用了Tobey(1990)中的Heckscher-Ohlin-Vanek(H-O-V)模型。國際貿易的要素稟賦理論(HO理論)中提出了兩種產品、包括資本和勞動兩大要素的H-O模型,而H-O-V模型是H-O模型向多要素和多產品的多維度方向延伸。此模型常以三種方式被引用:要素比例研究;通過要素密集度和貿易量指標建立多商品截面回歸來推斷要素稟賦;第三種方式就是本文中所用的,考慮到不同行業稟賦和個體特征而對某些特定生產要素和貿易量的回歸。特定要素作為解釋變量引入模型,能夠表現出其對某特定行業貿易量的直接性影響。H-O-V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為了研究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產業比較優勢的不確定性影響,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環境規制變量(ERS)及其二次項。環境規制強度表示一國對某行業排放污染的規制嚴格度。另外,針對本文所研究的多截面時間序列數據,如果出口量在時間上存在路徑依賴,則省略滯后的出口量會導致遺漏變量誤差,估計值就是有偏和不一致的,模型(1)中加入AR(1),即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項來反映出口量的動態變化,并且考慮到不同截面之間被解釋變量的非均勻性,把不可觀測且不隨時間變化的截面間個體效應記為ηi。這就構成了如(2)所示的動態面板模型:
(二)環境規制強度的計算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產業的出口量根據盛斌(2002)中SITC與GB分類的對應標準進行處理。環境規制強度則借鑒趙細康(2003)、傅京燕(2010)中的指標體系建立一個基于我國污染密集型行業實際污染產出的環境規制強度評價指標體系來計算。這套體系由一個目標層(ERS綜合指數)、三個評價層(廢水、廢氣和固體廢物)和若干個單項指標層構成(見表2),與上述兩位學者相比本文中的指標體系更為直觀和便于計算,需要的原始數據復雜程度較低。
在ERS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建立之后,需要從單項指標層開始逐個計算指標,再層層上推,最終匯總成ERS綜合評價指標。本文構建ERS綜合評價指標的具體步驟如下⑥。
1.計算各單項指標Eij。其中,j為單項指標類別,分別是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工業粉塵去除率、工業煙塵去除率和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j=1,2,3,4,5);i則為各個不同的產業,共n個(i=1,2,……n;n≤28);
2.計算各單項指標的權重,反映不同產業不同年份對不同污染物的治理力度和規制嚴格程度。權重的計算公式為Wij=PPVij/TPVij。其中,PPVij為i產業單位產值的j污染物排放,TPVij為所有產業平均單位產值下j污染物排放。從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各污染物單項指標的權重實際上就等于某產業單位產值污染物的排放水平與所有產業的該污染物排放水平的比值。
3.將各單項指標加權平均,計算評價指標層下對應污染物的環境規制程度并匯總,得到最終的產業環境規制強度指標ERSi。
四、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模型(2)由于加入了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就存在內生性問題,繼續沿用常規的LSDV或者FGLS方法處理面板數據模型,即使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假定條件得以滿足,得到的估計值仍將是有偏、非一致的。ArellanoandBond(1991)提出基于廣義矩估計(GMM)的工具變量法,該方法能有效地克服估計中的內生性問題。
在動態面板模型中,工具變量的選擇最為關鍵,本模型中選擇內生變量的兩階滯后項作為其工具變量。這背后隱藏著一個假設條件,即原始模型中的干擾項不存在序列相關。否則,上述工具變量設定方法就是有問題的。也正因為如此,做動態面板分析時,必須要執行AR(2)檢驗,這是保證工具變量合理性的一個方面。另外,對于某個內生變量而言,往往有多個工具變量可供使用,此時便會出現過度識別(over-identification)問題,類似于求解聯立方程時,方程的個數大于未知參數的個數這種情形。這就需要執行Sargan檢驗。
基于上述判斷,本文使用Stata11中的Xtabond2命令來完成GMM估計,結果見表3。如表3所示,對該模型估計中一系列系數、工具變量以及殘差序列的相關性進行檢驗,其結果分析如下:因Wald(6)184.02(6)20.052所以,2Wald檢驗拒絕了(除截距項外的)模型系數均為零的原假設,方程整體系數具有統計意義;因(20)27.51,Prob(20)0.12122,所以,Sargan檢驗接受了GMM估計的“模型過渡約束正確”的原假設;Arellano-Bond檢驗均接受了殘差序列不存在一階、二階自相關的原假設。通過上述檢驗,可以認為該動態面板模型在統計學意義上是比較理想的。但從現實意義的角度來看,系數的解釋還需要結合實際情況。
根據表3中的顯示,出口量的一期滯后作為解釋變量的系數是顯著的,這說明這四個行業的出口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效應,出口量上一期的變動對本期出口量有類似于慣性作用的影響,動態面板把這種影響與環境規制和其他要素稟賦對出口的影響分離,使后者系數的估計更加準確。
環境規制強度這一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統計顯著,且為負值,這說明環境規制的嚴格程度是影響污染密集型產業產品出口的重要指標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嚴格規制下的污染密集產業需要在污染治理、清潔技術開發、污染處理設施建設等環節加大投入,相對于環境規制寬松地區的企業其生產成本明顯偏高,產業競爭力也相應較弱,因此污染密集型產業在環境規制程度嚴格的地區缺乏環境要素稟賦,不具有比較優勢。
環境規制二次項的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也是統計顯著的,這表明出口量和環境規制程度之間呈現出“U”型的關系,拐點為4.19⑦。在拐點的左側,出口與環境規制的關系為減函數,環境規制程度越嚴格,出口量就越小,在拐點的右側,出口與環境規制之間的關系為增函數,環境規制的嚴格會增加出口,這是因為環境規制程度與經濟水平相適應,在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環境規制程度提高會增加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生產成本,損害其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同時會降低污染密集產品的產量,減少其出口。但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和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隨之上升,污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企業會加大清潔技術的研發投入和應用。一方面,企業的規模逐漸擴大,污染處理成本在總成本中占的比例會被產品數量分擔,高效的清潔技術會提高污染處理效率,降低污染處理的時間和成本。此外,生產的產品也更符合綠色環保的國際標準,符合日趨升高的行業標準和消費者偏好,在同類產品中的綜合競爭力上升,并能避免某些國家和地區的綠色貿易壁壘,從而其需求量和出口量也隨之上升,環境規制強度與出口貿易相互促進,曲線也轉而向上。
在2001~2009年間,污染最密集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延展加工業的平均環境規制強度為3.34,造紙及紙制品印刷行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平均環境規制強度分別是9.62、6.61和1.55。由此看來,污染密集型產業中造紙及紙制品印刷行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少數產業已經處于拐點右側的增函數上,消費者對此類產品的環保和可持續性要求逐漸提升。在充分發揮出產業產能的基礎上給予一定的環境政策或貿易政策來提高環境規制強度,可以激發企業清潔技術研發能力和應用水平,通過提高管理效率等途徑來降低產品成本,對其產業競爭力的綜合提升和比較優勢有正向促進作用。但全國所有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的平均值和大多數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指標都在1.5之下,距拐點還有一定距離,因此,對于大多數污染密集型產業,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仍不利于其發展。
對于其他要素稟賦的影響,資本要素的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是統計顯著的,這表明資本要素的積累對出口有正向促進作用,這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符合。資本充裕的污染密集型行業仍然可以通過增加投資和擴大生產規模來增加出口。而勞動力要素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勞動力投入的上升反而不利于出口。近年來,中國平均工資水平上升導致本土加工制造業的成本優勢逐漸喪失,同時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決定的勞動的邊際產量達到最大值后會開始下降,邊際產量為0時繼續投入勞動力會使總產量降低。另外,勞動力投入的上升并不意味著勞動力素質同步上升。熟練工種是稀缺資源,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存量極為有限,非熟練工種的增加甚至會降低邊際產量。企業的科技活動支出與出口也成正比關系,從技術投入到研發成功再到技術熟練應用之間有相當長的運作周期,因而技術要素對出口的促進作用沒有資本要素那么明顯。或者說,我國的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清潔技術研發和應用尚處于初級階段,還未能大規模利用來產生效益。
五、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2001~2009年四個污染最密集產業進行動態面板分析,定量測算環境規制與資本及其他要素稟賦對污染密集產業比較優勢的影響,本文認為無論是與環境有關的貿易政策還是與貿易有關的環境政策,其制定和出臺要充分考慮到行業的特點和發展需要,環境規制程度過高或者環保標準過于嚴格都會對產業和出口產生損害。同時,我國的污染密集型產業也要加快產業升級和整合,可以適當通過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來激勵企業增加清潔技術投入或提高管理效率等方法提高產業和產品競爭力,發掘產業的新增長點。
另外,我國污染密集型產業可以通過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途徑來提高產品產量附加值和貿易量,但在增加投入的同時要進一步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和技術的應用水平,最大程度地轉化為競爭力。污染密集產業比較優勢的形成還需要不斷提高勞動力的效率和素質,勞動力要素的投入離不開資本和技術要素,各種要素以特定比例投入才能把要素轉化為生產力。污染密集產品生產具有負外部性,環境政策的推出勢必要考慮到福利最大化,資本和技術在同類企業競爭中的作用都會歸結到消費者和社會福利上,效率與公平是環境政策體現的首要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