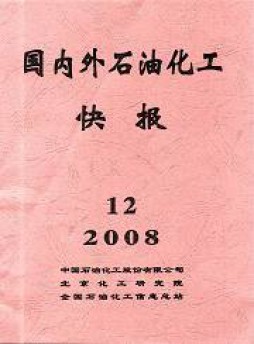國內城市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增長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內城市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增長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上海金融雜志》2014年第七期
一、文獻回顧
本文首先涉及有關金融發展的決定因素的文獻。LaPorta等(1997,1998)從法律的角度解釋了金融發展,他們發現,普通法國家在法律條文和執行上對投資者的保護比大陸法國家更強,金融發展水平更高。Beck等(2003)進一步發現法律淵源影響金融發展的主要機制是適應機制,即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普通法系的國家實行判例法,法官隨時可以根據新的情況來制造新的判例,法律對變化著的經濟環境適應能力強,從而有利于金融的發展;大陸法系的國家采用成文法,法官的權限小,法律制度比較僵化,不利于金融的發展。Rajan和Zingales(2002)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金融發展如何受制于利益集團的影響。他們認為,金融發展容易受到非金融業的產業利益集團和金融業利益集團的阻礙。非金融業的產業利益集團可以依靠自己的盈利來為新項目融資,金融發展只會帶來新企業的進入和競爭的加劇,故金融發展并不符合他的利益;而對金融業利益集團來說,金融發展不僅消滅了金融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租金,也將破壞他與產業的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形成的信用關系。其次,本文還涉及有關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經驗文獻。在宏觀層面的研究方面,KingandLevine(1993)、Levine(1998,1999)采用跨國截面的數據發現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面影響,尤其后兩篇文獻還將一國的法律淵源作為金融發展變量的工具變量,以便消除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逆向影響。周立和王子明(2003)基于中國部分省區的數據也表明,中國各地區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且初始金融條件對長期經濟發展有影響。在微觀層面的研究方面,RajanandZingales(1998)根據行業的數據證明,那些比較依賴外部融資的行業更加受益于金融發展,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則探討了企業的超額增長速度,即實際增長速度超過無外部融資的條件下的增長速度。他們發現,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該國超額增長的企業的比例就越大。最后,本文還涉及有關城市經濟增長的文獻。徐現祥和李郇(2004)搜集了我國216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數據,結果發現,我國城市的經濟增長存在絕對收斂和條件收斂。Zhang等(2012)與本文的內容頗為接近,也采取了中國城市的數據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這篇文獻沒有注意到城市的行政級別對金融發展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此外,鄧偉(2011)根據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不同行政級別城市的收入差距與國有經濟存在一定關系,在1999年之后,越是國有經濟比重較大的省份,省會城市與一般地級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二、變量和數據
(一)實證模型本文需要驗證的第一個假說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對金融發展的影響為正,為此設定如下回歸模型。1、因變量。在模型(1)中,findev表示金融發展。我們用兩個指標來反映城市的金融發展程度,一個是loan,表示城市的貸款總額/GDP,另一個是deposit,表示城市的存款總額/GDP。前一指標可以反映整個城市的融資能力,而后一指標可以反映金融對社會資金的動員能力。在模型(2)中,growth表示城市實際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2、解釋和控制變量。模型(1)和(2)中的pol為本文所要關注的解釋變量———政治地位。在中央集權的權威體制下,城市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行政級別和距離政治中心的距離。本文將城市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地位較高的城市,包括所有的副省級以上的城市和所有的省會城市,另一級是政治地位較低的城市,也就是除第一類城市之外的普通地級市(以下分別稱之為一級城市和二級城市)。如果一個城市屬于政治地位較高的城市,變量pol的值就為1,否則為0。為了了解政治地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是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我們分別在不加入findev和加入findev的條件下對模型(2)進行回歸,觀察系數pol的系數β1的變化。如果在不加入findev的條件下β1顯著為正,但在加入findev后,β1變得不再顯著,而β2顯著為正,就能確定政治地位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影響了經濟增長。模型(1)中的X代表影響城市金融發展的控制變量,具體變量如下:pgdp,人均GDP的對數。一個城市的金融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一般來說,人均GDP越高,對金融的需求就越大,金融的發展水平就越高。popden,人口密度的對數。金融機構的經營存在規模經濟,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金融服務的規模經濟越顯著,金融發展水平就越高。soe:國有經濟的比重。金融發展會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使國有企業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和更低的盈利水平。因此,作為對政府決策比較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國有企業對金融發展持抵制態度,國有經濟較多的城市不利于金融發展。proad,人均道路面積的對數。城市的基礎設施越便利,越有利于金融機構擴張自己的業務,金融的整體發展水平就越高。law,城市政府的執法能力指數,根據法與金融學的文獻,法治環境的改善有利于金融發展。模型(2)中的Y代表影響經濟增長率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pgdp的對數,初始的人均GDP,控制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收斂效應。soe,國有經濟的比重。open,對外開放度。我們用換算成人民幣的FDI數額除以GDP來表示一個城市的對外開放程度3。gov,政府規模。我們用財政支出/GDP來表示,這一變量反映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expfd,財政分權程度,我們用城市的人均財政支出除以全國的人均財政支出來表示。較高的財政分權程度意味著城市政府的財力較強,對經濟增長就能提供更大的支持。proad,人均道路面積的對數。edu,人口平均受教育時間的對數,代表人力資本的水平。
(二)數據本文采用2000-2010年間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的截面數據。中國目前共有286個地級以上城市。考慮到近年來資源價格上漲對一些礦產資源富集城市帶來的資源紅利,本文刪除了51個資源性城市,這樣最后得到了235個城市的樣本。少數地級市在2000年之前屬縣級市,但因行政級別升級前后的行政區域并未有太大調整,故將它們按現在的行政級別來處理。此外,有些發展較快的城市在2000-2010年間的行政區域有所擴大,我們按現在的行政區域范圍對相關變量的數值進行調整。本文的主要數據來自2000-2010年期間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該年鑒同時提供了各城市市轄區和所轄地區的數據,本文關注的是嚴格意義上的城市,除特別說明外,所有變量都采用市轄區的口徑。金融發展指標的測算涉及城市存貸款的數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只提供了2003年之后的存貸款數據。幸運的是,《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分別提供了2000年之后的城市所轄地區和城市所轄各縣市的貸款數據,將前者減去后者即可得到2000-2002年市轄區的貸款數據。但是,對于2000-2002年的存款數據,我們仍只能從《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得到城市所轄地區的數據。因此,2000-2010的loan均根據城市市轄區的口徑來測算,而對于deposit,2000-2002年的值按城市所轄地區的口徑來測算,2003-2010的值則按城市市轄區的口徑來測算。國有經濟的比重按城市所轄地區的口徑來測算,所涉就業人數的數據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直接提供了各城市的名義人均GDP的數據。對于實際人均GDP的計算,我們采用城市所在省份的GDP平減指數對名義人均GDP進行折算,后一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齡來自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變量的計算涉及城市的人口規模,我們均統一采用常住人口的口徑。最后,2001年各城市法治水平的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競爭力年鑒2002》4。
(三)變量的統計特征表1提供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由于我們的回歸方法主要根據自變量2000年初始值對因變量進行回歸,故除了變量growth之外,表2只顯示了各變量2000年統計特征。首先分析該表上半部分的信息,從中可以看到:第一,我國城市近十年來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年均增長率的平均值達到10.7%;第二,兩個金融發展指標loan和deposit的平均值分別有1.205和1.596,說明我國城市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第三,從各變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及標準差來看,我國城市的發展呈現出相當大的不平衡。經濟增長率最快的城市達到了23.9%年均增長率,最慢的城市只有1.8%,金融發展水平最低的城市只有0.13,最高則達到2.81,其他發展指標如lpgdp、edu、open、proad及popden等也有很大的差異。
三、政治地位對金融發展的影響
這一部分討論城市的政治地位對金融發展的影響。表3是分別以loan和deposit作為因變量的估計結果。由于在下一部分關于金融發展對增長率的回歸中,我們均采用金融發展變量在2000年的初始值,故表3中的列(1)和(3)的回歸均采用2000年的樣本值。同時,為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也在該表中的列(2)和(4)分別給出了按所有變量2000-2010年的平均值和2003-2010年的平均值的估計結果。另外,考慮到城市所在省份的個體差異,我們還在回歸中控制了省份虛擬變量。在表2的全部四列估計結果中,政治地位pol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顯著性水平高達1%,說明政治地位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金融發展水平。而且,在經濟意義上,pol的系數最低也達到了0.586,最高則有0.948,這意味著一級城市的金融發展水平要比二級城市至少高0.586,政治地位的影響相當明顯。比較列(1)與(3),或列(2)與(4)可以看出,金融發展選擇loan或deposit,pol的估計系數都相差不大。最后,比較列(2)和列(1),或列(4)和(3)還可以看到,用各變量的平均值回歸所得到的pol的系數要比用2000年的樣本值回歸所得到的結果更大,這可能是因為2000年之后政治地位較高的城市在金融發展上的優勢越來越明顯5。再看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soe的系數除列(3)顯著為負外,其余各列都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2000年之后國有經濟的比重已經大幅度減少,對于金融發展的阻礙作用已不太重要。popden和proad和系數基本都顯著為正,說明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利于金融發展。對于law的系數,除列(3)為正外,其余各列皆為負,只是不太顯著,說明法治環境這一變量并不有效地解釋中國各城市的金融發展。最后,人均GDP的系數基本上都顯著為負,這說明金融發展并不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
四、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這一部分再討論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最終影響經濟增長。本文采用對于增長實證研究常用的截面回歸的方法。為消除增長率對金融發展等變量的逆向影響,所有自變量均采用2000年的初始值。為了觀察政治地位是否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我們先不加入金融發展變量,觀察變量pol的系數是否顯著為正,然后再加入金融發展變量,觀察pol的系數的顯著性水平或數值是否變小,同時金融發展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與前一部分的回歸類似,我們這里也控制省份虛擬變量。與前一部分的回歸相對應,金融發展變量我們先采用貸款方面的指標loan,然后再用存款方面的指標de-posit,表4和5分別是相關的回歸結果。
(一)回歸結果表3和4的列(1)只控制了初始人均GDP,pol顯著為正。列(2)則在列(1)的基礎上加入金融發展變量loan或deposit,這兩個變量都顯著為正,而同時pol的顯著性水平和數值都變小,這說明pol對因變量的影響被loan或deposit所吸收,政治地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正是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而實現的。與列(1)和(2)類似,列(3)和(4)在進一步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基礎上也顯示了pol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影響了經濟增長。兩個表中loan和deposit的系數分別是0.01和0.02,這意味著金融發展水平每提高10%,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提高1個百分點,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經濟意義上也是比較顯著的。此外,對比列(1)和(3)還可以看到,在不加入金融發展變量的情況上,列(3)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后,pol的數值變小,但顯著性水平仍保持在5%的水平。這說明城市政治地位的高低也與影響經濟增長的對外開放、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方面有一定的關系,但不及與金融發展的關系那么顯著。換句話說,政治地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還是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
(二)穩健性分析6我們從三個方面討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首先是樣本的選擇問題。本文剔除了51個資源性城市。事實上,即使加入這51個城市,以上基本結果仍然大致相同。唯一的區別就是變量edu不再顯著,這可能是資源性城市的增長主要還是依賴自然資源稟賦,而不是人力資本。另外,本文的城市樣本中包括了四個行政級別最高的直轄市,它們的政治地位最高,可能會強化政治地位的影響。但是,即使刪除這四個城市,前面的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不變。其次是金融發展變量deposit的測度問題。由于數據的缺失,我們只能按地級市所轄地區而不是從市轄區的口徑來測度2000年的deposit。為此,我們再用2003年市轄區的deposit及控制變量2003年的樣本值對2003-2010的增長率進行回歸,只要剔除51個資源性城市,估計結果就依然保持穩健。最后是自變量2000年的初始值的可靠性問題。受經濟周期的影響,金融發展等變量的數值容易波動,從而導致回歸結果的扭曲。為此,我們用2000-2002年三年的平均值代替2000年的數值,重新對因變量進行回歸,估計結果依然保持穩健。
五、結論
本文根據2000-2010年中國城市的截面數據從金融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城市的政治地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首先證明,城市的金融發展水平與其政治地位正相關。然后我們進一步證明,城市的政治地位對經濟增長存在正向影響,而一旦加入金融發展變量,政治地位的影響就會被金融發展變量所吸收,但在不加入金融發展變量的條件下控制其他變量,政治地位的影響就會仍然存在。這就表明,城市的政治地位主要是通過金融發展的渠道而影響經濟增長,政治地位越高,金融發展水平就越高,經濟增長也就越快。本文的結論意味著,在中國經濟的轉軌時期,政治權力仍然影響著城市的經濟發展,進而導致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原因就在于政治權力影響了金融的發展。在國有銀行所主導的金融體制下,中央政府往往按城市政治權力的大小來配置金融資源,而國有銀行也需要向政治等級更高的政府來尋租,于是政治地位較高的城市集中了較多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源。因此,要縮小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應該從金融發展的角度著手,大力發展中小型的民營金融機構,才能有效地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使金融資源的配置更加均衡。
作者:鄧偉王高望單位:南京財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
擴展閱讀
- 1國內媒介文化
- 2國內公債史
- 3國內購物旅游探究
- 4國內檢察權分析
- 5國內村民分化研究
- 6國內小額信貸監管分析
- 7國內武術文化研究綜述
- 8國內物流金融
- 9國內毒情形勢表述
- 10國內翻譯研究綜述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國內產業調研
- 2國內安全保衛論文
- 3國內外形勢論文
- 4國內對財務風險的研究
- 5國內博士論文
- 6國內市場營銷方案
- 7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研究
- 8國內工程造價管理現狀
- 9國內的公共藝術
- 10國內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