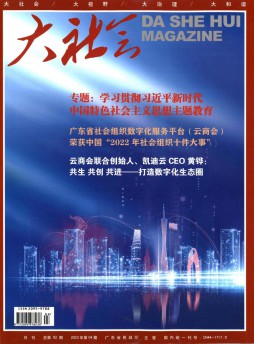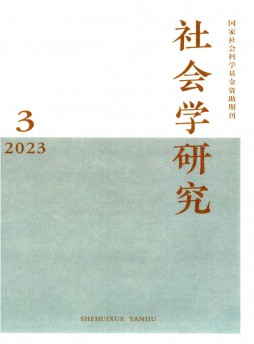社會中心主義視角下的腐敗治理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中心主義視角下的腐敗治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2015年第五期
世界上治理腐敗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國家中心主義治理;二是社會中心主義治理。前者強調國家及政府擁有堅定的決心和信念,建立相應的反腐敗制度(法律)及專業的反腐敗機構;后者則強調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合理的競選,政府責任機制以及強有力的公民社會(Johnston,2005)。在現實中,兩種模式各有優劣,亦都存在相應的問題。基于此,約翰斯頓(2005:150)認為:對于腐敗治理的理想模式而言,需要建立一個社會行動聯合體。該聯合體強調兩個方面的因素:既有領導者的堅定決心和意志,又有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個案。然而,在以往的文獻研究中,大部分學者更多地從制度借鑒與學習的視角來剖析香港個案。他們認為香港肅貪成功的原因在于堅定的政治決心與信念(Quah,1999);獨立的專業肅貪機構廉政公署(ICAC)(Kuan,1981;Mc-Walters,2003;Nikos,2010;Wong,1981);香港的其他優勢,例如人口規模較小、經濟總量較高(Quah,1999)。不可否認的是,香港模式不乏國家中心主義所強調的堅定的政治決心,強有力的制度建設。但除此之外,香港模式還擁有另外一個層面的內涵,即社會中心主義所強調的積極的社會參與。不無遺憾的是,已有的研究并沒有將這個層面提升至特別重要的地位。作為世界少有的成功典范,香港模式的獨特性就在于它不僅僅是政府推行的腐敗控制,還包括積極的社會參與。因此,本文旨在借助社會中心主義的分析框架來重新審視和挖掘香港腐敗治理的成功經驗,將長期被忽視的社會參與要素拉回學術視野中。
在社會中心主義理論的框架下,國家與社會需要及時的溝通,國家需要對社會的訴求予以關注和回應,同時公民能夠有廣泛的政治參與機會。腐敗最為普遍的理解是“公共權力的濫用”(Heidenheimer,1989)。已有文獻表明,對于公共權力的約束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橫向的內部約束機制,其訴諸的是權力主體之間相互制約和監督;另一方面是縱向的外部約束機制,其訴諸的是權利主體即公民社會對國家的監督和制約。國家中心主義視野下的腐敗治理模式所強調的正是第一個方面的約束機制,其強調政治動員與制度設計的重要性。然而,這一治理模式存在兩個弱點:一是對縱向的外部約束機制的忽略;二是對公民權和公民身份建設的忽視(李輝,2013)。上述兩個弱點恰恰是社會中心主義最為強調和重視的。現有各國的歷史都表明,在從腐敗到清廉的治理改革過程中,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設固然重要,但保持和維系改革的動力問題卻更為關鍵。社會中心主義模式下的社會監督正是為腐敗治理改革提供持續動力的源頭所在。因此,社會中心主義模式對于推動一個政體從腐敗到清廉是有幫助的,甚至比國家中心主義的作用更強大。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針對香港廉政公署的年度報告進行深入的內容分析,進而梳理出社會參與的基本歷史脈絡。全文結構如下:第一,1974年之前的歷史回顧;第二,1974年到1997年的發展;第三,1997年之后面臨的新形式的腐敗及其發展。
一、市民參與的發端:從“難民”到“市民”(1974年之前)
香港自1840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腐敗就一直存在(Palmier,1985)。作為以華人為主體的殖民地,腐敗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生活方式(Palmier,1985:123)。隨著時間的推移,腐敗的影響不斷深入(Kuan,1981:16)。英國殖民政府早在1898年就引入英國的法律加以管制(《行為不端處罰條例(MisdemeanorsPunishmentOrdinance)》)。然而,這并未有效治理遍布整個社會的腐敗現象(Kuan,1981),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戰后香港的人口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而非真正的市民。這些難民的首要任務是解決溫飽問題。因此,當時的人們并未意識到腐敗對于他們來說是一種嚴重的問題(Lee,1981:101)。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隨著二戰結束,香港開始進入到現代化轉型發展階段。快速發展的工業化使得英國殖民政府希望借助香港尋求更大的經濟利益,而當時腐敗問題對經濟的影響也開始顯露端倪(Lethbridge,1974;Kuan,1981)。對此,英國殖民政府首先頒布了新的法律———《預防腐敗條例(1948)(ThePreventionofCorruptionOrdinancein1948)》。建立了專門的肅貪機構(Lee,1981:5),即在警察局內部的刑偵調查署(CriminalInvestigationDepartment)成立了一個半獨立機構反貪污處(Anti-Corrup-tionBranch)(Kuan,1981)。與此同時,市民的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代難民已經被新一代的土生土長的市民所代替(Lo,1993)。由于這些難民的第二代深受西方教育的影響,因此他們更加重視自由和權利。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警察系統內部的集團式腐敗日益嚴重。與此同時,市民社會的力量不斷增長(Lo,1993;Chan,2005;Ku,2002),訴諸于社會不公的街頭運動也不斷出現。警司葛柏貪污事件①成為引爆市民不滿情緒的導火索。媒體的積極揭露導致市民發起了著名的“反貪污、抓葛柏”運動。這場運動第一次真正體現出了公民個人積極參與揭露貪污進而打擊貪污的重要作用。為了平復民怨,穩固統治,殖民政府一方面在1971年英國殖民政府頒布了《防止賄賂條例(thePreventionofBriberyOrdinance)》;另一方面,在新加坡肅貪經驗的基礎之上,建立了肅貪辦公室。
眾多已有的共識都認為葛柏事件成為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的導火線,也開啟了香港肅貪的新紀元。同時也有學者通過深入梳理葛柏事件,指出當時的殖民政府總督麥理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當時的政府首領,麥理浩堅定的肅貪決心促成了廉政公署的成立以及之后的強有力的肅貪治理(Rep,2013)。無可否認,葛柏事件之后,政府迅速而強有力的制度建設行為對香港的腐敗治理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較少文獻注意到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殖民政府借助葛柏事件所開啟的腐敗治理大幕,并非只是源自政治領袖的政治意愿;相反,在某種程度上它恰恰是殖民政府的一種被迫選擇。根據盧鐵榮(1993)的研究發現:葛柏事件爆發時,香港的市民主體已經成為第二代移民,當時香港社會衍生出兩種價值沖突:其一是關于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矛頭直指英國的殖民統治者;其二是關于社會階級之間的社會不公的矛盾。這兩種價值沖突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的爆發。其中最為著名的葛柏的腐敗案件被媒體曝光后,上述市民群體中的價值沖突被充分引爆出來。如此,來自社會民眾的強烈的不滿轉變為廣泛的社會運動,這帶來了殖民政府的統治危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殖民政府才必須借助打擊腐敗贏得民心,緩解合法性危機。因此,葛柏事件促使正在興起的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到腐敗治理當中。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香港的廉政公署的成立、香港肅貪新歷史的開啟,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力量的促成。
二、市民參與動機的保障:獲得實質性好處(1975~1997年)
葛柏事件的持續發酵直接促成了更為獨立的專業肅貪機構(廉政公署)的成立②。成立之初,廉政公署傾向于打擊公共部門的公務員腐敗,而較少打擊商業腐敗(Lo,1993:103)。據廉政公署的年度報告顯示,在1974年到1977年的5年內,共有269名警察被指控,這一數字是廉政公署建立之初的拘捕人數的四倍(Manion,2004:40)。雖然廉政公署自誕生之日起就積極肅貪,但市民卻并未表現出極大的信任。很多市民表示廉政公署想要肅貪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他們認為貪污賄賂是中國傳統的習俗,很難被根除。葛柏貪污案件表明殖民地香港的警察集團式腐敗非常嚴重,葛柏只是眾多警察腐敗人員中的冰山一角。因此,廉政公署針對警察系統的集團式貪污進行了深入的偵查,發動了一場專門的肅貪運動。在1970年末,廉政公署清除了所有的警察集團式腐敗(Manion,2004:72),使得警察集團腐敗成為過去式①。顯然,香港廉政公署對于警察系統集團式腐敗的根治是贏得民眾認可、獲取廣泛民意支持的重要舉措。正是這種自上而下的肅貪決心使得民眾對廉政公署產生了信任,從而能夠開始積極參與舉報等反腐敗活動。
20世紀80年代后的香港進入到工業化發展的快車道。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廉潔而公平的商業環境成為香港社會的最大需求。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廉政公署的偵辦策略從公共部門逐漸轉向私營部門。據廉政公署的年度報告統計數字顯示,自1980年起,涉及私營部門的腐敗案件數目逐漸增加;而涉及政府部門的個案數字逐漸下降。至1982年,私營部門涉及腐敗的個案(247例)數首次超過政府部門的個案數(126例),此后一直如此。與之相伴的是殖民地香港也進入到一個相對自由的發展時期(Lo,1993)。自由言論、結社權利以及司法獨立、法治的充分保障使得這個時期的市民社會充滿活力(Ma,2008)。這個時期,市民對于腐敗的容忍度愈加下降,積極參與舉報。根據廉署接獲的投訴案件的統計亦顯示,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民眾對于私營部門的腐敗投訴案件不斷增加并逐步超過政府部門的投訴數目。約翰斯頓(2005)指出,“腐敗治理達到的最好狀態就是有一個擁有廣泛民意且能夠持續支持政府反腐敗的公民社會”。在民意支持下,自20世紀80年代起,香港的腐敗治理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紀元。
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也就是過渡期的后期,香港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訴求民主的政治選舉活動(例如區議會選舉)和政黨活動開始出現;社會運動呈現出多元化格局,涉及到人權、反對歧視、身份認同等各種主題(Ku,2002)。在過渡期的后期,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初,更多的涌現出訴諸于民主直選的政治性的社會運動(So,2011)。這些新的發展機遇促使市民社會的力量不斷壯大。同時,在過渡期后期,出于對1997年回歸之后的考慮,殖民地政府加快引入了人權法案(Lo,2009、2012;Kwok&Lo,2013)。公眾的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隨之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公民積極參與舉報貪污。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選舉活動的增加,廉政公署接獲的貪污舉報數字持續攀升。其中,1993年和1994年的情況尤其顯著(見圖1)。另一方面,市民對于廉政公署自身的監督也逐漸增強起來。香港在1992年引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并由立法會頒布了《香港人權法案》。人權法案的引入使得公眾開始注意到廉政公署的權力是否過于不受限制從而有可能侵犯個人權利。公眾對此高度憂慮和質疑。在媒體和公眾輿論的壓力下,殖民政府在1994年2月委任了一個以蘇海文博士為主席的獨立權責檢討委員會,專責檢討廉署的權力和問責制度,并于年底呈交檢討報告書。在這份檢討報告書中“總共做出了76項結論和建議,范圍包括:廉政公署的任務,獲得資料的權力,搜查與檢取;逮捕、扣留與保釋;扣留旅行證件;將財產處置的限制;調查程序;調查的保密;查閱公共機構的資料;職員的委任、管理及終止聘用;問責制度以及廉署五個咨詢委員會的架構與職責。”
這是廉政公署自1974年成立以來第一次遭遇公眾質疑。相對于廉政公署建立之初的舉報而言,20世紀90年代后期所爆發的這次事件更能充分顯示出市民日益增長的監督權力。這種來自社會的監督權力對于腐敗的預防打擊和腐敗機構自身的廉潔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市民能夠充分參與到舉報、監督的行為中,因而香港的腐敗治理呈現出典型的社會中心主義色彩。回顧香港20世紀80年代到回歸前整個腐敗治理的進程,不難發現,無論是從公共部門向私營部門的轉向,還是針對人權法案對于廉政公署權力的質疑,社會民眾都表現出極大的參與熱情。如果說早期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集中根除集團式腐敗的運動中,政治領導的堅定肅貪決心促使民眾開始認可廉政公署,那么這之后的十幾年時間內,民眾還能一如既往的支持反腐敗的原因就涉及到約翰斯頓所提及的民眾參與的動力問題。約翰斯頓認為,“民眾需要原因和動機去維持他們的行動:他們必須要相信他們有義務減少腐敗并從中得到好處”(Johnston,2005)。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正是經歷現代化轉型且經濟發展最為迅猛的十年,香港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些快速發展的背后源于香港良好的經濟投資環境:香港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和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稱譽海外②。經濟的快速增長充分落實到每一個公民身上,使其受益。盧鐵榮(1993)的研究表明在當時民眾普遍感到從反腐敗中獲得了實質性的好處。這使得民眾參與反腐敗成為一種常態。因此,只有真正讓民眾獲得腐敗治理成功所帶來的實質性好處才能保證市民的持續參與。
三、社會參與的核心內涵:廉潔文化成為基因(1997~2013年)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行高度自治。廉政公署在1997年回歸之后,繼續保持獨立的專業特性,從殖民地時期向港督負責轉變為向特首負責。在人員構成與財政資金上都繼續獲得足夠支持。斯科特(2013)的研究表明,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之后精簡了公務員隊伍,從189139人精簡至163637人,精簡幅度達到13.5%①,但廉政公署各個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數目不減反增了(見圖2)。另一方面,財政資金的數據也表明,廉政公署作為香港的專門肅貪機構獲得了有力的財政支持。從圖3中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政經費就一直在增加。從廉署檢控的統計數字上看,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后,無論是公營部門還是私營部門,整體上都沒有較多的案例增長。但是,例外的年份發生在1997~1999年,從1997年開始,廉署檢控的數字開始增加,至2000年達到高峰值608例,其中涉及政府部門的個案為144例,涉及私營部門的則為455例;此后略有減少,但在2002年又有所增長。回歸之后,廉政公署在肅貪方面依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各項統計數字也表明香港的貪污狀況都未出現集團式貪污“死灰復燃”的現象。然而,由于政經環境的改變,由于政府新公共管理的推行,除了按照法律界定的傳統形式的貪污行為之外,新形式的貪污———利益沖突①卻在高層官員中逐漸顯露出來(Scott,2013)。斯科特(2013)的研究表明,1997年回歸之后香港的政經環境的變化導致公務員人員構成和管理上的變化:其一,高層公務員逐漸本地化。本土的高層公務員在退休后會傾向于受雇于私營機構,這使得公務員退休管理面臨很大的挑戰。其二,第一任“特首”來自商界,他致力于推行私有化為導向的新公共管理變革。與之相對應的正是兩種最為典型的利益沖突形式:一種是延后利益,即公職人員在退休或離任之后去私營機構工作以換取曾經在擔任公職時交換利益獲得的好處(Scott&Leung,2008:366);另一種是在私有化運動下,公職人員利用公共服務外包或其他機會尋求私人利益。
隨著利益沖突現象的增多,香港特區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公務員事務局轄下的ACPE與ICAC的聯合模式,一起防范和打擊利益沖突。根據廉政公署的年度報告顯示,廉政公署一方面依靠防止貪污處對政府及公營機構制定各種相關的防止利益沖突指引,另一方面借助社區關系處的教育資源推廣一系列涉及公務員誠信的倫理道德教育活動。從統計數字上看,防貪處制定利益沖突指引的部門自1998年后不斷增加,平均每一年都會涉及到2~3個政府及公營機構部門。社區關系處所做的防止利益沖突的教育活動也平均每年都有1~2個專項講座。但是,由于利益沖突被界定為腐敗是非常困難的。一旦認為利益沖突涉及腐敗,運用何種方法進行管治也是目前香港面臨的一個問題。因而僅僅依靠以廉政公署和ACPE為主的制度治理就顯得較為單薄。從廉署接獲的舉報案例數目來看,從1999年到2000年間顯示出較高的數字攀升(見圖1)。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入到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9年以來,檢控數字和舉報數字亦都有明顯的攀升。以2009年為例,檢控數字達到342例,2010年則增加到393例;而舉報數字也顯示出2009年3450例,2010年略為減少(3427例),2011年4010例,2012年3932例。相比較1999年前后的數字增長,近年來的數字攀升表明了一種新的社會狀況,即“市民亦可能因為不滿某些政府官員的行為,因而向廉署投訴,希望討回公道”②。普通民眾舉報數字的持續增長表明了民眾對于新型腐敗的不能容忍,以及對廉政公署與政府不能進行有效的管治的不滿。除此之外,市民在近年來還積極參與各種反對貪腐和利益沖突丑聞的社會運動中。香港近年來的高層官員的涉及利益沖突的丑聞不斷增多,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斯科特(2008;2013)的研究表明,一旦有涉及利益沖突的政治丑聞出現,民眾和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加強更嚴格的管治。民眾對于官員的誠信要求越來越高,也希望政府能夠建立更加強有力的法律制裁。相比較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社會參與,近年來香港社會民眾訴求的主題更加集中和鮮明。這與香港的政經變化都有密切的關系。在回歸后的幾年里,在中央政府的幫助下,香港雖然度過了金融危機,但經濟衰退卻一直持續發酵。香港人的低身份認同感以及深層次的社會發展焦慮感在不斷加劇(So,2011)。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訴諸于反對貪腐問題的社會運動不斷涌現,他們在監督政府,批判貪腐問題上的能力也不斷增強。公眾對于反腐問題的高度關注以及投身于公民運動表達不滿的行為充分顯示出香港民眾作為重要的社會力量起到了重要的監督公權力的作用。民眾舉報、媒體曝光、市民運動表明香港擁有充分的社會力量,進而能夠對公共權力的濫用等腐敗相關行為予以監督。這也正是依靠權利來監督權力的最好體現。在整個過渡時期,香港的快速經濟發展讓市民真正從反腐敗中獲得了實質性好處,帶來了市民參與動機的重要保障。然而1997年回歸之后,尤其是近年來的香港實際上貧富差距在不斷加大。公開數據顯示,從1971年開始,香港地區的基尼系數不斷上升。1971年初,基尼系數為0.43;1986年至1996年,這一數值開始出現跳躍性增長,由0.453升至0.518,隨后增速放緩,直至2012年達到0.537的歷史高位①。社會不公等矛盾不斷激化,市民所獲得的實質性好處是在下降或減少。然而,市民的反腐敗參與不僅沒有中斷,反而更加積極和多元,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通過深入剖析,本文認為支持市民參與動機的另外一個重要保障就是成熟的廉潔文化。來自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報告顯示,公眾對腐敗持有較強的厭惡感,同時公眾相信廉潔社會對于香港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在2012年的調查報告中顯示,有99.2%的受訪者認為保持香港社會的廉潔將會有益于香港吸引外資,帶來各種經濟收益。同時,在2011年的年度調查1500名隨機受訪者中,約有80%的人對于腐敗持“零容忍”態度。而從另外一個數據也可以看出,自2001年首次進行相關調查以來,香港市民對于腐敗的容忍度的平均分為0.7(0代表完全不能容忍腐敗,10代表完全可以容忍腐敗)(詳見表1)。香港的個案表明公民參與是反腐敗的重要組成部分,零容忍的廉潔文化或信仰則能轉變為公民舉報行動的堅強決心(Chan,2005)。利益沖突這種新的腐敗形式在近年來愈演愈烈,按照現有的香港法律卻難以界定與偵辦。香港的廉政公署以及政府相關部門陷入了一種制度困境。然而,由于香港市民已經培養起了成熟的廉潔文化,社會參與的動力一直持續不斷,因此其已經成為制度缺陷的重要彌補措施。成熟的市民文化、積極的社會參與,使得民眾對于官員及公權力的監督成為一種自覺,這恰恰是社會中心主義所強調的最為重要的內涵。
四、結語
在OECD給治理腐敗開出的藥方中,強調腐敗問題的治理主要依賴三種途徑:建立有效的透明化的政治系統;強化打擊腐敗的行動;以及支持積極的公眾參與。在以往的研究中,香港模式的解讀被過多地聚焦于廉政公署這套獨立的專業肅貪機構上。因而,這似乎已經造成一種誤解:只要建立一個類似于ICAC的專業反腐敗機構,腐敗就能被成功治理了。本文通過對廉政公署的文本梳理與解讀發現,香港模式不僅強調政府在腐敗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亦重視有序、合法、專業化、制度化的公眾參與。這種基于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于一身的獨特模式才是香港腐敗治理的精髓所在。這也正是約翰斯頓提出的社會行動聯合體建構的內涵所指。社會中心主義的腐敗治理模式應該包含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整個社會在道德風氣上擁有抵制腐敗行為的文化與觀念;二是普通民眾擁有參與反腐敗的合理途徑“(李輝,2013)。上文的分析已經表明,早期的香港市民也視腐敗為生活的一個部分,認為關系和人情等傳統文化勢必會與腐敗相伴相生。但是,經過葛柏事件;經過廉政公署的大力打擊貪污;經過20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廉潔環境的重視,香港市民對腐敗現象零容忍的廉潔文化已經深入人心。市民觀念的轉變是伴隨著社會政經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的,是伴隨日益成長和成熟的公民社會的發展而發生的。因此,這是香港社會能夠長期保持廉潔的重要的社會文化基礎。此外,普通民眾參與反腐敗擁有較為合理的途徑:一是公眾具有合法且制度化的舉報渠道。廉政公署的統計數字顯示出市民在舉報貪污上不僅可以有通道而且有實名保護制度,這使得全社會都能夠形成舉報的良性循環。二是公眾有合法參與表達不滿的制度渠道。無論是在早期的“反貪污,捉葛柏”事件中,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對于廉政公署權力質疑的事件中,以及在近年來針對高層官員利益沖突的社會運動中,公眾都能夠通過合法的、有序的方式表達意見,參與監督公共權力。基于社會中心主義的腐敗治理提供了一條社會監督公共權力的路徑,是一種體外監督。香港個案對我們的啟發是:如果說國家(政府)的堅定決心和領導者的堅強意志以及獨立的反腐敗制度設計是一個國家(地區)治理腐敗必不可少的,那么社會公眾參與則是一個國家(地區)從腐敗到廉潔改革進程中必須重視的要素。只有民眾真正視腐敗為必須鏟除之惡疾,能夠參與監督公共權力,才能使得所有的制度設計落實到實處。中國的腐敗治理不乏社會參與,李輝(2013)的研究表明自中共蘇維埃時期起至今公眾參與都能找到身影。近年來,一系列改革正在將公眾參與腐敗治理逐漸制度化、有序化。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舉報監督制度的改革。中央紀委監察部2009年開通了12388舉報熱線,最高檢開通12309舉報熱線;2013年9月新版中央紀委監察部官方網站開通上線,網絡舉報數量呈現明顯上升之勢。據報道,2013年9月2日至10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舉報網站統計的網絡舉報數量達2.48萬多件,平均每天超過800件,而在開通之前的同年4月至8月每天只有300件①。同時,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土資源部等五部門官方舉報網站日均瀏覽量增加了兩倍多,網民舉報數量和舉報受理數量增加近1倍①。這些都表明腐敗治理的改革正不斷加強和重視公眾有序、合法地參與。腐敗治理是一個持久而長遠的改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的積極參與是確保其可持續進行的動力因素。顯然,香港個案的意義在于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路徑,依靠有序、合法、制度化的公眾參與來培養零容忍的廉潔文化,從而建立起有效的體外監督模式。
作者:李莉 單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 上一篇: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評價范文
- 下一篇:道教在草原地區的傳播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