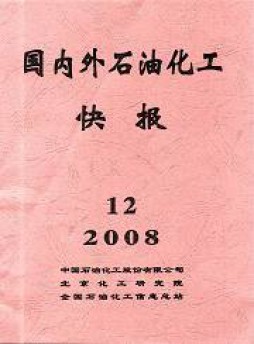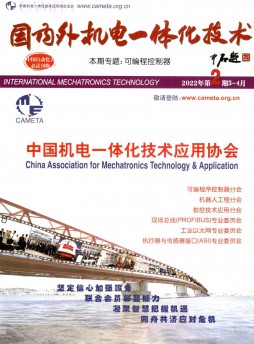國內外企業政治風險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內外企業政治風險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國際石油經濟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伊拉克政治的地區背景與歷史傳統
當前的伊拉克政治格局一方面取決于中東地區的整體背景,一方面取決于伊拉克國內近百年來的政治歷史傳統,其“政治碎片化”現狀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011年底美軍撤離之后,此前被美國強大軍事力量壓制的地區背景和歷史傳統開始發揮更大的影響。
1.宗教民族對立與地緣政治因素伊拉克國內的地區割裂和“政治碎片化”有著深層次的地區整體背景。第一,在涵蓋中東、北非、中亞廣大地區的伊斯蘭世界,遜尼派與什葉派在關于宗教理論、文化傳統和政治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巨大分歧和長期對抗。第二,阿拉伯人、波斯人、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等多個民族在漫長的歲月中持續碰撞、相互融合,形成了政治模式各異的現代國家,也埋下了今日整個地區政治波動不斷的根源。第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個地區政治大國持續競爭,爭相對周邊國家施加影響。第四,出于地緣政治因素考慮,美國等外部力量也在持續影響著該地區的政治進程。因此,在地區宗教民族對立與地緣政治因素等大背景的影響下,伊拉克形成了極為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現狀。從宗教民族角度看,伊拉克西部與北部主要是遜尼派阿拉伯人居住區,中部與南部是什葉派阿拉伯人居住區,東北部是庫爾德人居住區(見圖1),三個地區彼此相對獨立,各自與宗教民族同源的外國地區之間的關系甚至比本國其他地區更緊密。從政治模式角度看,2003年以來,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什葉派政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背后的阿拉維族雖然信奉什葉派,但實質上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奉行宗教寬容政策),且率先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議會制民主選舉模式(有別于埃及、敘利亞和薩達姆時期民主模式下的軍事獨裁),被海灣地區的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等遜尼派王室國家視為洪水猛獸。從地緣政治競爭角度看,位于中東地區核心地帶的伊拉克不僅石油儲量巨大,而且水資源最豐富、農業條件優越,同時是連接周圍山區、沙漠和波斯灣海路的交通樞紐,是美國、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外部力量競相爭奪的焦點,也是恐怖組織和極端勢力覬覦的發展空間。
2.政治現狀的國內歷史根源過去近百年間,伊拉克經歷了英國扶植的王國、阿拉伯復興黨領導的總統制共和國和2003年美國入侵后建立的議會制聯邦共和國三個階段,雖然國家名稱和政治模式一再改變,各派本土強權和外部力量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伊拉克政治模式的實質幾乎沒有變化。第一,世襲制家族部落政治是維系各種社會形態與國家權力組織之間關系的基石。主從關系網——保護人和人組成的社會網絡——貫穿于伊拉克政治歷史的始終,一張張以當權者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主從關系網伴隨著“部落政治”的起伏使“當權者—核心利益小圈子—部落—家族”成為代替國家正式行政機關來發揮作用的權力鏈條,從而使世襲制和“影子國家”成為維系伊拉克國家政權運作的真正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依靠世襲制建立起來的團體保證全體成員榮辱以共,他們在權力游戲中成為或依附于最強者,追逐并保障團體物質利益。2003年美軍入侵以來,活躍于伊拉克政壇的各黨派都是此前被薩達姆壓制的世襲政治家族,而失勢的遜尼派民眾也紛紛依附于部落領袖以求自保,形式上的新政體并沒有改變世襲制家族部落政治的實質。第二,石油財富分配是伊拉克政治活動中最重要的主題。石油出口收入是中央政府手中鞏固核心群體、打擊異己力量的最主要手段,同時成為伊拉克國內矛盾的根本動機——中央政府利用石油財富發展軍事力量維持統治,產油區民眾認為受到政治經濟歧視而醞釀反抗。從伊拉克王國時期開始石油開發,到2013年美國幫助制定《一體化國家能源戰略》,石油開發一直是國內政治的焦點;與此同時,石油財富引起的紛爭強化了世襲制的作用,為了爭奪物質利益,家族部落模式成為中央當權者和地方反抗者共同依賴的工具。第三,使用暴力和對暴力機關的重視與爭奪是伊拉克政治始終無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從20世紀初英國殖民統治開始,掌握暴力機關一直是中央政府得以立足的根本;而中央政府僅僅占據了核心大城市并對農村部落實行羈縻控制的現實,迫使掌權的歷屆中央政府在缺乏有效統治的基礎上,將使用暴力作為應對地方問題的首要方法。這在2003年美國入侵削弱中央政府之后更加明顯,地方民兵團體、反叛武裝和安全部隊共同演繹的暴力鬧劇每天都在上演。2012年底中央政府軍與庫爾德地區武裝“自由斗士”激烈沖突;2014年開始中央政府軍、遜尼派地方部落武裝和恐怖組織“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持續對峙,6月恐怖組織的進攻蔓延到整個西部和北部地區。軍事沖突和對峙之外的恐怖暴力活動遍布全國,并且幾乎每個宗教民族派別和利益團體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恐怖暴力活動。
二、國內政治對伊拉克油氣開發模式的影響
在經濟發展落后但石油儲量極大的伊拉克,油氣開發收入是各派力量維持地方支持和發展軍事力量的關鍵,因此,伊拉克國內政治斗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石油財富的分配方面。2013年6月,伊拉克中央政府公布的《一體化國家能源戰略:2012-2030》(IntegratedNationalEnergyStrategy,INES)為伊拉克能源行業勾勒出了極為美妙的前景,為全球各家石油公司描繪出了極具吸引力的藍圖。與此同時,透過這份由博思管理咨詢公司(Booz&Company,著名美國政府事務和國防業務服務商)制定的戰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規范伊拉克油氣行業——國內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的國家能源政策無處不反映著伊拉克的政治現實,體現著錯綜復雜的政治安排。
1.中央政府與庫爾德地區政府實行兩套油氣開發模式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南部地區與庫爾德地區政府控制的東北部地區同時實行兩套油氣開發模式,使伊拉克油氣開發在事實上處于地區割裂狀態,并圍繞著吸引國際能源公司投資和原油出口渠道等核心問題糾紛不斷。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南部地區,2007年5月,美國幫助制定的新《石油天然氣法》雖未獲得議會通過,但被馬利基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批準。該法案允許外國企業以產品分成合同方式參與伊拉克石油開采,但是迫于國內壓力,伊拉克中央政府進行的4輪招標①都只向外國企業授予技術服務合同(TechnicalServiceContract,TSC)。伊拉克中央政府組建了北部石油、中部石油、南部石油和米桑石油等4家國家石油公司,代表國家在與外國投資者組成的作業合資公司中持股,執行技術服務合同。在庫爾德地區政府控制的東北部地區——主要包括達胡克(Dahuk)、埃爾比勒(Erbil)和蘇萊曼尼亞(Sulaymaniyah)三個省及部分爭議地區,相對于中央政府較為苛刻的技術服務合同,庫爾德采取的是國際上較為流行的產品分成合同(ProductionSharingContract,PSC),直接向外國公司按比例支付原油,對外國公司的約束更少,留給外國公司的利潤空間更大。中央政府與庫爾德地區政府之間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對《伊拉克憲法》相關條款的理解上。《憲法》第112條規定,中央政府擁有對2005年(《憲法》頒布時間)時未恢復生產的全部油氣田的排他性管理權。但是,庫爾德地區的原油生產都來自于2005年后勘探開發的新油田,因此,庫爾德地區政府認為其有權處置區內油氣田。中央政府依然對庫爾德地區政府和外國公司所簽署的合同持堅決反對態度,并威脅制裁投資于庫爾德地區的國際投資者。此次大選中,庫爾德地區聯盟是馬利基派別之外獲得議會席位最多的政治力量,也是馬利基不得不爭取的盟友。在庫爾德人已經取得了油氣獨立開發權之后,下一步將要爭取的是獨立出口權,而伊拉克石油出口的有關規定使這個國內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2.原油出口收入的國內與國際政治博弈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和第1510號決議,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必須存入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伊拉克發展基金”賬戶(DevelopmentFundforIraq,DFI),首先扣除5%用于賠償薩達姆侵略科威特造成的戰爭損失,剩余95%由伊拉克中央政府根據財政預算支配,資金收支過程受美國嚴格監管。也就是說,無論伊拉克政局如何變化,伊拉克國庫實際存放在美國;一個未來能夠日產900萬桶原油——達到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和美國等世界一流能源生產國水平——的重量級選手,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伊拉克石油部下屬的國家石油營銷組織(SOMO)全權負責石油銷售,也是伊拉克原油的唯一商業出口渠道。出口收入納入政府財政預算,按比例分配給中央政府和地方省級政府。在出口收入使用方面,伊拉克政府大量采購美國軍火和機械設備,并積極邀請波音、通用等美國企業在伊拉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美伊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并未因為美軍撤離而疏遠,反而隨著伊拉克國民經濟的恢復而日益密切。但是,出于對什葉派長期通過控制中央政府而占據絕大多數石油收入的不滿,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回擊。由于在政治上缺乏話語權,遜尼派經常對伊拉克北部的石油出口管道進行武裝襲擊,致使位于北部遜尼派聚居區的基爾庫克管道系統在此次大選前完全中斷。自2013年1月由于開發招標和財政收入分配問題與中央政府間矛盾激化后,庫爾德地區不再通過中央政府的管道系統出口原油,改用卡車向土耳其和伊朗出口。與此同時,庫爾德地區試圖徹底擺脫對中央政府的依賴,將其對預算分配不合理和撥款不及時的不滿轉化為爭取獨立原油出口途徑的努力。2013年12月中旬,庫爾德地區獨立的輸油管道已與土耳其邊境的費什喀布爾(Fishkabur)中轉站成功連接并完成測試;2014年1月中旬,庫爾德原油已經抵達土耳其地中海沿岸杰伊漢港(Ceyhan)油庫;5月22日,第一船約100萬桶庫爾德原油駛離杰伊漢港。伊拉克中央政府對此強烈反對,于5月23日在國際商會(ICC)對庫爾德地區政府、土耳其政府和杰伊漢港運營公司Botas進行起訴,并贏得了美國的支持。一個主權國家政府在國際仲裁法庭起訴其地方政府的行為讓外界清楚地認識到伊拉克國內“政治碎片化”的冰冷現實。與此同時,伊拉克中央政府通過美國、伊朗、土耳其等對伊拉克國內政治有影響力的國家進行斡旋,將伊拉克國內政治的地區背景表露無遺。
三、中國石油企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
國際化經營中的政治風險是指由政策變化和政治變化所引起的、難以預測的經營環境改變(不連續),是非市場類風險的總稱。一般而言,海外市場的政治風險可以具體解釋為所在國政治決定的結果(財政、貨幣、貿易、投資、產業、收入、勞動等政策所構成的復雜環境)和政治變動(換屆、合并分裂、恐怖活動、騷亂、政變、內外戰等)對實現預期經濟活動結果和價值的影響,體現為企業戰略、財務或人員方面的損失。就伊拉克市場而言,中國石油企業在當地開展業務所面臨的主要政治風險主要包括以下3個方面:1)日益嚴重的“政治碎片化”現實使各派力量出于選舉和談判的目的大肆訴諸于恐怖暴力活動,使政治目的誘發的社會安全問題愈演愈烈;2)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選中均贏得一部分議會席位,雖不足以改變整體格局,但是擁有了與中央政府在石油收入分配和地方事務管理權方面討價還價的政治資本;3)當地社區組織和石油工人是國內政治和國家政策的終端承受者,也是伊拉克宗教、民族矛盾和家族部落政治斗爭的主要執行者。
1.社會安全形勢持續惡化此次全國議會大選不僅沒有解決伊拉克國內地區割裂與“政治碎片化”問題,也沒有緩和由來已久的宗教民族對立,反而使各派力量借助選舉機會制造了更多的糾紛和恐怖暴力活動,進一步暴露了國內矛盾,使社會安全形勢在大選前后持續惡化。根據聯合國數據,2013年伊拉克平民(包括警察)受恐怖襲擊死亡7818人,受傷17981人,傷亡人數已達到了2005年至2008年伊拉克內戰和美軍大規模打擊恐怖活動以來的最高峰。進入2014年,社會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第一季度伊拉克平民(包括警察)受恐怖襲擊死亡1666人,受傷3335人,軍隊死亡362人,受傷509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約55%。大選前后的4、5月份,伊拉克平民(包括警察)受恐怖襲擊死亡1213人,受傷2419人,軍隊死亡336人,受傷531人,上述數據還不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武裝和恐怖組織三方對峙的西部安巴爾省。目前,幾乎每個宗教民族派別和各種利益團體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恐怖暴力活動,有些是為了恐嚇民眾,破壞選舉,有些是為了宣傳某種思想和主張,有些純粹是出于報復。在美國軍事顧問和武器裝備的支持下,伊拉克軍隊和警察可以應對大規模的軍事沖突,但是對小規模的恐怖暴力活動無能為力,首都巴格達、北部尼尼微(Ninawa)、迪亞拉(Diyala)、薩拉丁(Salahiddin)和基爾庫克(Kirkuk)等省問題最為嚴重。6月,隨著恐怖組織迅速占領了北部地區的主要城市,恐怖分子也向中南部滲透,恐怖襲擊數量大幅增加,恐懼氛圍彌漫全國。目前,恐怖暴力活動的主要目標是伊拉克本國人,對外國人的威脅反而有所降低。除了破壞北部地區的輸油管道之外,近期也沒有出現針對石油行業的恐怖襲擊和暴力事件。除了庫爾德自治區之外,包括北部6個重要油田在內的全部油田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但是,隨著伊拉克大選后政治談判的進行和反恐戰爭的持續,各派力量為了顯示實力和制造緊張氣氛,會繼續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恐怖組織也有可能對油田進行侵擾,極有可能波及到油氣行業和外國人員。
2.各省本地干預不斷增強伊拉克國內地區割裂與“政治碎片化”問題給中國石油企業帶來的另一個潛在挑戰是油田所在的各省政府希望加強對油氣開發的控制和干預,迫使石油公司承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雙重行政負擔,并增加更多本地化內容,例如提高當地人比例、服務當地化等。在逐漸失去對庫爾德地區油氣開發控制權的同時,伊拉克中央政府還不斷面臨著地方各省的挑戰。2013年6月底,伊拉克全國議會通過了對2008年《各省權利法》的修正案,賦予各省在內政方面更多權力,特別是大幅提高了各省的油氣收入分成,從此前的每桶原油、每桶成品油和每150立方米天然氣的1美元分成提高到5美元。盡管該修正案仍須經中央政府公報(目前仍未)并經馬利基領導的管理委員會在2年內監督實施,但是這一重大政治變動明確說明了伊拉克中央與地方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地方各省不斷加強掌控油氣資源的愿望。目前伊拉克國內地方小黨林立的狀況給了各省政治力量更多的談判籌碼,迫使希望連任的馬利基在聯合政府的下一屆任期內做出更多的讓步。這將使投資于伊拉克的國際能源公司不僅需要應對中央政府,還需要花費更多精力與越來越強勢的地方省政府——這些省政府往往缺乏油氣開發專門知識,但更重視社區勞工等本地問題——打交道,大幅增加非生產性成本,影響開發效率。
3.社區勞工問題愈演愈烈社區勞工問題是中國石油企業在世界各地投資經營都會遇到的難題,在伊拉克,由于當地特殊的歷史傳統和政治現實,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2010年,艾哈代布油田(Ahdab)在開發過程中受到社區沖突的嚴重影響,2012年加拉夫油田(Gharaf)、2013年西古爾納2期(WestQurna-2)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2013年11月,為油魯邁拉油田服務的貝克休斯和斯倫貝謝兩家公司的外籍員工與當地員工、本地居民爆發沖突,失控的當地民眾襲擊了兩家公司營地,迫使BP、斯倫貝謝和貝克休斯三家公司減少駐派人員,部分地區暫時停產。此次沖突的直接原因是在阿舒拉節(11月4日)期間,國際能源公司所雇傭的安保公司的外籍員工(遜尼派埃及人)蓄意破壞當地員工和群眾(什葉派)的紀念活動,而沖突的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居民對石油開發利益分配的強烈不滿。盡管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都試圖從法律框架和行政審批方面加強對油氣行業的干預,但是由于伊拉克始終未能建立有效的國家權力鏈條和社會管理機制,世襲制家族部落政治始終在地方事務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從中央政府拿到合同的外國企業需要與各地區部落酋長協調解決具體問題。一方面石油公司提供的收入讓鄰近部落產生了糾紛,另一方面外國力量的突然出現讓閉塞的居民經歷了非常嚴重的觀念沖擊。許多農民抱怨石油開發用水導致農業用水不足,糧食減產;另一部分居民強烈抗議中央政府迫使他們將土地賣給石油公司;而更多的居民對石油開發并沒有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表示失望,對外籍員工占據工作機會且與當地居民關系惡劣尤其不滿。雖然石油開發能夠帶來巨額收入,但是并不能夠帶來充足的就業機會。對于一個失業率超過60%、1/4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國家來說,石油行業僅僅能夠雇傭2%的適齡勞動力②,無法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做出實質性幫助,卻造成了社區間和社區內部爭奪石油行業工作職位的緊張情緒。伊拉克現行政治模式難以給社區勞工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只能將負擔轉嫁給國際能源公司。面對不斷累積的社區勞工問題,中國石油企業必須深入社區詳細了解情況,借鑒其他公司的經驗和教訓,避免造成嚴重損失。
作者:查金才曾濤單位:中國石油集團長城鉆探工程有限公司
擴展閱讀
- 1國內媒介文化
- 2國內公債史
- 3國內購物旅游探究
- 4國內檢察權分析
- 5國內村民分化研究
- 6國內小額信貸監管分析
- 7國內武術文化研究綜述
- 8國內物流金融
- 9國內毒情形勢表述
- 10國內翻譯研究綜述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國內產業調研
- 2國內安全保衛論文
- 3國內外形勢論文
- 4國內對財務風險的研究
- 5國內博士論文
- 6國內市場營銷方案
- 7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研究
- 8國內工程造價管理現狀
- 9國內的公共藝術
- 10國內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