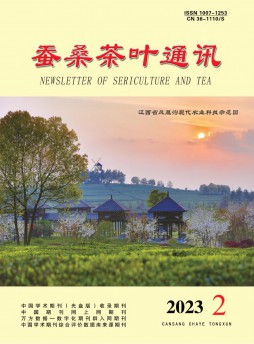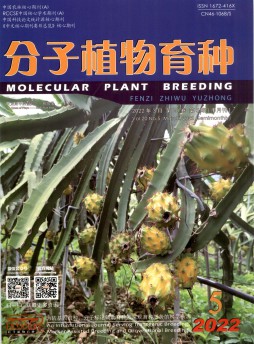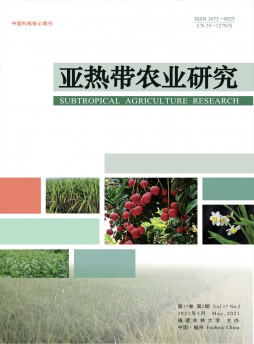茶文化的歷史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茶文化的歷史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中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江南(尤其是江蘇)是中國茶文化發(fā)源地之一。據(jù)古籍《廣陵耆老傳》記載,晉元帝(公元317―323年)時,廣陵(今江蘇揚(yáng)州)有位老婦人,每天提一壺茶去市上叫賣。茶香味濃,飲者甚多,但怪的是從早賣到晚,壺中茶始終不竭。她把茶錢全分給窮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認(rèn)為“有傷風(fēng)化”,將她逮捕入獄。夜深人靜時,老婦人攜茶具飛出獄窗,杳無蹤影。揭去這個故事的神話外衣,即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賣大碗茶”的文字記載。
唐代是飲茶、制茶大發(fā)展時期,商業(yè)空前繁榮。陸羽的《茶經(jīng)》進(jìn)一步推進(jìn)了茶業(yè)和茶文化的發(fā)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陸羽曾走遍江、浙、贛各地產(chǎn)茶區(qū),江南的南京棲霞區(qū)、句容茅山、丹陽、無錫、蘇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跡。《茶經(jīng)》―――這部中國第一部茶學(xué)經(jīng)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寫成的。至今,仍有蘇州虎丘“陸羽井”、南京棲霞山“試茶亭”等紀(jì)念“茶神”陸羽的遺跡。舊時江南開茶館的多供奉陸羽的瓷神像,當(dāng)生意不旺時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興隆。
江南歷代名茶輩出,至今蔚為煙酒茶糖大觀。產(chǎn)茶既盛,茶的買賣自然興旺。如浙江紹興、寧波、臺州一帶出產(chǎn)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稱“江南第一名茶”,銷路頗廣。茶最初于清代外銷時叫做“貢熙”,意為專門進(jìn)貢皇上康熙的。19世紀(jì)時,“貢熙”在倫敦市場上的售價不亞于珍寶。
明清徽幫茶商在江南占有相當(dāng)市場,不少茶行棧、茶樓應(yīng)為徽商所開(至今南京街頭上大部分茶行仍為安徽人經(jīng)營)。民國后,揚(yáng)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爭市場,稱鎮(zhèn)揚(yáng)幫、福建幫。江南茶商也遠(yuǎn)至外地行商,至遲在清代雍正年間,蘇州花茶就大量運銷東北、華北、西北市場。遼寧錦州市“天后宮”,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蘇州“關(guān)東莊”茶商捐款的記載。抗戰(zhàn)時南北交通阻隔,華北茶商無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葉產(chǎn)地,便云集南京,從皖南等地購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愛喝的花茶運回北方,可見“北方幫”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躍。
另外,江南及長江流域一帶還盛行“茶會”,這是包括許多種商品買賣在內(nèi)的交易活動。舊中國各行業(yè)、各商幫一般都有其約定的茶樓(館)作為這種活動場所。商人在“茶會”上飲茶時商談行市,其中上海的“茶會”最盛。(責(zé)編 張圣榮)
第2篇
同樣的還有陳中孚在《茶嶺》一詩中記載海南茶嶺茶樹的景象,“天柱峰頭撥曉云,靈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綠筍方知貴,雷發(fā)槍旗未足珍。”在燒水備具方面,例如宋東莞人趙必王象《和同社錢梅》寫有“呼童滌茶皿”,在《避地惠陽鼓峰用徐心遠(yuǎn)韶》寫有“風(fēng)供松葉暖茶灶”;又如南宋瓊州人白玉蟾在《清勝軒夜話》一詩中寫有“茶鐺無火召玉童”;又如南宋詩人楊萬里曾任廣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廣東提點刑獄,任職期間寫有飲茶的詩句,如在《二月一日雨寒五首》中有“茶甌火合對爐熏”;宋越州人李光被貶瓊州期間,寫有《即事十二首》,其中有“旋添活火待煎茶”;宋番禺人李昴英在《蒲澗山行宿景泰呈諸友人》中有“旋摘新芽撥澗泉”。宋東莞人張登辰在《茶磨》一詩中寫有“枯葉旋煎魚眼水”。在烹茶方面,如白玉蟾在《贈盧隱居》一詩中寫有“且自烹茶學(xué)玉川”;又如坡在惠州度過第三個春節(jié)時,他在《新年五首》中寫有“茶槍燒后有,麥浪水前空”,后被貶謫到儋州時,愛飲茶的他又寫了《汲江煎茶》一詩,詩中描述了坡在貶謫期間烹水飲茶,通過飲茶來掃除自己消極的情緒。李昴英在《碧霄》中有“茶烹石鼎抱茅燒”。
在茶湯方面,白玉蟾在《凝翠》中有“茗花涌白雪”,又在《題甕齋》有“茗花浮枕斗清芬”;宋舒州人朱翌被貶謫到韶州,在韶州居住十九年之久,他在《元日登城》一詩中寫有“春生茶碗結(jié)瓊花”,又在《喜雪》一詩中寫有“客從暖浮茶乳白”。在飲茶及體會方面,楊萬里在《食車螯》一詩中寫有“老子宿酲無解處,半杯羹后半甌茶”。白玉蟾在《送郭進(jìn)之》一詩中有“茶甘齒頰香”。宋南海人劉鎮(zhèn)在《念奴嬌》一詞中寫有“玉川風(fēng)味如許”。宋詩人唐庚謫居惠州時在《雜詩二十首》中寫有“南方禁太飽,茗碗直須寬”。宋李昴英在《滿江紅》一詞中寫有“卻坐間著得,煮茶桑苧”,把自己比作陸羽,可見李昴英非常愛好烹茶和飲茶。
一、以茶修身:佛道普遍的修行方式
茶很早就已經(jīng)傳到廣東并與宗教人士結(jié)緣,據(jù)《晉書》記載:“單道開,敦煌人也,……日服鎮(zhèn)守藥數(shù)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氣,時復(fù)飲茶蘇一二升而已,……(東晉穆帝)升平三年至京師,后至南海,入羅浮山。”可知,敦煌人單道開入羅浮山修行,亦將飲茶的方式帶到羅浮山。唐代僧人與道士好茶,因而促進(jìn)了茶風(fēng),許多名茶的烘焙亦是出自他們之手。五代至宋禪宗獨盛,禪僧對于茶的愛好一直延續(xù),并更盛于唐,不僅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供佛、贈香客等離不開茶,茶亦是寺廟重要日常經(jīng)濟(jì)來源,成為普遍種植的經(jīng)濟(jì)作物之一。此外,茶有不發(fā)的茶性,對于修行僧人的欲望亦有所抑制,有助于修行悟道。通過宋代廣東寺廟的僧人、道觀的道士在日常修行生活中與茶打交道的過程,可以清楚地展現(xiàn)茶與宗教人士生活的密切程度。從相關(guān)史料可知,宋代廣東寺廟和道觀香火興盛,發(fā)達(dá)的宗教文化將士人們津津樂道的品茶文化傳向田野,走向大眾,大大促進(jìn)了廣東茶文化的發(fā)展。茶與僧人的結(jié)緣由來已久,且一般來說,僧人飲茶之風(fēng)較道士來得興盛,從在僧家長大的陸羽撰寫的《茶經(jīng)》就可以知曉,料想陸羽應(yīng)是受其師傅智積禪師愛好飲茶的習(xí)慣而被感染。僧家向來種有茶葉,如宋韶州曲江人余靖在《游水南寺》寫有“雙剎聳浮云,層軒絕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余靖.武溪集(卷1).四庫全書集部)。據(jù)《景德傳燈錄》記載:韶州“則川和尚:師入茶園內(nèi)摘茶”(《景德傳燈錄》第3冊,卷8,《則川和尚》.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寫的是在韶州的白云寺、南華寺等寺院,向來有僧人開辟茶園種茶。在日常修行過程中,以茶供佛和飲茶成為僧人的必修課之一,如東莞人李春叟在《題云溪寺》寫有“杖屨前溪踏曉霜,僧茶那定攪饑腸”,又如在李昴英的《贈云峰演庵主》一詩中的“佛粘土壁煎茶供”。宋時,文人到訪南華寺,寺院都會設(shè)齋菜及茶水招待,或者與寺僧飲茶論道,如朱翌多次游訪南華寺,留有“人眾不烹茶”(《南華具素飯烹茶詩》)、“飲香休問水流西”(《丙寅十月游南華》)、“斗茶夸顧渚”(《南華五十韻》)等茶詩。寺院中,不僅飲茶成為日常生活必需,而且在日常師傅與弟子的對話中,處處充滿禪機(jī),有時于理論之際,亦常以茶示意,引起談話機(jī)鋒,并使對方了解所論的事,如《景德傳燈錄》記載:韶州“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吃茶,居士據(jù)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么道不得?師云:只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為什么卻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吃茶。居士云:阿兄吃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景德傳燈錄》第3冊,卷8,《松山和尚》.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又如,韶州白云祥和尚條:“韶州白云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問如何是和尚家風(fēng)。師曰:石橋那畔有遮邊無會么。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為什么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xiàn)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yáng)?師曰:今日未吃茶。”(《景德傳燈錄》第7冊,卷23,《白云祥和尚》.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在南方廣東,茶很早就與道教結(jié)緣。廣東的羅浮山、西樵山等歷來是古代道家修行的勝地,對在羅浮山修行的僧徒與道士們來說,飲茶有助于驅(qū)趕睡魔,何況宋代羅浮山有嶺南第一泉的卓錫泉水,更是好茶好水兩絕佳,在南宋廣東英德人鄭玠的《茶庵》一詩中如此寫道:“道人宴坐碧山阿,啄木敲門擬客過。吾境本無妖魅事,日長翻有睡為魔。少水仍將活火煎,茶經(jīng)妙處莫虛傳。陸顛所在閑題品,未試羅浮第一泉。”(《茶庵》二首詩,清宋廣業(yè)輯康熙五十六年刊《羅浮山志匯編》卷一九作逍遙子詩,第一首題為《茶庵》,第二首題為《羅浮茶》)南宋道士白玉蟾《張道士鹿堂》中寫有:“清夢繞羅浮,羽衣延我游。新茶尋淮舌,獨芋煮鴟頭”。廣東博羅人陳煥在《黃龍洞口道人送茶及筇竹杖》一詩中寫道:“露泣新芽九節(jié)筇,芽如雀舌節(jié)如龍。烹來習(xí)習(xí)風(fēng)生腋,拄上羅浮第一峰。”留元崇在游覽羅浮山慈濟(jì)庵時寫有“歸自星壇日未斜,草庵留住一杯茶。道人自點花如雪,云是新收白露芽”(《慈濟(jì)庵二首》)一詩。南漢時,有烏利道人云游到南海西樵山煉丹,開辟茶園種茶,據(jù)《南漢書•烏利道人傳》:“烏利道人,不知何許人,時稱之曰烏利游方。至西樵山。耽噴玉巖之勝,構(gòu)屋棲焉。辟谷食,能用禁咒。于所居側(cè)辟園,遍植茶株。晚喜燒煉。巖下有丹井二,泉水赤、白各一。丹成,遂羽化”。
二、以茶待客:民間普適的禮俗習(xí)慣
茶發(fā)揮著以茶待客的功能,甚至在最南方的瓊州,都有“客至但請坐飲茶”的民間禮俗,可知茶已經(jīng)逐漸深入和普及到廣東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李昴英在《后峒月溪寺》一詩中寫有“茗苦苛留客”。據(jù)宋朱彧《萍洲可談》記載:“鄒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貶新州。媒孽者久猶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廣東提刑鐘正甫,就新州鞠問。志完事不下司。是時鐘攜家在廣州,觀上元燈,得旨即行;漕帥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傳出關(guān)矣。眾愕然。鐘馳至新,將志完拘之浴室。適泰陵遺詔至,鐘號泣啟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聞使者哭泣,罔測其事,意甚隕獲,良久,鐘遣介傳語,止言為國恤,不及獻(xiàn)茶,且請歸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后東坡聞之,戲云:‘此茶不煩見示’。”
第3篇
關(guān)鍵詞:茶 茶文化 發(fā)展態(tài)勢
在我國,茶的應(yīng)用可追溯到神農(nóng)氏時期――唐代陸羽的《茶經(jīng)》有云:“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氏。”,然而茶的發(fā)現(xiàn)和應(yīng)用不能等同于茶文化的產(chǎn)生。“茶文化”的歷史始于被人們飲用之后超出其自然效應(yīng)的范圍,逐漸演變出一種社會功用,并升華成一種精神文化享受之后,正式萌芽于兩晉南北朝時期。
1、兩晉南北朝時期――茶文化的萌芽
茶開始發(fā)揮其社會功用并以一種文化的面貌出現(xiàn),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然而,論其緣起,可追溯至漢代。
秦漢以前處于發(fā)現(xiàn)和利用茶的階段。秦漢時期,茶作為風(fēng)靡大江南北的重要商品而被廣泛傳播和飲用。漢代茶葉貿(mào)易的興盛將茶飲推向千家萬戶,而將茶提升為一種社會功用并以文化的角色出現(xiàn),主要是漢代文人的功勞。
飲茶自古為文人所好,漢代是我國第一個封建盛世,國力強(qiáng)盛,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使得儒學(xué)、經(jīng)學(xué)等各流派思想文化展現(xiàn)空前繁榮,各階層杰出的思想家、史學(xué)家、賦家與詞人不斷涌現(xiàn)。然而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大一統(tǒng)的皇權(quán)專制制度之下,茶開始與儒家思想有了關(guān)聯(lián),并成為文人追求“平等、仁愛”的精神知音。隨著文人飲茶之風(fēng)的興起,飲茶亦因文人的氣質(zhì)而逐漸變得更富有文化韻味,這也便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茶文化的萌芽做好了鋪墊。
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腐敗,社會風(fēng)氣奢糜。儒家提倡“儉”、“廉”以正身養(yǎng)性,而茶本身的清苦、質(zhì)樸、自然的特質(zhì)剛好與“儉”、“廉”的品德相一致,因此,有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以茶養(yǎng)廉”以對抗奢糜之風(fēng)。此時,飲茶已逐漸向一種提升人情操和精神境界的文化演變。以茶倡廉的做法開始受廉潔之士的喜愛。東晉陸納以茶待客、桓溫以茶代酒,是朝廷官員以茶養(yǎng)廉的典型代表;南朝齊武帝遺詔以茶祭祀并要求“天下貴賤,咸等此制”的故事,正是帝王以茶表示簡樸的例子。自此,“以茶代酒”、“以茶養(yǎng)廉”一直是我們發(fā)揚(yáng)廉潔、簡樸精神的優(yōu)良作風(fēng)。
此外,南北朝時期,文化興盛,茶業(yè)興起,儒家、佛家、道家、清談家與玄學(xué)家之間的思想交融碰撞頻繁,然而各家皆少不了茶。隨著玄學(xué)和道教的興起,茶甚至已作為一種社會功用被廣泛引入宗教領(lǐng)域。南朝劉敬叔的《異苑》中曾提到剡縣陳務(wù)妻子以茶祭鬼魂的故事;陶弘景的《雜錄》中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寫的便是關(guān)于神仙飲茶以修養(yǎng)的故事。隨著茶與文化思想領(lǐng)域的關(guān)系日漸密切,茶文化亦隨之初現(xiàn)端倪。
2、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全盛時期,國家呈現(xiàn)空前盛世,經(jīng)濟(jì)文化無比繁榮,國泰民安。我國茶業(yè)大興,飲茶習(xí)俗傳遍大江南北,舉國皆飲。這為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
其次,茶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還與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有關(guān)。
唐代大興佛教,禪宗主張靜心、苦修和頓悟,茶之清苦于佛家坐禪悟道時產(chǎn)生的“止睡和靜氣凝神”等積極作用使得僧人飲茶成風(fēng)。茶與禪宗精神聯(lián)系日趨緊密,禪茶文化興起。唐代李咸用的《謝僧寄茶》中以“空門少年初志堅,摘芳為藥除睡眼”描述了“以茶止睡”的功效;唐代封演的《封氏見聞記》卷六有記載:“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xué)禪,務(wù)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zhuǎn)向仿效,遂成風(fēng)俗。”由此可見,唐玄宗時茶已被佛家用于傳教,且茶與禪之間關(guān)系密切。
唐代“茶圣”陸羽亦出生佛門,他將飲茶視為一種藝術(shù)行為與過程,創(chuàng)造了茶藝,并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學(xué)和茶文化專注《茶經(jīng)》。《茶經(jīng)》是茶文化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將“儒、釋、道”三教思想滲透于茶事的制作過程之中,融物質(zhì)與精神為一體,以內(nèi)容與形式結(jié)合的手法詮釋著茶文化的真諦。陸羽好友、著名茶人、詩僧皎然不僅以“九月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傳遞了自己對茶的情感,并道出了茶人超脫的精神品格以及茶與禪境之間的相通。此詩也是對陸羽《茶經(jīng)》思想的詮釋。
陸羽在《茶經(jīng)》將茶事提升至精神層面,對茶人的品格和情操進(jìn)行了定位,并提出將飲茶作為提升人精神品德和個人修養(yǎng)的手段,這為后世茶文化的發(fā)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和研究依據(jù)(如圖1)。
圖1《陸羽煮茗圖》
此外,每一階段茶文化的發(fā)展皆離不開文人的推動作用,唐代亦不例外。
唐代科舉制度嚴(yán)格,詩風(fēng)鼎盛,一來飲茶可以止睡凝神,二來以茶代酒可提神助興、醒文思、促靈感。文人雅士的好茶,自然而然加深了茶與自然山水、文學(xué)藝術(shù)之間的聯(lián)系,也便促進(jìn)了茶的藝術(shù)和文化性質(zhì)。唐《鳳翔退耕傳》中關(guān)于會試奉茶以提神的記載:“元和時,館客湯飲待學(xué)士者,煎麒麟草。” (據(jù)史料記載,詩中“麒麟草”為道家對“茶”的稱謂);唐代著名詩人盧仝的《七碗茶詩》以“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來形容飲茶助興的神奇功效。唐末劉貞亮在《茶十德》文中將茶文化總結(jié)為“茶十德”,即:“以茶散郁氣;以茶驅(qū)睡氣;以茶養(yǎng)生氣;以茶除病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yǎng)身體;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亦是對茶的文化功用的總結(jié)。
隨著不斷被挖掘著更深的文化內(nèi)涵,茶文化已被正式烙上民族文化的印記,被提升為一門文化學(xué)。
3、宋代――茶文化的成熟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承上啟下的轉(zhuǎn)折時期。它于傳承唐代經(jīng)濟(jì)文化的基礎(chǔ)上開拓演進(jìn),形成了足以與唐代文化并肩屹立的宋文化。繼唐之后,不論是政治、科學(xué)、思想還是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 都閃耀出了奪目的光彩,宋代文化達(dá)到了登峰造極的狀態(tài)。這也是后世常將唐宋文化并稱的緣由。清代蔣士銓曾對宋文化評價道: “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后,開辟真難為。”;近代歷史學(xué)家陳寅恪亦于《鄧廣銘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jìn),造極于趙宋之世。”。
唐朝茶文化是由文人和僧侶引領(lǐng)發(fā)展的時代,在宋代則不然。在經(jīng)濟(jì)文化大蓬勃發(fā)展的推動下,中國茶文化得到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不斷成熟,制茶技藝亦更加精湛。
宋代,歷代皇帝、上流社會王侯將相、達(dá)官貴人嗜茶成風(fēng),宮廷飲茶成為新的風(fēng)尚。每有宮廷會試或宴會,以茶宴客(如圖2――宋徽宗的《文會圖》所示);皇帝與群臣之間亦常以茶饋贈以示恩寵和友好。因此,宮廷飲茶成為宋代茶文化發(fā)展的最大推動力。
圖2《文會圖》
宋徽宗趙佶甚嗜茶,并著有《大觀茶論》,其以“陰陽相濟(jì),則茶之滋長得其宜”、“谷粟之于肌,絲之于寒,雖庸人孺子皆知,常需而日用,不以歲時之遑遽而可以興廢也。至若茶之為物,善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dǎo)和,則非庸人孺子之可得而知矣。沖淡簡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而好尚矣。”等段落分別論述了茶的知識以及茶與人的精神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大觀茶論》中所談及的“清”、“和”、“淡”、“簡”、“靜”不僅體現(xiàn)了宋徽宗本人的茶道思想,也是中國茶道精神內(nèi)涵的最早概括。
除此以外,民間“斗茶”活動的盛行也對茶文化的發(fā)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斗茶”,又為“茗戰(zhàn)”,是我國古代以競賽的形式集體品評茶品質(zhì)優(yōu)劣的一種活動,即人們常說的“品茗大會”(如圖3)。宋人唐庚在《斗茶記》中關(guān)于“斗茶”的記載:“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斗茶于寄傲齋,予為取龍?zhí)了胫谄淦罚阅碁樯希炒沃!保凰位兆诘摹洞笥^茶論》亦有相關(guān)記載:“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竟為閑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策之精,爭鑒別裁之。”由此可見,斗茶多為文人志士以作消遣或是閑士斗富的手段。
圖3《群仙集祝圖》斗茶會
茶不僅能滿足人們的物質(zhì)享受,更能滿足人的思想與精神需求。茶在宮廷內(nèi)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民間“斗茶”活動的開展,使得茶文化不僅演變?yōu)閷m廷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了民間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門特色。自此,舉國內(nèi)外的產(chǎn)茶、制茶、烹茶技藝亦有了極大提升,茶文化得到了跨步發(fā)展。
由此可見,自宋代開始,茶文化的性質(zhì)開始逐漸從清雅高尚向世俗轉(zhuǎn)變。
4、元明清時期――茶文化曲折發(fā)展
宋代末年,受社會官僚的奢靡之風(fēng)的影響,以團(tuán)茶為主流。因團(tuán)茶多追求外表的精致與奢華,茶風(fēng)便日漸脫離了茶文化追求樸實、自然意境的初衷,茶文化的精髓呈現(xiàn)敗落趨勢。
至元代,豪放粗狂的蒙古族統(tǒng)一中原,北民南遷,南方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皆受到極大沖擊。我國傳統(tǒng)茶文化思想更是受到影響,幾乎呈現(xiàn)中斷的狀態(tài)。直至忽必烈時期,因其喜好并熱衷學(xué)習(xí)中原文化,飲茶文化才得以逐漸復(fù)蘇。然而宋朝末年流傳的“團(tuán)茶”制作工藝精細(xì)而繁瑣,被蒙古族人視為繁文縟節(jié)因而團(tuán)茶地位亦逐漸被散茶替代。隨著散茶的發(fā)展,飲茶文化逐漸走向民間。
明朝時期,制茶技藝空前發(fā)展。朱元璋出生草寇,重視民間疾苦,主張與民生息,而團(tuán)茶生產(chǎn)過程過度精細(xì)會增加茶農(nóng)的負(fù)擔(dān),于是下令廢除了團(tuán)茶進(jìn)貢制度。朝廷都不好團(tuán)茶了,民間自然就不會大量生產(chǎn),這也就促進(jìn)了散茶的大力發(fā)展,團(tuán)茶的再度被棄使得團(tuán)茶技藝開始隕落。明初的飽學(xué)之士多以茶雅志,如著名的“吳中四杰”,四人琴棋書畫無不精通的才子卻都不得志,皆好茶。唐寅的《事茗圖》、《烹茶畫卷》、《琴士圖卷》等都是其以茶雅志的傳世茶畫。
唐寅的《事茗圖》
明末清初,茶文化發(fā)展鼎盛,逐漸由民間飲茶文化演變出茶俗與茶禮。隨著封建科舉制度的推行和朝堂的腐敗,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對現(xiàn)實失去信心和希望,喜歡飲茶以明志,市民泡茶館的嗜好使得茶館演變?yōu)楦餍懈鳂I(yè)好茶之人的聚集地,茶館文化是清代社會形勢的真實寫照與濃縮,茶館文化開始發(fā)展至。然而,此時的茶文化僅限于閑玩且日漸市民化,原先茶人飲茶的高潔情操與理論精髓亦逐漸被拋棄。
清朝末年,國家飽受帝國主義摧殘,社會動蕩不安,百姓民不聊生。茶文化從文人引領(lǐng)的時代徹底地結(jié)束,飲茶主體由文人向平民轉(zhuǎn)化。在此時期,中國傳統(tǒng)的茶道精神和制茶技藝不斷衰退,茶文化精髓自此隕落。然而,正因如此,也便有了民間“早晨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著名說法,我國茶文化開始正式走向千家萬戶。隨著茶與人們生活的日趨緊密,茶文化的主要精神開始被茶俗文化替代。飲茶、賞戲、會友等“茶館文化”大興。
由此可見,元明清時期,我國茶文化總體呈現(xiàn)曲折發(fā)展態(tài)勢,茶文化的性質(zhì)由文人茶向百姓茶演變、特征由“雅”轉(zhuǎn)變?yōu)椤八住薄kS著清末國家的衰敗,傳統(tǒng)茶文化精髓亦隨之日漸纖弱。
參考文獻(xiàn):
[1]孫洪升.唐宋茶業(yè)經(jīng)濟(jì)[M].北京: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