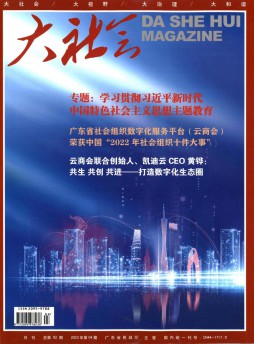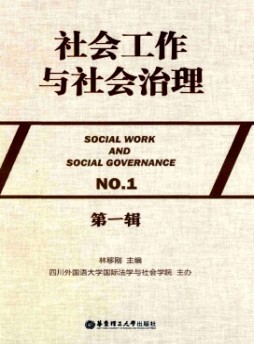社會結構與民眾訴訟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結構與民眾訴訟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張青單位:云南大學法學院
人民法庭所處的社會場域
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生活棲息于自身的世界即社會空間之中。這一空間由人們的互動所產生,它具有多維的位置和方向,而且每種社會生活的運作形式均可以由其所處的社會空間的形狀即社會結構予以預測及解釋。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人民法庭的日常運作亦必然在一定的社會空間中展開,欲理解鄉村司法的運作邏輯及訴訟構造,并對其作出適當的評價,則不可不對人民法庭所處的社會空間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當然這里對社會場域的描述只是一種服務于目前分析進路的有選擇地“拼貼”,并不意味著對整個場景和關系的完整呈現。
(一)錦鎮人民法庭的轄區
錦鎮人民法庭地處武陵山區東北部,下轄石溪和錦鄉兩個鄉鎮,89個行政村,約9.5萬人。由于地處武陵山區腹地,其轄區地形十分復雜,盡管石溪與錦鄉互相接壤,然兩地地理環境迥異。人民法庭所在地的錦鄉由于有一條河流縱貫東西,其轄區多為河谷臺地,地勢較為平緩,錦鎮便坐落于河谷平地,兩岸邊緣則多懸崖峭壁。崖頂為高山地區,錦鎮的轄區一直延伸到河流南岸崖頂的高山地區,河流北岸崖頂則為與之比鄰的石溪鄉所轄,境內山巒重疊起伏,山丘、平壩、盆地、槽坦縱橫交錯。復雜的地理環境加上鄉民居住分散增加了鄉民的訴訟成本和出行的困難。為了避免多次往返造成的交通、成本等方面的困難,許多卷入訴訟的鄉民在法庭第一次開庭時基本上都會接受法庭的調解,而法庭也樂于利用這一重要籌碼向當事人施壓,迫使其接受調解。對當事人而言不利的交通、成本等因素,卻成為支撐法庭行動策略和技術的有利資源。
隨著滬蓉高速和宜萬鐵路相繼通車,旅游業及相關產業成為當地政府重點扶持的項目。為了加快發展步伐,當地不少政府官員片面追求企業數量,而疏于對企業質量的管理。許多企業根本不具備法定的注冊資本,成為法官所謂的“皮包公司”即空殼公司。于是征地、補償糾紛以及涉及鄉鎮企業的債務糾紛也隨之增多。對于這兩類糾紛,法庭法官均感頭痛,因為它們均涉及地方政府“發展工作”的重點,如果依律裁判勢必得罪鎮政府,執行也比較困難。而且這類糾紛往往涉及面廣,矛盾尖銳,稍有不慎便可能將矛盾的焦點引向法庭。因此人民法庭在接到此類案件時基本上不會受理,而是運用“立案政治學”將當事人打發出去,甚至建議當事人去上訪,找政府。
(二)錦鎮人民法庭與鄉政府及法律服務所的關系
盡管從法律角度看,人民法庭屬于縣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隸屬于縣人民法院。其與鄉政府既非隸屬關系,亦非平行關系。然而在實踐中,鄉鎮人民法庭事實上處于鄉政府的領導之下,人民法庭在案件辦理中不僅要考慮法律問題,更要考慮政府的政治目標、形象,維護政府的權威及地方穩定。不惟如此,法庭還經常應鄉政府的要求參與一些行政性事務。據當地人民法庭副庭長介紹,自2005年以后,法庭很少參與明顯的行政事務,但是對于鄉政府處理的一些復雜的糾紛,法庭庭長還是會經常被要求參與調解。鄉政府還從包括人民法庭在內的鄉鎮各單位抽調人員組成了一個綜治維穩中心,負責處理一些棘手的行政調解糾紛。在此,人民法庭實際上已經被整合到黨和政府綜合治理的實踐之中,并且在這種總體實踐中處于從屬地位。其實縣法院也處于相似的位置。
①在調研期間,按照法庭日程,本來有一個財產案件需要強制執行,可是并未如期執行,因為那段時間正是縣、鄉兩級政府換屆選舉期間,法庭接到縣法院領導通知,為了保證選舉期間的穩定,暫緩強制執行。即使在平時,法庭對強制措施的適用也經過層層審批,審批的標準不是法律,而是是否利于社會“穩定”。這使得法庭在鄉民面前顯得比較“軟”,有鄉民幾次當著庭長的面這樣評價法庭。也正是因為“軟”,人民法庭在許多情況下必須依賴鄉政府的協助。庭長多次強調,在地方工作中,離開政府什么事都做不成,尤其是遇到當事人鬧事時,法庭根本無法獨自應付。法庭自身權威不足,造成對政府權力的依賴,而這種依賴又強化了法庭的從屬地位,弱化了鄉民對于法庭作為一個中立機關的信任,于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錦鄉與石溪鄉只有一家法律服務所,辦公地點就在錦鎮人民法庭大院旁邊,其了轄區內90%以上的案件。法官和法律服務所的人員非常熟悉,平時經常互相往來。由于法律服務所不屬于政府部門,而且作為一個主要面向轄區內的糾紛提供法律服務的單位,其在業務活動以及案源等方面要受制于人民法庭。法律服務所的工作人員為了獲取更多的案源,順利開展業務活動,不得不與法庭搞好關系。法庭的一個法官曾經提到一名法律服務所的人員由于在訴訟過程中過于較真,使法官的調解工作很難進行,引起了法庭所有法官的不滿,最終被迫離開本縣,到鄰縣一個法律服務所執業。
①這說明如果拋開個人交情,人民法庭與法律服務所是一種典型的縱向支配關系,其中法官居于主導地位,法律服務所必須依附于人民法庭。在這種關系結構中,一旦當事人的訴求與法庭意愿相左,人很難為當事人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相反,他們會默契地轉向法庭一邊。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筆者在數次庭審旁聽中,經常可以看見法律服務人員與法官互相配合,給當事人做工作。在此過程中,法官偶爾還會請人幫忙去辦公室取文件、拿印泥等,此時人的角色似乎又成了法庭的工作人員。
(三)錦鎮人民法庭與鄉民的“距離”
人民法庭的法官在談到工作中面臨的困難時,一句口頭禪便是“我們不比縣法院”。細究起來,這句話的背后透射出由于與當事人的“距離”過近而給法庭帶來的種種壓力。這里的距離并非時空上的間隔,而是包含了更為廣泛的意義,在此不僅表示物理距離,也包括心理距離。在人民法庭的法官看來,直接扎根于鄉村的法庭與縣法院相比,同鄉民的“距離”太近了,以至于法庭工作帶來沉重壓力。首先,人民法庭設置在鄉村集鎮上,相對于到縣城法院,鄉民很容易就能到達;其次,人民法庭的法官基本上都是本地人,由于人民法庭的法官流動性很小,他們基本上處于主要由鄉民組成的社交網絡中,如果對法官的判決不滿意,當事人很容易找法官鬧,甚至去法官家里耍潑;第三,雖然法庭剛剛搬進了新修的辦公大樓,周圍也設置了圍墻、大門以及監控設施,但是由于法庭人手有限(一個庭長,一個副庭長,一個審判員,一個書記員,還有一個協警,但是不常在法庭),而且法官所處的環境及其社交圈子的鄉土性,使得法庭的大門不可能像縣法院那樣嚴加看守,只要鄉民愿意,很容易就能進入;最后,前述各種因素互相交織,加之傳統心理的影響,鄉民對“城里人”都有一種莫名的敬畏,居住在城里的法官更是“城里的干部”,而派出法庭的法官更本沒有這種優勢,無論出于客觀條件還是工作需要,他們不僅不能像縣法院法官那樣與鄉民保持距離,相反他們必須想辦法與鄉民“拉近”距離。與鄉民長期交織在一起,很容易就失去距離帶來的神秘感,鄉民們漸漸地從心理上將法庭的法官置于一個較近的位置。古語說“近則不遜”,適當的距離則可以樹立一定的威信,這對于一個精于世故的中國人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西方法社會學學者通過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第三方的權威性與其同對立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關系、文化、優勢地位)成正比。當鄉民們不再把法官視為高高在上的擁有權威的主體時,他們在法官面前便少了顧忌,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耍潑鬧事。
人民法庭與當事人的“近距離”,一方面為法庭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同時也為法庭工帶來了諸多壓力,面對當事人的無理取鬧,法庭往往無計可施。為了防止出現類似的尷尬,法庭總結的經驗就是一般不直接作出判決,盡量以調解的方式結案,對于那些無法達成調解而執行又有難度的案件則采用“立案政治學”將其排除在法庭之外。
(四)錦鎮人民法庭的內部考核管理方式
根據縣法院出臺的2011年案件質量評估指標顯示,縣法院主要依據“三項指標”對人民法庭進行考核,一是質量指標,二是效率指標,三是效果指標。在質量指標中,上訴改判和發回重審率以及再審改判和發回重審率被要求控制在1%以下;效率指標中,對簡易程序的使用率要達到75%以上,正常期限執結率要達到99.5%以上;在效果指標中,對上訴率要求控制在20%以下,申訴率要求在0.3%以下,信訪投訴率在0.5%以下,實際執行率以及執行到位率要達90%以上,調解率達50%以上。
①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三項指標中對于法庭審理案件的上訴、再審和執行的考核要求是極其嚴格的。且不說當事人上訴后的處理結果如何,單就當事人的上訴本身即作為縣法院對法庭進行否定評價的標準,而法院內部的錯案追究制雖屢遭批判,然實踐中仍被繼續推行。在錦鎮人民法庭,無論是二審或者再審,一旦案件被發回重審或者被改判,該案即被視為“錯案”,在年終考評上就會被扣分。而對執行率的考核,更成為法官頭疼的心病。由于該縣實行的是人民法庭自審自執,原則上法庭對于自己審理的案件要自己執行。雖然特殊情況可以請求執行庭協助,但是法庭很少申請協助。因為這不僅關系到法庭的面子,更重要的是頻繁請求協助會讓法院領導認為法庭無能,無形中會影響到法庭的考評以及庭長的工作業績。為了順利通過考評,法庭還將自審自執原則進一步落實到了承辦法官的個人頭上。然而由于前述諸般原因,如果法庭真正對每個案件進行強制執行,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最終的結果是,法庭從立案之初到案件最終處理全過程,都會首先考慮執行問題,并采取相應的策略,“立案政治學”會再次得到運用,在處理過程中,為了避免強制執行以及當事人上訴、申訴,法庭會千方百計地以調解方式結案。
法庭的經費來源也是法庭熱衷調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錦鎮人民法庭所在的縣法院,法官的月基本工資大約2000元左右,如果在鄉鎮人民法庭綜合起來一個月可以拿到4000元左右,有些“工作有方”的法庭拿得甚至更多。以錦鎮法庭為例,縣法院會按照法庭處理的案件數量劃撥辦案經費,一般是每辦結一件230元,如果是以調解結案,則另計50元,也就是調解結案的每件是280元。此外,縣法院還會按照法庭的人數給每人每年8000元的辦案補貼。因此,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法庭也樂于調解。
鄉村司法與案件的社會結構
前面的分析展示了錦鎮人民法庭所處的社會結構,為解釋并預測法官以及法律服務人員在鄉村司法活動中的行動邏輯提供了條件,但尚不足以細致全面地展示鄉村司法的運作及其構造。由于涉及糾紛的當事人雙方各自的社會地位、背景、收入、環境、文化及性格等千差萬別,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力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大量的經驗研究也表明,許多在法律技術特征上相同的案件處理結果卻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這說明案件本身所具有的社會結構也制約著司法程序的運作方式和形態。正因為如此,布萊克認為“每一個案件都是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的復雜結構……案件的社會結構可以預測和解釋案件的處理方法。”
在錦鎮的司法活動中,糾紛當事人雙方的身份、糾紛本身的性質、復雜程度等因素對其是否被法庭作為案件受理有著直接的影響。如果糾紛一方當事人涉及政府利益或者政府的政治目標,或者案件涉及面廣,矛盾尖銳,如山林、土地糾紛,以及其它可能難以執行的案件,法庭一般會拒絕受理。對于少數受理了的此類案件,也是事先征求縣法院的意見后才立案。因此,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臺帳上有65%以上的案件都是離婚案件,還有約30%左右的案件為贍養、解除同居關系及普通借貸糾紛,涉及政府、企業以及山林、土地的糾紛極少,不到2%。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類糾紛就很少發生,事實上這類糾紛在最近幾年頻繁發生,就在筆者調研期間,就有七件類似的糾紛被提交到法庭,其中除了一件在請示縣法院后予以立案以外,其它的均被法庭以各種策略排除在法庭門外。
在排除了當事人雙方勢力明顯懸殊的棘手案件之后,所剩的便主要是當事人雙方基本上勢均力敵的普通民間糾紛。但是所謂的勢均力敵也只是表面上的,或者說宏觀層面的。盡管參與糾紛的當事人大多都是農民,但是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法庭審理案件的方式、策略和結果。如果一方當事人背后的支持團體實力雄厚、背景強硬到可能會影響法官本人的利益時,在法庭與社會“距離”很近,又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程序保障法官中立地位的情況下,法庭必然會向強勢一方傾斜。但是法官自己也承認,這類極端的案件在鄉鎮上占的比重較小,大多數都是普通村民間的糾紛。然而通過一個多月的參與觀察顯示,即使是最普通的村民間的糾紛,依然存在力量對比上的差異。這里的力量是廣義上的力量,只要是可以影響法庭裁判的因素都可以歸結為一方當事人的“力量”。例如有的當事人比較明事理,容易被說服,而有的當事人則比較蠻橫無理,稍有不如意便抵賴撒潑,這時候,經驗老道的法官可能就會將工作的中心轉向明事理、息事寧人的一方,而不會無益地對蠻橫之人做工作。毫無疑問在這里力量的強弱不是當事人后面的財富以及地位,而是看誰最蠻橫,最能耍潑。在鄉村社會中,只要一方當事人沒有前面所說的那種極度優勢的情形,那么耍潑、抵賴是非常有效的力量,法官為了保證調解成功并執行到位,不得不遷就耍潑一方,而迫使另一方妥協。此外,性格頑固一方當事人在法庭更容易取得勝利,家里一無所有的當事人也占有較大優勢。而且這種力量對比是流動的,一方當事人在一個階段可能比較容易說服,在下一階段可能變得蠻橫,這時候力量對比關系可能倒過來,因此法官為了獲得調解的成功,有時候不得不反復調整調解方案和做工作的對象。這使得法庭看起來有點像墻頭之草,哪邊的風力強,便倒向哪邊。
當事人之間的力量對比與訴訟構造
人民法庭所處的社會結構,及其處理的案件結構互相作用,共同塑造了其運作的模式,使得鄉村司法呈現出獨特的法庭構造。人民法庭所處的社會場域決定了其受理糾紛的主要類型,即以離婚案件為主的普通民間糾紛,以調解為主的案件處理方式,以及與案件審理的特定利益關系。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的鄉村司法實際是法庭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以離婚案件為主的普通民間糾紛的司法活動。而法庭同案件處理方式、結果間特殊的利益關系,為法庭在司法過程中搖擺的立場埋下了伏筆。①鄉村社會案件的結構尤其是當事人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官在調解過程中的位置和方向。法官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會選擇最有利的位置進行調解。因為法律服務人員基本上完全受制于法庭,故其在法庭中也會選擇對自己利益最優的位置,即緊跟法官的腳步,迎合法官的思維對當事人進行說服。由此,可以得出如圖3-1所示的法庭結構:在圖3-1中,豎軸與橫軸垂直相交于圓心O,橫軸與圓形成B、C兩個交點,分別代表法庭審理中的當事人雙方的位置,其中C特指力量對比中強勢一方當事人,豎軸與上半圓形成交點A,代表法官在庭審中的理想位置。從圖中可以發現,A、B、C三方實際構成一個等腰三角形,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與當事人B、C保持等距離。這實際是現代司法活動的理想構造。在鄉村司法過程中,由于法官與案件處理存在著固有的利益關系,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法官的位置會隨著當事人雙方的力量對比而發生位移。如圖所示,在開庭之初,當事人雙方力量對比尚未明顯時,法官基本上能夠保持在中立的位置,隨著訴訟的不斷推進,體現當事人之間力量的信息不斷展現于法庭,法官為了追求調解的成功,說服工作的重點將會轉向弱勢當事人一方。(因為要想得到強勢一方當事人的讓步顯然更加困難)這時法官的位置就會向強勢一方當事人C的方向移動,到達A'的位置。法官在位移的時候會有一個合理的預計,一是法律的底線,其次是對方當事人以及社會公眾的心理承受底線。一旦突破這個底線,法官的位置就比較危險,因為這很容易被上級追究法律責任。
①所以除非出現力量極端失衡的情形(如一方當事人涉及政府,而政府在這方面立場強硬),法官的位置只會隨著當事人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無限接近C,但不會與C重合。因為與C重合意味著法官完全放棄了中立的裁判者的立場,而加入到當事人一方,這是與法官更大的利益相沖突的。在此有必要強調的是,法官在訴訟中的位置是法官在諸多限制性條件下進行利益權衡的結果,這個行為本身并不足以作為評判法官個人品行、操守的標準。有些法官在開完庭后很憤怒,因為明明知道那個耍潑抵賴的當事人理虧,事實也證明其理虧,但是卻無能為力。
理想狀態下,人與其所的當事人近似地處于同一位置,即B、C所在的位置。在現代法制健全的國家,律師的利益主要與其提供服務的質量有關,然而在錦鎮的司法環境中,法律服務人員的利益卻與法庭和法官緊密相關。因此在庭審中,無論是原告的人還是被告的人,只要他們來自法律服務所(不僅限于本鄉鎮,由于法庭庭長流動性很強,只要是本縣范圍內的法律服務所人員與各法庭庭長都較為熟悉),他們便會默契地配合法官的調解。法官認定的事實、確定的解決方案、責任劃分等,人基本上不會提出異議。而且只要有利于實現法官的處理意見,人一般也不會就對方當事人或者人的言行提出抗辯。
換句話說,在庭審中,人的立場不是在其的當事人一方,而是“貼心”地站在法官的立場。因此,人的行動也會與法官保持“同步共振”,人的位置會隨時同法官保持對稱。如圖所示,弱勢一方的人會跟隨法官的位移而從B點移動到B'處,強勢一方人也不會完全站在當事人立場,而是采取同樣的策略,從C點移動到C',與法官的位置保持大致的對稱。
圖3-1表明,在錦鎮的司法活動中,當事人聘請的法律服務人員事實上更多地是在為法官的調解活動服務,他們在法庭中的位置和立場都以法官的位置和立場為參照,類似于法官位置上的一個投影;而法官的立場和位置并未固定在等腰三角形的頂點,而是隨著當事人之間的力量對比左右移動,最終定格在強勢當事人一方。因此法庭中的弱者最終成為“眾矢之的”,所有的勸解、批評、教導、威脅等集中向其襲來。法律服務人員并未增強當事人的力量,相反可能起到削弱當事人力量的作用。
②有學者曾經以傘形結構描述我國刑事司法的構造,而鄉村司法則更像一把倒置的雨傘,其中長長的傘柄象征著強勢一方當事人,周圍的傘骨及其組成的傘面則象征著由法官和人組成的力量之網,它們共同指向代表弱勢一方當事人的傘尖。模型中假定了雙方當事人都以法律服務人員做人,但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每個當事人都會聘請法律服務人員,而這種情況下仍然可以該模型予以解釋。這個模型的核心在于法官與法律服務人員之間的支配關系,如果當事人聘請的是與法官陌生的律師,或者與當事人親密的親友等作為人,則不太可能處處站在法官的立場,這就意味著法官的調解難度會加大。這也是人民法庭為什么更希望法律服務人員的真正原因。此外,在法庭作出判決的極少情況下,該模型同樣具有解釋力,因為法官即使以判決結案,其還是會考慮到執行、上訴、申訴等問題,進而考慮當事人對判決的態度,因此前述的力量對比依然會發生作用。
鄉村人民法庭司法:局限性與可能性
鄉村司法呈現出的倒立的傘狀結構,凸顯了鄉村司法中弱者愈弱、強者愈強的現狀,其結果是使得人民法庭的司法活動陷入“強制不行、合意不純”的尷尬局面,并進而引起鄉村司法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即人民法庭是否滿足了人們對懲強扶弱的傳統正義的需求,是否實現了凈化社會風氣、引導社會價值觀、培育公民意識的社會目標?如果其運作的客觀結果是使強勢者成功地逃避其應承擔的責任,迫使弱勢的權利者作出妥協,那么鄉村司法的合法性基礎何在?
要使人民法庭真正成為權利的保護者,不論是強勢者還是弱勢者,使其裁判結果真正建立在事實和法律上,而不是當事人雙方的力量對比,使其重拾司法的合法性,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因為鄉村司法之所以呈現出這種構造,并不僅僅是法庭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造成問題的原因復雜,但并不意味著就沒有解決問題的途徑,在充分認識問題的癥結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務實的改革,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上述弊端的發生。
首先,切斷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官同案件結果之間的利益關系。由于出現上述構造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便是法官與訴訟結果有著大量固有的利益關系,因此,可以通過一些切實可行的辦法減少法官同案件間的利益關聯:一是改革形式主義地單純以申訴、上訴、發回重審或者改判等本身作為考核指標的管理方式,而代之以實質違法性為標準進行考核,即只要法官沒有被最終證明有實質性的違法行為,不得因為當事人的前述行為而對其作出否定性評價,也不得以前述形式標準對其他法官加分;二是取消對調解案件進行獎勵的做法,以此減少法庭強制調解的利益動機,同時純化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并設置相應的程序機制予以保障;三是實行縣法院執行庭統一執行的制度。由于法庭人力、物力有限,且與當事人“距離”過于接近,要求其自己負責執行,實在強人所難。因此除非簡單、容易的執行案件以外,原則上由執行庭統一執行,法庭只是協助執行單位;四是進一步尊重、落實部門間的職能分工,明確法庭的職責,使得法庭在裁判時更多考慮如何實現法律正義,而對于適合調解的案件則考慮如何在尊重當事人間合意的情況下平息糾紛,對于明顯違法胡攪蠻纏者應該果斷地采取強制措施,而不是為了維穩(而且“維穩”一詞在許多地方已經被嚴重濫用、扭曲)而一味遷就。
其次,鄉村法律服務所與法庭間的這種支配地位在短期內可能無法有效解決,除了加強對其監管外,很大程度只能依靠律師行業逐步發展,在未來條件成熟時最終取代法律服務所。但是只要法官的中立地位得以基本確立,法律服務所人員也可能成為鄉村司法中一支積極的力量。上面只提供了一個粗略的方向,其中許多措施需要深入論證,而且這些措施背后的問題也沒有進一步挖掘,囿于篇幅及水平的限制,在此就不一一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