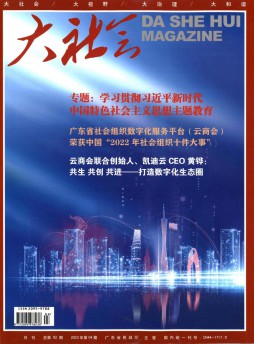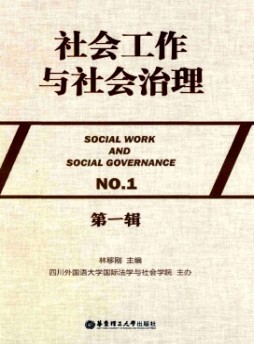社會學派的歷史成就論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學派的歷史成就論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草創(chuàng)時期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芝加哥社會學系創(chuàng)辦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為斯莫爾(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斯莫爾早年在科爾比學院(ColbyCollege)主修神學,1876年研究生畢業(yè),其后3年他在柏林和萊比錫主修歷史學,1879年他從德國返回美國,進入著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并于1889年獲得博士學位。1889年至1892年斯莫爾任科爾比學院教授并出任校長,此間他對社會學產(chǎn)生興趣,出版《社會學導論》(AnIn-troductiontotheScienceofSociology)。1890年芝加哥大學校長哈伯會見斯莫爾,希望他加盟到新創(chuàng)辦的芝加哥大學,斯莫爾建議哈伯組建社會學系,這一建議得到采納。斯莫爾于1892年成為新創(chuàng)辦的社會學系教授并出任系主任,直到1925年他從這個職位上退休。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會學》(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會學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爾的學術(shù)貢獻主要在于讓美國社會學界開始關(guān)注德國的社會學成就,他同時也是《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創(chuàng)辦者(1895年創(chuàng)辦),他在學術(shù)的獨創(chuàng)性方面成就有限,法里斯在《芝加哥社會學》一書中評價說:“除了自己的學生外,很少有社會學家認為斯莫爾的學說是有用的,當他退休后,他的作品僅僅被少數(shù)對社會學發(fā)展感興趣的人所閱讀。”但是法里斯也承認斯莫爾對社會學系的建設貢獻很大,應當受到人們的尊重。事實上,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創(chuàng)立使美國社會學向前邁出了關(guān)鍵的一步。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誕生于19世紀的歐洲,學術(shù)界,斯賓塞、塔爾德、涂爾干、齊美爾等人對社會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美國學者直到19世紀的最后幾年才開始涉足社會學,主要學者包括沃德(Lester.Ward,1841-1913)、薩勒(WilliamGrahamSumner)、吉丁斯(Franklin.Gid-dings,1855-1931)以及羅斯(EdwardA.Ross,1866-1951)等。這些學者充滿個性和自信,雄心勃勃,試圖在社會學領域取得領先地位。然而,擺在美國社會學建設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其中之一就是社會學發(fā)展的體制化,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創(chuàng)辦大大刺激了美國其他大學社會學發(fā)展的步伐,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建成后的一兩年內(nèi),哥倫比亞大學、堪薩斯大學和密歇根大學都先后創(chuàng)辦了社會學系。不久耶魯大學、布朗大學也先后開辦了社會學系。十幾年后,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以及加利福利亞大學也先后開辦了社會學系[8]。
一般來說,學派形成的標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學術(shù)領域出現(xiàn)了若干領軍的學術(shù)領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學術(shù)追隨者,有相對固定的研究機構(gòu)和平臺,有比較充沛的學術(shù)研究經(jīng)費來源,能夠就某些共同的領域開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當?shù)膶W術(shù)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著類似的表達風格。對照這些標準,很難說早期芝加哥社會學派是一個成熟的學術(shù)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學建校之初確實出現(xiàn)了一批為美國社會學建設添磚鋪瓦,影響卓著的人物,這些人物不僅僅來自社會學系,同時也來自哲學系,他們是哲學系的杜威和米德。杜威和米德雖然不屬于社會學系,但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以及心理學理論對美國早期社會學的影響極其深遠,他們不僅是芝加哥哲學學派的領軍人物,同時也是芝加哥社會學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另一位被視為早期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先驅(qū)人物的是庫利,庫利終生執(zhí)教于密歇根大學,但因其學術(shù)思想與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繼、相互影響,也因為庫利與杜威、米德曾經(jīng)互為師生、共同執(zhí)教于密歇根大學,學術(shù)界將庫利也歸入到早期芝加哥社會學派。當然早期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主要力量在社會學系。法里斯如此描述當時社會學系創(chuàng)基者所面臨的緊迫局勢,他說:“當1892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成立的時候,沃德、薩姆納、斯賓塞以及吉丁斯的聲音主導著美國社會學界,涂爾干代表著國外社會學界的聲音,芝加哥大學沒有其他任何部門提供社會學方面的培訓。因此,未來將要創(chuàng)造什么樣的社會學,未來的使命究竟如何,一切都不甚明了。”社會學系系徽的圖案設計成一只絕美的鳳凰從烈火中飛騰而出,寓意著讓科學輝耀人生,徽碑下方篆刻如詩的格言:探索和發(fā)展。在芝加哥社會學派的諸位奠基者中,如果說斯莫爾的主要學術(shù)貢獻是把德國社會學思想介紹到了美國的話,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馬斯等人則在各自領域?qū)ι鐣W發(fā)展做出了獨特貢獻,其中托馬斯的貢獻尤大。
托馬斯(1863-1947)出生于弗吉利亞州拉賽爾鄉(xiāng)(RussellCounty)的一個農(nóng)莊,1884年畢業(yè)于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ofTennessee),主修文學和古典,1886年成為該校第一位博士畢業(yè)生并留校講授自然史和希臘文學。1888至1889年他在德國伯林和萊比錫繼續(xù)求學,專攻心理學和民族學,這段研究經(jīng)歷極大改變了他的思想方向。1889年他返回美國并在奧伯林學院(OberlinCollege)講授英語,期間通過閱讀斯賓塞的作品對社會學產(chǎn)生興趣。1893年在他30歲的時候,他前往芝加哥大學注冊成為該校的研究生,并于1896年獲得他的第二個博士學位。1895年起他成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講師,1910年成為全職教授。1918年因涉及一樁丑聞,被迫離開了芝加哥大學前往紐約繼續(xù)從事美國化研究工作,1923年起他開始在新社會研究學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擔任教職,也間斷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授課。1927年托馬斯當選為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主席,1942年在伯克利(Berkeley,Califorria)退休。托馬斯是芝加哥學派主要成員中研究成果最多、學術(shù)思想最豐富的學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學派》一書中這樣評價托馬斯:“他是一個充滿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而且成果豐富的人,因為他不受陳規(guī)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夠超越任何學術(shù)禁錮,他對美國社會學的貢獻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學的任何同僚都要大。”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會起源導論》(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nóng)民》(與茲納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馬斯在其作品中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社會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義(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論和概念,他的“四項基本欲望”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也頗為流行。托馬斯對于社會學的貢獻首先在于他較早擺脫了傳統(tǒng)社會學在個人與社會發(fā)展解釋上的生物學觀點,而代之以歷史分析和現(xiàn)實分析的觀點。劉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國社會學和實用主義》一書中如此評論道“:盡管托馬斯因為他的作品而被人們銘記,但是人們忘記了他是以一個純粹的生物社會學家開始他的職業(yè)生涯的。”
歐洲社會學深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以生物學觀點解釋個人與社會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歐洲社會學學術(shù)傳統(tǒng),其中,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學說是典型代表。托馬斯早年求學于德國,沉迷于斯賓塞,一段時間中他也深受歐洲這一社會學傳統(tǒng)的影響。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馬斯認為男人天生就是一種偏愛流浪、攻擊和狩獵的動物他認為沖動衰退是一種病態(tài),而農(nóng)業(yè)和定居這類生活方式會使人類器官退化;他認為男人在形態(tài)上的發(fā)展比女人更重要,異族通婚源于男性尋求更多陌生婦女的愿望;他認為人類對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類生存中最主要的驅(qū)動力,他將社會看作是一種純粹的生物環(huán)境。上述觀點體現(xiàn)在他的博士論文《論性代謝的差異》(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論文首頁就寫明:“一個日益明顯的事實是,一切社會事實都源于生理現(xiàn)象。”但是當他1907年出版《性與社會:性別的社會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時,他的情況卻開始出現(xiàn)了變化,他在解釋人類行為方面開始擺脫生物決定論的影響。此后,托馬斯提出了態(tài)度價值以及情境定義等重要概念,既反對社會決定論,也反對心理還原主義,而是強調(diào)人與社會環(huán)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響。
托馬斯對社會學的貢獻還體現(xiàn)在開創(chuàng)了社會學研究的文化人類學傳統(tǒng)。文化人類學發(fā)源于歐洲,這是一門從人的角度出發(fā)研究文化的科學,至19世紀末期文化人類學已經(jīng)相當成熟,大師級的學術(shù)人物和學術(shù)著作均已出現(xiàn),如英國弗雷澤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實上,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全稱為“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類學才成為該校一個單獨的部門。托馬斯研究的課題主要集中在性別種族、社會人格以及文化差異、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會起源導論》中對種族智力存在差異的觀點提出了尖銳批評,這一立場和觀點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人類學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觀點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為》一書中,他以收集到的諺語等材料說明各種族不同的智力天賦,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維方式。托馬斯的研究領域顯然與芝加哥社會學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領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CharliesHenderson)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機構(gòu)、勞工問題以及社會保險等方面。與其他同仁相比,托馬斯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題材與歐洲文化人類學研究更為接近。
事實上,正是托馬斯開啟了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傳統(tǒng),在20世紀前后幾十年間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在托馬斯的影響下,一批學者紛紛走上了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在這一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些人物包括斯塔爾(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頓(RalphLinton)以及薩丕爾(EdwardSapir)和科爾(FayCooperCole,1929年成為分離出去的文化人類學系首屆主任)等。托馬斯對社會學最為重要的貢獻恐怕在于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將經(jīng)驗主義理念和方法應用于社會學研究,開啟了芝加哥社會學派實用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影響了整個芝加哥學派的發(fā)展,為芝加哥學派提供了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將這一思想和方法應用于具體的社會學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卻是托馬斯。在這方面劃時代的巨作就是《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nóng)民》,這一巨作由托馬斯與波蘭學者茲納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至1920年出版。馬丁•布魯默認為這套書的出版標志著社會學從抽象理論和學院式研究的傳統(tǒng)轉(zhuǎn)移到更切合實際的經(jīng)驗研究方向。
托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較濃厚,但是從《社會起源導論》起,他的作品中經(jīng)驗材料明顯增多。《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nóng)民》則被視為經(jīng)驗描述與理論概括的典范之作,這部著作的研究對象是當時身處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nóng)民(主要是當時美國的波蘭移民)。他利用捐贈人提供的五萬美元研究經(jīng)費在1809年至1913年間走遍歐洲許多國家,進行走訪調(diào)查。1913年在他最后一次訪問華沙時,他認識了當時供職于波蘭移民保護局的茲納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國內(nèi)外旅行中,托馬斯廣泛收集來自波蘭農(nóng)民群體的書信、有關(guān)新聞報道數(shù)據(jù)、庭審記錄、禱文、小冊子等材料,以作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材料的大部分來自美國國內(nèi),托馬斯通過在報紙刊登廣告有償閱讀的方式獲得這些信件。移民是當時美國社會乃至世界變化的一個縮影,從某個角度來說,關(guān)注歐洲和美國的波蘭移民就是關(guān)注整個美國和整個世界當時正在發(fā)生的巨變。
1899至1910年的11年間,在美國移民總數(shù)中波蘭移民占四分之一,這些波蘭移民大多選擇在芝加哥、匹茲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這樣的大都市居住,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萬波蘭人移民到美國,這些來自波蘭和東歐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經(jīng)濟上陷入窮困,他們大多因為這些原因選擇移民美國。選擇波蘭農(nóng)民作為研究對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些波蘭移民在差異性的社會環(huán)境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顯著特征,托馬斯試圖從這一社會群體中去發(fā)現(xiàn)諸如社會人格、情境決定、態(tài)度和價值之類的秘密,揭示個人與社會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社會心理事實。托馬斯收集到的那些書信之類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關(guān)鍵的作用,這些“偶然材料”真實地記錄了波蘭移民在相互交往的歷史中所發(fā)生的一切真實的故事,他們的經(jīng)歷、文化、傳統(tǒng)、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信仰等。用這類“客觀材料”研究波蘭移民群體是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它避免了來自主觀因素的干擾。事實上,為了確保研究的客觀性和研究結(jié)果的準確性,托馬斯甚至拒絕在研究中采用訪談之類的東西,他認為這種面對面的訪談本身就是對訪談對象和生活過程的干預,甚至操控。《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nóng)民》的面世為社會學經(jīng)驗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會學派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
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全盛時期
1915年伴隨著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加之前期社會學系學術(shù)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會學進入到全盛發(fā)展階段,這一階段一直持續(xù)到19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繪當時的情景,他說:“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為社會學系的核心人物,在整個二十年代他們?nèi)缛罩刑欤械恼系K已經(jīng)被先行者斯莫爾、文森特和托馬斯等人清除。士兵們已經(jīng)從戰(zhàn)場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陣營,國家一片欣欣向榮,整個城市充滿了生機。更加不可忽視的是,大量研究經(jīng)費很快變得唾手可得,社會學已經(jīng)一切準備就緒,一個全盛時期即將在芝加哥大學出現(xiàn)。”但是所謂全盛必須要有具體的人去做具體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創(chuàng)造才可能到來。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會學即將步入全盛之際,其實潛伏著種種危機。馬丁•布魯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說:“在1915年的時候絕對沒有跡象顯示在未來十五年中芝加哥社會學會主導未來美國社會學的發(fā)展。”布魯默給出的數(shù)據(jù)顯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間,在社會學系執(zhí)教的教師從8名減少到5名。在此期間,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爾教授于1924年退休(又說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會學處于巔峰時期僅有三名社會學教授,他們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學術(shù)界傾向于認為芝加哥社會學走向全盛與帕克加盟社會學系關(guān)系甚大。帕克于1913年(又說1914)進入芝加哥社會學系,帕克的一生充滿職業(yè)傳奇和學術(shù)傳奇,他1887年畢業(yè)于密歇根大學哲學系,大學畢業(yè)后做了11年新聞記者,1897年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1899年赴德國繼續(xù)求學,并于1904年獲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任了一年哲學助教之后,又到美國南方從事黑人民權(quán)活動近十年,在他50歲的時候再次回到大學講壇。
帕克進入芝加哥大學的最初幾年中潛心教學,培養(yǎng)學生,只發(fā)表了為數(shù)不多的論著:包括論文《次級群體中的種族同化》;60頁的小冊子《人類行為的原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環(huán)境中人類行為調(diào)查》。1921年他與伯吉斯合編的教材《社會學導論》出版,這部一千多頁的教材為他帶來了極大聲譽,該書包括14個社會學主題,收錄196篇閱讀篇目,參考文獻達到了1700項,這本教材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分別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評論說:“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寫的這部著名的教科書被許多社會學家認為是最具影響的社會學著作,1921年之后美國社會學的方向和內(nèi)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這本教科學設定的。”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畢業(yè)于肯菲舍學院(KingfisherCollege),隨后進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繼續(xù)求學,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學業(yè)。1912至1913年在托萊多大學(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至1915年在堪薩斯大學任教,1915至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伯吉斯成為帕克最密切的學術(shù)合作伙伴,他們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會學導論》外,還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環(huán)境中的人類行為調(diào)查》(1925)等作品。真正使芝加哥社會學形成學派,流傳身后的成果是此間進行的“都市生態(tài)結(jié)構(gòu)研究”以及“都市行為研究”,法里斯評論說:“20世紀20年代芝加哥社會學系最引人注目和和廣為人知的進展是他們在都市生態(tài)方面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創(chuàng)性研究。”
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這些大規(guī)模的研究活動中扮演了總設計師的角色。“都市生態(tài)結(jié)構(gòu)”“、都市行為研究”這樣的理論念頭和設計出自帕克大腦之中一點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進入芝加哥大學之前主要職業(yè)是新聞記者和社會•社會學研究與社會調(diào)查•活動,他十分看重實踐和實驗活動。在從事新聞報道的十幾年中,他就養(yǎng)成了觀察城市發(fā)展和城市生活的習慣,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環(huán)境中的人性調(diào)查》就是他早年對城市觀察和研究結(jié)果。他說“:城市在擴展,滋生于其中的各類人性也在不斷顯現(xiàn),這使得城市變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這里我們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會的種種場所。”進入社會學系之后,他在學術(shù)上更自覺地將實用、實驗和效用作為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方向。在《社會學導論》中他非常明確地闡述道“:從某種流行的觀點來看,現(xiàn)在的社會學已經(jīng)成為一門實用科學,社會學很快將成為這樣一門科學,它在解決某一問題時得出的結(jié)論也將完全適用于同類其他問題。實驗方法將進入社會生活、工業(yè)發(fā)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個領域,在所有這些領域,人類實際上被各種或明或暗的法則所制約引導。但是,這些法則很少被人們以理論假設的方式和實驗證明的方式予以闡明。如果要區(qū)別這兩種方法,我們選擇調(diào)查而不選擇研究。”帕克將正在興起的芝加哥這座都市看作一個巨大的社會實驗場,他說:“社會學研究工作應該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個社會實驗室,這意味著應該去收集那些影響城市社會生活的各種材料,并對材料進行歸納和分析。”
他的學術(shù)研究目標是要摸清楚這個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種人類行為。就像當時許多社會學家一樣,帕克深受達爾文和斯賓塞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學說的影響,以生物學的思想和方法去觀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來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態(tài)。帕克1902年在德國求學時跟隨黑特納(Hettner)學習地理,他堅信:“每一個社會學專業(yè)的學生都應該了解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其實,文化歸根到底就是一種地理現(xiàn)象。”到芝加哥大學后,他開設的其中一門課程就是“實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過這門課程,帕克鼓勵研究生們走進城市、走進社會,以繪制地圖的方式去呈現(xiàn)這座城市地產(chǎn)、商業(yè)、舞廳、、犯罪等各行各業(yè)的分布和結(jié)構(gòu),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為。其他各種實證研究方法,如訪談、觀察、數(shù)據(jù)收集、文獻分析也被廣泛運用。這類經(jīng)驗研究方法的廣泛應用對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最終形成至關(guān)重要,這些經(jīng)驗方法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學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態(tài)并不是終極目的,最終目的是要透過都市生態(tài)去研究人類行為。正如法里斯所說:“都市結(jié)構(gòu)只是豐富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的一個背景,生態(tài)學不過是進入到這背景中的一條路徑,它們最終都指向都市行為。”
芝加哥社會學派所倡導的都市生態(tài)研究最終指向行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會失序等等具體的都市人類行為課題,圍繞這些課題產(chǎn)生了一大批調(diào)查研究,這些成果大多由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許多作品獲得出版。這些研究作品包括: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導工作,他們?yōu)檫@些調(diào)查的實施提供了關(guān)鍵的理論概念、框架和具體的研究方法手段,他們合作的都市生態(tài)學著作《都市社區(qū)》(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與社會群體》(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還為學生們提供了寫作范本。勞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會學家的傳記》中給出了帕克具體指導學生從事都市研究的詳盡數(shù)據(jù)。在1921至1931年15項有關(guān)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7項研究獲得出版,帕克為其中的三本書寫了序言。
在42本有關(guān)種族、文化、倫理關(guān)系的學生著作中,帕克給于具體指導或?qū)懶蜓缘闹魅缦拢ㄆ渲胁糠肿髌窞閷W生們畢業(yè)后所寫):2.博士論文《人類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實上,芝加哥社會學的成功仰賴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評論的:“縱觀20世紀20年代芝加哥社會學成功的歷史,這些成功應歸功于大量在冊學生,知名學者,大量優(yōu)秀的師生作品以及創(chuàng)新精神。所有這些凝聚成極高的士氣,使社會學系的繁榮一直延續(xù)到30年代。”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即使是在全盛的十二年中規(guī)模都不是太大,這種類型靈活的機構(gòu)建制反而使社會學系能夠充分利用學生進行科研創(chuàng)造,同時接納本校其他專業(yè)領域的學者參與進來,共同打造具有明顯跨學科特征的社會學體系。以下數(shù)據(jù)可以顯示社會學系的發(fā)展狀況。1895至1915年美國大學授予社會學博士學位人數(shù)98人,各大學數(shù)量分布如下:
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衰落
一般認為芝加哥社會學派從3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第二代芝加哥社會學派主導核心人物的先后離場。作為社會學系凝聚人心的核心人物,帕克于1931年到1932年間進行了為期一年的世界旅行,1934年退休。此間另一個核心人物伯吉斯卻忙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似乎已不像從前那樣專注和執(zhí)著。往更后面說,系主任法里斯(EllsworthFaris,1874-1953)1939年退休,奧格本(Ogburn,1886-1959)于1951年退休,沃思(Wirth,1897-1952)于1952年過早離世,伯吉斯也于1951年退休。法里斯認為布魯默(HerbertBlumer),斯托弗(SamuelStouf-fer),休斯(EverettHughes)等人構(gòu)成了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第三代人物,但是他們的學術(shù)成果、學術(shù)影響被世人接受卻在更后。
第二,在激烈競爭中學術(shù)競爭力衰退。3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學界競爭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加利福利亞大學等院校的社會學建設發(fā)展迅猛,迅速躍居為美國社會學的領軍機構(gòu)。與此同時,哈佛大學也在謹慎發(fā)展社會學專業(yè),先后引進了索羅金(PitirimSorokin),齊默曼(CharleC.Zimmerman)以及帕森斯(TalcottParsons)等領軍人物。二戰(zhàn)以后哈佛大學社會學發(fā)展更是突飛猛進,斯托弗(Stouffer)加盟哈佛大學社會關(guān)系系(DepartmentofSocialRela-tions),新建的實驗室投入使用。遍及美國的社會學專業(yè)紛紛在全國許多院校出現(xiàn),這些院校包括俄亥俄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康奈爾大學、依阿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夏威夷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以及耶魯大學。
第三,年輕人才隊伍退化,社會學發(fā)展后勁不足。1930年代中期以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學術(shù)著作出版逐漸萎縮,博士論文出版數(shù)量很少,學生們離開學校后很少再從事社會學研究并出版著作,除了休斯和斯托弗等人之外,很少有人對美國社會學發(fā)展有所貢獻。社會學芝加哥學派衰落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是《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的創(chuàng)刊以及社會學研究學會(SociologicalRe-searchAssociation)發(fā)起成立。在此之前,以芝加哥社會學系為核心的《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895年創(chuàng)刊)和美國社會學家學會(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在美國社會學發(fā)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它們的排他性也限制了其他院校社會學的正常發(fā)展。對于學術(shù)資源的獨占引起了同行的不滿,最終導致新的學術(shù)刊物和學術(shù)組織的誕生,這一事件標志著美國社會學重心的轉(zhuǎn)移。布魯默認為芝加哥社會學派衰落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伴隨著美國地方化和區(qū)域化的逐漸消失,一個統(tǒng)一的、一體化的美國開始形成,30年代以前芝加哥社會學所關(guān)注的都市問題、移民問題、種族文化問題開始淡化并淡出,一些全國性的話題上升為社會學關(guān)注的主題,研究方法也從田野考察轉(zhuǎn)移到觀察研究(Surveyresearch),在這一大背景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優(yōu)勢地位開始被他人所取代。
作者:柯澤單位:西南政法大學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