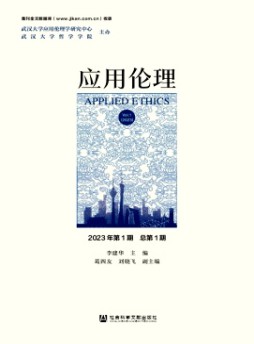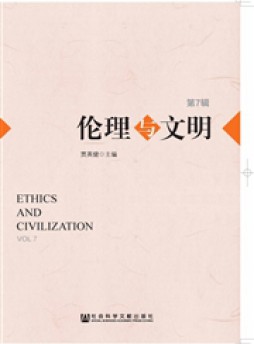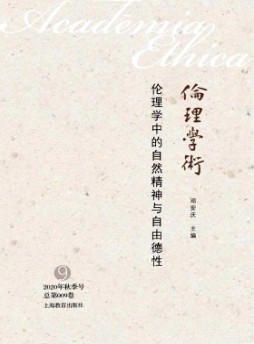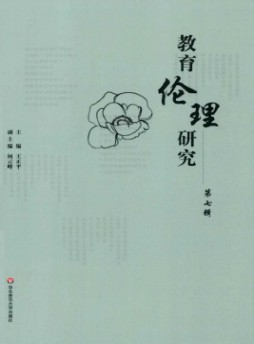倫理學理論中的物質(zhì)源泉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倫理學理論中的物質(zhì)源泉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郝云單位:臨沂大學物流學院
經(jīng)濟學家克拉克認為,“所謂財富,是指那些物質(zhì)的、可以轉(zhuǎn)讓的、數(shù)量有限的人生幸福的源泉。”可見,財富的內(nèi)涵是它的物質(zhì)承載、價值兌換以及屬人的主觀感受種種規(guī)定性。經(jīng)濟學的財富范疇還有著被產(chǎn)權(quán)化所定義的剩余產(chǎn)品、產(chǎn)權(quán)、可兌換性等特征。上述規(guī)定同時揭示了財富的多向度性質(zhì)。倫理學視域中的財富研究,在于提升對財富本質(zhì)的倫理認識,確立財富的價值存在方式及其規(guī)定性,使倫理學意義上的財富理解與經(jīng)濟學、法學等對財富的解讀相互促進和補充。筆者認為,倫理學對財富的審視,主要應(yīng)從“尺度倫理”、“他屬倫理”、“應(yīng)然倫理”以及“共享倫理”來進行。
一、“尺度倫理”:從“質(zhì)料因”向“目的因”過渡
財富具有物的屬性與價值屬性、客體性與主體性雙重特征,相應(yīng)地,衡定財富的價值也有兩種尺度,即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物的尺度體現(xiàn)了財富的客觀性狀,是財富的“質(zhì)料因”;人的尺度則重在揭示財富對主體的意義、財富占有的合理性、分配的公正性以及財富追求的目的等,是財富的“目的因”。“質(zhì)料因”與“目的因”雖然在規(guī)定性上不同,但它們是相互依賴和相互轉(zhuǎn)化的。財富的“尺度倫理”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從“質(zhì)料因”向“目的因”的過渡過程。因此,財富倫理向度的價值標準不僅在于探討物的價值,還在于以人的尺度去把握財富的意義,更在于將物的價值納入到人的價值體系中,矯正物的尺度所導致的偏頗,凸顯人的主體性存在,使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達到辯證統(tǒng)一。財富的“質(zhì)料因”向“目的因”的過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xiàn)出來:
首先,從物的尺度向人的尺度過渡。一是從財富概念的認知看,財富雖然代表著一定的物,以物質(zhì)財富作為主要的度量標準,但它又表現(xiàn)為人與財富的關(guān)系。馬克思對此作了深刻的論述,他認為:“財富的獨立的物質(zhì)形式趨于消滅,財富不過表現(xiàn)為人的活動。凡不是人的活動的結(jié)果,不是勞動的結(jié)果的東西,都是自然,而作為自然,就不是社會的財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是從財富追求的目的看,財富的目的不能偏離人的目的。英國經(jīng)濟學家威廉•湯普遜把財富直接與人的幸福聯(lián)系起來。他說:“生產(chǎn)財富的唯一理由終歸是因為它能增加謀求幸福的手段。”可見,人的尺度的強調(diào)可以幫助矯正單一的物的尺度,使財富真正成為謀取幸福的手段。三是從財富的價值實現(xiàn)途徑看,財富的價值體現(xiàn)在人們之間通過物的交換,從交換價值中實現(xiàn)財富的價值。早在古希臘時期,色諾芬就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定義財富:“一只笛子對于不會使用的人而言,賣出去才是財富。”這表明,財富通過交換把財富與主體、主體與主體結(jié)合起來,并在對主體的意義中得到確認。四是從財富的增長角度看,財富的增長不僅是自然的過程,也是價值實現(xiàn)的過程。如今,財富的增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不斷加深,對財富的審視尤其不能無視財富和人的關(guān)系,關(guān)注財富的主體性、關(guān)心人的利益實現(xiàn)成為必然的趨勢。
其次,從財富的貨幣價值的追求向人的生存?zhèn)惱砟繕说淖非筮^渡。物的尺度的顯性標準在于對財富貨幣價值的度量。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都能以某種定量的貨幣價值來度量,如土地、房屋、黃金、石油、糧食、債券、股票等等。財富的創(chuàng)造受內(nèi)在價值增值的驅(qū)動,通過最大化的經(jīng)濟杠桿,使財富價值創(chuàng)造的功能發(fā)揮到極致。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的生存?zhèn)惱砟繕俗非笙嘁恢隆1M管不同時期財富的價值尺度相異,但它們都代表著每一時期人們對財富的期待和生存?zhèn)惱砟繕说慕y(tǒng)一性的訴求。農(nóng)耕時代的財富是以耕地、谷物以及養(yǎng)殖品等形式出現(xiàn)的,其財富的增長樣式表現(xiàn)為對地理環(huán)境的高度依賴。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此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處于不均衡狀態(tài)。因此,大凡土壤肥沃、交通發(fā)達的地區(qū)人口密集,財富聚集較多。人們的需求和生存?zhèn)惱砟繕艘彩苓@些條件的限制。工業(yè)時代的財富借助于先進技術(shù)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表現(xiàn)為多樣化的工業(yè)品等以及貨幣資本等;生產(chǎn)要素的增加使人們的需求得到了較大的滿足。后工業(yè)時代,隨著計算機信息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金融產(chǎn)品、知識經(jīng)濟的出現(xiàn),財富的價值形態(tài)出現(xiàn)了較大變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商品專利技術(shù)、票據(jù)、有價證券等形式的出現(xiàn)尤其是金融業(yè)的發(fā)展,使財富的形態(tài)具有不確定性特征,財富的形態(tài)更趨虛擬化,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財富的追求和發(fā)展態(tài)勢看,人類追求財富的步伐正不斷加快。在各個時期財富的推進中,經(jīng)濟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經(jīng)濟學使財富的追求建立在理性、科學的基礎(chǔ)上。財富的價值創(chuàng)造功能為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滿足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而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及生存目標的需要又成為財富創(chuàng)造的“動力因”。
再次,從財富的經(jīng)濟合理性向倫理的價值合理性過渡。財富的經(jīng)濟合理性在于財富的增長合于效率,倫理合理性在于財富的合德性。只有建立在二者統(tǒng)一的基礎(chǔ)上,財富才具備真正的合理性。從效率角度看,以何種經(jīng)濟手段來促進財富的增長是其重點。財富增長的經(jīng)濟理論有多種樣式,如勞動生產(chǎn)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勞動生產(chǎn)理論認為,要促進財富的增長,就要提高勞動生產(chǎn)力,從而增加財富增長的量。在貨幣經(jīng)濟中,生產(chǎn)即所得,因此,可借助于生產(chǎn)力的提高使生活改進。因之,追求生產(chǎn)力的提高成為財富不斷增長的動力與目標。新制度經(jīng)濟學則認為,經(jīng)濟史的演進與制度變遷相聯(lián)系,充分認識到制度變遷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意義。從倫理的角度看,重點在于財富創(chuàng)造的正當性、財富分配的公正性以及財富獲取的合理性等。正如韋伯所說:“確實,一種企業(yè)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搏得上帝的青睞,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標準,換句話說,必須根據(jù)它為社會所提供的財富的多寡來衡量。”
二、“他屬倫理”: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
倫理學的“他屬”要求重在對財富私向化傾向的限定及對其社會化傾向的張揚。財富的追求時常面臨兩種價值選擇的難題,表現(xiàn)為利己傾向與利他原則的矛盾。經(jīng)濟學觀念與倫理學觀念的差異往往存在于經(jīng)濟理性的利己傾向與倫理理性的利他原則的對立中。財富的“他屬倫理”表明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認識這種過渡。
首先,“自利說”的困境促使財富觀念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在財富的倫理觀念上,近代西方的“自利說”一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存在著對利己主義財富觀的單向度的張揚。然而,現(xiàn)實的選擇告訴人們,利己與利他的矛盾不可回避,主張“人性自利說”者也試圖尋求解決之策。如霍布斯從利己主義出發(fā)提出了“自然法”理論的國家政治學說,以契約的形式來調(diào)整利己與利他的關(guān)系;斯賓諾莎的理性利己主義則賦予理性以調(diào)節(jié)的功能,用以調(diào)節(jié)個人與他人的關(guān)系。經(jīng)濟學家們也不可回避個人財富與公共財富的關(guān)系問題。如自由主義學派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自動公益說”、約翰•穆勒的“利益合成說”、馬歇爾的“利益均衡論”,都是對財富分配機制的有益探索;制度經(jīng)濟學派則用道德、法律、經(jīng)濟手段(康芒斯)、意識形態(tài)(諾斯)、團隊(德姆塞茨)、交易成本(科斯)及產(chǎn)權(quán)等約束條件,來控制人的利己或搭便車行為。以上諸種觀點都認為要有協(xié)調(diào)和保障機制來解決利己與利他的矛盾,既使個人財富得到應(yīng)有保障,同時也在客觀上增進社會財富。
其次,社會財富增長的實現(xiàn)促使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是辯證的關(guān)系:如果單從個人的角度出發(fā)獲取個人財富,而不去推動社會財富的增進,則既不能使社會財富增長,也會阻礙個人財富的獲得。經(jīng)濟學家阿羅對亞當•斯密的“自動公益說”提出了質(zhì)疑,他在關(guān)于社會選擇問題的研究中提出“不可能定理”,認為無數(shù)個人偏好不可能集結(jié)形成共同的偏好,因而凝結(jié)著共同偏好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能存在。這實質(zhì)上否定了亞當•斯密的追求個人財富自動促進社會財富的判斷。而阿羅推論的前提則是假定人的行為選擇是利己的,追求個人財富的最大化。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理論中,許多觀點證明二者不能簡單劃等號,如“囚徒困境”就說明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是不一致的,說明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追求自利的最大化不一定會導致集體最優(yōu)均衡。而倫理學的“他屬”原則有助于解決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矛盾問題。在倫理學說史上,許多倫理學家在對個別財富肯定的同時,對公共利益和社會財富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以休謨等人為代表的情感主義認為,人類具有無私的仁慈之心,具有促進人類幸福和社會公益的普遍傾向。休謨還提出了正義原則作為外在的規(guī)范以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的實行。
再次,追求一般財富的欲望促使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馬克思早就把個人財富的欲望與所有人的財富的欲望聯(lián)系起來,并強調(diào)只有上升到一般財富,才是真正財富追求的動力源泉。他指出:“因為每個人都想生產(chǎn)貨幣,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這種欲望創(chuàng)造了一般財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為不斷重新產(chǎn)生的一般財富的源泉。由于勞動是雇傭勞動,勞動的目的直接就是貨幣,所以一般財富就成為勞動的目的和對象。作為目的的貨幣在這里成了普遍勤勞的手段。生產(chǎn)一般財富,就是為了占有一般財富的代表。這樣,真正的財富源泉就打開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一般財富”體現(xiàn)了共同追求的財富,而只有對一般財富的追求才會成為財富的真正動力源泉。
三、“應(yīng)然倫理”:從“情欲、任性”的特殊性存在
向普遍性的法理精神過渡倫理學的“應(yīng)然”要求提出從單個人的“情欲、任性”的特殊性存在進入到普遍性的法理精神的層面。作為倫理學的財富,必定是脫離了單個人特殊的、帶有“任性”的私欲,而轉(zhuǎn)向?qū)餐娴年P(guān)懷。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家庭不但擁有所有物,而且作為普通的和持續(xù)的人格,它還需要設(shè)置持久的和穩(wěn)定的產(chǎn)業(yè),即財富。這里,在抽象所有物中單單一個人的特殊需要這一任性環(huán)節(jié),以及欲望的自私心,就轉(zhuǎn)變?yōu)閷σ环N共同體的關(guān)懷和增益,就是說轉(zhuǎn)變?yōu)橐环N倫理性的東西。”財富的應(yīng)然倫理要求逐步跳出單個人的主觀性、特殊需要的財富觀念,使客觀性要求與主觀性要求達到統(tǒng)一。倫理學重點關(guān)注對排斥了“情欲、任性”的正當性和公正性的思考。檢視正當性和公正性從“情欲、任性”的特殊性存在向普遍性的法理精神的過渡,就要對二者進行歷史和現(xiàn)實的追問,并確定和完善二者的內(nèi)在要素,達到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的統(tǒng)一。
首先,從正當性的角度看,要注重對正當性之多重意涵的思考,使其法理精神內(nèi)涵得到充分體現(xiàn)。財富正當性的多重意涵表現(xiàn)為:一是財富身份的正當性。在古代,由于生產(chǎn)力的低下以及財富的稀缺,人們既對財富有著強烈的渴望,同時又對財富存在偏見,財富一度被視為邪惡的代名詞。到了近代,財富才被漸漸恢復其善的評價。新教倫理把人們在現(xiàn)世生活中謀求利益的經(jīng)濟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功視為被上帝選中的標記,這使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正當?shù)匚弧T谫Y本主義時代,對財富的追求有了很高的地位,甚至被奉為人的最高標準,直至財富成了統(tǒng)治人的工具。
二是財富量的正當性。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財富的正當性有明確的數(shù)量界限。他把對財富的追求的方式和限度作為區(qū)分“經(jīng)濟(家務(wù)管理)”和“致富術(shù)”的標準。這兩者的區(qū)別是:前者是由自然賦予的,而后者是由經(jīng)驗與技巧獲得的;前者正當,后者不正當。托馬斯•阿奎拉把商人的職能定義為從事交換的行為:如果旨在追求無限的贏利,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名譽的”;但是如果追求必要的甚至高尚的目的,例如自立、慈善事業(yè)或者公共服務(wù),它就成為合法的。
三是財產(chǎn)權(quán)的正當性。在古希臘、羅馬時期,追求財富只是自由人的特權(quán),不是所有人都有同等自由地追求正當利益的權(quán)利。亞里士多德肯定統(tǒng)治階級追求財富的權(quán)利,極力限制奴隸對財富的追求。近代西方在哲學上、倫理學上的人性自利說的出現(xiàn),賦予了每個主體以平等享有各種利益的權(quán)利:洛克將財產(chǎn)權(quán)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權(quán)利”,從人權(quán)的角度為個人追求財富的合理性辯護;穆勒將“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視為立法和道德的基本原則。從以上關(guān)于正當性的判定標準看,隨著社會認識的不斷深化,對財富正當性的判斷也逐步擺脫了“任性”的糾纏。
其次,從公正性的角度看,要注重對制度變遷及分配關(guān)系變更的再認識。財富的公正性的“任性”向普遍的法理精神的過渡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定社會的分配制度。在階級社會中,各個階級、個人或集團的利益是通過分配來實現(xiàn)的,而分配是由生產(chǎn)資料的占有形式?jīng)Q定的。二是一定社會的財產(chǎn)權(quán)保護制度。財產(chǎn)制度是對個人財富的確認和保護,同時也是對整個社會財產(chǎn)權(quán)的確認與保護。它的演進過程經(jīng)歷了從特殊性到普遍性的過程。財產(chǎn)保護制度作為一種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本身具有其合理性,不僅推動了個人財富的增長,而且在促進社會財富增長中持續(xù)發(fā)揮著重要的激勵作用,越來越具有普遍性的法理精神的特征。三是國家財富與個人財富分配的合理性。這里的個人財富代表了普遍的個人利益即人民的利益,是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概念。穆勒在《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中說:“總產(chǎn)量達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無需再那么關(guān)心絕對產(chǎn)量的增加與否,此時最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總產(chǎn)量的人數(shù)相對來說應(yīng)該有所增加。”“如果人民大眾從人口或任何其他東西的增長中得不到絲毫好處的話,則這種增長也就沒有什么重要意義。”
四、“共享倫理”:從被資本宰制的社會向人的全面發(fā)展過渡
倫理學的“共享”目標決定了從資本宰制的社會向人的全面發(fā)展過渡。資本運行的邏輯常與道德和人的全面發(fā)展的要求背道而馳。在以往階級社會中,法律保護的往往是統(tǒng)治階級的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馬克思認為,共同利益一旦以階級利益獨立存在,個人利益就會異化:“個人的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異化,同時又表現(xiàn)為不依賴于個人的、通過交往而形成的力量,從而個人的行為轉(zhuǎn)化為社會關(guān)系,轉(zhuǎn)化為某些力量,決定著和管制著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在此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運行的矛盾性質(zhì),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改變經(jīng)濟制度:這種制度阻礙了真正共享財富之目標的實現(xiàn),因此失去了倫理性。要實現(xiàn)從被資本宰制的社會向人的全面發(fā)展過渡,發(fā)揮“共享倫理”的功能,需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注重效益增長與財富共享兩大財富發(fā)展重要指標的設(shè)定。財富的目標不是單個人的利益實現(xiàn),而是對共享目標的追求,這體現(xiàn)了倫理向度的目標趨向。在財富的生產(chǎn)和創(chuàng)造活動中,要使財富共享并非易事,二者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時常出現(xiàn)。
其次,需要處理好公正與效率的關(guān)系。對此經(jīng)濟學家歷來就有爭論,有的經(jīng)濟學家認為,效率與公平是不相容的一對矛盾:強調(diào)公平就會影響效率,追求效率就要犧牲公平。不過總體來看,經(jīng)濟學逐步認識到公平對促進效率的重要性。當然,對公平促進效率的判斷也要有辯證的、歷史的思考。庫茨涅茨探討了經(jīng)濟增長過程中個人收入差距的長期變動趨勢,即“倒U假說”,認為:在經(jīng)濟增長的早期階段個人收入差距趨向擴大,特別是在從前工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轉(zhuǎn)變的時候,這種擴大趨勢會更迅速;隨后出現(xiàn)一個穩(wěn)定的時期,此時個人收入差距趨向縮小。他的理論對于研究我國財富增長與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問題具有參考意義。倫理學則從共享目標的角度看待公平問題,注重社會中獲益較少人群的利益,強調(diào)最大限度地滿足窮人的需求。羅爾斯很重視結(jié)果公平問題:“雖然財富和收入的分配無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須符合每個人的利益,同時,權(quán)力地位和領(lǐng)導性職務(wù)也必須是所有人都能進入的。人們通過堅持地位開放而運用第二個原則,同時又在這一條件的約束下,來安排社會的與經(jīng)濟的不平等,以便使每個人都獲益。”被羅爾斯稱為“差別原則”的第二原則,實際上是倡導結(jié)果公平、全民福利。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則提出了更為具體的窮人福利原則。他認為,許多經(jīng)濟學家往往只把收入和商品作為福利的物質(zhì)基礎(chǔ),因此在研究不平等時只研究收入不平等。這就忽略了與貧困有關(guān)的其他因素,如事業(yè)、缺醫(yī)少藥、缺乏教育以及社會排斥。“從實證分析看,收入不平等與其他有關(guān)空間內(nèi)的不平等的關(guān)系,可以是相當遠并隨情況而變的,因為收入以外的多種經(jīng)濟因素,會影響就個人處境和實質(zhì)自由而言的不平等。”
針對我國的公平問題及財富共享性問題,鄧小平早就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shù)人富起來、大多數(shù)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xiàn)社會主義本質(zhì)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yīng)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共同富裕”的目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決定的。如今,社會總體財富有了很大的增長,但是從整個社會來看,富人與窮人的財富占有的差距已經(jīng)較大,目前的利益矛盾比較突出。和諧社會的建構(gòu)要求利益均衡發(fā)展,使財富真正為廣大國民所享有,這樣才能夠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xiàn)。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chuàng)造了財富增長的奇跡,人們的財富增長和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貧困問題得到了很大改善,但還有諸多問題要解決。貧困問題包括教育公平、醫(yī)療衛(wèi)生、政府支持、就業(yè)、住房保障、公平公正、法制化進程等。在現(xiàn)階段,我國提出了“初次分配也要講公平”,這的確是實現(xiàn)財富共享性增長的重要路徑。以往我們只關(guān)注二次分配不公的情況,加大稅收和轉(zhuǎn)移支付,卻忽視了初次分配的公平問題,導致目前初次分配的不公平問題比較突出。而如果不實現(xiàn)初次分配的公平,靠二次分配來解決是很困難的。并且,過度依賴二次分配來解決公平問題將會加大稅收力度,從而降低生產(chǎn)的積極性,影響財富增長的量。
再次,追求財富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統(tǒng)一。財富的最終目標是滿足人的需要,就是說財富總是作為手段價值存在的,如財富與權(quán)力結(jié)合,使財富作用有不斷擴張的趨勢。財富借助于所有權(quán)使其作為達到其它目的的手段,這就無形中賦予了財富所有者以“權(quán)力”。凡勃倫認為:“擁有財富,起初只被看作是能力的證明,現(xiàn)在則一般被理解為其本身就是值得贊揚的一件事。財富本身已經(jīng)內(nèi)在地具有榮譽性,而且能給予它的保有者以榮譽。”(凡勃倫,第25頁)以上所說的只是從財富中內(nèi)生的權(quán)力,還有外在權(quán)力。如果外在特權(quán)與財產(chǎn)權(quán)結(jié)合也會使財富的作用不斷擴張。而權(quán)力如果介入不當,就會限制財富的正當增長。然而,財富與權(quán)力的結(jié)合更多地體現(xiàn)在擁有財富對人的意義上。人們對財富不應(yīng)是為占有而占有,而應(yīng)是為享受而占有。人們構(gòu)建和擁有財產(chǎn)權(quán),總是為了促進自己的各種利益。財富與人的自由也是聯(lián)在一起的:人們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自己的自由和目的,同時又加強了自己的主體性存在。這是財富作為手段價值延伸的重要趨向和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