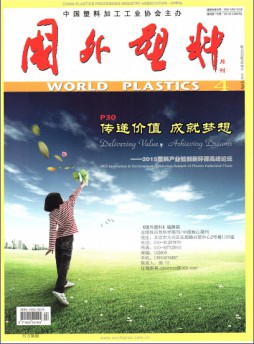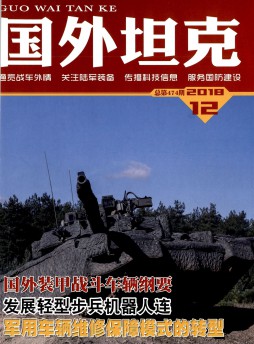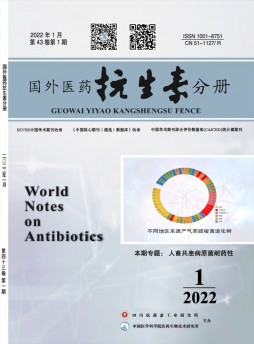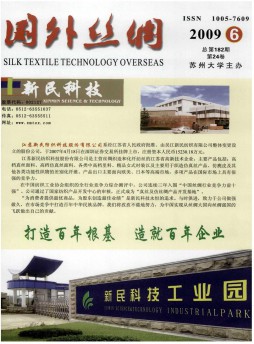國(guó)外文學(xu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國(guó)外文學(xu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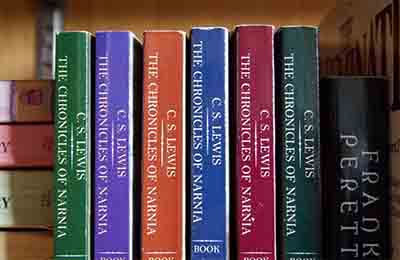
自20世紀(jì)的80年代初以來(lái),國(guó)內(nèi)的美國(guó)文學(xué)研究界率先與國(guó)外接軌,對(duì)在美國(guó)流行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各種新思潮、新理論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進(jìn)和審視,從新批評(píng)、現(xiàn)象學(xué)批評(píng)到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從讀者反應(yīng)批評(píng)(接受美學(xué))到符號(hào)學(xué)、闡釋學(xué)、敘述學(xué)——這里面當(dāng)然又包含了神話原型的批評(píng)、女權(quán)/女性主義的批評(píng)、精神分析學(xué)的批評(píng)、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等,緊接著是鋪天蓋地的后現(xiàn)代主義,然后又是熱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后者不僅把早先的女性主義、少數(shù)族裔批評(píng)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批評(píng)。在短短十幾年的時(shí)間內(nèi),戰(zhàn)后美國(guó)文學(xué)所涉及的所有理論問(wèn)題,幾乎都被我們審視了一遍。這些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jìn),對(duì)于解放我們的思想,改變過(guò)去那種以意識(shí)形態(tài)劃線為指歸的簡(jiǎn)單化的文學(xué)認(rèn)識(shí),對(duì)于更新我們的批評(píng)觀念,拓展和深化我們的文學(xué)視野,起了相當(dāng)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從90年代末開(kāi)始,盡管國(guó)外重要理論流派的翻譯出版仍在繼續(xù),然而理論研究的總體勢(shì)頭卻明顯大不如前,國(guó)內(nèi)一些研究學(xué)刊雖然仍不斷在刊發(fā)理論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這些文章的大多數(shù)可以說(shuō)只停留在對(duì)于七八十年代所關(guān)注的理論問(wèn)題的轉(zhuǎn)述上,很少看到對(duì)一些新的理論問(wèn)題的開(kāi)拓和深入的探討。這樣一種幾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復(fù)的局面其實(shí)已經(jīng)延續(xù)了相當(dāng)長(zhǎng)一個(gè)時(shí)期,卻沒(méi)有引起我們理論界的足夠重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dāng)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從事國(guó)外思潮追蹤研究的學(xué)者,往往只是盯著自己所熟悉的幾位理論明星不放,而對(duì)那邊的學(xué)術(shù)狀況缺少一種整體的和遞進(jìn)的把握。國(guó)內(nèi)為數(shù)可觀的理論研究論文的引述只局限于有數(shù)的幾位理論家最經(jīng)常被提及的幾部(篇)論著,而很少有對(duì)他們?cè)趯W(xué)術(shù)期刊上發(fā)表文章的引述即為明證。其實(shí),美國(guó)學(xué)界所謂的“理論鼎盛”時(shí)期應(yīng)該說(shuō)早已經(jīng)過(guò)去,那里反對(duì)理論或?qū)碚撨M(jìn)行質(zhì)疑的聲音不僅早就存在,而且越來(lái)越響,現(xiàn)在甚至還帶上了一種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對(duì)以“解構(gòu)”為代表的“理論”和以“政治正確”(PC)為代表的政治化傾向的清算,認(rèn)為正是由于這些年理論的膨脹以及這些新潮理論所加深的一種懷疑主義的氛圍,導(dǎo)致了文學(xué)的衰落和整個(gè)美國(guó)人文教育的滑坡。美國(guó)理論界的這樣一種聲音,在我們的理論研究界則似乎很少聽(tīng)到。而對(duì)于這樣一派意見(jiàn)的了解,不僅對(duì)于正確地把握美國(guó)思想理論界的現(xiàn)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對(duì)于我們自身理論研究的健康發(fā)展,無(wú)疑也會(huì)提供非常有益的啟迪。
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文學(xué)會(huì)是美國(guó)最大的人文學(xué)科學(xué)會(huì),國(guó)內(nèi)外會(huì)員達(dá)三萬(wàn)多人,該學(xué)會(huì)會(huì)刊《現(xiàn)代語(yǔ)文學(xué)會(huì)集刊》向來(lái)是美國(guó)學(xué)界主流思潮的喉舌,然而,它的最近一期破天荒地開(kāi)辟了一個(gè)題為“為什么主修文學(xué)——我們將告訴學(xué)生什么?”的筆談專欄,12位大學(xué)教授就這一話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注:Publicationof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PMLA),Vol.117,No.3,May2002.)。“為什么主修文學(xué)?”這一提問(wèn)本身顯然已認(rèn)定今天的美國(guó)大學(xué)生在選定自己專業(yè)的問(wèn)題上對(duì)主修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懷疑。而提問(wèn)的下半部分——“我們將告訴學(xué)生什么?”則說(shuō)明教師們?cè)谶@個(gè)問(wèn)題上也困惑重重。首篇筆談?dòng)啥趴舜髮W(xué)羅曼語(yǔ)言文學(xué)系主任貝爾(DavidF.Bell)教授撰寫,他在文中列舉的他所在學(xué)校中的教師、學(xué)生對(duì)待文學(xué)的態(tài)度,就很能說(shuō)明問(wèn)題的嚴(yán)重性和緊迫性:
最近,我的一個(gè)同事在樓道里碰到我,她對(duì)我說(shuō)她非常高興,因?yàn)樗磳⑼V顾v授文學(xué)課的學(xué)術(shù)生涯了。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時(shí)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訴我,他實(shí)在想象不出除了搞文化研究外,還有別的什么場(chǎng)合可以教文學(xué)——換句話說(shuō),文學(xué)文本就是最大限度地用來(lái)說(shuō)明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歷史的或理論的主題,與其他文化表述沒(méi)什么兩樣。難怪現(xiàn)在的本科生對(duì)主修文學(xué)表現(xiàn)出日益遞減的興趣。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進(jìn)入大學(xué)以后,比起過(guò)去一茬一茬的學(xué)生來(lái),他們對(duì)學(xué)文學(xué)的興趣要小多了,因?yàn)樗麄內(nèi)雽W(xué)后所遇到的老師,在不少情況下都是對(duì)文學(xué)文本沒(méi)有興趣或充滿懷疑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學(xué)生當(dāng)然就越來(lái)越?jīng)]勁了。(注:DavidF.Bell,“AMoratoriumonSuspicion?”Publicationof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2002,pp.487-90.)
美國(guó)大學(xué)文學(xué)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國(guó)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學(xué)科領(lǐng)域眾多的有識(shí)之士感到憂心忡忡,其實(shí)早已是個(gè)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被美國(guó)《時(shí)代》周刊選為美國(guó)最佳社會(huì)批評(píng)家的哥倫比亞大學(xué)英文系的德?tīng)柊嗫?AndrewDelbanco)教授于兩年前發(fā)表長(zhǎng)文,對(duì)當(dāng)下美國(guó)人文教育危機(jī)及其原因進(jìn)行分析(注:AndrewDelbanco,“TheDeclineandFallofLiterature”,TheNewYorkReviewofBooks,Nov.4,1999.)。文中列舉了多個(gè)重要大學(xué)的校長(zhǎng)和著名學(xué)者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看法。那一年任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文學(xué)會(huì)主席的賽義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說(shuō):“如今文學(xué)已經(jīng)從……課程設(shè)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殘缺破碎、充滿行話俚語(yǔ)的科目”;曾任耶魯大學(xué)教務(wù)長(zhǎng)、普林斯頓大學(xué)研究生院院長(zhǎng)、時(shí)任梅隆基金會(huì)人文學(xué)科顧問(wèn)的科南(AlvinKernan)教授在1990年時(shí)就出版了以憑吊文學(xué)為題的專著《文學(xué)之死》;另如斯各爾斯(RobertScholes)、埃里斯(JohnM.Ellis)、伍德林(CarlWoodring)這樣的著名教授,他們也都發(fā)表了論述文學(xué)和文學(xué)專業(yè)何以衰落的專著。在他們看來(lái),文學(xué)之所以沒(méi)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論、新思潮、新方法的沖擊,是這些新潮理論將文學(xué)指涉“真實(shí)”的價(jià)值一步步地掏空。正如耶魯大學(xué)的斯各爾斯所說(shuō),這些年來(lái),“我們聽(tīng)任自己被人說(shuō)服,接受了所謂談?wù)摗鎸?shí)’是不可能的說(shuō)法”。現(xiàn)在文學(xué)成了與其他符號(hào)系統(tǒng)(如時(shí)尚、肢體語(yǔ)言、運(yùn)動(dòng)等)一樣的東西。倘若說(shuō)當(dāng)初是解構(gòu)主義抽去了文學(xué)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內(nèi)涵,那么今天,一個(gè)反向的潮流又沖了過(guò)來(lái),在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聲浪中,雖說(shuō)強(qiáng)調(diào)了文學(xué)要同它這樣那樣的屬性(民族、階級(jí)、性屬等)聯(lián)系在一起考量,然而我們卻看到,文學(xué)研究被進(jìn)一步“殘片化”(fragmentation)的勢(shì)頭卻有增無(wú)減。目睹文學(xué)日益退場(chǎng)的嚴(yán)峻形勢(shì),畢業(yè)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學(xué)校長(zhǎng)陸登庭(NeilL.Rudenstine)在1998年的全校畢業(yè)典禮上發(fā)出呼吁,號(hào)召要從教育的最本質(zhì)意義的高度去認(rèn)識(shí)人文學(xué)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實(shí)的措施對(duì)人文學(xué)科加以保護(hù)。
近一二十年來(lái),杜克大學(xué)作為美國(guó)文化政治一大重鎮(zhèn),名氣格外地顯赫。大名鼎鼎的馬克思主義批評(píng)理論家詹姆遜是該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該校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刊《社會(huì)文本》則是當(dāng)代左翼激進(jìn)理論的前沿陣地。前幾年,在那個(gè)被炒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索卡爾后現(xiàn)論造假案”中,索卡爾(AlanSokal)那篇題為《跨越邊界:試論量子引力轉(zhuǎn)換闡釋學(xué)》的偽論文,就是《社會(huì)文本》發(fā)表的(注:關(guān)于這一事件的前后真相,請(qǐng)參見(jiàn)《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1997年第2期“動(dòng)態(tài)”欄《索卡爾騙局與后現(xiàn)代相對(duì)主義的惡劣影響》一文。紐約大學(xué)的理論物理學(xué)家索卡爾于1994年秋向《社會(huì)文本》投去一文,聲稱20世紀(jì)理論物理學(xué)發(fā)展完全印證了“后現(xiàn)代”哲學(xué)、政治學(xué)的理論,編輯部五位編輯審讀后一致同意讓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會(huì)文本》特刊上發(fā)表,然而索卡爾接著卻在另一學(xué)刊《交流》上披露說(shuō),他那篇論文只不過(guò)是一篇故意背謬常理、充滿錯(cuò)誤和與前提不符的推論的大雜燴,他的目的是為了耍弄一下編輯們意識(shí)形態(tài)的偏見(jiàn)。美國(guó)《批評(píng)探索》(CriticalInquiry,Winter2002)載文,詳細(xì)分析了該事件的始末及其對(duì)美國(guó)學(xué)術(shù)界的影響(JohnGuillory,“TheSokalAffairandtheHistoryofCriticism”)。)。而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末,當(dāng)“政治正確”(PC)之風(fēng)潮剛開(kāi)始席卷美國(guó)各大學(xué)校園時(shí),杜克大學(xué)就成了這場(chǎng)“文化戰(zhàn)爭(zhēng)”的一個(gè)小舞臺(tái):反PC一方由美國(guó)國(guó)際大赦前主席、政治學(xué)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D.Barber)領(lǐng)銜,而贊成PC的則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費(fèi)什(StanleyFish)掛帥,雙方曾為了哪些書(shū)籍可以擺放在校園書(shū)店的書(shū)架上而惡語(yǔ)相向,吵得不可開(kāi)交。巴伯發(fā)現(xiàn),校園書(shū)店的書(shū)架上每七本政治學(xué)書(shū)籍中就有一本的書(shū)名含有“馬克思”的字樣,于是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認(rèn)為不必要的書(shū)撤下;而費(fèi)什則稱巴伯所組織的“全國(guó)學(xué)者同盟”杜克大學(xué)分會(huì)是一群“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同性戀者”;巴伯一派的人則又反唇相譏說(shuō),費(fèi)什的用語(yǔ)與50年代麥卡錫主義者指控別人為“共黨”如出一轍,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國(guó)《新聞周刊》(Newsweek)曾發(fā)表關(guān)于“政治正確”運(yùn)動(dòng)的長(zhǎng)篇報(bào)道,其中多處涉及杜克大學(xué)在這一風(fēng)潮中的地位和影響。)。
在這樣一所深深卷入社會(huì)政治旋渦之中的大學(xué)里,發(fā)生貝爾教授所說(shuō)的教授和學(xué)生從文學(xué)系勝利大逃亡的情況,按說(shuō)是不該讓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員流失和師生對(duì)文學(xué)興趣銳減這一現(xiàn)象的背后,是否還有更直接的原因,這倒是需要我們這些從事文化思潮研究的人進(jìn)一步思考的問(wèn)題。貝爾教授對(duì)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lái)美國(guó)大學(xué)文學(xué)系的主導(dǎo)思想的變革是這樣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謂的“理論鼎盛”時(shí)期。各種文學(xué)理論據(jù)說(shuō)都是要教會(huì)我們?nèi)绾稳フ莆瘴谋荆皇潜晃谋舅莆铡5牵碚摰奈淦骱芸炀捅坏暨^(guò)頭來(lái),成了反對(duì)理論的武器,反而導(dǎo)致了本應(yīng)讓理論有效地包容文學(xué)文本的種種批評(píng)范式的衰落。貝爾說(shuō),接下來(lái)是“理論鼎盛時(shí)期的結(jié)束”,在過(guò)去幾年中雖也出現(xiàn)了對(duì)于理論的反思,然而這些卻并沒(méi)有從根本上改變?cè)诶碚撃甏斐傻膶?duì)于文學(xué)和高雅文化的懷疑。對(duì)于文學(xué)的懷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貝爾指出,在這理論的鼎盛及衰落的整個(gè)歷史過(guò)程中,最為突出的一點(diǎn)就是對(duì)德里達(dá)解構(gòu)主義來(lái)了一個(gè)不折不扣的簡(jiǎn)單化,它在美國(guó)就被當(dāng)成了對(duì)德里達(dá)思想的理解(注:SeeHermanRapaport,TheTheoryMess:DeconstructioninEclipse,New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將會(huì)自行解構(gòu)”——這樣一個(gè)被稀釋了的、簡(jiǎn)單化的德里達(dá)主義造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誤解,那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個(gè)謊言,都是騙人的。但是,在理論的鼎盛期完結(jié)之前,解構(gòu)主義的另一位理論大師德曼早年親納粹的歷史污點(diǎn)被揭露,而德里達(dá)的理論在解決這一時(shí)期美國(guó)大學(xué)校園政治問(wèn)題上又顯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們漸漸把注意力轉(zhuǎn)向了福柯。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福柯更重視控制文學(xué)話語(yǔ)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學(xué)看成是一個(gè)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場(chǎng),一個(gè)與其他話語(yǔ)場(chǎng)一樣的由各種力量構(gòu)成的話語(yǔ)場(chǎng)。但是,貝爾指出,這樣一種看法卻更加煽起了對(duì)于文學(xué)的懷疑之火。而且,美國(guó)人在對(duì)待福柯時(shí)與他們對(duì)待德里達(dá)一樣,也是持一種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簡(jiǎn)單化態(tài)度。他們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為“訓(xùn)誡控制”這一標(biāo)識(shí)性的話語(yǔ)框架去理解,而福柯式分析的種種精妙之處,卻都在這樣的簡(jiǎn)單化理解中丟失殆盡。當(dāng)然,要說(shuō)一點(diǎn)也沒(méi)剩下,那也有點(diǎn)偏頗。不過(guò),福柯的視角在理論鼎盛結(jié)束后之所以還能夠剩下些許,則主要是因?yàn)樗梢员容^便捷地嫁接到一種更加政治化的批評(píng)之上的緣故。
貝爾在對(duì)美國(guó)學(xué)界過(guò)去二十來(lái)年的大致?tīng)顩r作如上回顧后,接著又對(duì)當(dāng)下的美國(guó)學(xué)界狀況作了這樣一番切中肯綮的歸納:
伴隨著理論鼎盛的消退以及隨后留下的懷疑主義,文學(xué)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變得越來(lái)越重要了。以各種美國(guó)形式的面目出現(xiàn)的分析匯總起來(lái)統(tǒng)稱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學(xué)典律轟去,而這種文學(xué)典律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受過(guò)教育的人的整個(gè)智性積累的一部分。對(duì)文學(xué)典律的控制及對(duì)其邊界的重新劃定,向來(lái)是女性主義批評(píng)、非洲裔美國(guó)人研究以及同性戀及性別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則希望再前進(jìn)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統(tǒng)統(tǒng)消弭。典律問(wèn)題向來(lái)是一個(gè)帶有根本性的問(wèn)題,因?yàn)閷?duì)文學(xué)文本的價(jià)值判斷是傳統(tǒng)批評(píng)家與后現(xiàn)代批評(píng)家對(duì)壘交鋒的一個(gè)戰(zhàn)場(chǎng),這些后現(xiàn)代批評(píng)家對(duì)傳統(tǒng)批評(píng)家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進(jìn)行質(zhì)疑,后者即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權(quán)決定一部文本的價(jià)值,這一決定難道不總是一種對(duì)什么可以被允許進(jìn)入話語(yǔ)進(jìn)行控制的壓迫性舉措嗎?如果是的話,那么最好的解決辦法也許就是放棄價(jià)值判斷,把文學(xué)范疇盡可能地放大,這樣就把高雅與低俗以至所謂典律的概念都統(tǒng)統(tǒng)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對(duì)貝爾教授在筆談中對(duì)現(xiàn)狀的分析的轉(zhuǎn)述,均請(qǐng)參見(jiàn)《現(xiàn)代語(yǔ)文學(xué)會(huì)集刊》(PMLA,Vol.117,No.3,May2002),第487—489頁(yè)。)
我在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貝爾教授的陳述,乃因?yàn)槲野l(fā)現(xiàn)他極其言簡(jiǎn)意賅地勾勒出了文學(xué)如何在當(dāng)下美國(guó)大學(xué)中一步步失落的過(guò)程及其背后的原因,這與我這些年來(lái)對(duì)美國(guó)當(dāng)代思潮進(jìn)行追蹤研究過(guò)程中所獲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對(duì)于我們所研究的對(duì)象國(guó)中人文思潮所發(fā)生的這樣一種變化,原先被掩蓋的思潮逐漸抬頭甚至又卷土重來(lái)的傾向,我們卻視而不見(jiàn),那我們研究的價(jià)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由于美國(guó)的特殊地位,我們對(duì)美國(guó)問(wèn)題的研究一直給予極大的重視。在文化研究方面也不例外,對(duì)美國(guó)的文學(xué),對(duì)美國(guó)的文化思潮、文學(xué)理論動(dòng)向,我們都給予了特別的關(guān)注。然而,我覺(jué)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太側(cè)重于前臺(tái),太關(guān)注當(dāng)下和表面的熱鬧,誰(shuí)善于吸引眼球,我們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誰(shuí),而缺少一種兼聽(tīng)、兼顧的沉穩(wěn)和成熟。造成這樣的情況,其實(shí)我們的媒體也應(yīng)該負(fù)一定的責(zé)任。因?yàn)槊襟w往往希望簡(jiǎn)單明了,希望能單刀直入地把一種理論、一種傾向說(shuō)得個(gè)涇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白越好。而在這樣一種心態(tài)的驅(qū)動(dòng)下,我們上面所談的問(wèn)題多年來(lái)在我們的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只屬于一股不為人們所重視的潛流。
現(xiàn)在,德?tīng)柊嗫啤⒇悹杺冎赋龅膯?wèn)題已經(jīng)由潛流變成了明流。難道我們還不該就此而對(duì)我們自己的研究進(jìn)行一點(diǎn)反思嗎?而首先或許應(yīng)該對(duì)什么是“文學(xué)”反思一下:究竟還有沒(méi)有可稱之為“文學(xué)”的這樣一種東西?因?yàn)閱?wèn)題明擺著,如不為“文學(xué)”劃出一個(gè)大體的范圍,我們就無(wú)法圈定我們對(duì)它的期待,無(wú)法期望“文學(xué)”來(lái)為我們做點(diǎn)什么。當(dāng)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試圖重新找回“文學(xué)”的想法,在一些已經(jīng)接受了后結(jié)構(gòu)(解構(gòu))主義假設(shè)的人眼里,會(huì)顯得很過(guò)時(shí):“還文學(xué)邊界呢,人家早已把文學(xué)研究擴(kuò)大為文化研究、文化批評(píng)了。”是的,一點(diǎn)不錯(cuò),我知道這些年在整個(gè)美國(guó)文學(xué)界,正如貝爾所說(shuō)的,女性主義的批評(píng)、非裔美國(guó)人研究以及同性戀及性別研究等早就在對(duì)文學(xué)典律重新進(jìn)行闡釋和占領(lǐng),甚至早在它們之前,解構(gòu)主義就已經(jīng)抹去了文學(xué)與其他所有文類之間的界限,而緊跟其后的“文化研究”現(xiàn)在又儼然成了大勢(shì)所趨的主流。當(dāng)然,在當(dāng)下的主流派看來(lái),這一局面也是一番激烈交鋒的結(jié)果。記得在六七年前,我就曾在一些小文章中談及布魯姆(HaroldBloom)這樣的文壇巨擘在那場(chǎng)“文化戰(zhàn)爭(zhēng)”中的無(wú)畏表現(xiàn)。勇敢的布魯姆當(dāng)時(shí)幾乎是在進(jìn)行著一場(chǎng)“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他在最短的時(shí)間內(nèi)推出了一部皇皇578頁(yè)的《西方的典律》(TheWesternCanon: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與主流派摧毀傳統(tǒng)文學(xué)典律的努力進(jìn)行抗?fàn)帯?墒敲绹?guó)《時(shí)代》周刊在報(bào)道此事時(shí),用了一個(gè)布魯姆“為死人、白人、男人叫好!”的標(biāo)題(注:“HurrahforDeadWhiteMales!”Time,Oct.10,1994,pp.50-51.),著實(shí)讓人覺(jué)得有點(diǎn)當(dāng)年我們所經(jīng)歷過(guò)的的勁頭。布魯姆后來(lái)在接受《新聞周刊》的采訪時(shí)以一種疲憊無(wú)奈的口吻說(shuō)道:“我們已經(jīng)戰(zhàn)敗,……文學(xué)研究已經(jīng)被一種叫做文化批評(píng)的令人驚嘆的垃圾所替代了!”但正是在這篇訪談錄中,布魯姆拋出了一個(gè)包括他所謂的“一切假馬克思主義者、假女權(quán)主義者以及注了水的福柯和其他法國(guó)理論家的門徒”的集合名詞——“憤懣派”(theschoolofresentment)。他認(rèn)為,正是這批心地虛偽的“憤懣派”,正在把原本不應(yīng)有任何功利價(jià)值的文學(xué)變成了社會(huì)改造的工具(注:“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
布魯姆把文學(xué)看成是沒(méi)有任何社會(huì)功利性的“無(wú)為之物”,顯然也有其偏頗之處。但是,他所使用的“憤懣派”一語(yǔ),則被當(dāng)代美國(guó)最重要哲學(xué)家之一羅蒂(RichardRorty)接了過(guò)去,后者又特別就“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xué)閱讀”這一話題,在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文學(xué)會(huì)的1996年年會(huì)上做了一次專題演講。會(huì)后,他把這一演講整理成文,正式發(fā)表在《高等教育編年史》上(注:RichardRorty,“PointofView: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Higher
Education,Feb.9,1996.)。羅蒂本人雖然是哲學(xué)家,卻從來(lái)不認(rèn)為哲學(xué)只應(yīng)是理念與邏輯的組合,他認(rèn)為哲學(xué)中也應(yīng)該充滿浪漫的想象,因而他在自己的哲學(xué)探索中素來(lái)對(duì)文學(xué)和文學(xué)想象厚愛(ài)有加。他認(rèn)為,文學(xué)本該有自己獨(dú)特的內(nèi)涵和功用。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發(fā)現(xiàn)當(dāng)下的美國(guó)大學(xué)文學(xué)系和文學(xué)研究學(xué)界已越來(lái)越被一種以“知曉”(knowingness)為目的的傾向所控制,他心目中文學(xué)的那種令人凜然起敬、令人煥發(fā)熱情的功能則不見(jiàn)了。而這樣一種情況正發(fā)生在布魯姆稱之為“憤懣派”的這樣一批大學(xué)文學(xué)教師的身上。羅蒂說(shuō),這些教師所走的這條道路,正是幾十年前哲學(xué)家們放棄“靈悟”(inspiration)而轉(zhuǎn)向?qū)I(yè)化的道路。這樣做的結(jié)果將怎樣呢?羅蒂回憶了在他年輕時(shí)哲學(xué)領(lǐng)域中發(fā)生的由艾耶爾(A.J.Ayer)取代懷特海(A.N.Whitehead)而成為英美哲學(xué)家仿效典范的過(guò)程:在羅蒂的心目中,懷特海是那種具有人格魅力、天才型的、浪漫的、華茲華斯式的人物,而艾耶爾則屬于邏輯型的、容不得任何一點(diǎn)雜質(zhì)、追求徹底知曉的那樣一種人,艾耶爾希望哲學(xué)成為一種科學(xué)團(tuán)隊(duì)式的工作,而不是靠英雄人物發(fā)揮想象去取得突破。他承認(rèn)懷特海是一個(gè)優(yōu)秀的邏輯學(xué)家,但認(rèn)為是詩(shī)歌把他給毀了。為此,艾耶爾把一切令人凜然起敬的情緒統(tǒng)統(tǒng)視為神經(jīng)性的毛病。而正由于這一緣故,羅蒂指出,是艾耶爾使英美哲學(xué)界漸漸形成了一種“干澀”的氛圍,默多克(IrisMurdoch)在她《反對(duì)干澀》(“AgainstDryness”)一文中曾對(duì)此有過(guò)嚴(yán)厲的批評(píng)。羅蒂認(rèn)為,現(xiàn)在美國(guó)文學(xué)領(lǐng)域也在重復(fù)著這一轉(zhuǎn)變,其結(jié)果就是如布魯姆所說(shuō)的那樣,“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學(xué)研究,把文學(xué)研究變成了又一個(gè)“沉悶的社會(huì)學(xué)科”,使文學(xué)系變成了一潭學(xué)術(shù)死水(注:RichardRorty,“PointofView: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
HigherEducation,Feb.9,1996.)。
說(shuō)到這里,我覺(jué)得有必要作一點(diǎn)聲明,我這么左右開(kāi)弓地援引布魯姆、羅蒂這些大牌教授的話,其實(shí)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至今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布魯姆把“文化研究”一概視為垃圾,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我覺(jué)得他所指出的問(wèn)題中至少有兩點(diǎn)值得我們注意:一是文學(xué)的徹底政治化,二是一窩蜂地扎堆。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一個(gè)國(guó)家的大學(xué)講堂,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弘揚(yáng)這個(gè)國(guó)家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使其精華得到傳承。而在當(dāng)年的中,我們所看到聽(tīng)到的則是對(duì)自己文化傳統(tǒng)的一筆勾銷,是所謂“古人、洋人統(tǒng)治著我們的學(xué)校,封、資、修統(tǒng)治著我們的課堂”,而基于這樣一個(gè)估計(jì),我們的任務(wù)當(dāng)然就被確定為“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guò)來(lái)”。對(duì)于曾經(jīng)有過(guò)切身經(jīng)歷的我們來(lái)說(shuō),看到今天美國(guó)大學(xué)校園中正在發(fā)生的一切,看到“文化研究”把昔日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基本上定性為所謂由白人、男人主宰的“毒黃蜂”(WASP)(注:“毒黃蜂”(WASP)四個(gè)字母取自“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意為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構(gòu)成的英美主流文化,“政治正確”(PC)運(yùn)動(dòng)就是要對(duì)這樣一種壓迫婦女、壓迫黑人和其他少數(shù)族裔、壓迫同性戀者的主流文化進(jìn)行清算和批判。),把文學(xué)文本認(rèn)定為統(tǒng)治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喉舌,把文學(xué)批評(píng)作為為“地位低下者”(subaltern)行使代言的使命,所有這一切都讓人有一種似曾相識(shí)的感覺(jué)。當(dāng)然“文化研究”也有做得好的,比方說(shuō),賽義德的對(duì)東方主義的揭露和批判,再比方說(shuō),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對(duì)莎士比亞的研究,從中窺見(jiàn)伊麗莎白時(shí)代階級(jí)力量的此起彼伏等。然而,學(xué)術(shù)大腕們播下的龍種,收獲的卻很可能是數(shù)量可觀的跳蚤,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窩蜂地扎堆,照葫蘆畫(huà)瓢。說(shuō)來(lái)也有好幾年了,翻開(kāi)美國(guó)的主要學(xué)刊,幾乎滿眼看到的都是這種“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guò)來(lái)”的清算批判性文章。這股風(fēng)當(dāng)然也刮進(jìn)了國(guó)內(nèi)的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界。人家搞女權(quán)主義/女性主義,我們也搞女權(quán)主義/女性主義,人家搞非裔美國(guó)文學(xué),我們也搞非裔美國(guó)文學(xué),像托妮·莫里森或艾麗絲·沃克這樣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右逢源,一下子紅遍了天;人家那里據(jù)說(shuō)是華裔文學(xué)走紅了,我們這邊也一陣風(fēng)似的追趕,《戈勇士》、《喜福會(huì)》、《唐老亞》……對(duì)于重要的經(jīng)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沒(méi)有,然而研究的視角卻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訴了我們什么——要么是明言的,要么是隱含的——總之,即羅蒂所謂的“知曉”:讀康拉德,從他書(shū)中去摳對(duì)待殖民主義的態(tài)度;讀福克納,讀的是美國(guó)南方在對(duì)待農(nóng)奴、黑人、婦女等問(wèn)題上的態(tài)度;讀亨利·詹姆斯,讀他對(duì)待古老的歐洲與美洲新大陸兩種不同文化的態(tài)度,讀他對(duì)于筆下女性的態(tài)度,甚至他的一些極為次要的短篇小說(shuō)中的兒童形象,也硬要把他們闡釋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兩性性別沖突的犧牲品……
現(xiàn)在有一種思維方式則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這種思維方式在我們的許多理論性研究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我們?cè)谠u(píng)說(shuō)不同思想的交鋒和爭(zhēng)論時(shí),往往會(huì)把雙方爭(zhēng)論的論點(diǎn)懸置,或抽取出來(lái),放入一個(gè)仿佛真空的狀態(tài)中來(lái)進(jìn)行抽象的比較,并試圖評(píng)判雙方論點(diǎn)的對(duì)錯(cuò),而這樣一種比較和評(píng)判,其是非對(duì)錯(cuò)往往是早已由評(píng)判者自己的認(rèn)識(shí)預(yù)先設(shè)定好的。在這種思維方式主宰下,說(shuō)得好像是頭頭是道,殊不知思想的爭(zhēng)論和交鋒,一旦離開(kāi)了爭(zhēng)論的當(dāng)下性,特定的時(shí)間和空間,即離開(kāi)了爭(zhēng)論特定的歷史性,其實(shí)是無(wú)法判定其是非對(duì)錯(cuò)的,即使判定了,也是毫無(wú)實(shí)際意義的。換句話說(shuō),如果說(shuō)爭(zhēng)論中一方的命題有某種正確性,那么它的正確性只能是在當(dāng)時(shí)那個(gè)具體的情況下、針對(duì)其對(duì)方命題的偏頗而言,甚至可以說(shuō),一方命題的正確性是包含在另一方命題的偏頗性之中的。就布魯姆與時(shí)下主流派之間的爭(zhēng)論來(lái)說(shuō),正是由于時(shí)下主流派把文學(xué)當(dāng)作自己所信奉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再現(xiàn),所以布魯姆對(duì)文學(xué)典律的呼喚才格外具有振聾發(fā)聵的意義;也正因?yàn)闀r(shí)下人們都認(rèn)為文學(xué)就是要告訴你這樣那樣的事情和道理,所以布魯姆所謂的“文學(xué)不是要教會(huì)我們?nèi)绾蜗騽e人說(shuō)話,而是要教會(huì)我們?nèi)绾蜗蜃约赫f(shuō)話”(注:“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才格外能引起我們的深思。其實(shí)換一個(gè)角度思考,問(wèn)題就會(huì)很清楚:所有那些“文化研究”所要告訴我們的種種道理,難道我們不是都可以從政治課本、社會(huì)調(diào)查報(bào)告和新聞報(bào)道中獲得,而且是更加便捷地獲得么?既然如此,我們何以要舍近求遠(yuǎn)地訴諸文學(xué)?而沿著這一質(zhì)詢的思路再追問(wèn)下去,那么文學(xué)與別的文類究竟應(yīng)該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或許就是,它不僅包含著“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的表述”(阿諾德語(yǔ)),而且這種得到最佳表述的最佳思想,必須由我們獨(dú)自去品味,默默地含化,它才能沁入我們的心脾。這是一個(gè)“潤(rùn)物細(xì)無(wú)聲”的過(guò)程。它不僅會(huì)使人的認(rèn)知更加豐富,品位得到提升,而且它會(huì)在人們心里融會(huì)、凝聚成某種信念,使人在情感、道德和精神上得到某種歷練和升華,從而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也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文學(xué)在一個(gè)人的修養(yǎng)教化、從粗鄙走向文明的過(guò)程中,將發(fā)揮其他文類無(wú)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現(xiàn)在這種日益政治化的文學(xué)研究中,我們已經(jīng)很難再看到文學(xué)的這一至關(guān)重要的功能了。
如果說(shuō),把文學(xué)再一次從濃重的社會(huì)政治化的陰影中解放出來(lái)是我們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另一項(xiàng)當(dāng)務(wù)之急就是要對(duì)業(yè)已過(guò)去的這場(chǎng)“理論熱”進(jìn)行反思。我這里指的反思,還不是僅僅停留在“理論熱”這一現(xiàn)象本身,而是要在尋回被放逐的“文學(xué)”的同時(shí),對(duì)過(guò)往的各種文學(xué)理論切實(shí)作深入一步的質(zhì)詢。現(xiàn)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現(xiàn)成的結(jié)論性的評(píng)價(jià)作為自己認(rèn)識(shí)的出發(fā)點(diǎn)了,這些老生常談的口頭禪早已成為思維的印轍,只會(huì)把我們引向那些活力全無(wú)的認(rèn)識(shí)偏見(jiàn)。我們現(xiàn)在需要的是一種認(rèn)識(shí)的提升,當(dāng)年理論鼎盛時(shí)期所聽(tīng)到的一些評(píng)價(jià),現(xiàn)在往往已經(jīng)過(guò)時(shí)而不再適用,其實(shí)理論家們自己也在發(fā)展和變化。例如,現(xiàn)在的德里達(dá)與1967年他的《論書(shū)寫》等三部論著同時(shí)問(wèn)世時(shí)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我們看不到這樣的變化,仍一味停留在他們針對(duì)當(dāng)年那特定的需要而說(shuō)過(guò)的一些故意立異鳴高以與前人劃清界線的言論上,那可就是最大的“時(shí)代誤置”(anachronism)了。
去年德里達(dá)來(lái)中國(guó)訪問(wèn),他在離開(kāi)中國(guó)前為上海的一份文學(xué)報(bào)刊的題詞中,意味深長(zhǎng)地自稱是“過(guò)路人”。對(duì)他的訪問(wèn),我曾寫過(guò)一點(diǎn)沒(méi)有署名的文字,現(xiàn)在看來(lái),正好可以嵌入此文,作為我對(duì)于美國(guó)文論熱思考的一部分。德里達(dá)訪華期間,在北京大學(xué)、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三聯(lián)書(shū)店《讀書(shū)》編輯部以及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作了幾場(chǎng)學(xué)術(shù)講演。讓人們頗感意外的是,他講演的基調(diào)與多年來(lái)我們心目中所持有的那個(gè)“解構(gòu)”印象,好像有不小的錯(cuò)位和落差:我們期待的“解構(gòu)”多是鋒芒畢露的批判,而德里達(dá)的運(yùn)思卻集中在“寬恕”的可能;我們期待的“解構(gòu)”是一種所向披靡的激進(jìn)姿態(tài),而德里達(dá)卻毫不掩飾自己的“保守”……這也就難怪了,一些聽(tīng)眾反映,在聆聽(tīng)了解構(gòu)大師的講演之后,愈加感到被潑了一頭霧水。原因何在?我覺(jué)得最主要的就是我們自己沒(méi)有認(rèn)真去讀大師自己的論著,沒(méi)有追尋著他長(zhǎng)期以來(lái)一貫的思想軌跡,將他前后各個(gè)階段的著作聯(lián)系起來(lái)閱讀,而只聽(tīng)信了我們媒體上刊發(fā)的本來(lái)就已經(jīng)是二手介紹的轉(zhuǎn)述。
不可否認(rèn),20世紀(jì)的最后三十年,拉康、巴特、福柯、阿爾都塞和德里達(dá)這五位法國(guó)思想家,把整個(gè)西方思想理論界攪得個(gè)疑霧迷漫,作為一個(gè)整體,他們的巨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們所遭遇的批評(píng)和反駁,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前的。這種思想的交鋒和砥礪(并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陳說(shuō)),使當(dāng)代西方思想文學(xué)理論、政治話語(yǔ)和文化研究著實(shí)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而與此同時(shí),他們激進(jìn)的理論也在悄悄地修正著自己,在時(shí)隔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來(lái),原先激進(jìn)的理論鋒芒早已所存無(wú)多。德里達(dá)本人就是一個(gè)最能說(shuō)明問(wèn)題的例子。正像德里達(dá)自己反復(fù)咀嚼的那句“文外一無(wú)所有”所隱含的意思一樣,“解構(gòu)”也是斷然不能跳到西方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之外進(jìn)行的。到了80年代之后,德里達(dá)的“解構(gòu)”也許已經(jīng)明確地定格為一種堅(jiān)持思想自由、探索意義之可能性的方法。也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他在1993年發(fā)表的《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ofMarx)中,心悅誠(chéng)服地承認(rèn)自己也屬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
這些年,德里達(dá)已沒(méi)有什么足以引起學(xué)術(shù)界轟動(dòng)的力作發(fā)表,但他一如既往地在人們視而不見(jiàn)的各個(gè)思想接口處自由地思考著、求索著。要說(shuō)“解構(gòu)”,這也許就是真正的“解構(gòu)”。1994年10月,他來(lái)到美國(guó)費(fèi)城附近的維拉諾瓦大學(xué),這是一所基督教圣奧古斯丁教派創(chuàng)立的相當(dāng)老派的大學(xué)。德里達(dá)像使徒傳道一樣,向那里的幾位被他稱之為“非常重要的哲學(xué)家”的教授傳授“解構(gòu)的精義”(deconstructioninanutshell)。在這次講話中,德里達(dá)即已明確無(wú)誤地?cái)[出了回歸傳統(tǒng)的姿態(tài)。他說(shuō)“解構(gòu)”從來(lái)就是把學(xué)術(shù)體制、學(xué)術(shù)良心放在第一位,從來(lái)沒(méi)有對(duì)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和體制發(fā)起攻擊;他直言不諱地稱自己是一個(gè)“保守的人,熱愛(ài)傳統(tǒng)體制的人”;他說(shuō)是一些報(bào)刊的壞記者對(duì)他進(jìn)行了歪曲,說(shuō)他不尊重閱讀文本,然而他對(du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偉大典籍”從來(lái)都是充滿敬意,根本不像他們所說(shuō)的那樣是到這些典籍中去搜尋差異和矛盾,故意找茬。總之,他再三地強(qiáng)調(diào):“解構(gòu)”不是一種從外部引入的機(jī)械的辦法,而是文本中本來(lái)就存在的,說(shuō)到底是文本自行解構(gòu)(注:SeeBrianVickers,“DerridaandTLS”,TimesLiterarySupplement,Feb.12,1999.)。
對(duì)于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理論也一樣,如果直到現(xiàn)在仍停留在吉爾茲(CliffordGeertz)的“深描”說(shuō)到福柯的“歷史斷層”說(shuō),仍然在格林布拉特的“商討”(negotiation)、懷特(HaydenWhite)的“歷史為話語(yǔ)的建構(gòu)”說(shuō)以及芒特羅斯(L.A.Montrose)的“文本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本性”等概念上兜圈子,那就太沒(méi)有意思了。這種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從20世紀(jì)80年代經(jīng)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羅斯、伽勒赫(CatherineGallagher)等英國(guó)文藝復(fù)興研究學(xué)者之手,形成了一種博學(xué)、高雅而且充滿機(jī)智的批評(píng)寫作,在此后幾乎整整一代人的時(shí)間內(nèi),模仿者蜂起,卻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對(duì)這樣一種批評(píng),現(xiàn)在看來(lái),它其實(shí)主要并不是一個(gè)理論的問(wèn)題,而是如格林布拉特從一開(kāi)始就始終堅(jiān)持的那樣,它主要是一種批評(píng)實(shí)踐。為弄懂這批新歷史主義的批評(píng)家何以以這樣一種方法來(lái)看待和重構(gòu)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文本,我們或許是需要化一點(diǎn)時(shí)間來(lái)探討一下他們的認(rèn)識(shí)假設(shè),他們所采取的批評(píng)方法的理由和具體的做法,但要說(shuō)這里面有多少理論深度,則實(shí)在說(shuō)不上。相反,如果像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只把它當(dāng)作個(gè)理論問(wèn)題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末倒置了。而實(shí)際的情況是,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即使是在實(shí)踐的層面上,對(duì)于這一批評(píng)的批評(píng)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倫比亞大學(xué)專門研究莎士比亞的凱斯坦(DavidScottKastan)教授發(fā)表《理論之后的莎士比亞》一書(shū),對(duì)所謂“過(guò)了景”的新歷史主義提出了相當(dāng)激烈的批評(píng)。他聲稱新歷史主義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過(guò)去,說(shuō)這一批評(píng)是屬于上一代的、業(yè)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義的插曲,而現(xiàn)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歷史,因此不再有用”;他還說(shuō)這一批評(píng)所慣用的“軼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他希望看到一種“事實(shí)更加充分的歷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經(jīng)被廢止的傳統(tǒng)歷史主義的老路上。
然而幾乎就在同時(shí),格林布拉特與他的合作伙伴,新歷史主義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實(shí)踐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PracticingNewHistoricism,2000)回應(yīng),與他們當(dāng)年的立場(chǎng)一樣,格、伽二人仍堅(jiān)持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不是理論,而只是一種批評(píng)“實(shí)踐”。新老兩派的爭(zhēng)論,一時(shí)間又給人以新歷史主義依然寶刀不老的印象。去年,我撰寫過(guò)一篇題為《新歷史主義還有沖勁嗎?》的短文,報(bào)道了英國(guó)資深批評(píng)家克爾莫德(FrankKermode)在《紐約書(shū)評(píng)》上發(fā)表的對(duì)兩本新歷史主義新著的長(zhǎng)篇評(píng)論(注:此文發(fā)表在《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2001年第4期的“動(dòng)態(tài)”欄中。克爾莫德的文章題為《廢墟上的藝術(shù)》,見(jiàn)《紐約書(shū)評(píng)》(NewYorkReviewofBooks)2001年7月5日。)。克爾莫德本人也是專治文藝復(fù)興文化史的大家,因而這場(chǎng)“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大戰(zhàn),為我們了解美國(guó)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的現(xiàn)狀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對(duì)于凱斯坦對(duì)新歷史主義的批評(píng),克爾莫德似乎并不領(lǐng)情。因?yàn)樵谒磥?lái),這位凱斯坦所使用的話語(yǔ)仍然充滿了新歷史主義和其他時(shí)新理論的術(shù)語(yǔ),而一旦離開(kāi)這些術(shù)語(yǔ),他的一套批評(píng)就寸步難行。與某些新歷史主義者一樣,他也把他們之前的歷史稱作“實(shí)證主義”、“無(wú)理論依托”一類,認(rèn)為“傳統(tǒng)的歷史主義都簡(jiǎn)單地以為它們的建構(gòu)是對(duì)過(guò)去清晰明了、客觀公正的表述,沒(méi)有受到考察者興趣傾向的過(guò)濾”。但這一句“露怯”之語(yǔ)使克爾莫德發(fā)現(xiàn),凱斯坦的參考書(shū)目中居然連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里(W.B.Gallie)這樣的歷史學(xué)大家也不曾提及(筆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歷史是一門人們?cè)谧约旱男撵`里重新體驗(yàn)往事的學(xué)科;歷史學(xué)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動(dòng),在自己的經(jīng)驗(yàn)范圍內(nèi)重新思索過(guò)去,才能發(fā)現(xiàn)各種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動(dòng)態(tài))。克爾莫德于是不無(wú)諷刺地說(shuō),他倆的論著《歷史的觀念》和《哲學(xué)與歷史理解》分別發(fā)表于1946年和1964年,對(duì)于當(dāng)下的現(xiàn)代思想家們來(lái)說(shuō),這些著作或許已過(guò)于陳舊而使他們興趣杳然,而這樣一疏忽,他們也就能把歷史撰寫要受考察者的興趣和先定假設(shè)的影響說(shuō)成是他們自己的發(fā)現(xiàn)了。
克爾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為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的理論依據(jù)又做了一點(diǎn)墊補(bǔ),他們?cè)谧约盒轮皟烧聦?duì)該批評(píng)本身所作的論述中,又增加了德國(guó)18世紀(jì)哲學(xué)家赫爾德作為他們的先師,是赫爾德最早明確指出了“文學(xué)與歷史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啟發(fā)了他們開(kāi)始關(guān)注“把所有有關(guān)某特定文化的書(shū)寫的和視像上的記錄看成是一個(gè)同一的符號(hào)系統(tǒng)”的可能性,因而過(guò)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來(lái)支撐對(duì)所關(guān)注的某特定文化現(xiàn)象(例如莎士比亞的一部劇作)的闡釋。例如蒙田的一則兩女成婚的記錄,即被格林布拉特作為闡釋莎劇《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裝現(xiàn)象的佐證;而19世紀(jì)美國(guó)浸禮會(huì)雜志的一則關(guān)于父親嚴(yán)懲任性子女的記錄,則被追溯到莎士比亞時(shí)期英國(guó)的孝悌準(zhǔn)則,并作為分析《李爾王》一劇中李爾與女兒之間關(guān)系的旁證。格、伽二位在他們的新著中仍按這一既定的套路,例如把15世紀(jì)荷蘭畫(huà)家約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領(lǐng)圣餐禮》的油畫(huà)與另一位大畫(huà)家烏切洛的作品在圣餅處理方式上進(jìn)行比較,認(rèn)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餅被故意處理成空白,并進(jìn)而認(rèn)為,這種特殊的再現(xiàn)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會(huì)內(nèi)的不同教義之爭(zhēng)。克爾莫德對(duì)格、伽二位的這一得意之筆進(jìn)行了再審視。但他一針見(jiàn)血地指出: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這種任意從文化背景中尋求論證的做法,向來(lái)就為人所詬病。他們從成千上萬(wàn)的可能性中任意挑選出能為己所用的“閃光細(xì)節(jié)”,并不是這些細(xì)節(jié)本身會(huì)發(fā)光,而是因?yàn)樗鼈兡芘c早已存在于他們頭腦中的一個(gè)想法“發(fā)生共鳴”。那個(gè)想法太誘人了,它能使作者跑到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和神學(xué)思想的網(wǎng)絡(luò)中任意穿行。然而,克爾莫德強(qiáng)調(diào)指出,令人激動(dòng)的東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討論范·金特的畫(huà),卻只字不提那油畫(huà)由于年久而畫(huà)面破損、圣餅處的油彩剝落而造成了空白這一簡(jiǎn)單的事實(shí),這恰好反映了新歷史主義者寧愿拒絕實(shí)在的歷史事實(shí)而愿意遷就幻想的心理傾向。一直到文章的結(jié)尾,克爾莫德仍對(duì)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窮追猛打,他語(yǔ)氣尖刻卻充滿睿智地指出,新歷史主義追尋事實(shí)的興趣固然值得贊許,然而“理論”卻給了它胡說(shuō)八道的權(quán)利,因?yàn)楝F(xiàn)在的“事實(shí)”早已是“文本”與“語(yǔ)境”的交織,人們于是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都與他們談?wù)摰脑掝}相聯(lián)系,這樣做的結(jié)果使大量的聰明才智和學(xué)術(shù)努力都白白地浪費(fèi)了,而文學(xué)作品本身,卻像1642年清教主義的英國(guó)議會(huì)勒令在所有劇院門口掛上“不得入內(nèi)”的牌子一樣,被剝奪了審美關(guān)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無(wú)法對(duì)所有的理論派別一一涉及,但情況可以說(shuō)是大同小異,“理論熱”的消退已斷然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個(gè)事實(shí)。然而還有另一個(gè)不容忽視的事實(shí),這就是我們經(jīng)過(guò)這一番“理論的洗禮”之后,則再也無(wú)法回到前理論的純真時(shí)代了。也正因?yàn)檫@個(gè)緣故,對(duì)于理論的反思是絕對(duì)必要的,惟如此,文學(xué)研究才能像鳳凰涅pán@①一樣,從理論的煙灰中再一次地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