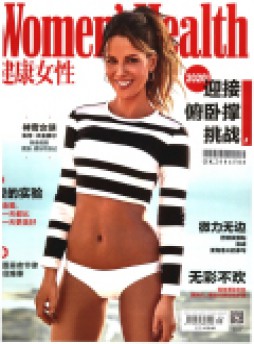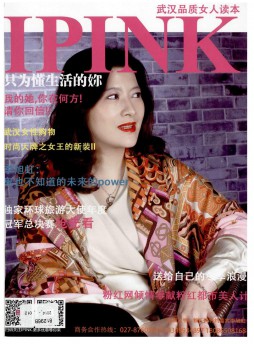女性小說疾病敘事及其倫理選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女性小說疾病敘事及其倫理選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摘要: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中出現不少疾病敘事現象,疾病敘事是作家鋪展故事倫理線索、建構復雜人物關系與情感扭結的有效手段。這些女性作家的疾病敘寫和藝術實踐,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中值理論”、中世紀奧古斯丁等人的宗教倫理學、新教改革派倫理學以及英國功利主義倫理學思想理念等具有一定的淵源關系。疾病敘事可以見出女性作家倫理意識與倫理選擇的時代性、混融性與交互性,亦可反觀19世紀倫理觀念及倫理實踐之明顯局限,在性別、階級、宗教、科技等層面,具有悖反性、雙重性、神秘性、自反性等特征。
關鍵詞:疾病敘事;女性小說;倫理結;倫理選擇;倫理意義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后期,英國社會出現了一批令人矚目的女性小說作家,如簡·奧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瑪麗·雪萊、蓋斯凱爾夫人以及喬治·艾略特等。她們的小說創作從中產階級的客廳莊園到都市里的平民生活,從哥特式的古堡、怪物描摹到現實歷史題材的挖掘呈現,構成了英國文學史上一道奇麗的文學風景線,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與探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其小說文本疾病敘事及其相關倫理問題的探究,學界雖有涉獵,但迄今尚未發現較為系統的耙梳與闡析。因此,本文擬聚焦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特別是在英國文學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女性小說作品中的疾病敘事,對女性小說家復雜多元的倫理理念、其筆下人物面臨的多重倫理困境以及艱難的倫理選擇進行觀照詮釋,從而探析其小說所承載的道德訴求與倫理意義。
一、疾病敘寫:疾病類型與倫理結
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文本涉及到各種類型的生理器質性疾病敘寫,如感冒、發燒、肺炎、肝炎、傷寒等。一般性的器質性病癥本身不是本文研究的重心,筆者側重探討的是引起主要或者眾多人物關注,促成人物性格發展,且彰顯人物道德意識與倫理觀念,締結或者解構某類倫理結的疾病敘寫。疾病類型主要有生理疾病、心理疾患、變形怪胎與漫畫式疾患等。而此類敘寫,涉及到一些常見的疾病類型與關鍵的倫理結。奧斯丁在《傲慢與偏見》中曾寫到吉英的感冒,病癥是喉嚨痛和頭痛。雖說只是小病痛,但對此病痛的反應,則可以燭察周邊人物的倫理觀念與情感態度。《理智與情感》中寫到了瑪麗安發燒,后來確診為斑疹傷寒。這個患病的過程,同樣牽動了周邊的主要人物,如瑪麗安的姐姐埃莉諾、暗戀瑪麗安的布蘭頓上校,以及移情別戀的負心郎威諾比。同樣地,蓋斯凱爾夫人在《露絲》中寫到了詹妮的“病痛”、“咳嗽”與小鎮的傷寒。不過,在這里,傷寒成了一種大面積流行的瘟疫。《呼嘯山莊》也寫到了感冒、咳嗽、肺癆;《懷爾德菲爾山莊的房客》則寫到海倫丈夫的墜馬以及之后的發燒與患病等。除了一般的感冒、發燒、傷寒外,19世紀的女性小說文本還涉及到一些遺傳性疾病。如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說《簡•愛》中,瘋女人伯莎·梅森便是一位遺傳性疾病患者。這個牙買加富裕家族的女繼承人,變身為被囚禁在閣樓上的“丑惡的吸血鬼”,長著“蓬亂的長發”,“嘴唇又腫又黑”,“額頭上有著深深的皺紋”,“寬闊的黑眉毛豎起在布滿血絲的眼睛上”(C.Brontë,JaneEyre311),變成了一頭“野獸”,一只“鬣狗”,匍匐在地,“抓著”“嗥叫著”(C.Brontë,JaneEyre321)。其實,19世紀女性小說中涉及精神心理疾患的作品不在少數。“要發現關于精神疾病的女性視角,我們必須求助于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日記和小說,雖然這種文學只涉及到中產階級和貴族婦女的經驗。但弗羅倫斯·南丁格爾的書信和日志,夏洛蒂·勃朗特的心理小說,瑪麗·E.布萊頓的感覺小說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女性生活歷程之危機的層面,它比維多利亞精神病醫學的解釋更加豐富,更為復雜”(肖瓦爾特41—42)。南丁格爾的論文《卡桑德拉》對中產階級女性的沉默、壓抑、病態、瘋狂與死亡現象進行了追問;布萊頓的《阿德萊小姐的秘密》中的同名主人公阿德萊小姐因為精神病最后被關進了瘋人院(肖瓦爾特53)。夏洛蒂·勃朗特《維萊特》不僅描寫了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器質性疾病,還涉及了精神心理上的疾病。露西·斯諾的心理疾病便是環境刺激壓抑生成的典型案例。露西,一個寄宿學校的教師,陰郁、消沉,克己隱忍、愁腸百結,“像一個呆在囚籠里的、死氣沉沉的遁世者”(吉爾伯特古芭427),是一個精神上無法“站立”的女子:“她﹝指貝克夫人,引者注﹞似乎放大了她身體的比例,也放大了她的衣裙。她遮蔽了我,我被藏起來了。她很了解我的弱點;她能估算出精神癱瘓癥——那種自我肯定意識的徹底欠缺——的程度,由此而來,在一件重大事件上,我就能夠承受打擊”(勃朗特526)。這是一個謙卑抑郁甚至有幻覺幻聽的孤獨女子的精神寫照。另外,《呼嘯山莊》中的希刺克利夫也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患,抑郁陰沉、行為詭異。變形怪胎的出現無疑具有更多的戲劇性元素。《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身體畸形、精神分裂。弗蘭肯斯坦夜以繼日地工作,創造了“人造人”。這是一個“龐然大物”,“一個大約八英尺高,按比例放大的巨人”,然而卻先天畸形:“他那黃色的皮膚幾乎覆蓋不住下面的肌肉和血管。他有一頭飄動的有光澤的黑發、一口貝殼般的白牙,但這華麗只是把他那濕漉漉的眼睛襯托得更加可怕了。那眼睛和那淺褐色的眼眶、收縮的皮膚和直線條的黑嘴唇差不多是同一個顏色”(Shelley45)。這個造物本來是弗蘭肯斯坦的科學夢和精神狂想曲,具有“開天辟地”和“最具智慧”的性質,他幻想自己如上帝創造亞當一樣,成為“人造人”的祖先,如今對此造物卻只有“恐懼”與“厭惡”(Shelley41—45)。對女性作家筆下的身心疾患進行觀照后,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那就是有一類疾患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疾患,只不過是女性作家在塑造人物時運用反諷手段對疾病進行的漫畫式處理,目的是昭示人物的精神心靈狀態與倫理價值取向。此類病癥在奧斯丁筆下是一類很特別也很有喜劇色彩的書寫。《傲慢與偏見》中班納特太太的“神經衰弱”便是一個經典的案例。她是一個“智力貧乏”、“不學無術”、“喜怒無常”、嫁女心切的母親,年輕時仗著貌美嫁給了班納特先生,但“只要碰到不稱心的事,就自以為神經衰弱”(Austen,PrideandPrejudice4)。《曼斯菲爾德莊園》中也有這種“準疾病敘事”。范妮的小姨媽貝特倫夫人是個典型的“富貴閑人”,“大事聽托馬斯爵士(其丈夫)的”“小事聽她姐姐的”,對兩個女兒的教育問題,“不聞不問”,剩下的就是裝模作樣地繡繡“沒有用處又不大漂亮的大件針線活,對孩子還沒有對她那只叭兒狗關心,只要對她無妨,她就由著他們”。后來,她借著身體不大舒服,住到了鄉下的莊園里,成天窩在沙發上睡眼朦朧。這是一種更嚴重的“精神癱瘓癥”(Austen,MansfieldPark50—51)。
疾病情節鏈上最具有矛盾沖突功能的事件,就構成了文本的倫理結。聶珍釗先生認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任務就是通過對文學文本的解讀發現倫理線上倫理結的形成過程,或者是對已經形成的倫理結進行解構”(20)。以此作為邏輯起點綜合考察可以發現,小說文本中疾病敘寫關涉的核心倫理結,大致有婚姻危機、臨終遺囑、宗教救贖等不同特質類型。疾病敘事聚焦某些人的病痛,由此呈現人物自身的身心狀態,周邊人物的情感態度、功利算計、宗教意識等,關涉性格塑造與倫理審視。與疾病敘寫密切關聯的倫理結,無疑可以更集中深切地展現人物的精神心靈世界。簡•愛在明晰自身與羅徹斯特的婚姻其實是重婚的事實面前,將會何去何從,就是倫理結。簡•愛在與羅徹斯特歷經周折確定戀愛關系,即將走向婚姻殿堂、享受塵世的幸福之時,突然發現羅徹斯特早已結婚、且以不法手段囚禁了自己的瘋妻伯莎·梅森。值此,簡•愛遭遇的就不僅僅是重婚障礙,更是信任危機,從而面臨著艱難的道德考驗與倫理選擇。《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麥琪與斯蒂芬、菲利普的情感糾葛中,也包含著一場愛情婚姻危機:麥琪與仇敵之子菲利普的相惜相憐(期間插入許多有關菲利普殘疾的敘寫)、麥琪與表妹未婚夫的暗生情愫,便構成了這個三角戀愛關系的最具破壞性與爭議性的倫理結。自然,在《米德爾馬契》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卡索朋的衰老與病容,以及他發病后對多蘿西婭造成的精神壓抑:多蘿西婭既震驚于視若先哲的丈夫卡索朋的偏狹、脆弱、多疑,亦糾結于對自己感受與判斷的質疑。不幸婚姻的種子也就在這種疾病敘寫的敷設中徐徐生根發芽了。《米德爾馬契》寫病中的費瑟斯通故意以遺囑為誘餌,達到對圍繞在其周邊的親屬們的愚弄與支配目的的行為,亦構成了核心倫理結。這個倫理結的解構,即遺囑真相的公開。費瑟斯通兇悍狡黠、吝嗇冷酷,對遺囑內容秘而不宣,誰也不知道他的遺囑會是什么樣子的,又全都不甘心分不到一杯羹。于是,匪夷所思的表演夸張上演:這些人天然是不會忘記血緣關系的,現在老人臥床不起,他們更是紛紛登門請安,人數也顯著增加了。這并不奇怪,因為當可憐的彼得坐在鑲護壁板的客廳里他的扶手椅上的時候,各種殷勤的小爬蟲雖然把這個家看作他們理應朝拜的圣地,廚師卻只給他們準備一杯白開水,他們并不受歡迎。(Eliot575)直到最后,覬覦者兩手空空、暗自嗟嘆(一眾親友);淡泊者無牽無掛,我行我素(瑪麗·高思);失落者撫平創傷、砥礪前行(弗雷德)。因而遺囑的宣告與真相的揭示,亦是倫理結的最后敞開與倫理線的合理發展。小說中也有以宗教救贖為核心構建的倫理結。蓋斯凱爾夫人小說《露絲》中同名主人公露絲的失身見棄、隱姓埋名,就是一個倫理結。當小鎮上的人知道她的道德污點后,紛紛疏遠她,甚至侮辱、踐踏她的人格。傷寒癥的流行便成為倫理結解構的一個契機:露絲毅然選擇在醫院擔任護理傷寒病人的護士,成為拯救眾人的“天使”、一個“道德新人”,最終以自身的死亡成為獻祭的“犧牲”。露絲在奉獻自我中實現了道德超越,也重建了被他人信任與關懷的倫理新秩序。這個洗滌自身、懺悔贖罪故事的展開過程,便是倫理結解構的衍進過程。同理,《懷爾德菲爾山莊的房客》中也設計了類似的倫理結:海倫離家出走惹得流言四起,回鄉服侍荒淫無度、病重在身的丈夫,恪守宗教倫理,以善行與稍顯嚴謹刻板的基督徒義舉獲得馬卡姆與周圍人的深層次認同,成為解構婚姻危機與締結新的倫理關系的轉捩點。瑪麗·雪萊的小說倫理結則肇始于科技異化下科學怪物的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的對抗性矛盾。弗蘭肯斯坦“從白骨間采集骨殖,用褻瀆的手指攪動了人體結構的天大秘密”(Shelley43),從解剖室和屠宰場尋求合成“人造人”的細胞與組織,以嶄新的科技手段制造了“人造人”怪物,卻無法滿足其基本的人倫情感需求,令其陷入倫理身份的痛苦與焦灼之中不能自拔,形成整個故事倫理結構中最核心的矛盾沖突——獸性與人性的激烈沖突。怪物天生丑陋畸形卻有一顆善感柔嫩的心。不難發現,在自我懷疑與自我追問的漩渦中走向瘋狂與毀滅的怪物,正是作家倫理思考與道德審問的文學表達。
二、疾病敘寫方式與隱喻功能構建
明確了疾病敘寫內容后,我們再來辨析作家的疾病敘寫方式及其隱喻功能,以便進一步理解作家的倫理旨歸。就疾病續寫方式而言,19世紀女性小說家中采用限制敘事視角較多的當屬勃朗特三姐妹。讓人印象深刻的疾病敘寫,在《簡•愛》一書里有兩處:一處是海倫·彭斯罹患肺炎死去,另一處就是伯莎·梅森的瘋狂章節,采用的都是“我”——簡·愛——的視角來觀察敘事的。《懷爾德菲爾山莊的房客》也采用了限制視角,以書信體與日記體敘事、連綴成書。海倫看顧病重丈夫亨廷頓的事件,是以海倫寫信給自己弟弟的方式,被其弟之好友亦即自己未來戀人馬卡姆獲悉的。《呼嘯山莊》里小希刺克利夫身體孱弱、經常咳嗽、發燒,他與凱瑟琳·林惇的交往,則經由女仆耐莉以第一人稱敘事加以交代。《弗蘭肯斯坦》選擇的是以書信文體前后編綴,采用第一人稱三重視角:第一重視角是事件的旁觀者R.華爾頓;第二重視角是弗蘭肯斯坦,他對自己制造“人造人”的經過以及災難性后果進行敘述;第三重便是怪物的視角。這樣的設計既有著第一人稱視角的近距離和可信度,又適當彌補了限制視角的局限性,從不同角度聚焦怪物與相關人物,令讀者獲得更多有效信息。此類限制性視角的選擇有效增強了疾患敘寫的真實性和現場感,類似于電影鏡頭中的“即視感”。奧斯丁、蓋斯凱爾夫人以及喬治·艾略特則更多使用零度聚焦敘事。《米德爾馬契》中獨具特色的疾病敘事,頗值得一提。其作者艾略特匠心獨運,以瑪麗·高思的視角“觀察”老費瑟斯通周邊的財產覬覦者。瑪麗·高思既是老費瑟斯通的親戚,又是他的家庭女工,既是護理者又是傳令官。盡管身份卑微,但對覬覦財產的那些人來說,她又是一個需要結交和攀附的對象。而瑪麗·高思就像作家安插的一名偵察員,她對大大小小、親親疏疏的探望者的心理了如指掌,對病者的癖好、冷酷與狡黠也是洞若觀火。有意思的是,艾略特在對后來的遺囑宣布會的描敘中,依然讓高思占據著這個“觀察者”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瑪麗·高思。在大家目不斜視、正襟危坐的時刻,她正可以趁此機會觀察所有的人。聽到‘茲將遺產分配如下’時,她看見每一張臉都發生了不易覺察的變化,仿佛有一條微弱的電流從它們上面掠過”(Eliot596)。面對遺囑宣告,咒罵的、嚎啕大哭的、啜泣的、臉色蒼白的、無動于衷的〔……〕合成一幅人性百態圖。作者巧妙地將這些“小爬蟲般”的“低級人物”置放于此,表達其對金錢異化人心,親情倫理淪喪的深度憂思。不同的視角選擇,共同完成了作家對角色倫理選擇的觀照與審視。就疾病敘寫的頻次與篇幅而言,筆者通過對翻譯文本的閱讀與不完全統計發現,19世紀英國女性作家筆下或多或少均涉及了疾病敘事,但不同作家涉及的疾病類型,描寫的篇幅、頻次還是有較大差異的。例如《呼嘯山莊》(楊苡譯本)涉及“病”123次,“醫生”23次,“病人”10次,“病情”3次,“病痛”2處,“感冒”2處,“發燒”5次,“熱病”3次,“發狂”7次,“肺癆”2次,“咳嗽”10次;《阿格尼斯•格雷》(薛鴻時譯本)涉及“感冒”3次,“發燒”3次,“抑郁”3次;《懷爾德菲爾山莊的房客》(蓮可、西海譯本)涉及“病”12次,“發燒”12次;《傲慢與偏見》(王科一譯本)涉及“病”53次,“病人”8次,“病情”4次,“神經衰弱”3次;《理智與情感》(武崇漢譯本)涉及“病”88次,“病情”12次,“病人”11次,“感冒”4次,“發燒”1次,“傷寒”2次,“抑郁”5次;《曼斯菲爾德莊園》(孫致禮譯本)涉及“感冒”1次,“發燒”3次,“病情”13次,“病人”5次;《諾桑覺寺》(金紹禹譯本)涉及“患病”1次,“病人”1次;《勸導》(裘因譯本)涉及“病”61次,“病人”6次,“感冒”3次,“傷勢”2次,“感染”3次;《弗蘭肯斯坦》(劉新民譯本)涉及“怪物”32次,“瘋狂”13次,“憂郁”19次;《米德爾馬契》(項耀星譯本)涉及“病”335次,“醫生”160次,“醫院”116次,“病人”69次,病情18次,病癥2次,“醫療”30次,“醫療改革”2次,感冒1次,發燒1次,傷寒6次,熱病13次,斑疹傷寒1次,“歇斯底里”1次,抑郁2次等。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在英文中“病”有多種翻譯方式,為相對精確計,此處均以中文表達為依據進行統計,選取對象亦多是19世紀英國文學史上比較優秀的小說文本。數據顯示,“感冒”、“發燒”等一般病癥,幾乎在所有列入考察的小說文本中都會出現,而傷寒、斑疹傷寒這樣的比較兇險的病癥就只在《理智與情感》《露絲》《米德爾馬契》等文本中出現,尤其是《米德爾馬契》涉及的次數比較多,因為男主人公利吉蓋特就是一名具有先進醫學理念,擁有改革抱負的青年醫生,處理各類疾病特別是疑難雜癥是他的職責所在,醫院、醫療、病人、醫患關系、醫療改革等內容所占篇幅自然最多。疾病敘事的類型、頻次、篇幅,一方面體現了作品題材內容與思想意識的偏重,另一方面亦與作家的專業知識結構與日常疾病體驗密切相關。首先,從知識結構層面看,喬治·艾略特學識淵博,涉獵廣泛,其知識結構遠比其他女性小說家廣博深厚,在文學、宗教學、倫理學、神學、醫藥學、軍事學、歷史學等方面均有豐富儲備與理解,因之被譽為“托爾斯泰式”的女性作家。而奧斯丁、勃朗特三姐妹、蓋斯凱爾夫人、瑪麗·雪萊等人也都出身知識分子家庭,要么是牧師家庭出身,要么是名門之后。
瑪麗·雪萊的父親是政治哲學家威廉·戈德溫,母親是女權主義者、哲學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瑪麗對哲學、文學、歷史、化學學、生物學、醫學具有濃厚興趣。也即是說,女作家們對醫學藥理知識的積累與把握,導致她們在小說作品中有選擇地借助自己的知識體系以豐富其對于疾患的認知與詮釋。其次,從疾病與死亡經驗層面看,勃朗特三姐妹的母親、兩個姐姐均死于肺結核,后來艾米莉、安妮也死于肺炎。這一體驗在《簡·愛》對海倫肺癆的描寫中有所反映;三姐妹的小弟弟勃蘭威爾意志薄弱、酗酒放縱,因病而死,這一慘痛體驗在《懷爾德菲爾山莊的房客》中對亨廷頓的描寫上得到了映射。《弗蘭肯斯坦》的問世,盡管是瑪麗的藝術天賦使然,但雪萊與拜倫兩位天才詩人的哲學會話以及達爾文博士的科學實驗等,亦是催生天才之作的催化劑(Shelley4)。而母親死亡、姐姐自殺,與雪萊的感情糾葛,懷孕、疾病、孩子夭折等,都是《弗蘭肯斯坦》憂郁、感傷、崇高之基調形成的揮之不去的影響源。可以說,瑪麗·雪萊五十余年的人生一直與疾病與死亡交鋒:出生不久,母親去世;生育四個孩子,三個夭折;一次流產,險些喪命等,這些經歷都令女作家對疾病與死亡有著旁人無法企及的深刻體驗與慘痛感悟。瑪麗·雪萊將科技進入人類、人類社會導致的悲劇性后果與自身的命運多舛緊密地糅合在一起,繼而進行了生動地藝術呈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女性作家在對疾病進行敘寫時,往往會涉及到各種類型的動物意象。這些動物意象集中體現病者及其周圍人的精神人格,自然也就隱喻著不同的情感態度和倫理境界。另外,她們筆下還對女性瘋狂、科學怪胎等特殊話題深度關注,亦契合了作品內在的隱喻功能。《簡•愛》中寫到閣樓上的瘋女人出現時,以羅徹斯特的口吻,使用了“鬣狗”“狼嚎”“野獸窩”“妖怪洞”等字樣,凸顯瘋女人的兇悍與野蠻。寫到簡•愛時,羅徹斯特則親切地稱之為“女兒般親愛的小母羊”;回憶自己曾經受到簡•愛的幫助時,則充滿父親般的仁慈與袒護,稱簡•愛是“孩子氣的小巧的家伙!仿佛是一只紅雀跳到我腳跟前,提議要用它那細小的翅膀背負我似的”,并贊美它是“精靈”(C.Brontë,JaneEyre339)。不難看出羅徹斯特對伯莎•梅森的怨恨與嫌棄、對簡•愛的疼惜與愛慕。有意思的是,這種口吻是得到了傾聽者簡•愛的“默許”的。簡•愛甚至很享受這樣的稱謂。因為敘事者,也就是潛在的作者把簡•愛描寫成一個瘦弱、矮小但堅毅,富有強大心靈力量的女子,與小紅雀精靈般的存在、能夠給予羅徹斯特以支撐與幫助的情形高度契合。而在簡·愛心中,身陷窘困的羅徹斯特就如一頭正在站立起來的“喘息的獅子”,雖然遭遇了拒絕和打擊,但依然孔武有力,充滿男性的陽剛美(C.Brontë,JaneEyre343)。由此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類別的動物意象的出現,特別是在疾病敘寫的時刻,無疑預示著情感傾向與價值選擇:我們可以看出羅徹斯特與簡•愛合謀的對瘋女人的擯棄,也見出羅徹斯特與簡•愛的內在情感聯盟和互相認同。羅徹斯特將簡•愛比作精靈,簡•愛將羅徹斯特喻為“獅子”,都是美好意象,寓意肯定性情感。而“鬣狗”“狼嚎”“野獸窩”“妖怪洞”,自然都是丑惡意象,昭示否定性情感。再來審視一下《米德爾馬契》中的動物意象刻畫。弗雷德生病時,母親文西太太驚惶失措、性情大變。“她不再關心那一向顯得鮮艷華麗的衣服,成天像一只生病的鳥,眼睛沒有神,羽毛凌亂,對聽到、看到的一切,哪怕是她平時最關心的,她也覺得興味索然”(Eliot548)。可見,母愛的真摯與力度。文本中寫到老病號費瑟斯通的親友們時使用的是“各種小爬蟲”(Eliot575)。而最終獲得全部遺產饋贈的卻是一位名叫李格、長著“蛙類呆板神情”(Eliot593)的陌生人!呆板丑陋的蛙類特征,已經暗示了李格精神品性的局促偏狹。作者有意使用丑陋的動物意象,來暗示其潛藏的道德批判與倫理審視。女性瘋狂在維多利亞時代已經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歇斯底里、暈厥、厭食、瘋狂等,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小說文本中經常出現的現象,也是女性作家精神心理原發性力量的變形。毋庸贅言,桑德拉·吉爾伯特與蘇珊·古芭的《閣樓上的瘋女人》中精彩地詮釋了這種現象。就倫理維度而論,這種隱喻是男權時代的文本策略,也是對女性艱難的倫理處境的一種文學表達。她們的情緒敏感、經濟困窘、性別焦慮、職業掙扎、精神空間逼仄,都是造成以上精神心靈疾患的深層原因。①
三、疾病敘寫的倫理映射與倫理選擇
上文論及了文本中的疾病類型與書寫方式,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考察疾病敘寫所承載的不同倫理觀念,從而對時代、人物、作者等不同維度的倫理現實與倫理選擇進行辨析與檢視,以見出小說文本中倫理觀念與倫理意識的時代性、混融性與交互性。瑪麗·雪萊曾在自己作品的序言中明確提到其創作初衷,開始只是單純地想構思一個可以嚇壞讀者的幽靈故事。在后來的序言里,作者有了新的補充性說明:“我對各種情緒或性格里所存在的可以影響讀者道德傾向的東西,并非沒有注意。﹝……﹞我在這方面主要關心的還是對親情之溫馨和普世道德優越性的展示”(Shelley10)。喬治·艾略特因其作品的宏大敘事,展現了維多利亞時代充滿危機和困惑的社會現狀以及有關婚姻愛情的深度思索而被詹姆斯稱為“如此罕見的講故事的人,同時又是如此罕見的道德家”②。的確,即便是最不愿意付諸道德訴求的作家,也無法不關注親情倫理,而疾患敘寫這一特殊維度正是檢驗自身精神心靈、他人人心向度、社會關懷程度的試金石。必須指出的是,在維多利亞時代,這種倫理觀念又具有更復雜的存在樣態,是亞里士多德的“中值理論”、中世紀奧古斯丁宗教倫理、宗教改革派倫理觀念以及功利主義倫理觀念等的多向度呈現,因之,同一時代的文學文本中亦存在著不同時代倫理觀念的蹤跡。維多利亞時代女作家筆下的小說具有與亞里士多德“中值理論”相契合的“適度原則”。考察《尼各馬可倫理學》我們發現,“中值理論”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德性中強調的一個關鍵術語。“‘適度’畢竟是人類情感的一個顯然的理想狀態。亞里士多德也用中值概念來處理智慧之德性,特別是用來討論公平正義之德性。”所謂“中值”,就是“中間境界”,并非是一個精確點,而是兩級之間的一個平衡區域(布爾克24—29)。這種“適度原則”在女性小說中最明顯的體現便是奧斯丁的“有節制的憎惡”。奧斯丁小說盡管充滿睿智的反諷和對中產階級的道德批評,但她從不過分激烈地渲染情感,增強這種憎惡的個人色彩。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結局中,她寫道:“讓別人去描寫罪惡與不幸吧。我要盡快拋開這樣一些令人厭煩的話題。我急欲使每一個人,每一個沒有犯多大錯誤的人重新稍微高興起來,剛才的那類話我就不再往下說了”(Austen,MansfieldPark457)。相比于夏洛蒂·勃朗特的激越激情、艾略特的客觀嚴整,奧斯丁正是這樣一位“理性的道德批評家”。也正因為如此,在描寫吉英感冒、瑪麗安傷寒、貝特倫夫人身體不適、班納特太太神經衰弱時,奧斯丁都保持了對周邊人物的態度上的“適度”原則。彬格萊姐妹的尖酸刻薄、虛情假意,威諾比的懺悔與自辯,班納特先生的譏嘲,都控制在一定的“中值”范疇之內。難怪麥考萊先生評價奧斯丁:“奧斯丁小姐,作為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來說,是一個最危險的榜樣。﹝……﹞像她那樣去寫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不去涉及任何更高的悲劇情感和生活中更有激情的方面,她的藝術之美在于其具有逼真如畫的魅力,而同時又毫無現實中的單調乏味”(朱虹33)。自然,《曼斯菲爾德莊園》中對富貴閑人貝特倫夫人的反諷,也沒有達到令人厭憎的程度。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另一個關于快樂與幸福追求的持續性和不斷完善性的倫理觀點,在中世紀奧古斯丁的神學著作中有了一定的回響,“人的最終完善在于獲得上帝的接受”。“一個真正熱愛上帝的人,總是那么積極主動地,使自己的行為自動地與神和道德的律法相結合”(布爾克64—65)。在疾病敘事中,我們不難發現小說中人物如何虔敬上帝的內容。《懷爾德菲爾山莊的房客》里,海倫雖遭丈夫背棄而離家出走,但聽聞丈夫病重,旋即趕回悉心照顧病榻上的丈夫亨廷頓,并認為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亨廷頓卻惡狠狠地回敬說:“這是基督徒的寬容精神,由此你希望在天國為自己獲得一個更高的職位,在地獄為我挖一個更深的坑”(A.Brontë,TheTenant524)。面對怨憤和惡毒,海倫恪守基督徒的寬容與忍耐,以至于馬卡姆譏嘲海倫的做法是“在豬面前撒珍珠”③。但海倫卻“積極主動地”投身到勸善說教的基督義務中,當仁不讓地充當道德家與批評家。這些相關描寫無疑釋放出一個信息,那就是作為新教徒家庭成員的安妮,恪守自奧古斯丁以降的基督教的向善觀念。另外,女性作家的小說創作還嘗試將勸善說教與新教倫理進行無縫結合。
16世紀宗教改革后,新教脫離天主教而形成了許多宗派,主要包括英國國教、安立甘宗、歸正宗、信義宗、浸禮宗、公誼會等教派。19世紀的英國對宗教的態度是比較復雜的,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和啟蒙主義精神的熏染,存在信教與不信教之間、信教程度高低之間、國教與非國教之間的多重矛盾沖突,但也不乏宗教寬容精神。更其重要的是,新教倫理強調最大限度的節儉與節制欲望,靈魂向善。這一時代精神在維多利亞時代女作家筆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現。《露絲》一書涉及到浸禮會教徒(瑟斯坦牧師)、天主教徒(費思,瑟斯坦之姊)與國教徒(女仆薩莉)共處一室,時有摩擦但和諧共處的場景。浸禮會教徒瑟斯坦·本森牧師虔信獲得救贖不可或缺的一個條件就是善行。因之,當傷寒肆虐、人人自危時,節儉自律、素雅質樸的露絲日以繼夜、嘔心瀝血地工作,坦然穿梭于病人之間,以自己的善行“贖罪苦修”,“在疾病與災難的重圍中”顯得“美麗”“溫柔”,也讓其私生子列奧納德終因她的贖罪行為而得以“挺著腰板兒走上埃克萊斯頓的大街小巷”,人們因為膜拜露絲而善待其子(蓋斯凱爾夫人449—451)。露絲宗教救贖的老路子,雖然宣揚了仁愛、寬恕、奉獻、犧牲等崇高偉大的宗教倫理精神,但也暴露了時代與作家倫理意識的局限,那就是預設了露絲失貞即是“有罪”這一倫理結,真正的罪人貝林漢倒絲毫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約和道德拷問,顯示出倫理原則的雙重性。新教倫理意識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堅定不移的職業觀念。巴克斯特與路德都認為“職業是上帝的旨意,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并盡量將其利用起來。”“職業是上帝向人類頒布的圣旨,它命令人類要為增添上帝的榮譽而勞動,”并“將這么做視為一種責任”(轉引自韋伯146—147)。《米德尓馬契》中弗雷德在遺產期望落空后,其不得已的人生規劃,就是選擇一種自己可以從事的職業。瑪麗·高思拒絕焚燒遺囑(即第二份取消所有人財產繼承權的遺囑),客觀上成全了弗雷德的人生規劃,否則一旦弗雷德繼承了大宗財產,必然遠離誠實的勞動與自力更生。瑪麗也一直把服侍病人費瑟斯通的工作看做是自己的一份職責,并以獲取傭金養活自己,并不時可以幫補家庭而覺得充實快樂。由此觀之,瑪麗·高思的選擇不僅是獨立個性的體現,其職業觀念也是有時代的宗教倫理觀念作為強大的精神支撐的。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宗教與哲學理念也有一定程度的新變。人們在道德與功利之間融入了更多的思考與探索。在18、19世紀的英國,占主導地位的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思想。杰勒密·邊沁在其1776年發表的《論政府片斷》中宣稱:“功利是一切美德的驗證和尺度〔……〕照顧普遍幸福的義務是最高的義務,也是一切別的義務都包括在內的義務”(轉引自索利224—225)。詹姆士·穆勒等人進一步完善了這一理論體系。他們一致認為:“人類的惟一目的就是謀求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與否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閻照祥281)。這種功利意識不僅在現實生活中催發了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合理層面,也是英國小說中個人奮斗精神力量的哲學思想淵源之一。在疾病敘事中,對幸福與快樂的追尋,對財富與安逸的向往,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情形,就對應了功利主義追求的二重性:一來,可見人物的高尚目標與積極行為方式,如簡•愛、海倫、露西、露絲等的追求愛情、幸福、平等,具有奉獻精神;二來,亦窺見人物的卑俗目標與消極行為方式,如費瑟斯通、貝茨夫人、亨廷頓、貝林漢等追求權利、欲望、享樂的極端利己主義。綜上,從19世紀英國女性小說描寫的日常生理與精神心理疾患、畸變怪物、漫畫式病癥等現象入手,本文考察了疾病敘寫的類別、疾病關涉的倫理結、疾病敘寫方式及其隱喻功能,闡析了疾病敘寫的視角選擇、頻次篇幅敷設、動物意象營造,以及作者的知識結構與個人經驗等。疾病敘事是作家鋪展故事倫理線索,建構復雜人物關系與情感扭結的有效手段;在疾病面前,人物的情感心理、職業道德、宗教意識、功利欲望、社會心態等的描摹、呈現、揭示、暴露,直逼精神世界與靈魂幽微,是進行倫理檢視與拷問的極佳路徑。基于此,本文追本溯源,試圖厘清疾病敘事的倫理學哲學基礎,揭示作家藝術實踐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世紀奧古斯丁等人的宗教倫理學、新教改革派倫理學,直到英國功利主義倫理學思想理念等的淵源關系,指出疾病敘事不僅可以見出女性作家倫理意識與倫理選擇的時代性,亦可彰顯其倫理觀念與倫理意識的混融性與交互性,呈現出人類歷史進程中道德探索與倫理構建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特征,共同維系了一種相對穩定的道德水準與倫理秩序。我們也不難發現,在作家疾病敘事與倫理結構的敷設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肯定了節制、行善、責任、勞動(工作)、追求幸福、敢于奉獻等生活理念,踐行關懷倫理的人本、尊重、責任、寬容、情境原則,具有積極的倫理價值與現實意義。當然,從小說文本疾病敘事與倫理結構本身,我們亦可反觀19世紀英國的倫理觀念及其實踐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在性別、階級、宗教、科技等層面,顯示出悖反性、雙重性、神秘性、自反性等特征,表明人類行為之倫理價值與倫理意義的探求,仍有提升與完善的巨大空間。
作者:金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