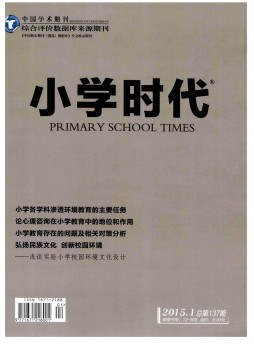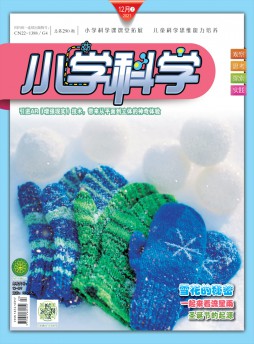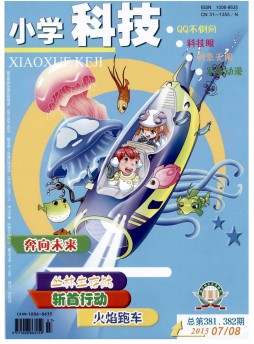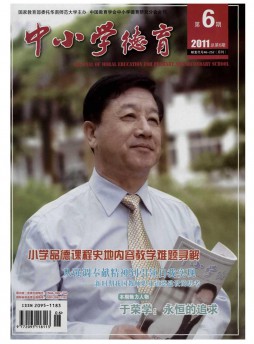小學語文教師兒童文學素養現狀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小學語文教師兒童文學素養現狀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通過對臨汾市幾所城市小學語文教師的問卷調查與個別訪談發現,臨汾市城市小學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現狀不容樂觀,主要存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知識欠缺、對兒童文學的分級分層閱讀認識不充分、缺少豐富的閱讀兒童文學作品的經驗、組織學生開展閱讀活動的能力欠缺、兒童文學創作和指導兒童創作素養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小學語文教學的效果。
關鍵詞:臨汾市;城市;小學語文教師;兒童文學素養
兒童文學素養是“人們在長期的對兒童文學進行研討、閱讀中形成的知識水平和文學藝術涵養”。[1](P.86)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是語文教師在語文教學和文學教育活動中,在長期閱讀和鑒賞兒童文學作品的過程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關于兒童文學的綜合素養。對于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的內涵,學術界并沒有統一的定論。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北京師范大學陳暉教授的論述,她認為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對兒童文學的基本情感和態度;對兒童文學的全面認識和理解;豐富的閱讀兒童文學的經驗;組織學生開展閱讀活動的能力和技巧。[2](PP.154-155)小學語文教師的教育教學對象是處于童年期的6、7歲至11、12歲的兒童,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課文80%以上屬于兒童文學的范疇。“兒童”特征對小學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提出了特殊的要求。2016年12月的我國首個國家級全民閱讀規劃———《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指出:“少兒閱讀是全民閱讀的基礎。必須將保障和促進少年兒童閱讀作為全民閱讀工作的重點,從小培育閱讀興趣、閱讀習慣、閱讀能力。”小學語文教師是少兒閱讀的引路人和指導者,小學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是少兒閱讀乃至全民閱讀的重要保障。筆者聚焦臨汾市城市小學,對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展開調研。在設計調查問卷和訪談問題時,筆者從小學教師專業標準的三個維度,參考陳暉教授關于語文教師兒童文學素養內涵的論述,緊扣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學的結合點,在山西省臨汾市的四所城市小學(臨汾市第一小學、堯都區南街小學、解放路小學、五一路學校)中,選取一至六年級的語文教師作為調研對象。本次調研主要采取個別訪談、座談討論與問卷調查的方式,共發放調查問卷214份,回收有效問卷214份,回收率為100%。
一、兒童文學基本理論知識欠缺,對兒童文學的認識不全面、不深刻
訪談中,受訪教師一致表示兒童文學對于小學語文教學非常重要。首先是兒童文學理論知識,教師在教學中都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的遺憾,尤其是在兒童詩、散文、科學小品文等非敘事性課文的教學中,找不到作品的切入口,且對于敘事性作品,如兒童故事、童話、寓言故事之間的異同也很難把握。筆者跟受訪教師一起觀看了薛法根老師的《霧凇》教學錄像。討論中,受訪教師都對薛法根老師精準把握文體特點的兒童文學素養大為贊賞,然而自己在教學中很少有這樣的兒童文學的文體意識,因此不能還原《霧凇》一文的文學特征,更不能以讀促寫,啟發學生根據自己的生活和情感需要,用恰當的語體、文體進行書面表達。由此可見,受訪教師只認識到兒童文學素養之于小學語文教學的重要性,而沒有真正掌握兒童文學理論知識。從被調查的小學語文教師的學歷情況來看,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占42.4%,大學專科學歷占50.5%,中專學歷占7.1%,后取本科、專科學歷的教師占38%。其中只有8.8%的教師在入職前系統地學過兒童文學這門課程,他們大多是新入職的教師,工作年限不超過五年。而28.2%的教師則表示完全沒學過。從這個統計中可以看出,高等師范院校兒童文學的課程建設并不理想,不能滿足基層實際教育教學的需要。筆者在訪談中得知,教師對兒童文學理論的了解大多是通過自學,在教學中不斷積累。在職后進修中,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教師對兒童文學的學習只能做到粗略了解,很難全面系統地學習。調查中,對“兒童文學的主要特征有哪些”的回答多集中在“篇幅短小”“朗朗上口”“淺顯易懂”等表象特征上,教師對“童心”“童趣”這個本質特征的理解不深刻。在“你認為兒童文學對兒童的成長有哪些作用”的調查中,答案集中在“拓寬知識面”“思想品德教育”兩個方面,而很少有教師能從“豐富兒童的精神世界”“培養兒童的文學藝術趣味”“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與閱讀習慣”“對兒童的心理撫慰”等方面,深入理解兒童文學對兒童成長的作用。這與多年來應試教育的大背景相關,也說明教師的教育觀念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筆者在訪談中發現,某小學低段學生的閱讀書目中同時安排了《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教師們只知道二者都是兒童文學經典,并沒有意識到民間童話與個人抒情童話的本質區別,以及它們分別適合哪個學段,也不能從童話發展的角度去認識二者各自的文學價值。可見,小學語文教師對兒童文學的認識還停留在淺表層面,認識是模糊的、片面的,兒童文學理論素養是欠缺的。
二、對兒童文學與兒童年齡特征的關系認識不明確,對兒童文學的分級分層閱讀認識不充分
兒童是發展中的人,兒童文學緊扣兒童年齡特征,從兒童的認知水平、語言思維發展、人格氣質形成等角度出發,符合兒童的閱讀興趣和接受能力。兒童文學的閱讀應該是分級分層的,有明顯的階段性,這與小學語文教學的階段性是相契合的。兒童文學分級閱讀,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下稱《課程標準》)中體現為分學段閱讀。筆者在對低、中、高三個學段學生適合閱讀的兒童文學文體的調查中發現,對于“適合低段小學生的兒童文學的文體”,教師們基本能夠定位在兒歌、童謠,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上,這與《課程標準》低段閱讀目標中提到的文體相一致。在“適合中段小學生的兒童文學的文體”“適合高段小學生的兒童文學的文體”的調查中,答案則較為混亂,這與《課程標準》中段、高段閱讀目標中提到的敘事性文體、說明性文體概念相一致,究其根本還是教師對兒童文學的文體及特征認識不清。近些年,受國外分級閱讀的影響,我國的分級閱讀研究出現了飛躍式的發展,建立了一大批分級閱讀研究中心和機構,一大批兒童文學作家和研究者、語文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兒童心理學家、閱讀推廣人和出版人積極參與,分級閱讀的分級標準、書目以及評價體系等分級閱讀的基本理論已經建構起來。筆者在訪談中了解到,教師們對當前最有影響力的由新教育研究院、新閱讀研究所研制的“中國小學生基礎閱讀書目”,由親近母語研究院研發,并經梅子涵、朱自強、彭懿、談鳳霞等兒童文學專家審定“小學生分級閱讀書目”知之甚少。在“你能為低、中、高三段的小學生設計一個閱讀書單嗎”的調查中,教師們基本上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只有關注過小學生閱讀書目的教師才有自信。朱自強依據小學階段兒童語言、心理發展的狀況,總結了體現語言形式、文體形式的次序、規律、結構的五項原則:從口語到書面語;從韻文到散文;從“故事”到“情節”;從“形象”到“意象”;敘事在先,寫景、抒情、議論在后。[3](PP.39-42)訪談中筆者向教師們推薦這篇文章,受訪教師一致認為,這篇已經發表四年的文章于他們就像是一盞剛剛點燃的明燈,讓他們對小學語文學習的階段性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三、缺少豐富的閱讀兒童文學作品的經驗,閱讀量有限
兒童文學作品的閱讀量,直接影響小學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大量閱讀中外不同文體的兒童文學作品,不僅能讓小學語文教師具體感知各種文體的兒童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提高他們對兒童文學作品的審美鑒賞能力,還能拓展他們的知識文化視野,并進一步了解小學不同學段兒童的心理。但從回收的調查問卷中可以看出,教師們的閱讀情況并不樂觀。100%的教師有閱讀兒童文學作品的愿望,但經常閱讀的教師卻只占到17%,“偶爾翻看甚至不讀”的教師比例高達83%。訪談中,對于兒童文學作品的閱讀,教師們也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多年的語文教學經驗告訴他們閱讀兒童文學作品十分重要,他們也有強烈的閱讀意識和愿望,尤其是那些自己孩子正在讀小學的教師;而實際生活中,由于教學任務繁重、時間緊張、缺少資源等原因,教師們真正認真閱讀過的兒童文學作品十分有限,沒能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據統計,小學語文教師偏向閱讀中外著名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更重視富有文學性和思想教育性的作品,相對排斥游戲、漫畫、冒險、懸疑類的作品,對當下非常熱門的“米小圈系列”“植物大戰僵尸”系列等了解不多,也不支持學生閱讀。由此可見,語文教師對兒童文學作品的閱讀不能與時俱進,也不了解兒童的閱讀口味,很少關注新出版的圖書和專家的推薦書目。在“你的兒童文學藏書量”調查中,只有1.3%的教師擁有較多的兒童文學藏書。“兒童文學在你的藏書中所占的比例”調查顯示,占20%以下的教師達90%以上。訪談中,筆者留心觀察教師們的辦公桌,堆滿桌子的是學生的作業、作文本,而書架上,幾乎都是教學用書,很難看到兒童文學作品。可見,無書讀,不讀書,已經成了小學語文教師的生活常態。在“你熟悉的兒童文學作家”調查中,排在前面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兒童文學作家:安徒生、曹文軒、楊紅櫻等,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的兒童文學作品的作者如金波、孫幼軍、許浪、薛衛民等也有列舉,而那些具有世界性影響、獲得安徒生獎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家如《洋蔥頭歷險記》的作者賈尼·羅大里、《長襪子皮皮》的作者阿斯特麗德·林格倫等卻少有人提及。在“你熟悉的兒童文學作品”調查中,對于問卷列舉的十部兒童文學作品,有教師最多選擇五部,還有三位教師一部都沒選,訪談中讓教師列舉出熟悉的兒童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丑小鴨》《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語文教材中的課文,有的籠統地列舉出《中國寓言故事》《中國神話故事》等小學語文教材中選文較多的經典。筆者針對《金色的草地》提出一些問題,但幾乎沒有教師了解普里什文和他的大自然文學,這篇以外的美文也無人知曉。可見,小學語文教師的閱讀受囿于各種主客觀因素,閱讀視野局限于課本,真正的閱讀還沒有在教學中展開。
四、組織學生開展閱讀活動的能力欠缺
《課程標準》中要求小學階段的學生課外閱讀總量不少于145萬字。如果按照每本書8萬字算,小學六年還不足20本書,平均每年不到4本書。與平均每年每人讀書最多的民族猶太人的64本和平均每年每人讀書最多的國家美國50本、日本40本等相比,對小學生閱讀總量的要求還可以再提高些。而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有效的閱讀,必須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和掌握多元的閱讀策略和方法,這就對小學語文教師的閱讀指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要給學生推薦適合他們理解、接受、符合他們審美趣味的優秀兒童讀物,還要在具體的閱讀活動中給予學生閱讀策略和方法的指導。調查中筆者看到,這幾所學校都有圖書室,有的學校還有專門的閱覽室,不少教室還布置有班級圖書角,可以說學校良好的閱讀環境為學生的閱讀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訪談中,許多教師表示自己組織學生開展閱讀活動的能力欠缺,受自己閱讀經驗的局限,學生的課外閱讀沒能落到實處。在“晨讀時間讀什么”的調查中,讀“自己或學校專門選編的內容”只占24.4%,大部分教師選擇“語文課本中的內容”。在“是否在班里定期舉辦讀書活動”的調查中,“每學期一次”占63.2%,“每月一次”占24.4%,“每周一次”占11%,“每天都有讀書作業”只占1.4%。從“你能駕馭的讀書活動”一題收集到的信息看,大部分教師選擇“班級讀書會”“朗誦比賽”“你講我聽”“我是小書蟲讀書比賽”等形式,而對教師要求比較高的、有創意的活動,如“為名著寫書評”“書本劇表演”“師生共讀一本書”等很少有教師愿意嘗試,至于綜合性較強的“閱讀文化節”“人文自然科學閱讀”等活動,則沒有教師選擇。在“你是一個小學生閱讀的推廣人嗎(能傳遞閱讀價值觀念,幫助小學生培養必需的閱讀興趣與純正的閱讀品位,獲得閱讀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等。)”調查中,只有5.6%的教師有這種責任感和自信心。筆者在訪談中了解到,向學生推薦兒童文學作品時,教師更看重“有用”和與語文教學“有關”的一些兒童讀物,要么是根據語文教材內容拓展閱讀,要么根據教師自己的閱讀經驗進行推薦,而不能從兒童的視角、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兒童的閱讀,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大多數教師對學生的課外閱讀指導沒有具體的計劃,從書目的選擇、方法的指導到深入討論,都沒有制定合理的讀書活動方案,而是視情況隨機進行,這又反映出閱讀活動的隨意性,很難落實到每個學生閱讀能力的提高上。
五、兒童文學創作和指導
兒童創作素養不足寫作是一個人表達思想、抒發情感的一種方式。小學的寫作教學目標,不是為了培養作家,而是幫助學生獲得一個社會人必備的基本生活能力。小學語文教師不必是一位作家,但必須有良好的寫作習慣,嘗試過各種文體、各種風格的寫作練習,能為學生提供優秀的示范,還要在學生寫作的精要之處給出到位的講解和指導,讓學生能意識到自己寫作中的問題所在,在不斷的修改中實現相對完美的表達。在“你有堅持寫作的習慣嗎”的調查中,只有12.3%的教師選擇“有”。在“你認為語文教師在作文教學中應該寫‘下水文’嗎”的調查中,只有34.3%教師認同小學語文教師在作文教學中親自試水。在“你進行過哪些文體的寫作練習”的調查中,筆者列舉了小學階段語文教材中可能出現的五大類文體:(1)韻文體:兒歌、兒童詩;(2)敘事體:兒童生活故事、童話故事、歷史故事、寓言故事、教育故事、兒童小說、幻想小說;(3)散文體:兒童寫景狀物散文、兒童寫人敘事散文;(4)科學體:科學文藝、科學說明文;(5)多媒體:兒童劇本。統計結果顯示,教師們對教學中涉及比較多的文體,如寫景狀物、寫人敘事散文,敘事體中的兒童生活故事、教育故事、童話故事有所嘗試,而對于文學性較強的詩歌、小說、兒童劇本,科學性較強的科學文藝則很少下筆嘗試。小學階段是一個文體感性經驗的積累期,小學生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初步感知文體特征,積累各種文體的讀寫經驗。弗萊說:“詩只能從別的詩里產生,小說只能從別的小說里產生。”[4](PP.54-58)小學生應該通過大量經典作品的例子來學習寫作,把握并運用一種文體的讀寫規則。小學語文教師作為寫作指導者,應該是經典作品的介紹者、解讀鑒賞者,也應是學生學習文體讀寫規則的指導者。教師在指導中有“試水”的體驗,才能從寫作表達者的角度給學生以切實的引導。以上問題直接影響小學語文教學的效果。如教師文體意識的缺乏導致其在閱讀教學中舍本求末、教師閱讀量少導致閱讀教學拓展不開、組織學生開展閱讀活動的能力欠缺導致語文活動課形同虛設、兒童文學創作和指導兒童創作素養不足導致寫作教學成為語文教學中的軟肋。筆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論述。
參考文獻:
[1]黃耘.小學教育專業本科生兒童文學素養的培養研究[J].高教論壇,2009(7).
[2]陳暉.通向兒童文學之路[M].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05.
[3]朱自強.兒童文學分級閱讀:指向能力與素養的發展規律[J].人民教育,2014(22).
[4]張隆溪.文學理論的興衰[J].書屋,2008(4).
作者:李繁單位:山西師范大學臨汾學院
- 上一篇:現代文學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范文
- 下一篇:漢語言文學審美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