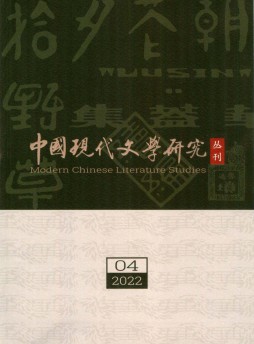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學(xué)是由作品、藝術(shù)家、世界、欣賞者“四因素”①構(gòu)成的。而這四個因素中,“欣賞者”在各種文學(xué)史書寫中是最被輕視的,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傳統(tǒng)文學(xué)理論以文本和作者為中心,它并不否認(rèn)讀者的閱讀對于文學(xué)的意義,但它認(rèn)為對作品的閱讀和理解即是對內(nèi)在于作品中的作者意圖或客觀意義的認(rèn)知,因而讀者只是被動地接受作品,從意義的角度,讀者的閱讀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所以,傳統(tǒng)的文學(xué)史基本上是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而適當(dāng)?shù)丶由衔膶W(xué)的“世界”比如思潮、流派、期刊、社團(tuán)、組織等。但接受美學(xué)(在文論中具體表現(xiàn)為“接受-反應(yīng)批評”)產(chǎn)生以后,“讀者”對文學(xué)的作用和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接受美學(xué)認(rèn)為,作品的意義不是作者的意圖,而是讀者從中讀到了什么,伽達(dá)默爾否認(rèn)文學(xué)的認(rèn)知性,他認(rèn)為文學(xué)閱讀是一種歷史理解活動,并且向未來無限開放。文學(xué)不是被擺在那兒的東西,它存在于意義的顯現(xiàn)和理解之中,理解是文學(xué)“真理”發(fā)生的方式,作品的生命就在于讀者的閱讀,也即接受。接受美學(xué)深受現(xiàn)象學(xué)哲學(xué)的影響,認(rèn)為作品的潛在意義只是通過閱讀才能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文學(xué)作品的意義不是取決于它自身,而是取決于它實現(xiàn)價值的過程,它本質(zhì)上是接受的效果史,讀者實質(zhì)性地參與了作品的存在。接受美學(xué)把讀者上升到和作家、作品平等的地位,也即作家、作品和讀者構(gòu)成了整個文學(xué)活動的“三足鼎立”,有人甚至認(rèn)為接受美學(xué)導(dǎo)致了文論研究的“讀者接受”“轉(zhuǎn)向”。但我認(rèn)為,接受美學(xué)的確導(dǎo)致了人們對文學(xué)的因素及過程有了全新的理解,與傳統(tǒng)文論相比,文學(xué)研究的確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讀者、閱讀以及與此密切相關(guān)的傳媒等都到了空前的重視,“接受心理”、“視域融合”、“期待視野”、“效果史”、“焦慮”、“對話”等都成為文學(xué)理論的重要問題,但這種改變更多是在理論上的,也即文學(xué)理論的探討,解決的是文學(xué)理論問題,而文學(xué)史及其觀念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文學(xué)接受理論產(chǎn)生之后的文學(xué)史仍然是傳統(tǒng)的作家-作品中心主義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接受美學(xué)主要是解決文學(xué)接受的理論問題、原理問題,比如文學(xué)接受在整個文學(xué)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文學(xué)接受的語境問題,接受的時代、民族、地域等特性問題,接受的心理問題,還有接受的過程、接受的途徑等,具體可以再分為文學(xué)“閱讀學(xué)”、文學(xué)“解釋學(xué)”(或“闡釋學(xué)”)等,接受美學(xué)雖然不脫離具體的作家作品等歷史現(xiàn)象,但它主要是理論形態(tài)的,主要是論證抽象的結(jié)論,史實只是零星“論據(jù)”,而不是完整形態(tài),所以,接受美學(xué)本質(zhì)上不解決文學(xué)接受的史實問題,而只是解決文學(xué)接受的認(rèn)識論問題。
第二,讀者以及閱讀的歷史資料有限,這極大限制了文學(xué)接受史的書寫。由于傳統(tǒng)的文學(xué)作家-作品中心觀念,作家的傳記材料被重視,保存得比較完整,挖掘得比較充分。作品也保存得非常完好,手稿、初版本、修訂版等都被珍視,甚至內(nèi)容相同的不同版本,不同印刷本,以及手抄本等也保存完整,所以各種文學(xué)史書寫從來不缺乏作家材料和作品材料。但讀者及閱讀材料就完全不同了,由于讀者及閱讀在文學(xué)史中無足輕重的地位,大量的原始資料缺乏有意識的保存,比如讀者的閱讀筆記,閱讀對讀者的文學(xué)觀、人生觀以及品德修養(yǎng)的影響等過程材料,還有圖書的發(fā)行量,作品的讀者群體構(gòu)成等,傳統(tǒng)的文學(xué)研究中它們都是不重要的,這種觀念和研究方式不僅導(dǎo)致了文學(xué)史家對這些材料的無視,更重要的是導(dǎo)致了讀者自己和出版機(jī)構(gòu)對這些材料的輕賤,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在一些非文學(xué)研究的著作、日記和書信等書籍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根本就無法支撐文學(xué)接受史。歷史必須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礎(chǔ)上,文學(xué)接受史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充分。另一方面,與作家和作品資料相比,讀者及其接受資料可以說浩瀚無邊,既豐富也復(fù)雜,且變動不居,收集的難度非常大。同時,作家和作品的問題相對集中,而讀者的問題漫無邊際。所以相比較而言,作家的文學(xué)史比較好寫,作品的文學(xué)史也比較好寫,思潮流派社團(tuán)等文學(xué)現(xiàn)象的文學(xué)史也比較好寫,文學(xué)接受史最難寫,不僅在于資料缺乏,更是因為問題復(fù)雜,頭緒眾多。
第三,文學(xué)接受史的很多理論問題并沒有解決。接受美學(xué)主要是解決文學(xué)接受的理論問題,而文學(xué)接受史作為歷史形態(tài)屬于史的范疇,也有它自己的理論問題,比如“讀者”問題,作家、批評家、文學(xué)研究專家,這當(dāng)然是讀者,可以說是特殊的讀者,或者高級的讀者,他們的閱讀經(jīng)驗和感受比較多地形成文字并保留下來。但還有大量的普通讀者,比如專業(yè)學(xué)習(xí)者諸如文學(xué)研究生,普通大學(xué)生,中小學(xué)生,他們在文學(xué)課堂和課外、語文課堂和課外的閱讀,也應(yīng)該是文學(xué)接受的重要部分,還有工人讀者、農(nóng)民讀者、商人讀者,他們對文學(xué)的閱讀則是文學(xué)接受更重要的內(nèi)容,更能夠代表普通文學(xué)消費意義上的接受。但讀者及閱讀的區(qū)分,收集這些讀者及其閱讀資料的方法、途徑等問題,理論上根本沒有人探討。再比如“接受”問題,閱讀是否就是一種接受?認(rèn)同一種作品當(dāng)然是接受,但不認(rèn)同呢?合理的理解和闡釋當(dāng)然是接受,不合理的理解和闡釋是否是接受呢?如果說閱讀是接受,那么“收藏”是否是接受呢?還比如文學(xué)接受與文學(xué)發(fā)展的關(guān)系問題,是按照作品的經(jīng)典化過程來寫接受史呢?還是按照讀者對文學(xué)的接受本身來寫接受史呢?有些作品比如通俗文學(xué)不僅在產(chǎn)生之時有很多讀者,之后也一直擁有很多讀者,那么這種接受是否是文學(xué)接受史的重點?這些問題文學(xué)史中都沒有深入探討并解決。
接受史在“史學(xué)”的層面上也有諸多難題,它有點近似于法國年鑒學(xué)派所開創(chuàng)的“私人生活史”②,如果說作家-作品的文學(xué)史是文學(xué)宏觀史,讀者對文學(xué)的接受史則可以說是文學(xué)微觀史,它需要我們從浩瀚的歷史材料中披金揀沙,從而勾勒出清晰的過去是隱含的文學(xué)另類歷史。但作為一種新的文學(xué)史或者專題史,它遠(yuǎn)比傳統(tǒng)的作家-作品史復(fù)雜,一個作品的接受史、一個作家的接受史就非常復(fù)雜,長時段的整體的文學(xué)接受史就更復(fù)雜,其復(fù)雜性不僅表現(xiàn)在內(nèi)容復(fù)雜,因素很多,還表現(xiàn)為讀者及閱讀的變遷是無常的,無窮盡的,眾相的,因而全面性的呈現(xiàn)將是宏篇巨制的。正是因為文學(xué)接受史面臨著諸多難題,所以,雖然接受美學(xué)上世紀(jì)60年代就產(chǎn)生了并得到廣泛的認(rèn)同,大家都認(rèn)識到讀者及閱讀的重要性,都認(rèn)識到出版、傳播的重要性,都認(rèn)識到文學(xué)理解和文學(xué)闡釋的重要性,但文學(xué)接受史卻非常少,西方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筆者見到最早的中國文學(xué)接受史是馬以鑫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主要是論述現(xiàn)代時期的讀者如何接受現(xiàn)代文學(xué)從而如何參與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接受”是接受美學(xué)的接受,但“讀者”卻是與作品產(chǎn)生同時期的讀者。另外還有: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主要研究李白的影響史、效果史、闡釋史等,“以李白為個案,對其人、其詩的歷代影響和被接受過程進(jìn)行梳理和探討。”③這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文學(xué)接受史。藤井省三的《魯迅〈故鄉(xiāng)〉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xué)空間》,《故鄉(xiāng)》本來已經(jīng)夠小了,但藤井省三的這本書還把主題限定在中國現(xiàn)代、當(dāng)代教科書中的《故鄉(xiāng)》,非常具體、“小題大作”,扎實厚重。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主要考察經(jīng)典作品的接受史及詩學(xué)意義,是“接受史研究”而非“接受史”,即理論形態(tài)而非歷史形態(tài),其資料來源以傳統(tǒng)常見文獻(xiàn)為主。尚學(xué)鋒、過常寶、郭英德三人著的《中國古典文學(xué)接受史》,論述中國文學(xué)從先秦到清代各時期以及重要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來源,也即它們?nèi)绾卫^承前代文學(xué),“繼承”當(dāng)然也是“接受”,但這和接受美學(xué)中的讀者對作品的閱讀意義上的“接受”有很大的差異。尚永亮的《莊騷傳播接受史綜論》,全書三篇只有“下篇”才是真正論述《莊子》和《楚辭》的接受問題,且時間上僅到中唐為止。而近期出版的方長安著《中國新詩(1917—1949)接受史研究》,則是一本厚重的中國文學(xué)接受史研究著作。它主要是從傳播、“選本”、文學(xué)史、批評與“經(jīng)典化”的角度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新詩特別是經(jīng)典詩人和名篇進(jìn)行了接受角度的研究,是新詩接受史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雖然具有專題性,但對于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新詩選本,對這些選本進(jìn)行統(tǒng)計,在統(tǒng)計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分析,從而研究批評家對新詩的接受以及新詩愛好者、普通新詩讀者對新詩的接受以及這種接受對于新詩經(jīng)典化的作用和意義。作者還收集了大量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著作,并對這些著作中關(guān)于新詩及名篇的敘述與定位進(jìn)行分析,從而研究文學(xué)史是如何接受新詩的,從一個特殊的角度研究新詩接受問題。最重要的是,本書提出了很多問題,對于我們研究文學(xué)接受史,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研究新詩接受史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的很多方法都為文學(xué)接受史研究打開了思路,其嘗試也為文學(xué)接受史研究提供了經(jīng)驗。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寫作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是可能的。我認(rèn)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新的學(xué)術(shù)增長點,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要成為成熟的文學(xué)史,要真正呈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傳播、讀者閱讀以及意義生成、價值實現(xiàn)的復(fù)雜過程,從而構(gòu)筑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從作家到作品到讀者接受的完整的文學(xué)史拼圖,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包括理論上的問題,材料上的問題,正如於可訓(xùn)先生在序言中所說:“所有現(xiàn)存的文學(xué)史料和研究成果,大都是為傳統(tǒng)的文學(xué)史研究準(zhǔn)備的,是適應(yīng)傳統(tǒng)的文學(xué)史研究的寫作要求的,從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學(xué)史,無論是整體的還是文類的,都必須重新發(fā)掘、收集、整理文學(xué)史料。”④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的建構(gòu),我覺得目前可以從三個方面努力。
第一,加強(qiáng)文學(xué)接受史理論研究。目前,接受美學(xué)、文學(xué)接受反應(yīng)批評都非常成熟,概念和術(shù)語清晰,問題明確,體系完備,但文學(xué)史接受理論卻相對缺失,框架、基本問題都沒有建立起來。其實,文學(xué)接受史學(xué)不完全屬于文學(xué)理論,它更多地屬于“史學(xué)”范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研究,不僅需要我們轉(zhuǎn)變文學(xué)觀念,還需要我們轉(zhuǎn)變史學(xué)觀念,只有解決文學(xué)接受史理論上的問題,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才能夠進(jìn)入真正的自覺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只有文學(xué)接受史理論得以建立,讀者閱讀、出版發(fā)行、文學(xué)教育及其效果等這些因素得到重視,文學(xué)研究才會有意識地收集這些材料,有意識地保存這些材料,從而為研究過去的文學(xué)接受史,現(xiàn)實的文學(xué)接受狀況作資料上的積累準(zhǔn)備。
第二,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可以由小做起,從微觀做起,再由小到大,由微觀到宏觀。比如先研究一個經(jīng)典作品的接受史,或者研究一個經(jīng)典作家的接受史,然后再研究一個群體或一個時期的經(jīng)典作品、經(jīng)典作家接受研究。可以先研究一種文類的文學(xué)接受史,然后再研究各種文類的文學(xué)接受史,最后把各種文學(xué)接受史綜合起來,書寫總體性的時代性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其實,傳統(tǒng)的文學(xué)史也是從具體的作家、作品批評與研究開始的,也是從具體的文學(xué)現(xiàn)象研究開始的,沒有具體的文學(xué)批評積累,沒有長期的文學(xué)史研究,綜合性的文學(xué)史寫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可以由易做起,先易后難。現(xiàn)在看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資料在選本、文學(xué)史、出版發(fā)行和傳播、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等方面相對豐富和完整,我認(rèn)為我們可以先把這些方面的接受史做起來,比如從選本的角度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從文學(xué)史教材的角度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從出版發(fā)行和傳播的角度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從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的角度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讀者文學(xué)閱讀以及評價的情況非常復(fù)雜,但大致來說,讀者可以區(qū)分為兩類:專業(yè)讀者,包括文學(xué)批評家,文學(xué)研究者,文學(xué)史教授,作家,他們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閱讀感受、理解、批評、文學(xué)對他們的影響等,很多都通過文字的方式存留于世,并延傳下來,由于材料的相對充分,所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專業(yè)讀者及閱讀層面的接受史相對容易寫一些,因而可以先寫這種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二是普通讀者,包括中小學(xué)生、大學(xué)生、普通知識分子、工人、農(nóng)民、商人,特別是底層人民,他們的閱讀和專業(yè)讀者有很大的差別,但他們?nèi)藬?shù)眾多,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的主體,他們的閱讀和接受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大的影響,但他們的閱讀感受,對作品的理解,作品對他們的意義過程等都沒有留下文字材料,所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普通讀者接受史寫起來難度更大一些,不僅是史料的缺少問題,還有對已有材料的理解、分析、勾勒的問題,這種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可以等到條件成熟時再寫。總之,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接受史雖然才剛起步,雖然還有諸多困難,成果非常少,缺乏可資借鑒的成功經(jīng)驗,但它非常具有前瞻性,它會彌補(bǔ)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缺陷,從而完善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研究環(huán)節(jié)。相信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
作者: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