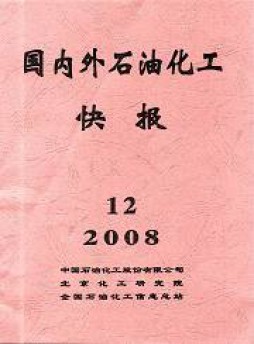國內社區報的困境與突圍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內社區報的困境與突圍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新聞界雜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內容之困:社區“生活報”與社區“黨報”如何平衡《海西晨報》社區報最初的內容設計是以百姓視角、百姓語言報道百姓的身邊人身邊事,理論上講,它是以軟新聞為主的社區“生活報”。然而,現實運作中,它卻一再面臨報道偏“硬”的問題。以《廈港晨報》為例,這份在廈門市老城區廈港街道創辦的社區報,近三期的頭版頭條分別為:六個街心公園項目要您共同參與;美麗廈港楊帆起航——以項目為抓手,扎實踐行群眾路線;踐行群眾路線共筑幸福廈港。這樣的社區報內容構架,更像是傳統意義上的機關報,如果我們把標題中的“廈港”換成“廈門”,類似作為市委機關報的《廈門日報》應該有的頭條,這些內容偏硬、不接地氣、難脫官腔,更似“社區黨報”。在生活還是管理的內容權重之困的背后,我們思考的是目前社區行政職能和傳播目標的調適問題。以廈門為例,其城市規模決定了大多數“社區”、“村”這樣的居民組織單位無法容納一份報紙的存在,社區報的運營更適合以“街道”這一行政單位為依托。我國政治的現實是,要在任何“街道”辦“社區報”,就必須獲得街道黨工委、辦事處以及上級區委宣傳部門的認可和支持。這就決定了《海西晨報》將創辦社區報的“第一桶金”來源鎖定在街道黨工委、辦事處這樣的“處級”行政單位上。從與思明區廈港街道合作的《廈港晨報》,到與同安區大同街道合作的《大同晨報》再到與鼓浪嶼風景名勝區管委會、鼓浪嶼街道辦合作的《鼓浪嶼晨報》,《海西晨報》系列社區報創辦的路徑基本為:報社與街道一級黨工委達成協議,由街道黨工委支付一定的開辦費(這樣的開辦費可讓報社基本達到“保本”的最低要求),由報社派出采編發行人員從事具體的采編工作。這就意味著:報社與街道黨工委辦事處對社區報的不同認識和需求會直接反應在對內容的博弈上。報社的目的是通過社區報服務受眾以贏得受眾最后獲得廣告收益,街道辦則將社區報作為創新和改進社會管理模式的新方法,視為宣傳和服務街道黨工委辦事處中心工作的平臺。一個是以信息消費為導向的市場動機,一個是以管理為導向的宣傳動機;一方要“軟”,一方要“硬”;雖然報社在協議中全部保留了對社區報的終審權,但作為出資方的街道辦卻在選題設置、甚至具體稿件的選擇等問題上居于主導,因此,社區報無法消減“機關味”,而對社區讀者而言,生活服務類的社區傳播才是他們的現實訴求。
(二)發行之困:精確投遞與模糊投遞如何確定《海西晨報》社區報創辦之初,其發行目標是實現對社區人群的高覆蓋和掌握讀者數據。從社區報的發行方式來看,它是區別于讀者付費訂報的“模糊投遞”。與傳統的“精確投遞”相比,“模糊投遞”存在三大弊端。第一,無法準確掌握讀者數據。以《廈港晨報》為例,根據街道方面提供的統計數據,廈港街道共有居民戶1萬9千戶,人口3萬9千多人,加上轄區學校、單位、上級部門的發行需求,《廈港晨報》確定發行量為2萬5千份。這2萬5千份報紙由發行員根據街道方面提供的居民信息按戶投遞。但實際情況是,廈港街道地處廈門老城區,不少居民往往保留戶口后搬到新區居住。因此,有的房子里數據顯示只有一戶人家,卻實際租住著多戶,有的房子里卻沒人居住,還有不少長期無人使用的“死信箱”,里面塞滿了各種廣告傳單。對報社而言,無法獲取精準的讀者數據將直接導致發行浪費,尤其在缺乏物業管理的老舊小區比較明顯。第二,不能及時獲取投遞反饋。對自費訂報的讀者來說,若沒收到報紙就會立即向報社反映,報社就能立即修訂數據,補充投遞。然而,由于社區報是免費報紙,不少讀者并不知道有此“福利”,或者對報紙抱著可有可無的態度,即便沒有收到也不會主動打電話到報社反映,這也不利于社區報的發行和精確投遞。第三,難于監控投遞過程。因為是模糊投遞,報社對發行質量缺乏有效的監督手段。甚至發生拾荒者一個信箱一個信箱地把報紙抽出來當廢紙賣掉的事件,而發行員卻對此視而不見,這是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監控措施所致。
(三)廣告之困:微收益與高投入何如調和社區報本身較主報低廉的成本可以壓低分類廣告價格,吸引那些無力承擔主報廣告費的客戶來做廣告。因此,分類廣告成為包括《海西晨報》社區報在內的我國社區報對廣告市場的最大預期。如《海西晨報》在社區報矩陣中推出“社區黃頁”的分類廣告模式,以社區報低廉的印刷發行成本作為定價的參考坐標。以一份發行量在2萬份的社區報為例,測算的單個版面成本為1002元,為吸引客戶,直接以1200元/版的報價招徠客戶。如此低廉的價格,應該說對許多社區商家小店鋪具有吸引力,然而,實際情況是除了印刷發行成本,高昂的人力成本成為攔路虎。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第一,業務員人數不足。在微利模式下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只能選擇薄利多銷。社區報分類廣告的目標客戶,大多缺乏通過大眾媒體刊登廣告進行營銷的經驗,要把這些被動的潛在客戶變成真實的客戶,就需要點對點、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可即便是在一個常住人口三到四萬的社區,這樣的小店數量也在四百家左右,這顯然不是一般廣告公司或者實行廣告自營的報社的人力所能承受的。第二,業務員能力不足。《海西晨報》曾嘗試讓發行站介入社區報的分類廣告業務,讓發行員在投遞報紙的同時,承擔起廣告業務員的角色。這樣做表面上解決了人數不足的問題,卻產生了更高的溝通成本,因為哪怕一塊小小的報花廣告,從創意到文案到視覺呈現,都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而這些顯然是發行員所不具備的。第三,投入產出比失衡。分類廣告的特點是客戶海量和利潤微小,提高投入產出比的捷徑就是規模化生產,這需要三個前提,即:社區報本身有強大的廣告吸引力;有流程化的作業模式;有自覺投放的客戶群體。這是一個和時間賽跑的游戲,而這與作為投資主體的主報的期待存在矛盾。
(四)服務之困:版權、即時性需求與紙媒的天然缺陷如何滿足與彌合所謂服務,對紙媒來說,首先是資訊的獨家性與權威性。“全民記者”時代,投入專業采編力量的社區報仍具自身優勢,但這種優勢卻因為版權意識的薄弱而難以體現,甚至成了為他人做嫁衣。《廈港晨報》所服務的社區,毗鄰廈門大學,人文氣息濃郁,書店繁多,品類各異。記者經過大量的調查和實地采訪,在專業人士的指點下推出“廈港購書地圖”,而這一獨特的資訊服務產品卻迅速成為網絡社區論壇、微博、微信服務號的“拳頭產品”,由于當期社區報的投遞需要三到四天的時間,甚至出現了受眾還沒看到報紙,就已經在網上讀到相關內容的情況。如果說“內容為王”依舊是媒體競爭的王道,那么,在提供服務的競爭中,它的重要性似乎并不那么突出,因為在社區報及其有限的報道領域內,可以在內容上進行深耕的空間亦有限。更重要的是,受眾對服務的需求早已超出資訊,在移動互聯的新媒體時代,人們需要“心動”立即“行動”。換言之,一條打動受眾的服務信息如果不能立即轉換成消費行為,就很可能在下一秒鐘被另一條信息取代,而移動互聯媒體平臺的交互性、即時性支付功能無疑構成目前社區報分類廣告未必致效的因素之一。
二、以新媒體思維解困并探尋我國社區報的突圍之道
上述《海西晨報》社區報所面臨的困境讓我們意識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遠大于內部因素,它既考問著我們“要不要辦社區報”,又深刻啟示我們洞悉和順應傳統紙媒的轉型升級規律。作為社區報興起與發展的新媒體環境,既是新的媒介生態,同時也是更改變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生產體系的動力機制,它對我們思考社區新聞的定位以及發展戰略至關重要。Swot分析法表明,社區報所具備的strength(競爭優勢)是專業記者生產的專業內容,盡管由于版權保護意識的淡漠而有所淡化,但它依舊是傳統紙媒在與新媒體競爭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所在。weakness(競爭劣勢)則集中體現在紙媒介質與新媒體介質競爭中天然的技術性缺陷,新媒體在帶來threat(威脅)的同時也促使社區報打開媒體融合的oppportunity(機會之窗)。
(一)尋找新社區:從地域概念到人群概念的思維轉換城市的碎片化是社區報興起的前提。有研究者認為,“市民階層的成型是社區報發展的關鍵,社區成員對生活熱點的關注已經遠遠超過對政治熱點的關注;傳播媒體的環節缺失是社區報成功的契機”[1]。對地方報紙來說,本地新聞生產在新媒體時效競爭的擠壓下其同質化趨向越發突出,因此,有地域貼近性和利益相關性的本地獨家或原創新聞是社區報滿足社區成員需求的著力點。基于此,本文認為,尋找社區報的突圍之道,必須重回社區報誕生的原點,重新審視這片生存的土壤和社區報存在的價值。從媒介滿足本地本社區受眾需求的層面上看,任何報紙在本質上都可視作社區報,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理解“社區”的概念:即作為場所的社區,作為符號的社區和虛擬的社區。所謂社區報,就是服務于城市中的社區讀者,強調其歸屬性和認同感的報紙。從中不難發現,社區報的根本特色就是各種利益和關系的相關性。反觀我國社區發展實際,其作為場所的社區建設并不成熟,人們的社區觀念尚處于成長期。相比美國日本,其基于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成熟的公民意識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比如美國的教堂、日本的神社)所形成的社區,使他們對社區居民更具貼近性和粘合性,而且更能夠產生家園歸屬感以及有效激發其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目前,我國社區報以“街道”為載體,行政隸屬性強,主要用來傳遞基層社會組織的政策管理信息,它對普通市民的生活影響度小,尚無法聚合成社區成員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經常參加街道社區辦活動的是在家賦閑的老大媽。而反觀當下作為符號的社區和虛擬的社區,卻能喚起廣泛社會成員的有效參與,這是新媒體時代造就的新的社會關系的折射,是媒介社區已然崛起的寫照,它使傳統形態的以地緣和行政管控定位的社區報面臨嚴峻挑戰。由此,將“超細分”這一新媒體時代的紙媒生存法則與社區報概念進行嫁接,我們可以探尋社區報新的發展空間。如《海西晨報》近來推出的《夕陽紅周刊》、《廈門小記者報》和即將推出的《廈門物流晨報》,這些系列社區報正是瞄準了日益龐大的老年消費市場、學生群體以及以港立市的廈門特有的物流業主,運用社區報概念融合行業報的特征進而重新包裝媒介產品,以此提升受眾的忠誠度和廣告客群的吸附力,增強了社區報的傳播效力。又如《鼓浪嶼晨報》,它是服務每年一千四百萬登上鼓浪嶼的游客的社區報,借助移動人群的口碑效應和鼓浪嶼作為旅游熱地的品牌感召力,我們以流動符號為認同識別的載體,整合了實體社區和虛擬社區的人群“大數據”,拓展出品牌傳播的新空間,大大增強了《海西晨報》的市場運作能力與實力。
(二)聯姻新媒體:以移動互聯思維重構社區報生產鏈與需求鏈對我國社區報所面臨的“廣告之困”與“服務之困”而言,就是要完成從傳統的信息型媒體向關系運營型媒體的轉型,這也是當下整個報業轉型升級的重點。社區精神的核心特質是互動,具體到社區媒體,就是在公民社會背景下構建“公共空間”,使之成為社區生活的信息樞紐、意見表達平臺和交易終端。因之,聯姻新媒體成為大勢所趨。如何“聯姻”?如果僅僅是開通一個微博或者微信賬號,設置一個網絡論壇,開發一個app,那只是以傳統媒體的思維經營新媒體,不可能獲得可持續發展和優勢增長。聯姻新媒體,必須以新媒體的思維重構社區報的所有生產和環節,在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中再構需求鏈,從而開掘出新媒體環境下社區報利益最大化的“藍海”,對此,我們將實踐與思考歸結為三方面的策略——從內容包向樞紐型媒體轉型。以《廈港晨報》為例,目前基于廈港街道的新聞平臺有兩個:一為《海西晨報》社主管主辦的《廈港晨報》,另一個是廈港街道黨工委辦事處主辦的app客戶端“掌上廈港”;后者以新媒體形態轉發《廈港晨報》新聞,在這一“內容包”的初級模式下,盡管它也提供一些入口引導,被視作網上“便民服務大廳”,但由于街道與居民的聯系本來就不緊密,大多數社區居民認為其服務價值并不大。《海西晨報》目前正在規劃兩者的深度融合,著重在掌上客戶端開發社區消費查詢和預訂、網上支付功能,將社區報所采集和的消費信息與移動互聯消費平臺有機結合,不僅為商家開發客源,還試圖從中賺取流通領域的差價。從線型媒體向關系運營型媒體轉型。如果說紙媒是單向線型的傳播方式,那么,新媒體則是多向網狀的傳播方式。新媒體通過網狀傳播關系的構建,能將信息推進到關系運營的新階段。通過新媒體手段,讀者不僅轉換成用戶,而且這些用戶還能通過新媒體尋找各自的“圈子”,聚合成“圈子社區”(圈子共同體),而社區報則通過對這些“圈子”的影響,實現特定用戶的精準營銷,從而挖掘預期的價值洼地。如《海西晨報》針對老年群體推出的社區報《夕陽紅周刊》,就是按照趣緣將老年讀者群體細分轉換成老年攝影愛好者、老年旅游愛好者、老年歌唱愛好者、老年廣場舞愛好者等不同的圈子,再通過舉辦老年歌手大賽、老年相親會、老年廣場舞大賽等一系列活動,施加社區報在這些圈子中的影響力,最終實現020模式的盈利。從超細分向私人訂制轉型。所謂的超細分,即內容生產上小切口,深挖掘,就是微博微信中的專家型的“技術帖”,進一步說,就是對“內容為王”的傳媒理念的強化與轉化。新媒體時代的社區報,其目標受眾異質性強,必須轉換成用戶,且必須提供“私人訂制”化服務,才能成為有效傳播。這就需要對社區報所擁有的專家資源進行深度挖掘。以社區報健康專欄為例,版面空間內只能講述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而相親專欄,也只能是廣而告之的撒網似推介,而通過微信公眾號、app客戶端技術的開發,卻可以讓用戶通過輸入健康信息,獲得網上的專家意見;通過輸入關鍵詞查詢,找到合意的相親伙伴。當這些受眾注冊成為用戶后,社區報的發行之困就在用戶身份和參與方式的轉化下迎刃而解,而且還可以為下一步的大數據開發與運用打下基礎,積累社區資源與社會資本。
(三)提供新服務:社區電商構筑媒介消費廣平臺毋庸諱言,新媒體是媒體從內容為王到服務為王轉型的催化劑,作為傳統媒體的社區報,除了內容生產之“長”,其實還擁有發行隊伍之“長”。這表現在社區報不僅有深入社區采寫的記者,還有每天穿著紅馬甲穿行在社區大街小巷的發行員,他們是社區建設最好的參與者與共建者,更是物流配送中完成“最后一公里”難題的寶藏。對社區報而言,報紙內容的消費要延伸至報紙版面之外,也就是著眼于更廣闊的消費天地,才能聚合更多的人氣,吸引更多的社區居民主動參與,通常做法是搞活動,打通報道內容和社會服務,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良性循環。傳統報業生根并精耕社區這片土壤,必須善于利用深入采訪以及人際發行積累的人氣優勢、人緣優勢,一旦與社區電商結合,將構筑新的媒介消費平臺,促成新的社區消費服務模式。《海西晨報》引入電商概念,發揮物流配送優勢,憑借報社公信力和影響力,大力開發“晨報超市”,以有機、生態、無污染的放心食品為主打,將社區服務由信息提供向信息提供、服務提供雙管齊下升級,將報業經濟的鏈條從發行廣告的單一支柱延伸到物流經濟領域。目前運作顯示,依托社區報的資源優勢,不定期舉辦的一些社區的線下活動,獲得了較好回報。《海西晨報》的未來規劃是將“晨報超市”產品進一步細分,針對不同社區群體(這一社區當然也包括基于共同符號和利益述求的人群概念)進行更加精準的營銷。
作者:陳煒明單位:《海西晨報》副總編
- 上一篇:搜索營銷的廣告傳播措施范文
- 下一篇:新聞云下新聞業務的新趨勢范文
擴展閱讀
- 1國內媒介文化
- 2國內公債史
- 3國內購物旅游探究
- 4國內檢察權分析
- 5國內村民分化研究
- 6國內小額信貸監管分析
- 7國內武術文化研究綜述
- 8國內物流金融
- 9國內毒情形勢表述
- 10國內翻譯研究綜述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國內產業調研
- 2國內安全保衛論文
- 3國內外形勢論文
- 4國內市場營銷方案
- 5國內博士論文
- 6國內工程造價管理現狀
- 7國內的公共藝術
- 8國內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研究
- 9國內外建筑論文
- 10國內形勢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