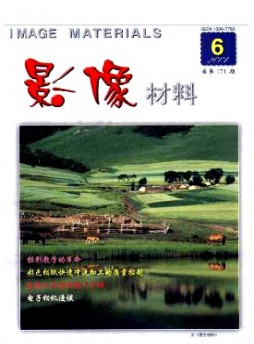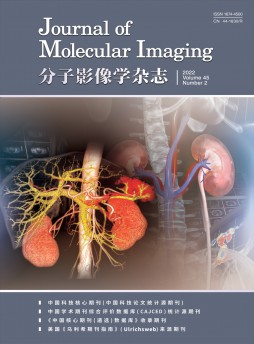影像史與圖書館文獻(xiàn)建設(sh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影像史與圖書館文獻(xiàn)建設(sh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圖書館界雜志》2015年第二期
1口述史學(xué)、影像史學(xué)的特點(diǎn)
口述史學(xué)作為一種新的歷史研究方法,與傳統(tǒng)史學(xué)研究方法有顯著的區(qū)別。張廣智先生說:“現(xiàn)代意義上的口述史學(xué),實(shí)際上是通過有計(jì)劃的訪談和錄音技術(shù),對(duì)某一個(gè)特定的問題獲取第一手的口述證據(jù),然后再經(jīng)過篩選與比照,進(jìn)行歷史研究。”[3]鐘少華先生認(rèn)為,“口述史學(xué)方法是一種獨(dú)特的方法”,“人民群眾的歷史性和歷史的群眾性都可以通過口述史來表述”[4]。由此可見,口述史學(xué)至少有四個(gè)特點(diǎn):一是歷史研究的資料來源由采訪所得,而非來自書本或其他文獻(xiàn);二是口述采訪的手段主要是錄音,有的還輔以攝影、錄像;三是采訪的對(duì)象不僅是一些重要人物,廣大的民眾均可參與;四是口述采訪得到的錄音材料經(jīng)整理形成文字,成為史學(xué)著作或史科的一部分。與口述史學(xué)類似,影像史學(xué)也改變了以文字書寫歷史的傳統(tǒng)形式,借助攝影、電影、電視等影像技術(shù),來記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影像史學(xué)所記錄與表現(xiàn)的,也不局限于一些重要人物,為平民參與歷史的書寫、展示歷史發(fā)展的過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影像史學(xué)通過生動(dòng)形象、豐富有趣的動(dòng)態(tài)描述,使枯燥無味的歷史知識(shí)變得鮮活直觀,拉近了歷史學(xué)家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正如黃樸民先生所說:“用現(xiàn)代意識(shí)對(duì)歷史進(jìn)行生動(dòng)鮮活的解讀,讓歷史從歷史學(xué)家營(yíng)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來,走入千家萬戶,走入每個(gè)人的心里。”[5]口述史學(xué)與影像史學(xué)在現(xiàn)代史、當(dāng)代史研究中具有獨(dú)特的優(yōu)勢(shì)。因?yàn)榭谑鍪贰⒂跋袷匪涗浀膶?duì)象,大多是活著的歷史的見證者。尤其對(duì)重大歷史事件參與者的口述采訪與影像記錄,更是國(guó)家珍貴的歷史資料,理應(yīng)成為圖書館文獻(xiàn)資源體系的組成部分。
2圖書館與口述史、影像史
目前圖書館的文獻(xiàn)資源體系基本由傳統(tǒng)紙質(zhì)文獻(xiàn)和數(shù)字文獻(xiàn)組成。以音頻、視頻記錄歷史的口述史、影像史,作為一種新型文獻(xiàn)類型,已進(jìn)入許多國(guó)家和地區(qū)圖書館館藏文獻(xiàn)體系,但是這類文獻(xiàn)資源在國(guó)內(nèi)圖書館界館藏體系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有的甚至處于微不足道或空缺狀態(tài)。
2.1國(guó)外圖書館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圖書館是目前世界上館藏最為豐富、現(xiàn)代化水平最高的國(guó)家圖書館。該館十分重視口述史、影像史資料的搜集開發(fā),并將其納入到“美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之中。“美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起源于1990年的探索性課題“美國(guó)記憶試驗(yàn)計(jì)劃”,1994年正式啟動(dòng)。“美國(guó)記憶”的內(nèi)容包括重要檔案記錄、照片、錄音、民俗宗教、文學(xué)乃至特定時(shí)期文化現(xiàn)象,幾乎是美國(guó)歷史文化的百科全書。“美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自成立至今,已擁有900萬件以上記錄美國(guó)歷史和文化的數(shù)字化藏品。該項(xiàng)目按主題共分18個(gè)資源庫(kù),下設(shè)140個(gè)專題資源[6]。這些專題資源可通過多種途徑在網(wǎng)上查詢。目前,“美國(guó)記憶”已成為美國(guó)公民教育的重要平臺(tái)和對(duì)外宣傳的一張文化名片。繼“美國(guó)記憶”之后,世界各國(guó)和一些國(guó)際組織實(shí)施了一系列類似的記憶項(xiàng)目,如1992年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發(fā)起的“世界記憶”工程,2002年日本國(guó)會(huì)圖書館以記錄日本歷史文化為內(nèi)容的“日本年歷”。英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目前收藏有超過5萬份的錄音、影像及相關(guān)文獻(xiàn)資料,1987年還設(shè)立了“國(guó)家生活故事”,以采集制作口述史資料。荷蘭國(guó)家圖書館負(fù)責(zé)的“荷蘭記憶”項(xiàng)目,記錄荷蘭的人文、歷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資料。德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以當(dāng)事人講述的視頻短片為特色資源,建立了“我們的故事—民族的記憶”資源庫(kù)。值得一提的是,由新加坡國(guó)家圖書館負(fù)責(zé)規(guī)劃實(shí)施的“新加坡記憶”,它是由每個(gè)國(guó)民和家庭記憶所組成的參與人群和范圍最廣的國(guó)家記憶項(xiàng)目。該項(xiàng)目于2011年正式批準(zhǔn),由新加坡政府直接領(lǐng)導(dǎo)。“新加坡記憶”除征集照片、實(shí)物外,大量地采用了口述史、影像史方法。不過,新加坡的口述史、影像史研究與實(shí)踐,主要是在國(guó)家檔案館。新加坡國(guó)家檔案館下設(shè)口述歷史中心和聲像檔案處,其藏品十分豐富,1999年就有電影膠片、錄音帶、錄像帶8340盤,口述歷史訪談17000部[7]。
2.2國(guó)內(nèi)圖書館目前國(guó)內(nèi)已有多家公共圖書館從事口述史、影像史資料采集制作。一些公共圖書館建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記憶項(xiàng)目,如首都圖書館的“北京記憶”、上海圖書館的“上海年華”、長(zhǎng)春圖書館的“百年長(zhǎng)春”,專門搜集和整理地方特色文獻(xiàn)。湖南省圖書館的“抗戰(zhàn)老兵口述史”、山西社會(huì)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的“山西抗戰(zhàn)口述史”、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口述史資料館、大連大學(xué)教授李小江的“20世紀(jì)(中國(guó))婦女口述史”等,是較早開展的口述史項(xiàng)目。港澳臺(tái)地區(qū)也有類似項(xiàng)目開展,如“香港記憶”“香港口述歷史庫(kù)藏計(jì)劃”“澳門記憶”“臺(tái)灣記憶”等。這些項(xiàng)目都是在傳統(tǒng)館藏文獻(xiàn)和數(shù)字資源的基礎(chǔ)上,著重搜集口述史、地方文獻(xiàn),形成專題資源庫(kù)。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于2012年正式啟動(dòng)“中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該項(xiàng)目以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重大歷史事件、重要人物為專題,以圖書館原有館藏文獻(xiàn)為基礎(chǔ),以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口述史、影像史等新文獻(xiàn)為補(bǔ)充,進(jìn)而建立專題文獻(xiàn)資源庫(kù)體系。目前,“中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中心在口述史、影像史采集制作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迄今已完成和正在進(jìn)行的口述史項(xiàng)目有:大漆髹飾、蠶絲織繡、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中國(guó)遠(yuǎn)征軍、馮其庸專題、我們的文字等20余個(gè)專題資源建設(shè)。目前,已對(duì)超過200位各界人士進(jìn)行了口述史訪問,獲得視頻資源總時(shí)長(zhǎng)600多個(gè)小時(shí),出版了《大漆中的記憶》《絲綢中的記憶》《大漆髹飾傳承人口述史》《我們的文字》等4部專著,并舉辦了“中國(guó)年畫”“大漆的記憶”“絲綢的記憶”和“我們的文字”4場(chǎng)“中國(guó)記憶”系列展覽,以及數(shù)10場(chǎng)學(xué)術(shù)講座,累計(jì)參觀人次、聽眾數(shù)10萬,取得了良好的社會(huì)效益。
3口述史、影像史的采集整理
3.1采集對(duì)象口述史、影像史資料的采集對(duì)象主要有兩類,即“國(guó)家記憶”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3.1.1“國(guó)家記憶”。所謂“國(guó)家記憶”,就是國(guó)家的歷史,民族的歷史。國(guó)家和民族的歷史,可以從最高的國(guó)家層面來考察,可以從一個(gè)地區(qū)來考察,也可從一個(gè)社會(huì)群體甚至個(gè)人來考察。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各個(gè)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民族、地區(qū)或個(gè)人的歷史,都是“國(guó)家記憶”的組成部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歷史中最原始、最真實(shí)的載體———個(gè)人,其生命是十分有限的。自然生命的消失,自然與社會(huì)環(huán)境的改變,都會(huì)帶走一部分歷史。某些歷史對(duì)于“國(guó)家記憶”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公共圖書館負(fù)有傳承文明的重大使命,在資源建設(shè)中,進(jìn)行口述史、影像史資料采集,不僅是對(duì)館藏資源的豐富和擴(kuò)充,更是在“為國(guó)存史”,履行傳承文明的神圣使命。“國(guó)家記憶”內(nèi)涵豐富,諸凡自然地理、語言文字、科學(xué)技術(shù)、傳統(tǒng)遺產(chǎn)、文化藝術(shù)、社會(huì)民生、政治歷史等,都屬于口述史、影像史的研究范疇。
3.1.2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根據(jù)2003年10月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第二條定義,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指被各社區(qū)群體、有時(shí)為個(gè)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huì)實(shí)踐、個(gè)人表述、表現(xiàn)形式、知識(shí)、技能及相關(guān)的工具、實(shí)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chǎng)所”[8]。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最大的特點(diǎn),是以人為本的活態(tài)文化遺產(chǎn),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jīng)驗(yàn)、精神,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是民族個(gè)性、民族審美習(xí)慣的“活”的顯現(xiàn)。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資源異常豐富,包括民間文學(xué)、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tǒng)戲劇、曲藝、雜技與競(jìng)技、民間美術(shù)、傳統(tǒng)手工技藝、傳統(tǒng)醫(yī)藥、傳統(tǒng)民俗等。截至2013年12月,中國(guó)入選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項(xiàng)目總數(shù)已達(dá)38項(xiàng),國(guó)務(wù)院正式的前三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累計(jì)達(dá)1530項(xiàng)(包括擴(kuò)展項(xiàng)目),國(guó)家級(jí)代表性傳承人1488名。2014年7月16日的第四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共298項(xiàng)[9]。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乃至各市縣也都相繼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名錄。
3.2采集方法圖書館進(jìn)行口述史、影像史的采集,可以采取以下三種方法,即獨(dú)立采集、合作采集、征集或購(gòu)買。
3.2.1獨(dú)立采集。獨(dú)立采集是目前國(guó)內(nèi)圖書館界進(jìn)行口述史、影像史采集的主要手段。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已經(jīng)完成或正在進(jìn)行的口述史、影像史采集工作,以獨(dú)立采集為主,不排斥必要的合作。以該館“中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中心編的《大漆髹飾傳承人口述史》為例,該項(xiàng)目在進(jìn)行過程中,分別對(duì)北京雕漆技藝、平遙推光漆器髹飾技藝、揚(yáng)州漆器髹飾技藝、天臺(tái)山干漆夾纻技藝、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等19個(gè)項(xiàng)目、25位傳承人進(jìn)行了口述采訪和現(xiàn)場(chǎng)拍攝,由項(xiàng)目組成員獨(dú)立完成[10]。此外,蠶絲織繡、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中國(guó)遠(yuǎn)征軍、馮其庸專題、我們的文字等,也均由“中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中心獨(dú)立采集。
3.2.2合作采集。無論是“國(guó)家記憶”還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其數(shù)量都十分巨大,要對(duì)其進(jìn)行口述史、影像史采集,需要很大的物力與人力支持,絕不是某個(gè)圖書館所能完成的。因此,勢(shì)必需要進(jìn)行有效的合作,包括圖書館業(yè)內(nèi)的合作與跨界合作。就圖書館業(yè)內(nèi)合作而言,某些跨地區(qū)、跨領(lǐng)域的項(xiàng)目,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在合理分工、優(yōu)勢(shì)互補(bǔ)的前提下進(jìn)行,實(shí)現(xiàn)資源的共建共享。就跨界合作而言,一方面是圖書館以外的部門或單位可能已經(jīng)對(duì)某些項(xiàng)目進(jìn)行了口述史、影像史采集,有了一定的基礎(chǔ)(當(dāng)然還未完成);另一方面是因?yàn)槟承┹^為專門的項(xiàng)目,若與相關(guān)部門合作采集,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效果。2009年10月,云南省檔案館與新加坡國(guó)家檔案館就雙方合作搶救云南口述歷史項(xiàng)目簽署了備忘錄,這是兩國(guó)檔案工作者進(jìn)行跨國(guó)合作、搶救少數(shù)民族口述歷史檔案的一項(xiàng)嘗試,值得圖書館界學(xué)習(xí)借鑒[11]。
3.2.3征集或購(gòu)買。“國(guó)家記憶”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各族人民共同擁有的珍貴遺產(chǎn),通過口述史、影像史記錄,加以永久典藏,具有十分重要的價(jià)值,對(duì)于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因此,建議有關(guān)部門盡快出臺(tái)相應(yīng)的政策法規(guī),鼓勵(lì)民眾把所有已經(jīng)制作完成的口述史、影像史作品,無償?shù)乩U送圖書館特別是向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繳送,由圖書館永久保存。同時(shí),對(duì)于某些征集確有困難的口述史、影像史作品,建議圖書館在進(jìn)行文獻(xiàn)采訪計(jì)劃時(shí),撥付專項(xiàng)資金加以購(gòu)買,力爭(zhēng)做到口述史、影像史資料不缺位、不遺漏。此外,圖書館也可通過社會(huì)或個(gè)人捐贈(zèng),獲得口述史、影像史資料,以充實(shí)館藏。
3.3資料整理口述史、影像史的資料采集,是資源建設(shè)的基礎(chǔ),只有經(jīng)過整理,才能真正進(jìn)入圖書館文獻(xiàn)資源體系。在口述史采集資料整理中,將錄音訪談的內(nèi)容轉(zhuǎn)換成文字是很艱苦、很重要的一步。因?yàn)橥ǔT诳谑鍪凡杉^程中,受訪人會(huì)脫離事先擬定的內(nèi)容加以講述,或是受訪人文化水平不高,講述時(shí)不按預(yù)設(shè)的順序,或是語言表達(dá)不太規(guī)范。在整理成文字稿時(shí),必須進(jìn)行較大幅度的調(diào)整。但是,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關(guān)鍵的是要對(duì)其講述的內(nèi)容進(jìn)行文獻(xiàn)、其他當(dāng)事人甚至實(shí)物佐證。在對(duì)影像資料整理過程中,必須對(duì)資料進(jìn)行符合歷史、合乎邏輯的編排,通過藝術(shù)手法的處理,增強(qiáng)其歷史的真實(shí)感與感染力。有些歷史的紀(jì)錄片,可能進(jìn)行了藝術(shù)處理,甚至可能改變了某些歷史真相,因此在整理時(shí)需要查閱有關(guān)資料進(jìn)行核實(shí),或者與其他當(dāng)事人、或是實(shí)物相互佐證。另外,作為一種文獻(xiàn)資料,在進(jìn)入圖書館館藏體系之前,都必須依據(jù)文獻(xiàn)分類、著錄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編目加工。
3.4開發(fā)利用口述史、影像史經(jīng)過采集整理,正式進(jìn)入圖書館館藏體系,可以供讀者閱讀觀看,也可為社會(huì)提供服務(wù)。對(duì)于口述史、影像史資料,圖書館可以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shì),通過多種方式開發(fā)利用,如將口述史整理成書正式出版,將錄音資料制成錄音制品,影像制品可直接向公眾播放。還可以舉辦各種公益性展覽或是學(xué)術(shù)講座,作為圖書館履行社會(huì)教育職能的重要形式。口述史、影像史資料還可以做成許多專題數(shù)據(jù)庫(kù),在圖書館網(wǎng)站上展示。有條件的圖書館,可設(shè)立專門的口述史、影像史資料閱覽室(或資料室),供讀者平時(shí)瀏覽與利用。特別是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作為國(guó)家總書庫(kù)、中文文獻(xiàn)資源最大收藏機(jī)構(gòu),建議盡快出臺(tái)相關(guān)政策,積極開展口述史、影像史資料采集整理與開發(fā)利用工作,在保存“國(guó)家記憶”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領(lǐng)域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堅(jiān)信,在不久的將來,口述史、影像史必將成為圖書館文獻(xiàn)資源體系中的一支生力軍。
作者:全根先 單位: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