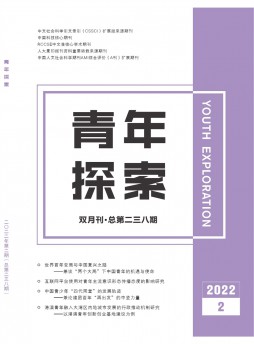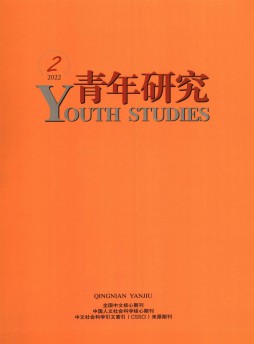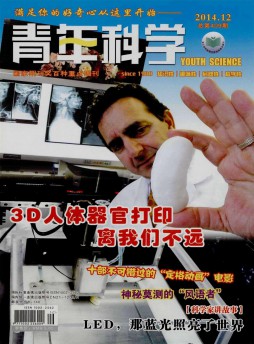青年農(nóng)民工婚姻實(shí)踐的考察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青年農(nóng)民工婚姻實(shí)踐的考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南方人口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短暫的遺忘:“苦痛”記憶的現(xiàn)實(shí)展演、強(qiáng)化與再表述
實(shí)際上,口述不僅僅是語言表達(dá),它還是社會(huì)操演,有具體的場景和聽眾,有具體時(shí)空的限制,有具體時(shí)空條件下的手勢和表情(納日碧力戈,2003)。村莊共同體所共同經(jīng)驗(yàn)的“苦痛”記憶經(jīng)由生動(dòng)鮮活的口頭敘事在村莊中、在代際間流傳,對村民的婚姻觀念有著強(qiáng)大的塑造力,對他們的婚姻行為也有著限定和規(guī)制。趙(現(xiàn)年40歲,男,現(xiàn)仍在外務(wù)工)上世紀(jì)90年代初就率先外出打工,是當(dāng)?shù)氐谝慌獬鰟?wù)工者,趙外出打工幾年后,原本貧窮的家庭逐漸的殷實(shí)起來,趙在外面打工3年后帶來了一個(gè)“媳婦”,據(jù)說女方是四川的,家在一個(gè)山村,人長得很漂亮,當(dāng)時(shí)都夸他有本事,不僅掙了錢,又帶了個(gè)媳婦來,成為茶余飯后人們的談資和羨慕的對象,趙結(jié)婚之后不久,夫妻兩人常常因生活中的小事而爭吵,漸漸的發(fā)展為打罵,留下3歲的女兒,“跑了”。村中的外出務(wù)工青年謝(男,28歲)說“就那個(gè)女的事多,吃不慣這,吃不慣那,俺這天天就是吃面食,她非得天天吃米飯。對趙挑這挑那,其實(shí)是自己經(jīng)不起在農(nóng)村過苦日子,你看村里其他人經(jīng)人介紹的媳婦沒有一個(gè)跑的,就是跑(回娘家),也沒啥,在家消消氣,過兩天就回來了,你看她這,跑了就跑了,到哪找去,留下個(gè)小孩真是遭罪啊,帶個(gè)孩子就難找媳婦了,趙現(xiàn)在都還是光棍,外來的(媳婦)還就是不可信啊。”村里的李(女,70歲)說“男的(趙)在外面打工認(rèn)識的女方,那女的是外面來的,咱也找不清(不清楚)人家家里是啥情況,他男人家里面不也找不清嘛,要不女的跑了咋找不回來呢?要是女方是當(dāng)?shù)厝耍剑ㄋ┘揖驼抑耍F(xiàn)在到哪找,大海撈針,跑了那么多年了也到現(xiàn)在也沒找著,人家是自由戀愛,雙方自己談的,又沒經(jīng)過媒人,也沒有按俺這的規(guī)矩來”。趙的經(jīng)歷成了村莊“痛苦”記憶的現(xiàn)實(shí)展演和再現(xiàn),并再次為帶有經(jīng)驗(yàn)性和警示性的“苦痛”記憶的講述注入了新的活力。對于草根村民而言,真實(shí)的歷史事實(shí)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所記憶的歷史是什么,以及他們對所記憶的歷史的理解和闡釋(肖青,2008)。發(fā)生在趙身上的新的“苦痛”故事與先前的舊的“苦痛”故事建立了勾連,在村民的心中它們具有前后的因果性。趙的故事無疑是村莊關(guān)于久遠(yuǎn)的婚姻的“苦痛”記憶的再現(xiàn)和展演,同時(shí)也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村莊共同體的“苦痛”記憶。時(shí)間不是線性的綿延,空間也不是方位的拓展,而是一種與人的生命狀態(tài)、精神體驗(yàn)、文化歷史甚至宗教觀念緊密相關(guān)的復(fù)雜織體(王炳鈞等,2006)。青年人經(jīng)由新故事對舊有敘事的再次展演和再表述,時(shí)空似乎即刻發(fā)生疊合,他們體認(rèn)到了舊故事所具有的“苦痛”的真實(shí)性,這觸發(fā)了青年的“苦感”。與此同時(shí),當(dāng)?shù)卮迕竦幕橐鲇^念的結(jié)構(gòu)被重構(gòu)和強(qiáng)化,也再次彰顯了由“苦痛”記憶所圈劃“苦痛”的記憶與“閃婚”的促發(fā)21的熟悉的婚姻圈和婚嫁區(qū)間的可靠、穩(wěn)定,而超出這一范圍也就意味著風(fēng)險(xiǎn)和不確定性。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和限定了婚姻圈的范圍和界限。集體記憶與過去有關(guān)———這是一種已經(jīng)經(jīng)過現(xiàn)在的各種需要過濾和塑造的過去(加里•艾倫•法恩、艾彥,2007)。舊的“苦痛”的記憶似乎為此提供了例證,而村中新的“苦痛”記憶又再次佐證了這種觀念的正當(dāng)性與合法性。
二、婚姻實(shí)踐:記憶與規(guī)范的互動(dòng)
Y村當(dāng)?shù)厮駨牡幕閼倌J接幸粋€(gè)變遷的歷程,即:由傳統(tǒng)的婚戀模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閃婚”模式———“媒妁之言,自主決定”的轉(zhuǎn)變,而Y村僅有的超出當(dāng)?shù)厝怂J(rèn)可和可把握空間的自由婚戀⑤的范例(趙的婚戀模式)也成為村民苦痛記憶的構(gòu)成部分和新的表述。具有經(jīng)驗(yàn)性和未來指向性的“苦痛”記憶經(jīng)由實(shí)踐在婚姻模式和婚姻儀式的變遷中發(fā)揮著媒介的作用。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huì)中,婚姻由父母包辦,婚姻當(dāng)事人沒有什么擇偶的自由。這在50、60年代的Y村有著明顯的體現(xiàn),這種婚戀模式雖歷經(jīng)社會(huì)主義改造,農(nóng)村集體化運(yùn)動(dòng),但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更,在集體化的困難時(shí)期,家長的組織地位作用反而得以凸顯。在新政權(quán)建立后,各種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結(jié)構(gòu)都發(fā)生了巨大變革,但在短時(shí)間內(nèi),特有的時(shí)代中在其制度和社會(huì)特性所型塑下的人們的行為和心理并不能即刻也隨之變革,具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在農(nóng)村更加凸現(xiàn)(施磊磊,2008)。我們都通過已由以往經(jīng)驗(yàn)建構(gòu)而來的范疇來領(lǐng)會(huì)感知各種外在刺激和制約性經(jīng)驗(yàn)(布迪厄,華康德,2004:179)。經(jīng)由不同代際之間的表述和建構(gòu),這一集體共同體認(rèn)的記憶生發(fā)出一種反向界定的“力”(power),這種力規(guī)制和形塑著人們的婚戀觀念,并有著經(jīng)驗(yàn)性的啟示功能。一旦越出似乎就會(huì)有與引發(fā)“苦痛”記憶的同樣事件發(fā)生,發(fā)生在村民趙身上的婚姻事件,就是忘卻村莊苦痛記憶的“悲劇”再現(xiàn)和重演。這也致使“苦痛”記憶所具有警示性的作用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在村民觀念中的強(qiáng)化。在鄉(xiāng)村社會(huì)中與血緣、地緣相契合的信任結(jié)構(gòu)同樣呈現(xiàn)出一種差序格局,依血緣、地緣距離由近及遠(yuǎn)向外推衍(施磊磊,2008)。同樣為了防止自己的女兒在外面“上當(dāng)受騙”,也為了相互能有個(gè)照應(yīng),他們都希望女兒嫁得近些。而當(dāng)?shù)嘏郧嗄暌渤鲇趯Α翱嗤础庇洃浿信魅斯脑庥鍪顾齻兣c父母的觀念達(dá)成了一致。村民謝,50歲左右,一子三女,其二女兒(現(xiàn)年27歲)有著“特殊”的經(jīng)歷。村民劉說:“她二閨女以前在外面打工時(shí)與一個(gè)廣西小伙子談戀愛,最后到廣西結(jié)了婚,那個(gè)男的家在一個(gè)窮山溝,家庭經(jīng)濟(jì)情況不好,結(jié)婚后,女的一直在男方家,小孩出生以后,孩子由男方父母帶,男方家人才放心讓兩個(gè)人一起外出打工,將近6年了她二閨女只回過兩回娘家,謝一家子人沒有一個(gè)去過男方家的,據(jù)說辦婚禮時(shí),男方只在當(dāng)?shù)剞k了幾桌酒,請了幾個(gè)親戚朋友,婚禮儀式都非常簡單,在俺這是不可能的。那個(gè)閨女長的確實(shí)好,本來能嫁個(gè)好人家,現(xiàn)在倒好被人家“領(lǐng)跑了”,她家里人雖然生氣但也沒有辦法,家里甚至有了不認(rèn)她這個(gè)閨女的想法。過了幾年她二閨女帶上孩子和男方一塊到家里來。那時(shí)謝的女兒已經(jīng)好幾年沒有和家人見面了,謝見了女兒就是幾巴掌,之后,兩個(gè)人抱頭就哭”。雖然市場化對農(nóng)村的婚戀規(guī)范和觀念有著巨大的沖擊,女性外出務(wù)工者的觀念也在不斷經(jīng)歷重構(gòu),為超出傳統(tǒng)的婚嫁圈和婚姻規(guī)范提供了某種可能,但是謝二女兒的經(jīng)歷無疑成為當(dāng)?shù)嘏酝g人及其家人的“苦痛”記憶,對經(jīng)驗(yàn)性的規(guī)范的僭越似乎就會(huì)有“苦痛”的經(jīng)歷出現(xiàn),在這一點(diǎn)上,當(dāng)?shù)嘏郧嗄昱c其父輩有著一致的觀念。“在外面打工的,肯定都是家里條件不好的,說不定還沒有俺這經(jīng)濟(jì)條件好呢,要不誰去打工受罪啊”,“與其到外地去吃苦受累,還不如在家門口找個(gè)婆家享福呢”。穆的故事、趙的故事以及村中趙二女兒的故事之間有著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即都有著對村莊原有的負(fù)載著村民實(shí)踐理性的婚姻規(guī)范和婚嫁區(qū)間的僭越,并且有著一致的結(jié)果:苦痛事件的出現(xiàn),這種帶有警示性的故事的不斷建構(gòu)和表述致使當(dāng)?shù)鼗榧奕Φ南鄬袒6@種婚嫁圈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劇了當(dāng)?shù)厝说幕橐鼋箲],因?yàn)樵谙鄬袒幕榧奕?nèi),適婚男女的比例和絕對數(shù)量是一定的,為了給自己的子女“說上”在既定的人選中擇取好的,更加匹配的對象,就必須趁早挑選。這在一定程度上為當(dāng)?shù)鼗橐龅哪贻p化、快速化提供了助力。此外,由于外出青年務(wù)工人員在城市中的工作性質(zhì),工作時(shí)間的緊迫性,以及他們在城市人眼里的被社會(huì)“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致使他們在城市中的戀愛機(jī)會(huì)空間被擠壓殆盡,很難進(jìn)入城市婚戀市場。加之外出青年務(wù)工人員獨(dú)立的經(jīng)濟(jì)地位和自決意識的生發(fā)以及父母在子女婚姻決策權(quán)上的式微這些背景構(gòu)成了他們的婚姻實(shí)踐的大的背景框架,在這一框架下,他們經(jīng)由實(shí)踐理性的選擇,借用傳統(tǒng)婚姻的模式和自由婚戀的內(nèi)核,即這種兼具傳統(tǒng)性和現(xiàn)代性的婚戀模式———“閃婚”模式。雖然他們在城市中也習(xí)得了蘊(yùn)含著現(xiàn)代性的各種觀念和行為方式,但是隨著場景的轉(zhuǎn)換,他們在鄉(xiāng)間場域被塑造的習(xí)性又重新被喚起,并在鄉(xiāng)間場景中實(shí)踐著屬于自己的“閃婚”邏輯(施磊磊、王瑤,2010)。因?yàn)椤伴W婚”的模式從訂婚到最終的結(jié)婚會(huì)有相當(dāng)可觀的花費(fèi),在女方?jīng)]嫁給男方之前,依照當(dāng)?shù)氐幕榧蘖?xí)俗,男方在重大節(jié)日要帶著禮物到女方家走動(dòng),雖然在婚后男方也要在過年過節(jié)時(shí)到女方家走動(dòng),但是所需要禮物的費(fèi)用相較女方嫁給男方之前卻大大降低。為了減低到女方家走動(dòng)的花費(fèi),男方一般會(huì)選擇迅速完婚。在鄉(xiāng)土場域內(nèi)縈繞著“苦痛”記憶的長期婚姻實(shí)踐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衍生出來的應(yīng)對不確定性和失敗婚姻的策略會(huì)在村民的心中逐漸積淀出一種具有地方質(zhì)素的感知能力。這種地方感是日常生活中積累起來的一種感覺經(jīng)驗(yàn)。這種感覺經(jīng)驗(yàn)只有在一定的區(qū)域內(nèi)才是有效的,越出此邊界,感覺世界就會(huì)消失。這種感覺經(jīng)驗(yàn)不具備普遍意義,而只具備區(qū)域性特征(楊念群,2004)。這種在鄉(xiāng)土情境特有的婚姻實(shí)踐基礎(chǔ)上所生發(fā)出來的地方感對村民的婚戀行為有著獨(dú)特的導(dǎo)引作用,鄉(xiāng)民們往往憑借從感覺世界提煉的原則安排日常生活(楊念群,2004),在地方感的導(dǎo)引下構(gòu)建出的為當(dāng)?shù)剜l(xiāng)民可把控的婚姻實(shí)踐規(guī)范進(jìn)一步規(guī)制鄉(xiāng)民的婚戀實(shí)踐行為。記憶在婚戀的特有實(shí)踐邏輯中是不可或缺的序列,起著中介作用。婚姻實(shí)踐的整體互動(dòng)邏輯圖示如圖1所示:
三、結(jié)語與討論
Y村村民共同體所共同表述和建構(gòu)的集體的“苦痛”記憶塑造著當(dāng)?shù)厝说幕閼儆^念并影響著當(dāng)?shù)鼗橐瞿J降淖冞w。原本發(fā)端于個(gè)體身上的婚姻失敗經(jīng)驗(yàn)的故事經(jīng)由代際之間的口述被不斷表述和傳遞著,這種帶有經(jīng)驗(yàn)性和未來指向性的集體可感的“苦痛”記憶具有一種反向界定的力(power),形塑著當(dāng)?shù)卮迕竦幕閼儆^念、規(guī)約著當(dāng)?shù)厝说幕閼傩袨椤M瑫r(shí)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當(dāng)?shù)厝说幕榧迏^(qū)間,這種試圖摒棄可能引起“苦痛”記憶的“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因素的企圖將婚嫁區(qū)間界定在了村民熟悉、并承載著社會(huì)資本和信任的鄉(xiāng)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村莊共同體所不斷表述和建構(gòu)的“苦痛”記憶具有當(dāng)?shù)卮迕窕橐鰧?shí)踐經(jīng)驗(yàn)代際傳遞積累的性質(zhì)。村莊中新的婚姻失敗故事的發(fā)生是作為忘卻集體“苦痛”記憶的身份出現(xiàn)的,而這構(gòu)成了對舊敘事的重新表述和建構(gòu),同時(shí)從另一層面上強(qiáng)化了村民們對“苦痛”記憶的印記。在談話和交流中可制造過去,建構(gòu)過去的記憶(哈拉爾德•韋爾策,2007:105-106)。為了不讓同樣的事件在自己身上發(fā)生,家庭成員之間、同輩群體之間在不斷的傳述著這一記憶,而這種村莊共同體的現(xiàn)實(shí)利益需要使這一發(fā)生在個(gè)體身上的關(guān)于婚姻的“苦痛”事件轉(zhuǎn)化為了村民集體的一種苦痛的記憶。如康那頓所言,我們對現(xiàn)在的體驗(yàn)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有關(guān)過去的知識。我們在一個(gè)與過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聯(lián)系的脈絡(luò)中體驗(yàn)現(xiàn)在的世界,從而,當(dāng)我們體驗(yàn)現(xiàn)在的時(shí)候,會(huì)參照我們未曾體驗(yàn)的事件和事物(保羅•康納頓,2000:2),從而使得過去的記憶具有經(jīng)驗(yàn)性和可參照性,這也構(gòu)成了代際之間苦痛記憶不斷傳遞、表述和再建構(gòu)的動(dòng)力。經(jīng)由實(shí)踐理性的選擇,他們借傳統(tǒng)的婚姻框架,和現(xiàn)代的婚戀內(nèi)核,塑造出來新的婚戀模式:閃婚模式———“媒妁之言,自主決定”。傳統(tǒng)的婚姻習(xí)俗被界定在熟悉的鄉(xiāng)村,而外出青年務(wù)工人員經(jīng)濟(jì)的獨(dú)立和現(xiàn)代觀念的生發(fā),又為自主決定提供了現(xiàn)代內(nèi)核。但這與布迪厄所講述的情形有所不同,布迪厄指出父母權(quán)威的動(dòng)搖,年輕人對新價(jià)值的向往,剝奪了家庭在婚姻締結(jié)過程中的主要中介作用。與此同時(shí),“媒人”的介入也越來越罕見(布迪厄,2009:47)。在Y村雖然父母等家庭成員在婚姻決策的權(quán)力上在不斷式微,但媒人的介入并非越來越罕見,而是作為成就一樁婚姻的必要前提出現(xiàn)的。而這種差異之所以出現(xiàn)與Y村特定的婚姻實(shí)踐有著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在市場化的語境下,婚姻行為主體自身婚姻觀念和經(jīng)濟(jì)地位的變化以及不同代際間被不斷表述的“苦痛”記憶與行動(dòng)主體婚姻實(shí)踐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對當(dāng)?shù)鼗橐鲆?guī)范的建構(gòu),在這一婚姻框架中有著眾多的婚嫁儀式和不宜男女雙方父母參與其中的彩禮價(jià)格的商討等事宜,媒人的中間人角色自然不可或缺。市場化的語境中,經(jīng)由記憶作為中介,行為主體的婚姻實(shí)踐與當(dāng)?shù)氐幕橐鲆?guī)范有著動(dòng)態(tài)的互動(dòng),促使婚姻模式的變遷,即由傳統(tǒng)的婚戀模式向閃婚模式的變遷,而這種被行動(dòng)主體建構(gòu)出的新的閃婚模式和婚姻規(guī)范又在規(guī)制著當(dāng)?shù)卮迕竦幕橐鰧?shí)踐。
作者:施磊磊單位:安徽工業(yè)大學(xué)管理科學(xué)與工程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