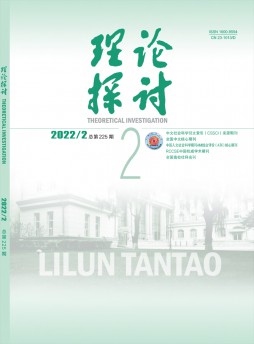探討山地民族教育與本土知識傳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探討山地民族教育與本土知識傳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古苗寨平鰲的教育發展回顧
平鰲是位于貴州省錦屏縣境內清水江畔的一個古老苗寨,在平鰲苗寨的歷史上,這里曾是獨立于王化之外的“生苗”地方,直至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平鰲納版入籍,正式成為黎平府屬地,幾經變遷后,1992年改屬錦屏縣平略鎮。平鰲歷史悠久,民族文化濃郁,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尊師重教、人才輩出之地。“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有書不讀子孫愚,有田不耕倉中虛”,這是至今仍流傳于平鰲苗族的兩句諺語,從中生動體現出了平鰲苗族先輩對教育的深刻認識和理解。
(一)以生產生活技能為主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現代教育理論中三大基本教育類型之一,[5]是人類個體最為基本的教育形式。“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家庭是兒童在入校接受學校教育之前最為重要的教育場所,父母的為人處世和言傳身教對于子女性格的形成、生活習慣的培養以及智力的開發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平鰲苗族的家長歷來都相當重視子女的家庭教育。從懂事起,男童便開始受到父親關于犁田插秧、開山栽杉、架箱放排、抓魚狩獵、砍柴燒炭、待人接客等基本生產生活技能和待人接物之道的教育和熏染。而女孩子則更多是受到母親關于燒飯洗衣、砍柴割草、燒酒釀醋、紡紗織布、刺繡蠟染、唱歌跳舞等家務和才藝的訓練。關于苗族家庭教育的實際狀況,黔東南苗族理詞有形象的描述:里屋的娘,中堂的爹,母教閨女,父教兒郎,哥教弟弟,姐教妹妹。教才明事理,導才開心竅。相教共做吃,互導共做穿。姑娘要手巧,男兒要勤勞。[6]在婦女日常生活的每一環節,通常都會用背帶背著孩子。可以說,幾乎所有平鰲苗族的小孩,都是在母親的后背上長大的。正因如此,父母對子女生活技能的教育,并非是具體明確的指導,而大多是在長期耳濡目染的過程中逐步教會的。另一方面,由于平鰲苗族的農業生產主要以傳統的耕作方式為主,農事活動受時令的影響和限制較為明顯,所以在插秧、收割等農忙季節,人們往往會忙于農事而無暇顧及家中各項事務,此時小孩便會承擔起做飯、洗衣、割豬草、打掃衛生等日常家務勞動,在家庭生活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通常情況下,平鰲苗族小孩往往在小學二、三年級時就開始陸續參與家務勞動,經過長期實踐逐漸學會了生產生活的技能。
(二)以民族文化為主的村寨社區教育
村寨社區是我國廣大農村百姓生產生活的基本地理單元,大多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儀式習俗都是在村寨社區中得到最集中的展現,平鰲苗寨亦是如此。在平鰲苗族,最具全社區性質的活動莫過于一年一度的苗年、重陽節等重大節日以及婚禮、喪葬等生活習俗。在這些節慶活動中,當地苗族的文化特色得以集中的展示,社區中的小孩甚至一些淡忘了本民族生活習俗的年輕人都會受到了最直觀的教育。在苗年和重陽等節日期間,往往都會舉行全民性質的大型祭祀儀式以及斗牛、斗鳥、對歌等苗族傳統競技活動。而在婚禮或喪葬儀式中,人們則會演唱相應的迎親或哭喪等苗族歌曲。無論是過年過節還是婚喪嫁娶等重大場合,通常都是小孩子最喜歡湊熱鬧的地方,在這些場合之下耳濡目染,小孩子自然而然地習得了各種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知識和技藝。此外,平鰲苗族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教育場所———祠堂。除了祭祀祖宗外,祠堂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年輕人進行教育。每年的清明節期間,是平鰲苗族祭祀祖宗的重要日子,這天全宗祠的男女老少都會集中在祠堂中拜祭祖宗。拜祭過程中,主持拜祭儀式的值年長都會詳細講述祖先艱苦創業的光輝歷史,并教育后代人要繼承先祖遺志,發揚先祖優良傳統,孝敬老人、關心小孩等。在平鰲姜家上祠中,“出弟”、“入孝”的規訓雕刻在祠堂正門的左右兩側,時時教育子孫后代要謹記祖宗遺訓。
(三)以讀書識字為主的學校教育
平鰲的學校教育肇始于清朝乾隆年間文人姜化隆開辦的本村第一所私塾。同一時期稍晚的時候,本村的姜兆黃、姜為宏、姜相榮、姜承智、姜宣藩、姜宣昊甚至文斗苗寨的姜周仕均也紛紛在平鰲設立了私塾。由此,平鰲苗族的學校教育日漸興起并發展壯大。這些私塾先生大都是當地熱心教育事業的地主富戶,他們招收學徒不受門戶之見、貧富之分的影響,有錢就收取一定量的糧食谷物作為學費,家庭貧困的學生則無需繳納學費而同樣受到教育。受這些熱心人士的影響,本村的其他村民百姓也積極支持私塾的發展。由于當地山高坡陡且居住分散,為了解決學生求學時上山下坡的不便條件,村民們便自發組織修建了通往私塾的小路,不但極大地方便了學生的往返,而且在當地形成了一種尊師重教的濃郁氛圍。平鰲苗族的私塾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為當地民族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民國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國民政府在平鰲設立了平鰲初級小學,由此開啟了該村政府辦學的新時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平鰲承襲了平鰲初級小學的建筑和設施,繼續發展本村的教育事業。半個多世紀以來,為了不斷適應本村教育發展的需要,平鰲小學先后進行了四次較大規模的改造建設,其中前三次都是在原址的基礎上進行擴建或改建。然而,由于原校址位于村寨正中央,隨著當地人口的不斷增長,原有的校舍已經不能滿足學生求學的需求,2005年,為了創造一個安靜的教育和學習環境,學校通過多渠道籌措資金,在村子西口另辟新地進行重建。新建的學校占地面積5323平方米,校舍面積1068平方米,建有教學樓和教職工宿舍各一幢,以及一個960平方米的硬化操場,一條長120米的渣土跑道,并購置了單雙杠、乒乓球臺、籃球架等各種體育設施。栽植各類花草樹木兩千余株,綠化草皮420平方米,鐵欄桿圍墻總長175米。在教學設施方面,建有一個18平方米的圖書資料室,藏有各類圖書近3000冊,可以滿足各個年級段的學生以及村民的閱讀需求。平鰲小學現有專職教師8名,一至六年級6個教學班,在校生共計88人。學校開設有語文、數學、英語、科學、品德、美術、音樂、體健、綜合、地方知識等課程。截至目前,平鰲小學走過了大半個世紀的歷程,已經成為以三板溪、桃子坳、平鰲(即原彰化鄉所屬三村)三村所組成的教育片區完全小學。近幾年來,國家實施了“兩免一補”的教育政策并逐步擴展至整個義務教育階段,平鰲小學現有六個教學班的88名學生全部免除了學雜費和書本費。對于成績優異、家庭困難的學生,學校還實施了“一幫一”的幫扶機制,確保學齡兒童都能夠正常入學教授教育。2008年,平鰲順利實現了“兩基”目標,并通過國家“兩基”評估驗收,平鰲教育的發展由此邁上了新的臺階。
二、教育發展與本土知識傳承
少數民族的本土知識,是在本土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下產生的,與本土的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它既是少數民族生存性智慧的結晶,也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體現。民族地區的教育與一般教育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它承擔著傳承本民族文化知識的功能,這關系到我國的民族團結和文化安全問題。民族教育學家哈經雄、滕星等人在《民族教育學通論》一書中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教育,在擔負人類共同文化成果傳遞功能的同時,不僅要擔負起傳遞本國主流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時也要擔負起傳遞本國各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二人還進一步指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目的在于“繼承各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加強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促進多民族大家庭在經濟上共同發展、在文化上共同繁榮;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與和睦相處,最終實現各民族大團結”。[7]平鰲小學在苗族本土知識教育方面作出了一些探索,開設了“地方知識”這一門課程,不過并未配備專職的教師,而是邀請那些在苗語、山歌、剪紙、刺繡、釀酒等方面有專長的村民來為學生授課,授課時間根據授課人的時間臨時安排,學生則根據自己的興趣組成不同的小組進行集中學習。在課程內容上,則是授課人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體會而自由發揮,所以這門課程也沒有編制相應的固定教材,這就使得“地方知識”課程無法達到系統連貫地講授本土文化知識的目的。筆者認為,要想系統而連貫地講授民族本土知識,除了要提高學校以及學生的認識之外,主要應從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和人才培養等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在課程設置方面,平鰲小學成功之處就在于打破了平時的班級單位,而以興趣為標準組建新的學習小組進行集中學習。在此基礎上,應對不同的課程內容進行系統評估,根據課程內容的性質系統規劃課內與課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授課形式,從而使本土知識得到活態傳承而非死板的知識。其次,開設本土知識課程,就必須對本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知識進行總結提煉,并分門別類地編制相應的教材,從而使教師的講授和學生的學習都有章可循。再次,本土知識課程的講授,要求授課人必須熟知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并且能夠熟練運用漢語和本民族語言授課,這是目前多數民族地區開設本土知識課程的一大難題。因此,培養既諳熟本土知識又能夠熟練運用苗漢雙語授課的專業人才是化解目前民族教育中本土知識課程困境的關鍵所在。
作者:胡展耀單位:貴州師范學院貴州民族學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