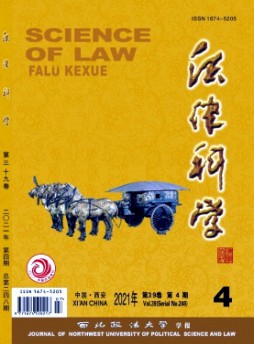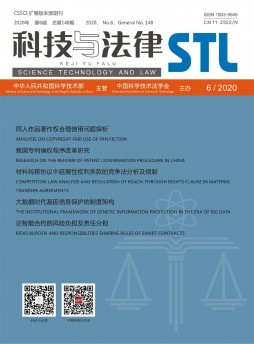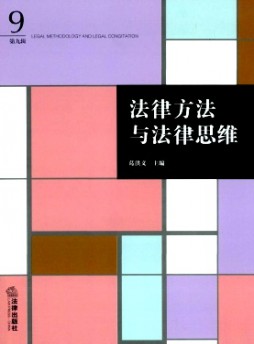法律研究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法律研究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但是在現代民法法系各國的民法典中,鮮有看到有關于"人"這一概念的直接定義。譬如在德國民法典中,首先躍入讀者眼簾的, 并不是"人"而是"自然人"--"第一條 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于是我們不禁要問,究竟什么才能稱作是民法上的"人"?民法上的"人"究竟是什么樣的?
一、人與自然人
1、"自然人"語詞的雙重內涵
"自然人"這一漢語語詞,在不同的語境下有著不同的含義。從其原始的字面意思來看,即是指依自然規律出生的人,指向的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與其對等的有德語中的"Mensch"以及羅馬法中的"homo"等。然而,在民法中,正如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所言,"’自然人’不是自然生存的生物意義上的人的概念的翻版。’自然人’這一概念表述了生物性意義上的人因被立法者賦予享有權利能力資格而成為民事主體或者成為法律人格的法律確認過程或邏輯歸結。"其含義應當與德語中的"Person"或羅馬法中的"persona"對等,指的是法律上的人,即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很顯然,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差距。那么,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人該如何成為一個法律上的"自然人"?"為權利之主體,第一須有適于享有權利之社會的存在,第二須經法律之承認。" 作為"Mensch"的自然人,已經具備了享有權利的肉體,即自然屬性;倘若他生活在一個民法社會中,他便具備了享有權利所需的第二個屬性--社會屬性;這時候,他只需要第三個屬性--"法律之承認"便可成為一個"Person"。從這里可以看出,其實自然人并不必然是民法上的"人"。在奴隸社會,這一點尤其明顯。奴隸雖然也是生物意義上的"自然人",但是完全不具備人格,只是一個主體支配的客體而已。然而,在當代,一切自然人必然是民法上的"人",而民法上的"人"也僅限于自然人與法人(筆者不承認第三類民事主體)。現代社會普遍而平等的人格授予漸漸消磨了人們對于人格的敏感記憶。然而,有關平等且無差異的人格的民法共識顯然不是從古至今就融入民法的。
2、只有自然人才是"人"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普遍認為,既然自然人是上帝的創造物之一,那么和自然人一樣,作為上帝創造物的動物、植物乃至沒有生命的物體也可以具有人的品格。其實不僅僅是歐洲,古羅馬法把神、惡魔當做"人",古埃及把貓當做"人",泰國把白象當做"人"……不一而足。哪怕是到今天,恐怕仍然有相當多的人會認為除卻自然人以外的很多事物都可以成為"人格"的載體。但是隨著人類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這種制度和觀念發生了轉變。在13世紀,著名思想家托馬斯·阿奎納提出:"自然人是上帝所創造的唯一的、既作為被創造物又同時作為其他的被造物之王或者主人的造物,這一點可以從圣經中看出來。"這種理論將自然人從"被造物"中獨立出來,成為"只有自然人才是人"這一理論的基礎。其后,隨著15、16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這一理論終于得到了其在法律上的最終確立與肯定。由于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發現了巨大的自然資源,如果認為這些動物、植物甚至沒有生命的礦藏和自然人一樣具有人格并對其加以法律上的保護的話,顯然不利于新世界的開發。
3、一切自然人都是"人"
"只有人格人是法律主體, 人并非必然是法律主體。"很顯然,雖然只有自然人才能成為民法上的"人",但不代表所有的自然人都是民法上的"人"。自然人因為擁有上帝給予的智慧而從"被造物"中獨立出來,擁有"人性"或"人格"。最初的時候,這所謂的"人性"或"人格"并不是一起給予每一個人,它僅僅局限于一個家族或者一個集體當中。在這個家族或者集體中,人和人之間存在著法律關系,對彼此負有權利和義務,是"人"。但是不同家族或集體之間就不存在什么法律關系,因此敵人對自己來說就算不上"人",即使殺死他也不用負什么法律責任。這顯然是較為原始的宗族式集體主義社會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因為有限的生產能力不得不依附家族、集體。奴隸離不開奴隸主,農民離不開地主,家族成員離不開家長,平民離不開權貴。信仰的差別、貴賤的區分、財產的多寡都可以成為是否具備人格的理由。然而,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沖破了這些限制。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民法中"人"的概念。理性法學家和啟蒙思想家們認為,人格應是法律中最高級的概念,它應當超越地域、種族、宗教的限制,不分彼此地給予一切自然人,除此以外不應當附加任何條件。這無疑是民法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它與平等、公平正義等原則緊緊相連,成為與等級社會、異教徒法、奴隸制相抗爭的有力武器,并為近現代民法運作模式提供了技術基礎。
二、人與人格、權利能力
1、人與人格的異同
人格,來自于羅馬法中的"persona"一詞,最初指的是戲劇中的假面具。后來經過羅馬法學家的引申,成為一個法學上的概念,指代"享有法律地位的任何人"。從這一點上來看,人和人格的概念十分接近。事實上,著名法學家愛杜亞德·惠爾德在其1905年出版的《自然人和法人》一書的開始就介紹說:"人的概念與人格的概念在法律中常常是在同一個意義上加以使用的。這兩個詞表示的是同一個特性, 一個具有多方面屬性的東西。因為沒有人不具有人格, 同時人格也離不開人, 所以這兩個概念常常可以被作為一個概念來使用。"不過嚴格地來說,人和人格不是一回事。這就好比面具或許可以代表面具后的人,人和面具也確實難舍難分,但是畢竟人和面具是兩個事物。人格在法律上至少具有三重含義:一、指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的個人和組織。二、作為民事主體的必備條件的民事權利能力。三、從人格權客體的角度來說,人格是一種應受法律保護的利益,通常稱為人格利益。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只有采第一種含義時,人和人格才是同義的。
2、人與權利能力
權利能力是指法律關系主體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或資格。這一概念在現代民法中的地位顯得極其重要,以德國民法典為例,第一條規定的便是關于權利能力的內容。當代大多數民法法系國家的民法典和民法學著作中也往往充斥著"權利能力"這樣的詞語。與之相較而言,"人"這一概念則愈發顯得難覓蹤跡。這就又回到了我們在本文一開始所討論的問題。為什么自然人、權利能力等概念在民法典中首先得到規定,而"人"這樣一個總括性質的重要基礎概念卻顯得相對落寞?這還要從德國著名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的有關理論說起。康德提出,"(法律上的)人是指那些能夠以自己的意愿為某一行為的主體。""人不能服從那些不是由他(他自己單獨或者和他人一起)、而是由別人制定的法律。"根據這一理論,自然人以其自身的能力對己負責。換句話說,人之所以為"人",不是因為他天然地具有上帝賜予的絕對智慧,而是因為他能夠對自身的權利義務抱有善意或者惡意的心態,以及對其行為是有益還是有害的內心意思。這樣,法律上的"人"的概念就和自由這一基本原則緊緊聯系在了一起,民法的自由理想也因此得以在"人"的理論中得以實踐和體現。顯然,康德的這一理論更加強調人在法律關系中的作用,強調的是"法律關系的主體"而不是"人",雖然這個"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當時很清楚的是且只能是自然人。
康德的理論的一個間接后果便是催生了"權利能力"這一概念。因為既然強調的是"法律主體"而非"人",那么對"人"這一概念的探討就變得不再那么重要。大家更加關注的是"人"能在法 律關系中發揮什么作用。因此"權利能力"理論的誕生也理所當然。至此,民法上的"人"已高度抽象,甚至于已經剝離出"權利能力"這一相對獨立的概念。而真正確立權利能力在德國法中的地位的是德國著名法學家薩維尼的法律關系理論。在這個以法律關系為中心的理論體系中,人只是建立法律關系的必要條件而已。決定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承擔者的要素是權利能力而非人本身。人究竟是什么不再重要,因為人不再是法律的基礎,與作為建立法律關系的關鍵要素的權力能力比起來,自然得到相對較少的關注。而在此理論指導下編纂的德國民法典則沒有像法國民法典一樣單獨設置"人編",也沒有對"人"作過多的論述。很顯然,這時候的"人"只是一定的權利與義務、一定的時間與地點、一定的法律制度與后果的連接點而已。這樣的"人"的概念只是一個工具,立法者借助這個工具去建立作用于社會的規范體系。
3、權利能力與人格的比較
關于這兩個概念,很多學者認為它們屬于同一個范疇,理由是它們都是主體地位在民法上的肯認。"民事權利能力、人格、民法中的地位實質是一回事,這是成為民事主體的基本條件。"而另外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權利能力僅僅是能夠作為權利義務主體之資格的一種可能性, 同權利主體顯然有別。"還有的觀點認為"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統一,構成自然人主體資格的完整內容。所以,自然人的主體資格或者人格就是指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我個人認為,權利能力和人格還是不同的概念,至少不完全相同。根據之前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人格"有著多重的含義,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與其說它是一個法律概念,倒不如說其是一個倫理學上的概念。而權力能力則是民法上的"人"不斷抽象化的結果。它是一種技術化的產物,本質上是"人"的一種特征,作為建立法律關系的關鍵因素而存在。當"人格"是"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的個人和組織"的時候,權力能力和行為能力只是其資格或能力的集中體現;當"人格"是"法律賦予的成為民事主體的資格"的時候,它才和權力能力相同;而當"人格"是"自然人的民事主體資格"的時候,除了民事權利能力,它可能還包括民事行為能力。所以說,不能夠簡單地將人格與權利能力等同,要視情況而定。
三、人與法人
1、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1804的法國民法典并沒有規定關于法人的有關內容,因為法國民法典是極端浪漫的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拿破侖擔心封建勢力會借助有法律主體地位的團體或組織卷土重來,因此在民法典中貫徹了絕對的個人主義。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民法也由完全的個人本位逐漸向社會本位靠攏。1900的德國民法典終于開創了法人制度,它借助"權利能力"這一概念成功地讓自然人與法人得以在同一民事主體制度下共存。
德國民法典的創造基本上規定了現代民法上"人"的表現形式。現當代的多數學者都同意這樣的觀點:民法上的"人"不僅指自然人,還包括法人。當然,為了方便的需要,"人"這一語詞有時候僅指自然人,作為與法人相對立的民事主體而存在。
不過對于這樣的"二元式"的有關民法上的"人"的表現形式的理論,有人持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民法上的"人"不僅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還包括合伙等第三類民事主體。甚至有人還認為,國家有時也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筆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支持第三類民事主體的學者的理由主要是合伙等團體組織具有權利能力,它們所欠缺的只是責任承擔能力,給予它們民事主體地位將更加有利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然而,合伙等團體組織畢竟是依靠其每一個成員的財產對其整個組織負責,其本身并不具有獨立的財產和責任。與其說其是一個獨立的民事主體,倒不如說其是一群懷有共同目的的自然人的集合。所以我個人認為所謂的"第三類民事主體"僅僅是自然人的延伸而已。至于國家則是完全的公法主體,雖然有時候可以參與民事活動,但并不能因此而獲得獨立的民事主體地位。
2、法人本質的相關學說
(1)法人否認說。根據這個學說的觀點,法人是完全不存在的。所謂"法人",不過是多數個人或財產的集合。此說又可細分為目的財產說、受益主體說和管理者主體說。法人否認說完全無視現實生活中大量具有獨立功能的社會團體、組織,在民法的社會本位趨勢越來越明顯的今天,顯然已不符合潮流,在這里也就不多做介紹。
(2)法人實在說。此說認為,法人是確實存在的客觀實體。這就好比生物意義上的自然人,在法律賦予其法律上的地位之后,成為法律上的"自然人"。而法律為這樣的"自然人"設計制度、建立秩序,正是由于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著生物意義上的自然人。換句話說,法律現象必有其現實生活中的基礎。從這點出發,"法人"的概念和制度之所以形成,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具有獨立地位的社會團體或組織作為依托。這一學說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米香(Michoud)和沙萊耶(Saleilles)。而德國學者貝色勒(Beseler)和基爾克(Gierke)等進一步發展了這個學說。他們提出法人有機體說,認為法人本質上是自然有機體或社會有機體,是真實而完全的人。作為自然人,它的有機性在于具有個人意思這一因素,而法人也有得以成為有機統一體的意思因素,即具有不同于個人意思的團體意思。這種法人有機體的觀點,在現今世界有著十分眾多的支持者。
(3)法人擬制說。此學說的創造者依然是德國偉大的法學家薩維尼。他認為,法人之所以具有人格,完全是立法技術的結果,即人們為了滿足社會需要而比照自然人為某些社會團體或組織擬制法律上的人格。"正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卡爾·拉倫茨所言:’對法人言,其所謂’人’則具有法律技術上及形式上的意義,乃類推自然人的權利能力,而賦予人格,使其得為權利義務的主體,而滿足吾人社會生活的需要。’"至于法人本身,由于其并不具有類似于自然人一樣的自由意志和意思表示能力,所以并不能天然地成為民法上的"人"。應該說,薩維尼的法人擬制說比較符合社會現實,也易為常人所理解與接受,是受到最多推崇的有關法人本質的學說。
四、民法上的"人"的構建及其影響
1、"理性人"的構建
經過前面一系列的論述,我們對所謂民法上的"人"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印象:由自然存在的生物意義上的人,到擁有"上帝賜予的絕對智慧"的人;由純粹的自然人民事主體,到包括具有獨立民事主體地位的社團或組織--法人;由多樣化的現實中的人,到抽象的無差異的權利能力……顯然,民法上的"人"的構建體現出由感性走向理性、由具體走向抽象、由倫理性走向技術性、由多樣化走向統一化,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的總體過程與趨勢。這種構建過程的最終結果便是誕生了一個民法上的"理性人"的模型。而所謂的理性,"即誠如康德所說的, 理性不僅僅是一種人類認識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規律的能力, 而且也包括人類識別道德要求并根據道德要求處世行事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使人與動物相區別, 并且使得人具有尊嚴。所以, 人永遠得為目的而非為手段。" 在這樣的"人"的模型的指導下,每個個人的情感、性格、偏好都被一齊剔除,民法永遠不需要知道他們來自于何方、從事何種職業、擁有何種社會地位,因為他們的血肉和五臟六腑已被掏空,統一戴上民法為他們準備好的無差別的完美的"理性"面具,作為一個抽象的民法上的主體而存在。
2、"理性人"假設的影響
"理性人" 構建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產生了一個機械的無任何色彩的民法世界。這種情況帶來的好處是:在技術上,提供了統一的運作模式和基礎,便于法律規范發生其作用,提高了法律關系變動的效率,大大提升了民法作為一個社會調節器的能力;在倫理上,抹平了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各種差異和不公,通過理性讓人們擺脫家庭、社會的諸多束縛,走向自由,有利于公平正義的實現;在經濟上,有利于加快加強民事主體 之間的競爭與交流,同時也使得民事主體的行為變得可以預測,增強了交易安全。然而,它的缺點也顯而易見:過于統一的權利能力的授予缺乏靈活性,即便有"行為能力"這個緩沖工具的存在,依然無法掩飾其僵硬性;現實世界中的人畢竟是各種各樣的,追求平等是沒有錯,但是這同時也會喪失對個體的具體的人文關懷;將法人與自然人簡單地通過權力能力統一于同一民事主體制度之下,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反而可能造成實際上的不完美。
當然,所謂"理性人"的假設所帶來的影響遠遠不止以上列舉的這些。然而對于這樣的結果,我們又應當做出怎樣的思考?
五、對民法上的"人"的重新考量
眾所周知,民法是一部以人為本的法律。民事主體制度是以自然人(個人)為本位進行設計的,法人的擬制完全是類比自然人進行的,而其他組織則僅僅是自然人的延伸而已。所以說,個人是民事主體的最基本的原型。然而,隨著近現代民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團或組織以法人的形式涌現出來,個人的形象變得越來越抽象、越來越虛弱,似乎很難再得到往日的關注與重視。筆者認為,需要重新認識個人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價值。顯然,如果我們一味地追求民法在技術上的完美與成功,反而有可能會背馳于民法原本的價值與宗旨。因此,我們需要對抽象的"人"重新注入血肉,追尋新的方向。
第2篇
1.1認識錯誤的概念刑法中的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刑法上的認識與客觀實際情況存在不正確的認識。行為人發生這種錯誤時,就產生了是否阻卻故意的問題。[1]故意與過失是認識因素的范疇,行為人的認識因素不同,故意或過失會影響到行為人的意志因素,進而影響到犯罪行為的罪過形式。
1.2認識錯誤的分類我們知道,認識錯誤及其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系密切。故意或過失作為認識因素的兩個方面,認識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刑事責任的承擔。可見,在發生認識錯誤的場合下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追究理應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認識錯誤的分類。我國刑法理論采取傳統的分類方法,把認識錯誤分為法律上認識的錯誤和事實上認識的錯誤。[2]
2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
2.1法律認識錯誤及刑事責任法律認識錯誤,有學者稱之為“違法性錯誤”。本文采納“法律認識錯誤”的說法,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及刑事處罰存在不正確的認識。法律認識錯誤通常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2.1.1想象犯罪行為不構成犯罪,行為人誤認為構成犯罪,即刑法理論上通常所說的“幻覺犯”。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行為的性質,即行為人是無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為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而行為人誤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即行為人的行為性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處理,而不是以行為人的意志為轉移。
2.1.3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行為在罪名和罪數、量刑輕重有不正確的理解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已構成犯罪,但對其行為觸犯了何種罪名,應當被處以怎樣的刑罰,存在不正確的理解。筆者認為這種錯誤認識并不影響其犯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既不影響定罪,也不影響量刑,司法機關按照他實際構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于法律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在刑法理論上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二種學說。否定說認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責任”。筆者贊同“不知法不可免責”的觀點,不承認法律認識錯誤可以阻卻刑事責任。總之,筆者認為,法律上的認識錯誤,不論上述列舉的何種情況,都不影響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和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是:不免責,按照法律的規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實認識錯誤與刑事責任所謂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的事實狀況的錯誤認識。事實認識錯誤可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試圖從客體的認識錯誤、對行為性質、犯罪對象錯誤、犯罪手段錯誤、打擊錯誤、因果關系認識錯誤[3]。五個分類對事實認識錯誤及其刑事責任進行論述。
2.3.1客體的認識錯誤客體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侵害的客體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符合。客體認識錯誤可能影響罪過形式、犯罪的既遂與未遂,甚至可能影響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對象的認識錯誤所謂犯罪對象錯誤,是指行為人預想加害的對象與實際加害的對象不一致。
對行為對象的認識錯誤,有以下幾種情況:①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相同的社會關系。②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的社會關系不同。③誤將犯罪對象作為非犯罪對象加以侵害。④誤將非犯罪對象作為犯罪對象加以侵害。
2.3.3行為認識錯誤行為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性質或方式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符合。行為認識錯誤主要包括兩種情況:第一,行為性質認識錯誤。第二,行為方法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實施行為時對自己所采取的方法產生不正確認識,從而影響危害結果的發生。
2.3.4犯罪手段的認識錯誤指行為人對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認識錯誤。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況:①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來會發生危害結果,但行為人誤認為不會發生危害結果。②行為人本欲使用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但由于認識錯誤而使用了不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③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行為人因為愚昧無知而誤認為該手段可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
2.3.5打擊錯誤打擊錯誤,也稱行為誤差,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對象實施侵害行為,由于行為本身的差誤,導致行為人所欲攻擊的對象與實際受害的對象不一致。筆者認為,如果這種打擊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就不能認定為同一犯罪,而應在主客觀相統一的范圍內認定犯罪。
2.3.6因果關系認識錯誤因果關系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和造成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實際發展進程的認識錯誤。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情況:①危害結果雖然發生,但并不是按照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的發展所預見的進程來實現的情況(有學者稱為狹義的因果關系的錯誤)。②行為人實施了甲、乙兩個行為,傷害結果是由乙行為造成的,行為人卻誤認為是甲行為造成的(有學者稱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結果已經因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沒有故意地實施了可能產生一定結果的行為后,才產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態的自然發展,導致了結果發生(有學者稱事后故意)。④犯罪構成的提前實現,是指提前實現了行為人所預想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認定這種行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關鍵在于行為人在實施第一行為時,是否已經著手實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結論,則應認定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結論,則否認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實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于事實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理論上大致有三種學說:具體的符合說、法定的符合說、抽象的符合說。理論和實踐中的通說是“法定的符合說”。依此學說,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質的法益或在構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過上述分類分析,當發生事實認識錯誤的情況下,行為人如何承擔罪責?因為筆者承認事實認識錯誤可以阻卻刑事責任,故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對于具體事實錯誤的處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說;而在抽象事實錯誤的場合下,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當實際的犯罪事實較重而行為人沒有認識到其重時,應依輕罪處理;當客觀犯罪行為輕時,則一律依輕罪處罰。
關于認識錯誤,我國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作為一種理論,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承認的。對于具體事實錯誤的處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說,而對抽象事實認識錯誤的場合,則應堅持主客觀一致的原則,既反對只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想象定罪,也不能單憑客觀后果而歸罪。對于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就我國的國情,仍應堅持“不知法律不免責”的傳統原則,反對“不知者無罪”的肯定說。
摘要:本文對刑法上認識錯誤的概念、分類及歷史沿革進行了介紹,并詳細論述了認識錯誤與刑事責任的關系,對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提出了一些個人的見解,以期達到深化認識錯誤理論的目的。
關鍵詞:法律認識錯誤事實認識錯誤刑事責任關系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版.第220頁.
第3篇
關鍵詞:法律規避;效力
一般認為,法律規避(evasionoflaw)是指當事人故意制造一種連結因素,以避開本應適用的準據法,而使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適用的行為。
傳統的觀點以當事人所規避的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為基點來判定規避行為是否有效。總的說來,這種傳統的觀點有三種:肯定規避外國法的效力;只否定規避內國法的效力;所有的法律規避行為均無效。
盡管在這方面有立法和司法實踐的佐證,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簡單,對實際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法律規避行為缺乏具體而理性的分析。
筆者認為,因為法律規避涉及規避主體、規避行為、規避客體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關系,所以,不管規避的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范,都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其效力。
一、當事人所規避的法律規范是否足以保證其正當利益能夠實現
這涉及到所謂的良法惡法說。當然,判定是否良法,要受到不同文化傳統觀念的影響。但同樣肯定的是,隨著信息社會的來臨和各國間包括文化層面交流的日益增多,判定良法惡法的標準有一個統一的道德底線,如平等、人權、人性化、以人為本等觀念。按這種現代的觀念看,世界上確實存在過惡法,而且現在還有部分國家和地區存在著不能說是良法的法,如過去法西斯德國的法、南非種族隔離法、法國和意大利曾經存在的不準離婚的法、有些國家禁止有色人種與白種人通婚的規定等。
筆者并非說惡法非法,而是說惡法沒有法的現代道德基礎。盡管它仍在其法域內有效,但其他國家或地區甚至該法域內的居民有理由否認或規避此類惡法,這種規避行為應該被認為是正當的、有效的,因為此類法沒有現代社會公認的最基本的道德基礎,阻礙了當事人作為一個人的正當利益的實現。
現在的問題是,在此類法域內的法院是否可以根據上述理由不適用自己國家制定的法?其實,就法律規避而言,當事人都是利用了雙邊沖突規范的指引。既然國家制定了這種作為本國整體法律一部分的沖突規范,從而被當事人所利用,這是國家制定這種沖突規范時所應想到的,而且制定出來就是為了讓居民利用的,不能說這種利用違反了制定國的法律。至于當事人最終規避了制定國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范,而使對自己有利的準據法得以適用,這正是沖突規范指引的結果。所以,制定國的法院以此認定和裁判,不能說沒有適用自己國家的法律。一國的法律體系是一個整體,若以當事人規避制定國實體法為由認定規避行為無效,那么,制定國的沖突規范本身是不是還要適用?還是不是法?這時就難以自圓其說了。
二、當事人主觀上是否存在惡意
一般地說,學者、立法及司法實踐都反對“客觀歸罪”,體現在法律規避上,判定當事人的規避行為是否有效,也必須考慮到當事人的主觀方面。判定當事人主觀上是否存在惡意,要看其規避當時是否想要擺脫良法善俗的規制并對其想要規避的法域的公共秩序產生特別重大的不良影響,而不能僅僅看其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法律適用。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和本能,而人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絕不能只根據當事人的這一做法而否定法律規避的有效性。
當然,作為對立的雙方,當事人追求對己有利的法律適用,一般地說,會對對方的利益造成不利或損害。但是,在很多情況下,許多事情不能兩全其美。一方面要看對方的利益是否合法而不合乎現代社會共通的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觀念,另一方面,還要看當事人當時在合法而不道德的情況下所受到的痛苦、不幸、損害和犧牲。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1878年法國鮑富萊蒙(Bauffremont)妃子被迫改變國籍求得離婚的事情。按今天的道德觀點來看,法國法院當時的判決是很不人道的,而且這個判決沒有考慮到人類社會和法律的進步因素和趨勢,因而沒有創意,只是個片面地固守法條的教條主義樣本。
所以,當事人是否存在惡意,應該放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和領域內去考察,充分考慮哪一個利益更大、更代表了最新的合乎道德的發展趨勢、更值得保護。最糟糕的是,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還只顧暫時的所謂合法的利益而下判,從而犯了“歷史性”錯誤。
三、當事人規避的事由是否正當或值得同情
這一點也要從所規避的法是否良法和現代社會一般的道德來判定,另外,還要考慮到當時當事人事由的緊迫程度。比如,當事人在當時的法域里,因為不能夠合法地離婚而致精神病、自殺或面臨終生不幸和痛苦,因為投資等方面面臨急迫的巨大損失的危險,而所在法域的法律不能很好地給他以適當及時的救濟,這時,他被迫選擇規避這個法域的法律適用的行為就是正當的和值得同情的。假若其所在法域的情況正好相反,則他肯定不會選擇這種費時費事的規避行為。
所以,當事人規避事由的正當性是與其所規避法域的法律的不正當性緊密相連的。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四、當事人的規避行為是否預示或促進法律的進步
我們不能說,任何時候任何國家的法律都是對的。從法律及其體系的歷史看,都有一個漸進有時甚至是暴發式的進步過程,而且,具體到每個國家,法律進步的情況有的快有的慢,千差萬別,甚至直到現在,還有些國家因宗教、文化傳統等因素而保留了較多的落后成分。這些法律成分,之所以說它落后,是因為它們已經不符合現代社會一般的普遍的道德觀念,因而也是不正當的。這種情況在轉型期的國家和社會里也比較多見。
所以,既然法律有不正當的法律,則當事人規避法律的行為就有可能是正當的,而法律有內國法和外國法之分,則當事人規避內國法也就有正當的可能性。
不管當事人規避的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關鍵是看其規避的行為是否預示著或將促進法律的進步。只要能夠充分地判定其所規避的法律是不正當的,就可以充分地肯定其規避法律的行為是正當的,而且也說明其所規避的法律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就也同時說明當事人的規避行為預示著或將有可能促進所規避法律的進步。這種情況在我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甚至直到現在持續地發生。我們對待這種規避法律行為的態度也比較經常地寬容大度,說明我國的司法實踐與部分學者的簡單武斷的觀點也不相符。
另一方面,平等不但是國家與國家、公民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還有各國法律之間的平等含義,因為各國的法律也是它們各自的象征。這就要求每個國家的法院要平等地對待他國法律、尊重他國法律,只要他國法律是正當的。筆者之所以堅持正當性標準,是因為各國在現代司法實踐中多以這種標準來判定當事人的規避行為是否正當、合法。這是有實踐基礎的。部分學者認為當事人只能規避外國法,而不能規避本國法,這是人為地簡單地看問題,不符合各國法律平等的現代國際法原則,是對他國法律的不尊重。所以,無論內國法外國法,只要其不正當,當事人都有規避的理由和邏輯基礎。
同樣是法國法院的判決,1878年對鮑富萊蒙案和1922年對佛萊(Ferrai)案的判決就是這樣不合情理、自相矛盾的判決,原因只是后者規避的是外國法(意大利法),而前者規避的是法國法。今天看來,這種判決的理由不足為例。
另一個足以說明問題的事例是我國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首先,我國法律沒有規定法律規避的效力問題。其次,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項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這說明,我國對法律規避的態度是,不是凡規避我國法律的行為都無效,只是規避我國法律中強制性或者禁止性規范的行為才被認定為無效,而對于規避外國法根本就沒有規定,其目的可能在于具體情況具體處理。所以,我國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在法律規避問題上也不是區分內國法外國法而簡單地處理的。
五、對傳統觀點的批判
有學者認為,當事人規避法律是一種不道德行為,是欺詐行為,而“詐欺使一切歸于無效”(Frausomniacorrumpit)。他們在這里也是運用了道德、正當的概念,而且,他們在運用時的內涵和外延與筆者運用時沒有跡象表明有什么不同。那么,這一概念只用于當事人的行為而不用于其所規避的法律,不用同一概念去審視當事人所規避的法律是否正當,這種雙重標準本身就是不公平、不正當、不道德的。正如筆者上面分析的那樣,世界上確實存在過而且現在也存在著不正當、不道德的法律,不分內國法外國法,那么,就不能只斥責或否定當事人的規避行為,而絕口不提其所規避的法律是否正當、是否道德。這種片面的觀點,起碼極不利于法律的進步和發展,不但弊大于利,而且它本身也是不科學、不正當的。另一方面,籠統地說當事人規避法律都是“欺詐行為”,企圖一棍子打死,這種說法不但不科學、缺乏分析,而且也顯得武斷和專橫。在公權勢力大于私權,而限制公權、保護私權成為現代社會各個國家一種趨勢的情況下,這種觀點也極不合時宜,顯得落伍。把“欺詐”簡單地、不講理地扣在規避當事人的頭上,從而從容地運用“欺詐使一切歸于無效”的法諺,這正是此種觀點的陰險之處。
事實上,早先的學說并不認為法律規避是一種無效行為,如德國的韋希特爾(Waechter)和法國的魏斯(Weiss)認為,既然雙邊沖突規范承認可以適用內國法,也可以適用外國法,那么,內國人為使依內國實體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為或法律關系得以成立,前往某一允許為此種法律行為或設立此種法律關系的國家設立一個連結點,使它得以成立,這并未逾越沖突規范所容許的范圍,因而不能將其視為違法行為。一些英美法系的學者也認為,既然沖突規范給予當事人選擇法律的可能,則當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而選擇某一國家的法律時,就不應該歸咎于當事人。這些觀點是很有道理的。
還有必要說明的是,沖突規范也是一個國家法律的組成部分,制定它就是為了讓當事人遇到利益沖突時對法律有所選擇。當他規避某一法律時,另一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依法作出了一種選擇,這是遵從法律的指引作出的行為,沒有什么不當的問題。當然,若國家在立法上明示堵住了某種選擇,則他作出這種選擇時就可能是錯誤、不當的。但是,如果立法上沒有設置某種“安全閥”,那就是立法者的過錯,是法律的漏洞,絕不能把這一失誤歸結到規避當事人的頭上。另一方面,從一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和整體來說,司法者不能不適用同樣是法律組成部分的沖突規范,否則就是執法不公、有法不依、玩弄法律。
所以,把法律規避稱為“僭竊法律”(fraudealaloi)、欺詐設立連續點(fraudulentcreationofpointsofcontact)等等,這種稱法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先入為主的不正當不公正評價因素。在對當事人的法律規避行為及其所規避的法律進行具體而公正的分析評價之前,就把他的行為看作“僭竊”、“欺詐”,是偏見的、片面的和不科學的。筆者主張采用“法律規避”一詞,因為“規避”基本上屬于中性的詞語,不至于讓人一看就有某種偏見,從而留下深入、具體思考的余地,使對法律規避的正當公正評價和法律由此的進步展現出一束理性的曙光。
六、最后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筆者在本文中所用的法域一詞,包括國家、地區以及由于觀念形態不同而形成的法律族群。筆者認為,研究法律規避首先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加廣闊的領域內去全面地把握,力求先從普適性方面整理出它的概念和要件,才能進一步就某領域內的法律規避問題作出更具體的分析研究。而且,事實上,世界范圍內的法律規避有時也確實發生在區際(如美國的州與州、我國的內地與港澳臺之間)、人際(如不同的宗教地區和信徒之間)的法律抵觸之中。這就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地分析、歸納、總結、研究。例如,按照美國國際私法,婚姻的實質成立要件適用婚姻舉行地法,若居住在密歇根州的表兄妹要結婚,故意避開本州不準表兄妹結婚的規定而到允許其結婚的肯塔基州結婚,這也是一種法律規避。又如,在敘利亞,人的身分能力適用其所屬宗教法,于是,一個基督教徒受到應給付其妻贍養費的判決后,即改信伊斯蘭教,因為按照伊斯蘭教法,夫無須贍養其妻,這也是一種法律規避。
本文中所用的規避當事人是指規避法律的一人、多人或人的團體,而不包括受規避行為影響的對方。
本文的觀點建立在對私權的尊重和保護、對公權的限制和服務性規范基礎之上,其背后是日益普及、重要并日益完善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也考慮到法律的道德底線,如以人為本等,因為道德在某種意義上是法律存在的價值和基礎,也是法律的力量之源。
筆者認為,以前甚至更遠期的司法判例不應該被簡單地用來證明關于法律規避效力的傳統的觀點。理論不應僅僅是已有司法實踐的傳聲筒,而應基于對實踐的理性認識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判斷,進而良性地影響和引導實踐。那些古遠的判例不應該成為現代社會遵循的典范,也與現代社會日益頻繁復雜的法律規避實踐不相符。理論研究應在現代實踐的基礎上預見性地開出一條新路子。
筆者反對關于法律規避的僵化的傳統觀點,主張對法律規避的效力問題作具體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
筆者主張法律規避的效力既不能簡單地用內國法外國法的區分來解釋和判定,也不能簡單地僅僅審視規避者行為表面上是否與法律相抵觸,而應在道德分析和法律體系平等相待的基礎上,既分析規避者的行為,又分析被規避法律的理性價值,具體判定每一個或每一類法律規避行為的效力。
參考資料:
1.《國際私法新論》,韓德培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2.《沖突法論》,丁偉主編,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3.《國際私法》,韓德培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
4.《國際私法案例選編》,林準主編,法律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5.《沖突法》,余先予主編,法律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