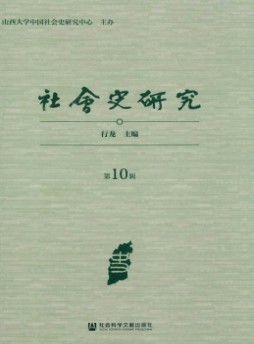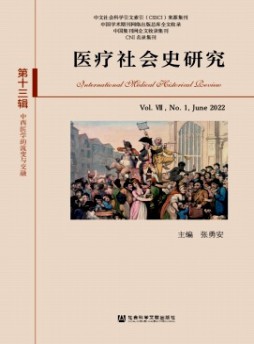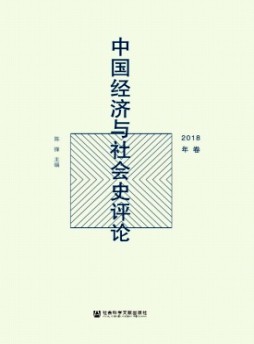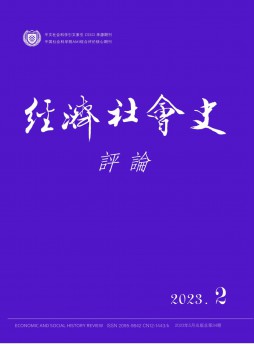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的哲學(xué)討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的哲學(xué)討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盧梭說(shuō),人生而自由,卻無(wú)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生而自由的人之“生”,可以做兩方面的解釋。一是從自然中走出的人,即從人類(lèi)起源的角度上談人的“出生”狀態(tài);二是就個(gè)體生命而言,未經(jīng)現(xiàn)代文明“污染”的孩童,才是盧梭眼中自由之人“生”。“無(wú)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的判斷,把文明和文化當(dāng)做束縛自由的枷鎖,無(wú)論是人類(lèi)還是生命個(gè)體,都是在自由的生命的起點(diǎn)上,逐步套上自己定制的枷鎖,并且由此展開(kāi)生而自由的人因不自由而渴望自由的全部旅程。盡管盧梭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枷鎖”做了大量的分析,并且在這些分析中對(duì)這些束縛自由的枷鎖鞭撻討伐,但是和其他啟蒙主義思想家一樣,盧梭本人絕不是反對(duì)人類(lèi)進(jìn)步,更不是反人類(lèi)的。他并沒(méi)有把文明理解為全部社會(huì)罪惡的淵藪,相反,他所推崇的“自然”,恰恰是在自由基礎(chǔ)上容納著人類(lèi)進(jìn)步全部?jī)?nèi)容的真正文明。如果把盧梭的判斷當(dāng)做一個(gè)“問(wèn)題”的話(huà),那么,這個(gè)判斷可以分為兩個(gè)層面:人,是如何“生而自由”的?人,能否走出“無(wú)往而不在的”“枷鎖”,從而獲得真正的自由??jī)蓚€(gè)問(wèn)題引發(fā)出本文的主題。以自由存在形態(tài)之反映的自由社會(huì)史,以及以對(duì)自由社會(huì)史之反思、批判、領(lǐng)悟?yàn)閮?nèi)容的自由概念史,就是人類(lèi)關(guān)于自由的全部歷史。而這一歷史的展開(kāi),無(wú)疑是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體貼和領(lǐng)悟自由的基本方式。當(dāng)我們?cè)趦蓚€(gè)歷史參照系中品味人類(lèi)自由之里程時(shí),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的敘事方法,就不僅僅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手段”問(wèn)題,它本身就是一個(gè)哲學(xué)問(wèn)題。
一、社會(huì)史中的客觀性與解釋原則
人類(lèi)社會(huì)總是以文化的形式譜寫(xiě)自己的文明歷史。在歷史中呈現(xiàn)的文化,可以表現(xiàn)為未必言說(shuō)、任由歲月侵蝕,但卻以自身的存在而彰顯歷史的“器物”,也可以表現(xiàn)為貌似可以任意言說(shuō)、但實(shí)際上一定有著內(nèi)在規(guī)定的“觀念”。器物文化與觀念文化交織出的歷史,構(gòu)成人類(lèi)歷史的基本表現(xiàn)方式,也由此成為走出歷史、并且仍然以各種方式創(chuàng)造歷史的現(xiàn)代人的寶貴財(cái)富。現(xiàn)代人之所以為現(xiàn)代人,不是因?yàn)樗畹哪莻€(gè)時(shí)代如何“現(xiàn)代”,而是因?yàn)樯硖幀F(xiàn)代的人,擁有歷史。作為觀念史的表達(dá)方式,社會(huì)史和概念史是任何一種關(guān)涉到歷史的理論的基本研究路徑或方法。前者指“歷史表述史”,后者指“歷史反思史”。在研究實(shí)踐中,這兩種研究路徑互相闡發(fā)并相互參照,瑞因哈特•考斯萊克認(rèn)為,社會(huì)史表現(xiàn)為“在將人類(lèi)生活的所有‘歷史表述’還原為‘社會(huì)狀況’的同時(shí),也由‘社會(huì)狀況’引出‘歷史表述’”;概念史表現(xiàn)為“把‘社會(huì)史’特別是‘政制史’的分析與‘概念史’的問(wèn)題結(jié)合起來(lái)。”①顯然,社會(huì)史是關(guān)于“存在”的歷史,它更加傾向于歷史的真實(shí)表達(dá),因此它以還原歷史的方式表述歷史,并且由此構(gòu)成歷史學(xué)的基本方法。但是,社會(huì)史畢竟不是自然史,它的存在是以歷史中的人以及人和人之間的事情為核心的。確切說(shuō)來(lái),是以過(guò)去的人和過(guò)去的事情為歷史描述對(duì)象的。那么,如何還原歷史的真實(shí)性,以哪種方式才能夠獲得歷史的真實(shí)性,就不再是一個(gè)歷史學(xué)的問(wèn)題,而是一個(gè)哲學(xué)問(wèn)題了。比如,歷史“表述”的方法問(wèn)題上,就存在著“言談”和“書(shū)寫(xiě)”真實(shí)性問(wèn)題的爭(zhēng)執(zhí)。傳統(tǒng)理論中,“眼見(jiàn)為實(shí)”的生理習(xí)性使我們更加相信感官所獲得的直接信息,因而也就相信與感官同一維度上的“言談”。我們相信第一次實(shí)現(xiàn)直立行走的猿是人類(lèi)擺脫必然從而獲得自由的開(kāi)端,我們相信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dòng)是近代社會(huì)擺脫神的桎梏爭(zhēng)取人的自由的努力,我們相信攻打巴士底獄是法國(guó)大革命中為自由而戰(zhàn)的悲壯努力,我們也相信,歷史上的馬克思曾以一部“工人階級(jí)的圣經(jīng)”引發(fā)了自由發(fā)展史的空前革命。
我們之所以“相信”,是因?yàn)槲覀冋J(rèn)定,在人類(lèi)歷史上,不僅有著自由的渴望,更有著自由的奮爭(zhēng)。由奮爭(zhēng)所譜寫(xiě)的歷史是有據(jù)可查的,是一種可以歸結(jié)為“言談”的科學(xué)———任何科學(xué),直面的都是經(jīng)驗(yàn)。以“經(jīng)驗(yàn)”為“實(shí)”的認(rèn)識(shí)原則是亞里斯多德伊始的西方經(jīng)驗(yàn)哲學(xué)所固守的基本原則。近代社會(huì)的科技革命、工業(yè)化大生產(chǎn)以及包括宗教改革在內(nèi)的社會(huì)變革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成就,進(jìn)一步固化了由培根、伽利略、牛頓及洛克等堅(jiān)持的經(jīng)驗(yàn)主張?jiān)诂F(xiàn)代化社會(huì)中的地位。但是,這種以求實(shí)為特征的基本原則,即便是在傳統(tǒng)哲學(xué)中也同樣屢遭詬病。和科學(xué)不同,歷史中的“事”必須通過(guò)“說(shuō)”的手段才能展現(xiàn)出來(lái),如何“敘事”的問(wèn)題,不能仰仗著感官通道所獲得的感覺(jué)或印象。所謂的間接經(jīng)驗(yàn),已經(jīng)是被人們言說(shuō)過(guò)的經(jīng)驗(yàn),因此不再是經(jīng)驗(yàn)了。現(xiàn)代哲學(xué)對(duì)科學(xué)的重新理解,也在這個(gè)層面上給出了人類(lèi)認(rèn)識(shí)的非科學(xué)通道。德里達(dá)站在后現(xiàn)代的立場(chǎng)上,對(duì)“言談”和“書(shū)寫(xiě)”兩種表達(dá)“真實(shí)”的方法進(jìn)行了分析。按照他的理論,傳統(tǒng)哲學(xué)和人類(lèi)歷史中所看重的“言談”方式,不具有、也不應(yīng)該具有以“更加真實(shí)”的身份統(tǒng)攝書(shū)寫(xiě)歷史的權(quán)力。當(dāng)然,這絕不意味著“書(shū)寫(xiě)”的真實(shí)性分量更重,在解構(gòu)主義看來(lái),“言談”與“書(shū)寫(xiě)”的任何偏重,都可能導(dǎo)致形而上學(xué)的二元對(duì)峙和主客二分,其結(jié)果必然是邏輯帝國(guó)的形成。于是,歷史的真正意義,不在于以何種方式表達(dá)出來(lái),而在于以何種方式“解構(gòu)”出來(lái)。德里達(dá)的解構(gòu)是歷史的現(xiàn)代解構(gòu)。它不僅包含著歷史中器物文化的解構(gòu),也包含著歷史中觀念文化的解構(gòu)。于是,歷史的“表達(dá)”與關(guān)于“表達(dá)歷史”的解構(gòu),同樣成為現(xiàn)代哲學(xué)的重要課題。無(wú)論怎樣,解構(gòu)主義關(guān)于“言談”和“書(shū)寫(xiě)”關(guān)系的探究,再次觸及到歷史的“表達(dá)”問(wèn)題。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基本途徑,社會(huì)史不可能離開(kāi)觀念的表達(dá)。在這種表達(dá)中,社會(huì)史力求以“客觀性”的筆觸完成對(duì)社會(huì)或歷史的描畫(huà)。
問(wèn)題在于,應(yīng)該如何界定這種客觀性呢?社會(huì)史中的客觀性,絕不是歷史中所有客觀存在的泛泛例舉,更不是社會(huì)中種種瑣事的簡(jiǎn)單鋪敘,否則,就不會(huì)有黑格爾所強(qiáng)調(diào)的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原則了。歷史與邏輯之統(tǒng)一中所強(qiáng)調(diào)的“邏輯”環(huán)節(jié),鋪墊了社會(huì)史所選擇的范圍及其意義。因此,這里的“客觀性”,不再是拘泥于歷史中所有存在的客觀性,而是一種具有標(biāo)志性的存在,即形成此種歷史的那個(gè)時(shí)代的一種標(biāo)志。由此而構(gòu)成的歷史客觀性,被稱(chēng)之為“時(shí)代的客觀性”。換句話(huà)說(shuō),只有那些能夠展現(xiàn)歷史的時(shí)代性的東西,才能納入社會(huì)史的眼簾,并且能夠在社會(huì)史的“求真”過(guò)程中,解釋其客觀性問(wèn)題。比如,在“自由”的社會(huì)史中,我們之所以選取了直立行走、文藝復(fù)興和法國(guó)大革命等等,是因?yàn)檫@些“事實(shí)”標(biāo)志著人和自然關(guān)系的處理、人和神的關(guān)系處理、以及人和人關(guān)系的處理過(guò)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時(shí)代,完成了自由的一個(gè)段落,因而也就構(gòu)成了客觀譜序自由社會(huì)史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這樣,在這種客觀性的解釋中,就已經(jīng)暗含著一個(gè)基本內(nèi)容,我們是根據(jù)什么來(lái)確定時(shí)代的標(biāo)志性問(wèn)題,并由此而把此問(wèn)題納入社會(huì)史的樂(lè)章之中?哲學(xué)把構(gòu)成社會(huì)史樂(lè)章的主旋律,稱(chēng)之為“解釋原則”。社會(huì)史的解釋原則,不是歷史中普通存在的客觀性原則,而是某個(gè)歷史階段人類(lèi)所形成的共識(shí)的客觀性原則。某個(gè)歷史時(shí)期共時(shí)性的客觀存在,是人類(lèi)精神發(fā)育與發(fā)展的標(biāo)度,是人類(lèi)認(rèn)識(shí)水平與實(shí)踐水平的標(biāo)志,也是歷史承接與延續(xù)、并且在承接和延續(xù)中顯現(xiàn)歷史階段性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能夠構(gòu)成時(shí)代共識(shí)的尺度,即時(shí)代的解釋原則。海德格爾說(shuō),存在是向“此在”敞開(kāi)的狀態(tài),作為此在的“人”,以哪種方式表達(dá)“在者”的“在世之在”,那么“存在”就以哪種方式規(guī)定并顯現(xiàn)你的存在。我們的存在是既定的和無(wú)法改變的,但世界如何展開(kāi),卻依賴(lài)我們的時(shí)代性的共識(shí)。金錢(qián)拜物教成為基本共識(shí)時(shí),世界以經(jīng)濟(jì)方式向我們展開(kāi);官本位成為基本共識(shí)時(shí),世界以制度腐敗形式向我們展開(kāi)。這樣,社會(huì)史所追求的客觀性問(wèn)題,便以時(shí)代性的共識(shí)性解釋原則表現(xiàn)出來(lái)。當(dāng)一個(gè)時(shí)代認(rèn)可了某種解釋原則,意味著這個(gè)時(shí)代已經(jīng)以時(shí)代性的共識(shí)為自身打下了歷史性的標(biāo)志。那么,社會(huì)史以此為前提,論證此種解釋原則所能包容的社會(huì)之全部,就不過(guò)是一項(xiàng)技術(shù)工作了。在這個(gè)意義上,一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史或問(wèn)題史,所形成的應(yīng)該是在時(shí)代性解釋原則基礎(chǔ)上以概念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的“觀念史”。在這里,概念不過(guò)是“觀念”的表達(dá)方式,而“觀念”所反映的,則一定是共識(shí)基礎(chǔ)上的解釋原則。比如,工業(yè)革命,宗教改革,契約精神,是以概念的形式表達(dá)了近代西方社會(huì)整體進(jìn)步的觀念,而這一觀念,是建立在“社會(huì)進(jìn)步”這一共識(shí)原則基礎(chǔ)上的。社會(huì)史要尋求的,首先是構(gòu)成觀念的共識(shí)“是什么”,其次才是在這種共識(shí)原則下對(duì)歷史中的社會(huì)的解釋或描述。當(dāng)我們找到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共識(shí)性解釋原則之后,就意味著我們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上”去看待歷史的存在和歷史中生發(fā)的問(wèn)題,這就是社會(huì)史的客觀性所指。當(dāng)整個(gè)近代社會(huì)都把自由理解為“擺脫束縛”的時(shí)候,那么,認(rèn)識(shí)束縛自身的枷鎖,就是理解自由的前提,而如何從束縛中解脫出來(lái),就成為爭(zhēng)取自由的社會(huì)活動(dòng)。康德在《什么是啟蒙?》中關(guān)于啟蒙的經(jīng)典解釋?zhuān)菍?duì)自由認(rèn)識(shí)的時(shí)代性標(biāo)度,而500年來(lái)西方社會(huì)人與人、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處理和構(gòu)建,就是在這樣一些理解中,逐步走向人們所期待著的自由的存在史。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結(jié)論,以客觀性追求為目的的社會(huì)史,在“表達(dá)”歷史內(nèi)容時(shí),任何一種形式的“求真”,都以客觀性的解釋原則為前提,而這種解釋原則,又來(lái)自一個(gè)稱(chēng)之為時(shí)代的人類(lèi)或人類(lèi)群體的共識(shí)。然而,任何一個(gè)時(shí)代都不可能化為歷史的永恒,歷史不可能永久地駐足于某個(gè)特定的歷史時(shí)段。當(dāng)一個(gè)時(shí)代以結(jié)束自身的方式開(kāi)啟另一個(gè)時(shí)代時(shí),該時(shí)代所謂共識(shí)性的解釋原則,便會(huì)被新的時(shí)解為一種“合法性的偏見(jiàn)”。于是,討論、質(zhì)疑、反思、批判這種時(shí)代性的共識(shí),就成為思想由“現(xiàn)存”設(shè)法移居為“現(xiàn)實(shí)”的一種努力。這種思想的努力,構(gòu)成概念史的基本篇章。
二、概念史的邏輯主張與普遍性追求
由概念構(gòu)筑的歷史和社會(huì)史一樣,也一定是思想的產(chǎn)物。從形態(tài)上看,概念總是以“反思”的方式力求將觀念提純,并且在這種提純過(guò)程中,形成可以獨(dú)立于直觀的經(jīng)驗(yàn)世界之外的理論形態(tài)。正是這種獨(dú)立性的求索,使不同時(shí)代關(guān)于某種思想所形成的概念,按照某種理論的要求鏈接起來(lái),形成概念自身的歷史。同樣是一種歷史,同樣是關(guān)于歷史的觀念性表述,社會(huì)史和概念史當(dāng)然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概念史有著自身形成的歷史,有著在自身歷史中所形成的有別于社會(huì)史的鮮明特點(diǎn)。首先,概念史中的概念,不再是觀念的表達(dá)形式,而是任何一種觀念得以建樹(shù)的根基。我們知道,文明的發(fā)育仰仗著思維能力的提升,由“抽象”而形成的概念,曾力求將概念所要反映的內(nèi)容進(jìn)行一般性的整理,因此,概念以“一般”的特征作為思想形成和思想交流的工具。在這個(gè)意義上,任何一種觀念,都首先仰仗著概念作為基本單位,并以概念的形式完成觀念的鋪敘。在這種鋪敘中,觀念將遵循概念的邏輯完成自身的整體性構(gòu)建,由此,能夠解釋歷史的觀念,不再是單擺浮擱的概念,而是一個(gè)能夠具有概念史意義上的概念集合,一個(gè)能夠?yàn)橛^念的解釋獲得支撐的概念體系。其次,概念史中把概念當(dāng)做對(duì)象時(shí),它所涉及到的概念不再是某種解釋原則下對(duì)事實(shí)的表述工具,因?yàn)樗旧砭褪且环N解釋原則。關(guān)于世界的說(shuō)明或解釋?zhuān)瑏?lái)自于概念本身,而不是解釋原則下的概念。顯然,構(gòu)成解釋原則的概念,不僅僅是具象事實(shí)抽象的結(jié)果,它的形成,經(jīng)歷了“完整的表象蒸發(fā)為抽象的規(guī)定”和“抽象的規(guī)定在思維行程中導(dǎo)致具體的再現(xiàn)”②的基本路徑。
由此而構(gòu)成的概念,是一個(gè)理性的綜合,它不僅以概念之間的邏輯鏈接著彼此的關(guān)系并由此形成概念的歷史,并且在這種鏈接中不斷以反思和批判的手段審視著“鏈接”的合理性問(wèn)題。正是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概念的歷史有可能區(qū)別于歷史中的其他,獨(dú)立為人類(lèi)可以作為一個(gè)“對(duì)象”來(lái)加以把握的歷史性存在。概念與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的觀照,是概念史要解決的第一要?jiǎng)?wù):它必須要在概念的主觀載體中映照出客觀性的特質(zhì),從而解釋和解決經(jīng)驗(yàn)世界所遇到的一切問(wèn)題。在概念史中,這個(gè)問(wèn)題被理解為對(duì)“普遍性”的追求問(wèn)題。傳統(tǒng)哲學(xué)中,如何獲得最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是其建構(gòu)概念史的最為關(guān)鍵的邏輯步驟。蘇格拉底、柏拉圖在西方哲學(xué)挺立兩千年的理由,就是由于他們所設(shè)定的理念世界,能夠以“本體”的形態(tài)實(shí)現(xiàn)概念最大普遍性的欲求,并且由此而解決概念自身的客觀性問(wèn)題。康德利用先驗(yàn)范疇的合理性演繹所完成的“立法”過(guò)程,也是通過(guò)將知性的普遍性訴諸于先驗(yàn)的手段,實(shí)現(xiàn)了有限認(rèn)知領(lǐng)域中的客觀性、普遍性及其必然性問(wèn)題的解決。而不滿(mǎn)足于知性思維方式的黑格爾,則用自身所搭建的辯證思維方式,將古希臘哲學(xué)中的理念世界擴(kuò)展為絕對(duì)精神的世界,并在絕對(duì)精神的邏輯力量支撐下,完成了傳統(tǒng)哲學(xué)歷史上最為完美的概念史演繹。第三,從功能的角度上看,概念史和社會(huì)史也有很大區(qū)別。社會(huì)史以“表述歷史”為基本功能,因此它對(duì)歷史的表述,一定會(huì)在確立相應(yīng)的社會(huì)史解釋原則的前提下得以成立。而這個(gè)解釋原則,來(lái)自于被解釋的歷史中的“共識(shí)”,因此,社會(huì)史一般以觀念形態(tài)的靜態(tài)表述作為表達(dá)歷史的基本方法。換句話(huà)說(shuō),社會(huì)史是一種靜態(tài)觀察,靜態(tài)描述的過(guò)程,它的理論也是在相對(duì)穩(wěn)定的歷史階段性中構(gòu)造出來(lái)的。黑格爾認(rèn)定“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時(shí)才飛出樹(shù)林”,十分準(zhǔn)確地描述了社會(huì)史的這一“歷史之后述說(shuō)歷史”的特征。概念史則不然,構(gòu)成概念史的概念,不僅僅要觀照歷史,而且更要觀照現(xiàn)實(shí)和未來(lái)。因此,在時(shí)間上,它不以過(guò)去所發(fā)生的歷史為唯一的解釋內(nèi)容和參照,也不以現(xiàn)實(shí)所生發(fā)的一切存在為唯一平臺(tái)。恰恰是在歷史接續(xù)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走向未來(lái)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中,構(gòu)造出能夠作為解釋原則的基本概念,從而構(gòu)造出概念史中一個(gè)個(gè)理論環(huán)節(jié)。也就是說(shuō),概念史是思想變動(dòng)中概念的生發(fā)過(guò)程,這些概念對(duì)其內(nèi)容的彰顯,不是靜態(tài)的說(shuō)明,而是動(dòng)態(tài)的、批判性的超越。而由這些概念鏈接起來(lái)的歷史,有著可以獨(dú)立于內(nèi)容的自身邏輯。傳統(tǒng)哲學(xué)中,無(wú)論是康德的先驗(yàn)邏輯還是黑格爾的辯證邏輯,都是服務(wù)于概念史的基本邏輯的。從方法上說(shuō),社會(huì)史是一種分析的結(jié)果,即以已經(jīng)形成的某種歷史為對(duì)象,分解之后形成觀念的歷史,概念史則是綜合的結(jié)果,即在一個(gè)確定的或不確定的邏輯路向上祭起批判之大旗,以思想的邏輯批判思想的觀念。
社會(huì)史立足于某個(gè)解釋原則之普遍認(rèn)定的求解和應(yīng)用,它往往以某個(gè)歷史時(shí)段解釋原則的形成,以及這些解釋原則如何獲得共識(shí)性作為理論前提。對(duì)于社會(huì)史來(lái)說(shuō),存在的合法性是第一位的,它要表述的,就是歷史中合法的、因而是現(xiàn)實(shí)的存在。概念史則立足于自身邏輯的演繹,它不僅要考慮構(gòu)成解釋原則的概念能否解釋歷史或現(xiàn)實(shí)的存在,更要追求自身的合理性問(wèn)題。因此,社會(huì)史對(duì)社會(huì)的種種形態(tài)和現(xiàn)象的認(rèn)定,是以其合法性的追溯為核心,而概念史在概念的理性演繹中,則以合理性的求證為核心。在這樣一個(gè)前提下,社會(huì)史強(qiáng)調(diào)的是解釋原則的共識(shí)和認(rèn)同,而概念史則以社會(huì)史的解釋原則之反思和批判、以社會(huì)史的存在之討伐為內(nèi)容。概念史最為輝煌的成就,莫過(guò)于近代社會(huì)伊始的理性主義所構(gòu)造的邏輯大廈。當(dāng)?shù)芽栆浴拔以趹岩伞钡氖侄握归_(kāi)理性自身的審視后,由“清楚明白”而確定的“我在”,就以主體的身份成為一個(gè)認(rèn)識(shí)論中的理性原點(diǎn)。“清楚”的含義首先要排除任何經(jīng)驗(yàn)性的東西,因?yàn)槿魏谓?jīng)驗(yàn)都會(huì)由于被遮蔽而不能被理性直觀;“明白”則是理性邏輯的要求,任何“清楚”的直觀對(duì)象,都應(yīng)該在邏輯的引領(lǐng)下與經(jīng)驗(yàn)世界對(duì)接。顯然,在這個(gè)原點(diǎn)上,無(wú)論是天賦觀念還是單子或?qū)嶓w,都以“普遍性”的認(rèn)定完成了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轉(zhuǎn)向之后關(guān)于主體的自信。近代社會(huì)關(guān)于理性的“神話(huà)”確立了人追求理性的崇高,關(guān)于科學(xué)的“神話(huà)”堅(jiān)定了人認(rèn)識(shí)自然的執(zhí)拗,而關(guān)于人類(lèi)解放的種種“學(xué)說(shuō)”,又在人的世界里譜敘和構(gòu)造了一個(gè)又一個(gè)理想世界。人類(lèi)關(guān)于自由的歷史,就在理性之普遍性的旗幟下,以獨(dú)特的邏輯主張譜寫(xiě)了概念史中自由篇章的全部?jī)?nèi)容。
近代社會(huì)關(guān)于理性的濫觴一方面以普遍性的堅(jiān)守捍衛(wèi)了概念史的邏輯至上,但另一方面,又在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反思過(guò)程中,對(duì)理性的普遍原則,以及由此而構(gòu)筑的概念史的合法性提出質(zhì)疑。比如,在康德看來(lái),啟蒙運(yùn)動(dòng)關(guān)注的應(yīng)當(dāng)是人的理性脫離了自然狀態(tài)進(jìn)入文明后,如何行使自身的合法權(quán)利的問(wèn)題。為啟蒙運(yùn)動(dòng)所熱衷的理性之光,如何能普照人類(lèi)文明的角角落落,并為人類(lèi)的生存與發(fā)展提供永恒的普適性原則?人類(lèi)“不成熟狀態(tài)”的擺脫,是自由的理性限定還是自由的信仰訴求?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口號(hào)是“要有勇氣運(yùn)用你自己的理智”③那么怎樣才能在理智的運(yùn)用中擺脫對(duì)理性自由的種種限制,從而可以“永遠(yuǎn)有公開(kāi)運(yùn)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④呢?康德時(shí)代的啟蒙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在激情甚至狂熱的理性崇拜中開(kāi)始了對(duì)自身的反思:休謨關(guān)于理性普遍性的懷疑使得理性有限性問(wèn)題暴露于陽(yáng)光之下;盧梭對(duì)自由與必然關(guān)系的另類(lèi)解說(shuō),又在對(duì)人類(lèi)罪惡歷史的解剖中,為似乎已經(jīng)是晴空萬(wàn)里的傳統(tǒng)意義世界理論帶來(lái)了一片烏云。從解構(gòu)主義的立場(chǎng)上看,休謨與盧梭在他們的問(wèn)題和思想中,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消解了人類(lèi)仰仗理性信念建構(gòu)起來(lái)的意義世界。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啟蒙運(yùn)動(dòng)之后擺脫理性權(quán)威的吶喊,不是要在人的活動(dòng)中尋找并回歸某種不變的終極本質(zhì),而是要改變?nèi)说默F(xiàn)實(shí)生存境遇。只有站在這個(gè)角度上,才能充分理解作為社會(huì)史中“事件”和作為概念史中“意義”的啟蒙運(yùn)動(dòng)。人類(lèi)的歷史,既不是社會(huì)存在史的簡(jiǎn)單鋪敘,也不是概念邏輯的理性演繹。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層面上,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
三、“世界觀”旗幟下的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
無(wú)論是“表述”一個(gè)社會(huì)的社會(huì)史,還是“反思”一個(gè)社會(huì)的概念史,都有著各自的歷史成因,因而也有著各自的不同。在人類(lèi)文明的進(jìn)程中,駐足于一個(gè)時(shí)代的概念史,就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思想驛站,因而往往重合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史。換句話(huà)說(shuō),任何一種歷史的表述或演繹,都是以“在場(chǎng)”的現(xiàn)實(shí)為平臺(tái)來(lái)表達(dá)“不在場(chǎng)”的歷史,那么,如何實(shí)現(xiàn)“在場(chǎng)”與“不在場(chǎng)”之間的統(tǒng)一,就是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紛爭(zhēng)乃至各自努力的方向。不得不以存在的歷史證明概念的合法性,或不得不以邏輯的形式證明存在的合理性,不僅成為概念史或社會(huì)史擺脫不了的夢(mèng)魘,而且也往往成為滋生的基本土壤。恩格斯甚至由此給出一個(gè)頗有爭(zhēng)議的論斷:“全部哲學(xué),特別是近代哲學(xué)重大的基本問(wèn)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wèn)題。”⑤思存關(guān)系的角逐,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各自的偏執(zhí)及其局限。黑格爾之后的哲學(xué)逐漸意識(shí)到,“自由”不能是自由存在歷史白描基礎(chǔ)上的渴望,也不能是自由概念歷史演繹中所寄托的激情,自由和自由的爭(zhēng)取,應(yīng)該是同一個(gè)問(wèn)題。因此,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中的自由問(wèn)題,必須在一個(gè)有別于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新世界觀創(chuàng)立中重新認(rèn)定。當(dāng)馬克思認(rèn)定以往的“哲學(xué)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wèn)題在于改變世界”⑥,并以此為根基創(chuàng)建改變世界的哲學(xué)時(shí),“觀世界”的哲學(xué)理論變成“世界觀”的理論,世界,不再是僅供“解釋”的世界,而是可以“改變”的世界。
世界觀旗幟引領(lǐng)下,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有了走出舊有局限、重新審視自身并開(kāi)辟全新領(lǐng)域的可能。在這種世界觀中,時(shí)間的一維性不再是歷史展開(kāi)的唯一依托,因而歷史不再是一個(gè)簡(jiǎn)單存在的所謂客觀史;同樣,理性邏輯的自洽性不是概念鋪敘演繹的唯一法則,因此概念體系的完滿(mǎn),不意味著歷史及其指向的完美。人類(lèi)歷史本身就是一個(gè)容納著未來(lái)、以有別于理性邏輯的實(shí)踐邏輯構(gòu)造出來(lái)并且努力展現(xiàn)未來(lái)的實(shí)踐史。這意味著,求真求實(shí)的社會(huì)史之客觀性依據(jù),不過(guò)是科學(xué)體系真實(shí)所求之憑據(jù)在歷史領(lǐng)域的再現(xiàn),而科學(xué)是回答不了自身何以客觀的問(wèn)題的。同樣,以規(guī)律或目的為歸宿的理性之普遍性推演形成的概念史,同樣無(wú)法解釋動(dòng)變之歷史何以有不變之初衷的終極問(wèn)題。馬克思“改變世界”的視角,實(shí)際上開(kāi)辟了一個(gè)新的歷史視域,這種歷史視域的構(gòu)建消解了形而上學(xué)的舊有旨趣,并以“世界觀”的形式締結(jié)了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理論與實(shí)踐、在場(chǎng)性與不在場(chǎng)性問(wèn)題的因緣。包含“天才世界觀萌芽”的《提綱》關(guān)于以往“哲學(xué)家”性質(zhì)的判斷,絕不是虛無(wú)主義或獨(dú)斷主義的產(chǎn)物。在馬克思眼中,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的傳統(tǒng)哲學(xué),從來(lái)沒(méi)有也不可能放棄了“改變世界”的要求。以自由問(wèn)題為例,在任何一位哲學(xué)家的理論中,無(wú)論是社會(huì)史中關(guān)于自由的理論再現(xiàn),還是概念史中關(guān)于自由的理性渴望,都從來(lái)沒(méi)有放棄過(guò)關(guān)于自由的爭(zhēng)取。以笛卡爾和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西方歷史,不僅僅是自由探究的歷史,而且也是自由爭(zhēng)取的歷史。這種自由開(kāi)辟了人與自然、人與上帝、人與人關(guān)系解釋的新路徑,也在主體的設(shè)置、人性的恢復(fù)、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人權(quán)問(wèn)題上,譜寫(xiě)了輝煌的樂(lè)章,它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志就是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興起。
馬克思認(rèn)定這些哲學(xué)家們不過(guò)是在“解釋世界”的根本原因,是因?yàn)樗麄儗?duì)世界的“改變”,永遠(yuǎn)閾限于對(duì)世界的“解釋”之中。無(wú)論是理性的訴求還是現(xiàn)實(shí)欲求的伸張,社會(huì)史的解說(shuō)與概念史的演繹,都以理論自身合理性的論證為基本原則。綜觀近代哲學(xué)的自由訴求理論,有著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以契約論求得自由的主張,也有著如康德、黑格爾終極意義上的自由理論。前者毫無(wú)例外的以某種“原初社會(huì)自然狀態(tài)”的理論假設(shè)為前提,后者又都以理論的自洽作為合理性的基本依據(jù)。在這樣一些理論中,自由不過(guò)是來(lái)自歷史或理性本身的延續(xù),而不是人類(lèi)現(xiàn)實(shí)活動(dòng)爭(zhēng)取的結(jié)果。由此而構(gòu)造出的改變世界之舉措,也曾有過(guò)鞭撻現(xiàn)實(shí)世界黑暗的言論,卻無(wú)法找到現(xiàn)實(shí)世界黑暗之源頭;也曾對(duì)未來(lái)社會(huì)給予無(wú)限憧憬,但卻無(wú)法找到由現(xiàn)實(shí)世界通向未來(lái)世界的實(shí)踐途徑。因此,在解釋世界的框架下所從事的改變世界的行為,無(wú)法越過(guò)理論與實(shí)踐、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溝壑,對(duì)于世界的局部性改變,不過(guò)是調(diào)整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上帝的某種關(guān)系,它不能保證在新的關(guān)系中確立自由的永恒天地,更不能保證新的關(guān)系中根除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ài)的根由。在這樣一種理論中,康德所希翼的永久和平,只能化為永久的期待。同樣,把新哲學(xué)的旨趣聚焦于“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也從來(lái)沒(méi)有放棄解釋世界的理論要求。在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中,從來(lái)沒(méi)有放棄理論解釋世界的功能。而這個(gè)思想,來(lái)自于馬克思關(guān)于人及其人之自由的認(rèn)定。
《巴黎手稿》中的馬克思曾經(jīng)憧憬著“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社會(huì)組織,其中“自由人”的概念卻仍然保留著由異化而異化復(fù)歸的精神演繹痕跡。“萊茵報(bào)”及其“德法年鑒”時(shí)期的生活踐履,是馬克思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由質(zhì)疑到批判的出發(fā)點(diǎn),而二者分界的地方,恰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解釋方式和改造方式之不同。在馬克思看來(lái),關(guān)于解釋世界的美好和證明不是來(lái)源于理論自身的邏輯,而是要來(lái)源現(xiàn)實(shí)世界自身的邏輯,所以馬克思解釋世界的邏輯,只能產(chǎn)生于改造世界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之中。恰恰是在確立改變世界的理論宗旨基礎(chǔ)上,才有了在對(duì)私有制的現(xiàn)實(shí)批判基礎(chǔ)上完成的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的現(xiàn)實(shí)性規(guī)定,而自由的問(wèn)題,也在馬克思的這種規(guī)定中,擺脫了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的對(duì)峙關(guān)系,在人類(lèi)的物質(zhì)性實(shí)踐活動(dòng)中得到充分說(shuō)明。《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來(lái)說(shuō),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⑦在這個(gè)判斷中,馬克思一反傳統(tǒng)哲學(xué)的邏輯路向,認(rèn)為人的本質(zhì)不是彼岸世界的理論懸置,任何以“非現(xiàn)實(shí)性人”為基礎(chǔ)的關(guān)于人的抽象規(guī)定,都無(wú)法真正解釋人和人的所謂本質(zhì)問(wèn)題。傳統(tǒng)哲學(xué)在2000多年歷史中憑借著邏輯的力量而抽象出來(lái)的各種“本質(zhì)”,構(gòu)造了關(guān)于人之本質(zhì)的概念史的重要內(nèi)容,而這些停留在概念上的本質(zhì),只能把人理解為一個(gè)不具有感性存在意義的純粹理性存在。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關(guān)于人和人的活動(dòng)的所有解釋?zhuān)荒軠S為“醉醺醺思辨”中的空洞概念。離開(kāi)現(xiàn)實(shí)世界去構(gòu)筑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完滿(mǎn)體系,用解釋世界的框架來(lái)推演和判定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合理性,不可能說(shuō)明人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
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只能在現(xiàn)實(shí)性的基礎(chǔ)上才能加以認(rèn)定的理論,已經(jīng)消解了概念史所奉行的理性邏輯之神圣性。當(dāng)馬克思把人理解為感性存在時(shí),同樣拒絕了以日常生活簡(jiǎn)單活動(dòng)的白描作為本質(zhì)規(guī)定的社會(huì)史習(xí)俗。在批判費(fèi)爾巴哈人本主義基礎(chǔ)上,馬克思把人的本質(zhì)理解為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它表明了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一的、不變的,而是在包含著物質(zhì)關(guān)系與思想關(guān)系在內(nèi)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制約中形成,并隨著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改變而改變的。人的思想關(guān)系、政治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文化關(guān)系等內(nèi)容,都是“存在著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系,哲學(xué)的任務(wù)既不是要撇開(kāi)這些關(guān)系去追求純粹的存在,也不是要把這些關(guān)系做簡(jiǎn)單的社會(huì)史般的白描,而是要用“本質(zhì)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手段,在力圖改變世界的基礎(chǔ)上解釋人的現(xiàn)實(shí)本質(zhì)的決定性因素。馬克思的結(jié)論是,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各種復(fù)雜關(guān)系中,真正能夠決定人的現(xiàn)實(shí)本質(zhì)的,是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于是,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狀況的分析,成為馬克思“解釋世界”理論的重要內(nèi)容。另一方面,既然人的本質(zhì)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而由人的活動(dòng)所構(gòu)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又是不斷變化的,那么,傳統(tǒng)哲學(xué)中,以人的本質(zhì)之確定性和不變性為前提的種種“本質(zhì)前定論”或“本質(zhì)終定論”,就不過(guò)是借助形而上學(xué)思維習(xí)性描述出來(lái)的無(wú)法實(shí)現(xiàn)的主觀愿望而已。《資本論》中對(duì)于資本主義社會(huì)運(yùn)行規(guī)律的分析中,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的思想得到完整的闡釋。譬如,剩余價(jià)值理論不僅揭示了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苦難的淵藪,而且認(rèn)定世界歷史狀態(tài)下私有經(jīng)濟(jì)的蔓延,一定會(huì)使人在不合理的社會(huì)制度下浸淫出越來(lái)越多的自私和貪婪。在這樣一個(gè)僅靠物質(zhì)欲望支撐的社會(huì)中,任何道德說(shuō)教和宗教的信仰,都無(wú)法掩飾和改變社會(huì)關(guān)系的邪惡,由此而塑造出的不自由的人性,也不可能在任何一種單純的理性批判中得以改善。這一切說(shuō)明,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革命,改變并創(chuàng)造新型社會(huì)關(guān)系,才是創(chuàng)造以自由為本質(zhì)的人的唯一手段,而在自由人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lái)的社會(huì)群體,才是被稱(chēng)之為“共產(chǎn)主義”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
縱觀馬克思哲學(xué)的基本理論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作為一種理論,馬克思當(dāng)然是在用概念去述說(shuō)和解釋歷史,但是這種概念不是邏輯上的定義或演繹,事實(shí)上,馬克思從未為任何一個(gè)概念做過(guò)邏輯學(xué)意義上的嚴(yán)格定義,這些概念不是來(lái)自簡(jiǎn)單的邏輯抽象,而是來(lái)自改變世界的現(xiàn)實(shí)需要。在這樣一種需要下,不在場(chǎng)的歷史不是“過(guò)去了”的“史實(shí)”,而是一個(gè)完全可以服務(wù)并解釋現(xiàn)實(shí)的在場(chǎng)行為。同樣,包括自由人聯(lián)合體在內(nèi)的社會(huì)圖景,也不是僅僅以未來(lái)形式召喚現(xiàn)實(shí)的一種理想,而是一個(gè)孕育在改變世界之中并且化為改變世界行為的在場(chǎng)性現(xiàn)實(shí)運(yùn)動(dòng)。恩格斯把馬克思的哲學(xué)稱(chēng)之為“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僅僅是改變了我們觀世界的結(jié)論或方法,更重要的是讓本來(lái)就置身于世界中的我們,在改變世界的過(guò)程中完成了解釋世界的任務(wù)。世界觀旗幟下展開(kāi)的社會(huì)史與概念史所孕育的問(wèn)題,涵蓋著人類(lèi)精神最為執(zhí)著的追求;能夠以哲學(xué)的形式產(chǎn)生全新世界觀的時(shí)代,是一個(gè)能夠喚醒思想變革的偉大時(shí)代。與人類(lèi)文明共生的自由問(wèn)題,就是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它涵蓋了人類(lèi)所關(guān)注的所有問(wèn)題的基本旨趣;以自由為主題的世界觀所創(chuàng)造的時(shí)代,就是這樣一個(gè)時(shí)代,它刻畫(huà)了人類(lèi)歷史的每一次發(fā)展與進(jìn)步,并以未來(lái)?yè)湎颥F(xiàn)實(shí)的視域開(kāi)辟,完成了歷史、現(xiàn)實(shí)和未來(lái)的對(duì)接。因此,無(wú)論是自由的社會(huì)史之表述,還是自由的概念史衍生,都將在世界觀的旗幟下開(kāi)墾出屬于人類(lèi)的自由之路,并且在人類(lèi)自由之旅的行進(jìn)中,朝向自由本身。
作者:侯小豐 單位:遼寧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