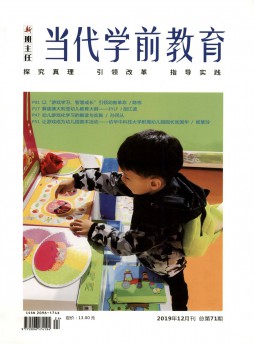學前教育的頂層規劃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學前教育的頂層規劃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學前教育憲法保障的規范基礎
立憲主義憲法最核心的價值在于基本權利的保障。憲法是基本權利的證明書,也是基本權利的“護身符”。公民的基本權利只有得到憲法的確認和保障,才不至于被公共權力所侵犯和忽視。憲法作為“法律中的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確認和保障直接關系到其他法律對公民具體權利的確認和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憲法永恒的主題,憲法一般由公民權利條款(人權規范)和國家組織條款(組織規范)兩大部分構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始終居于核心地位。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作用是憲法最原初的作用,也是憲法最終極的作用。學前教育的憲法保障之關鍵和起點則是學前教育憲法規范載入憲法,即作為一種憲法權利的確立。
(一)作為政策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
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予以區別對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規定為基本權利,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則作為政策目標,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被當作是需要立即實現的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作為政策目標則是國家應該努力實現的理想,其實現有賴國家具備的經濟文化資源和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該政策性類型的憲法權利的條文表述通常不是出現在專門的憲法權利章節中,而是出現在“國家政策目標或原則”之類的章節中。單就我國憲法第19條規定的“國家……發展學前教育”而言,其出現在憲法“總綱”中,是“國法秩序的綱領”關于教育事業的憲法規范。這屬于“以規定政府義務為內容的規范”,以德國法學家阿列克西關于憲法規范分為主觀性規范和客觀性規范兩大類型的視角來看,我國憲法第19條的規定屬于客觀性規范,并非一種授予主觀權利為內容的主觀性規范。如果僅僅依據該條款來看,這就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作為政策目標或原則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
(二)作為宣認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
與作為政策目標或原則的形式不同,宣認性的憲法權利是在憲法文本的權利章節中直接規定學前教育。學前教育權利成為明確的憲法權利而不是政策目標。與作為政策目標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相比,這種意義上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具有的一個最為明顯的優勢是,它是一種主觀性憲法權利的確認,國家負有尊重和保護的義務,不得以經濟社會條件為由而推諉塞責。我國憲法第46條作為受教育權的憲法規范,直接明確地宣認了公民受教育權的憲法權利的性質和地位,這一點乃學界共識。但應該看到,該條款或是第49條,都并非是對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直接宣認。然而,依常識理解,該條款字面含義即隱含有學前教育憲法權利。作為一種明確的權利類型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呼之欲出,欠缺的只是憲法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
(三)作為推定的學前教育憲法權利
法律不可能窮盡一切潛在的權利,除法律明確宣示的權利以外,尚有法律默示的權利、法律漏列的權利、法律未預測到的新生權利等,“權利推定是以法律明示的權利或者與之相關的法律原則、立法宗旨為依據,推定出默示權利及其他應有權利的存在并確認其合法性的過程。”阿列克西也指出存在一種根據憲法基本權規定而派生出來的規范,這些衍生規范如果能夠通過正確的基本權論證,從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權規范推衍得出時,便可視為有效的基本權規范。
根據我國憲法第19條、第46條和第49條之規定,綜合來看,憲法確立了學前教育的憲法規范。學前教育憲法權利不僅僅是政策性的憲法權利,而是明確的基本權利,顯然具備憲法權利的性質、地位和效力。在我國1982年憲法中,學前教育已經入憲,這是學前兒童教育權利與憲法規范的結合。從憲法的視角看,一種新的憲法規范———學前教育權利憲法規范自此產生。學前教育權利和法律關系不是僅局限于教育法律或法令等位階較低的法律文本中體現,而是同時在憲法文本中呈現。
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雙重屬性
憲法權利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但并非一般的權利,而是一種基本權利。在英美語境下則一般使用“人權”概念,而德國憲法習慣以“基本權利”或“基本權”稱之,日本則謂之“基本人權”。
我國憲法上的用語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這種由憲法規范的權利是一種基本性的重要權利,并非僅是一種“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實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當今立憲主義憲法權利與“人權”和“基本權”概念本質相當,實際上包括了近代憲法的“市民性和政治性權利”以及現代憲法上的“經濟性的和社會性的權利”。所以,在憲法學理上,一般將憲法權利分為自由權和社會權。自由權是一種消極權利,是指個人要求國家權力作出相應不作為的權利。社會權則是一種積極權利,即個人要求國家權力作出相應作為的權利。近代憲法主要保護自由權,現代憲法則主要保護社會權。學前教育憲法權利一般而言總體上屬于社會權范疇,但同時具有自由權的內容和面向,是一種兼具社會權和自由權的綜合性權利。自由權和社會權“二分法”的憲法學理有助于深入理解學前教育憲法權利。
(一)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社會權屬性
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社會權是作為基本權利的受益權功能,所對應的是國家的給付義務。為保障學前兒童受教育的憲法權利,國家以積極的立場、態度和手段,幫助和保護學前兒童的學習權利。至少包括“入學請求權、必要教育設施的創設請求權、獲得教育資助權”等內容。國家要在“提供入學機會、建設教育條件和給予教育資助”等重要關鍵方面對學前兒童負擔起職責,積極履行國家義務。
當前學前教育的國家戰略層面,要在高度重視學前教育發展的基礎上,切實加強學前教育事業的投入。中央和地方財政要為學前教育的長足穩定發展奠定物質基礎,同時積極吸引社會有利力量促進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國家財力有限的區域和地方,更要積極、合理地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在國家加大投入、增加給付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學前教育師資力量的培育和建設。沒有一支數量和質量匹配的幼兒教師隊伍,學前教育的發展、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保障和實現等就只是空談。因此,學前教育國家給付的使命任重道遠。國家保障學前兒童憲法權利的關鍵和核心是保障學前教育的平等,力求縮小并最終消除城鄉差別、區域差別,以及在性別、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差異。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社會權之終極價值追求和最為現實所窘迫的是保障學前教育平等,實現起跑線上的教育公平。在學前教育發展法律規范的憲法金字塔頂端,必須一以貫之以平等。就學權利平等、教育條件平等和教育效果平等三個層次,在學前教育的憲法權利“追求和奮斗”中一個不能少。
(二)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自由權屬性
“國家無權制定法律束縛個人在物質、智力、道德諸方面進行發展的自由,但是顯然國家強制所有人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并沒有違背這一原則,因為受教育恰恰是個人活動發展的前提條件。”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家的積極給付,但這并不意味著學前兒童在學前教育中就沒有了自由。國家保護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終極價值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這對立憲主義憲法而言,即是其終極價值的追求———“人的尊嚴”。國家對學前教育的積極介入是為了“人的尊嚴”之追求,也受到“人的尊嚴”之尊重的限制。這種尊重就體現了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自由權維度。在非義務化階段和當下,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自由權方面的關鍵是入學選擇問題。是就近入園還是擇園,涉及到學前兒童及其家長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入園難”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從憲法權利的視角來看,是憲法權利受到侵害和威脅的一大癥狀。從總供給的角度來看,解決“入園難”有待國家給付在社會權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在一定條件下,某個階段中的結構性問題是自由權保障問題。學前教育入學選擇是一項基本自由,國家負有的職責是破除妨礙學前兒童及其家長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各種行為、制度和規范。
學前教育在世界教育發展潮流中有普及化、義務化的趨勢,學前教育義務化有利于憲法權利的保障和實現。義務化對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社會權方面來說意義非凡,但義務化所要求的普及強制可能對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自由權方面帶來挑戰甚至威脅。當前,不入園或在家學習的方式或做法屆時將可能成為一種法律意義上的不可行。學前兒童在家學習的方式能否繼續成為學前教育的一種選擇和自由必將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話題。以立憲主義“人的尊嚴”的價值蘊含和追求來看,在追求和推動學前教育普及化和義務化的大前提和大戰略下,可以強調和著重國家提供普及免費的學前教育,但不奉行強制入園的理念和原則,以“入園”和“在家”兩種方式并舉推動學前教育的發展。適齡學前兒童在家學習的選擇和自由應得到國家的尊重。對這個問題,國家應該也可以在更高層面上保障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即由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兒童學習具有顯著的積極效應,國家應當給予有需要的學前兒童家長以適當、必要的教育幫助,以促進學前兒童在家學習成為一種實現憲法權利的合理選擇和有效途徑。
學前教育憲法保障的實現路徑
要讓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從憲法文本走向現實生活,需要憲法規范得到切實有效的落實,這種憲法才不是名義上的憲法,而是“體現了立憲主義精神,并具有規范實效性”的“規范憲法”。這樣一來,學前教育的憲法規范也就走向了規范憲法意義上的學前教育。這個動態的實踐過程也是學前教育憲法權利走進生活、走向現實的過程。這是學前教育憲法權利規范具體化、現實化的過程。國家有關機關和部門應切實承擔職責,履行義務,促進學前教育憲法保障的實現。
(一)學前教育立法的迫切需要
學前教育在我國1982年憲法中入憲后,立法機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相關或涉及學前教育的教育法律。如,199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1991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1993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995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有關學前教育立法工作在教育立法進程中附帶性啟動,但并沒有明確、專門的“學前教育法”立法。在20世紀末“初步形成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法律體系”顯然還缺乏學前教育法這重要一環。但十多年來,教育立法工作不再是立法機關的工作重心,學前教育立法遲遲未能啟動,甚至不能進入立法規劃的視野。
新世紀伊始,學前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從2004年開始,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中編辦、教育部等部門先后到江西、江蘇、山東、河北等地進行了學前教育立法調研,了解各地在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和管理方面的經驗和問題,梳理了立法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為正式啟動立法工作做了基礎性的工作。2009年學前教育立法正式納入《全國教育事業“十一五”發展規劃》和教育部“十一五”立法計劃。2010年國家陸續頒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和“國十條”,教育尤其是學前教育受到高度關注。適逢新一屆人大將組成并繼續展開立法工作,學前教育立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通過學前教育立法使得憲法中的學前教育條款法律化、具體化,這種實現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立法保障是最有力、最基礎的權利保障途徑和方式。憲法由于高度抽象性以及根本法的地位,決定了憲法規范難以直接適用、執行。學前教育立法對學前教育的憲法保障具有無與倫比的作用和意義。
(二)行政權的積極貢獻
即使學前教育憲法權利有了立法保障經由立法而具體化為法律權利,并不必然自動地成為學前兒童實際享有的權利,其實現很大程度上還依賴國家行政權力的積極作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立法不易,執法更難。學前教育發展的憲法保障依賴于行政權力的積極功能。這在給付行政時代的中國語境下尤為關鍵。據國務院法制辦統計,中國有近80%的法律法規是由各級行政機關貫徹執行的。
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具有很強的社會權屬性,需要國家權力積極作為來保障實現。相比立法權力,行政權力具有更強的能動性和給付功能。現代行政法尤為強調關注積極行政服務行政所具備的憲政功能和意義。德國行政法之父奧托•梅耶的經典名言“憲法消逝而行政法長存”在中國學前教育法語境下可謂相當暗合。目前,學前教育的法律規范總體而言是行政法的天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構建了學前教育法律規范體系的基本骨架和血肉。學前教育憲法權利的保障和實現如果沒有行政權力的支撐將蕩然無存。從這個意義上講,學前教育的行政法可以說是一種“具體化憲法的行政法”。
《教育規劃綱要》和“國十條”是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藍圖,是我國學前教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這兩個文件是國務院在國家戰略層面發展學前教育的宣告,是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向行政法權利轉換的重大舉措,也是行政權對學前教育憲法貢獻的生動寫照。我們期待國家有關行政機關和部門在不同層級不同區域就該綱領性文件進行細化、展開和落實。經由行政權力貫徹落實學前教育執行工作,學前教育憲法權利必將得以大范圍、深程度地走向現實,從法律權利逐步變成現實權利。
作者:馮強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