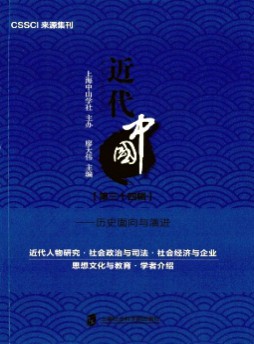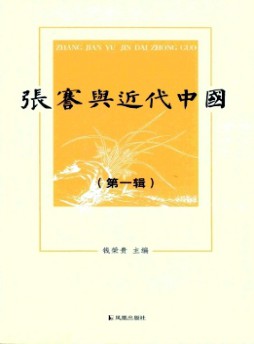近代高等科學(xué)教導(dǎo)的歷程與展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近代高等科學(xué)教導(dǎo)的歷程與展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維新運動時期高等科學(xué)教育的發(fā)展
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人對傳統(tǒng)高等教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全面改造。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fù)、譚嗣同、黃遵憲等為首的維新派,代表中國資產(chǎn)階級,要求更多地引進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這已經(jīng)超出了洋務(wù)派偏重學(xué)習(xí)西方實用科技的狹隘局限。康有為在《請開學(xué)校折》中向皇帝建議:“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xué)制”,主張省府立專門高等學(xué)校和大學(xué),京師設(shè)大學(xué)堂,學(xué)習(xí)內(nèi)容主要是本專業(yè)課程,同時也學(xué)習(xí)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等基礎(chǔ)課程,要求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nèi)引進西學(xué),培養(yǎng)中西貫通的政治人才。同時,他們將西學(xué)進一步地分為藝和政兩部分,前者指自然科學(xué)、工程技術(shù)等,后者指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1895年、1896年成立天津中西學(xué)堂、上海南洋學(xué)堂。1898年醞釀多時的京師大學(xué)堂也開始正式開辦,它是我國近代第一所新式的國立大學(xué),為全國最高的學(xué)府,也是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guān),標志著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了創(chuàng)建和確立階段。這一時期,高等科學(xué)教育的課程設(shè)置、體制規(guī)模都有了很大的擴展。例如,京師大學(xué)堂章程明確提出京師大學(xué)堂的辦學(xué)宗旨為:中西并重、觀其會通、不得偏廢;把西學(xué)作為學(xué)堂的一門課程,而不是學(xué)堂的全部學(xué)習(xí)內(nèi)容。按照章程,京師大學(xué)堂在課程設(shè)置上開設(shè)了溥通學(xué)和專門學(xué)兩類課程。溥通學(xué)作為基礎(chǔ)課程,為每個學(xué)生必修,主要學(xué)習(xí)經(jīng)學(xué)、理學(xué)、中外掌故學(xué)、諸子學(xué)、初級算學(xué)、初級格致學(xué)、初級政治學(xué)、初級地理學(xué)、文學(xué)和體操學(xué),另設(shè)英、法、俄、德、日五種外語,20歲以下學(xué)生任選一種。而專門學(xué)則學(xué)習(xí)高等算學(xué)、高等格致學(xué)(法律學(xué)歸此門)、高等地理學(xué)(測繪學(xué)歸此門)、農(nóng)學(xué)、礦學(xué)、工程學(xué)、商學(xué)、兵學(xué)、衛(wèi)生學(xué)(醫(yī)學(xué)歸此門)。由此可見,維新派在“中西貫通”的理念下,使得京師大學(xué)堂成為調(diào)和新舊思想、融貫中西學(xué)術(shù)與交匯科學(xué)與人文的大熔爐。然而,清末中國出現(xiàn)的新式高等教育機構(gòu),它們只是“現(xiàn)代”大學(xué)的雛形,創(chuàng)辦發(fā)展極其有限,還無法培養(yǎng)高水平的技術(shù)人才。但是,維新派推崇的科學(xué)教育內(nèi)容,在洋務(wù)時期的高等科學(xué)教育基礎(chǔ)上,內(nèi)涵要廣泛的許多。1904年癸卯學(xué)制的頒布和實施,科學(xué)教育以法令刑事被證實納入教育體系中,科學(xué)教育有了較為可靠的制度保障。此時,科學(xué)教育在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快速發(fā)展的態(tài)勢:從1905年到1909年,全國已有農(nóng)業(yè)、商業(yè)、理工等專業(yè)學(xué)校16所,學(xué)生1881人;實業(yè)學(xué)校254所,學(xué)生16649人。到1911年,127所高等專門學(xué)校中,理工農(nóng)醫(yī)類學(xué)校共23所,學(xué)生達2196人。《奏定學(xué)堂章程》所規(guī)定的21種理工農(nóng)醫(yī)專業(yè)中,就開設(shè)有465種完全由西方傳入的自然科學(xué)課程。癸卯學(xué)制在各級學(xué)校中規(guī)定了不同程度和分量的科學(xué)教育內(nèi)容的課程設(shè)置,使得學(xué)生既可學(xué)習(xí)到普通的科學(xué)知識,還能根據(jù)各自的情形學(xué)習(xí)專門的科學(xué)技術(shù)。
民國時期高等科學(xué)教育領(lǐng)域中科學(xué)與人文的紛爭
1912年民國政府建立初期,在科學(xué)救國思潮的推動下,教育界進步人士十分重視高等科學(xué)教育的發(fā)展,強調(diào)加強大學(xué)科學(xué)教育是培養(yǎng)科學(xué)救國人才的關(guān)鍵。因此,教育家們主張設(shè)立“自然科學(xué)”系和專門的研究機構(gòu),這是實現(xiàn)高等科學(xué)教育化的重要舉措,也是培養(yǎng)科學(xué)救國人才的重要渠道。高等學(xué)校的科學(xué)教育迅速發(fā)展,全國各高校普遍設(shè)立自然科學(xué)系或者理工系,而且科學(xué)類系數(shù)數(shù)量40年代首次超過人文類系。1917的北京大學(xué)和1920年北京高師、南京高師分別建立了心理實驗室,這標志著近代科學(xué)教育思潮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影響,加上引進的一些諸如杜威等外來學(xué)者的教育思想廣泛流傳,多元化的科學(xué)思想的滿足了觀念上更新的需要,中國科學(xué)教育在實踐上呈現(xiàn)出快速發(fā)展的趨勢,且特別注重科學(xué)教育方法和科學(xué)精神的提倡,但對科學(xué)主義傾向的同時也夸大了科學(xué)、科學(xué)教育的作用,輕視甚至出現(xiàn)排斥人文教育的現(xiàn)象。然而,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有關(guān)于科學(xué)與人文教育的關(guān)系問題開始有了探索。1923年前后,推崇唯心主義哲學(xué)的張君勱在清華大學(xué)給學(xué)生作了一篇關(guān)于《人生觀》的演講,引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科學(xué)與人生觀”的大論戰(zhàn),在“科學(xué)派”和“玄學(xué)派”中引起軒然大波,至此,科學(xué)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紛爭拉開序幕,由此也引發(fā)了人們對科學(xué)與人文之間的關(guān)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各教育家們對大學(xué)教育應(yīng)該培養(yǎng)“通才”還是“專才”的探索也由此展開。
1916至1923年期間,蔡元培時任北京大學(xué)的校長,最初主張“宜特別注重文理兩科”,但到后來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進一步主張“溝通文理”。1918年9月,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xué)式演說詞》中說:“近并鑒于文科學(xué)生疏忽自然科學(xué),理科學(xué)生輕忽文學(xué)、哲學(xué)之弊,(故)為溝通文、理兩科之計劃。”他從文科教育為突破口,開始整頓北大,宣傳并落實了科學(xué)教育與人文教育交融的理念。在蔡元培口述的傳略中,他道出:“那時我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他談到:“孑民有發(fā)現(xiàn)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xué)、文學(xué)均與科學(xué)有關(guān),而哲學(xué)則全以自然科學(xué)為基礎(chǔ)。乃文科學(xué)生,因與理科隔緣之故,遂視哲學(xué)為無用,遂不免流于空談。理科各學(xué),均與哲學(xué)有關(guān),自然哲學(xué),尤為自然科學(xué)之歸宿,乃理科學(xué)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xué)為無用,而陷于機械的世界觀。”對于文理之間的關(guān)系,他進一步地指出,“文科的哲學(xué),必根基于自然科學(xué);而理科者最終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xué)。從前心理學(xué)附入哲學(xué),而現(xiàn)在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xué)的人文方面,應(yīng)屬文科。而源于地質(zhì)學(xué)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因此他認為,文理兩科之間,“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建議溝通文、理,合為一科”,若文、理分科,容易造成兩者之間的嚴格界限,使學(xué)生習(xí)文者輕理、學(xué)理者輕文。對此,蔡元培在北京大學(xué)試行了“融通文理”的措施。1919年,北大正式廢去文、理兩科,在全校設(shè)14個系:數(shù)學(xué)、物理、化學(xué)、地質(zhì)學(xué)、哲學(xué)、中外、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學(xué)、經(jīng)濟、政治和法律。另外,大學(xué)本科“融通文、理兩種之界限:習(xí)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xí)理科中之某種(如習(xí)史學(xué)者,兼習(xí)地質(zhì)學(xué);習(xí)哲學(xué)者,兼習(xí)生物學(xué)之類);習(xí)理科者,不要不兼習(xí)文科之某種(如哲學(xué)史、文明史之類)。”
1921年,東南大學(xué)在南京成立,郭秉文時任校長,他完全以美國大學(xué)教育制度作為東南大學(xué)的藍本進行辦學(xué),提倡文理并重、學(xué)術(shù)并重,集文、理、工、農(nóng)、商、教育于一體;提倡多科并重,使學(xué)與術(shù)、通才與專才、基礎(chǔ)與應(yīng)用相互補充,平衡發(fā)展,而不是將兩者截然劃分開來。在他的主持下,東南大學(xué)既設(shè)文科、理科,也設(shè)工科、農(nóng)科、商科。這樣設(shè)系的好處是,易收學(xué)科互濟互補之效,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專才不致流于狹隘,有利于提高教學(xué)質(zhì)量,開展研究工作,培養(yǎng)多種人才。1929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規(guī)定大學(xué)教育的目標:“大學(xué)及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xué),充實科學(xué)內(nèi)容,養(yǎng)成專門知識技能,并切實陶融為國家社會服務(wù)之健全品格。”“師范教育……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xué)教育及最嚴格之身心訓(xùn)練”的規(guī)定。
1931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令教育部執(zhí)行國民會議通過的《確立教育設(shè)施趨向案》,根據(jù)“大學(xué)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學(xué)及實用科學(xué)為原則”的精神,高等教育的辦學(xué)就此向注重實科的方向傾斜,要求對文法科嚴格奢侈,分別歸并或停年招生、或分年結(jié)束,而將所節(jié)余的經(jīng)費移作擴充或改設(shè)理、工、農(nóng)、醫(yī)等科之用,從而對大學(xué)文科的反展有所限制。可見,政府十分重視實用科學(xué)的作用,提倡科學(xué)和科學(xué)教育,大學(xué)對人才的培養(yǎng)在于教授實用性科學(xué),養(yǎng)成專門的技術(shù)人才,側(cè)重應(yīng)用性,科學(xué)教育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即便如此,我國大學(xué)科學(xué)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滲透的辦學(xué)特點也表現(xiàn)的十分凸顯。如清華大學(xué)校長梅貽琦從儒家傳統(tǒng)的“大學(xué)之道”出發(fā),結(jié)合當時的社會實際,提出了大學(xué)應(yīng)當實施“通才教育”,這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他看來,大學(xué)教育應(yīng)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貫徹通才教育的主要措施是以學(xué)分制為主體的,“選修課制”,“共同必修課”三者結(jié)合成三位一體的學(xué)習(xí)制度。1933年開始,根據(jù)通才教育原則,學(xué)校規(guī)定大一不分系,以后文、理、法、工各院學(xué)生在大一修習(xí)包括自然、社會與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課。在清華大學(xué)規(guī)定的1936-1937年度分年課程表中,中國文學(xué)系組第一年必修課學(xué)程包括了國文、第一年英文;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以上二科中選一科);邏輯、高級算學(xué)、微積分(以上三科中選一科);普通物理、普通化學(xué)、普通地質(zhì)學(xué)、普通生物學(xué)(以上四科中選一科)。
這打破了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格和發(fā)展方面的單一性,使學(xué)生能夠揚長補短、各得其所,為日后各展其能、其所用奠定了堅實基礎(chǔ)。梅貽琦校長于1941年4月發(fā)表的《大學(xué)一解》中指出,清華大學(xué)的畢業(yè)生,無論學(xué)哪個學(xué)科專業(yè),有一共同的要求,即“他們對于人文學(xué)科、社會學(xué)科、自然學(xué)科這三大部分應(yīng)有相當準備”,因為這三部分“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不過梅貽琦不主張“通專并重”,認為大學(xué)四年并重之說“窒礙難行”。此外,當時擔(dān)任浙江大學(xué)校長的竺可楨,在通與專的問題上,他也認為大學(xué)如果只是注重應(yīng)用科學(xué),而置科學(xué)理論和人文社會科學(xué)于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因此大學(xué)應(yīng)實行通才教育,注重科學(xué)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他曾在民國政府教育部的一次會議上,進言將“通才教育“寫進大學(xué)組織法的第一條。他說,“大學(xué)一、二年級中,工學(xué)院自宜打定數(shù)、理良好基礎(chǔ),文法等院自宜重視文學(xué)、經(jīng)濟及中外歷史,以備專精。雖然,彼此不可偏廢,仍宜相互切磋,庶幾知識廣播,而興趣亦可盎然。”
因此,他非常注重給學(xué)生打基礎(chǔ),重視開好基礎(chǔ)課,將數(shù)學(xué)、物理、化學(xué)、英文、國文、生物和通史都定為一年級學(xué)生的課程。另外,他還主張學(xué)生知識面要寬,學(xué)生除本系課程外,自二年級起,必須學(xué)習(xí)一輔系課程,鼓勵學(xué)生跨系自由選讀,最后達到精通本學(xué)科、旁通邊緣學(xué)科、文理滲透、觸類旁通的目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科學(xué)事業(yè)遭受了災(zāi)難性的打擊,各大學(xué)的學(xué)生不少人中斷了學(xué)業(yè),流亡失學(xué)。然而政府對高等教育進行了統(tǒng)一管理和規(guī)范,因此高等科學(xué)教育的發(fā)展并未停止。1938年9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大學(xué)課程會議,公布了《文理法三學(xué)院各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規(guī)定了課程整理的原則。同年11月,公布了公、農(nóng)、商三學(xué)苑的共同必修科目。1939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學(xué)及獨立學(xué)院及各系名稱》,其中規(guī)定在理學(xué)院所設(shè)系的名稱上趨于統(tǒng)一。1944年8月,教育部召開第二次大學(xué)課程會議,修正公布了《文理法師范四學(xué)院分院必修科目表》,其中規(guī)定了文、理、法、師范學(xué)院的院系選修和必修課程以及應(yīng)達到的學(xué)分。到1948年抗戰(zhàn)結(jié)束,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高等科學(xué)教育得到了相當?shù)陌l(fā)展。此外,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抗日根據(jù)地也得到了發(fā)展,1940年9月,自然科學(xué)院在延安成立,這是由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創(chuàng)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學(xué)校,設(shè)立物理系、化學(xué)系、生物系、地(質(zhì))礦(冶)系,自然科學(xué)院于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學(xué),分設(shè)機械工程、農(nóng)業(yè)、化學(xué)工程三系。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國初步形成了以傳授自然科學(xué)知識為主、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高等科學(xué)教育體系。
總結(jié)啟示
第一,高等科學(xué)教育的發(fā)展并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而是貫穿著科學(xué)與人文的斗爭、融合,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反復(fù)的發(fā)展過程。至清朝末年開始,隨著洋務(wù)派的“中體西用論”發(fā)展到維新派的“會通中西觀”,都反映出人們企圖調(diào)和“中學(xué)(人文)”與“西學(xué)”(科學(xué))之間的矛盾讓科學(xué)進入高等教育的努力,但二者的界線仍是分明的,本、末、體、用的文化論是清末的高等教育改革者們誰也擺脫不掉的。因此,對高校科學(xué)教育的認識也停留在零散、感性的水平上,缺乏系統(tǒng)性。而后的民國時期,雖然受到戰(zhàn)爭的影響,但是在教育先輩們對“通才”教育的努力探索下,使得科學(xué)教育與人文教育得到進一步的融合和互動,這給當時的中國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一批大學(xué)在異常艱苦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里奇跡般地取得了巨大成就。當今社會,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目前高校科學(xué)教育還存在著諸多弊端需要改正,在今后對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過程中也會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就告誡我們,任何的教育變動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廣大教育工作者從多方面進行系統(tǒng)和全面的考察與研究,并作出長期的努力。
第二,歷史上眾多思想家曾對高校科學(xué)教育進行過廣泛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對當前高校大學(xué)生的科學(xué)素養(yǎng)教育的開展具有很強的指導(dǎo)意義。洋務(wù)運動的高等科學(xué)教育發(fā)展,培養(yǎng)了一批掌握西方自然科學(xué)技術(shù)的知識份子,雖然對人才的培養(yǎng)目標、課程設(shè)置和教學(xué)水平還無法達到一個高度,但這對以經(jīng)學(xué)為主傳統(tǒng)教育是一個突破,同時也促進了當時中國科學(xué)的發(fā)展和資產(chǎn)階級新思想的形成。特別是民國時期以來,一些著名大學(xué)校長提出的具有時代特征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大學(xué)理念,對我國高校科學(xué)教育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蔡元培的“文理滲透”思想以及梅貽琦和竺可楨的“通才”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們的教育思想各有側(cè)重,但都十分重視培養(yǎng)通才,塑造學(xué)生的人格,強調(diào)科學(xué)與人文的綜合發(fā)展,以實現(xiàn)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在辦學(xué)實踐中,他們對以往大學(xué)過于注重培養(yǎng)專才的現(xiàn)象,提出了批評,并在各自大學(xué)中進行融合科學(xué)教育與人文教育關(guān)系的大膽探索。雖然這些思想觀念和教育實踐已經(jīng)過去了大半個世紀,其間我國的政治、經(jīng)濟、科技、文化也發(fā)生了重大的變革,但這些思想的精髓和實踐經(jīng)驗仍然具有現(xiàn)實指導(dǎo)意義,而且應(yīng)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普遍關(guān)注。我們應(yīng)當善于總結(jié)先輩們的經(jīng)驗教訓(xùn),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索高校科學(xué)教育的道路上作出正確合理的判斷,避免出現(xiàn)同樣的問題。
第三,不能機械地借鑒他國的建議,而應(yīng)有針對性地、有選擇地學(xué)習(xí)和參考國外教育的有效經(jīng)驗,結(jié)合中國的實際,加強本土化的探索。我國的近代科學(xué)與科學(xué)教育是從西方引進的,但對其引進介紹卻是膚淺和殘缺的,只停留在堅船利炮、聲光電化等科學(xué)知識和實際應(yīng)用的層面,尤其缺乏的是科學(xué)精神、科學(xué)方法、科學(xué)觀念的引入和建立。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gòu),實際上都是有意仿照西方大學(xué)的,但是并沒有成為西方那樣的各類學(xué)科。這就告誡我國在新時期、新形勢下應(yīng)當注重我國教育的實際情況,提升對文化素質(zhì)教育和通識教育的認識,吸取他國對解決中國高等教育問題行之有效的經(jīng)驗對策,探討中國特色的文化素質(zhì)教育的理想與合理模式。
作者:陳琳王巍單位:武夷學(xué)院人文與教師教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