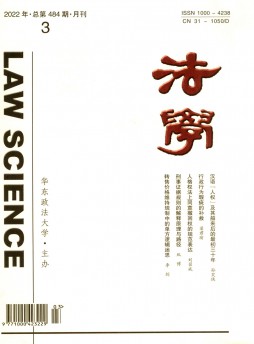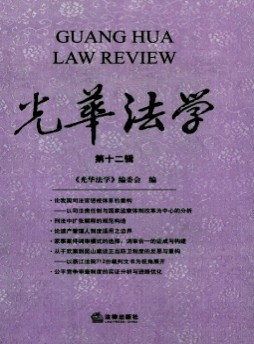法學(xué)刊物是促進法學(xué)發(fā)展的必備品質(zhì)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法學(xué)刊物是促進法學(xué)發(fā)展的必備品質(zhì)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如我們所知,都是在“歡迎投稿”的邀約之下,有的法學(xué)刊物壓根就不發(fā)法學(xué)本科生的文章,而有的法學(xué)刊物是原則上不發(fā)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作者的文章。壓根不發(fā)本科生的文章或原則上不發(fā)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者的文章,盡管是以來稿很多,而好稿子也很多為“堂皇”理由,但骨子里的原因則是: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者能寫出什么像樣的文章?即對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者的文章水平懷有一種“先天性歧視”。其實,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者中,仍有“后起之秀”和“青年才俊”,而在博士生學(xué)歷者中照樣有“江郎才盡”者,乃至本來就是“博士不博”者。那么,作者的職稱身份呢?對應(yīng)著有的法學(xué)刊物原則上不發(fā)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者的法學(xué)文章,有的法學(xué)刊物原則上不發(fā)講師以下職稱者的法學(xué)文章。其實,在講師以下職稱者中,也不乏“后起之秀”和“青年才俊”,而副教授以上職稱者中也不乏“專家不專”者。這是職稱較低作者投稿,或曰從事法學(xué)這門學(xué)問所遭受的“冷遇”。其實,前面所說的“冷遇”,不僅是指文章不可能被發(fā)表,甚至指的是文章根本不可能被審閱,即如有人所描述的,“拆開之,墻角之”。有的法學(xué)刊物盡管也刊發(fā)碩士生以下學(xué)歷者或講師以下職稱者的文章,但有時卻通過對他們收取版面費來體現(xiàn)他們與那些博士以上學(xué)歷者或副高以上職稱者的“身份之別”。
有的法學(xué)刊物的用稿條件使得單純博士學(xué)歷者或副高職稱者在正高職稱作者面前也被以版面費而降了一格。于是,學(xué)歷較低和職稱較低的作者一邊埋怨這種“區(qū)別對待”的不公平,一邊自嘆自己學(xué)歷或職稱的“先天性不足”。而埋怨和自嘆之余,大多數(shù)作者便“發(fā)奮圖強”,即抓緊提高學(xué)歷或提高職稱,因為法學(xué)領(lǐng)域發(fā)表文章的這種特殊的“身份法”是一種潛行的“強制法”,而他們又不甘心放棄他們心愛或鐘愛的法學(xué)這門學(xué)問。而實際情況是,真正講究影響的法學(xué)刊物對來稿作者是不作“身份歧視”的。再就是作者是否學(xué)術(shù)盟友的身份。事實上,作者是否學(xué)術(shù)盟友的身份也變成了極少數(shù)法學(xué)刊物對待法學(xué)來稿的一種潛規(guī)則。這里所說的學(xué)術(shù)盟友包括兩種類型:一是畢業(yè)于同門的學(xué)術(shù)盟友,甚至僅僅是校友,二是站在相同學(xué)術(shù)立場或在學(xué)術(shù)派別中屬于同一“陣營”的學(xué)術(shù)盟友。于是,學(xué)術(shù)盟友的身份便在來稿是否能被刊用的定奪中起著掂量的作用,至少是本來在可刊發(fā)可不刊發(fā)之間,學(xué)術(shù)盟友的身份就可決定著刊發(fā)。相反,本來在可發(fā)與可不發(fā)之間,非學(xué)術(shù)盟友的身份便可能將導(dǎo)致一篇來稿將“有來無回”。在學(xué)術(shù)上,“對敵”才是最好的老師。而與一種理論和學(xué)派進行爭鳴和批判本身就是對它的一種支持,即讓它引人注目地活躍在學(xué)術(shù)論壇上。[1]那么,法學(xué)刊物對來稿作者身份應(yīng)持寬容的心態(tài),特別是非屬學(xué)術(shù)盟友的“學(xué)術(shù)對敵”。最后是作者是否同事包括高校同事的身份。某較有影響的法學(xué)刊物,其聲譽一直不看好,原因是刊發(fā)本單位包括本高校同事作者的文章較多,即我們所說的“自刊率”較高。心照不宣的一個事實是,“自刊”的文章往往是穿過一種特殊的“綠色通道”,即在文章粗看還說得過去的情況下,由正副主編直接拍板,或由責(zé)任編輯“先斬后奏”。由于沒有經(jīng)過嚴格的審稿程序,“自刊”的文章可以視為沒有經(jīng)過“公平競爭”,從而沒有經(jīng)過“實力競爭”。那么,至少在“程序”上,自刊文章的質(zhì)量是值得拷問的。于是,“自刊”文章可以視為擠占了至少有著“程序”體現(xiàn)的高質(zhì)文章的刊發(fā)機會,即與讀者見面并引起法學(xué)共鳴和爭鳴的機會。“自刊率”較高違背了“學(xué)術(shù)市場”的“公平競爭”與“實力競爭”法則。“因身份而異”使得有的法學(xué)刊物在相當程度上將法學(xué)學(xué)術(shù)的平臺變成了一種“身份割據(jù)”,甚至變成了正副主編作“私下交易”的一種“策略”,其對法學(xué)發(fā)展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這些法學(xué)刊物應(yīng)胸懷法學(xué)發(fā)展的大局而寬容來稿作者的身份,以讓不具有相應(yīng)“身份”者也能夠暢通地發(fā)出自己的學(xué)術(shù)聲音,從而有助于法學(xué)的發(fā)展與繁榮。在法學(xué)刊物對來稿作者的“身份寬容”中,“不薄新人”是一種最有力和最集中的體現(xiàn)。
二、法學(xué)刊物應(yīng)寬容學(xué)術(shù)的“片面深刻”
幾乎所有的法學(xué)刊物都反感那種從概念到特征等面面俱到的法學(xué)來稿,因為這樣的法學(xué)來稿被視為采用了“教科書體例”,而“教科書體例”的法學(xué)來稿在讓人“厭讀”的同時又被視為“熱剩飯”,即難見新觀點或難見觀點創(chuàng)新。那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法學(xué)刊物都想采用“片面深刻”的法學(xué)來稿,因為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深刻的片面突破全面,因而在舊的全面面前,它是叛逆,是反動。但正是這種片面引起的深刻,瓦解了人類的思維定勢,促進了思想的成長。而思想總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個水平上,片面的深刻必然否定片面本身,無數(shù)個深刻片面組成了一個新的全面。這樣,在人類思想史上就呈現(xiàn)一個全面———片面———全面的否定之否定的發(fā)展軌跡。而恰恰是這種片面,代表了一種否定性的力量,一種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力量,成為人類思想發(fā)展的偉大動力。”[2]可是,有的法學(xué)刊物卻“出爾反爾”。有的法學(xué)刊物在不予采用的回復(fù)中稱作者這個概念沒交代,那個問題沒談到,即反而由“片面深刻”又走向了“面面俱到”。而在回復(fù)意見中所稱的那些沒交代和沒談到的,有的根本不影響作者對本論題的集中論述,有的竟然是“業(yè)內(nèi)人士”“常識性”的東西。于是,被拒絕用稿的作者在郁悶之中又疑慮著:審稿人或責(zé)任編輯或正副主編的專業(yè)水平到底是否“適格”?而所謂專家意見到底是否“專家不專”?其實,在大力提倡法學(xué)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當下,法學(xué)刊物更不應(yīng)該口頭上反對“面面俱到”而在實際做法上卻又出于“面面俱到”而拒用確實有創(chuàng)見的學(xué)來稿,至于來稿的創(chuàng)見大小則另當別論。其實,“面面俱到”難以達致“片面深刻”的道理很簡單,正如對一個平面施力:同樣的施力,如果受力面積大,則壓強就小;如果受力面積小,則壓強就大。
法學(xué)刊物苛求“面面俱到”有時或時常會“流失”真正有創(chuàng)見的法學(xué)來稿。筆者的一位學(xué)界同仁的一篇文章被某法學(xué)刊物以“論述不全面”而拒稿,結(jié)果這篇文章被發(fā)表在比該法學(xué)刊物更優(yōu)的法學(xué)刊物上,并且被《新華文摘》摘錄。筆者的另一位學(xué)界同仁的一篇文章被某一屬于“二級權(quán)威”的法學(xué)刊物以類似的理由予以拒稿,結(jié)果這篇文章在被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轉(zhuǎn)投之后,竟然發(fā)表在權(quán)威性和學(xué)術(shù)性都被大家公認的《法學(xué)研究》上。而筆者經(jīng)歷的一個投稿“遭遇”是,筆者的一篇關(guān)于“類型化思維”的文章投往某一較有影響的法學(xué)刊物,審稿人對文章的創(chuàng)見性給予了較為充分的肯定,但編輯部“集體議決”或“圓桌會審”時僅以此稿“沒有進一步交代另一個問題”而最終“宣判”此稿“死刑”。一番郁悶之后,筆者將此稿予以轉(zhuǎn)投,結(jié)果發(fā)表在更有影響的另一法學(xué)刊物即《法律科學(xué)》上,并且被中國人民大學(xué)書報資料中心的《刑事法學(xué)》予以全文轉(zhuǎn)載。對于諸如此類的投稿“遭遇”,我們不能以“因禍得福”或“塞翁失馬”來作事后性的心理平衡,因為諸如此類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說明了法學(xué)刊物的審用稿機制還是存在著相當?shù)膯栴},而這些問題的存在已經(jīng)拖延了有創(chuàng)見的法學(xué)文章本應(yīng)能夠及早發(fā)揮對法學(xué)發(fā)展的影響。需要強調(diào)的是,有過類似“遭遇”的作者們并不會沉浸在“因禍得福”或“塞翁失馬”的“沾沾自喜”甚或“暗自竊喜”之中,因為最終出現(xiàn)的投稿結(jié)果已使他們自信和確信:他們的水平能夠使他們的文章登上法學(xué)刊物的“大雅之堂”,從而在一個更高的平臺上擴大他們的學(xué)術(shù)影響。包括筆者在內(nèi)的學(xué)界同仁的類似投稿“遭遇”牽扯到法學(xué)刊物如何在法學(xué)發(fā)展中對待法學(xué)創(chuàng)新問題。就刑法學(xué)的發(fā)展現(xiàn)狀,有學(xué)者指出:“相對于大陸法系國家上百年的刑法學(xué)理論傳統(tǒng),我國刑法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積累是薄弱的。
當前,我國刑法學(xué)正處在一個轉(zhuǎn)折點上:既有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難以適應(yīng)理論發(fā)展與法治建設(shè)的需要。如何完成我國刑法學(xué)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是擺在我國刑法學(xué)者面前的迫切任務(wù)。我們再也不能滿足于刑法的理論現(xiàn)狀,應(yīng)當以一種改革的精神推動我國刑法學(xué)的發(fā)展,使其適應(yīng)新時代法治建設(shè)與發(fā)展的需要。”[3]其言無疑是在強調(diào)著中國刑法學(xué)亟待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又是何其艱難!那么,法學(xué)刊物在這種勢在必行的法學(xué)創(chuàng)新中,對于那些雖只是提出問題,但已經(jīng)事關(guān)基本理論的創(chuàng)新的法學(xué)來稿,應(yīng)盡量慎重對待,而非隨意或草率地棄之一邊,特別是業(yè)內(nèi)審稿專家給予充分肯定的法學(xué)來稿,因為雖然這樣的來稿論述沒有“面面俱到”,但“提出問題就等于解決了問題的一半”,而愛因斯坦則更指出:“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shù)學(xué)上或?qū)嶒炆系臋C能而已;而提出新問題、新理論,從新的角度去看舊問題,則需要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xué)的真正進步。”而所謂慎重對待,可以是讓作者再予以補充論述,或有待于他人將遺漏的方面作為新的問題予以提出和解答,以將問題的討論“傳承”下去。“專家不專”并非指所有的審稿專家,那么,法學(xué)來稿的“片面深刻”問題還牽扯法學(xué)刊物如何對待審稿專家的審稿意見。
就筆者所知,大部分法學(xué)刊物是充分重視刊外專家的審稿意見,也就是說,一篇法學(xué)來稿如果通過專家審稿,基本上就能夠被刊用。但也有極少數(shù)法學(xué)刊物,編輯部成員的“集體議決”或“圓桌會審”使得專家的“審稿通過意見”只構(gòu)成了一篇法學(xué)來稿能夠被錄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便使得專家審稿意見被予以不當?shù)摹暗凸馈保瑥亩埂澳涿麑徃濉贝蛄撕艽蟮恼劭邸?jù)說某個較有影響的法學(xué)刊物,其編輯部成員在“集體議決”或“圓桌會審”時,只要有個別人挑出一個不輕不重的“毛病”,則通過專家評審的,甚至得到專家充分肯定的一篇文章也就被判了“死刑”。為體現(xiàn)對法學(xué)來稿中的“片面深刻”的尊重,法學(xué)刊物似乎應(yīng)建立一種特殊的答辯機制。在現(xiàn)行法學(xué)刊物的運作中,審稿專家或正副主編,甚或責(zé)任編輯對一篇法學(xué)來稿所指出的任何一個“缺陷”或“不足”,似乎指出者的認識或想法就是無可置疑地正確,而被指出者即來稿的作者必錯無疑。其實,指出者包括審稿專家未必就是正確的,而被指出者即來稿的作者未必就是錯誤的。
因此,對于指出者和被指出者之間那些似是而非的分歧,應(yīng)允許被指出者即來稿作者作出必要的、充分的答辯即作出解釋、說明。這種答辯即解釋、說明,目的在于求得指出者特別是審稿人與來稿作者之間的一種共識,而這種共識可以再用來充實文章的論述,即便是采用注釋的方式。臺灣的學(xué)術(shù)刊物包括法學(xué)刊物有著不同于大陸法學(xué)刊物的做法,即它們會將作者與編者的意見分歧交代在注釋中。而它們對來稿,無論是否最終刊用,只要是審稿方有不同認識或看法的,他們都會詳盡而中肯地列出來以供作者斟酌,這樣就讓作者與審稿方有了進一步的溝通與交流,同時也是作者可以進行“答辯”乃至“申辯”的機會。相對于大陸有的法學(xué)刊物來那么一句“審稿未獲通過”,要讓作者心理溫暖得多和安慰得多。在筆者看來,所謂“來稿太多”不是“含糊拒稿”的理由。當然,若雙方之間達不成共識,指出方仍然享有拒刊來稿的“權(quán)力”。至于答辯的進行,可以是雙方采取電話或電子郵件等切實可行的方式,也可以以責(zé)任編輯為媒介“中轉(zhuǎn)”雙方的認識或想法。不過,這里要交代的是,就審稿意見的“答辯制”并不與“匿名審稿”相沖突,因為初審意見已經(jīng)形成。筆者有過得不到“答辯”或“申辯”的經(jīng)歷和感受。下面就是一例:國人整體上沒有信仰,是我們自認的事實。有感于我們的刑罰執(zhí)行即行刑長期以來停留于政治說教,從預(yù)防再犯的宗旨出發(fā),筆者在兩年前就思考過一個甚至是讓人感到滑稽的問題即“行刑的宗教介入”,最后形成《論行刑的宗教介入》一文。此文的主題思想是,行刑的宗教介入是指在行刑過程中對罪犯施以宗教教化,通過對其犯罪人格進行救贖和培養(yǎng)倫理自律以預(yù)防其再犯;行刑的宗教介入通過謙卑和大愛來對罪犯進行著靈魂救贖與倫理自律的培養(yǎng);行刑的宗教介入以神職人員與罪犯之間進行宗教信條的“交通”為現(xiàn)實體現(xiàn);行刑的宗教介入促進著罪犯的自我實現(xiàn)并修復(fù)著罪犯的道德判斷能力,最終助推著法治文明和整個社會文明的發(fā)展進步;行刑的宗教介入所走向的是正義行刑。在此文向某較有影響的法學(xué)刊物投稿后,該法學(xué)刊物不予刊用的理由即審稿人的意見是:行刑的宗教介入與法律從宗教中分離出來的歷史發(fā)展正好相悖。如果說真是一種相悖的話,則“行刑的宗教介入”,不謙虛地說,也算是一種“片面深刻”吧。遺憾的是,該法學(xué)刊物沒有給予筆者一個答辯甚或申辯的機會,而筆者已經(jīng)準備好的答辯或申辯是:行刑的宗教介入將開啟行刑事業(yè)發(fā)展的一個新方向。但是,我們首先要遇到并力爭要克服的是觀念問題,因為在我們的主流意識中,宗教是麻痹乃至愚弄人的東西,而行刑則是積極意義上的“改造”人的事業(yè)。但是,宗教與人類社會發(fā)展相始終的事實說明著宗教之于人類社會發(fā)展有其可資利用的一面。但要強調(diào)的兩點是:首先,行刑的宗教介入并非整個刑事法治的宗教化;再者,法律與宗教的分離可以看成是“形”的分離,但就“神”而言,兩者在某些方面或領(lǐng)域還會超越歷史地存在著“一絲一縷”的聯(lián)系,畢竟宗教曾經(jīng)是法律的母體。我們的社會問題之所以越來越多,是否與“分離”越來越多有關(guān),包括分離歷史、分離傳統(tǒng)和分離“母體”?筆者已經(jīng)準備好的答辯或申辯內(nèi)容已經(jīng)大部分出現(xiàn)在投稿的正文之中。《論行刑的宗教介入》最終得以在《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法學(xué)版》2012年第5期上與讀者見面。這篇文章讓筆者產(chǎn)生很深感慨的不是“發(fā)表難”,而是我們對宗教信仰問題的“本能性”反應(yīng),正如伯爾曼認為,“整體性危機”的兩個征兆是法律信任的喪失和宗教信仰的喪失。[4]而“雖然伯氏所指向的對象是‘西方人’,但是從其論述中,映證到我們‘東方人’身上,處處都能感同身受。欠缺了西方社會濃郁的宗教信仰的支撐,我們‘東方人’所處的現(xiàn)實危機不是更弱而是更強。遺憾的是,我們以社會性質(zhì)的對比而悄悄地把這種‘危機’給‘優(yōu)越’掉了。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是不是潛伏的最大‘危機’?”[5]下面是筆者不能行使“答辯權(quán)”或“申辯權(quán)”的另一個例子。筆者最近向某法學(xué)刊物投寄了一篇關(guān)于“刑法立法正當性”的文章。此文的主題思想是:保護人們的基本需要、吻合共同的社會心理、蘊含“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應(yīng)體現(xiàn)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標準,應(yīng)被看成是刑法立法正當性的若干層面,且此若干層面之間存在著相互說明和層層遞進的關(guān)系。而正是在此若干層面的相互說明和層層遞進之中,刑法立法才獲得了穩(wěn)固的正當性根基。但該法學(xué)刊物以審稿人的意見,即所謂作者“偏法益保護而棄人權(quán)保障”而否定了此文的寫作價值。筆者向責(zé)任編輯作了如下答辯或申辯:從保護人們的基本需要、吻合共同的社會心理、蘊含“最低限度的道德”和體現(xiàn)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標準中,我們可以肯定刑法立法的正當性根基是在“外顯”乃至“彰顯”著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但不能由此得出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被淡化乃至丟棄的結(jié)論,因為人們的基本需要包含著每個公民個體包括潛在犯罪人與已然犯罪人的需要,共同的社會心理匯聚了每個公民個體包括潛在犯罪人與已然犯罪人的心理,“最低限度的道德”融合了每個公民個體包括潛在犯罪人與已然犯罪人的道德,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標準又能夠使得每個公民個體包括潛在犯罪人的一般危害行為被排斥在犯罪圈之外,正如現(xiàn)行刑法第13條“但書”所昭示的那樣。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又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可以印證筆者的前述理解。那么在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與人權(quán)保障功能的關(guān)系。我們以往是將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與人權(quán)保障功能相并列的,現(xiàn)在看來,這種并列是有問題的,因為犯罪(嫌疑)人的人權(quán)也是一種法律應(yīng)予保護的利益即所謂法益。那么,我們應(yīng)該用上位概念與下位概念的關(guān)系來處理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與人權(quán)保障功能的關(guān)系,而在法益保護功能之下與人權(quán)保障功能相并列的是保護(維持)秩序功能(即以往常說的保護社會功能)。這樣,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便包含著或蘊含著人權(quán)保障功能。或許正因如此,在刑法立法階段較多得到體現(xiàn)的或得到“外顯”乃至“彰顯”的,是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而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則似乎被“淡出”了。實際上,我們應(yīng)動態(tài)地把握刑法人權(quán)保障功能的體現(xiàn),因為刑法實踐是一個從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再到刑罰執(zhí)行的動態(tài)過程。而在筆者看來,在刑法立法階段,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因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的“外顯”或“籠罩”而呈“隱性”,但從刑法司法階段往后,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將變得逐漸“顯性”或“淡入”,而其“顯性”或“淡入”又集中體現(xiàn)在罪刑法定原則、罪刑均衡原則(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和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的司法貫徹之中。而筆者的前述理解,可以得到刑法“首先”是“善良人的大憲章”,“然后”才是“犯罪人的大憲章”的印證。
因此,本文在探討刑法立法的正當性根基問題時不能無視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而事實上也沒有無視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刑法的人權(quán)保障功能在刑法立法正當性根基的討論中以何種方式得到展示,則取決于論題的需要,而論題的需要又是刑法立法在刑法實踐中的特殊階段性所決定的。但在作出前述答辯或申辯之后,審稿人仍然不為所動,那么筆者便只能無語了,因為審稿人在刑法功能的二元論中已經(jīng)不能自拔,而“極端地說,所有的二元論其實都是一元論,折中有時恐怕比只執(zhí)一詞更難。墻沒騎成反栽倒在一邊的墻角。諸多二元立場表面看來折中無偏倚,實際上均有所側(cè)重。”[6]在筆者看來,那種“和稀泥”式的“二元論”或“折中論”實質(zhì)上是沒有自己的學(xué)術(shù)立場,當然也就沒有自己的觀點。將保護社會和保障人權(quán)二者同時視為刑法的等重或“等量”價值的“二元論”或“折中論”也是如此。而如果“和稀泥”式的“二元論”或“折中論”是出于暗中討好學(xué)術(shù)對立的雙方,則是連最起碼的學(xué)術(shù)責(zé)任感都喪失了。提出法學(xué)刊物運作中用稿方與投稿方的“答辯制”似乎滑稽可笑,但其實并不可笑,因為投稿方需要文章被發(fā),而用稿方需要有文章可發(fā),雙方之間可以看成是一種特殊的買賣關(guān)系,即用稿方是“買方市場”而投稿方是“賣房市場”,只不過此買賣關(guān)系圍繞的是文章的質(zhì)量而已。那么,用稿方與投稿方之間的答辯或申辯權(quán)且看成是一種“討價還價”,是公平合理的“學(xué)術(shù)交易”。公平合理可以看成是法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理念,那么當用稿方與投稿方之間就學(xué)術(shù)問題的答辯或申辯也能夠體現(xiàn)公平合理理念的時候,又有什么值得可笑的呢?而作為法學(xué)學(xué)術(shù)平臺的法學(xué)刊物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如果是法學(xué)刊物覺得用稿方與投稿方的“答辯制”滑稽可笑,那只能意味著法學(xué)刊物在一種“盛氣凌人”之中而將公平合理的法學(xué)學(xué)術(shù)市場變成了“買方市場”。更為甚者,如果我們承認確實存在著“專家不專”的現(xiàn)象,則不僅實行法學(xué)文章投稿“答辯制”具有合理性,甚至實行兩名以上最好是三名專家匿名審稿制也具有合理性,而特別是三名專家匿名審稿制,其能夠發(fā)揮幾近于訴訟“合議制”的功效。可以這么認為,答辯制與多名專家匿名審稿制相結(jié)合,能夠更好地實現(xiàn)法學(xué)文章發(fā)表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答辯制與多名專家審稿制相結(jié)合的發(fā)表機制,意味著法學(xué)刊物能夠盡量是法學(xué)創(chuàng)作者的發(fā)聲平臺,而盡量避免法學(xué)刊物就是刊物主辦者包括或特別是正副主編的聲音壟斷。
三、法學(xué)刊物應(yīng)寬容來稿文風(fēng)的“民主自由”
在社會交往中,聽到一位法學(xué)同仁告知這么一件事:他的法學(xué)投稿僅因某法學(xué)刊物的主編覺得文字“花哨”而被拒用,而事后他通過某種途徑得知審稿人和責(zé)任編輯對他的法學(xué)投稿中的觀點及論證予以很大肯定。于是,這里便牽扯法學(xué)刊物在錄用法學(xué)文章時如何對待法學(xué)文章的表達風(fēng)格即文風(fēng)問題。法學(xué)文章可以看成是用法學(xué)概念演繹而成的一種作品。法學(xué)文章的論述應(yīng)是專業(yè)語言的地道表達和準確表達,這應(yīng)該是我們的共識。那么,一篇法學(xué)文章是一板正經(jīng)的法言法語的通篇連貫,還是可有特定風(fēng)格的個性展現(xiàn)?或曰可否允許一種文風(fēng)上的“民主自由”?當下的中國法學(xué)研究可謂陣營龐大,而在此龐大的陣營中,可以說每個“參與者”即每個從事法學(xué)研究的人都會有著自己的文風(fēng),特別是那些非法學(xué)本科背景的“參與者”即法學(xué)研究者。這樣,原來是中文背景的人,其法學(xué)文章可能就會禁不住呈現(xiàn)出詩意化的文風(fēng)色彩,或曰禁不住散發(fā)出一股文學(xué)味;原來是哲學(xué)背景的人,其法學(xué)文章可能就會禁不住呈現(xiàn)出思辨性的文風(fēng)色彩,或曰禁不住散發(fā)出一股哲學(xué)味;而原來是歷史學(xué)背景的人,其法學(xué)文章可能就禁不住呈現(xiàn)出近乎老態(tài)龍鐘的文風(fēng)色彩,或曰禁不住散發(fā)出一股史學(xué)味。那么,在不影響準確達意,且簡練流暢的前提下,法學(xué)刊物應(yīng)寬容特定學(xué)科背景的人在法學(xué)文章中的特定文風(fēng)。而如果是某種“學(xué)科味道”太濃以致于影響別人特別是審稿人和編輯們對來稿的法學(xué)嗅覺,則某種“學(xué)科味道”就要收斂或予以“稀釋”。否則,對此類法學(xué)來稿不予錄用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文章畢竟要讓人看懂,且首先要讓編輯們和審稿人看懂。
在當下的法學(xué)文章投稿中,因文風(fēng)不合法學(xué)刊物的口味而被拒稿的情況是有的。只要不是太過,法學(xué)刊物不應(yīng)因法學(xué)文章的文風(fēng)個性而拒稿,以使得確實有創(chuàng)建的法學(xué)文章能夠在法學(xué)研究的百花園中綻放其彩,發(fā)出其聲。如果更進一步地看問題,當一篇法學(xué)文章從頭至尾都是法言法語在一種“莊重嚴肅”之中紛至沓來,那種閱讀的沉悶感或許多少會影響閱讀者對文章內(nèi)容的接納程度。有人在評價張五常的經(jīng)濟學(xué)著作時指出:“張五常教授善于把深奧的經(jīng)濟學(xué)原理和方法,用散文般優(yōu)美的語言進行表述,而且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也是信手拈來,往往能夠通過大家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揭示出一個深刻的經(jīng)濟學(xué)原理。”[7]而其對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的評價則是:“在這本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的‘差序格局’這一概念,極為深刻地解釋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文化原因,盡管費老在文中對‘差序格局’并沒有進行多少學(xué)理上的論證,而更多的是一種散文性質(zhì)的描述,但我們卻能夠發(fā)現(xiàn)這個概念背后天才般的想象力。”[7]80-81那么,在筆者看來,即便是專業(yè)類的著述包括法學(xué)論文,只要是有利于其表述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則作者采取一種輕松、活潑、自然的文風(fēng)便是未嘗不可的,甚至是應(yīng)該的。而如果是這樣看問題,則法學(xué)論文在語言風(fēng)格上有些許詩意,或散發(fā)出些許散文般的氣息,不僅是可以的,甚至是應(yīng)該的。易言之,法學(xué)論文文風(fēng)的文學(xué)化不僅是可以的,甚至是應(yīng)該的,只要其不“過度”,甚或只要其不變成一篇關(guān)于文學(xué)方面的論文。而如果我們的法學(xué)刊物能夠甚或應(yīng)該接受適度的文風(fēng)文學(xué)化的法學(xué)論文,則采用比喻、排比等修辭,甚至巧用大家熟知的古今詩詞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前述“手法”或許將使得一篇法學(xué)論文不是在自言自語,而是“娓娓道來”。
國內(nèi)法學(xué)界,諸如蘇力等學(xué)者的法學(xué)著述包括法學(xué)論文,大家都覺得具有相當?shù)摹翱勺x性”,甚至是“享受性”,這與其輕松、活潑、自然的文風(fēng)是直接相關(guān)的。而如果我們回眸歷史,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其充滿詩意的,甚至是帶有“革命激情”的文風(fēng)不僅絲毫未損其關(guān)于法的思想觀念的“本真表達”,而且讓當時和后世的讀者們產(chǎn)生一種“喜聞樂見”的感受。法布爾是法國的昆蟲學(xué)家和作家,他之所以被達爾文贊揚為“難以效法的觀察家”,乃是因為他的《昆蟲世界》被視為“科學(xué)與詩的完美結(jié)合”。我們是否也可以從中獲得對待法學(xué)文章的文風(fēng)問題的啟發(fā)呢?即法學(xué)文章可否有一點“詩意”乃至一點“激情”呢?好的內(nèi)容要有好的形式為之服務(wù)。文風(fēng)可以看成是法學(xué)論文的一種形式,而思想觀點可以看成是法學(xué)論文的內(nèi)容。那么,只要有益于法學(xué)論文內(nèi)容的表達,即只要有益于法學(xué)論文的內(nèi)容能夠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并且首先是被責(zé)任編輯和審稿人理解和接受,作為形式的法學(xué)論文的文風(fēng)可以各放異彩,包括文學(xué)化的“手法”。那么,如果我們是在一篇文章中討論犯罪論體系問題,則作者在交代犯罪論體系的國內(nèi)理論流變及當下態(tài)勢時可不妨采用如下表述: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路走來,中國刑法學(xué)的犯罪論大致分為如下兩個階段:首先是對前蘇聯(lián)的犯罪理論“情有獨衷”階段,其集中體現(xiàn)是在前蘇聯(lián)的犯罪概念和犯罪構(gòu)成理論的基本框架之下“同心同德”地縫縫補補;接著是對前蘇聯(lián)的犯罪論“依依不舍”和對他國犯罪論“移情別戀”的對峙階段。其中,對他國犯罪論的“移情別戀”又分為對英美法系的犯罪論和對大陸法系犯罪論的“各有所愛”,且前者集中體現(xiàn)為對“雙層式”犯罪論體系的簡便易行相當好感,而后者則體現(xiàn)為對“三元遞進式”犯罪成立理論體系“愛莫能耐”。于是,犯罪論體系的“三國鼎立”便構(gòu)成了中國刑法學(xué)犯罪論的當下格局,且來自前蘇聯(lián)的“四要件整合式體系”與來自大陸法系的“三元遞進式體系”經(jīng)常發(fā)生“邊界沖突”,而來自英美法系的“犯罪本體與排除合法辯護夾心式體系”則保持低調(diào)的“中立”。遙望“四要件整合式體系”當初的“獨霸天下”,我們喜憂難辯地迎來了中國刑法理論的“大變天”。筆者覺得,前面的這段表述或許因恰到好處地使用“比喻”手法而使得問題顯得形象可感的同時,又給人一種輕松愉悅的“閱讀感”。那么,當我們在一篇文章中討論刑法學(xué)中更為具體的一種罪過形式即過于自信的過失時,作者不妨可用一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來觀照其“輕信危害結(jié)果可以避免或不致發(fā)生”的意志因素,從而使得閱讀者包括責(zé)任編輯和審稿人更加能夠在一種形象可感之中,理解和接受作者本人對過于自信的過失這種罪過形式所持的看法或認識。所謂“膾炙人口”,不僅是我們對文學(xué)作品的要求,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我們對法學(xué)作品的要求。筆者的一位學(xué)界同仁曾經(jīng)告訴筆者一件事:他的一篇文章被某一較有影響的法學(xué)刊物刊發(fā)了,但他的文章被該刊物行使“刪改權(quán)”之后已經(jīng)變得有點“面目全非”,而刪改的理由則是關(guān)于文風(fēng)方面的。該同仁痛心地告訴我:被刪改的部分包括他自覺是最出彩的部分,而最出彩的部分又包括文字表達方面,而該部分的刪改甚至損傷了他原本的觀點,以致于該法學(xué)刊物本身在他論述的問題上已經(jīng)不經(jīng)意地走向了“自相矛盾”。
由于該法學(xué)刊物的“身份”即“二級權(quán)威”,刪改之痛也只有忍了和認了。在筆者看來,如果因為文風(fēng)或表述問題需要完善,最好是讓作者本人刪改,因為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文章的“本意”。實際上,一篇法學(xué)文章的文風(fēng)相當于一種“調(diào)味”,或相當于一種“門面”,其能夠激起包括責(zé)任編輯和審稿人在內(nèi)的閱讀者的閱讀欲,或令其產(chǎn)生一種“先入為主”的心理效果,是符合常人心理的。這就難怪有的作者在將一篇法學(xué)文章投寄之前反復(fù)進行文字打磨,而其文字打磨包括文風(fēng)方面即文字表達方面。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禁不住“張揚”出作者本人的較強個性,但恰到好處的文風(fēng)只會增加法學(xué)投稿被采用的幾率,但前提是法學(xué)刊物本身對待法學(xué)來稿的文風(fēng)問題要有一個穩(wěn)妥乃至有點“克制”的態(tài)度,一切都應(yīng)服從于有見地的法學(xué)文章應(yīng)該早點與廣大讀者們見面,以引起法學(xué)共鳴和爭鳴,從而助益于法學(xué)的向前發(fā)展。
四、結(jié)語
寬容作者的身份、寬容學(xué)術(shù)的“片面深刻”、寬容作品文風(fēng)的“民主自由”,都是法學(xué)刊物寬容性的切實體現(xiàn)。在問題的實質(zhì)上,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就是法學(xué)刊物對法學(xué)發(fā)展的責(zé)任性,而其責(zé)任性又體現(xiàn)為克服學(xué)術(shù)心胸的狹隘性與其他方面的自私自利性。如果把法學(xué)刊物能夠決定一篇文章發(fā)與不發(fā)看成是一種“權(quán)力”,則作者所享有的僅僅是一種希望文章得到發(fā)表的“權(quán)利”。如此,則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便意味著“權(quán)力”對“權(quán)利”的謙讓,意味著法學(xué)作品擁有更多的發(fā)表機會。那么,只有提倡寬容性,法學(xué)刊物才能營造一種生動活潑的學(xué)術(shù)局面,才能使得法學(xué)的園地更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由法學(xué)刊物在法學(xué)活動中的地位所決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沒有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便沒有法學(xué)本身的寬容性;而沒有法學(xué)本身的寬容性,則法本身的寬容性以及法治的寬容性將受到“抑郁”。而反過來,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是對法本身的寬容性經(jīng)由法學(xué)的寬容性的一種傳承。我們也可這樣看問題: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是法學(xué)刊物對法學(xué)創(chuàng)作者學(xué)術(shù)勞動的一種尊重。在這種尊重中,法學(xué)學(xué)者們?nèi)菀讘汛б环N“榮耀感”和“成就感”,而此“榮耀感”和“成就感”會更加激勵其投身到法學(xué)研究的事業(yè)中,從而帶來法學(xué)的發(fā)展與繁榮。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對于法學(xué)創(chuàng)新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當然,提倡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與法學(xué)刊物從各個方面提高用稿要求并不當然矛盾,因為實際上,法學(xué)刊物不斷提高用稿要求是法學(xué)不斷發(fā)展的一種標志或征象。但提倡法學(xué)刊物的寬容性與提高法學(xué)刊物的用稿要求有著共同的目標,那就是促進法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與繁榮。在筆者所在法學(xué)院的資料室里,偶見同仁手捧一法學(xué)刊物一邊搖頭一邊感慨:“怎么會發(fā)這樣的濫文章?”與之交流后,筆者方得知:除了文章確實有點濫,還因為該法學(xué)刊物較有影響。于是,筆者最后要強調(diào)的是:“辦刊特色”或“用稿口味”不是法學(xué)刊物丟掉寬容性的理由,而“投我所好”應(yīng)當受到一定的節(jié)制。當然,提倡寬容性又并不意味著法學(xué)刊物要降低用稿質(zhì)量。
作者:馬榮春單位:揚州大學(xué)法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