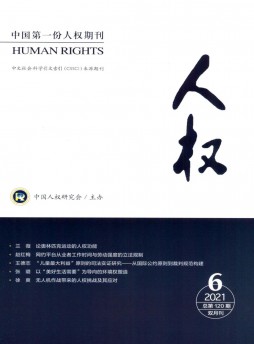人權(quán)哲學思想的價值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權(quán)哲學思想的價值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中華文化沒有內(nèi)生原創(chuàng)性的“人權(quán)”概念,近代中國人權(quán)思想的產(chǎn)生發(fā)展受到西方的個人主義的人權(quán),集體主義的民族權(quán)和階級權(quán)等觀念的影響,又由于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受到同樣源自西方的國家主權(quán)觀念的制約。中國傳統(tǒng)哲學土壤和近代歷史實踐,使中國人權(quán)哲學擁有獨具特色的中國式的人權(quán)價值觀。近代中國人權(quán)哲學開辟了中國哲學的新方向,人權(quán)實現(xiàn)的中國之路建立在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哲學觀之上。
關(guān)鍵詞:
人權(quán)哲學;近代中國哲學;中國特色
引言
權(quán)利,這個詞在中國古代漢語中,被解釋為“權(quán)勢及貨財”。延續(xù)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傳統(tǒng)思想,宣揚的是君權(quán)、父權(quán)、夫權(quán),而漢字的“人”或“民”未和漢字的“權(quán)”相搭配使用,也沒有什么兒童權(quán)、女權(quán)、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等概念。“權(quán)利”和“人權(quán)”的概念,是從西方傳入的外來詞匯本文主要分析1840年以后,受到西方哲學的重大影響,具有歷史傳承和開疆拓荒雙重任務的近代中國哲學思想之中的人權(quán)思想的內(nèi)容和邏輯,探究中國人權(quán)哲學,在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存在和價值,目的在于探討中國人權(quán)哲學對世界人權(quán)哲學理論的應有貢獻。
1“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人權(quán)概念的肇始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開始被瓜分肢解,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中華“老大帝國”被迫再次向西方文明(這一次是歐美,而非印度),敞開懷抱。“權(quán)利”一詞最早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在中國正式出現(xiàn),源自于1860年代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美國人惠頓的著作《萬國公法》,這個中文譯本是東亞世界的第一本國際法學書籍[1]。丁韙良還翻譯了《公法便覽》《公法會通》等大批國際法書籍,其中使用了“邦國之權(quán)利出于義理”,“各國之通例,既由其本有之權(quán)利而推……”,“均有不可奪之權(quán)利”,“論定邦國本有之權(quán)利”等有關(guān)現(xiàn)代意義上的權(quán)利的說法①。可以說,在19世紀中后期,對于“權(quán)利”,中國人是從認識國家權(quán)利而非個人權(quán)利開始的,在中國,“權(quán)利”概念是伴隨西方的國際法概念引入并傳播的。早期介紹西方思想影響最大的學者當屬翻譯家嚴復,1896年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曾用“權(quán)利”一詞表達英文中的rights。達爾文進化論震驚中國知識界,民族競爭、優(yōu)勝劣汰的救亡意識覺醒了。嚴復還翻譯大量西方啟蒙思想家的經(jīng)典,如孟德斯鳩《法意》、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密爾的《群己權(quán)界論》(OnLiberty)等,意欲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嚴復不是哲學家,介紹的哲學著作不多。1896年,清末重臣洋務派領(lǐng)袖李鴻章訪問美國,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抨擊美國1892年排華法案。李鴻章自詡“一名國際主義者”,抱怨清國僑民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quán)利,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他說:“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fā)活力,而競爭既適用于商品也適用于勞動力。”對于當時的美國,他質(zhì)問道:“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xiàn)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2]維新派領(lǐng)袖康有為承襲前朝大儒董仲舒、朱熹手法,托孔孟經(jīng)典,闡發(fā)自己學說,大力鼓吹進化主義、民權(quán)主義,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思想更新的維新派領(lǐng)袖梁啟超還看到了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衰落,對于西方政治哲學,接受其個人主義,而反對剛興起的國家主義,他說:“即以今日論,而國家之基礎(chǔ),豈不在個人?……故今日中國,凡百事業(yè),與其望諸國家,不如望諸社會;與其望諸社會,不如望諸個人,不獨教育為然。”[3]1919年到1920年,美國的杜威和英國的羅素兩位哲學家相繼訪問中國,這是中國人第一次聽到西方哲學的第一手介紹。不過對西方哲學,當時中國人能聽懂者少,能做深刻批評者則更少。所謂“中國近代哲學”,主要是西學東漸的引進哲學,哲學家馮友蘭總結(jié)說,這只是“西方哲學在中國”,沒有形成象禪學那樣的外國哲學中國化,因而,并沒有真正融入中國人的思想[4]。從歷史發(fā)展的實踐看,接納和消化外來思想,無疑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對來自西方的“權(quán)利”和“人權(quán)”概念的接受,要經(jīng)過不斷的鑒別、挑選、斗爭和反復的過程,才能吸收其有益的營養(yǎng)成分,做到融會貫通,提煉精華,最終成功形成本土化的人權(quán)概念。
2“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人權(quán)與國權(quán)的變奏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領(lǐng)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延續(xù)兩千年的封建帝制。1911年成立中華民國,這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在《中華民國之意義》一文中,指出“權(quán)利為人類同具之觀念,仆不能自外于人類,何能獨忘乎權(quán)利?”他在《三民主義精意》中說:“美國前總統(tǒng)林肯的主義,也有與兄弟的三民主義符合的地方……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quán)、民生主義。由是可知,美國有今日的富強,都是先哲的主義所賜。”但是,民國經(jīng)過兩次君主制的復辟,和隨后國民黨政權(quán)的專制獨裁,在這個形式上統(tǒng)一而新舊軍閥長期割據(jù)混戰(zhàn)的社會中,“民國”只剩一塊空招牌。1931年到1945年,中國人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形成了新的民族思想,認識到中國抗戰(zhàn)是世界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一部分,民族獨立是正義戰(zhàn)爭,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是中國的集體人權(quán)。林語堂在1939年說:“中國過去是一種文明,而不僅僅是一個民族”,“他們(中國人)只是一群試圖終生享樂以盡天年的蕓蕓眾生,沒有人可以對他們這種權(quán)利表示懷疑”[5]。然而,日本的入侵卻喚醒了中國人原本淡薄的民族國家意識,中華民族的心靈對于日本的殘暴政策是無法理解和完全排斥的。胡適在1942年聲言:與信奉“個人為國家而存在”和“極權(quán)黷武”的日本正相反,中國是愛好自由民主和平的國家[6]。馮友蘭在1946的文章中更是感嘆:“中國哲學不適于救中國,因為它是為了世界組織而有的哲學。”中國哲學教人“中庸勿過”,是“一個完全為了和平的哲學”。自古以來,中國人考慮問題本是從家庭和天下出發(fā),而不是從民族或者國家出發(fā)的[7]。但以國破家亡的切身之痛,中國的學生在1919年的歷史時刻,急切地喊出“外爭國權(quán),內(nèi)懲國賊”的口號,反映出中國人的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1948年12月10日,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quán)宣言》,這是人類人權(quán)事業(yè)發(fā)展中的里程碑。中華民國政府在去臺灣的幾個月之前,簽署了這個宣言。中國代表張彭春,出任《世界人權(quán)宣言》起草委員會副主席,對宣言的最終完成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將具有更為普遍性而非純粹西方的思想注入于世界人權(quán)宣言之中。”[8]例如,《宣言》的第一條是整個文件的基石和出發(fā)點,其表述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quán)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guān)系的精神相對待。”其中的“良心”一詞,就是張彭春提出加上的。他解釋說,“宣言應該既反映出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基于儒家傳統(tǒng)哲學的“民本”或“人本”的思想,張彭春說:“儒家的‘人’是全人類全部價值的基礎(chǔ)……它要求我們對他人表現(xiàn)出關(guān)心和尊重。”正如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說的那樣,“政治結(jié)合的目的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它的成員的生存和繁榮”。近代轉(zhuǎn)型的中國,封建王朝崩潰瓦解,新國家以“民國”命名,至少從形式上看,是人權(quán)觀念的勝利,歷史地證明了現(xiàn)代國家創(chuàng)立的目的在于民族保存、民權(quán)自由、民生幸福。歷史的規(guī)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中國不僅不是例外,甚至還是曾經(jīng)的引領(lǐng)者!
3科學與人權(quán)———人權(quán)是歷史的邏輯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的總司令”[9]。1915年他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運動”發(fā)起的標志。在創(chuàng)刊號致辭中,陳獨秀寫道:“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quán)并重。”陳獨秀是孔子和儒教的致命顛覆者,他說中國封建社會是“以人類不平等為原則之時代”,國故、孔教、帝制本是三位一體,儒家倫理是奴隸主義的舊道德,取而代之的新道德應是現(xiàn)代西方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影響深遠。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啟發(fā)和鼓舞,陳獨秀的思想在自由主義上并未停留很久,便轉(zhuǎn)向了社會主義。他在1920年批判馬爾薩斯的文章中說:“在財產(chǎn)權(quán)私有社會里,似乎不可因為有許多窮人生活資料不足,便馬上斷定是人口過剩,便馬上斷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資料以上增加的傾向,因為若將全社會合攏起來平均分配,不見得生活資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強盜大有余了,別人便當然不足呵。”1921年,在蘇俄的幫助下,陳獨秀和一起創(chuàng)建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誓言作“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隊”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可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呢?陳獨秀轉(zhuǎn)向馬克思主義后,在探索“自由”的道路上卻又歷盡曲折。1929年11月,因承擔大革命失敗領(lǐng)導責任以及反對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錯誤干預,在蘇聯(lián)的授意下,他被自己創(chuàng)辦的黨開除了。他反對專制集權(quán)獨裁的斯大林特色的社會主義,斷言“斯大林的官僚政權(quán)……,決不能創(chuàng)造社會主義”。“至于現(xiàn)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產(chǎn)力不能勝任領(lǐng)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若要硬說他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關(guān)心“人類自由之命運”的陳獨秀,認定正確的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必須是尊重人權(quán)自由的社會主義。20世紀40年代初,陳獨秀在他晚年的最后政治意見中指出:“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fā)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shù)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shù)特權(quán)之旗幟。”“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jīng)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中國革命的勝利實踐,符合人權(quán)發(fā)展的歷史邏輯,自由解放的正義目的終將達到,而不論道路有多漫長、曲折。
4集體人權(quán)———社會主義人權(quán)哲學
4.1民族自決權(quán)之民族獨立
1949年9月,為了籌建新中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在會議上自豪地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創(chuàng)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與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jīng)站起來了。”[10]20世紀初葉,國際上出現(xiàn)了民族自決權(quán)的概念,是和西方傳統(tǒng)的個人人權(quán)相對應的集體人權(quán)。民族自決權(quán)是指民族,作為一個集體,有權(quán)決定自己的命運,自主選擇自己的國家政治、經(jīng)濟制度等。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下,經(jīng)過艱苦斗爭獲得了民族獨立,把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變成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歷史進入新紀元,中國哲學也進入了新階段,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而形成的思想。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建立“新中國”,就要有“新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被確立為中國的教育方針,寫入具有臨時憲法地位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lǐng)》。
4.2民族自決權(quán)之人民民主
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二十八周年,寫下《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該文中,清楚的解釋了“人民”的概念: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xiàn)階段,是工人階級,農(nóng)民階級,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之下,團結(jié)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chǎn)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nèi)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jié)社等項的自由權(quán)。選舉權(quán),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nèi)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jié)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相信\擁護\選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國家的領(lǐng)導,是因為她讓人民生活幸福的承諾,和實現(xiàn)這一承諾的實際行動。人民認為這個黨是真正代表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而共產(chǎn)黨從不,也不屑于掩蓋其階級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人權(quán)哲學,為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終極目標的應有之義,就是:解放全人類。階級是階級社會對人的分類,而人權(quán)是人類永遠的追求。以為階級概念和人權(quán)概念是對立的觀念,完全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誤解。
5普世人權(quán)與近代中國人權(quán)哲學的價值———一種比較分析
5.1人權(quán)的適用范圍———所有的人都是人與西方啟蒙思想中“天賦人權(quán)”觀念不同,人僅僅基于生為人②,就享有人權(quán)的觀念,在近代中國沒有牢固地樹立起來。1948《世界人權(quán)宣言》規(guī)定了“人權(quán)”主體的無差別和非歧視原則:“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quán)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chǎn)、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qū)別。”但是,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等級社會中,“權(quán)利”觀念不發(fā)達,雖然有“人命關(guān)天”“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社會共識,但封建舊法律基本上是以不平等和殘酷鎮(zhèn)壓為特征的。近現(xiàn)代中國人權(quán)概念從西方引入,但是,“傾巢之下,安有完卵”,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急存亡之秋,爭取作為集體人權(quán)的民族權(quán),自然而然地成為比爭取個人權(quán)利更為優(yōu)先的選項。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才爭取到國家主權(quán)獨立,可惜在反封建爭人權(quán)的歷史道路上卻走了彎路。在如何保存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的問題上,出現(xiàn)了思想上的左傾的錯誤,再加上法律虛無主義思想,國家觀念中缺乏對個人人權(quán)和基本自由的保護的重視,過分強調(diào)階級的概念,有心無意地淡化國民的概念。新國家的名字中寫入“人民”二字,但是把誰歸入“人民”,卻是個嚴重的立場問題。人權(quán)的適用范圍,是應當包括所有的人。國家法律保護的范圍,是所有國民的人權(quán)。
5.2人權(quán)的法律性質(zhì)———基本權(quán)利對于“人權(quán)”中的“權(quán)”,東西方理解也有差異。在西方人權(quán)一般觀念中,由于人權(quán)固有的基礎(chǔ)性,所以認為人權(quán)是權(quán)利,不是義務,也不是責任。人的出生是被動行為,如果人權(quán)在性質(zhì)上不首先是享有權(quán)利,就根本談不上什么承擔義務和履行責任。人類的正義觀和人類的內(nèi)在需要緊密相連。每個人發(fā)自內(nèi)心地追求安全、富裕、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的渴望被認為是“享有自明的(primafa-cie)和假定的不可侵犯性”[10]。對這種需要的唯一限制是不得侵害別人的這些需要和包括了所有人利益在內(nèi)的公共利益的需要。1948年《世界人權(quán)宣言》第29條第2款規(guī)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權(quán)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確在于保證對旁人的權(quán)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并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而這一條,是整個宣言唯一的一條義務性規(guī)定。但是,中國兩千年以來,封建舊法律的形式特征都是“禮法合一”,“德主刑輔”,義務本位。在中國封建時代,“法律的唯一使命就是保障道德[12],而不是保護權(quán)利!清晚期以降西風東漸背景下形成的近代中國人權(quán)哲學,沒有獲得社會主流哲學地位。人權(quán),不僅是應被尊重和保障的“權(quán)利”,而且是應由憲法規(guī)定的權(quán)利。憲法,是現(xiàn)代國家的根本大法,規(guī)定和保障國民基本權(quán)利。而人權(quán)在性質(zhì)上,是高于一般權(quán)利的基本權(quán)利。但是,在近代的中國,從《臨時約法》開始的眾多所謂憲法,沒有任何一部被認真對待,沒有任何一部能承擔起保護基本人權(quán)的責任。
5.3人權(quán)作為一切價值的基礎(ch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總結(jié)“人權(quán)”概念的兩個基本涵意是:一,人權(quán)是基于人的權(quán)利,二,人權(quán)是人的基本權(quán)利。而要實現(xiàn)人權(quán),也至少應當回答兩個問題:一,人生活在什么樣的社會里,才能獲得幸福?二,這種人類幸福社會怎樣才能夠持久?西方人權(quán)哲學,建立在自由市場經(jīng)濟基礎(chǔ)上,更關(guān)注個人的尊嚴和現(xiàn)實的權(quán)利、自由和幸福;建立在國家體制為特色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上的中國人權(quán)哲學則更關(guān)注集體人權(quán)的整體的(而非個人的),將來持久的(而非現(xiàn)在當下的)幸福———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11]。但是,既然1945年通過的《聯(lián)合國憲章》和1949年通過的《世界人權(quán)宣言》,為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同意并參加,認可其所載明的“人權(quán)和基本自由”所規(guī)定的內(nèi)容,是主權(quán)國家應當遵守的法律義務和道德原則,那么其實并不存在所謂的西方戰(zhàn)勝東方,或者東方戰(zhàn)勝西方的偽問題。因為,如果認識到保障“人權(quán)”作為價值基礎(chǔ),是一切價值的價值,是近代并現(xiàn)代精神的最強音之一,那么,在實現(xiàn)“所有人的所有人權(quán)”的道路上,只會是開放的戰(zhàn)勝封閉的,科學的戰(zhàn)勝愚昧的,民主的戰(zhàn)勝獨裁的,進步的戰(zhàn)勝落后的。2012年,中國共產(chǎn)黨十八大對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最新概括,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也正是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lǐng)導的人權(quán)實現(xiàn)的中國之路的價值基礎(chǔ)。近代中國人權(quán)哲學開辟了中國哲學的新方向,歷史價值不容否認。繼往開來,汲取歷史教訓和不斷總結(jié)實踐,建立在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哲學觀之上的中國人權(quán)哲學,理應也能夠?qū)κ澜缛藱?quán)哲學理論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3.
[2]人民網(wǎng).李鴻章曾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抨擊排華法案[DB/OL].(2014-07-10)[2016-03-19].
[3]梁啟超.儒家哲學[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22.
[4]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趙復蘭,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87.
[5]林語堂.中國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14.
[6]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360-361.
[7]馮友蘭.哲學的精神[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81-82.
[8]公民月刊網(wǎng).人權(quán)之光《世界人權(quán)宣言》的中國元素[DB/OL].(2008-12-17)[2016-03-19].
[9].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3-403.
[10].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
[11]L.亨金,當代中國人權(quán)觀念的比較考察[M]//公法.張志銘,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82.
[12]吳經(jīng)熊.法律哲學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60-60.
作者:史國普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