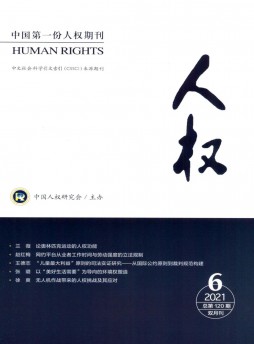人權(quán)概念異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人權(quán)概念異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nèi)容提要:
本文針對(duì)人權(quán)概念的混亂狀況,從邏輯的角度入手,說明人權(quán)是人作為人所應(yīng)享有的權(quán)利。其內(nèi)涵體現(xiàn)于以下三個(gè)矛盾:首先,商品經(jīng)濟(jì)賦予人權(quán)以自由平等的內(nèi)核,同時(shí)又使人不成其為人。其次,法律肯定并保障了人權(quán),同時(shí)又限制了它的范圍和實(shí)現(xiàn)。最后,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講,人權(quán)是我們的目的,但卻是理想的手段。
關(guān)鍵詞:法律,人權(quán),異化,類,共產(chǎn)主義
一、引言
人權(quán)一詞至今幾乎能在所有現(xiàn)代國家的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找到,并且無一例外的被描繪成一個(gè)令人向往的美好事物。論文百事通如“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zhuǎn)讓的權(quán)利,其中包括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逐幸福的權(quán)利。”[1]又如“人們生來并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quán)力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結(jié)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滅的人權(quán)。”[2]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自從有了人到現(xiàn)在,人們何曾在那樣的社會(huì)中生活過?哪怕只有一天。許多美好的藍(lán)圖只不過是寫在現(xiàn)實(shí)法律中的烏托邦罷了。
不僅如此,就連“人權(quán)”這兩個(gè)字的真正涵義也被人扭曲、偷換。“人權(quán)”成了口號(hào),成了策略;但卻從未真正成為“人的權(quán)利”。本文就是基于人權(quán)概念的這種混亂狀態(tài),進(jìn)而想替人權(quán)正名。
“人權(quán)”,顧名思義應(yīng)該是“人的權(quán)利”,而不是“非人的物之權(quán)力”。人是后面權(quán)的所有者。不像其他如財(cái)產(chǎn)權(quán)之類,前面的定語是權(quán)的對(duì)象。人權(quán)中“人”是主體而不是對(duì)象。這樣理解當(dāng)然是很膚淺的。所以本文在討論人權(quán)概念時(shí),一不考證其產(chǎn)生及歷史淵源,二不比較紛繁蕪雜的人權(quán)學(xué)說。而是從“人”的存在狀態(tài)入手說明“人權(quán)”一詞的內(nèi)在邏輯結(jié)構(gòu),即它是道德權(quán)利,是法律權(quán)利,并且還是一種社會(huì)理想;還要說明“人權(quán)”是人作為人應(yīng)享有的權(quán)利。
二、從“人”入手說人權(quán)
啟蒙時(shí)代諸先哲提出了人權(quán)概念,在他們那里人權(quán)是一個(gè)美好的理想,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基于某個(gè)先驗(yàn)的權(quán)威保障而肯定能實(shí)現(xiàn)的社會(huì)存在。不過實(shí)現(xiàn)是要靠人們?nèi)幦〉摹4蠓踩藗円玫侥澄锲罚傄韵旅媸聦?shí)存在為要件。譬如人權(quán),首先是他不為人所享有,或沒有充分享有;其次是人們實(shí)現(xiàn)它有可能性;并且人們對(duì)它有占有欲,也即它能滿足人們的需求。
(一)“人不成其為人”——人權(quán)產(chǎn)生背景
馬克思根據(jù)人在社會(huì)中的生存狀態(tài)把人類社會(huì)分為三個(gè)階段:“人的依賴關(guān)系是最初的社會(huì)形態(tài),在這種形態(tài)下,人的生產(chǎn)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和孤立的地點(diǎn)上發(fā)展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chǔ)的人的獨(dú)立性,是第二大形態(tài),在這種形態(tài)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質(zhì)社會(huì)交換、全面的關(guān)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gè)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huì)生產(chǎn)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huì)財(cái)富這一基礎(chǔ)的自由個(gè)性是第三階段。”[3]
在這里,馬克思通過對(duì)人與他人,人與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考察,重點(diǎn)說明每個(gè)階段人的生存狀態(tài)。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樂觀的,他認(rèn)為人是一步步走向自由的,走向進(jìn)步的。但從另一方面看,人卻是可悲的,至少在第三階段沒有實(shí)現(xiàn)之前,人們總是處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chǔ)”的異化當(dāng)中,處在因異化而“不成其為人”的狀態(tài)中。人權(quán)觀念正是在這種社會(huì)中生長出來,并顯得那么可貴。
說到異化,在第一階段中表現(xiàn)為“人的依賴性”。那是一種自然經(jīng)濟(jì)小農(nóng)社會(huì)。人們被固定到那小塊土地上,是其領(lǐng)主的工具或附庸,其精神世界則完全依托于上帝。勞動(dòng)不屬于自己,人們的價(jià)值不取決于自我,人們的尊嚴(yán)不由自己賦予。當(dāng)時(shí)的人是屬于土地、君主和上帝的。
第二階段,人們自然不用在異化為上帝的依附物了。人們有了商業(yè)社會(huì)起碼的平等和自由。這是馬氏所說的“獨(dú)立性”。但新的異化方式,即“人從人那里異化”,可以說仍然使人“不成其為人”。
人從人那里的異化源于人們的勞動(dòng)的異化。它使勞動(dòng)產(chǎn)品與勞動(dòng)者本身對(duì)立。“勞動(dòng)者同自己的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關(guān)系就像同一個(gè)異己的對(duì)象的關(guān)系一樣。”[4]在這種對(duì)立之中,勞動(dòng)創(chuàng)造價(jià)值越多,勞動(dòng)者越貶值,最終使勞動(dòng)者的人“從現(xiàn)實(shí)中被排擠出去,直至餓死。”[5]這種違悖人與商品本來應(yīng)是擁有者與被擁有者的關(guān)系的異化,使人失去了整個(gè)實(shí)物世界。不僅如此,人的生產(chǎn)生活也被排擠出去,僅成為人存在的手段。于是,人的本質(zhì):類-這個(gè)人所共有的共性,也就“變成了與人異類的本質(zhì),變成維持他的個(gè)人生存的手段。”[6]
到這里人終于完成了異化。人們把自己賴以生存的勞動(dòng)產(chǎn)品異化出去同自己對(duì)立,排擠自己;并由此把自己的本質(zhì)化為手段,以至于脫離這種本質(zhì),社會(huì)、他人乃至自己都是敵人是手段。這一事實(shí)的結(jié)果就是“人從人那里開始異化”。[7]一個(gè)人從其他人那里異化出去,并且社會(huì)中每個(gè)人都從人的本質(zhì)異化出去,人便真的“不成其為人”。人失去了本質(zhì),社會(huì)中的各種作為人的利益自然也要失去。抽象這種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便可以得出,我們所追求的人權(quán)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使人享有自己的本質(zhì)。人權(quán)不是無本之木,人權(quán)思想也不是空穴來風(fēng)。
這里仍有一個(gè)問題要解決。是什么使人在社會(huì)中異化得不成為人,而要尋求類似“人權(quán)”這樣的手段去追求呢?其實(shí)這要問勞動(dòng)者的產(chǎn)品被誰占有,以至于這種占有產(chǎn)生了讓人從物中,從其本質(zhì)中異化的力量。首先自然界不是,它只是受支配者。神靈也不是,這個(gè)虛假的東西只占有人們對(duì)它的供養(yǎng)。這樣只有是人,人本身。是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成果。占有一方是少數(shù),是不用參加那可惡的使人異化的勞動(dòng)的不勞動(dòng)者。這些人憑借商品社會(huì)中生產(chǎn)資料的私有制,占有勞動(dòng)者的勞動(dòng),使勞動(dòng)者失去自己的生產(chǎn)生活資料,失去自己作為人的本質(zhì)。這個(gè)社會(huì)的主要矛盾便成了非勞動(dòng)者同勞動(dòng)者及其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矛盾了。
(二)自由、平等的人才享有人權(quán)
異化這片惡土是不能產(chǎn)生有尊嚴(yán)、有價(jià)值、有個(gè)性的人的。真正成為人權(quán)種子的是商業(yè)社會(huì)的精神內(nèi)核:自由、平等。他們不僅是人權(quán)產(chǎn)生的條件,也是人權(quán)產(chǎn)生的精神內(nèi)核。
自由、平等源于人們交換中的共同利益及要求,交換領(lǐng)域中的人們互相交換自己的商品,以達(dá)到雙方滿足;人們互相服務(wù)。這種過程在雙方意識(shí)中這樣出現(xiàn)的:“⑴每個(gè)人只有作為另一個(gè)人的手段才能達(dá)到自己的目的;⑵每個(gè)人只有作為自我目的才能成為另一個(gè)人的手段;⑶每個(gè)人是手段同時(shí)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為手段才能達(dá)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當(dāng)作自我目的才能成為手段。”[8]“因此雙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雙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獨(dú)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一般利益就是各種自私利益的一般性。”[9]
這種共同的利益決定了某種主張的共同性。即要求交換雙方資格平等、人身自由。因?yàn)榻粨Q中,每個(gè)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xiàn)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fā)生關(guān)系。”[10]這樣,個(gè)人就是完全自由的,“誰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財(cái)產(chǎn)。每個(gè)人都是自愿的出讓財(cái)產(chǎn)。”[11]“就是說實(shí)質(zhì)上是以契約為媒介,通過互相轉(zhuǎn)讓而互相占有。這里邊已有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因素。”[12]此外,以契約為媒介在互相交換時(shí),雙方的平等身份是不可缺少的,否則只能是一方占有另一方。
在交換價(jià)值中,人才能與他人一樣實(shí)現(xiàn)自己在社會(huì)中的價(jià)值本質(zhì)-平等、自由地占有對(duì)方(其實(shí)也是占有自己)。
可見,人權(quán)自產(chǎn)生就離不開商品經(jīng)濟(jì)。一方面商品經(jīng)濟(jì)異化勞動(dòng)使人失去做人的資格,另一方面交換商品卻使人們懂得要求人權(quán),要求自由、平等。人權(quán)也正是在商品經(jīng)濟(jì)這個(gè)矛盾的揚(yáng)棄中產(chǎn)生發(fā)展的。如果說異化是人有史以來的生存狀態(tài),那么商品經(jīng)濟(jì)(特別是交換)卻為人們追求自身的價(jià)值,打破“不成其為人”的局面提供了平等、自由的有力武器。所以人權(quán)不出現(xiàn)于其他時(shí)代,而出現(xiàn)于商品經(jīng)濟(jì)統(tǒng)一天下時(shí),看來決非偶然。
(三)人權(quán)的內(nèi)涵
上文所講的異化問題是人權(quán)產(chǎn)生的反作用力;商業(yè)自由、平等又給人權(quán)提供精神基礎(chǔ)。但這些遠(yuǎn)遠(yuǎn)不是人權(quán)。他們是不能直接產(chǎn)生人權(quán)的,人權(quán)只能是類本質(zhì)和特定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
正如商品經(jīng)濟(jì)中人們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共同的平等、自由的要求一樣;異化社會(huì)中的人,基于其仍然為人,異于其他生物,而要求對(duì)類本質(zhì)的重新占有,以成為真正社會(huì)人,真正的去生產(chǎn)生活。這才是真正的人權(quán)要求。
人的類本質(zhì),本來就是人的共同本質(zhì)或自然本質(zhì),人們因之而成為社會(huì),社會(huì)因之而能體現(xiàn)每個(gè)個(gè)體的人的存在。在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中,所有的各種各樣的利益,如被某個(gè)個(gè)體所享有,其前提便是該個(gè)體是人,是社會(huì)的一分子,并且其他人也認(rèn)同這一事實(shí)。然而,異化社會(huì)卻剝奪了該個(gè)體去享受諸社會(huì)利益的資格。如果把該資格看作一種利益,那么人權(quán)就是對(duì)這種作為人能帶來的直接利益的要求和保障。它體現(xiàn)一種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所以在這里講人權(quán)與其他權(quán)利的區(qū)別就是,其他權(quán)利是基于某一個(gè)人、階層或社會(huì)之間某些利益或價(jià)值的一般性和一致性;而人權(quán)則是基于人類所有成員的類特征、類本質(zhì)之間的相互一致和認(rèn)同。
正是這種認(rèn)同致使人權(quán)要求一出現(xiàn)便被形成人們相互之間的倫理規(guī)范,并在道德上形成一種權(quán)利。從而賦予上文所說的人道主義以權(quán)威,不可違抗。此時(shí)人權(quán)要求一躍成為人權(quán)。
上文的般般敘述無非是想說明下面這一人權(quán)定義的合理性。所謂人權(quán),就是人作為人所應(yīng)該享有的權(quán)利。它包括以下兩層含義:
第一,人權(quán)是人作為人所應(yīng)享有的。“人之作為人”,第一個(gè)“人”字包括所有現(xiàn)實(shí)中的人,它是人權(quán)的主體。上文在講異化時(shí),大概會(huì)給人留下一種錯(cuò)覺,即生產(chǎn)資料所有者憑借私有制占有廣大勞動(dòng)者,使其異化得不成為人,所以人權(quán)應(yīng)是那廣大勞動(dòng)人民的而不應(yīng)讓產(chǎn)品占有者享有。事實(shí)并非這樣,上文同時(shí)也講了,異化只是人權(quán)產(chǎn)生的背景,并不能直接產(chǎn)生人權(quán)。人權(quán)產(chǎn)生于人們之間類的認(rèn)同。所以凡是這個(gè)社會(huì)中的人,只要是人,不分男女老少、階級(jí)等差別,都應(yīng)享受到人權(quán)。人權(quán)是普遍的。如果只讓人權(quán)囿于勞動(dòng)者以表明其有鮮明的階級(jí)性的話,人權(quán)就淪落為另一部分人壓迫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占有者,是反人權(quán)的。人權(quán)的階級(jí)性只存在于因法律對(duì)人權(quán)的確認(rèn)保障中使之成為一部分人的特權(quán)之中。第二個(gè)“人”字,則是抽象的,是以充分享有類本質(zhì),在社會(huì)中獨(dú)立的、由尊嚴(yán)的、有價(jià)值、有個(gè)性的人。其實(shí)這種“人”只有在人權(quán)真正實(shí)現(xiàn)后再能真正存在。
第二,人權(quán)最終表現(xiàn)為權(quán)利。只有這一點(diǎn)存在才算真的有人權(quán),否則則只是空泛的人道主義口號(hào),沒有任何權(quán)威性。人權(quán)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道德權(quán)利。因?yàn)槿藱?quán)產(chǎn)生是人類的相互認(rèn)同的社會(huì)產(chǎn)物,從一開始它就帶有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性質(zhì),并成為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一種調(diào)整規(guī)范,不論是自發(fā)的還是自覺的,凡是有悖人權(quán)的就將受到輿論譴責(zé),甚至良心上感到內(nèi)疚。人權(quán)是在道德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并存在的。當(dāng)然作為一種能實(shí)行于社會(huì)的權(quán)利,僅靠道德是不行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人權(quán)還表現(xiàn)為法律權(quán)利,這種權(quán)利雖然能為人切實(shí)享有,但已經(jīng)變了質(zhì),而存在于道德中的人權(quán)才是真正的。
另外,要注意人權(quán)存在的先決條件是人們之間自由、平等。這兩者還是人權(quán)的重要內(nèi)容。它們表現(xiàn)出人權(quán)精神中最基本的人道精神,是類本質(zhì)存在的最低要件
現(xiàn)在我們可以概括人權(quán)為如下:人權(quán)本質(zhì)上是以權(quán)威性的規(guī)范乃至是某種社會(huì)制度去肯定人之作為人所應(yīng)有的利益,使之成為法定權(quán)利。其根本意義在于人的本質(zhì)的復(fù)歸。
三、人權(quán)與法律
法律作為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在當(dāng)今世界確實(shí)比道德規(guī)范實(shí)效得多。以它來保證人權(quán)的實(shí)施肯定比純粹道德權(quán)利見效快。然而,人權(quán)與法律的關(guān)系絕不是這么簡單,它是一個(gè)由淺入深的否定之否定關(guān)系。
(一)人權(quán)是法律的權(quán)利(肯定)
法律是人們生產(chǎn)生活的自覺反映,是人行為本身必備的規(guī)律,真正的法律應(yīng)是保障人權(quán)的法律。應(yīng)該以維護(hù)人的尊嚴(yán)與價(jià)值作為其不便的價(jià)值取向,任何其他利益都不能干涉這一原則的實(shí)施。現(xiàn)在國家人權(quán)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其具體內(nèi)容及實(shí)現(xiàn)手段,并且協(xié)調(diào)不同主體間的關(guān)系的。法律從實(shí)體和程序兩方面來保障人權(quán)并借此表明自己的合法性。最關(guān)鍵的所在是法律有強(qiáng)制性,人權(quán)不被違背破壞必須由強(qiáng)制的制裁來保障。法律在這里表現(xiàn)得比道德優(yōu)越。可以說,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人權(quán)表現(xiàn)為法律權(quán)利是人權(quán)的需要也是法律的需要。當(dāng)然也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切實(shí)的享受到人權(quán)。
(二)法律,人權(quán)的限制(否定)
法律規(guī)定了人權(quán),同時(shí)也限制了人權(quán)。
首先,法律的產(chǎn)生在現(xiàn)存社會(huì)的基礎(chǔ)上。這是一個(gè)人普遍不成其為人的社會(huì)。在這里以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為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法律必須表現(xiàn)出其階級(jí)性,否則便不能實(shí)施甚至存在。所以法律只有去體現(xiàn)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占有者的意志;肯定一部分人占有生產(chǎn)資料,另一部分人被別人占有其勞動(dòng)產(chǎn)品;肯定從其勞動(dòng)成果及其類的本質(zhì)中異化出去這些現(xiàn)實(shí)具有合法性,并強(qiáng)制保證其不被徹底改變。
其次,因?yàn)榉煽隙水惢运豢赡芤匀藱?quán)作為其唯一的價(jià)值取向。其他的價(jià)值還表現(xiàn)在諸如政治目標(biāo)等等。當(dāng)法律保證這些價(jià)值時(shí)人權(quán)往往表現(xiàn)為特權(quán)。這本身就是對(duì)普遍人權(quán)的否定。孟德斯鳩說:“法律應(yīng)該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關(guān)。”此言不虛。當(dāng)人們的普遍權(quán)利與階級(jí)特權(quán)矛盾時(shí),后者高于前者是肯定的。不僅如此,某些集體利益,也往往實(shí)現(xiàn)在犧牲少數(shù)人人權(quán)的基礎(chǔ)之上。
再次,法律規(guī)定了某些人權(quán)為全社會(huì)成員平等享有,任何人不得侵害之。但是法律又規(guī)定實(shí)現(xiàn)這一權(quán)利的手段為少數(shù)人或一部分人所享有,這樣一來普遍權(quán)利就成為特權(quán)。并且這一部分往往是基本人權(quán)。如:商品經(jīng)濟(jì)四個(gè)階段中以生產(chǎn)為本,但生產(chǎn)的一方是生產(chǎn)資料所有者,另一方是自由得只剩下勞動(dòng)力的無產(chǎn)者。這時(shí)法律規(guī)定人們享有平等自由權(quán);結(jié)果它只能是一方平等的剝削勞動(dòng)力,另一方自由的出賣勞動(dòng)力的權(quán)利。所以“人權(quán)本身就是特權(quán)”。
最后,法律作為實(shí)現(xiàn)人權(quán)的手段,本身有局限性,表現(xiàn)在強(qiáng)制性上最為明顯。它一方面保障人權(quán)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卻以剝奪侵害者的人權(quán)為代價(jià)。譬如一個(gè)人侵犯了另一個(gè)人的某項(xiàng)權(quán)利,他受到強(qiáng)制性的處罰;那么這種強(qiáng)制無疑剝奪了它的人權(quán)。但是罪犯即使犯了罪也是人,仍然是社會(huì)中的一分子。而人權(quán)又是人作為人應(yīng)有之權(quán)。可見強(qiáng)制性本身是對(duì)人權(quán)的普遍性的限制。在沒有解決這種以惡制惡公正性、合理性問題時(shí),強(qiáng)制本身就是人權(quán)問題。
法律作為保障人權(quán)的工具較道德規(guī)范確有
一定優(yōu)勢(shì),但由于現(xiàn)代社會(huì)法律的這些特點(diǎn)使其不能真正達(dá)到保障人權(quán)的目的。它在確定人權(quán)的內(nèi)容時(shí),明確了人權(quán)的具體種類,但這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人權(quán),它只肯定不危及現(xiàn)存社會(huì)的那一部分。可以說作為工具的法律和作為目的的人權(quán)是矛盾的。雖然人權(quán)在現(xiàn)代社會(huì)表現(xiàn)為法律權(quán)利,但是法律不是人權(quán)的法律,人權(quán)也不是法律的人權(quán)。人們所享受到的人權(quán)是由法律規(guī)定的,這只是應(yīng)有人權(quán)的一部分;并且還有一部分,雖有規(guī)定但只是擺設(shè),不能真的為人所有。
(三)“被限制的人權(quán)”成為“真正的人權(quán)”(否定之否定)
現(xiàn)代法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讓法律深入人心,完成其道德化。也就是要求法律主體把守法內(nèi)化成一種道德義務(wù)。違法者不僅受法律的制裁而且要受到良知的譴責(zé)和社會(huì)輿論的非議,這個(gè)過程本身是法治的理想狀態(tài);它充分表明法的精神就是正義的道德理念精神。正如上文講過立法將人權(quán)的內(nèi)容和現(xiàn)實(shí)程序以明確的條文規(guī)定下來的同時(shí),不能窮盡所有的人權(quán),它只是確定了人權(quán)的一部分,并每每在這些權(quán)利上面烙上統(tǒng)治者利益的印跡。這種法律當(dāng)然也要為人遵守,深入人心,成為社會(huì)上人們的道德理念、規(guī)范乃至理想。這本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人們便以為這法律上的人權(quán)就是真正的完全的,并且我們已經(jīng)享受到了;任何反對(duì)現(xiàn)存制度的行為、思想都是反對(duì)人權(quán)的。于是真正的人權(quán)只能蛻變?yōu)橛须A級(jí)色彩的不完全的人權(quán)。其他的人權(quán)被抹殺,本來本質(zhì)上不公平的事被認(rèn)為正是我們所追求的。
這時(shí),現(xiàn)代資本主義工業(yè)帶來巨大的物質(zhì)財(cái)富,法律有可能建立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福利制度。馬克思當(dāng)年研究異化時(shí)那種工人極度貧困狀態(tài)已不復(fù)存在。人們認(rèn)為自己就已經(jīng)生活在一個(gè)平等、自由的社會(huì)中。孰不知這只是手段,福利制度是不能解決勞動(dòng)被他人占有的問題的。只要這一點(diǎn)存在,異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社會(huì)發(fā)展到了這里,人的異化卻已深入化、復(fù)雜化了。有人把它叫作“異化的異化”不無道理。這種異化突出表現(xiàn)在人們快樂的生活,卻沒有真正的實(shí)現(xiàn)其自由。人們?cè)谪S富的物質(zhì)面前獲得了虛假的解放,自以為占有了本質(zhì),自以為揚(yáng)棄了異化,自以為獲得了平等和自由。其實(shí)人們更深刻的失去了自己。這里不再是一種現(xià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強(qiáng)制,而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控制下的心理異化。
這一切隨著法治深入人心,已外化成一種道德存在。法律解決不了勞動(dòng)者異化的問題,那么法律與人權(quán)的矛盾就得不到解決。人權(quán)在現(xiàn)代社會(huì)表現(xiàn)為法律權(quán)利,然而法律不能完全實(shí)現(xiàn)人權(quán),反而使人權(quán)發(fā)展更加復(fù)雜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離人權(quán)更遠(yuǎn)了。這就是人權(quán)的悖論。現(xiàn)在人們所論述的人權(quán)之普遍性與階級(jí)性、現(xiàn)實(shí)性與理想性等矛盾無不根源于此。
人權(quán)與法律的否定之否定式的矛盾使人權(quán)不能真正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實(shí)現(xiàn)。充其量人們所能享受到的只有法律規(guī)定的那部分和存在于日常習(xí)慣、倫理中的由道德自發(fā)規(guī)范的那部分。這個(gè)社會(huì)里被法律限制的那部分人權(quán)變成了真正的人權(quán),不能說不是人權(quán)的可悲。要想真正實(shí)現(xiàn)人權(quán),怕要到自由人自由聯(lián)合的社會(huì)了。
也難怪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的人權(quán)“都沒有超出利己主義的人.在這些權(quán)利中,人絕不是類存在物,相反地,類生活本身即社會(huì)卻是個(gè)人的外部局限,卻是他們的原有的獨(dú)立性的限制。把人和社會(huì)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duì)他們財(cái)產(chǎn)和利己主義個(gè)人的保護(hù)。”可見上述悖論直接結(jié)果使人權(quán)被異化了。它本來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現(xiàn)在卻變成了自私自利的工具。
四、人權(quán)與理想社會(huì)
從古到今似乎每個(gè)偉大的哲人都為我們描繪了他自己的社會(huì)理想。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孔子的大同郅治到馬克思的共產(chǎn)主義,無不如此。它們都有一個(gè)共性,即構(gòu)建在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弊端的揭露基礎(chǔ)上。它們都按一定邏輯展開并推導(dǎo)出一個(gè)先驗(yàn)式的理想社會(huì),并且那里的人生活得總比現(xiàn)在好。特別是共產(chǎn)主義所設(shè)想的,那里的人不僅有豐富的物質(zhì)生活,而且人們揚(yáng)棄了異化,樹立了人的尊嚴(yán),實(shí)現(xiàn)著人的價(jià)值。
“共產(chǎn)主義是私有財(cái)產(chǎn)及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yáng)棄,因而也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duì)人的本質(zhì)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為社會(huì)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fù)歸,這種復(fù)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fā)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這不正是我們?nèi)藱?quán)概念中所包含的嗎?
人權(quán)是普遍權(quán)利,它意味著所有的人只要是社會(huì)中的一員,不論在種族、階級(jí)、信仰、膚色、財(cái)富、性別、國籍、知識(shí)、能力等方面有何具體差異,皆一律平等,擁有人之作為人的同等價(jià)值和尊嚴(yán)。如果這種平等超越出道德權(quán)利、法律權(quán)利而形成國家社會(huì)的運(yùn)作原則,那么這個(gè)社會(huì)不是共產(chǎn)主義又是什么?
人權(quán)是人類相互認(rèn)同的結(jié)果。在這種認(rèn)同中包含著和諧的因素。現(xiàn)在社會(huì)中人與人之間基于利益沖突是對(duì)抗的。表現(xiàn)在權(quán)力與義務(wù)的對(duì)抗,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對(duì)抗,個(gè)體與群體的對(duì)抗。所謂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只是表面的、一般的。人權(quán)雖然在人與人對(duì)抗中產(chǎn)生,但它卻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和諧統(tǒng)一。當(dāng)然這種和諧絕不是中國小農(nóng)式的和諧,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強(qiáng)烈的利益沖突,人只是義務(wù)的主體,只附屬于君權(quán)及其類似的權(quán)力。人權(quán)所昭示的和諧是合乎人的本性的。人們互相認(rèn)同對(duì)方的價(jià)值,尊重對(duì)方的尊嚴(yán),寬容對(duì)方的個(gè)性。享有權(quán)利是人們的義務(wù);履行義務(wù)是人們的權(quán)利。這種和諧中“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
對(duì)法律來講,人權(quán)是目的;但對(duì)理想社會(huì)來講,人權(quán)是手段。在理想社會(huì)中,人權(quán)不再是法律權(quán)利,不再是現(xiàn)在這種道德權(quán)利,它僅表現(xiàn)為人們自覺履行的人道主義。新晨
五、結(jié)語
上面分析了人權(quán)概念的邏輯內(nèi)涵,似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諸結(jié)論:
(一)人權(quán)是以權(quán)利形式確定下來的人道主義,其核心內(nèi)容是自由、平等。
(二)人權(quán)是對(duì)異化的否定,是人類本質(zhì)的重新占有。
(三)人權(quán)本身是道德權(quán)利;但現(xiàn)在法治社會(huì)中它表現(xiàn)為法律權(quán)利。
(四)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人權(quán)經(jīng)法律確認(rèn)而成為實(shí)在權(quán)利,但卻被從內(nèi)容和形式上限制。
(五)人權(quán)是理想社會(huì)實(shí)現(xiàn)的手段。
從以上五個(gè)方面理解人權(quán)才能算是全面的。其中充分體現(xiàn)人的主體性。整個(gè)社會(huì)是人的社會(huì),歷史也是人的歷史,人權(quán)無時(shí)不體現(xiàn)尊重人的價(jià)值、個(gè)性、尊嚴(yán)的精神。一個(gè)不把人放在首位加以重視的社會(huì),不論其法律規(guī)定多少人權(quán),社會(huì)福利多么豐富,恐怕都不能算是人權(quán)的社會(huì)。
注釋:
[1]《獨(dú)立宣言》
[2]《人權(quán)宣言》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1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