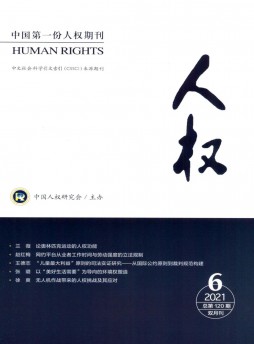人權保障與實體真實的博弈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權保障與實體真實的博弈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案情:被告人袁某因盜竊罪于2008年3月被判處拘役6個月,緩刑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在緩刑執行期間,于同年7月30日,伙同被告人柳某、顏某至本市宜川路、甘泉路附近,扒竊被害人洪某現金人民幣1000元,事后被公安機關抓獲,檢察機關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對其判決如下:撤銷原判對袁某的緩刑部分,執行拘役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對袁某此次犯盜竊罪,判處其拘役6個月,緩刑10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決定執行拘役6個月,緩刑10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一審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檢察院未抗訴。上級檢察機關出席二審法庭,認為一審判決對袁某適用緩刑于法無據,應當改判實刑。二審法院經審理亦認可了檢方的觀點。但是出于對上訴不加刑原則的尊重,二審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待二審裁判生效后由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以改判袁某實刑。這是一起極為普通的輕微刑事案件。上級檢察機關依法履行了國家公訴人的職能,指出一審裁判的錯誤。二審法院也嚴格遵守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中有關上訴不加刑的規定。表面上看來,這起案件處理得非常圓滿,實體真實得到了維護,程序也得到了切實的遵守。但是,在這起案件的背后,我們也發現了諸多問題。如此一個簡單的案件,卻要耗費大量的司法資源,甚至不惜推翻生效裁判,最終把被告人引向一個更重的處罰,上訴不加刑原則在此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而且這樣的處理程序并非是真正的公正。
一、在人權保障與實體真實的博弈中,實體真實往往會占據上風不難看出,司法機關在本案中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沒有任何違法之嫌。但刑訴法中寫得明明白白的上訴不加刑怎么就一晃變成了“上訴加刑”呢?這其中最關鍵的法律依據就是《解釋》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五)項,“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但判處的刑罰畸輕,或者應當適用附加刑而沒有適用的案件,不得撤銷第一審判決,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或者適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第一審人民法院重新審理。必須依法改判的,應當在第二審判決、裁定生效后,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從條文中我們不難想象,立法者在作出這樣的規定之前,必然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要么完全貫徹刑訴法上訴不加刑原則的精神,放棄對被告人追究少科處的那部分刑罰,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權益;要么對上訴不加刑原則做限制性解釋,僅從字面上把其理解成只適用于上訴審裁判之中,而人民檢察院為被告人利益提起的抗訴和再審之裁判則不適用該原則。選擇前者,意味著立法者對個案公正和實體真實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損;而選擇后者,則說明追求被告人程序性權益的價值取向在與有錯必糾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抗爭中,終因動力不足而遭到挫敗。立法者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后,選擇了后者,于是便有了上述規定。有錯必糾的刑事司法理念不但得到了馬克思主義“事實求是”理論的完美詮釋,而且已經深入人心,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也自然成為立法者在進行制度設計的時候所遵循的最高宏旨。另外,在司法實務中的現行體制釀成了司法機關對實體真實的傾向性追求。公安機關的職責就是要搜集盡可能多的有罪證據來偵破案件,檢察機關則要竭盡全力為被告人編織一張犯罪的“證據網”,以獲得公訴成功的結果,而法院就是要按照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迅速將被告人推向一個有罪判決,以準確實現國家刑罰權。只要司法機關順利地完成了上述任務,相應的辦案人員就會受到肯定性評價,而一般不會因為程序上存在的瑕疵受到懲罰,更不會因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不夠充分而受到否定評價!現行司法行政管理制度中針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獎懲機制幾乎完全圍繞著“偵破案件”、“公訴成功”和“審判不出錯案”而建立。這樣的獎懲機制不但無法催生司法工作人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內在動力,反而激勵他們為了保證案件質量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犧牲部分程序正義,甚至侵犯人權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與司法工作人員的素質無關,不恰當的制度設計才是罪魁禍首。因此一味的呼吁提高司法工作人員的素質,改變他們的執法觀念,這必然是徒勞的,只能是隔靴搔癢,不可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當人權保障與實體真實發生價值沖突的時候,無論是立法者還是司法工作人員,經過簡單的利益衡量,都更傾向于選擇后者,人權保障只能做出讓步。
二、程序迂回曲折,有違訴訟效益最大化原則這樣一起輕微的刑事案件,卻要經歷一場漫長的訴訟,一審,二審,再審,即使案件最終能得到正確處理,也沒有人會成為最終的“贏家”。被告人在歷經了長時間的忐忑不安后,最終由緩刑被改判實刑。司法機關卻要為這起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案件,不斷從有限的司法資源中擠出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從訴訟效益最大化的角度來看,這起案件的處理無疑是非常失敗的。有學者指出:“人類所從事的任何社會活動都必須遵循經濟性的原則,即力求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從而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3]刑事司法活動本身盡管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也同樣要遵循這一具有普適性的原理。刑事司法資源稀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司法機關面對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數量和趨于專業化、復雜化的新型犯罪案件,常常疲于應對。因此,如何利用稀缺的司法資源來處理更多的案件,將司法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降到最低,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當然我們并不贊同那種為了節省司法資源在程序上“偷工減料”的做法。對于訴訟效率的追求必須以保障訴訟公正為前提。美國學者麥克爾說:“如果只是追求經濟成本的最小化,我們就沒有必要開庭審理,提供信息,只需要拋擲硬幣或用其他方法就能成本低廉地作出一個解決爭執的判決”。[2]波斯納把訴訟效益視為公正在法律上的第二層含義,一個拖沓、漫長且耗費巨大的訴訟程序,不可能有公正可言。正如西方法諺所言:“Justdelayedisjustdenied(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尋求一個公正與效益的最佳契合點,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而很顯然,《解釋》的規定是以犧牲訴訟效益為代價來追求一個實質上并不甚公正的結果,這讓我們無法接受!
三、二審法院自我否定生效的判決,邏輯混亂,且有損法院權威在第二個問題中我們就已經談到,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然后通過再審程序來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不僅是對有限司法資源的浪費,這個做法本身在邏輯上就有混亂之嫌。二審法院先是維持該判決,然后通過另外一種程序迅速將自己的裁定推翻,無異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法院的權威也受到很大挑戰。按照通常的邏輯,二審法院要么對量刑不當的一審判決直接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罰,要么放棄對這部分刑罰的求刑權,姑且“縱容”一次被告人。前一種做法為上訴不加刑原則所明令禁止,第二種做法則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礙,而且是上訴不加刑原則的內在應有之義。因為上訴不加刑原則的實質就是國家有條件的寬容部分被告人,以犧牲個案公正為代價換取更大的價值目標。二審法院如果能根據我國刑訴法的立法本意而不是《解釋》的變通規定,對這樣的量刑畸輕的判決擺出一種寬容的姿態,縱使犧牲一點實體真實,也比“打自己臉”要好得多。烏爾比安在《論尤里亞和帕比亞法》的第1編中提出了一句著名的格言:“已決案被視為真理”,不到萬不得已“真理”是不能被推翻的。司法的權威性恰恰體現在這里,已經生效的判決對于訴爭事實具有終局確定力,如果隨意推翻,那么這部分業已紊亂的社會關系將永遠處在不確定狀態,法院定紛止爭的職能無法實現。司法的權威也必將大打折扣。另外,《解釋》的變通規定實質上是修改了刑訴法的規定,破壞了法律體系的統一。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維持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也即只有在原判正確的時候,才能做出維持的裁定。而《解釋》第二百五十七條卻規定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但判處的刑罰畸輕的案件,必須依法改判的,應當在第二審裁判生效后,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按照《解釋》的規定,二審法院對適用法律正確但量刑畸輕的案件首先要做出維持的裁定,待二審裁定生效后再通過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顯然,《解釋》的規定與刑訴法相沖突,作為下位法的《解釋》的相關規定應當歸于無效。
四、“必須依法改判”的標準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上訴不加刑原則存在被規避的可能性在這起案件中,上級檢察機關和二審法院均認為一審判決屬于“判處的刑罰畸輕……,必須依法改判”的情況。一審對被告人理應判處實刑卻適用了緩刑,這認定為“必須依法改判”沒有很大的爭議。但是,由于刑訴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中都沒有具體的認定標準,這也就留給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在諸多類似案件的處理中,最后是否會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糾正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可能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同樣的案件擺在不同的法官面前,可能會遭遇不同的處理結果,被告人可能會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此外,由于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受追求實體真實的價值取向的影響,更傾向于將“必須依法改判”做任意擴大化解釋。這樣一來,幾乎任何被告人單方上訴的案件都可以不受上訴不加刑原則的限制,只要被法院認定為屬于“必須依法改判”的情形,法院就可以以正當的理由把案件推向審判監督程序,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上訴不加刑原則也就通過另外一個程序變成了“上訴加刑”。因此,筆者認為必須通過立法制定一套可行的認定標準,規定哪些情形確屬“必須依法改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限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只有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設定一個界限,讓他們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使權力,權力才不會被濫用。只有這樣,上訴不加刑原則才能真正發揮它的作用而不至于被規避或架空。筆者認為,上訴不加刑原則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歸咎于立法的疏漏和不完善。立法者在進行一系列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時候,始終無法跳出“實體真實至上”的圈子,忽略了上訴不加刑原則在人權保障領域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而不是執法者的美德;它應該閃耀在法典中,而不是表現在單個的審判中。”[4]上訴不加刑原則是國家對處于弱勢地位的被告公民給予的特殊關懷,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人權保障方面所具有的優越性,是國家對公民的美德。立法者應當把這種美德貫徹在我們國家的法律體系之中,在立法上為執法者提供準確的價值指引,讓上訴不加刑原則充分發揮它保障人權的功能。我們期待著立法者能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