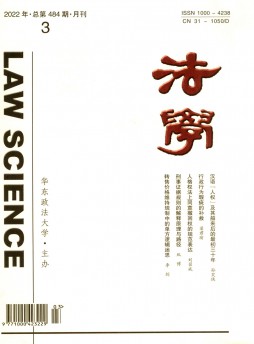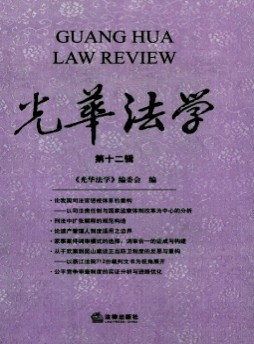法學(xué)規(guī)范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法學(xué)規(guī)范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經(jīng)過80年代的準(zhǔn)備,經(jīng)過認(rèn)真、求實(shí)、兢兢業(yè)業(yè)、甘于寂寞的努力,一批學(xué)者迅速成長。進(jìn)入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huì)人文學(xué)術(shù)界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氣象。特別是在文史哲這些有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領(lǐng)域,以及經(jīng)濟(jì)學(xué)等一些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已經(jīng)或正在形成一種學(xué)術(shù)的氛圍,正在建立比較嚴(yán)格的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相比之下,就整個(gè)法學(xué)領(lǐng)域來看,應(yīng)當(dāng)說,這種傳統(tǒng)和學(xué)術(shù)氛圍還比較差。盡管法學(xué)的所謂“核心刊物”有幾十種之多,不時(shí)也有一些高質(zhì)量的學(xué)術(shù),但總體來看,真正堅(jiān)持了嚴(yán)格的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的法學(xué)刊物也許只有一兩種,有些所謂的法學(xué)核心刊物實(shí)際連法學(xué)刊物都不能算。
由于刊物的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不嚴(yán)格,法學(xué)院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不嚴(yán)格,許多具有很好的學(xué)術(shù)潛質(zhì)的學(xué)生未能得到良好的訓(xùn)練,他們找不到良好的學(xué)術(shù)范本。在這個(gè)意義上,我認(rèn)為,法學(xué)界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尚未建立。
要建立或重建法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無疑需要全面的努力,面對中國實(shí)際、借鑒國外經(jīng)驗(yàn)、研究者的個(gè)人學(xué)術(shù)品質(zhì)和兢業(yè)精神、開展真正的學(xué)術(shù)批評,都是必不可少的。從目前來看具體可行的、而且必行的一步就是要建立學(xué)術(shù)規(guī)范。規(guī)范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當(dāng)然是實(shí)質(zhì)性的,但我在此僅就一些人看來并不起眼一點(diǎn)DD引文,這種形式化的規(guī)范,發(fā)點(diǎn)議論。我只是從引文對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建立的功能性角度來談,至于對引文全面分析,至少可以作一篇長文。
目前的法學(xué)著作、文章,除了少數(shù)外,引文很少。翻開法學(xué)著作和刊物,包括一些核心的法學(xué)刊物上發(fā)表的一些不錯(cuò)的文章,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文章從頭到尾沒有一個(gè)注。似乎一切觀點(diǎn)都是作者自己創(chuàng)新的,其實(shí)未必如此。這首先反映了的一點(diǎn)就是有些作者不讀書,或讀的很少(另外反映的是對他人的勞動(dòng)成果的不尊重,即今日流行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究其原因,我們當(dāng)然可以說法學(xué)界發(fā)表出版的有新見解的書籍和文章確實(shí)不多,但總還是有一些;而且還有一些相當(dāng)不錯(cuò)的調(diào)查報(bào)告、案件分析、社會(huì)報(bào)導(dǎo)和資料。但相當(dāng)多的搞法學(xué)的人似乎視而不見。如果不讀書,那么怎么可能學(xué)術(shù)的傳承,怎么可能建立學(xué)術(shù)的傳統(tǒng)呢?最好的情況也只能是“一切從我作起,從現(xiàn)在做起”;而我很懷疑法學(xué)界有那么多才子或“泰斗”。
沒有學(xué)術(shù)性的引文或引證,表明法學(xué)界沒有借鑒和學(xué)術(shù)積累。引文首先是一個(gè)選擇研究方向和題目的問題。如果不注意他人已研究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那么我們所作的大量研究就可能只是、而且目前實(shí)際只是在重復(fù)他人已經(jīng)作過的事,研究他人已研究過的專題,“發(fā)現(xiàn)”一些早已經(jīng)有的發(fā)現(xiàn)。這樣不僅浪費(fèi)了大量個(gè)人的和社會(huì)的資源,而且無法使自己的勞動(dòng)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礎(chǔ)上推進(jìn),中國的學(xué)術(shù)就不可能盡快發(fā)展起來,提高到一個(gè)新的水平;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一個(gè)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只要看一看這兩年來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論文,有多少論文是在重復(fù)著他人和自己!一些人把自己的(?)同一個(gè)觀點(diǎn)在各種報(bào)刊雜志上不斷重復(fù),最多變變句型和序列。這種論文實(shí)際上只是在作宣傳,而不是作學(xué)術(shù)研究。我并不一般地反對宣傳,也許在建立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開始時(shí)期,需要一些宣傳;但不能總停留在此。而且社會(huì)要有一個(gè)分工,如果還想在法學(xué)界當(dāng)學(xué)者的話,而不是在法律界或社會(huì)上當(dāng)活動(dòng)家、鼓動(dòng)家,就要不斷地研究新問題、提出新問題。而引文或觀點(diǎn)引證就是不斷推進(jìn)學(xué)術(shù)研究,深化研究水平的一個(gè)基礎(chǔ),一種保證。只有熟悉了某個(gè)領(lǐng)域內(nèi)一些主要的著作和文章,才可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矛盾和新問題,才可能(但不必然)有新的洞識,才可能推進(jìn)自己的思想;并進(jìn)而推進(jìn)法學(xué)界的研究。這里的形式性規(guī)范并不僅僅是形式的,而是具有實(shí)質(zhì)性的內(nèi)容的。[2]
同時(shí)引證他人,也就是理解他人的過程,是與他人對話的過程;而這個(gè)過程又是形成學(xué)術(shù)共同體,建立和保持學(xué)術(shù)對話的可能性和能力的過程。如果每個(gè)人都“從我作起,從現(xiàn)在作起”,即使每個(gè)人都認(rèn)真,那么也會(huì)各人有各人的話語、概念、命題,[3]這種多元的情況在某些方面有好處—可以防止一條路上走到底而形成僵化,但危險(xiǎn)在于難以對話,難以形成學(xué)術(shù)共同體,更不用說建立學(xué)術(shù)流派和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
引文在當(dāng)今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之不可缺乏,還因?yàn)樵谝欢ㄒ饬x上說,我們處于一個(gè)“知識爆炸”的時(shí)代,我們每個(gè)人不可能對所有的知識都有比較透徹的了解,甚至不可能對哪一門知識敢聲稱有完全的了解。[4]我們必須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事實(shí)上我們的對一個(gè)學(xué)科的大部分知識和判斷、每一個(gè)新觀點(diǎn)都提出或發(fā)現(xiàn),都是建立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礎(chǔ)上的,其中包括其他學(xué)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這種情況也許在現(xiàn)代、在法學(xué)界更為突出,因?yàn)樵谝欢ㄒ饬x上現(xiàn)代知識增長更快,因?yàn)榉▽W(xué)(當(dāng)然并不僅僅是法學(xué))是一門涉及社會(huì)所有方面(即學(xué)科)的實(shí)踐理性的學(xué)科。在這樣的條件下,為了保證論文的專科性(即還算是“法學(xué)”論文)同時(shí)保持它的新穎,我們就必須引證他人的觀點(diǎn)或研究結(jié)論。只要回顧一下當(dāng)代西方法學(xué)的發(fā)展,就可以看到哲學(xué)中的闡釋學(xué)和語言哲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和文化人類學(xué)以及其他學(xué)科或次學(xué)科對法學(xué)的全面滲透,因此波斯納在《法理學(xué)問題》中敢于說法學(xué)不是一個(gè)自治或自主的學(xué)科。[5]即使在我國近十幾年來,法學(xué)實(shí)際上也從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哲學(xué)和歷史中吸取了許多動(dòng)力,甚至可以說主要來自外部動(dòng)力。因此,法學(xué)研究對其他學(xué)科研究結(jié)果的借鑒是大量的、不可避免的。而大量法學(xué)文章不可能、也不應(yīng)當(dāng)為了論證之必要而將這些領(lǐng)域結(jié)果之可信性全部展開,而只能引證觀點(diǎn)。這樣,引證就是保證論文或著作寫的更有新意、更精粹、更言之有物、更緊湊、更集中于法學(xué)問題上的一個(gè)不可缺少的條件。
然而,引文還不僅是為文章寫的集中,它同時(shí)還可以幫助那些對文章所涉及的某個(gè)結(jié)論或論點(diǎn)、或者作為理論前提的某個(gè)結(jié)論和論點(diǎn)感興趣的他人,便于他們發(fā)現(xiàn)原始材料,查找原著,了解與法學(xué)有關(guān)的新知識、新學(xué)科、新領(lǐng)域。因此,引文在此又是一種發(fā)現(xiàn)和接觸新知識的渠道,一條信息公路。是法學(xué)界交流知識的一個(gè)載體。這為學(xué)者深入了解、確定有無誤讀、進(jìn)而開展有根據(jù)的批評和評價(jià)創(chuàng)造了條件。
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現(xiàn)在法學(xué)界的引文和引證比多年以前好得多了,但從我的閱讀來看,許多人對為什么要引證卻并不明白。現(xiàn)在許多人引文大都是馬恩、或小平同志的語錄,或者中央的決定等等。這種引文當(dāng)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但大量文章的引文都局限于此,就反映出許多問題。這種類型引文(包括對一些國內(nèi)外著名學(xué)者的引證)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當(dāng)作真理或結(jié)論來引用的,而不是作為論證過程或論點(diǎn)的必要組成部分或輔證出現(xiàn)的。一旦引文,似乎作者的觀點(diǎn)(如果還有作者的觀點(diǎn)的話)已經(jīng)穩(wěn)操勝券。這種引文方式就是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分析的中世紀(jì)對亞理士多德等人的著作的引用,[6]真理似乎已經(jīng)有了終結(jié),而不是為了在前人的或他人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這也是為什么法學(xué)刊物上引文多于觀點(diǎn)引證的癥結(jié)所在,其實(shí)即使是真理,也不必定要引文字,為了簡潔完全可以只引觀點(diǎn),這與引中國古代先哲不同,因?yàn)樗麄兊脑捯呀?jīng)很簡潔了)。這種引文風(fēng)格還反映出實(shí)際上法學(xué)界本身就沒有遵循“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其實(shí)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法律)上人人平等”的觀點(diǎn)。在他們的眼中實(shí)際上看到的是作者的話語,而不是作者的話語。其實(shí)法學(xué)和其他學(xué)界都有一些“小人物”作了不少有價(jià)值的研究或其中有
一些有價(jià)值的觀點(diǎn)和發(fā)現(xiàn),但很少被引證,有些人甚至完全抄了人家的觀點(diǎn)也不加引證。似乎引了這些人,人微自然就言輕。這種非學(xué)術(shù)化的引證實(shí)在反映了法學(xué)界存在的嚴(yán)重的非學(xué)術(shù)化傾向。在此,我并非批評法學(xué)界的人們都是有意搞非學(xué)術(shù)化,也許多數(shù)人確實(shí)是認(rèn)真的,只是大家都如此行為,又不理解為何這樣行為,那我也依葫蘆畫瓢吧;久而久之,習(xí)慣了,不感覺到這是個(gè)問題,這變成了另一種“規(guī)范”。這種“規(guī)范”延續(xù)至今,恰恰反映出法學(xué)界問題的嚴(yán)重性。期間,許多文史哲論文中也曾有這種傾向,但改革開放以后,這些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很快就恢復(fù)了比較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引文引證規(guī)范。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有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而法學(xué)界,長期以來沒有這個(gè)傳統(tǒng),所以建立的“規(guī)范”至今沿用。這才是最值得警醒的問題。
由此可見,引文和引證在學(xué)術(shù)論文和著作中有極其重要的多重實(shí)際功能,它并不只是體現(xiàn)了作者嚴(yán)肅認(rèn)真、有根有據(jù)、或尊重他人成果等抽象的精神性的因素,也不是為了使文章象文章、著作象著作[7]—否則的話,怎么理解有些大學(xué)者的某些論文也沒有什么引文和引證?引文和引證,在一定意義上,并不只是一個(gè)機(jī)械的程序或中國人所理解的形式,而是一個(gè)斟酌思考的結(jié)果,盡管這種斟酌思考并不總是、也不必是清醒的—否則的話,我們的一切文字都需要指出出處。因此,引文是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化中除了嚴(yán)格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批評之外的一個(gè)重要的組成方面。
就學(xué)術(shù)本土化而言,其實(shí)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化是學(xué)術(shù)本土化的一個(gè)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化,就不可能形成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和流派,不可能形成學(xué)術(shù)共同體,學(xué)術(shù)本土化也很難形成。
但是,學(xué)術(shù)本土化還具有它自己的意義。這一目標(biāo)的提出,在我理解是與中國學(xué)術(shù)從“熱”走向成熟的一個(gè)標(biāo)志,它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國學(xué)者不滿足于80年代對西方理論和思想的一般地和簡單地搬用。這也是中國人要在學(xué)術(shù)上以自己的身份走向世界的雄心的一個(gè)體現(xiàn),不滿足于只能被表現(xiàn),而是要自我來表現(xiàn)。這是我們幾代中國學(xué)者的努力目標(biāo)和理想。
就法學(xué)界來說,如何本土化。我國的法學(xué)不同于許多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學(xué)科,它們有一個(gè)相當(dāng)久的傳統(tǒng),有自己的命題、范疇、概念和語匯;目前的中國法學(xué)則不同,它的幾乎全部范疇、命題和體系包括術(shù)語都是20世紀(jì)以后才從國外進(jìn)口的,與中國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有較大差距。1949年以后,盡管法學(xué)沒有被取消,但法律被視為政治的附屬物(政法),不適當(dāng)?shù)貜?qiáng)調(diào)法學(xué)和法律的工具性,法學(xué)更缺乏學(xué)術(shù)的傳統(tǒng)。如何實(shí)現(xiàn)法學(xué)的本土化?已經(jīng)有許多學(xué)者在一般意義上指出,要注重研究中國問題,這是解決學(xué)術(shù)本土化的出路。但這還不夠。我同意梁治平的意見,不能僅滿足于以西方的理論框架、概念、范疇和命題來研究中國,因?yàn)檫@樣弄不好只會(huì)把中國人的經(jīng)驗(yàn)裝進(jìn)西方的概念體系中,從而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文化殖民的工具。我們應(yīng)當(dāng)注意在研究中國的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上,總結(jié)中國人的經(jīng)驗(yàn),認(rèn)真嚴(yán)格地貢獻(xiàn)出中國的法學(xué)知識。
具體說來,在目前,我認(rèn)為,除了注意研究中國問題外,我們這一代學(xué)人還應(yīng)當(dāng)特別注意不要為我們的學(xué)科所限定,應(yīng)當(dāng)注意交叉學(xué)科的法學(xué)研究。所謂交叉學(xué)科,也并不是要事先確定學(xué)科,而是根據(jù)對研究的問題的對象需要來豐富擴(kuò)大自己的知識,不讓自己的學(xué)科把我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限定死了,而是以一個(gè)多面手或通才的眼光來研究中國的法律問題。我認(rèn)為這可能是法學(xué)本土化的一個(gè)道路。因?yàn)槲覀儸F(xiàn)在的知識體系結(jié)構(gòu)、學(xué)科劃分基本是西方的,是西方近幾百年,特別是勞動(dòng)分工、職業(yè)化、專業(yè)化的產(chǎn)物。但世界并不就是如同這些學(xué)科那樣嚴(yán)格劃分的,學(xué)科和知識或世界之間并沒有一個(gè)嚴(yán)格精密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世界是一個(gè)整體,社會(huì)活動(dòng)是一個(gè)整體,知識也是一個(gè)整體,各學(xué)科都是你中有我我中你,從學(xué)科角度看,同一個(gè)行為中有不同學(xué)科的因素,因此學(xué)科只是人們便于研究學(xué)習(xí)而逐漸形成的一種觀察理解的角度和途徑。它很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縛。從古代來看,無論中外學(xué)者都不是那么嚴(yán)格限定于某個(gè)學(xué)科領(lǐng)域,相反他們的這種泛學(xué)科或“交叉學(xué)科”的研究使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沒有嚴(yán)格分科但極為博大精深的知識,后來才逐步形成學(xué)科。如果我們也堅(jiān)持這一傳統(tǒng)或態(tài)度,也許我們會(huì)在實(shí)踐中逐步形成一些新的學(xué)科領(lǐng)域,綜合一些方法,形成一些具有特色的本土化的領(lǐng)域,提出一些具有本土特色同時(shí)有普遍意義的概念、范疇和命題。我相信對世界可以有多種話語系統(tǒng)解釋,因?yàn)橹袊嗽谩暗馈薄ⅰ皻狻薄ⅰ袄怼边@樣的概念和相關(guān)命題同樣解說、理解了西方人用“物質(zhì)”、“精神”、“主觀”、“客觀”之類的概念解說和理解的世界。我們今天不想DD也沒有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可以依據(jù)DD以中國傳統(tǒng)的諸如“禮”“法”之類的概念命題將中國法學(xué)本土化。但中國昔日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至少啟示我們:學(xué)術(shù)不只有一種模式、一種構(gòu)架。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嚴(yán)格的法律、經(jīng)濟(jì)、政治和文化之分別,這些學(xué)科只是對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定義,而不是世界的原本分割。因此這種分割不是那么“理性的”,相反是“非理性的”“專斷的”(不具貶義)。如果我們不為我們受教育的學(xué)科或定位的學(xué)科所限制,采取一種寬泛的交叉學(xué)科研究,我們也許可以在法學(xué)本土化上走出一條新路。
事實(shí)上,近年不少中青年學(xué)者實(shí)際上是在以問題或研究對象為中心,而不是以學(xué)科為中心在進(jìn)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梁治平研究的法律還是文化或是社會(huì);樊鋼和林毅夫研究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實(shí)際上觸及了大量的政治和法律問題;汪暉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研究搞了一個(gè)章太炎和清末思想的知識考古學(xué)。這表明我們許多人實(shí)際上都是在打破學(xué)科的界限,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在跨學(xué)科地追求知識,而且我們互相對話、互相啟發(fā),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一些小的松散的學(xué)術(shù)群體。我們有西方文化帶給我們的學(xué)科包袱,但我們沒有西方人那么重;我們處于一個(gè)社會(huì)的巨大變革之中,我們不需要那么急迫地尋求自己的學(xué)術(shù)定位;我們有中國的現(xiàn)實(shí)和歷史;而且又正在出現(xiàn)一批很有潛力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這一切有可能使我們的學(xué)術(shù)本土化,包括法學(xué)的本土化,即形成中國的學(xué)科,提出中國的學(xué)術(shù)命題、范疇和術(shù)語,形成中國的學(xué)術(shù)流派。說句并非完全是玩笑的話,也許一不小心,世界就發(fā)現(xiàn)中國就出了一個(gè)世界級的大學(xué)者,或一個(gè)有世界影響的學(xué)派。不小心,在此并非調(diào)侃,因?yàn)槲蚁嘈砰L期積累,偶然得之;因?yàn)槲蚁嘈艢v史上太多偶然性、隨機(jī)性,雖然不是一切努力都沒有結(jié)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結(jié)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結(jié)果,更不可能有一個(gè)確定的結(jié)果。“‘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8]
注釋:
[1]據(jù)《中國期刊總目錄》,全國法律類的核心期刊有31種,法律類專業(yè)期刊有133種;上海的《民主與法制》這樣的社會(huì)性期刊被列為核心期刊,而《比較法研究》,這份無論的水平還是編輯水平都屬于國內(nèi)一流的學(xué)術(shù)雜志卻屬于非核心期刊。當(dāng)然,我并是在貶低《民主與法制》(我并不是擔(dān)心被控侵犯該雜志的名譽(yù)權(quán)),而是批評那些確定法律核心刊物的人。新晨
[2]由于某種誤解和濫用,人們不僅常常過分強(qiáng)調(diào)所謂的內(nèi)容,而且常常將形式和內(nèi)容視為絕對對立的。其實(shí),在哲學(xué)上看,沒有形式就沒有內(nèi)容。一張桌子和一張椅子的“內(nèi)容”都是一樣的,都是木頭,而之所以可以將之區(qū)別開來,就在于其形式。
此外形式和內(nèi)容都是人們?yōu)榱搜芯繂栴}、探討問題的便利而作出的主觀上的區(qū)分,形式性的可以具有實(shí)質(zhì)性的意義,例如法律上程序就是具有實(shí)質(zhì)性意義的。
[3]近年來,我曾遇到一些不滿意法學(xué)研究現(xiàn)狀、自己作學(xué)問相當(dāng)認(rèn)真的學(xué)者,但讀他們的著作卻感到極為艱澀,一些完全自創(chuàng)的概念、命題以及由此生發(fā)的論證,令人無法接近,不知該從何處下手批評(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包括欣賞)。
[4]這并非言過其實(shí)。知識的門類科目其實(shí)也只是一種大致的劃分,邊界并不確定;而現(xiàn)實(shí)中的問題常常不是按照學(xué)科門類劃分的。世界與我們的知識劃分并不是對應(yīng)的,我們的知識并不是、也永遠(yuǎn)不可能成為世界的精確畫圖。
[5]見,波斯納:《法理學(xué)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頁532以下。
[6]福柯,《作者是什么》,集于《最新西方文論選》,王逢振、盛寧和李自修編,漓江出版社,1991年,頁449-450.
[7]對這一問題的更為深刻的社會(huì)學(xué)解構(gòu),見福柯《作者是什么》一文。
[8]《史記?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