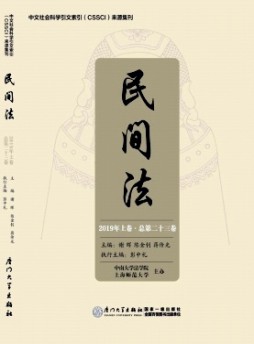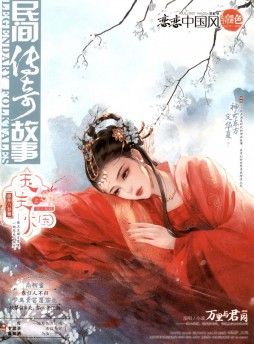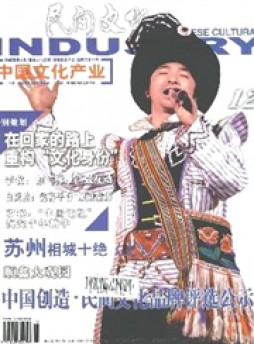民間音樂文化價值體現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間音樂文化價值體現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民間音樂文化研究中,民間音樂文化的價值體現一直是眾多學者所關注的內容之一。在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語境中,民間音樂文化與“非遺”保護的話語可謂難解難分,而作為一個文化分類和價值判斷的概念,“非遺”是否能詮釋民間音樂文化的價值?民間音樂文化究竟有怎樣的價值?這些價值怎樣才能在“非遺”保護語境下服務于民眾的現實生活中?這些都是有待探討的問題。事實上,眼下很多學者們都在忙于按照“非遺”標準對各種民間藝術進行打分和評估,做著流于表面的“非遺”保護工作,而對于民間音樂文化的價值產生問題,在觀念上認識模糊,在研究上流于形式,在學術上處于浮躁。而民間音樂文化所具有的被民眾所認同的內在價值,恰恰是其代有傳承的根源。只有對民間音樂文化內在價值進行深入探討研究,形成對民間音樂文化的真實認識,才能使對其保護的方法和途徑成為可能。本文以豫南皮影戲為例,從價值論層面入手,以探討民間音樂文化內在價值為主要視角,倡導在科學研究中關注民間音樂文化內在價值的保持與新生,以求促進民間音樂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關于“價值”一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描述:“物的效用,使那物成為一個實用價值”,“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就這個關系說,各個商品都是同種商品的平均樣品……一種商品的價值,對于他一商品的價值比例,等于一商品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對于他一商品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比例。”又說“當作價值來看,一切商品,都只是凝固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
看來,馬克思并沒有就“價值”一詞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和概念,并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者之間似有混淆。《現代漢語詞典》關于“價值”的定義:“價值:①,體現在商品里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的大小決定于生產這一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多少。不經過人類勞動加工的東西,如空氣,即使對人們有使用價值,也不具有價值。②,積極作用:有價值的作品\這些資料有很大的價值。”[2]545可以看出,概念①是一個明顯來自于《資本論》的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應該說,價值并非只是“商品”所特有的東西,如果只討論“商品”里的價值,對“價值”一詞的解釋無疑是不完全的,是有失偏頗的,甚至所得出的“價值……是勞動”的判定是錯誤的。因為這個判定,使生活中的“價值”完全不同于經濟學中的“價值”而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卻正是生活本身。定義②:“積極作用”讓我們似乎感覺到了“價值”的真容,但是卻是霧里看花,無法準確把握其真正含義。那么,該如何界定“價值”的定義呢?簡而言之,事物的有用性,就是該物的價值,即一種事物所具有的,能夠滿足另一種事物的某種需要的可能性。這是“價值”在物質世界的最基本的定義。因為在物質世界里,一切的物質、生命、現象、思維等都可以被稱為事物。因此,物的能滿足某種需要的可能性,即是該物的價值。就這個意義上講,豫南皮影戲的價值在于,一是滿足豫南民眾某種生活、精神需求的可能性;二是滿足社會文化研究需求的可能性。這兩個方面應該是豫南皮影戲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體現。
豫南皮影戲在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保護對象之后,對其進行研究的學者紛至沓來,有從事藝術學的、歷史學的、民俗學的、人類學等等,對豫南皮影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對豫南皮影戲的生存背景、音樂本體、還愿儀式、文化生態等方面做較為全面研究的(曹玲玉《河南羅山皮影戲音樂調查研究》、王傳厲《羅山皮影戲家庭愿戲的調查研究》),有對其唱腔的各種板式以及各種板式是如何連接的介紹(曾凡廣的《羅山縣皮影戲音樂研究》,耿玉琴的《豫南西調“皮摔”戲音樂唱腔初探》,付玉蘭的《豫南“皮摔”東調音樂唱腔牌子初探》);有對其影人的藝術造型、色彩運用、制作工藝的介紹(方丹的《羅山皮影造型、色彩及文化內涵研究》,劉松的《人、神和自然的交融—羅山皮影造型藝術分析》,蔡森林的《羅山皮影造型形式美初探》)等。可以看出,學者們對豫南皮影戲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有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工作,有學者在某些方面對豫南皮影戲給予了不厭其詳的介紹和耐心細致的分析。但作為“局外人”的學者、社會活動家等,在研究的同時也附加給了豫南皮影戲一定的觀念、評論甚至是商品化的包裝,大部分學者開門見山地指出豫南影戲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研究價值,這正是大多數局外研究者的心態和觀念。事實也正是如此,豫南皮影戲的價值毋庸置疑,但作為局外研究者通常是站在藝術價值、審美價值等層面上來看待和研究這些價值。當然,我們決不是反對對豫南皮影戲進行這些研究,如對其歷史淵源的研究、唱腔的研究、音樂調式調性研究、劇目文學價值研究、影人造型研究、影人色彩運用研究等,相反地,這類研究非常重要而且必要。一是了解豫南皮影戲的藝術魅力、審美價值;二對當下音樂、美術、文學等的創作提供借鑒;三是商業化的包裝演出,提高了藝人們的收入;四是與當地旅游業相結合,擴大了影戲知名度,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等等。這也是目前大多數民間音樂品種在研究與保護方面的做法和結果,即重在其外在價值的實現。事實上,民間音樂文化的外在價值只是“末”,其內在價值才是“本”。豫南皮影戲的內在價值在于它的生活價值、民俗價值、信仰與觀念價值,這是它的根本價值,是我們要重點探討的問題所在。
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豫南羅山皮影戲,自明代中葉傳入豫南地區,[3]60歷經400多年的歷史風雨,是什么力量使它綿延至今并在豫南大地久演不衰,這顯然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結果。幾百年來,豫南皮影戲一直存在并延續著自身傳承和發展的自然模式,這種自身傳承和發展的自然模式雖經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但始終能在其存在的社會和歷史時空中發生作用,也就是民眾所認可和在生活中實際使用的價值。傳承人李世宏以文字形式總結了豫南皮影戲的起源傳說,在記載的10個傳說里,有6個故事與中國古代皇帝而且大多是太平盛世的皇帝有關,如漢文帝劉恒、漢武帝劉徹、漢元帝劉爽、隋文帝楊堅、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其余4個故事則是描述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之時,皮影戲卻在豫南絕處逢生、異地開花。[4]通過其產生的多種傳說,可以看出影戲在豫南民眾心中的地位:一是崇拜和敬仰。對于草根百姓而言,古代皇帝都是天之驕子,無疑是人神之合體,抑或說就是神的化身,在豫南多神信仰體系中,皇帝特別是盛世明君亦是民眾信仰的神靈,由于與這些神靈的密切關系,使皮影戲更具有了神秘和神圣的意味。二是能帶來福音福祉,中國傳統農耕時代,對鬼神的崇拜成為對很多自然現象進行合理解釋的一種常態,侍奉好所有鬼神,使他們賞心悅目,則能帶來平安吉祥,皮影戲便成為鬼神崇拜的一種很好載體,成為“以虔敬所有超自然的神為第一目的的藝術。”
演影戲、看影戲都可以帶來風調雨順、家道興旺、升官發財、福祿永居。由于皮影戲的這種神圣地位,使皮影藝人也具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筆者在拙文《淮上“卷戲”的形成與音樂板式類型初探》中曾談到皮影戲源自唐代的講唱寶卷,最初皮影戲的演唱內容多是宗教故事,其劇本稱作“卷”,唱影叫“宣卷”,演出用的燈稱為“海燈”,都是佛教信徒的習慣,與講唱寶卷相似。演出前還要舉行宗教儀式,演員必須凈面漱口,焚香念贊,然后才可表演。演出多以酬神還愿為主,且演員兼有某種宗教職業身份。[6]可以看出,皮影藝人同其他專業民間藝人不同,他們不僅不是被人鄙視的“下九流”,而且他們還有比一般大眾高的地位,且常常具有雙重身份。早期是宗教職業和皮影藝人的雙重身份,現在是農民和皮影藝人的雙重身份。他們忙時務農,與周圍人身份相同,平起平坐;閑時受邀演戲,收入不菲,事主對其奉若上賓。不管是神圣的宗教職業還是有手藝的皮影藝人,在農民心中都是能與鬼神溝通和對話的人,甚至將其視為演出場合的神,都是值得崇拜和尊敬的人。在這一點上,豫南地區似乎一直延續著遠古時期民眾對巫覡的認識態度。那么,作為一個皮影藝人,在他們心中自然也一直有這樣的情愫——傳承皮影戲是一種榮耀,讓自己的“絕活”流傳于世是一種光榮,由此形成了一種開放式的師承方式:祖傳家授(血緣傳承)和廣招門徒。祖傳家授是為了家族榮耀的傳承自不待言,廣收門徒的師承方式只要舉行一個約定俗成的簡單、靈活的拜師儀式,首先要找一名引薦師引薦。找引薦師的作用有三:一表達對師父的景仰,二表示師父技藝超群,三顯示徒弟通情達理,使師父產生好感。其次,舉行拜師儀式。儀式上邀請見證師,目的是向江湖同仁宣告師徒關系的確立,同時也明確師徒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最后,徒弟學藝三年,期滿若出師即可自立門戶,行藝江湖。
豫南皮影技藝的傳授沿襲著傳統的口傳心授模式,師父有空時會教徒弟戲詞、操桿技巧、鑼鼓點子,徒弟觀察、體驗師父的一言一行,觀察學習師父的表演、唱念以及與鑼鼓管弦的配合,在跟師父跑碼頭的過程中學會應付各種狀況。另外一種學習技藝的方式叫“盤道”,這種技藝學習的方式似來自于佛教徒的辨經論戰。盤道先由徒弟之間進行,雙方藝人或演或唱或念,拿出自己的獨門絕活,你來我往,各不相讓,幾個回合下來,若還難分高低,則有師父們上陣盤道切磋,這是雙方徒弟開闊眼界、增長見識的大好時機。常言道“學藝不如偷藝”,徒弟們往往在師父盤道切磋的過程中,學到很多平時難以習得的技藝和規矩,悟性高的徒弟能在幾次盤道切磋中“偷”得雙方師父的絕活。在廣收門徒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一提,那就是“師訪徒三年”,這是豫南皮影藝人中流傳極廣的一句諺語。即徒弟已經舉行拜師儀式,在學徒期間,若認為師父藝不如人,可以謝辭師父,另謀他處學藝;若師父認為徒弟資質太差,學皮影戲沒有前途,則可勸退徒弟。師徒名分既定也不妨礙各自的來去自由。因此,豫南皮影戲的師徒之間是一種十分和諧的關系。羅山縣周黨鄉皮影老藝人岳義成老師傅,年已八旬,徒子徒孫遍及羅山諸鄉鎮,老人每每提起,總是充滿了自豪和驕傲,弟子們提起岳師傅也是崇敬有加。豫南羅山皮影戲列入國家非遺名錄后,也指定了“傳承人”,希望通過保護這些傳承人身上的技藝,進而使皮影戲得以更好傳承。事實顯示,傳承人能做的只是把皮影雕刻手藝和雕刻成品變成旅游商品換取經濟利益,或者是表演給上級領導、調查者、游客觀賞。
這也是目前大多數民間音樂品種保護的做法與結果,并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這種做法并不能體現皮影戲作為情感符號在豫南民眾中發揮其組織和諧生活的作用,這是因為皮影戲的傳承特別倚重于傳承者上述的傳承觀念和流傳區域的民眾信念,當國家政府對他們中的個人的角色另有期待,他們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角色去適應新的要求。事實上,在指定傳承人以后,豫南皮影戲的那些箱主們在心理上或者說在身份認同上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被指定為傳承人的箱主,大約有兩種心理狀態,一種是誠惶誠恐,感覺自己責任重大,又不知如何做才能盡到傳承人的責任和義務,由此產生一些焦慮;另一種是驕傲自大,認為自己技高一籌,勝人一等,本來很樸實的皮影藝人,卻平添了幾分驕氣。我們必須注意到,目前在豫南羅山縣60歲以上的皮影藝人就有50多人,能登臺的約49人,60歲以下的有數十人,常年演出的皮影戲箱有20多擔,且都是民間藝人的自發組織,政府認定的傳承人只是他們中的少數,但是應該說,每一位藝人都擁有著或者說都體現著不斷傳承的、延續的和完整的皮影藝術的價值,豫南皮影藝術之所以呈現區域性的整體特征,正是因為我們能夠從每個藝人的生命中看到這種藝術的整體性。
“非遺”語境下,政府部門、研究者或保護者總是站在一種超然的和“客觀”的立場來認識和界定皮影藝術,那么,“非遺”是否真正揭示了皮影藝術的價值實質,同時,用“遺產”的概念,將民間草根藝術——豫南皮影戲同其他有形的古跡、文物等等同視之,一方面強調了豫南皮影戲的某種重要價值,但同時也暴露了對皮影藝術內在價值的實現缺乏信心。事實上,皮影藝術幾百年來得到不斷地創造、傳承和使用,是作為一種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儀式表演、民眾觀念的呈現,這種認識到了一個應該回歸的時候了。據《羅山縣志》,羅山皮影戲是明代中葉傳入羅山。流行于彭新、鐵鋪一帶,而后擴及到青山、澀港、周黨、定遠等地區,逐漸遍及全縣。幾百年來一直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至今在豫南人民的社會生活中仍然十分活躍,如果說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記載,那么從那時起,時間的車輪在21世紀業已轉過了十余年,這期間約40年的時光流逝中,傳統的音樂藝術樣式在不斷地衰弱、沒落,甚至謝幕,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加以干涉,企圖使之保存、傳承。而據調查,皮影戲卻在豫南越演越火,頗有市場,眾多的民間皮影戲班常年演出于民間鄉鎮村落,活躍在人們的鄉俗禮儀生活中,各大廟會時期和春節前后,事主請戲需要提前一個月預約。皮影戲為誰而演又因何而唱?豫南農村有著濃郁的民間多神信仰氣氛,家家廳堂都會張掛以“祖宗昭穆神位”為主的多種神祗畫像,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習俗滲透于民眾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時,豫南地區自古就以“禮”為本,鄉俗禮儀活動豐富而完整,酬神了愿的民間習俗,推動著皮影戲作為“酬神”過程中重要內容的鄉俗禮儀儀式,酬神戲的演唱又使皮影藝人的祖師信仰和民眾的多神信仰得以延續和加強,其間多向度的關系構成密切互動,成為豫南皮影戲延續的內在驅動力量。
豫南民間鄉俗禮儀活動類型多樣,但都與民眾生活和民俗信仰息息相關,有明顯的功利性。如祈雨活動、祭祖活動、喪葬禮儀、婚嫁還愿、得子還愿、升學還愿、祛病還愿、起房蓋屋、母牛生犢等喜事還愿,也折射出羅山深厚的農耕文化底蘊。在這種功利性的鄉俗禮儀和民俗信仰觀念里,酬神了愿成為民眾共有的心理認同,皮影戲成為民俗生活中酬神了愿的最好媒介和載體,同時皮影戲的演唱進一步強化了民眾的多神信仰。如對觀音菩薩、王母娘娘、土地爺、龍王爺的信仰,表現在廟會、安土神、祈雨等禮俗活動中,這是以神為交往對象的禮俗活動;對祖先、家族新逝者的追悼,表現在祭祖、喪禮、遷墳等禮俗活動中,這是以鬼為交往對象的禮俗活動;在第三種看似以人為交往對象的禮俗活動,如婚禮、慶禮(各類慶典)、賓禮(接待賓客)中,實際上包含著對更多神靈的信仰。如生子禮、滿月禮對送子娘娘的信仰,壽誕禮對壽星神的信仰,賀起房蓋屋對魯班爺的信仰,賀大病痊愈對華佗的信仰等等,像賀參軍、賀上大學這類沒有具體神明可信仰的,那就是各路神靈一齊信仰的結果。因此每逢諸如此類的喜慶事,必唱影戲以示祝賀,如賀上大學在戲臺前掛上這樣的對聯:“金鼓齊鳴高科及第,笙簧同奏喜戲酬神”,橫批“金榜題名”,如果是賀參軍,則把對聯稍作變動,即“金鼓齊鳴報國從戎,笙簧同奏喜戲酬神”,橫批“保家衛國”,此類謂之“喜影”或“喜戲”;如遇盼兒求女、求福祈壽,祈求官運、財源亨通等事情,事主要在神明前發下誓愿,事后以影戲還愿,謂之“愿影”或“愿戲”。如因盼兒求女而許愿者,唱“送子娘娘領金銀,三蕭娘娘得金銀……”。如因病許愿者,則唱“華佗師傅收錢紙,小鬼小判得金銀……”。求神果報之后則要以影戲還愿,謂之“報神”……由此可以看出,地處大別山區的豫南村落社會、鄉民生活里,皮影戲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其功能滲透在民眾生活的每個角落,融化在每個鄉民的血液里。一擔擔戲箱年年歲歲行走在大山深處、淮河兩岸,為鄉民提供著精神的慰藉滿足著心靈的訴求,體現著民眾對豫南皮影戲的欣賞、依戀。還有更多的文化認同和信仰的力量,這種文化認同和信仰的力量就隱含在交通不便、相對封閉的豫南鄉鎮村落至今所保留的豐富和完整的鄉村禮俗傳統中。這種鄉村禮俗活動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就是敬神,它以娛神為旗幟,廣納民間文娛活動內容。名為娛人,實則娛神。將娛神與娛樂相糅合,使宗教生活、民俗生活與傳統民俗文化以及皮影戲有機結合在一起,使鄉村禮俗成為皮影戲的重要演出場合和賴以生存的沃土。除卻民眾的多神信仰是豫南皮影戲目前得以傳承、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還有皮影藝人的祖師信仰是另一支重要的信仰力量。藝人講究“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豫南,皮影箱主家都供奉有“供奉樂王教主之神位”的牌位,藝人家也都供奉有“樂王教主神位”。每逢農歷三月十六晚上,箱主就會為樂王教主上供、焚香、守夜,直至第二天樂王教主生日到來,屆時箱主帶領全班人馬舉行隆重儀式,祭祀祖師爺誕辰。豫南皮影藝人認為,祖師信仰是獲得更多臺口、平安順利演出的保證。
以上所述豫南皮影戲的師承方式、觀念和民眾多神信仰模式可看作是豫南皮影戲的內在價值的主要方面,它是人們相互交流、心理溝通的符號,其開放性也表現在內外價值的相互關聯。豫南皮影戲從形成之初,就擔負著娛人娛神的使命,在其流傳過程中,既重視其代表的神靈信仰,也重視作為娛人部分的藝術價值。其戲劇表演和酬神功能同為皮影戲的內在價值,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至70年代驟然改觀,“破除封建迷信”及大規模的深入城鄉每個角落的“破四舊”運動,迫使皮影戲轉化為單一的娛人功能。為了吸引更多人看戲,藝人們在影人雕刻、色彩運用、唱腔改良、表演技巧等方面經歷了努力運作,使藝術表現、審美意趣成為這一時期皮影戲的內在價值,人們會趕幾十里山路只為看一場皮影戲。歷史進入80年代末,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又一次重大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經濟的發展決定了文化走向,民俗文化、民間信仰在被長久抑制后有了強勢回潮。豫南民眾信仰的多路神明又回歸到了廳堂和廟宇之中,與鄉民的信念再次緊緊聯系在一起。民眾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與供奉的神明相聯系,遇壞事要請神靈保佑轉好,有好事要酬謝神靈的幫助。酬神的最直接方式就是給神唱戲,皮影戲這種輕裝易行、費用低廉、早期就有娛神功能的形式,最適合農戶請進家門來酬神了愿。于是,皮影戲的功能又悄然發生了改變,由娛人轉回到了娛神,民眾的信仰及觀念成為其內在價值,表演藝術價值外化。這是一種內外價值的互相置換。豫南皮影戲功能轉型迎合了時代轉型的契機,它深深植根于民眾生活觀念之中。當我們對皮影戲的保護僅停留在第一個層面——藝術欣賞層面時,是以頭腦中經驗藝術世界的模式為參照系而完成對皮影戲表面含義的理解,而皮影戲的意蘊不可能僅止于表面。
因此必須進入到第二個層面——文化層面。在這個層次,我們是以皮影戲形成、傳承的背景和文化歷史傳統為參照系,通過對影人造型來源、唱詞、音樂、劇本等的具體分析而體會皮影戲的深層含義,把握住戲中的意象。但是,即使是在這一層次上,作為所謂“局外人”的我們也還不能完全領悟皮影戲的深層意蘊。只有當我們由文化層次進而深入第三層面——隱喻層面,才能最后完成對其意蘊的真正領悟。“隱喻”在豫南皮影戲的演出、傳承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豫南,人們用皮影戲作為酬神了愿的載體,皮影演唱又進一步強化民眾多神信仰,皮影戲與民眾信仰構成一定隱喻關系的意象,故而擁有了真正強烈的表現力。置于民眾信仰(特殊參照系)中的皮影戲(隱喻結構),此二者相互折射出一系列暗示,在復雜的隱喻、暗示之間,憑借心靈所具有的超乎理性經驗的直覺感悟能力,使二者建立起一種平行的對應關系,最終完成對皮影戲演唱意蘊的領悟。“非遺”要保護也許應該是這第三層次,即民眾對待民間音樂文化的觀念,使其內在價值得到保護與新生,這可能才是真正的“非遺”意識體現,是一種活態保護,是從根源上的保護,離開了這種保護和民俗生活的滋養,民間音樂文化也許只能逐漸走向寂滅和枯死。
作者:郭德華 單位:信陽師范學院
- 上一篇: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范文
- 下一篇:民族音樂文化的獨特審美體驗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