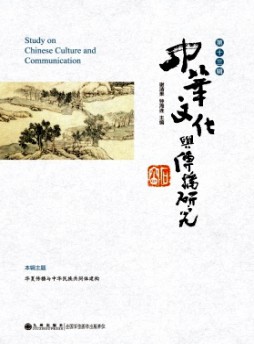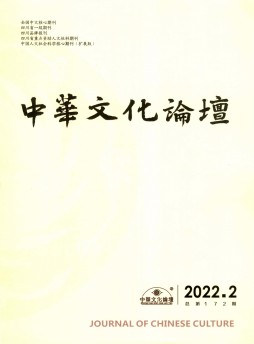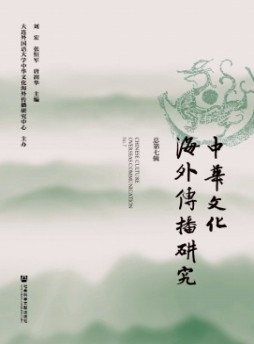中華文化一體多樣性及其現實意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華文化一體多樣性及其現實意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前言
21世紀來臨后,中華民族自身以及世界和東亞的發展形勢,給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光輝傳統的民族,帶來了更為有利的發展契機和更為美好的社會前景,我們民族現在是朝氣蓬勃,奮發向上,面貌變化一日千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中華民族如何加強自身的凝聚力和團結,這對于我們民族實現繁榮和強盛,具有重要意義。從學術思想的視角,回顧我們民族注重團結和凝聚力的歷史傳統,了解與此有關的觀念,對一些學術問題進行必要的辨析,我認為對于加強我們中華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團結是有裨益的。
在談論"中華"、"中華民族"或者與其有關的許多問題的時候,我們馬上遇到的基礎難題就是"民族"這個概念。1903年,梁啟超把瑞士-德國的政治理論家、法學家J.K.布倫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這個詞從此成為20世紀初期以來漢語中很常用的一個詞。它經常與"國家"和"種族"成為互相替代的同義詞。正因為這個詞如此廣泛的用法,在學術研究中我們就遇到了很多麻煩。為了遵循學術研究的基本邏輯,首先就需要對"民族"這個詞同"國家""種族"這兩個詞的意義的相似與差異,進行比較嚴格的辨證。
布倫奇利對于民族概念有嚴格的定義。他認為"民族"作為一個實在的研究對象,這個概念具有8個基本規定性:根源上同居一地,根源上同一血統,同一人種生理體質,同一語言,同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風俗,根源上共同進行經濟社會活動。我們可以看出,布倫奇利的定義具有明顯的形而上學的僵硬性,他沒有把民族作為一個處于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動、不斷相互發生關系的歷史事物,而把它個體靜態化了,因而,這個定義也就不能完全符?quot;民族"的實際狀況。但是,布倫奇利的規定性對于把握民族之間進行區分的特征,有一定的意義。例如我們中國人講"同文同種"(文字和人種),或者講"黃皮膚,黑頭發"(人種),或者講"長江黃河"(居住地),或者講"龍的子孫"(宗教、風俗),等等。這些話語都是對布倫奇利定義的某個或者某些規定性的實際說明。
今天,當我們使用"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時候,大體是在以下三個意義領域和語境中。一是在談論中華民族這個大的共同體作為國家、作為文化、作為民族的整體本身的存在、成長、發展等問題的時候,二是在談論我們這個民族國家與外部的關系(國際關系)的時候,或者國際情況對我們的影響的時候,三是在談論我們民族內部的關系和問題的時候,尤其是在談論漢族和其他民族(所謂少數民族)的關系的時候。
我們今天談論中華文化,基本概念是民族文化,即把中華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來談論。也就是說,我們"中華民族"在文化上是一個歷史形成的、具有很強的內部凝聚力的共同體。
二,由多生一的建構:"族群"與"民族"的同一
中華民族作為一鼉哂瀉芮康哪誆磕哿Φ墓餐澹竊誄て詰納緇嶗販⒄構討行緯傻摹?br>在這里,我們必須強調"民族"概念與"族群"概念的不同。實際上,"民族"(NATION)概念是一個現代政治文化概念,在民族的意義上,人們經常講"民族獨立"、"民族國家"等等。而族群(ETHNICGROUP)概念,則只是在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探討不同類型的人類族群的社會歷史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強調它們之間的差異和個性(特殊性)。所謂"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族群"組成的民族的說法,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話語,但它并不是嚴格的學術話語。
從古代以來,在亞洲東部這塊大地上,星羅棋布地生活著許多人類族群,從最北的黑龍江到最南的深圳、香港、澳門;從最東的東海海面、臺灣到最西的青藏高原,都有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這一點。也就是說,中華文化是在整個中華大地上共同發生的。當代學者把中國上古文明分為七個、或者八個、或者六個區域,一般認為主要的區域是黃河中游區,黃河下游區,江漢區,長江三角洲區,贛粵區,隴東塞外區。許多族群在自己社會生活的過程中,互相交往,進行經濟活動,也互相通婚,發生著血緣關系之間的融匯。這是一種很普通的社會歷史現象。所以,可以說,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族群是所謂"血統純粹"的族群。如梁啟超所說:"華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來,諸族錯居,接觸交通,各去小異而大同,漸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謂諸夏是也?quot;(《飲冰室合集》第11冊)非本族群的血緣關系與人種的融匯,是人類發展歷史中必然的事情;相反,不融匯、或者強制使其不融匯,則是不可能的事情。
經過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的長期的相互交往,也由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實際需要,許多小的族群(例如氏族)逐步聯合或者經過戰爭被合并,成為族群聯合體,成為一個更大的族群。這種由小到大的聯合或者合并的趨勢,導致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形成了一些區域性的較大族群,或曰"部落",然后就是部落之間的聯合,這是族群聯合體的更高的形式,形成為更大的族群。在關于"中國"的古代傳說中,處于黃河中游和渭河流域的那些族群逐步融匯為一,成為古代的羌人族群,而黃河下游的部族則形成為夷人族群(九夷),在北方有狄人族群,在西方有戎人族群,在江漢地區有古代苗人族群,在其南還有蠻人族群。漫長歷史中這六個主要族群的形成過程,就是中華民族的族群從多向少的整合過程,實際上,這六個族群,還可以進一步被概括為三個大的文化"族團":1,羌戎狄(華夏核心族群的前身);2,夷;3,苗蠻。
我們應該研究整合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對"整合"概念有一個理解。整合是由參與整合的各方面共同形成"普遍化特征"的過程。也就是說,在整合前,各個小族群都有他們不同于其他小族群的許多文化特點(或者特征),正因為這些特征或者特點,它才能作為一個確定的、實際的社會共同體,把自身(或者被其他族群把它)與其他族群相區別。因而在這時?quot;差異"是主要特征,是研究需要考察的主要方面。然而與整合前不同,在整合過程中,無論是以和平的交往方式還是以戰爭的交往方式,族群間開始溝通、來往,開始進行共同的事業(圍繞一件事情共同參與),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通婚,交談對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相互模仿學習,商議或者爭吵,通過上述許多交往手段,對對方進行相互規定,或者參照對方對自己進行自我規定,從內部或者外部,從相互或者自我,進?quot;可交流性"、以至"共生性"的社會、活動、語言、思想建構:即通過各種方式,使得雙方或者多方的相似性和共同性逐步增加,形成一些以至許多共同認可的東西,例如活動的共同規則、共同制度和共同禮儀;語言的可互懂性和可互表達性;共同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共同的風俗和習慣,等等。可以看出,不同于整合前的任何一方的、新的東西的生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人的物質的方面,即通過不同族群間通婚而形成新的人種,它在體質、形貌上必然超出原來族群的已有特征;另一個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思想文化方面,即把各方原有的不同的制度、禮儀、行為方式?quot;通行性"暫且"擱置",但又以它們的全部為文化資源背景,而根據當前現實交往和活動行為的實際需要的迫切性,尋求建構新的制度、禮儀和行為方式,以及與此有關的更為廣泛的新的文化符號系統。一個新的更大的族群的形成,就是以上述新的東西作為自己的人種基礎和文化基礎的。隨著這種整合過程的逐步升級,文化的東西越來越成為主要的東西,它的作用也越來越大,而涉及人的生理特征的人種的東西越來越居于次要地位,甚至于這種族群的整合,可以被直接地稱為"文化整合"。
當然,整合后的(擴大了的)新的族群的體質特征的形成和文化特征的形成,并不是平均地從構成它的原先各個小族群的特征中"抽取"出來的。各個小族群的體質的強弱和文化的強弱,決定著它們的特征在建構新的大族群的特征時的作用和被"吸收"的多少。所以,整合并不可能是"均質的"。例如中華民族的族群特征的鑄定,其文化符號特征,在很大的程度上最初是以吸收"華夏"族群的文化特征為主要內容的。華夏不是一個族群,而是"諸夏"(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泛指起源于北方河渭地區的族群,其首領為黃帝和炎帝。黃帝被古代傳說定為"三代"(夏、商、周)的先祖。在與東夷和苗蠻的交往中,華夏在實力和文化方面,都對它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華夏在這過程中也必然與它們有許?quot;互動",吸收了它們的許多文化要素。這種互動過程,以華夏文化的"普及泛化"為重要內容,它可以說是東夷與苗蠻的"華夏化",但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華夏的"東夷化"和"苗蠻化"。經過漫長的這樣一個過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基本族群樣態就形成了。這就是一個"由多生一"的建構過程。
我們應該理解,這里所說的"一",已經決不是整合前的那些小族群之一所具有的"單一性",而是一個對以前的那些小族群的集合體,即是一個在其中包含?quot;多"的一元體。它包含了以前的小族群所具有的那些適用于地方性的或者個別條件的人種和文化特點,但同時具有溝通已經被置于其中的各個小族群之間的關系、并打破它們的原有界限而成為"通則"的普遍框架。所以,大的族群的"一",不但包含通則的一致和一貫,而且也包含各個小族群原有的被遺留下來的、在大族群中并不通用的、但在地方和小范圍中仍然有效的各種"小"規則。由于這些小規則相對于大的通則來說是很多的,因而它們就是一種仍然活躍著的"豐富性",它們使得那個作為通則的"一"具有實際的具體運行基礎,通則在多樣性的條件下運行,多樣性成為通則的變異和表象,例如龍作為中華文化的普遍性的符號,中國文化被稱?quot;龍的文化",今日炎黃子孫都把自己視為"龍的傳人",這就是中華文化的普遍性("一")的傳統。然而,龍在古代中華族群的圖騰崇拜中,也有許多地方性的多樣形象。在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文物上,龍形飾紋和圖案很多,有的像龜,有的像魚,有的像鹿,有的像豬,具有豐富的多樣性的文化內容。實際上,龍這個普遍性的民族文化符號,包括了許多地方性族群圖騰的特點(參見羅愿《爾雅翼·釋龍》)。當然,在長久的歷史傳統中,龍的形象得到了中華民族這個(單數)大族群的普遍承認,而這就是文化整合?quot;一"與"多"的辯證法。
三、具有豐富內涵的一體文化模式
如果說先秦時期已經形成了中華文化一元化的思想理念基礎的話,那么,秦統一中國,則是從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實際構架上形成中國一元社會的初步舉措的開始。這使得一元的文化得以在現實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逐步落實。
中華文化的一元,不是一個封閉的塊狀實體,而是一個"核心加輳幅"的開放結構。
中華文化的核心,不是一個空間位置的中心點或者中心區域的概念,而是一個以思想理念為中心的多維立體結構。思想理念是整個文化的核心。
在春秋戰國的軸心時代,中華文化以夏文化區為主要區域,經歷了思想理念方面的"百家爭鳴"的多元共存的局面。當時主要的幾種有影響的思想理念,是儒、道、墨、法。其中儒家對后世的影響更為深刻和久遠。儒家思想作為多元中的一家,成為后世的主干文化,但它也不是"獨尊"的。儒家的基本思想理念就是人倫的道德精神,并以順應"天道"的"道家"的自然主義來補充之。人倫精神有其等級秩序("禮")和價值準則("義")的規范和操作原則,但這個基本理念系統中更重要的是"仁"的形而上學。"仁者愛人"成為比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更高的文化精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quot;(《論語·衛靈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同時,這個"仁"的形而上學,在政治上表達了"三代"以來的"宜民宜人"、"敬德保民"的"民本主義"。當然,儒家的仁學,作為中華民族一元文化的核心,是周文化精神的繼承,因而,它也必然繼承了周的人倫精神的宗法等級制度的精神,正是這種宗法等級精神,成為建構中華傳統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幾乎貫穿了中華文明的整個歷史。
仁的思想理念(伴之以宗法制度和道家的自然主義),作為中華文化數千年來的基本傳統,它并不是絕對的唯一傳統。先秦各家的思想在后世都有流傳存在,并在一些時候被分別作為儒家主干思想的補充而與儒家思想關系緊密,以致被儒家思想所吸納。例如在政治層面,儒法互補的情況歷史上就有很多。另外,一些非儒家思想在某一個時期或者階段也可能成為主導思想,但這總是一些短暫而不長久的歷史現象。唯有儒家的仁治成為一種具有內動力的文化模式。
儒家的"仁"的思想,被作為中華民族進行內部個人修養的文化教化的最高價值,被作為人與人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處理相互關系和存在問題的最高準則。也就是說,仁已經轉化為中華民族的根本屬性(規定性),所謂中華文化,就是仁的文化。反過來說,仁就是中華文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歷史上一些朝代為什么被滅掉?就是因為它們違反了中華文化的根本屬性--仁。秦雖然統一了中國的版圖,但是它"仁心不施","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賈誼《過秦論》),"舉措暴作而用刑太極"(《新語·無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可見,在中華民族這塊土地上,以仁為國,方有文明在。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元則(原則)。漢初黃老之治,并非棄儒歸道,而是以道家自然主義的"無為"方式,息擾民之事,廢酷吏刑罰,回歸到仁治的軌道上來。
仁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核心,作為其根本精神,它并不排斥其它文化形式作為它的補充或者激活它的內在豐富資源的方式和手段。也就是說,中華文化的一體模式是動態而不僵化的。只?quot;仁"的本體存在,只要"有利于"仁的本體,只要清醒地判明其它手段、方法均是圍繞著仁的本體的,那么,這些手段、方法都是可用而不必拒絕、計較的。有時為了維護、鞏固和加強"仁",甚至必須啟用一些并非本族群原來就認可的方法、手段。例如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年建元)執政23年后實行文化改革,廢棄華夏袍帶服裝改穿胡人短衣,廢除中原戰車改建騎兵,這并沒有使得趙國"胡化",而加強了國力。趙武靈王很懂得守元變用的靈活性。他認為,"圣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制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參見《史記·趙世家》)
同時,中華文化核心形態的價值理念特點,在古代就已經逐步消減了民族的人種學特征。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或者族群)的含義,超出了狹隘的人種界限,而把民族文化化了。孔子的時代,人們并沒有不同族群必須分割、分隔、分立的價值概念。也沒有族群(種族、氏族)優劣的概念。"夷夏之辨"并不是種族優劣之辨,而是文化先進與否之辨。人生活在什么種族(族群)中,是人不能選擇的,而人持有或進入何種文化,則是人可以選擇的。所以,文化雖然與種族、族群有關,但它們二者并非一回事,在它們之間可能會存在錯位,甚至根本的反差。孔子說?quot;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孔子感嘆中原戰亂,國家破碎,已經不成樣子,是一派文化頹廢景象;而夷狄那里形勢穩定,國家制度健全,不像中原這種沒有文化的樣子!所以,孔子甚至"欲居九夷"。有人認為,這會失去文化而變得"俗陋",孔子則自信地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孔子的自信,是對自己的文化的自信,他相信,如果自己"居九夷",就完全能夠以自己的華夏文化教化夷人(朱熹注《論語》?quot;君子所居則化"),使之"變夷為夏"。夷人的人種并不可能變化,但它們只要有華夏文化,就是華夏人了,種族概念在這里完全被文化概念消解了!進一步看,在《公羊春秋》中,族群是不是華夏,并不是一個固定的人種概念,夷狄與華夏都是可以互變的。這種理論有一個很有趣的表述:"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嚙。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也新夷狄也。"(《左傳·昭公二十三年》)道理是怎樣的呢?何休解釋說?quot;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敗壞,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春秋公羊傳解詁》)王室內亂、君臣上下敗壞,是春秋時期中原的普遍無行,這種行為無異于傳統話語中的夷狄,中原的華夏已經蛻變為新的夷狄了!它們已經喪失了主中原的資格;相反,如果夷狄能夠匡王室而行尊尊之禮,認同華夏文化,視華夏典章制度為己物而實行之,則就是華夏,可以有資格入主中原。所以,華夏和夷狄絕不是人種學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族群或者民族以文化為核心,以文化為轉移,這是中華民族的有特色的民族(族群)觀念。
這種"文化民族"的概念,是當代狹隘的人種學民族主義者不可能理解的。在當今世界上,狹隘民族主義以人種特征為所謂的依據,以"民族獨立"、"民族自決"為招牌,實際上進行分裂人類社會的活動,沸沸揚揚地制造民族不和和沖突。在這個時候,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民族"概念,對于解決民族矛盾,協調民族關系,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
四、一體中的多樣性:"天下大同"與"和而不同"
中華民族的族群(或者民族)觀念的一元多樣性,不但表現在其核心的思想理念化上,而且也表現在其輳幅的開放性上。關于這一點,我們首先應該說的是,中華民族十分重視自身的核心思想理念,因為這是它?quot;元";但對于自己民族理念的輳幅,則是持十分積極的開放性:一種豁達的無界態度。這種態度表現主要為:
其一,堅持"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普遍主義。也就是說,人類的種族,無論多么繁雜,皆因其為人,因而總是被納入儒家"仁愛"的交往原則的框架之中。對文化價值的生存意義的至上性和實質的強調,消解種族差異可能引起的隔閡。正因為此,在中國歷史上,在族群交往(沖突)頻繁、行為差異性的張力十分迫切的南北朝和五代時期,雖然一度造成中原華夏制度的失范,但這種族群沖突和差異張力,造成了暫時的分裂局面,但并沒有導致中國分裂為以人種界定或者以族群為單位的眾多的所謂"民族國家"(這與西方的情況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是:制度失范恰好造成了族群融合的可能性空間,制度失范期恰好就是族群融合期(,而不是族群嚴格界定期)。經過短暫的震蕩之后,"華夏制度"融入了更多的"夷狄"因素,因而具有了嶄新的文化活力,以一種新的文化姿態形成了向自身的"復歸"。而在這一時期參與交往沖突的所有族群,無論是"失敗者"還是"勝利者",最終都被華夏文化所淹沒、所覆蓋,都成為華夏民族(族群)的要素和成員;華夏文化本身也已經更多的包含了夷狄特點,更為廣闊浩蕩,非昔可比。中國歷史上"外族"入主中原的情況不止一次,新的統治族群盡管在人種、語言、文字各方面與中原華夏文化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華夏文化,"演變"成為華夏民族的成員,最突出的就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女真人,它們今日都以中華民族成員而自豪。
中華文化的這種核心一體性的特點,造成了東亞大地上許多族群的文化融合。換句話說,中華民族就是東亞的這些族群以華夏思想理念為共識的一個融合過程,也是它在各個歷史時期融合的結果。每個族群都不是被"吃掉",而是對推進、豐富甚至更新華夏思想理念作出程度不同的積極貢獻的民族成員。"一"是"多"的創造,在"多"不斷創造"一"的過程中,"多"不斷進入"一",成為"一"的要素。因為這種創造是不斷進行的,所以,這個"一"是不會僵死的,是不會停止新陳代謝的,而是動態的,是一種永遠具有活力的人類生命體--一個悠久而不衰老的民族。創造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民族,其他三個都消失了,惟有中華民族永葆生命活力,其原因恐怕也就在這里。
其二,堅持"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族群統一觀。古代中華文化認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史伯答鄭桓公)"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這里所說的"和",指相互的協調一致;"同"則是指絕對的機械的同一。中華民族在處理相互關系的時候,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力圖以原本的華夏文化"吃掉"或者"打敗"其他文化,而是對其采取和平交往的政策,采取吸收和融合的態度。
孔子早就有言在先。他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即要求:在族群交往中,哪怕一些族群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相對比較低,華夏族群也應該尊重他們,以禮待之。在這個指導思想下,才出現了如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典型化的歷史故事。
對于外來民族的文化,華夏族群一般都采取寬容吸納以至積極學習的態度。例如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盛唐,它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它在南北朝胡漢民族沖突與融匯的基礎上,以無所畏懼的胸懷,不設"胡"、"漢"界限,積極吸收胡文化,給華夏民族輸入了新鮮的文化血液,重振了民族精神。實際上,唐宗室本身就是胡漢混雜的血統,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母親都是鮮卑人,所以,李世民只有二分之一的漢族血統,李治只有四分之一的漢族血統。如果按照人種學的分析辦法的話,唐王朝就應該被定義為鮮卑人的政權了。在唐代,可以說漢人(漢民族)胡化得想當厲害。胡人的風尚,胡人的藝術、飲食、服裝和日常生活方式,對漢族影響很大。《貞觀政要》就直截了當地認為:"長安胡化,極盛一時。"(慎所好)元稹的一首詩對此有十分形象地描述。詩中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在那時,中華民族(無論是人種還是文化)的"本原性"就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從唐代以來已經有將近1500年了,在其間的更多變化,當是自不待言的。以回顧這些真實的變化為基礎,不知道我們有誰在今天能夠確證自己還具有"純真"的"漢?quot;血統呢!
當然,中華民族對于外來民族的涵化,其形式除過無界限融合之外,也還有更多的方式。例如中國"回族"的形成,就是信仰伊斯蘭宗教的阿拉伯人、中亞人、西亞人等等西來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過程。在13世紀到14世紀,由于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國版圖廣闊,中國本土的西部邊境對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亞人開放,致使他們有可能大規模進入中國,深入內地,"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卷),在有的城市,他們的數量很巨大,占到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造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見《明史·西域傳》)。遷徙來的阿拉伯、波斯等族群的人們,逐漸學會使用漢語,但以原來語言為基礎自定姓氏,而部分保留了中、西亞文字在傳統場合使用,信仰伊斯蘭教,保有許多中西亞伊斯蘭文化的風俗傳統。他們還對伊斯蘭宗教制度和事務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革,例如,在教理上以會同東西為宗旨創立了凱拉姆體系,并"援儒入回",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教義解釋系統;在教制方面,創立了"教坊"社區制;在節慶方面,稱"古爾邦節"為"忠孝節";在宗教建筑方面,擺脫了阿拉伯式的建筑風格,而采用了中國的樓閣庭院式風格,并置中華文化的傳統符號龍、虎于清真寺門前。七八百年來,就這樣逐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形成了華夏文化與阿拉伯、波斯文化相結合的"中國回族"。可見,中華文化的一元,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的排他性和封閉性是很不一樣的。這種一元,不但包含了族群的融匯而化合,也包含了對一元之中的不同族群根據自己的意愿所進行的在相互模仿、學習中的自我發展的多樣性的承認。
五、結論:幾點現實的學理思考
一,"民族"概念,歷來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由于近代西學風行中國,民族概念也多從西學引經據典,與中國文化歷史很有距離,也與歐美以外的文化歷史很有距離,造成了許多"以面包爐蒸饅頭"的世界現象。這是我們進行學術研究首先遇到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總是"以西論中",難免會生出許多謬誤和悖論。當然,西方學術中也有許多對于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有意義、有用的東西,我們應該學習。但總的來看,檢討中西文化研究的方法論的差異,考察概念的本原意義,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80多年后的一件大事。"民族"概念當屬此列。
二,西方從中世紀后期以來,經過漫長道路,逐步形成民族國家,之后,西方思想理論總是把民族概念政治化,并以這個政治化的概念所形成的各種學說來解釋自己和全世界。自然原有的種族存在,被與近代社會發生的各種問題攪為一團。種族被在進化論的框架中排列,種族被籠統地加上政治標簽。種族、民族與政治國家被盲目地劃上等號,……從16世紀以來,西方開始對全球進行殖民侵略,殖民主義和現代西方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中奉行對弱小種族進行掠奪、剝削和壓迫的政策,導致了弱小民族的反抗,形成了數百年來弱小民族的反抗斗爭,形成了19世紀和20世紀在世界范圍內風起云涌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民族解放"概念的被強調,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三,而對于已經擺脫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而獨立的民族來說,或者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被帝國主義惡意分裂了的民族,無論是各個民族內部還是各個民族之間,都應該以相互尊重、團結、合作為交往的基本宗旨,如果存在分歧,也應該本著為相互尋求理解而積極對話的態度,置異求同,發展共識,從雙方、全民族以至全人類共同的普遍利益為目標,以為大多數人民謀福利的善意態度,機智靈活地處理民族內部或者民族之間的問題,推進統一而反對分裂,推進合作而反對制造障礙。同時,無論是民族之間還是民族內部的各個族群之間,要認清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殘余勢力和其新變種企圖進行分裂而挑撥離間的陰謀,任何形式的所謂"獨立"、"分治"都是與中華民族的"天下大同"的神圣理想背道而馳的。以我有五千年文化教化之泱泱大中華,無論解決民族內部問題還是處理與外部民族的關系問題,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要以科學批判的態度,認真對待當前西方世界某些關于民族問題以及與此有關的某些"人權"理論,進行自己的獨立思考,以我們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歷史經驗為思想基礎,研究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問題。如此,我們不但能夠有效地解決自己民族內部的問題,而且能夠為全球人類解決民族、族群問題,提供有意的啟發。
四,民族、族群概念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生成物的概念。它具有相對穩定的人類學和人種學意義,而并不在原本上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其政治意義是西方近代"民族"概念的狹隘特色。所以,民族或族群概念,其豐富性在于它的歷史和文化性質。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規定性,是它的比較本源的規定性,而其政治意義和政治的規定性則是次生的。
四,民族、族群概念的政治規定性,是民族、族群本身諸多規定性之一問題。它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解決政治問題現實意義重大。但由于民族、族群問題的性質,如上所述,其根本在文化和歷史。所以,民族、族群的政治規定性和政治問題之根在文化和歷史之中。因而,只有抓住文化和歷史,才是抓住了解決民族所有問題(包括政治問題)的根本。
五,對于中國歷史過程中華夏民族的形成和各個時期的各種民族、族群關系的處理的經驗,可以開啟我們的思路,并使我們從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族政治神話的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消除我們對于種族"純潔性"、民族界限等等的機械形而上學的執著。中國人的"文化民族"觀念,以無種族歧視、無族群歧視的人類平等觀,以普遍性的博大胸懷,以積極善意的交往態度,以吸納、好學的靈活原則,以相互尊重、共存的寬容行動,形成了中華民族尚一尚統的文化風格,鑄造了生動而具有極大活力的"大一統"的華夏文化。這是全球人類的寶貴文化財富。這是我們值得在世人面前自豪的。
六,與此相比較,歐洲人雖然認識到了人類不同族群(民族)聯合與團結的重要,但"歐盟"理想的美好與其實際推進的艱難所形成的反差,成為西方社會最為迫切的一件難事。何況,"為統一歐洲尋找靈魂"的呼聲何時才能落實為歐洲思想家有效的文化杰作,時日之長短尚難預料。"一個沒有靈魂的歐洲聯盟"?這是歐洲以至整個西方現實的何等尷尬啊!這也是他們的政治學難題、社會學難題,實際上更是他們的民族學和人類學難題。他們所需要的文化思路,也許恰正是我們五千年積累起來的關于"仁"、關于"和而不同"、關于"一體多樣"等等的寶貴文化財富。
參考書目:(按作者姓名的漢語拼音音序排列)
博厄斯,弗朗茲:人類學與現代生活,劉莎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陳國燦、何德章(主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陳劍安: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陳連開: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
陳琳國、陳群: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甘黎民: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
陳慶德:資源配置與制度變遷:人類學視野中的多民族經濟共生形態,昆明:云南人民出
版社,2001。
陳育寧(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歷史探索:民族史學理論問題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
版社,1994。
戴裔煊:西方民族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5。
費孝通(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7。
甘黎民:四海之內皆兄弟:中華民族大家庭,沈陽:遼海出版社,2001。
顧定國:中國人類學逸史:從馬林諾斯基到莫斯科到,胡鴻保,周燕譯,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郭大烈(主編):民族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哈登:人類學史,廖泗友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9。
韓民青:哲學人類學,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
黃崇岳(編著):中華民族形成的足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
江華(等編著):民族之魂:中華民族文化透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
孔慶榕、李權時(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論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李康平(編著):中華民族精神,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李紹明:民族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李嗣水(等):中華民族精神論,濟南:泰山出版社,1998。
李亦國:人類學與現代社會,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7。
李宗桂(主編):儒家文化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林耀華:民族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第2版(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林卓才、王衛國(主編):中華民族精神與民族凝聚力: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第三次學術討
論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1994。
盧勛、楊保隆(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馬林諾斯基:科學的文化理論,黃劍波等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馬啟成、白振聲(主編):民族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馬戎、周星(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木芹:中華民族歷史整體發展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納日碧力戈(等):人類學理論的新格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彭年:秦漢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榮仕星,徐杰舜主編:人類學本土化在中國,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
阮西湖:人類學研究探索:從"世界民族"學到都市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瑟維斯,埃爾曼·R.:人類學百年爭論:1860~1960,賀志雄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
社,1997。
史密斯,G.埃利奧特:人類史,李申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宋蜀華(主編):民族學與現代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
泰勒:人類學。人及其文化研究,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9。
田曉岫:中華民族發展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王海龍:人類學入門:文化學理論的深層結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12。
伍雄武(主編):中華民族精神新論:各民族精神的融匯與凝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伍雄武: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凝聚新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蕭君和(主編):中華民族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蕭君和(主編):中華民族族體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蕭致治等著:中華民族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0。
肖君和:華魂。第三卷。中華民族大一統,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
徐杰舜(主編):本土化:人類學的大趨勢/.--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
許蘇民: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素質簡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9。
楊昌儒:民族學綱要,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7。
楊群:民族學概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楊文炯: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閾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北京:民族出
版社,2002。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編):中華民族文化海峽兩岸學術討論會文集,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5。
張江(等主編):命運:中華民族的昨天與今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張磊、孔慶榕(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張鑫昌、王文光:中華民族發展簡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7。
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編):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喚,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0。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人類學的趨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鐘年:文化之道:人類學啟示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周星:民族學新論,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3。
周光大:民族學概論,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7。
周建新(主編):民族學概論,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
莊孔韶(主編):人類學通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