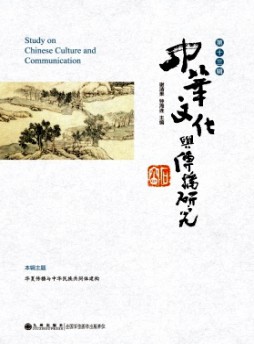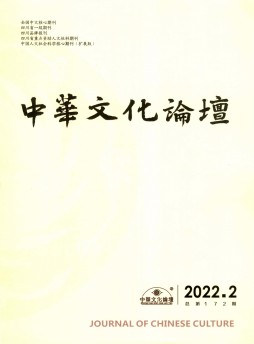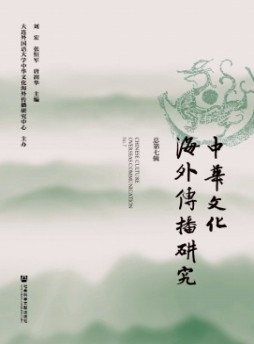中華文化海外分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華文化海外分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境內各民族文化及其與外來文化不斷交流、整合和發展的匯萃。她的中和、兼容匯通等特質,使她能夠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區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氣質向外潛移默化地滲透流傳,既可以融合于其他類型文化之內,又可以和諧地獨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區域之間。中華傳統文化的播遷,在世界文化史上別具一格。中華文化具有較強的涵化力和適應力,自秦漢開始不斷向海外傳播、移植,在東亞、東南亞文明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近代以來這種影響輻及歐美。從文化播遷的角度來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一)中華文化的傳播:“漢字文化圈”;(二)中華文化的移植:華僑文化;(三)中華文化的分異:華族文化。這三個階段遞相嬗變,各具特征。但第一階段說的是在華僑出現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一中華文化的移植:華僑文化16世紀以后,華僑出國經商謀生逐漸增多,華僑聚居區星星點點散布于海外城鎮。負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口,通過自身的遷移與僑居,將中華文化移植異域,形成華僑文化,在東南亞各地及后來在美洲滋生蔓長。西方殖民者開始在東南亞建立其殖民經濟體系,華商的中介、華工的拓荒在其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從而形成華僑出國的外部拉力。福建、廣東沿海,海外貿易素有傳統,不少人出國經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現一些海商武裝集團,以武力為后盾經營中國與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貿易。同時,人口壓力日漸增強,也驅動農民出海謀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動蕩,也驅使一些軍民出洋避難。在三佛齊(今蘇門答臘),有幾個華人海商武裝集團,占地為王,如廣東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數千閩粵軍民,“雄視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齊傳。)。今馬來西亞沙巴的一個小港仍被稱為“林道乾港”,相傳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裝與西方殖民者遭遇敗退留居之處。在爪哇,有廣東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灘之地上建起“百貨充溢”之貿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勝覽》“爪哇國”載:“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余家。”(注:又參見《東西洋考》卷3,下卷。)柬埔寨有籬木洲,也是“華人客寓處”。印尼的巴達維亞、菲律賓的澗內、泰國大城的奶該、緬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華人聚居區,巴達維亞、澗內華人曾達二三萬人。早期華僑聚居區一度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自成一體的社區,華僑文化與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世紀下半葉,明朝遺臣莫天賜開發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視文化的傳承,一時文風蔚然,幾與中土媲美。(注:黃錚:《從〈嘉定通志〉看越南華僑的歷史功績》,載《印度支那研究》1980/12月增刊。)1777—1886年加里曼丹島的蘭芳公司,可以說是中國國家制度的海外嘗試,其首領羅芳伯自號“大唐客長”,重視中華文化教育,遠道聘請中國書生開設講堂,免費教授。但在19世紀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將海外華僑視為莠民、棄民,不時實行海禁,不許華僑返回故鄉。這使華僑出國時斷時續,也使華僑不得不長期寓居異鄉。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不少華僑聚居區,文化的傳承缺乏連續性,中華文化的這些移植點多自然消失。一部分華僑,單身男性(此時絕少有中國女性出國)多與當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成雜交文化。例如,婆羅洲的杜孫人,自稱系華人后裔,初來種植胡椒,招致中國親友,納杜孫婦女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孫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屬裝飾品均同中國,栽植稻谷純粹華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長傅:《中國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鄉)人、緬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軍殘部流亡國外的后裔,與土著長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漢族習俗和信仰。緬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間小廟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廟中的文字全為漢字,直到近代,他們見到來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鄉之情熱心接待。菲律賓的伊戈洛特—華族(Igorrote-Chinese),是明末廣東饒平籍人林鳳所部“海盜”與土著雜居通婚的后裔,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自認為其后裔。菲律賓還有被稱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華僑與土著的混血后裔,現在占總人口的5%,幾乎完全被菲西社會所同化。印尼的土生華人,與新客華僑群體相對,雖已不懂華語,但仍保留若干獨特的中國文化傳統。海峽華人俗稱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紀,在政治上傾向于大英帝國,在種族上認同于華族,在文化與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國,生活習俗則融中、英、巫于一體。19世紀中期以后,華僑華人社會急劇擴大并發生深刻變化。五口通商,西方殖民者的經濟侵略越來越強烈地沖擊著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尤其是在小農經濟體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庭手工業受到致命打擊。廣東、福建首當其沖,大量農民破產。其時正值東南亞殖民經濟體系建立和發展時期,北美亦進入開發高峰,都需要大量勞動力。以契約華工為主要形態的中國移民就在這種內部推力與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大規模的出國潮,奠定了近代華僑社會的基礎。華僑分布日益廣泛,至二戰前后,東南亞各地,如“千島之國”的印尼和菲律賓,幾乎每個島嶼都有華僑居住,絕大多數華僑則聚居于各大城鎮,在城鎮總人口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1937年馬來亞(包括今馬來西亞的半島部分與新加坡)華僑達210余萬,占總人口的41.4%,其中新加坡占76.5%,而在馬來半島的21個重要城鎮中,華僑人數超過居民總數50%的就有17個。曼谷在19世紀和20世紀30年代,華僑人口一直占全部居民的1/2至2/3。1937年,南越重要商業城市堤岸的華僑人口占全部居民的49%,在西貢和柬埔寨的金邊,亦達30%左右。(注:轉引自陳碧笙主編:《南洋華僑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5頁。)珠江三角洲的廣府農民則通過國際港口香港和澳門,遠涉重洋,移徙到遙遠的美洲及檀香山、澳洲。中國移民及其后代在世界各地城鎮聚居,形成自成一體的華僑社會。親帶親,友帶友,由宗親或同鄉牽引出國,連鎖式互相提攜的移民形式造成同鄉同族聚居同一地區的現象。如泰國、柬埔塞以潮州人為主,菲律賓則以漳泉人為主,北美以廣府(珠江三角洲)人為主,檀香山以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占多數。與此相關,華人的職業分布也往往帶有地域性。親友相幫共謀生計下的華僑,其職業分布往往是以方言群為主集聚的,如19世紀舊金山的進出口行業全部被三邑僑商所壟斷韉厙南匆鹿萑床僮菰諤ㄉ較厝聳擲鎩#ㄗⅲ郝罄袂骸洞踴鵲交恕蘭兔攔松緇岱⒄故貳罰愀廴櫚?992年版,第26頁。)中華傳統文化隨著同鄉同族聚居城鎮的分布而移植異邦,并形成獨有的特色。中國傳統社會的同鄉會館、同業商會等民間組織也移植過去。以地緣紐帶維系的同鄉會館、以血緣紐帶維系的同姓宗親會、業緣關系組成的行會與商會,以及各種宗教組織、慈善組織甚至秘密組織,普遍存在于每一處華僑聚居區。這些社團的活動能量和社會作用,遠過于中國本土的同類組織。客居異國,人地生疏,華僑謀生有賴于同鄉同族之間相互提攜,守望相助。華僑面對的通常又是種族歧視的世界,而貧弱的祖國無力保護,華僑唯有抱成一團。作為所在國的外僑組織,在華僑與當地民族尚沒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對獨立的情形下,華僑社團成為內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質的組織,華僑的生老病死都與僑團緊密相關。在新客華僑遠涉重洋初抵異域時,僑團是他們的落腳點和中轉站;僑團負責為之尋找、聯系工作以資謀生。華僑之間出現矛盾由僑領調解和仲裁;華僑子女稍長送入僑團建立的義學和其他華校;病倒了有自己簡陋的醫院;生計無著時有慈善救濟;身死異地,葬入義山,或運回故鄉,如美洲的苦力華工遺骨,僑團組織船只千里迢迢運回故土安葬。在19世紀美國華僑社會中,會館是權力機構,負有保護照顧同鄉的責任。移民初抵,僑團派人接應到會館登記注冊,并暫時安頓下來,等待找尋、安排活計,淘金熱期間還貸款資助鄉親前往礦區。回鄉之前,也要經會館查實已經償清債務。(注: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9、32頁。)僑領則極類似于中國基層社會的鄉紳。在傳統中國,科舉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們社會地位高低的表征,鄉紳是農村社會的無冕領袖。在華僑社會,官品、科舉都與之遙遠,唯有財富成為社會地位的標尺,商人遂成為僑領,他們的作用比傳統社會中的鄉紳更大,在某種程度上兼為華僑自治社區的“父母官”。會館是華僑社會的中樞,嚴格說來,是華僑社會中各地域利益集團的組織,從而使華僑社會成為“幫”派林立的社會,也是華僑社會幫派爭斗的根源。頻繁激烈的內訌爭斗,既是廣東、福建農村宗族之間、村落之間、方言群之間械斗的海外延續,更表明華僑社會自成一個矛盾紛呈的社會,并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土著社會。如果華僑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區,華僑之間沒有利益沖突,就難以發生頻繁的有組織的內部爭斗。華僑華人方言群之間的這種幫派矛盾,盤根錯節,直至今日也沒有完全消失。華僑社會與當地主流社會隔離的相對獨立性,使移植異域的中華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辮,女子纏足,身著“唐裝”(男子穿布紐襟衫和寬頭褲,女子穿布紐斜襟),與土著的差異一目了然。飲食上,中式竹筷與西式刀叉、東南亞土著的手抓迥異,禮俗上的區別更為繁復。關帝、天后、觀音、城隍等神廟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隨著華僑的宗教信仰而“落戶”海外,豐富多彩的民間節日與慶祝活動也在海外展開。在價值觀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脈代續、香火延綿……。華文學校普遍興起,初以私塾和幫立學校等形式存在,講授四書五經,灌輸中國傳統價值觀念。1902年檳榔嶼創辦中華學堂,除講授現代新學外,其辦學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禮、義、廉、節。現代化學校從此逐漸增多,各地華校創辦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為禮義之幫。”(注:《椰蔭館文存》第2卷,第223頁。)華文學校一直處于中國政府教育部的間接控制之下。至二戰前趨于鼎盛,二戰之后更達到高峰。在馬來亞,1938年有華僑學校759所,大部分創辦于二三十年代,學生9.4萬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學生27.6萬人。印尼學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學生42.5萬人。同一時期,泰國有華校426所,越南270所,緬甸250所,菲律賓149所。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華文報刊自19世紀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現。至20世紀上半葉,東南亞、北美等地大量涌現。它們自視為中國報紙之列,報道祖國事件,關心中國政治,宣傳中國文化,它們在維護中國認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維新派與革命派,都以僑報為陣地,大開筆戰,展開激烈的論爭。強烈的中國政治色彩主導了僑報,增強了華僑“中國人”的意識。在移居國,華僑自視為飄零的過客,祖國和故鄉才是他們的終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歸鄉,不能遺骨異地,否則就覺得背棄祖宗廬墓,數典忘祖。他們忍辱負重,胼手胝足,為的是在家鄉建立和擴大家庭基業,期望有朝一日能夠衣錦還鄉。無論自己多么艱苦,他們都要將血汗錢寄回祖國的家庭,贍養父母妻子。經濟條件許可便在家鄉大興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書齋設教,墳墓敬祖”,以實現光前裕后的傳統理想。(注: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第118頁。)優裕者關懷宗族鄉梓,直至在國內舉辦公益事業,賑災濟貧,創立學校,興辦交通與實業。僑匯是華僑與祖國的一條經濟紐帶,據估計,1914年至1937年間,僑匯占中國國際收入的15.7%。(注:見《僑匯研究》,臺北:僑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處,1970,第14—15頁。)戰前廈門地區80%的家庭有賴于僑匯。在強烈的中國傾向驅動下,海外華僑社會與中國政治息息相關。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變了對僑民的態度,逐漸承認華僑為“大清子民”,“宣慰”、優撫、嘉獎,逐漸頻繁。在不同程度上開始保護僑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駐美公使,隨后在舊金山、紐約設立總領事館,在檀香山等地設立領事。1877年在新加坡設立總領事館,開明官員左秉隆、維新人士黃遵憲等出任總領事。他們具有強烈的振興中華責任,在華僑中宣揚對祖國的效忠,傳播中國文化價值觀。并整頓僑團流弊,調解華僑社會內部矛盾,整合華僑社會。此時正值華僑出國的高峰期,新客華僑的大量涌入,華僑與祖國聯系的加強,使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移植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從此華僑社會與中國政治緊密聯系起來,華僑民族意識萌發。20世紀以來,各地都成立了中華總商會,成為華僑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維新運動失敗后,康有為等流亡海外。繼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東南亞華僑社會中掀起更廣泛的活動,保皇派與革命派在海外展開激烈論爭,在華僑中激起強烈的中國人意識。在此之前,華僑社會是一個幫派的分裂社會,華僑活動局限于方言群內部,基本上只有“幫”的認同。論爭使華僑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整體,而不僅僅是閩南、潮州、廣府、客家、海南等狹隘的地域和方言群。辛亥革命在華僑社會的深入展開,激發了華僑的中國認同和愛國主義精神。華僑或捐資捐物,或奔走呼號,開展各種革命活動,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國發動和參加起義,獻身革命。孫中山高度評價“華僑是革命之母”。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民族危機更將廣大華僑推動到一個共同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抗日救國,如火如荼,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壯史詩。華僑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態環境下臻于極盛。中華文化在華僑社會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戰爭時達到頂峰。華僑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個中國世界。有位印尼土生華人的話道出了廣大華僑的心聲:海外華人要依靠祖國才能取得在異鄉的崇高地位,“土生華人必須協助中國,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賢傳:印尼土生華人的政治與民族認同》,載《現階段印尼華族研究》。)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中華文化向海外移植,在當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國為認同取向、以儒家思想為價值體系核心的自成一體的華僑文化。二中華文化的分異:華族文化1950年代中期以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東南亞殖民體系崩潰,獨立的民族國家相繼崛起,對華僑紛紛采取強制的或溫和的同化與融合政策。同時,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隔絕,使華僑華人與祖國的聯系中斷,中華文化的代續與傳承深受影響。國內實行,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并鼓勵華僑加入所在國國籍。華僑逐漸轉變為華人(華族),即由OverseasChinese轉變為EthnicChinese,中華文化在海外發生變異,由華僑文化轉變為華人(華族)文化。這種轉變也是華僑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19世紀的中國移民絕少女性,華僑社會基本上屬于單身社會,因而具有強烈的流動性,僑居心態濃厚。或者華僑與土著結婚混居,衍生為雜交后裔,乃至被完全同化。20世紀初,女性移民逐漸增加,兩性懸殊的情況開始緩和。這使華僑社會漸趨穩定,更重要的是形成純華人血統后代,即“僑生”,他們的價值觀念、經濟利益與新客華僑有所不同,與所在國的關系更趨密切。土生華人,無論是僑生還是混血,隨著他們在華僑華人社會中比例的不斷上升,華僑社會受其影響愈來愈大,并逐漸發生演變。至五六十年代后,逐漸完成了從華僑向華人的轉變進程。目前在東南亞十國中,共有華僑華人2000余萬,其中華僑只有86萬。以美國為例。19世紀美國華裔土生人數少,不足一成,并被視為次等華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華人已占半數。他們作為美籍公民,受美式教育,操英語,受美國意識形態影響較深。這樣,在華僑華人社會里,出現深受美國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影響的社會成分,他們對中國傳統思想日漸生疏。這個群體日益擴大著對華人社會的影響,推動著華僑華人融入主流社會。不過,二戰前認同美國的土生華人,盡管他們幾乎西化,但仍強烈地遭受到美國對少數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們存在著矛盾心理,在美國化與中國化之間彷徨。戰后,種族平等成為美國的國策,排華措施逐漸取消,華人在美國的地位提高,經濟處境改善,接受美國文化較深的土生華人,推動著華人社會朝向同化于美國主流社會方向的發展,疏遠了中國傳統文化。華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國轉變為效忠所在國,從中國僑民變為所在國的一個少數民族。從國家形態上來界定其民族屬性,都是所在國的國民。從人種或血緣關系來界定其民族的自然屬性,華族仍然是龍的傳人;從社會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屬性,華族文化仍具有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或在此基礎上發生變化的文化體系和價值觀念。這兩個因素的存在,構成了華族作為一個民族賴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礎,決定了它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立存在。應該注意的是,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文化范疇,也是一個政治范疇,因此,華族不屬于這一范疇。同時,世界范圍內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華族,每個國家的華族是各自國家內的一個少數民族,各不相同。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觀,在華人文化中已不復存在,因為華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認同于所在國。不僅如此,華僑向華人轉變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華人被主體民族同化融合的過程。華人在作為少數民族的演進過程中,致力于當地社會的整合。華人作為少數民族融于所在國的國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則成為所在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為國家文化的邊緣形態。僑居心態大大減弱,由落葉歸根轉變為落地生根。作為當地一個族群成為華人自覺意識。華人積極爭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對種族歧視。他們主動融入主流社會,加強與友族的交流,自覺參政議政。華僑華人一向遠離所在國政治,現在積極參政成為一大趨勢。在美國,70年代以前只有極個別的華人精英單槍匹馬進入政壇,此后參政成為全美華人的共識,開始采取聯合行動。1987年,美國華人名流發表《政治宣言》,成立華裔政治委員會。馬來西亞則有華人政黨,馬華公會有黨員50多萬,是第二大執政黨,此外還有民政黨、民主行動黨、人民團結黨、華人統一政黨等。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松·阿基諾是閩南許氏華僑的后裔,她競選總統時得到菲籍閩南人的大力支持。這種轉變推動華人自覺探研自身的發展演進史,加強對華僑華人歷史文化的研究,1963年,舊金山成立了“華人僑美歷史學會”。八九十年代此類學會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現。如新加坡的南洋研究會、華裔館,馬來西亞的“華社資料中心”(1996年改為研究所),日本華僑華人研究會,北美20世紀中華史學會,歐洲的歐華學會等。國際性的組織則有“國際客家學會”、“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等。有關華僑華人的學術研討會在各地相繼舉行,并舉辦各種展覽及建立華僑博物館。華文教育方面,華校的數量在二戰后達到高峰。50年代后期開始,東南亞各國政府相繼嚴格限制或禁止華文教育,華校規模、數量和學生數量銳減。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內容和目的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華僑時代的華校,教育的內容與中國本土學校沒有多大區別,主要是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等,其目的是為了灌輸中國價值觀。華人時代的華校,實際上只是一種漢語培訓,旨在培養學生能夠運用和使用漢語進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語言教學。在一些國家,即使這種漢語教學也不允許公開存在。1980年代以后,隨著華語地區經濟的相繼起飛及東南亞華商經濟的發展,華語的商業價值增強,華文教育作為一種功能性語言受到重視,在東南亞各國普遍復興,不過這與1950年代以前的華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語。華僑文學,是中國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稱為“漂泊文學”,反映了華僑在異國的失落心態,寄托著游子對祖國對家鄉的深深眷念。華人文學,則僅含有對血統的認同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華僑華人社團也全面當地化,從僑民組織轉為當地的國民組織,由戰前華僑生命共同體轉變為華人文化活動的組織。華人社團形式多樣,百花競放,學術團體、聯誼會、武術團體、藝術中心、交流基金、中醫中藥團體、職業培訓班……不一而足。傳統社團內增設有婦女組、老年組、青年組。有的社團還發展實業,如馬來西亞有“嘉應控股有限公司”、“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動內容多種多樣,傳統社團拓展服務面,直接服務所在國各族。馬來西亞華族文化節組織者認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華人才能適應時代變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簡單復制中華文化,而是要找尋華人傳統文化的精華,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強各族文化交流,實現“馬來西亞化”。應該指出的是,不管如何變化,華人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是割舍不斷的。中國畢竟是華人祖先的國度,必然存在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類的普遍心理現象。華人文化淵源于中華文化,對根的認同和文化源流關系、親近關系,必然使二者藕斷絲連。慎終追遠,華人不僅在廣東、福建等祖籍地開展聯系,而且涌至其發祥地中原尋根祭祖。在某些地區,華人文化的中華色彩仍然濃厚,在特定的時代,中華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馬華人社會,有華人說,來到這里,就像時光倒流,能夠找到本世紀前期中國社會的某些傳統。筆者耳聞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虛。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廣東義山一百周年紀念晚會”,節目內容雖不乏異國風格,但仍是以華人文化為基調。在美國華人社會,華人盡力融入主流社會,但隔閡與距離仍難以消失,他們因此自嘲為“香蕉人”——不管價值觀念、內心世界如何美國化,外表黃皮膚黑頭發始終改變不了,因此仍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異類,這種狀況使他們不得不回過頭來審視中華文化。世界各地的華族文化,是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融匯其他各種類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國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環境下生成和發展,因而豐富多彩、千姿百態。各國各地華族文化,在大體相同的起點上演進至今,形成異彩紛呈的局面,這取決于不同社會經濟背景、文化氛圍、生存環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發展歷程。滄海桑田,文化變遷的豐富多樣耐人尋味。(注:參見龍登高:《傳承與分異:中華傳統文化海外播遷散議》,載《東南亞研究》1996年第1期。)
擴展閱讀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中華護理學會論文
- 2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 3中華傳統文化論文
- 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論文
- 5中華傳統文化思想
- 6中華醫學論文
- 7中華護理論文
- 8中華教育論文
- 9中華傳統美德演講稿
- 10中華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