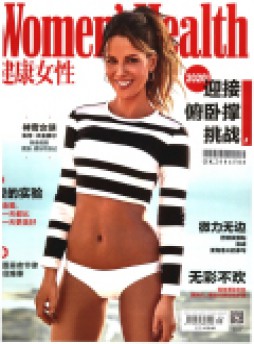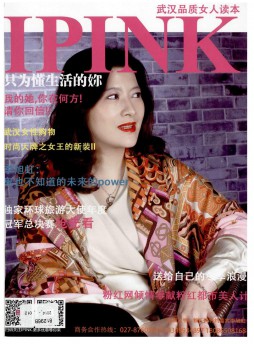女性文學批評態勢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女性文學批評態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新時期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與對西方文化、文學思潮及文學理論、批評方法的引進與借鑒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對于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的理論與文本的翻譯介紹,明顯地影響到中國新時期的女性文學創作與女性文學批評。
新時期的女性文學批評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下,從20世紀80年代對于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翻譯介紹,從孟悅、戴錦華、朱虹、李小江等學者對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嘗試與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推動下,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自娛自樂到眾聲喧嘩,出現了諸多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成果:學術專著就有盛英主編的《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李小江等主編的《性別與中國》、王緋的《女性與閱讀期待》、陳順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康正果的《女權主義與文學》、劉慧英的《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學導引》、陳惠芬的《神話的窺破——當代中國女性寫作研究》、林樹明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林丹婭的《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喬以鋼的《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低吟高歌——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論》、徐坤的《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喬以鋼的《多彩的旋律——中國女性文學主題研究》等。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視角研究中國女性文學的論文也層出不窮,壯大了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聲勢,使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熱潮,也使在西方影響下的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斷走向深入。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取得的成就,其學術價值和意義在于:
一、在對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翻譯與理解中,對于女性主義文學的概念、內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基礎。
二、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視角研究中國20世紀女性文學史,研究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拓展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在擺脫男權意識統治下的文學史寫作傳統中突出了女性文學的新視閾與新風貌。
三、以女性主義的方法觀照與研究中國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尤其注重對新時期女性作家創作的研究,使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在關注女性意識和女性文本中,呈現出一道新的靚麗的風景線。
四、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影響了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的發展,其越來越強盛的聲勢促進了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識的萌動與顯現,使眾多女性文學創作洋溢著濃郁的女性主義文學的色彩。
與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緣于婦女解放運動不同,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并不在意于通過文學批評為爭取女權的政治運動提供思想武器,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其說是對男權意識、男權政治的顛覆,倒不如說是意在對女性意識、女性文學的強調、推崇與展示,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始終基本囿于文學的范疇之內,并未走向文化學、政治學的視閾之中,在“雙性同體”、“軀體寫作”、“性別政治”等話語運用中,卻也常常潛在地、不自覺地陷入了男性的視閾與價值體系的規范之中。
綜觀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成就與現狀,我們也看到其中存在著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缺乏中國的理論與話語。由于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基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的理論、話語、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時甚至可以說全盤照抄。由于東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出發點、立足點等不同,由于東西方文化與女性文學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中,常常有與文學實際的脫節疏離之處,甚至有時成為隔靴搔癢難以貼肉。
二、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缺乏對于女性文學的詩性觀照。由于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是基于對女權政治的關注,對婦女解放的關注,因此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某種視閾看是一種政治學批評、社會學批評,因此大多忽略對于女性文學的詩性觀照。在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影響下,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很少從文學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學,而往往僅從女性意識、性別抗爭、女性命運、婚戀主題等社會學的視角進行研究,而甚少從文體特征、敘述方式、語言風格、象征隱喻等視閾展開批評,以致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疏離了詩性觀照,僅僅成為了一種社會學的批評。
三、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缺乏更為深入的文化觀照與探析。女性文學的創作是深刻地烙著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個民族的女性文學總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質,一定的文化也規范著影響著女性文學的創作與嬗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該關注文化,從文化視閾觀照女性文學,從女性文學視角探析文化的特性與流變,才能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著力于男性文化對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從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傾心于以女權的視角解讀經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進入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別詩學”的研究。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肖爾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權主義詩學》為題。從詩學的視角展開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成為世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新動向,從文學語言、敘述方式、文體類型等視角,研究女性文學特有的表達方式。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該努力建立中國文學批評的“女性詩學”,在接受借鑒西方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基礎上,繼承中國古典文學批評中的詩學傳統,努力建構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努力使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既關注女性的社會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棄對于女性主義文學的文學性的研究;既強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對于詩性的分析與探究,又加強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對于文化的關注。任何一種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獨立的,它與傳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正如肖爾瓦特所說的:“如果說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是婦女運動的一個女兒,那么它的另一對父母則是古老的父權制的文學批評和理論成果。”(肖爾瓦特《新女性主義批評》)我們既不能忘卻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產生于婦女運動的背景,也不能無視古老的父權制的文學批評和理論成果。
談女性文學研究的基礎性建設
喬以鋼
新時期以來,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經過近20年實踐,初步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主要標志是: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對其所進行的研究不再僅限于具體作品的一般性評論,而是已推進到對相關理論體系的探詢和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研究者從多方面審視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現實意義,嘗試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實踐,探索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中的性別范疇得以確立,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各自的方式對女性文學給予了程度不同的關注;一批研究成果以專著或論文的形式出版、發表,初步展現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生機。在此過程中,研究者主要從以下幾個層面開展工作:一是討論界定女性文學的研究對象和基本概念,闡發有關理論的哲學基礎和產生發展的現實依據,探討從事有關研究的理論基點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學中的男性中心主義,揭示其對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對女性創作的壓抑,呈露女性在現實生活和文學話語中的處境;三是追溯女性的文學傳統,探索女性意識、女性經驗在文學創作中的藝術表現。經過諸多學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進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面臨著不少困惑和問題。在此,僅就女性文學研究的基礎性建設談
一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關于研究對象的確立。一個研究領域的確立,總須以特定的研究對象為前提。就女性文學這一范疇所涉及的相關概念(如:婦女文學、女性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女性寫作等)來說,在多年的研究實踐中,一直處于多種理解并存的狀況。對此,現階段很難加以統一的界定,而這畢竟是一個關系到學科建設基礎的問題。筆者認為,該領域研究對象的范圍不宜過窄,而應具有較強的包容性。這實際上意味著,對研究對象自身所具有的豐富性給予充分肯定。盡管就研究者個體來說,完全不妨各自有所專攻,但若從整體研究格局考慮,關于研究對象范圍的認識理當全面涵括女性文學命題的各個方面。這不僅對學術視野和研究空間的拓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關系到對女性文學創作及研究的總體認識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避免對女性文學作過于狹隘的理解,才有可能將研究引向進一步深入。因此,我們不宜輕易將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場、女性視角的創作排斥在外,不可輕視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對女性本體問題的揭示、主動面向廣闊社會生活現實的頗具開放色彩的創作。與此同時,也很有必要加強對男作家創作中所表現的性別觀念、性別意識以及性別形象等方面內涵、特點的分析,從而更為充分地展現出女性主體性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中豐富多采的表現形態。
第二,關于理論資源的清理。在中國女性文學理論探討的過程中,存在著這樣的演變軌跡:20世紀80年代,基于對時代階級議題壓抑性別議題的反撥,“人性”話語體系中的性別差異論壓抑了階級話語;90年代以后,女性主義批評得到發展并產生了一定影響、同時也顯露出種種問題,不少學人開始強調個體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內部階級、種族等方面的差異,并由此出發考察性別與文學的關系。那么,如何“既不放棄歷史唯物論脈絡上的階級批判話語,又能把批判性別歧視制度的女性主義理論納入討論當中”(賀桂梅語),就成為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不僅如此,當我們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脈絡上的階級理論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脈絡上的性別理論、女性寫作理論有效地整合起來為我所用時,或許同樣有必要付出極大努力,去發現、梳理和認識中國歷史上有關婦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遺產及其在文學創作中的體現,從而避免僅以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和創作為參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傳統和文學創作實際。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得到綜合性的女性文學理論的建構以及多樣化的女性文學批評方法的確立。
第三,關于研究方法的多樣與互補。近些年來,女性文學研究的視野、思路和方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豐富與更新。此間西方女性主義觀念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些研究者嘗試以女性視角剖示長期以來男性中心文化對婦女的奴役,揭露傳統女性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鼓勵強化女性意識的“女性寫作”,體現了對壓抑婦女的傳統文化的批判精神。在此過程中,本身即帶有綜合性特點的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無疑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樣,它在具有自己的優勢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無論何時何地都適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狀態下的創作,也并非任何具有女性主義傾向的創作的所有側面都只能用它來加以評說。從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來說,創作主體的內部構成及文學產品的具體內蘊極為豐富復雜,這就決定了研究方法不可簡單化。在具體研究中,從對象的實際以及具體的研究目標出發,完全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操作方法。事實上,每一種視角都有其獨到處,也都有其遮蔽點。當然這之中視角和方法的選擇存在著能否盡可能優化的問題。如果我們著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標,現階段借鑒女性主義視角和批評方法或許確實是一種頗為有效的選擇。但即令如此,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模式而輕易否定運用其它方式方法進行研究在多角度認識研究對象方面的價值。多種方法的綜合、互補、靈活運用,恰恰是女性文學研究賴以贏得良好發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關于研究主體的學術素養。女性文學研究與人類性別問題密切相關,具有十分濃重的文化色彩,帶有一定的跨學科性質,這就對研究主體的知識結構、學術素養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如何在強調女性主體性的同時,自覺避免陷入女性本質論?如何防止在肯定女性視角時,無形中把婦女看成一個與男性二元對立的整體,認同實際上并不存在的“統一的女性經驗”,而忽視了女性內部受制于各種復雜因素所產生的種種差異?在具體的文學研究中,如何處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系、女性批評標準與文學審美標準的關系?如何大力增強研究成果的原創性?如此等等。這些問題的產生,固然由于有關問題自身十分復雜,理論本身尚不能相對自足;同時也與國內的研究實踐終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研究隊伍的學術修養、整體素質亟待提高有關。女性文學研究事業任重而道遠。唯其如此,更須實踐者具有腳踏實地、堅韌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對社會、面對研究對象的同時,同樣勇敢地面對自身的弱點,在扎扎實實的學習、思考和創造中前進、積累。
女性主義批評與男性文化視閾
丁帆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反對以男性文化話語霸權為核心的女性文化與文學研究取得了空前的進展,這種歷史的進步無疑是推動了人類兩性的和諧進程。但是,我們似乎卻要警惕另一種極端給人類社會的兩性關系帶來的巨大陰影!
據報載:今后女人生孩子將不再需要男人了!因為最近澳大利亞科學家發明了一種不使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術——單親無精生殖技術。看來,這一技術的誕生,對于那些女性同性戀者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
隨著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突飛猛進,人類在技術發展過程中愈來愈依賴物質的賜予,逐漸喪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嬰兒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進入生產流水線(據悉:未來嬰兒可能在電腦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為一個“胚胎加工廠”,嬰兒們將在這一條條生產線中誕生),這些人類的奇跡都在一個個發生著,但是,誰又能考慮到這樣一個奇跡呢?——人在充分物質化后,除了人體器官功能的全面蛻化外,人類的情感即將被消滅!人類最崇高的永恒主題——男女之間的愛情——也即將被那個巨大的電腦儲存器所刪除。
當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時候,當女人決定退出這個鮮活的情感世界的時候,那么,這個世界就會變得黯淡無色,成為一個悲慘的世界。如果是這樣,這并不表明女權主義的勝利,恰恰相反,它將預示著女權主義的徹底失敗!
人類在其文明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把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男權主義思想遍布了整個歷史的時間與空間,即便是后現代主義時空下的西方社會,男權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觀,應該說它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集體無意識”植入了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更可悲的是每一個女人都概莫能外,她們心靈的臣服,更加構成了男權文化的擴張性。推翻這個不平等的社會契約,使世界和諧起來,這才是女權主義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她們最后的目的終端。
然而,在反抗男權主義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過程中,有些持女權主義極端理論的人,總是將男人置于自己的對立面,帶著一種先入為主的天然仇恨來片面地詮釋這個世界,難免就有了些自掘墳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權主義的霸氣來雄視這個世界,以滿足一下稱王稱霸的欲望,這是犯了與男權主義政治文化同樣的歷史性錯誤。
最近,一直在讀“人文與社會譯叢”中的一些書籍,其中一位波蘭學者弗•茲納涅茨基在《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一書中說道:“以古老的常識‘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為例。在任何一個社會,女人從屬于男人都是社會秩序之規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真理’是不能懷疑的,因為懷疑它就意味著對兩性之間的所有關系模式提出了疑問。特例只是證實了上述‘真理’,因為任何男人——比方說一位怕老婆的丈夫——從屬于女人的關系,能被認為是不正常的。這一普遍結論容易與強調低層——比方說與貴族形成對比的惡棍——天生低人一等這一觀點共存。因為高級階層的女人簡直根本不與低級階層的男人相比較。社會沒有必要進行這種比較,因為低級階層的男人在社會上從屬于高級階層的男人;如果偶爾由貴族婦女統治惡棍,那么她是作為男人的代表出現的,比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這些對個人之‘優越’或‘下賤’的判斷是評價性的,價值判斷構成了所有常識性知識的核心;因為總有一個價值判斷直接包含于一個行為規則之中。”
實際上,男人作為社會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經被這個社會的知識界所否定,這個“真理”早已成為一個偽問題了,不存在任何假說的可能性了。因此,當今天的女權主義學者如果不是針對社會和那些非學術界的大眾發問與詰難,而是針對學術界的公理(除極個別的男權主義者之外)而責難,似乎是找錯了對象,有點與風車作戰的味道,因為我們在知識界的學術領域內,已經有了一個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新文化價值命題——男權主義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發展的文化價值觀,誰違背了這一學術公理,誰就要受到不僅是外界輿論的壓力,而且又會受到來自內在的良知的譴責。新晨
反之,如果女權主義也把自己的終極目標鎖定在“翻身”后進入壓迫與統治階層,而不是為人類兩性的和諧、平等、交融、互尊、互愛而奮斗的話,那將又是中國文化的一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呂后、武則天之流來作比附,因為這種比附本身就暗含著一種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視閾,以為女權主義的這種矯枉過正是大逆不道的,是應該全民共誅之的,女性應該也必須是受壓迫與奴役的。但是,誰都沒有想到的悖論是,即便如此,呂后、武則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蘭學者所說的那樣:“她是作為男人的代表出現的。”
由此,當我們來重新檢視許許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義作品的時候,就會發現很多可疑的問題。“五四”時期許多優秀的女性主義作家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乃至于到上一世紀的后半葉,完全依附于男權主義的統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合污,成為幫閑與幫兇?
我倒以為,當今的女權主義者們目前所要思考的一個深刻學術與學理的命題是——在女權主義理論甚囂塵上之時,在其激進的理論之下,有多少理性與情感成分是“作為男人的代表出現的”!也就是說,在許許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隱藏在其潛意識中的以男性文化視閾為基本價值判斷的思維悖論——如果這個問題都得不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權主義,恐怕一切都是徒勞的。
君不見,如今一些標榜女權主義和“新新人類”的先鋒派的女作家們,在其大量的描寫興奮點中,是以臣服與取悅于男性文化視閾而興奮不已嗎?!君不見,有許多女權主義的批評家們實際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說一個“女奴”的義理嗎?!真理往往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謬誤,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論急剎車與急轉彎,給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帶來的深刻經驗教訓,應該作為前車之鑒。惟有此,我們的女性主義批評才能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
在這個愈來愈物質化的時代里,女性主義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論疆域。女性只有與男性攜起手來,面對不合理的以男性主義文化為中心的政治統治格局,面對物質主義對人類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與奮斗,才能完整地表現這個時代真正的人性內容。
當這個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時候,這將是一個可怕的世界!這個世界離它毀滅的距離也就愈來愈近了。
誰最愿意看見這悲劇的一幕呢?!
有差異的聲音
——女性主義批評之我見
張凌江
盤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拓與突破性成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崛起與繁榮理當為中國當代學術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義學者(包括認同女性主義理論的男性學者)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或通過對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發掘被宏大敘事遮蔽的女性寫作的歷史軌跡,重建文學史的大廈,從某種角度說是填補著文學史研究的“空白之頁”,使歷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參與的敘事(如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盛英、喬以鋼《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等);或與女性寫作互動共振,分享、感應與品評女性寫作與女性文本獨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動與鮮明的美學取向,闡發對女性文本隱喻與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與親密關系,敞開被遮蔽的女性寫作(如李小江《女性審美意識探索》,徐坤《雙調夜行船》等);或采用現代女性主義立場和術語,重新切入男性書寫的文本,考察其性別表述、書寫女性的視點與態度、兩性關系中的權力關系分布等,辨識隱藏于各種堂皇敘事中話語霸權對于女性的壓迫,從而產生出新的“意義”,執拗地打開了一個歷來被男權文化有意無意折疊的闡釋與批評的扇面(如王家平《魯迅性學思想論略》、劉慧英《90年代文學話語中的欲望對象化》等)。這一系列女性主義批評實績,標志著女性學者性別主體意識的覺醒,及她們頗具特色的思維習慣與不同的責任關注,她們對傳統的男性中心的審美范式與解釋權威的顛覆,從主流意識形態中分離出“自己的聲音”,“有差異的聲音”,在一向是男性中心的學界豎起了女性主義批評的旗幟,顯示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學術創新活力與理論先鋒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義批評風頭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眾多的誤解、詰難和某種優勢話語的抵制,感受著壓抑、邊緣、弱勢狀態的艱辛,它在固若金湯的父權制政治與文化體制內部尋求突圍而又由于過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訐與重圍之中,它在男權話語網絡的雷區地形圖中閃爍其詞、跳越行進而又難免觸雷倒斃。如今審視方興未艾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現狀,評估其得失,并規定其發展趨向似乎為時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義批評反體制、反規約的形象。筆者僅就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文化立場、批判姿態與批評實踐的內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評判),以激發學界探討。
一、拆解與建構。對女性主義批評的責難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權文化這一否定過程中缺乏自覺的建構意識,在拆解、顛覆男權文化主宰的批評話語與審美范式的過程中,無意構建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體系與女性詩學規范。女性主義原則認為任何理論的建構,都不可避免地聯結著男權話語的知識網絡,并轉化為新的權力話語和權力體制,壓制新思想的萌芽。女性主義批評的這一在理論建構的無為姿態,與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關。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徹底性原則主張:“有效的女性主義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義,解構一切事物,拒絕建構任何事物”(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第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寫作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這種強調疏離、變異、流動、另類的游擊戰術,顯示了它的不可界定與不可規范,因而具有了無限的可能性和更廣闊的空間,形成“眾聲喧嘩”、多元并舉的“有差異的聲音”,當然也使它在男權制文化
體制下無所歸屬、無從著陸,成為拒絕建設自己的空中花園的精神孤兒與學術孤島。但問題是如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永遠“在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論體系,就會永遠是支離破碎的斷章碎片,永遠處于他者和邊緣而無法介入主流社會,無法納入歷史視野(也許根本就拒絕被吸附進男權制宏大歷史敘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學界的合法地位,滿足學科建設的需要,永遠承受不可言說、無家可歸的隱痛。
二、滯后的女性主義批評與前衛的女性寫作。縱觀當代文壇,空前活躍的女性寫作顯然超前于女性主義批評,它的前衛與激進姿態,使批評顯得滯后、被動甚至失語。如上世紀末衛慧、棉棉橫空出世,震撼文壇,而女性主義批評卻無法快速、有效、合理地從理論上闡釋、駕馭、主導。回顧當年的評論界,無論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評者,幾乎都是站在被男權觀念整合過的“男性閱讀”立場,對她們的文本施行扭曲與強暴,充斥著泛道德的、因襲的男權的聲音,皆不得要領,各說各話。筆者認為,衛慧們恰是后現論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與流暢淺顯的敘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構主流的“中國寶貝”,她們的文本徹底顛覆了男權權威話語和道統規范的傳統女性形象,他們對理想的破滅、個性的淪落、生活的無意義等等后現代癥侯發出了銳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她們如何迎合市場規則與“男性閱讀”——窺視與意淫的誤讀,那是男性市場規則與閱讀倫理的謬誤,正是由于這種偏離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謬種流傳,如何能歸罪于女性寫作?“男性的閱讀”無法思考女性寫作的反抗內質,不熟悉進而排斥女性文本中與性征有關的女性體驗的象征系統。由此可見,“女性閱讀”立場與“男性閱讀”立場,其政治設定與責任擔當是錯位甚至對立的。女性的肉體、感情、自然和私人領域的特征可能在文化批判與價值重估上更有意義,女性主義批評正是要通過強調對社會、文化的邊緣性和差異性的尊重,將女性體驗合法化,通過對女性文本的疏離性的發掘實現社會批判、與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見,女性主義批評不是具有女性性別的研究者的批評,正如女性寫作不是女性的寫作,而是以鮮明的女性主義意識、觀念、態度和立場從事的批評活動(包括男性學者),與女性寫作一起分享知識禁果,感受文化和歷史的壓抑,參與她們的反抗,主動疏離主流意識形態,促進女性寫作的特殊價值的實現,在批評界發出自己的“有差異的聲音”,而不是將女性寫作整合進男權體制與宏大敘事,祛除其“剩余價值”,在日益機構化、學科化、精英化的過程中,最終成為男權文化的附庸。所謂“有差異的聲音”是指女性主義批評的獨特的或女性的規范,那種對自己的性別更具自我意識,具有女性主義思想,對婦女利益更關心的女性主義批評之聲。同時也體現了男女體驗的差異,其差異導致了男女在思維方式、責任擔當與關注焦點等的不同。女性的主體、女性的自主意識與獨立價值是女性主義批評的基點之一,它與現實政治體制、文化網絡、學術語境形成的緊張的張力關系,正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女性寫作追求的最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