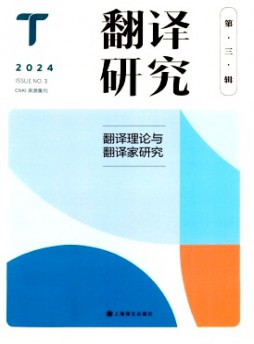翻譯視角轉(zhuǎn)換及文化元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翻譯視角轉(zhuǎn)換及文化元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孫藝風(fēng)先生在04年8月出版了《視角闡釋文化———文學(xué)翻譯與翻譯理論》,作為“翻譯與跨學(xué)科研究系列叢書(shū)”之一。該書(shū)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學(xué)翻譯的本質(zhì)進(jìn)行探索,即探討文學(xué)翻譯的復(fù)雜性。尤其對(duì)文學(xué)翻譯的特質(zhì)及所涉及的關(guān)鍵性理論問(wèn)題提出準(zhǔn)確的描述和展開(kāi)詳細(xì)的討論,系統(tǒng)深入地研究與文學(xué)翻譯相關(guān)的重要理論,在話(huà)語(yǔ)、文本、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等諸方面揭示文學(xué)翻譯的規(guī)律和特質(zhì)。全書(shū)除緒論外,共分十二章,大致可以分為四部分:緒論、翻譯理論(第一至四章)、文學(xué)翻譯(第五至八章)、翻譯中涉及的文化問(wèn)題(第九至十二章)。孫藝風(fēng)先生在書(shū)中多次提到,視角轉(zhuǎn)換的益處和必要性、闡釋在翻譯中的作用、以及在翻譯過(guò)程以及閱讀過(guò)程中文化差異所帶來(lái)的困難以及相應(yīng)的處理策略。可以說(shuō),這三項(xiàng)內(nèi)容貫穿全書(shū)始末,相互交融,構(gòu)成全書(shū)主線(xiàn)。
在緒論中,孫先生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地對(duì)三個(gè)問(wèn)題做出了評(píng)論。一、轉(zhuǎn)換視角可以改變心態(tài)與觀(guān)念,相對(duì)單一的本土文化視角應(yīng)借助它者的視角,從多個(gè)角度看待文化差異,“本土文化若要保持真正的個(gè)性化,必須要呈現(xiàn)多元化”。在翻譯過(guò)程中,譯者應(yīng)盡可能以多元的視角,綜合考慮翻譯中遇到的問(wèn)題。除譯入語(yǔ)文化視角外,還應(yīng)包括源語(yǔ)文化視角,以及源語(yǔ)文本作者的視角。在翻譯理論研究中,“更應(yīng)該站在一個(gè)足夠高遠(yuǎn)的視角,縱觀(guān)、把握翻譯活動(dòng)的全局,并盡可能地將涉及的各種因素納入研究視野之內(nèi)”。二、文學(xué)批評(píng)與闡釋息息相關(guān),既然是文學(xué)翻譯,勢(shì)必要詮釋文本,而在詮釋文本時(shí),由于文學(xué)意義的不確定性更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因此,闡釋不僅僅是意義的翻譯,更有寓意模糊性與延伸的翻譯。三、翻譯的真正挑戰(zhàn)在于文化信息的交流,而不應(yīng)僅僅關(guān)注語(yǔ)言間的差異。許多翻譯問(wèn)題,尤其是爭(zhēng)論不斷的不可譯性問(wèn)題,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而不是語(yǔ)言差異。不同文化需要經(jīng)過(guò)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補(bǔ)充。文化的互文關(guān)系是對(duì)文學(xué)翻譯的最大挑戰(zhàn)。孫先生提到的另外一個(gè)問(wèn)題是翻譯規(guī)范問(wèn)題:譯者在受到翻譯規(guī)范的約束后,如何協(xié)調(diào)原作的語(yǔ)言風(fēng)格和閱讀的審美視角,即是應(yīng)該注重翻譯規(guī)范,還是應(yīng)該強(qiáng)化翻譯的主體性。翻譯理論(第一到四章)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可以是理論的基礎(chǔ),但不等同于理論,理論大于經(jīng)驗(yàn)的總和。就翻譯而言,原作者的意圖和動(dòng)機(jī)以及譯者的意圖和動(dòng)機(jī)難以用經(jīng)驗(yàn)來(lái)解釋清楚。孫先生還提到中國(guó)翻譯界的一個(gè)認(rèn)知誤區(qū),就是希望建立所謂的中國(guó)翻譯學(xué)。翻譯學(xué)沒(méi)有什么國(guó)界可分,建立自我封閉式的所謂中國(guó)翻譯理論體系,只管外譯中,不理中譯外,那該理論的褊狹性就難以否認(rèn)了。關(guān)于翻譯理論術(shù)語(yǔ)的問(wèn)題,孫先生通過(guò)對(duì)“equivalence(對(duì)等)”、“sourcelanguage(源語(yǔ)、原語(yǔ))”等詞各方面的分析,充分說(shuō)明了關(guān)鍵性術(shù)語(yǔ)可能涉及到的巨大復(fù)雜性。對(duì)術(shù)語(yǔ)不加以規(guī)范統(tǒng)一,可能利大于弊。各種語(yǔ)言有各種語(yǔ)言的長(zhǎng)處與特色,語(yǔ)言聯(lián)合文化特色,使得該語(yǔ)言、文化中的讀者及學(xué)者對(duì)某個(gè)詞,包括術(shù)語(yǔ),產(chǎn)生不同于其他語(yǔ)言、文化下的讀者及學(xué)者的理解和細(xì)化,即不同語(yǔ)言文化促使人們看待學(xué)術(shù)術(shù)語(yǔ)時(shí)采用不同的視角,這樣也就改進(jìn)、細(xì)化了術(shù)語(yǔ)。“多元”地翻譯和使用學(xué)術(shù)語(yǔ),可以增加學(xué)術(shù)的活力,有助于學(xué)術(shù)水平的提高。當(dāng)然,充分利用術(shù)語(yǔ)靈活性的同時(shí),還要注意術(shù)語(yǔ)的統(tǒng)一性。譯入語(yǔ)讀者視角勢(shì)必與源語(yǔ)讀者的視角不同,因而產(chǎn)生譯入語(yǔ)讀者與源語(yǔ)讀者之間的距離。距離和視角息息相關(guān),視角的轉(zhuǎn)換可以立即改變距離,從而促使交際的順利進(jìn)行。人為地操縱距離給翻譯提供了調(diào)整、取舍、變通與歸化的空間。翻譯問(wèn)題通常是由于兩種語(yǔ)言之間的客觀(guān)距離造成的,而翻譯問(wèn)題的解決則需要人為的距離方能解決。視角的把握有助于距離的調(diào)整,其后便可以進(jìn)行各類(lèi)變通。符號(hào)之間的有效交際關(guān)系是通過(guò)距離的不斷調(diào)整來(lái)完成的,人為地制造翻譯距離可以縮短客觀(guān)上存在的語(yǔ)言距離。關(guān)于意識(shí)形態(tài),孫先生認(rèn)為譯者意識(shí)形態(tài)的存在會(huì)對(duì)翻譯產(chǎn)生干預(yù),但不應(yīng)夸大意識(shí)形態(tài)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意識(shí)形態(tài)這一文學(xué)作品的審視角度之外,文化視角同樣必不可少,二者關(guān)系互補(bǔ)。文化沖突比意識(shí)形態(tài)沖突更為常見(jiàn)。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之死”不等于源語(yǔ)的意義尤其是文化內(nèi)涵可以隨意棄之不顧或任意宰割處置,因?yàn)榇砥湮幕鷳B(tài)的源語(yǔ)文本有其文化意旨,可以規(guī)約意義。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忠實(shí)反映了對(duì)翻譯活動(dòng)認(rèn)識(shí)的簡(jiǎn)單化。翻譯是一種妥協(xié)的藝術(shù)。妥協(xié)意味著接受某種程度或形式的異質(zhì)。翻譯時(shí),為了完整表達(dá)源語(yǔ)的意義,目標(biāo)語(yǔ)本身必須不斷擴(kuò)展以與源語(yǔ)相匹配,這也會(huì)使目標(biāo)語(yǔ)系統(tǒng)趨于完善。翻譯行為總是試圖消除兩種語(yǔ)言及文化之間所存在的異質(zhì),就算明知不可為,也不斷地設(shè)法制造某種“假象”,讓人真?zhèn)坞y辨。異質(zhì)的消除是徒勞無(wú)功的,文化交流的意義是通過(guò)對(duì)異質(zhì)的了解和借鑒,更好地認(rèn)識(shí)、豐富和發(fā)展自身。
翻譯的前提是準(zhǔn)確無(wú)誤的理解,如果意義得不到準(zhǔn)確的把握,風(fēng)格的傳遞便無(wú)從談起。話(huà)語(yǔ)信息的傳遞不是自動(dòng)的,需要解碼,即釋義。所謂“不可譯性”,除了在翻譯轉(zhuǎn)換時(shí)所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障礙等因素外,還與源語(yǔ)文本的意義不確定性有直接關(guān)系。閱讀的寓意與語(yǔ)境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語(yǔ)境對(duì)于意義的產(chǎn)生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diǎn)在該書(shū)中有進(jìn)一步的論述,突出強(qiáng)調(diào)語(yǔ)境重構(gòu)對(duì)于翻譯的幫助。譯者應(yīng)重視闡釋道德,即不可依自己的好惡對(duì)源語(yǔ)文本任意刪略、發(fā)揮,或者厚此薄彼。文學(xué)語(yǔ)言與文學(xué)翻譯(第五到八章)翻譯文學(xué)作品時(shí),需要注意到語(yǔ)言的特質(zhì),而不能簡(jiǎn)單地翻譯意思或意譯。文學(xué)語(yǔ)言是一種特殊的語(yǔ)言,甚至可以說(shuō),簡(jiǎn)單地傳遞意義的基本信息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為了達(dá)到藝術(shù)目的,作者常常重新建立審美機(jī)制,通過(guò)獨(dú)創(chuàng)更新而生出新的美感。制訂翻譯策略時(shí)更應(yīng)努力克服死板僵硬的翻譯,使譯文保持鮮活態(tài)勢(shì),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時(shí)(可使讀者從中受益,獲得不同的視角),理清交錯(cuò)纏雜的互文和文化資源的關(guān)系,使得翻譯語(yǔ)言同樣具有強(qiáng)大而神秘的內(nèi)驅(qū)力和無(wú)限的可能性。翻譯時(shí),應(yīng)對(duì)原作進(jìn)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審視和挖掘,以更多樣的方法闡釋和復(fù)原,并充分考慮審美文化差異,小心謹(jǐn)慎地進(jìn)行文化移植以及對(duì)意象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與整合。
在文學(xué)作品中,信息是怎么傳達(dá)的,怎樣歪曲的,怎樣傳達(dá)不完整充分的,或者是如何不傳達(dá)、從而造成信息虧損的,都與編碼與再編碼有緊密的關(guān)系。這其中牽涉闡釋學(xué),更包含效果傳遞的問(wèn)題。再編碼時(shí)不應(yīng)只注重形式上的模仿,還有整體效果與風(fēng)格的模仿。譯者在重編碼時(shí)不可仗著已經(jīng)解了原碼就隨心所欲地翻譯,他需要在二者之間不斷調(diào)解。翻譯的目的不只是語(yǔ)義的傳遞,而是整體的意思。意思是一個(gè)很復(fù)雜的綜合體,決不僅限于語(yǔ)義,而是各種關(guān)系的總和。翻譯的對(duì)象除了基本語(yǔ)義外,還有一些相關(guān)成分不容忽略,如語(yǔ)氣、隱喻、效果等。翻譯的挑戰(zhàn)之一是在分析了各種成分的組成和特征之后(這一步驟本身已很難),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目的語(yǔ)里包容與合成這些成分。應(yīng)區(qū)分直譯與硬譯,矛盾的觀(guān)點(diǎn)是二者的區(qū)別標(biāo)準(zhǔn)是檢驗(yàn)譯文讀者看懂和看不懂。但直譯有時(shí)也無(wú)法達(dá)到交際目的,例如隱喻對(duì)象屬“文化特有項(xiàng)”時(shí),譯入語(yǔ)讀者就會(huì)很難領(lǐng)悟。漢語(yǔ)的字或詞在形式上沒(méi)有單、復(fù)數(shù)之分,也無(wú)冠詞確指,所以某些細(xì)微意思難以簡(jiǎn)潔地傳達(dá)出來(lái)。孫先生在這里提到一個(gè)概念,即場(chǎng)景的重構(gòu),隨后接著的是語(yǔ)境的重新構(gòu)筑。在重構(gòu)語(yǔ)境后,譯者的功能有近似于作者的地方;由于沒(méi)有現(xiàn)成的對(duì)應(yīng)值,他需要對(duì)自己的語(yǔ)言負(fù)責(zé),杜絕或減少誤解的機(jī)會(huì),同時(shí)還要設(shè)法最大限度地將原語(yǔ)的信息及包含的引申意義傳遞到譯文里去。(譯者可以避過(guò)分析原文這一步驟,而把這個(gè)過(guò)程留給讀者。)語(yǔ)言是一個(gè)約定俗成的符號(hào)與文化體系。規(guī)范這一概念的提出,實(shí)際上直面了翻譯所涉及的兩種不同語(yǔ)言系統(tǒng)中的差異,尤其是在語(yǔ)言方面的慣例。翻譯成功與否關(guān)鍵在于是否對(duì)譯入語(yǔ)中規(guī)范的存在有清醒的意識(shí)。主體意識(shí)同樣可以發(fā)揮很大的作用,在翻譯時(shí)應(yīng)進(jìn)行適度變通。變通有別于歸化,變通至少兼顧了“充分”與“接受”,變通在二者之間不斷游離,相機(jī)而行,以待良策,而歸化主要著眼于“接受”,甚至可能肆無(wú)忌憚。規(guī)范與主體意識(shí)密切互動(dòng),翻譯透過(guò)主體意識(shí),遵循一定語(yǔ)言的、社會(huì)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規(guī)范,使意義從源文本轉(zhuǎn)入譯入語(yǔ)文本。在文本轉(zhuǎn)換的過(guò)程中,規(guī)范可能造成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翻譯不能無(wú)視其存在。規(guī)范制約翻譯的同時(shí),還驅(qū)動(dòng)翻譯進(jìn)行創(chuàng)新。翻譯中文化問(wèn)題的探討(第九到十二章)不可譯性是翻譯中所涉及兩種語(yǔ)言之間文化不相溶性的一部分。對(duì)不可譯性的論爭(zhēng)實(shí)質(zhì)上源于對(duì)文化的考慮,而不僅是出于對(duì)語(yǔ)言特征的考慮。“文化翻譯”一詞,不僅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新領(lǐng)域,更是指全球社會(huì)日常生活中的一種述行理論,這使全球社會(huì)認(rèn)識(shí)到了文化間交流的重要性。各種各樣的文化都各自有其特性,但是我們必須要穿越翻譯中文化所指(culturalreferences)的莽林。翻譯是在各個(gè)文化之間進(jìn)行斡旋、調(diào)節(jié),因?yàn)槲幕歉鶕?jù)其時(shí)間與地點(diǎn)而得以界定的,所以,文化“他者”得以在翻譯中保存下來(lái)。有些文化之間是沒(méi)有直接對(duì)應(yīng)與對(duì)等關(guān)系的,所以想要盡善盡美地解決“翻譯”問(wèn)題極具挑戰(zhàn)性。一種文化能否發(fā)展,有賴(lài)于從他者文化和傳統(tǒng)中獲取新認(rèn)識(shí)與理解的能力。不能完全準(zhǔn)確地表達(dá)源語(yǔ)的意義,既有歷史的,也有文化的原因。既然所有文本都是在特定文化環(huán)境中生成的,那么,譯文則自然不同于原文。譯者的工作之難就不僅在于語(yǔ)言上的翻譯,更是歷史的與文化的翻譯。對(duì)他者文化的開(kāi)放性,使得譯者可以對(duì)來(lái)自他者文化背景和區(qū)域性傳統(tǒng)的作品進(jìn)行充分翻譯。
代表或體現(xiàn)某個(gè)特定語(yǔ)言系統(tǒng)的、富有鮮明民族特征的文化信息恰是翻譯需要傳達(dá)的內(nèi)容,也是譯入語(yǔ)讀者想要獲悉了解的主要方面。我們需要轉(zhuǎn)換的不只是語(yǔ)言符號(hào),更有文化符號(hào),譬如含有濃縮了大量文化信息的隱喻,其可譯性就是嚴(yán)重的挑戰(zhàn)。與形式和內(nèi)容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是隱喻,尤其是文化成分含量高的所謂文化隱喻(culturalmetaphor)。跨文化翻譯時(shí),不可貪圖便利,走只譯意義的快捷方式,應(yīng)注意在譯入語(yǔ)系統(tǒng)理搜尋對(duì)應(yīng)的隱喻形式,或調(diào)動(dòng)各種修辭手段重構(gòu)、甚至再創(chuàng)隱喻,盡量保留隱喻所具備的想象空間。翻譯研究應(yīng)涉及到文化學(xué)的研究與借鑒,從而超越僅在語(yǔ)言哲學(xué)的層面上討論翻譯差異。文化翻譯是傳遞信息的特殊形式,這種形式不應(yīng)拘泥于狹義的對(duì)應(yīng)值尋找,更應(yīng)設(shè)法在文化的層面進(jìn)行溝通、協(xié)調(diào),在多變形式的選擇中,挑選、改造有關(guān)形式,以獲取最佳值。在某種意義上,信息的傳遞是語(yǔ)境的傳遞,這樣可以使意思有相對(duì)的穩(wěn)定性。只有語(yǔ)言層面上的溝通與文化層面上的溝通相結(jié)合,才能達(dá)到真正意義上的溝通。譯者是文化使者,同時(shí)相對(duì)于原作者又是他者,但似乎難當(dāng)一個(gè)無(wú)意識(shí)的傳聲筒。一方面,譯者希望有自己的話(huà)語(yǔ)空間,不愿做沒(méi)有主體功能的他者,另一方面,有時(shí)他者又顯得十分令人向往甚至著迷,恨不能由他者取代自我(希望傳播外來(lái)文化的渴望)。鑒于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的主要方式脫離不了意識(shí)形態(tài)的影響,自然而然地,翻譯研究也要將意識(shí)形態(tài)納入研究范圍。語(yǔ)言是文化的載體,撥開(kāi)語(yǔ)言的迷霧,不難看到文化信息后面蘊(yùn)藏的意識(shí)形態(tài)意圖。對(duì)于文化的話(huà)語(yǔ)霸權(quán)需要顛覆和消解,而提倡包含差異的多元化文化社會(huì),就是對(duì)付不平等的有效途徑。
翻譯研究不應(yīng)局限于翻譯本身,改變視角從文化層面看待翻譯可以更方便地解決很多原本難以解決的問(wèn)題。本書(shū)談及的內(nèi)容其實(shí)遠(yuǎn)超過(guò)題目所及,孫先生用平實(shí)易懂的語(yǔ)言盡可能清晰地說(shuō)明了翻譯中可能遇到的大多問(wèn)題。如寓意模糊性與延伸的翻譯可以通過(guò)語(yǔ)境重構(gòu)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文化的互文關(guān)系是對(duì)文學(xué)翻譯的最大挑戰(zhàn),單單的直譯可能無(wú)法完成目的,可以聯(lián)合適度的規(guī)劃、意義及變通,而站在原文化視角可以協(xié)助譯者理解原文,進(jìn)而翻譯到位。由于譯入語(yǔ)規(guī)范也會(huì)限制直譯,應(yīng)盡可能繁榮、進(jìn)化譯入語(yǔ)及譯入語(yǔ)文化,使得翻譯與譯入語(yǔ)之間相互促進(jìn)。翻譯既是不同語(yǔ)言的比賽,更是不同文化的比賽,比賽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而是增進(jìn)友誼相互促進(jìn)。別人有別人的身體素質(zhì)(有的是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有的是由于現(xiàn)實(shí)差距形成的),從而形成相應(yīng)的技戰(zhàn)術(shù)。我們雖無(wú)法一味模仿,但可以通過(guò)媒介———翻譯,對(duì)其進(jìn)行充分的分析、認(rèn)識(shí)和了解,進(jìn)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甚至全部吸收。